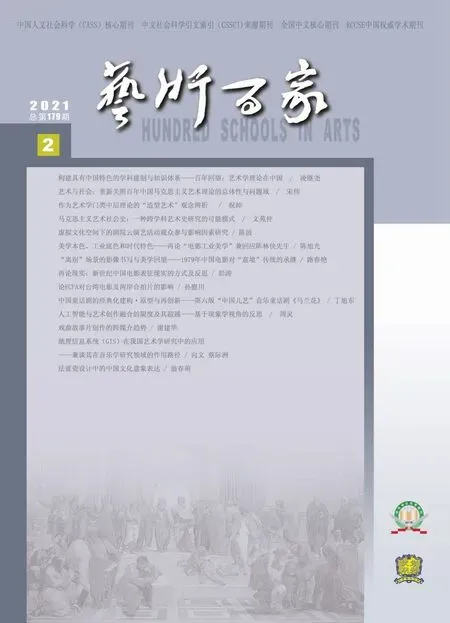中国早期水彩画民族化探究*
——以静物画题材为例
王绍波,亓文平
(青岛大学 美术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一、早期水彩静物画发展的社会语境
水彩静物画一传入中国就作为教学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和创作被重视①,许多早期的水彩教育先驱都致力于对静物画的研究和探索,他们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和天赋,在水彩绘画语言、形式以及审美表达方面不断拓展,为中国水彩的民族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水彩静物画作为水彩画的重要门类不仅有其完整的发展痕迹,而且为今天的水彩静物画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早期水彩静物画的研究来考察水彩民族化的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时间段大致是袁振藻在《中国水彩画史》中所称的“中国水彩成长期”(1900年至1949年)——这是中国水彩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地域范围来讲,我们以当时的水彩传播的重要城市上海为主,旁涉杭州、南京、苏州、广州等城市。早期的水彩静物画家又可以大致分为这样几个部分:一部分是土山湾画馆的培养的水彩画家,他们按照西方的教学体系,并受到海上画派的影响,因此他们水彩画风格带有一定的水墨画特征,以张充仁等为代表;另一部分,来自上海专科学校,基本上按照学院的教学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以王济远等为代表;第三类是以留欧或者留日,尤其是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一批早期画家,以林风眠、倪贻德、王悦之等人为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地方培养的本土画家,以王肇民为代表。
中国早期的水彩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颇为相似,水彩画家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语境中总要面临接受与排斥、融合与改造等问题。因此艺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在阐述日本的对外文化交流时说:“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均形成于同一时期,当艺术在某时期作为一种重要表达方式时,这几大文明总是能够为其艺术找到深厚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是被称为‘世界晚龄期养育的孩子’的日本,缺乏这种历史资源,而这个国家又时时需要为它巨大的创造活力寻找新鲜的思想和形式,开拓其相对狭窄的文化基础。每当这时,日本便似乎完全屈从于外来影响。然而,随之而来必然反应则是,这些外来的影响或被吸收,或被排斥,日本又会重新确认自己的传统并发扬之。”[1]25中国水彩成长期的静物画家也基本延续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模仿和研究西方水彩静物画的技法,再到有意识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探寻自我发展之路,这种艺术观念在上个世纪体现的尤为明显,早期水彩画家张充仁的一段话可以说是这种观念地集中反映,他说:“由于水彩画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相对比较年轻,因而对它的研究同样处于极度稀少的状态,在中国则几乎是一片空白,因而,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我们没有前人已经开拓过的道路可走,因而不得不自己来做开拓者。在没有道路的地方踩出道路,插上路标,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参考。虽然我们知道这样走会有困难,但我们也得大胆地探索一下。”[2]97他的这种思考几乎代表了早期水彩画家的一种集体意识,他们的实践也的确启发了水彩画的后继者。
二、早期水彩静物画的民族化探索
最早水彩静物画风格的融合可以追溯到李叔同、李铁夫等人。1905年李叔同创作的《山茶花》(图1)一直被视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早期水彩画之一,尽管此作品还有很强的花鸟画风格,但是历史意义重大,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画家对于水彩画一种不自觉的认识和探索。正如李叔同在东京所写的文章《水彩画法说略》中所说:“西洋画凡十数种,与吾国旧画法稍近者,唯水彩画。”此语传达两个信息:一是水彩画和水墨有天然的亲近感,这是水彩在中国能被广泛接受的基础;于是,相对于国画“旧法”,留洋者把水彩画作为一种新的绘画方法有意识去学习的。李叔同的《山茶花》对于水彩静物画的发展而言更多是先导和启示意义。较早把西方的水彩静物画呈现给中国大众的是留学英美的李铁夫,他在1933年画的水彩画《瓶菊》(图2)中不仅展示了对于西方静物画的研习,另外还传达了一种东方意象。画家利用中国画地书写方式,充分发挥了水分和色彩交融产生的效果,而形成了类似水墨的韵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探讨水彩民族化的先声。
作为最早进行西画传授的机构,上海的土山湾画馆无论是在教学对象、培养目标还是教学内容上都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作为较早的一批水彩画学习者,他们一方面接受的是法籍教师的绘画理念②,另一方面又在和海上画派的画家广泛接触中,受到中国画的启发。这两种思想在水彩画家张充仁身上表现的十分明显。他少年时期便在土山湾画馆学习绘画基础课,跟徐咏青学习水彩画,掌握了严格的西方绘画的写实技巧。1931年,他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油画高级班学习油画,这期间他的水彩画受到英、法水彩画家地影响。他曾反复临摹法国水彩画家维涅尔作品,尽管后来把工作的重心转向雕塑,但是,水彩画的探索一直没有间断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这些特点体现了画家对于水彩民族化问题的思考, 具体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图1李叔同《山茶花》

图2李铁夫《瓶菊》 38cm×58cm广州美术学院藏
首先,采用传统国画表现的题材,不施底色背景,以突出主题物的形象。张充仁的静物画中经常出现桂鱼、蟹子、白菜、荸荠、石榴等蔬果形象,这些形象选择与西方的静物画略有不同,却常见于传统的蔬果题材的绘画。早在宋代《宣和画谱》对中国画分科时,就专设蔬果一科。后来在艺术市场的特殊审美需求下这种题材一直存在各个时期,沈周、边寿民、扬州八怪以及海派的任伯年、虚谷等都有这方面的作品。如果把边寿民、李鳝以及任伯年画的《江南风味》(图3)和张充仁的静物《双鲫小青菜》(图4)做一下比较,可以看到张充仁既吸收当时英法国家的一些水彩的表现技巧去表现静物的质感,又利用中国画擅长的留白形式突出物象,并且只保留简洁、微妙的静物投影,在平面上保持一种立体感和空间感。袁振藻在《中国水彩画史》中对此评价说:“(他)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突出主题的手法,运用西方的光、色、立体造型的办法,创造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张充仁本人认为这样的画法既能够突出静物、空间感,又能给观众更多的想象力。③他利用投影的精微变化,创造了一种心理上真实,而并非完全凭借物体的质感来表现。 其次,相比较于西方静物画的焦点透视原则,他的水彩静物画采用了俯视的角度,类似水墨画中的散点透视,并注重画面中的平面构成方式。如果把张充仁的《石榴橄榄》分别与当时欧洲的静物画比较,可以看出张充仁放弃了西方静物画中焦点透视的原则,而更注重点线面的经营,以及对于“势”的营造。这样类似俯视的观察角度,就不太会受到近大远小,颜色冷暖等西画绘画规律的影响。再次,他非常注重水彩画的写意性,主张水彩画一气呵成。他认为绘画应该以形写神,尤其是画面的精气神。他的水彩静物画经常会出现写意味很足的线条,既能使画面变得灵动活泼,又增加了画面的感染力。第四,受到国画中博古图题材的影响,选择古物和有寓意的静物。金石学和考古学在清代时十分盛行,也影响花鸟题材的表现,尤其是海上画派,经常会把一些青铜古物作为表现的对象,任伯年、吴昌硕都有此类题材的作品。这种博古画④类似于我们所常说的静物画,从张充仁的水彩静物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题材对他的影响。《紫水盂小白梨》(图5)和任伯年《岁朝清供》(图6)比较,无论是构图还是颜色的选择都有相似之处。这种国画题材一般多受到文人的青睐,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对这样题材的借鉴,也有突出水彩静物画文人性的一面。⑤另外,在一张祝贺女儿婚礼的《玫瑰与如意》中,一瓶鲜艳的玫瑰取意“花好月圆”,两只柿子意喻“事事如意”,这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写意花鸟画常用的表现手法。

图3任伯年《江南风味》169.7cm×92.7cm

图4 张充仁《双鲫小青菜》28cm×38cm

图5张充仁《紫水盂小白梨》 30cm×40cm

图6 任伯年《岁朝清供》
张充仁认为水彩画有独特的色彩特征,并因民族文化的审美心理、艺术家个人审美偏好和特定阶段的审美感情而对相同的色彩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认知与感应。这些想法与中国画对于主观和心理等方面的强调异曲同工。根据民族审美心理去认识水彩画,张充仁并非是孤行者,当时在上海,以及周边城市聚集了一大批的画家投身其中。李咏森(1898-1998)说:“二三十年代常和上海水彩画家王济远、潘恩同、张眉孙、张充仁等一起切磋画技,并钻研英国水彩画家波宁顿、布兰温、弗林特和法国水彩画家维尼尔的作品,吸收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3]43。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除了上海美专,离其不远的苏州美专也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画家李咏森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部分水彩静物作品也采用了张充仁留白的方式,但是他更偏向于对物体质感的表现,因此,画面中的留白有时候是作为一种色彩层次存在,而少了张充仁画面中对于水墨韵味地追求。《莲藕》(图7)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一张作品,尽管大面积留白,但是画面非常写实,尤其是对于莲蓬绿色的运用,使人能够感觉到新折莲蓬的丝丝清新,包括对莲子和藕的细节刻画,都带给人一种逼真的感觉。与之相比,张充仁对静物的刻画则少了这种真实性,而是更加注重色彩之间的交融和对于笔法的强调,这或许与自身所接触书画环境不无关系。而潘思同、张眉孙以及冉熙多是上海美专毕业,有的留校继续任教,有的则任职于出版社等机构。1928年,潘思同与陈秋草、方雪鹄等人在上海成立“白鹅画会研究所”,大约在同一年张眉孙也加入其中,教授水彩画。冉熙也在上海美专担任过水彩教学,或许是因为基础教学的原因,他们的水彩风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有一种朦胧的诗意,而他们的水彩静物画则选择英国水彩写实的表现方法。

图7 李咏森《莲藕》 27cm×38.5cm
然而同是上海美专毕业又留校任教的王济远则选择了另外一种道路。他的水彩静物画(多是花卉,也有蔬果一类)在构图形式上借鉴了中国的工笔画形式,或是单色背景的折枝花卉,有时候会用色彩背景渲染,或是单纯水果特写,但今天看来大多较为拘谨。他采用了传统国画题款加印章的方式,因此从表面上看近似于传统的工笔画,但是与工笔画描摹制作不同的是,他采用了书法挥写的方式,强调线条书法用笔,并利用不同色系的线条交融、并置来表现物体的体积和质感。实际上,王济远在早期接受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其绘画实践也多集中在油画,在他到欧洲和日本考察后,对西方油画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这时候他的绘画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他认为:“画到极致,便没有中西之风,也没必要非得分出个上下高低,谁主谁次。”⑥他在编著的《水彩画》一书中说:“其实水彩画,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画”[4],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那个时代大部分画家所具有的共性。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济远的水彩静物探索,以《双色鸢尾花》(图8)为例,画家的整幅画花枝舒展,舞动的画面透出生机,画面采用花鸟画家恽寿平近似没骨的表现手法,略施色彩变现花卉的体积,中国画的水墨元素和西方绘画的块面变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不留痕迹,与西方静物画相比,又显得更加放松、自由、生机盎然。王济远对水墨画的理解决定了他更加注重对于水的掌握和发挥,在其随笔《武林春水》中说:“水彩来之趣味,在水分之中包含气韵,使心绪与物溶解,而将以自慰自乐。”这种对于绘画主体性地强调,类似于石涛所言:“我写此纸时,心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5]画家有意识地强调情感的能动性以及技法中对于水的发挥⑦。回顾中国百年水彩的时候,范迪安对这种潜意识地探索阐释地更为明确:“中国画家接触水彩之后,面对陌生的画种,很快把民族绘画的感悟力融汇进去,那种水光天色的感觉可以表达的很充分。现在看起来,有些作品拘谨已隔八十年以上,但那种水色迷蒙、氤氲化醇的气息依然非常鲜活,画面依然新鲜、水气淋漓,这说明中国画家在运用水彩的方式上很有自己特殊的美学经验。”[3]

图8 王济远《双色鸢尾花》 27cm×38cm
这种水彩画的主观性表达除了这些借鉴中国绘画的方式的画家,当时还有一批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艺术家。他们对水彩静物画的探索又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制。其中以画家林风眠、常玉、倪贻德、王悦之等为代表,他们把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对形式的强调和中国画对心性和情感的抒发结合起来,进而创作出形式新颖,又有东方韵致的作品。林风眠的静物画,颜色饱满,形式感强,充满情感张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常玉的作品,尽管也带有强烈的构成美感,但是他的静物画表现却是含蓄、内敛,甚至带有一种略有哀伤却空灵的东方禅意。他们从西方现代艺术的视角去寻找与中国水墨画的共通之处,他们思考的是绘画作为本体语言的纯粹性,因此在他们的探索中逐渐模糊各种艺术之间的界限,所以林风眠说:“绘画就是绘画,不分中西。”倪贻德、王悦之都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的成员,当时,这个社团集中了中国最前卫的艺术家庞薰琹、王济远、周多、张弦、丘堤等人。庞薰琹在“决澜社”的宣言中写道:“我们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时代的精神……野兽派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达达派的猛烈的超现实主义的憧憬,二十世纪的艺坛,也应该出现一种心性的气象了。”汲取现代艺术的营养来改造水墨画,塞尚作为“现代艺术之父”自然是那个时代中国画家竞相模仿的对象。假如说倪贻德的水彩《静物画》(图9)带有模仿塞尚的影子,王悦之的静物画对“现代艺术之父”的借鉴已经有了更为强烈的个人特色,他水彩静物画的(图10)线条、明暗、色彩都表达的十分简练概括,偏向一种高级灰的纯净,他的作品注重画面结构安排,整个画面已经有了一种中国水墨画的独特的韵致,可以说他更看重的是塞尚静物的精神。1926年,王悦之曾经应国立西湖艺术院之聘前往杭州担任西画系主任。他的水彩画实践止于1937年,年仅四十三岁的他因病去世。尽管王悦之被某些评论家称之为“中国西画民族化第一人”,但是真正在形式和意蕴方面影响较大的水彩静物画家是王肇民,他的水彩探索也代表着中国早期水

图9倪贻德《静物》 31cm×43cm

图10王悦之《静物》 34cm×42.5cm
彩画从技法、形式融合一直到精神内涵探索到达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并且这些探索早已经在“决澜社”成员的油画实践中初见端倪⑧。
王肇民的静物画(图11)是从民族精神出发,利用黑、红等浓重的带有传统审美趣味的色彩,透过精密的画面经营,从而散发出凝重恢弘的气魄,画面虽小却庄严、宏伟。用评论家迟轲的话说:“他的画可称为东方和西方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出色成果之一,他的水彩画使具象美和抽象美高度统一,把西方艺术的色彩美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笔法融为一体。”[6]52王肇民更多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水彩静物画,具体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他非常强调画格,用清浊来判断作品的好坏,这就把静物画上升到精神品格和民族精神的文人画境界;其次,他强调形神一体,认为写形和写神是不分的,可以划等号,他用古代的画论“神者形也,形者神也,形之于神,不得有异”来阐释水彩画的问题。再次,他注重画面的意趣,强调书法用笔对于水彩画语言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对于传统文化地深入理解,因此他提出民族风格是学来的,是作者立足于现实,在传统的发生、发展、交流、演变的过程中学来的,不学便不了解民族风格,其作品中也不可能有民族风格的出现。

图11王肇民《荷花玉兰》 55cm×39cm
从某程度上说,中国早期水彩画静物画的民族化探索可谓百花齐放,不同的境遇和经历以及学识和天分造就了不同的风格。倪贻德说:“近代艺术的趋向,我们可以说,便是由客观的表面的描写一变而为自我内心的表现的一种趋势……艺术的意义是表现自己的心像,我们心目中所见到的自然,已经有我们自己的人格融化在里面,我们是在对象中看见了自己,所以自然的像不像,不是那么重要的事,重要的是画中的形色,能否适于我们心的需要”。[7]这可以说是对张充仁、林风眠、王肇民等水彩先驱在水彩民族化问题探索上的一种呼应,也可以说艺术家从单纯的视觉刺激开始慢慢转向对于绘画心理以及精神内涵的探讨。
三、结论
从1900年到1949年,中国水彩画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全国各地水彩画会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1900年前后出生的一批水彩画家处在人生的黄金年龄,他们或者经过国内美术院校地训练,或者留洋归国,从慢慢吸收到消化,进而尝试水彩画民族化探索。用评论家对于张充仁的评价:“作品不仅坦示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而且吞吐了西方文化的形、色、意。他努力吸纳古今,兼并东西艺术精髓,积极探索孕育艺术悟性与民族魂魄的‘形归气’”,无疑水彩静物画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天来看这些绘画带有着很强的时代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画家的真诚和各种文化思想碰撞的痕迹。
袁振藻《中国水彩画史》中说:“从中国水彩画发展的历史来看,创造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水彩画,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并在实践中深化认识。一般从使用中国传统绘画的工具、材料和表现方法入手,从中国艺术众多的形式风格中吸收营养。进一步学习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文艺理论中更深层次地去理解我们民族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如精神气质、审美情趣等等方面)。只有从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上去理解民族特色,才能更自如地应用于水彩民族风格创造。”回顾中国水彩画的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林立,他们风格迥异而且个性鲜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新鲜事物传入到中国后的上升繁荣,但是深究其中缘由,我觉得和那个时代画家综合素养的深厚是分不开的。首先,他们大多都有很好的国学素养,大部分水彩画家能够熟练掌握书法或者水墨,这些都决定了他们能够在两种媒介之间进行对比分析,然后进一步理解;其次,他们大多留过学或者直接接受的是外籍画家的传授,因此,他们无论在视野还是技法的掌握上都比较纯粹,毫无保留地去吸收一切营养;最后,他们对于水彩画保持一种热忱。这种热忱代表艺术家对水彩艺术的热爱,也能反映出他们一种无功利的心态。他们的绘画充满了实验性质,这种对水彩静物画的创造态度来源于那个时代对于艺术家所造成的压迫感和奋进意识。或许,把水彩画作为一种重要的实验画种还存在着像学者李超所分析的心理因素,“那就是在西画东渐的文化情境中,中国画家自觉地意识到中国画发展前途的问题,必须寻找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融合之路”[7]。
或许王肇民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对这种分析的呼应:“在我写的《话语拾零》中,对如何体现民族风格则未感祥谈,因为这个问题谈起来难免抽象,而且确实有些不可言传的地方。我的具体的做法有四点:一、多看中国的画论、诗论、文论、乐论、历史,以便在文艺理论上和人物作风上,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观念。二、通过实践,了解中国文艺作品的意境和笔法。三、结合西洋现代的画论和画作和自己的实践的心得,使中国传统的民族风格现代化。四、在作画时,多多依赖现实的启发。总的说来,如此而已。”[3]51我想这些话不仅是他对水彩民族化探索的经验总结,也能够为我们今天水彩画的发展提供指导意义。
①西洋画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期,一般研究者比较注重水彩,倪贻德曾在《水彩画概论中》指出这样几点原因:(一)因为材料价值比较低廉,平常的人,都可以有具备的力量。(二)因为水彩画的趣味,在于和平优秀,很适合我们民族的性格。(三)因为水彩画的性质,和我们的国画很相近,国人因为向来的习惯,所以对水彩画的研究的兴味,也格外的浓厚了。倪贻德《水彩画概论》,光华书局,1927年版。
②土山湾画馆以训练培养宗教画人才为主要目的,教学方法采用工徒制,由法籍传教士教授擦笔画、木炭画、钢笔画、水彩画、油画等技法,用范本摹绘圣像,也临摹欧洲名画出售。
③“在构图上我喜欢用单纯的布排来突出主要物体,必要时才画背景,如画白花或者淡色物体时。一般地尽可能不添背景,我以为背景原为衬托静物及表现空间而有的,如不画背景也能突出静物、显出空间感,那不画还比画好,更见概括集中。因为这样就不限定静物所存在的环境,可让观众凭想象去安排。”郁贤镜主编《张充仁艺术研究系列——绘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④人以“博古图”寓意学问博大,不同凡俗,图案多为:古器物,如古瓶、古铜器、书画、琴棋,再配加一些吉祥图案,居官及文人雅士多以其装饰庭堂或作送礼之用。属于花鸟画科的写意或工笔画种,期间还夹杂界画的一些笔法。博古是杂画的一种,后人将图画在器物上,形成装饰的工艺品,泛称“博古”。如“博古图”加上花卉、果品作为点缀而完成画幅的叫“花博古”。
⑤张充仁曾在《中国画概论》这篇文章中专门谈到“博古画”对其进行了简单的陈述,并评论道尽管和人物、山水、花鸟这些大的门类不能相比,并不是人人都喜爱它,“但却一直存在,近似于西洋画的静物。”郁贤镜主编《张充仁艺术研究系列——文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⑥王济远的这种观点可以代表当时绘画群体的一种共同的态度。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的册子第六页有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题写“西崇实地,中尚虚神。以薪传薪,谁主谁宾。”水印。当早期水彩画艺术家真正全面的接触西方艺术后,他们自然会产生对于民族艺术的自信,在传播和接受西画的过程中,逐渐思考中国水墨画的现代化。
⑦黄宾虹在给傅雷的信中说:“古人善书者必善画,以画之墨法通于书法。观宋元明人法书,……其字迹真伪至易辨。真者用浓墨,下笔时必含水,含水乃润乃活。王铎之书,石涛之画,初落笔似墨渖,甚至笔未下而墨已滴纸上。此谓兴会淋漓,才与工匠描摹不同,有天趣竟是在此。而不知者,视为墨未调和,以为不工。非不能工,不屑工也。”黄宾虹《黄宾虹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
⑧我们可以从“决澜社”画家庞薰琹、丘堤等人的油画静物画创作中,看到他们借鉴民族艺术的特色而开创的新局面,尤其是丘堤,她的静物大气稳重,具有中国水墨画的意蕴,在一种近似禅意的画面中,透露出一种肃穆安宁。由于见到很多西方的绘画这面镜子,因此这些画家更深入关注民族艺术精髓的地方。陈丹青曾对丘堤的画赞赏道:“她(邱堤)的静物画,以我所见,我愿意说是中国第一,好在哪里呢,她同样是画花啊,瓶子啊,衬布啊,她知道避俗,出手非常简静,简单的简,安静的静,她的画不比瓦拉东好,但是比瓦拉东高,第二就是她的素心,这个话不好解释,她的画就有点像清蒸菜啦,她的优雅是她人优雅,那么第三就是见‘'物性’,‘物性’这个又分两层,一个就是她画的那些东西,就是不修饰、不渲染,是物体的恰如其分,也是她对物体的那种敬意和爱意,那么另外一层呢,就是材料的‘物性’,就是颜料和笔,这个邱先生敷色、行笔、起止、收束,她始终不温不火,到处都是浓淡得宜,这很难做到的。……不光是本事,就所谓温良恭俭让入了画,就是邱先生这种境界。”水彩画通常是早期画家民族化探索经常采用的画种,但是由于许多历史原因,留存稀少,但是我们仍然能从其它形式的作品中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