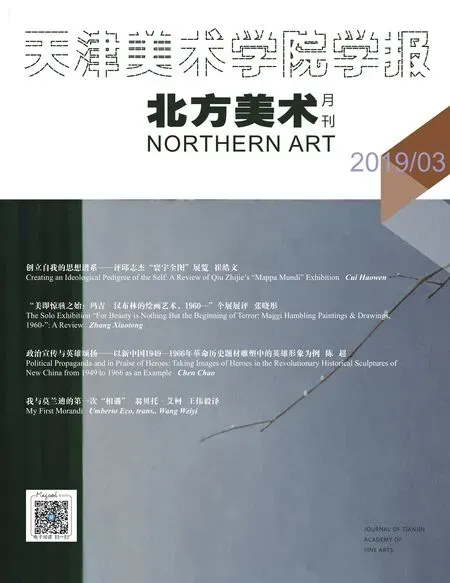“蟾见鳖惊时”
——朱然墓漆画“宫闱宴乐图”
任平山 闵 锐
Ren Pingshan and Min Rui
一
三国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东吴名将朱然去世,安葬在丹阳郡,即今安徽马鞍山市。墓室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今在原址建有公园。尽管发掘时在后室券顶发现了一个早期盗洞,墓中还是出土了各类漆木器约80件,其中不乏异常精美的绘画精品。漆器部分来自蜀地。发掘者在报告开卷写道:“出土的大量漆器,填补了我国汉末至六朝时期漆器工艺史上的空白,为我国美术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
朱然墓考古简报发表在《文物》1986年第3期,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相关情报在汉唐考古和美术史界常被使用。但笔者所见,以这批漆画为专题的研究跟进较缓。后续文章为数不多,且主题局限在绘画风格、工艺赏析和故事介绍方面。笔者过去也感觉这批漆画固然精美,其内容无非是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及墓室壁画的重复。最近重新读图,发现漆画“宫闱宴乐图”不仅可以弥补同类汉画名称缺乏和细节不清的缺陷,其个别图像为汉画所罕见,更填补了中国乐史空白。然此漆画不仅未被汉乐研究者重视,近年专文,如《魏晋南北朝百戏研究》等亦忽略之。故撰此文,以补缺憾。
二
“宫闱宴乐图”是一件木胎漆案的案面装饰,外框纹饰红色为地,内画宫闱黑色为地。宫闱各类人物55个,许多带有榜题。考古简报介绍此图时,直接记录的榜题只有8个。其他榜题,部分转化为描述性的文字,部分未予记录。下文遵照图像,依次介绍观众和表演者。
宴会的享用者及其仆从围绕分布在表演者——亦即画面四周(图1)。

图1 朱然墓漆画“宫闱宴乐图”
图像上层为一排墙体,五窗,窗户中各有一或二人向内窥视。无榜题。画像目的,盖表现人物所处环境。
帷帐左侧一排,绘制了露天而坐的十个人物。男女两两一组,跽坐于席。席前有五副餐具。从左往右,第一组男女身旁榜题写作“皇后”“子本也”;第二组男女榜题写作“平乐侯”“夫人也”;第三组男女榜题写作“夫□”(夫人),另在第三第四组人物中间榜题“都亭侯”,不知所指左侧还是右侧男子;第四组男女旁边榜题“夫人”;第五组男女中间榜题“长沙侯”。长沙侯的食具下方绘有一只大鼎,榜题“鼎也”。
“皇后”右侧有一帐,内坐一男,身形较他人高大。他左拥右抱二女子。依照汉画的惯例,此男子在整个画面中地位最为尊贵。帐外一人拱手站立,当为随时恭候召唤的仆人。
帷帐斜下方,有一人跪地举案,榜题写作“黄门侍”。汉代,黄门侍郎为皇帝近侍。《后汉书·百官志》云:“黄门侍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座。”故可确认帷帐中男子为皇帝。漆画黄门侍郎身后还站立一人,右手反背身后,榜题写作“侍者”。此侍者上方复立一男子,双手持物,身前榜题“直□”。
帷帐正下方,站立四个男子,皆以钺柄立地,左手扶放钺头。人物头上有榜题,写作“虎贲”。他们是皇帝的贴身护卫。《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
画面左下角,距离皇帝帷帐最远的一端,绘制了四个手持弓箭的卫士,榜题写作“羽林郎”。羽林军为皇家禁卫。《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画面中的羽林郎负责宴席的外围防务。
虎贲郎下方(画面右下角),绘制一门。一女子手捧食物正从门下穿过(榜题写作“女直使”),一男子(榜题写作“直门人”)在后拉住她的衣袖。该男子身后,复有榜题,写作“大官下”。该女子身前,复有榜题,写作“大官门”。这两个榜题陈述人物所处位置、环境。在女子前面,两个男子一前一后,抬着盛满食物的担架往里走。担架前面榜题“□使也”,担架上方榜题写作“大官食具”,交代器物所属。
三
接下来介绍舞乐表演的人物及榜题。表演者分为两组,分布在画面中央、左侧及下方。
第一组表演为百戏杂技,共三排。
距离皇帝和皇后最近的表演者,为一男子。他左足点地,右腿后曲,双手抛接五剑。身前榜题“弄剑”(图2)。
弄剑者身后为一男子,右手高举一杆,杆上顶一盘状物。身前榜题“□□人”。榜题前二字破损,第二字右侧可识别出“竟”,故推测榜题之意为顶“镜”人。
顶镜人身后为一女子,宽袍大袖。身前榜题“武女也”,盖舞女之意。
舞女身后为一男子,赤裸上身,双腿弯曲跨步,姿态滑稽。身前榜题“俳奴也”。
第二排表演者,以抛丸表演为首。在弄剑者的下方,有一男子,身体一边旋转,一边双手接抛五个圆球,旁边榜题“弄丸人”。
弄丸人旁边一段距离,一鳖、一蟾相向而视。鳖旁榜题写作“作蟞(鳖)”,鳖蟾中间榜题写作“蟾见蟞(鳖)惊时”(图3)。

图2 弄剑、弄丸、侏儒、寻橦

图3 转镜、舞女、俳优、鳖蟾、连倒
蟾蜍身后有一男子,奔跑中将一大车轮歇在右肘之上。榜题写作“转车轮”。
第三排表演者,其首为一高一矮两位男子(图2)。高者以手触向矮者头顶,矮者以手触向高者大腿。高者头顶榜题“长人”,矮者头顶榜题“□人”,第一字保存较好,但难辨识,似有上下两个丑字重叠。榜题所指,当为与“长人”形成对比的漆画短人侏儒。《广雅·释诂》谓“侏,短也”。
高矮人旁,是一组五人表演的寻橦。一男子手持十字长杆,高高升起,身旁榜题“执□人”。长杆上挂有三人,做出不同的杂技动作。考古简报描述道:“橦上有一转盘,一伎俯卧盘上作‘腹旋’表演,横杆两端的伎人双腿反勾,作‘跟挂’动作。”由于这组表演对空间有特殊的要求,故而在画面上占据两排。杆上人物在画面上位于弄丸人和鳖蟾之间。持杆大汉旁边复有一人抬头向上观望,身前榜题“小儿”。
寻橦表演旁边,为一组四个人在长长的毯子上做出姿态不同的翻滚、倒立。第一人头上二字榜题模糊不清,第二人头上榜题剩一“连”字,或为连倒。第三第四人之间榜题“鴈(雁)行时”(图3)。
连倒表演之后,为一男子,跪地敲鼓。身前榜题“执节人”。
第二组表演者在第一排俳优表演身后。为一组跽坐奏乐的三人小型乐队。其首男子,双槌敲鼓(鼓下有一动物);中间男子吹排箫;末位男子双手合拢嘴边,乐器不明,似吹埙。乐队前方榜题“鼓吹也”。乐队和俳优之间,复有榜题“大乐”。《汉书·刑法志》载:“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
四
宴乐图中的确有许多内容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室壁画中频繁出现。其难得之处在于画家在大部分表演者的旁边精心书写了榜题。对于这些图像的内容和名称,我们可以还原到汉末三国时期的称谓,与此同时,榜题和图像互为锚定,意义较为明确,可以校对学界依据古代文献的片言只语做出的推测。
(1)旋镜,以长杆支顶起旋转的盘状物。类似今日杂技传统曲目“转盘子”。汉画像中有此图像,学界称为“旋盘”[2]。虽然无法根据漆画图像分辨所旋道具,但阅读榜题,可确定为“镜”。
(2)倒立表演者榜题写有“鴈(雁)行时”。“雁行”显然是汉末倒立表演的一个术语,再现了这种表演的复杂性。汉画一般只绘一人。朱然墓宴乐图中呈现不同姿态的四人,据此,“雁行”应由不同姿态的连续翻滚、倒立,组合成具有高度技巧性的表演。
(3)寻橦为汉画所常见。挂杆上人物通常以身形短小、灵活柔软为特征。漆画中,寻橦表演者带有“小儿”榜题。榜题人物身形矮小,且头上明显剃成娃娃髻,可确认为少儿。挂在高杆上的表演者有着同样的发型和身形。事实上,旁边的倒立表演者也是如此。这是少儿作为汉代杂技表演者的身份首次得到确认。
乐史界流行一种说法,以为寻橦由侏儒表演发展而来。《国语·晋语》“侏儒扶卢”,当以侏儒作滑稽状为正解。韦昭注:“扶,缘也;卢,矛戟之柲,缘之以为戏。”王国维以为“此即汉寻橦之戏所由起。而优人于歌舞调戏外,且兼以竞技为事矣”,导致许多学者皆谓都卢寻橦源自春秋时候的“侏儒扶卢”。殊不知“都卢,体轻善缘者也”,而与《国语·晋语》“侏儒不可使援”相矛盾。
(4)寻橦表演者不是侏儒,现在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因为除了表演者的“小儿”榜题,漆画在小儿旁边绘制了真正的侏儒。侏儒、小儿身高相当。但侏儒穿着完全是成人式的,且长有成年人的面孔,胡须隐约可见。和他一起出现的是一高个男子,榜题“长人”。从身材判断,此人身高亦属于反常。长人和侏儒相互比较,双方都很惊讶。二人表演具有一定情节,姿态语言相互动作,明显带有对白。汉李尤《平乐观赋》云“侏儒巨人,戏谑为耦”,应为此景。
(5)漆画中绘制了俳优。由于四川所出“说唱俑”的精彩表现,俳优形象为人熟知。俳优表演以逗笑为目的。陶俑和汉画中,俳优总是形象怪诞,裸体歪歪扭扭,裤子松松垮垮。部分俳优还伸出舌头,做出夸张的表情。
古籍时将俳优、侏儒并举。《荀子·正论》云:“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哉。”汉刘向《列女传·夏桀末喜传》谓昏君夏桀败国时云:“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
又春秋时,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辅助鲁定公,诛杀齐国俳优。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故而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开篇谈道:“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乐记》称优侏儒。颊谷之会,孔子所诛者。《穀梁传》谓之优,而《孔子家语》、何休《公羊解诂》,均谓之侏儒。”[3]后世中国戏曲史编撰多以王国维说为蓝本。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虽有疑虑,也还是予以认可,以为四川出土的俳优俑皆双腿偻曲,歪嘴龇牙,装束与蔡邕《短人赋》相合。[4]赋云:“侏儒短人……形貌有部,名之侏儒。”
朱然墓漆画“宫闱宴乐图”大约是侏儒表演图像在考古发掘中首次确认。俳优出现在同一场合。他身高正常,绝非侏儒。
古籍将俳优侏儒并举,是因为二者表演都以逗笑取乐为目的。《汉书·徐乐传》中,徐乐形容歌舞升平,谓:“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汉书·司马相如传》亦云:“俳优侏儒……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显然,侏儒和俳优都是从事滑稽戏的表演者。但漆画呈现了两种滑稽戏的微妙不同。俳优以滑稽的肢体及语言为表演元素,侏儒则未必。漆画中,侏儒的脸并无丑化。对于那些不被同情心折磨的观众,侏儒的滑稽来自正常行为和不正常身体的冲突。
因此,侏儒固然可以表演俳优戏(《史记·滑稽列传》“优旃者,秦倡侏儒”自言“我虽短也、幸休居”),但俳优多半不是侏儒。此外,漆画俳优榜题“俳奴也”,暗示此俳优从属于贵族而非市场。
(6)鳖和蟾蜍,位于杂耍表演者,亦即整个画面的中心。何以在人群中间出现体型巨大的动物?
蟾蜍在汉画中一般和月亮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又或者与兔、九尾狐、三足乌等一起出现在西王母左近。在神话体系中,蟾鳖同时出现的场面不如前者普遍。山东平阴县孟庄画像石中可见一例。[5]
两栖世界的邻居在表演的人群中邂逅。“蟾蜍与龟”在东汉张衡著名的诗歌《西京赋》中亦并举。与同诗前段谈及昆仑灵沼的“鼋鼍巨鳖”不同,“蟾蜍与龟”出现在诗歌后段“临迥望之广场……总会仙倡……”中,盖描绘广场上种种妙戏歌曲。图像与诗歌对读,可知漆画中的鳖和蟾蜍,其实和旁边杂技俳优一样,属于表演的一个部分。鳖和蟾由人装扮,即戏剧史所谓“象人之戏”。
据《汉书·礼乐志》,汉哀帝性不好音,即位后下诏,罢乐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开列了一份下岗乐人名单,涉及“常从象人四人”“秦倡象人员三人”。后人对于象人有两种解释。三国时孟康注曰:“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同时期韦昭指出象人为“著假面者也”。唐代颜师古似乎认为二注存在矛盾,同意孟康的解释。如是,则漆画中的鳖和蟾蜍,动物装扮非常全面,应也支持孟康。
在为古代戏剧分类时,乐史学界对象人戏的解释较模糊,主要因为在演出形式乃至角色方面,象人戏和傩戏都类似,甚至重叠。象人戏可能包含傩戏,以及由傩戏分化出的其他表演。傩戏带有娱乐性,但主旨是祭祀。象人戏则可能摄入了源自傩戏而又独立于祭祀之外的表演。因此,《平乐观赋》云“龟螭蟾蜍,挈琴鼓缶”,而将之与侏儒表演并举。
朱然墓漆画中,鳖和蟾的动作都是拟人化的,表演者并非纯粹扮演一种动物,更多是以动物来扮演人。榜题“蟾见鳖惊时”将表演的主旨锚定在戏剧性情感,而非傩戏主题——人和神话世界的关系上。为了突出这一特征,画家生动刻画了鳖手足无措、蟾目瞪口呆的惊讶表情,让人忍俊不禁。
朱然墓出土的两件圆漆盘底端写有“蜀郡作牢”及“蜀郡造作牢”字样。“宫闱宴乐图”漆案是否由蜀郡画工绘制,目前尚无定论。不过四川地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中,拟人化的蟾常常在西王母座前以一种手舞足蹈的形象出现。四川省博物院所藏三块,分别出自成都新都区青白乡、成都新都区新农乡、什邡市蒐集。[6]此类图像的左右下方,分别表现为向西王母复命的使臣和或坐或行的男女。蒐集画像砖(图4)男女肩上飘羽,学界辨识为仙人。笔者认为,此二仙人即是墓主夫妇瑶池赴会,观看歌舞之景。西王母世界蟾蜍带有滑稽感的歌舞,与朱然墓“宫闱宴乐图”漆案中的“蟾见鳖惊”分享了汉人对于长乐未央的生活想象。

图4 什邡蒐集西王母画像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