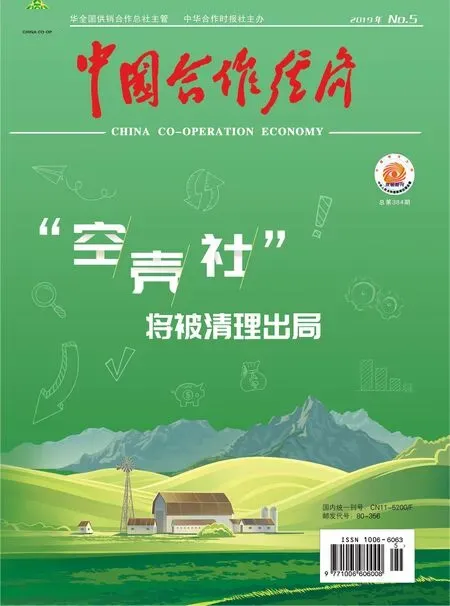对“空壳社”清理中“规范办社”的认识
马彦丽 何苏娇

与纯粹的“空壳社”相比,更重要的是促进合作社的规范发展。现在,造成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不规范现象是多重原因造成的,非常复杂,可能还需要大量的研究,以逐步形成共识,加以改进。本文仅提出判断合作社是否规范的标准和常见的掩饰不规范的做法,希望引起注意,助力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3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提出清理整顿六类合作社,这一行动回应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实践中人们对合作社发展质量问题的关切,可谓恰逢其时。
清理整顿“空壳社”十分必要
截至2018年9月底,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量达到213.8 万家,入社农户突破1 亿户,约占承包农户总量的48.5%。然而,合作社数量的激增一直伴随着学界对合作社质量的质疑。关于“空壳社”的占比,有“三个三分之一,四六开(倒)、三七开、二八开”等不同说法。苑鹏研究员认为,“空壳社”的存在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形象及政府的公信力受损。事实上,除了合作社形象和政府公信力受损,不规范的合作社充斥业内,还会挤占运行规范的合作社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政府通过多渠道的优惠政策支持合作社发展的背景下,错误的示范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整体的生态恶化,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有学者将合作社类比投资者所有的企业,认为既然从无清理空壳企业之说,也没有必要清理“空壳合作社”。但实际上合作社和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投资者所有的企业不享受合作社特殊的税收优惠。如美国的合作社可以享受单一税收,中国在2008年发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其次,合作社作为弱者的联合体还享有多种政府扶持资金。这里并不是说投资者所有的企业不享受政府补贴,政府补贴有多元目标,例如技术研发、环保、产业升级、出口补贴、国企补贴等,但是合作社受财政扶持的主要理由是在此之外的。由于合作社被认为是弱者的联合体,完成了本应由政府担负的某些功能,如促进农业发展、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具有益贫性等。因此,扶持是有条件的,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就应该正本清源。
相比“空壳社”更需重视合作社的“异化”问题
根据《方案》,要清理整顿的合作社包括六类,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二和第三种情况(无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不善停止运行)的特征是无生产、不运行,是真正意义上的“空壳社”;第四条到第六条涉及违规和违法活动,包括涉嫌以合作社名义骗取套取国家财政奖补和项目扶持资金;群众举报的违法违规线索;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如变相高息揽储、高利放贷和冒用银行名义运营等,无论是否空壳社均应治理,不单是“空壳社”的问题;而第一条“无农民成员实际参与”,应该是强调合作社的不规范问题,农民未参与、被参与或参与极少。虽然有“度“的不同,但共同的特征是合作社由大股东控制,对合作社表现出茫然和漠然。
相比“空壳社”,异化的合作社的示范效应更加糟糕。这一类本来不是合作社,但是将自己包装成合作社以获取更多的优惠政策。一个组织往往同时拥有几个牌子,如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合作社等,以方便随时站队,争取国家的优惠政策。“大股东控股普遍,而普通社员受益不多”说的正是这类合作社。从后果看,不但压制了真正的合作社的发展空间,而且对政府扶持政策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例如,由于此类合作社的益贫性很弱,很难保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三个允许”的正当性。此外,这类合作社本身也存在较大的隐患,其必须以合作社的面目来包装自己,而后又在所谓一系列的规范政策下承担某些政策风险和财务风险。例如,一些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为了突出合作社的固定资本、流动资产规模,把公司的资产记入合作社,为了所谓的规范,把本来挂名的合作社社员的账户要做“实”,假如相关主体主张权利,会非常尴尬。
将“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作为合作社是否规范的底线
判断一个组织是否为合作社,应该基于“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这一底线。所谓“传统”(或经典)的合作社虽然越来越少,但并非不存在,这里的重点是如何认定什么是“传统的”的合作社。如果照搬“罗虚代尔”原则或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原则,“传统的”合作社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恐怕没人会这样想。国际上合作社判定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作为一种章程自治的组织,实践中很难找到两个制度一模一样的合作社,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的苛责更无必要。但从根本上看,合作社的本质是社员所有、社员控制和社员受益,与此相适应,社员的经济参与(出资)、民主控制和按惠顾额返还盈余是合作社的核心原则,符合上述原则就是合作社。要执行上述原则,前提是“所有者和惠顾者同一”。虽然近几十年来西方出现了比例合作社、新一代合作社等新的合作社类型,一些合作社在发展中引入外部资本,实行了封闭的社员资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人一票”,也不再是全部按惠顾额返还盈余,但合作社的底线没有变,只有所有者就是使用合作社的这些人,才能保障合作社的本质。

常见的掩饰合作社不规范的几个做法
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如何一边“异化”又一边发展的呢?在合作社自我宣传以及一些官方的文件中,经常看到“民主管理好、经济实力较强、服务成效明显、产品质量安全”云云,与学者们对合作社异化程度的评价对照,似乎大家描述的不是同一个对象。原因在于为了满足法律要求以期获得相应的政府扶持,合作社往往用似是而非的文字包装自己,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一些概念。调研发现,合作社常用以下手段和表述方法来掩盖自身的表里不一。
第一,合作社社员资格边界模糊。潘劲研究员曾经提到,中国的合作社往往釆用双重标准:在寻求政府资助、争取项目以及应付各种考核时,合作社会尽可能扩展自己的成员边界,以获得“带动农户数”的最高评分,但凡与其交易的农户都成了合作社成员;而在涉及成员权益方面,例如在分享盈余以及量化政府补助时,合作社又尽可能缩小其成员边界,往往以持股成员或核心成员甚至少数发起人为基数,以减少利益外溢。在社员边界模糊的背后是社员的虚假参与问题。笔者在对一系列蔬菜合作社的调研中发现,相当比例的农户并不知道(或不认为)自己是合作社的社员。按政策需求确定社员的数目还体现在示范社的评比中。由于农业部牵头发布的《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中将国家级示范社的社员数设定为最少100个,因此我们看到的许多有志于示范社评比的合作社的社员数都刚好在100个以上,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第二,用“N 个统一”模糊社员参与不够的现实。合作社通常宣称自己提供多项服务,实现所谓的“N个统一”,如统一供种、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市场销售、统一品牌、统一加工等,实现了为农户服务的目标。实际上,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合作社的服务功能主要集中在浅层的信息服务和偶尔的技术培训,购买、销售的统一程度还很低,社员并不特别依赖合作社的销售渠道,也没有特别的忠诚度。由于中国的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还不健全,所谓的统一生产标准在很多合作社还停留在字面上。的确,有很多合作社都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品牌,甚至有绿色产品、无公害产品的认证,问题是大多数品牌知名度低,难以维护,很难带来产品溢价,与合作社的社员参与程度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模糊“二次返利”的概念。“二次返利”(或惠顾返还)体现着合作社的质性底线。惠顾返还体现了对弱小成员利益的保护,鼓励成员关注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是保护成员经济利益的制度基础,偏离惠顾返还原则会使合作社公司化。然而,实践中一些合作社将优惠的生产资料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以优惠价格提供的技术和服务、地租、雇工工资等与二次返利混淆,提出合作社实行保底分红、一次让利与二次返利相结合等提法,但实际上有意无意模糊了二次返利的本质,包装合作社已经异化的事实。
在合作社经营中,地租、雇工工资显而易见属于成本,无需多论。所谓的“保底分红”则是迎合了意识形态中保障农民收入的需求,但实际上,一个小小的合作社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面前是无力保底的。农户如果不承担风险,而又要求分红也不合逻辑。在实践中,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常常是随行就市,同时用似有若无的微小分红迎合政策的需求,营造为社员服务的幻象。
所谓“一次让利”也存在理论上的根本缺陷以及实践中不能落实的双重问题。实践中,由于普遍存在的成员边界模糊问题,“搭便车”会使所谓的“一次让利”难以实现。这里可以根据对社员产品的质量要求分两种情况:假定合作社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没有特别质量要求的产品(例如要达到无公害或有机标准),会引致社员及非社员的大量交售,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没有必要;假定产品有特殊要求,所谓的一次返利可以看做对特殊质量要求的溢价,其本质上还是市场交易行为。任大鹏、于欣慧(2015)提到,“一次让利”就像是一块面纱,使弱小成员关注了眼前利益,却遮蔽了他们本该得到的更多合作社后续经营的利益。
第四,混淆领办企业、合作社和社员的资产和收入。合作社的资产和收入归属不清。一些由农业企业领办的合作社将企业的资产与合作社的资产混淆,声称有上千万元、上亿元的固定资产,但实际上真正属于合作社的资产非常有限。一些合作社将社员自己的固定资产算作合作社的资产,例如某蔬菜合作社,在计算合作社的固定资产时,将社员的蔬菜大棚计算在内。一些合作社夸大其注册资金或股金,一些合作社将社员拥有的生产设施(例如果树、鱼塘、土地、蔬菜大棚等)作价入股。但是,所有的参与者心知肚明,这些资产不能对合作社的债务负责,也不作为盈余分配的依据,没有现实意义。在销售收入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些合作社将领办企业的销售收入以及社员自身的销售收入与合作社的销售收入混为一谈,夸大了合作社的经营业绩。
混淆领办企业、合作社和社员的资产和收入与模糊社员资格的边界目的是一样的:通过扩大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来迎合政府的规模偏好,在真正涉及利益和资产所有权确认的时候再采用另外一套计算标准。其负面效果是牺牲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的规范性,将其置于灰色地带。
第五,用难以证实的数据夸大合作社的服务成效。在合作社服务成效的宣传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严谨,用难以证实的数据夸大合作社的服务成效。例如一些合作社宣称实行统一购买和统一销售,推行统一的生产标准,但与实际调研的结果大相径庭。在合作社的情况介绍中,常常可以看到合作社实际带动多少农户,并使社员增收多少。但实际上,除非进行针对社员的详尽调研,否则上述数据无据可考。廖小静等(2016)基于广泛调研的研究发现,合作社对普通成员生产和收入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而由于成员异质性,核心成员受益程度普遍高于其他角色的农户,更是证实了上述论断。
概括起来,与纯粹的“空壳社”相比,更重要的是促进合作社的规范发展。本文仅提出判断合作社是否规范的标准和常见的掩饰不规范的做法,但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不规范现象是多重原因造成的,非常复杂,可能还需要大量的研究,以逐步形成共识,加以改进。希望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