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时代“分享艰难”
吕东亮

陈宏伟的小说《台风过境》,讲述的是扶贫攻坚和移民拆迁的故事,都是当下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也自然地携带了敏感性。题材敏感,讲述的难度就大,作者陈宏伟迎难而上,将故事讲得如此精彩,如此丰富,如此有分寸感,真是难能可贵。
小说中的区扶贫办主任郁洋是党的基层干部的代表,虽然身上没有什么先进典型模式化的光辉,但推进工作能力强,解决问题办法多,其干练品格和担当精神无疑是值得称道的。郁洋一方面要面对主管领导的严格要求、上级督导组的严苛检查,一方面还要应对相当棘手的广大群众的复杂诉求,既要讲法讲理讲规矩,又要顺乎人情、承受不公、善于忍耐、左右逢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小说的描写极为到位,尤其是对于郁洋处于上级领导和巡视组夹缝中的悲苦难言的心态、面对拆迁对象马忠良时的收放自如状态的描写,是颇为传神的。区政府里和他一样不容易的,还有乡长、村长、驻村第一书记,还有区委书记和区长,小说中都做了精彩的点染式描写,笔墨不多,却也都意味深长。小说中的区长虽然相对于郁洋等人来说高高在上,却也承受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以及升迁的烦恼,还有无处倾吐的牢骚。对此,小说描写道:“王区长忽然嗓门一高,‘你们都向我解释清楚了,每个人都择得很清,可是想过没有,我能拿着你们说的这套词儿,去跟上面领导解释吗?我可以吗?你们告诉我!最后几句问话简直是吼叫出来的,室内的空气仿佛都在震颤,所有人都噤声不语,区直单位头头脸上的笑意也消退了,甚至悄悄低下头,躲避着王区长锐利的眼神。”
联想到小说之前对于区长仕途升迁不顺而在大会上多次失态责斥干部的描写,我们不难理解这位区长内心的委屈和怨愤。比较容易被读者当成郁洋对立面解读的,是检查组的胡组长和钉子户马忠良。胡建华组长看起来盛气凌人、动辄大怒,似乎有些主观主义,但其敏感过度的作派,何尝不是之前检查组屡被糊弄的反映呢?其粗暴武断的结论又何尝不是嫉恶如仇的一种别样体现呢?关于扶贫中的数据填报问题,小说有意安排胡组长讲了一番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你这个在农民家的墙壁上钉扶贫笔记本的办法不错,像我们建立扶贫档卡一样,这是一种形式,看上去并不代表内容。有一些干部诟病当前的扶贫工作,说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说什么纸上扶贫。说的对不对?我认为对。但他们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一叶障目,盲人摸象,没能领会事物的实质和内涵,自负无知,可悲可叹。我们要求扶贫档卡必须逐户校准,做到零差错,看上去是形式,但要知道形式决定内容。形式不真实,内容必然虚假。如果扶贫档卡不清,必然责任不清,责任不清,帮扶措施必然也是一盘糊涂账。形式工作落实不到位,就是懒政怠政,为官不为!”这一番讲述是有见地的,明显超出了社会上对于扶贫表格填报的一般认识,也显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小说还写了胡组长进村调查时从自己口袋拿出了500元钱给贫困户,令郁洋和乡村干部们感慨唏嘘。作者这一笔补得实在是好,没有这一笔,胡组长就简单化了,生活的复杂性被大大简化了,叙述的分寸感也受到损害。
马忠良也是如此,他不是一般小说中那种类型化的蛮不讲理、唯利是图的无赖刁民,尽管诉求不够合理,但确实存在着利益不被尊重、付出不被理解的问题,有着为他人所难以认同的悲苦。马忠良的处境其实折射了我们当下盘根错节的利益状况。传统习俗与现代法权的矛盾,个人付出与集体权益之间的矛盾,在既往的漫长日子里虽然长期隐没,却在拆迁赔付中集中呈现了出来,这是哪一个高明的法官都难以厘清的官司。一个村庄的拆迁转型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转型就更是如此,人们面对这些不堪其扰的问题,真是处处艰难。虽说艰难,但马忠良还是不甘受欺,内心中积蓄了越来越强烈、令人心惊的反抗力量。他在暴风雨所摧毁的废墟中重建蛇王庙的壮举是颇为感染人的,小说写了郁洋的感慨:“老马是个牛人。”牛人是不简单的,他的对立面也就不簡单了。小说结尾写了郁洋和马忠良的惺惺相惜,借蛇王庙这一“孤独、异类的城堡”来隐喻郁洋和马忠良孤独的、郁愤的内心,反映出复杂生活尤其是交错的利益格局对当下世人灵魂的雕刻和塑造,显现出了作者对时代之典型心灵的关怀,对于小说的精神品质是一种明显的提升。
《台风过境》关注当下火热生活,敢于直面现实的困顿,在精神向度上又契合主旋律,令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这股冲击波有着为人所瞩目的意识形态关怀,那就是借用刘醒龙经典中篇小说《分享艰难》而来的“分享艰难”。《台风过境》如同题目所示,也如同小说描写的故事一样,是具有冲击力的。小说的精神也体现出“分享艰难”的时代认知——小说中的区长、郭副书记、乡长、驻村第一书记连同胡组长、马忠良和郁洋一样都不容易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呀,小说如果再写写郁洋仕途上的困顿、懊恼以及家庭情感生活的危机、烦恼,可能就更像现实主义冲击波了——尽管这种“分享”是不为人知或者说是分享者所不愿意承认的。在这里,提及“现实主义冲击波”,并无看低《台风过境》的意思,恰恰相反,我特别欣赏“分享艰难”的意识,这也是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必然症候。假如现在真有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让冲击波来得更猛烈些吧!
《台风过境》在精神品质上是突出的,在叙事艺术上也臻于炉火纯青之境。小说对每一个小人物、对人物的每一个小动作都十分留心、十分体贴,几乎没有空洞的、缺乏意味和温情的闲笔。在整体的叙事节奏上,小说也把握得张弛有度,与小说的故事保持着内在的和谐,呈现出较高的艺术完整性。可以说,《台风过境》标识着陈宏伟小说的一个新高度。言及此,我不妨展开来谈谈陈宏伟的小说。在我的印象中,陈宏伟是以讲述申城故事而开启自己的小说创作历程的。这座他所生于斯长于斯的的豫南小城,似乎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和观察生活、理解世界的基点。大概是太过于熟悉小城中的故事了,他早期的小说创作的重心似乎是为了锤炼自己的技巧,这使得我读起他早年的小说明显地感到作者是一个小说创作的熟手,干脆利落,而绝不拖泥带水、冗繁臃滞。但可能因为太在意叙述的快意或者说有意炫耀自己的技法吧,读他的小说,我看到的是一个绞尽脑汁想把故事讲得吸引人的作者。对于这些故事,他充满自信,因而叙述者的形象也就不免有些口若悬河、唾沫横飞,甚至遮掩了故事本身的意味。一些作品甚至有明显的酒席段子的风味,刻意取巧、止于讽喻,故事也就虚弱,而且格调不高、意蕴肤浅,笑过之后便什么也不会留下。这是我对他早年作品(2010年之前)的一点不全面的印象。
近年来,陈宏伟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一味讲求对故事中世态人情的机智理解和犀利反讽,而是对故事中的当事人予以了更多体贴,在“理解之同情”中自然而然地注入了悲悯的情味。这个变化带给他的小说质地的影响是明显的。叙述变得柔软而从容了,即便有些枝蔓,也带有曲径通幽的妙趣,语言也在慢速的叙述中变得精准了。叙述的步速一放缓,叙述者就有足够的话语空间来表达和盛放一些抒情和沉思的内容了,叙述者也就可以讲求一下场景的气氛韵味和意象的象征含义,小说也就在格调趣味上提升了一步;反过来,这同时使得小说的叙述开合有度、疏密有致,颇有些名家的气象了。他的引起较大影响的作品《如影随形》(原发于《江南》2011年5期,《小说选刊》2011年10期和《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增刊第三辑选载)就是如此。《突围》(原发于《文学界》2011年11期)、《爱吃薄荷糖的女孩》(原发于《清明》2012年4期)和《看日出》(原发于《江南》2013年2期)等篇也是如此。在故事进行中,作者真是“贴着人物写”;在故事必要的间歇,作者又跳脱出来进行审视,不自觉地带有悲悯的意味。这里,用悲悯一词似乎有些大了、重了,小说本身没有这般“重口味”,但那種气息是萦绕在字里行间的。我想换用弱一些的词来形容他的小说的这种品质,就用“感慨”吧,确实是感慨不已的那种情味。作者不是居高临下、哲人精英般地审视这些小人物,因而这些小人物也就不像很多我们熟悉的那种作品所描写的那样可悲、可怜、可笑,他们活得很认真、挣扎得很认真、郁闷得也很认真,如同你我。这里面有陈宏伟的自我感慨在,因而有浓郁的抒情成分。这时的作者,不再是那个冷漠而又机智的嘲弄者,而是在生活的地壳中摸爬滚打从而识得轻重、活出感觉的慨叹者。叙述艺术的醇熟和作者历练的醇熟是一致的。
陈宏伟长期在基层政府工作,近年来也承担了扶贫工作任务。《台风过境》中的故事就包含着他从事扶贫工作的一些经验。陈宏伟在《台风过境》中的创作谈中说:“我的确在底层机关参与过两年扶贫工作,经历的生活感受颇为复杂沉重,这更加让我认识到,扶贫作为基层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得太少了,近乎被文学界无视。这岂不也是不正常的?为此,就算这个题材对小说再不利,我愿意正视它一次,哪怕最终归于失败。很显然,台风过境是一个隐喻,它包含的艺术密码非常简单。但是现实生活的山川、河流、温度和湿度,人物的样貌、情绪和气息我又觉得很难用一个隐喻去表述,那是一种不可言传的意境,写作的时候我沉醉其中,甚至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相混淆。我力图写出真正贴近现实的小说,不要飞翔,如果是藤蔓植物,就将根系扎得深一点,再深一点。”陈宏伟谈到了“扎根”的问题,也契合当下文学界对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强调。对于陈宏伟来说,“深扎”是自然的、内在的,不带有任何的姿态性和时段性,因而他所获得的人世经验、人性经验也是浑融的,笔锋也顺理成章地携带着来自人世的深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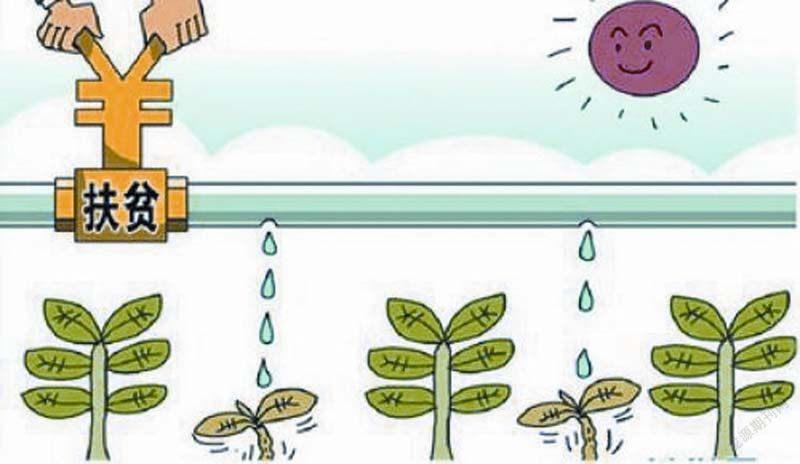
陈宏伟是1978年出生的小说家,是可以归为80后小说家之列的,但陈宏伟无意攀附80后的荣誉,有着自我的选择和坚守,我对此是十分赞成的。近来读了一些80后作家创作的小说,总是感到其中实感经验的贫乏,这大约与我的阅读趣味相关,但也不能不指出:现实生活确实给作家的经验储备带来了难题,这个难题尤其严重地反映在80后作家的创作中。就以《收获》杂志选编的选本《2016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作品选?中篇小说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来说,书中收录的孙频的作品《我看过草叶葳蕤》尽管有书写时代变迁的抱负,故事却令人遗憾地流为落魄艺术家、老女人婚外情、抑郁女性性爱癖、南方阴湿氛围等元素的拼贴,看上去更像一个附庸风雅的三流导演所拍摄的文艺片,其中偶尔显现的有着现实生活意义弥散感的书写也因此被稀释了。选本收录的张楚的《风中事》也只不过写了作家自己所偏爱并赋予其名士做派的底层警察的恋爱史,试图由此勘破时代的情感生活秘密状况,小说所试图积聚的东西在叙事方面都显得唐突,经不起现实生活情理逻辑的推敲,而“风中事”的命名也显得过于虚张。孙频和张楚都是当下风头正健的80后优秀作家,他们的佳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经验的虚弱以及想象的拼贴化,是很能说明“深扎”的必要性的。也是基于此,我真诚地希望陈宏伟能将这种“深扎”的自然性、内在性长期保持下去。
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自己的生活图景和阅读图景的规限中进行创作的。陈宏伟的起点不算低,很早就显现出老辣之气,但这老辣真正经得起反复品咂,无疑是在这些年。从世事洞明到悲悯存在、分享艰难,我相信这是一个写作者通往成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