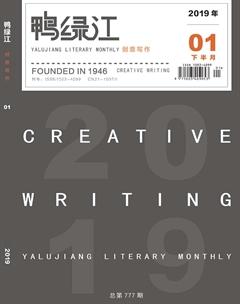《朗读者》: 寻求艺术的创意
董卿 闫皓
董卿:让我选择一个词形容此刻的感受,我想应该是“惶恐”。感谢有思想、有观点、有立场的奖项给予《朗读者》,这是我拿到的最特殊的奖牌。我从业已经二十多年,1994年进入电视行业,经历中国电视文艺制作鼎盛时期。而后慢慢感受到它被冲击,也慢慢听到电视行业越来越难的声音。今天能以制作人的身份站在这里领文化类的奖项,何其幸运!我也觉得非常惶恐,未来到底可以做什么,做多少?是文化类节目的春天真的到来了,还是观众只是在看惯某类节目后换了口味?我们只能不断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我做节目时一直在思考,朗诵不光是电台可以做,剧场可以做。我会考虑如何把原本存在于剧场或原本在电台可以收听的节目拿到电视屏幕上。我们的节目不是纯粹的朗诵节目,大部分不是在听你的朗诵艺术,不是只需要声感享受就够了,更多时候是情感节目,这是有温度的真实朴素的。
各自的存在都有合理性,未来在剧场或电台依然还会有这种节目存在,《朗读者》则会保持其核心价值所在。将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对国家与社会有贡献的人,有高尚品格的人和有特殊经历的人请到现场,用他们的影响力传播我们想传递的价值观。朗读让我们看到,无论过去十年还是一百年,文字中仍然有可以与现代人契合的精神,无论社会怎么变迁,总是有一些东西不会改变。
闫皓:从《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请问您进入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初心为何?是什么驱动着您不断尝试新的角色,向更深入的节目制作与创作中延展?
董卿:(这)其实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主持人做了二十多年,便会越来越清晰自己的定位,越来越知道自己的特长、喜好和风格,而且必须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才能说有了自己的风格。一个主持人形成风格由很多种重要的因素决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先天的基因,可能会慢慢地在职业生涯中被挖掘出来。
我很幸运的是,回顾职业生涯的二十几年,(我)赶上了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我从浙江电视台起步时(1994)正是电视综艺最黄金的时间,那时我是新人,做了许多最基础的工作;到中央电视台时(2002)赶上了盛大国家事件电视节目制作的黄金时代,到目前来看,那时是一个高峰。我们经历了每年的青歌赛、2008年的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六十周年,面对这些国家大事,中央电视台都要在第一时间发声,因此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去历练自己。
对于主持人来说,先天个性中所蕴含的东西加上后天给予的时机慢慢就打磨出了你的样子。就像你是一块泥还是一块砖,是能够做陶还是能盖屋,经过一些火候就可以把你锻造出来。进入到文化节目领域,其实是遇到了,遇到了我想要的,而且是在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
闫皓:为何选择做《朗读者》这样一档人物故事讲述与朗读艺术结合的节目?
董卿:说到底,《朗读者》是一个有文化属性的电视节目。既然它是一个电视节目,就要符合电视传播的特性。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电视传播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在于要能够同理、同情。这个“理”指大家能达成基本共识,不能要求大家都同意;这个“情”指观众能够基本找到共鸣,这样这个节目才能是最有效的。
千古文章,是人写的,也是在写人,人是更大的范畴,人裹着文出来。所以《朗读者》先要有访谈,然后才能朗读。现在大家都能够接受了,在第一季的时候很多人会问:“那能不能先读,读完再聊?”后来发现一定不行,如果只是单纯地读,便很像过往剧院的朗诵会。名家名篇朗诵的形式在剧院存在几十年了,或者说吟诵这种形式在中国就已经存在几千年了。现代文明中,电视传播需求不一样,所以便不能单纯是朗诵艺术的展现,而是要寻找一个契合点。我蛮喜欢把《朗读者》看成是“借现代的人,还经典的魂”。出现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个身边的人,近到大家都是学生,远到九十几岁的神一样的、佛一样的人物。但是不管多远多近,你总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打动你的地方。人们在获得某种情感共鸣和理解之后,再来重新审视这个文本,不管以前是否读过,总会有一些新的领悟。建立在之前讲述的那个人物或故事的基础上,那些已经被淡忘的或者是被忽略的经典读本,会重新焕发出新的光芒。温故知新,途径就是通过生活在身边的人,去帮我们打开那个通道。
闫皓:我们看到在《朗读者》人物访谈环节中,无论是主持人、嘉宾还是现场观众都是饱含感情的。电视节目常常会有被人诟病“煽情”的情况,《朗读者》是如何拿捏情感表现的尺度的呢?
董卿:对这个问题我说两点。其一,开始我也怕眼泪多了,怕有人说煽情,后来我渐渐发现大家都很能接受,几乎没有过这样的诟病。那天碰到毕淑敏老师,她还说:“我特別喜欢看你眼里含着眼泪在听着人家说的样子。”我说:“其实我已经把那些镜头剪掉了一半。”我不想以我的情绪过多地影响观众的情绪,希望大家尽量保持客观。
其二,真情与煽情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是我做主持人这么多年的一个心得体会,你是真的在与他对话,还是抱着目的在套话。现在不是说有套路吗?你已经知道你想到达的那个点,然后你不惜手段,去到达那个目的,那一定会被观众诟病。这就是所谓“煽”,有太多功利心在里面,在消费这个人的情感,或者是大众的情感。我比较倾向于只是客观地、真诚地与他沟通,想听他说,想把这件事情讲明白了,谁也不预设要冲那个痛哭流涕的方向去,而是娓娓道来,这件事情一是一, 二是二。
就像这一期讲“父亲”,父亲这个词一听就蛮有情感饱和度的,很多人一听这个词就会有波动,特别是离家的年轻人,或者是年纪长一些、父亲已经不在了的人,会有情感共鸣。所以,我们在选故事的时候会考虑各种侧面,五个嘉宾有五个维度。比如,“父亲”这期的嘉宾中,有从来没见过父亲的、英烈的后代,但是节目中没有说“伟大”“崇高”这类很拔高的词,只是在讲述她想了解她的父亲,那个只活在照片里的父亲;有徐国义教练这种,自己没有孩子,可是他所培养的队员就成了他的孩子,这样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就多了一个非血缘的维度;还有就是魏世杰这种,除了科学家的角色外,父亲的角色对于他而言可能更艰难、更漫长,但是他心甘情愿。所以,好像每一个父亲都很朴素,但每一个父亲也都有伟大的地方。
闫皓:说到主题词,《朗读者》每一期的主题词及围绕主题词展开的卷首语与开场白都被广泛传播。请问您是如何想到这种节目模式的?每期的主题词又是如何选择的?
董卿:你看,节目中的“札记”“朗读亭”“访谈”“朗读”以及“金句摘选”,组合起来有没有很像一本杂志?最早有札记,是因为作为制作人,我与他们(节目组)聊天时可能会讲一些我的思想和理念,他们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让观众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节目,这可能就是札记最初的雏形吧。至于主题词,天底下有这么多汉字、这么多词,怎么定每一季十二个主题词呢?我们通常需要开很多很多会。所有的主力导演每个人都独立写出二十到三十个词,分享时会发现有重合,出现了一些彼此相似的词,就归并分类。我也会提我的想法,比如提议做“父亲”的时候,我就同大家阐述我的理念—我要让父亲中什么样的人物来呈现“父亲”这个关键词,我希望最终让大家觉得“父亲”这两个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所以,很多东西是经过了千万次的实践,在实践中摸索、打磨出来的,你不去做,就不知道会有这一步,谁也做不到把每一步都想好了,形成特别规整的模式。
闫皓:朗读亭已经成为《朗读者》一个非常鲜明的标志了,朗读亭所到之处都会引发大家进亭录音的热潮。请问朗读亭的创意是如何诞生的?它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董卿:朗读亭也是在开策划会时提出的想法——设置这样一个环境,让大家有情感倾诉的地方。其实朗读亭也成了最让我感动的部分,它是一种线下的形式,在节目中能体现的并不多。第一季我们摆放的时间很短,一共只有三至四个月的时间,而且朗读亭是流动的,每个城市只放置一个月左右。但就是这么短的时间,也有几万人去朗读亭,上海有人最多排队等了九个小时,就为了进去读那几分钟。而且里面的朗读也都很真诚,很多读本选得都很上乘,这让我感到意外。可能,这就是真实的、现代社会的情感采集器,也是现代社会中国人情感世界多方面的展现。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国外那么鲜明的宗教信仰,国外很多人有跪下来忏悔和倾诉的习惯,而我们却比较少,但朗读亭仿佛就承载着这样一种功能。当然也是借助节目的影响力,观众们看到节目里我们很诚恳的态度,被感动、被带动。我相信愿意进入朗读亭的人大多数应该看过《朗读者》,如果没有看过可能也不会想到去参与,所以只要看过,他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以什么样的态度。朗读亭让我感受到节目的基调被大家接受,甚至被很多人追随,观众们也愿意为父亲、母亲、同学、男朋友、愛人去读。我就觉得我们给观众的回报太少了,每期(放朗读亭的剪辑)只有两分钟。
闫皓:除了朗读亭这种线下的互动形式,《朗读者》还在喜马拉雅、爱奇艺、新浪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网络平台对《朗读者》节目传播所起的作用的?
董卿:(它们)起到了非常好的辅助传播作用。现在已经很难用收视率来衡量一个电视节目的传播到底有多广了,因为现在机顶盒就只装在几千户人家,那个东西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不能说对所有节目来讲,收视率都失效了,但是对一些网络传播度特别广的电视节目,应该用多个指标来衡量。新媒体传播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共鸣,而我们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节目源。比如《朗读者》在喜马拉雅上的收听率就非常高,第一季结束的时候有4.75亿(人次),现在已经过7亿(人次)了,它有一个逐渐沉淀的过程。在地域上,《朗读者》突破了央视制作的电视节目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几乎没有收视的魔咒,它在喜马拉雅上的收听率最高的地域恰恰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闫皓:但我们也发现《朗读者》的一些片段在网络上传播的文字标签仍然比较明星向,重噱头,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董卿:这个我可以接受。任何媒体都有自己的特性,而你说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网性。既然在那个平台播,我就还是尊重他们的传播特性。而且,你要相信既然已经把自己扔进了大海,那你就要有水性,不能说“不行,我得上岸,我不能跟你们扑腾”。大家都是在一个水域里面,一样可以看出谁能游得更远,而且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兴趣之所在嘛!不过,我们节目制作的根还是在电视,这是我们与网络综艺的根本区别,我们是从央视的高度和宽度给自己定义。
但是,两季节目做下来,你会发现并没有不可突破性。大家在网络上看了太多五彩缤纷的、“一个人身上恨不得有二十几种颜色”的画质之后,再来看《朗读者》的画质,他们会觉得很好,是另外一种选择。我个人是酷爱电影的,我跟团队也说我们不能只以电视节目的制作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是要去“够”电影画质的。所谓电影的需求就是每一个镜头都有语言,比如长镜头便有它存在的道理,你能体会它的内心,它会告诉你它要发生什么了。而电视节目不是,电视节目更多是为了让观众看懂,比如舞台上有三个人,我们要做这个游戏,我们只要让你看懂这个时空里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它不会挖掘这个动作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但我要求《朗读者》的镜头要有语言,因为我们有内心,我们有很深厚的内容,是经得起挖掘的,人的脸、人的眼睛、人的手甚至人的肩膀,都是一种语言。
闫皓:两季的《朗读者》讲述了上百个人物,阐释了二十余个主题词。设想一下,把他们连缀在一起会有怎样的图景?
董卿: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人生与文学,就是那么简单。没有比人生更丰富的东西了,也没有比文学这个世界更触动人心的了。文学照理讲应该比电影还要深厚,电影是从文学脱胎而来,把这个故事用画面展现出来。文学本身是那么浩瀚,我个人也是在整个节目中受益匪浅,我们团队也这样。第二季录制结束,我跟团队说:“可能很少有一个节目凝聚着制作团队那么多的伤痛,但同时又有那么多的幸福。”当面临很多压力甚至打击的时候,你跨过去了便会觉得自己在成长,伴随着节目的制作在进步。自己因为节目而变得更好,可能是职业生涯里特别满足的事情。
闫皓:您觉得在制作《朗读者》过程中,自己比较深刻的成长是什么?
董卿:我觉得是对人的理解。在和一百多位来自各个领域的、最优秀的、最具代表性的、有特色的人物谈话当中,你一次又一次认知到人的深度,他们或者说他们的思想是深不可测的,就像刚才看到的那篇爱默生的作品。是什么能够让人永久长生?是思想的源泉和力量。我在同现代人的对话以及找寻文本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被这样的思想所震撼,所滋养。
观众看到的节目嘉宾不过六七十人,内外加起来一百多人,但是我们的名单上、我们接触过的是五倍六倍的,也就是五六百人。我们要不停地筛选,首先人物要能进入到我们的嘉宾名单,然后你想邀请人家,人家也未必能来。这个人如果不能来,那么主题词中他缺失的这一部分由谁来替补?我们就得重新寻找新的人物。有时,我们搭建的节目框架美极了,如果设想的嘉宾都能够来,那就是满分的作文,可偏偏冥冥当中被抽掉两块“积木”,我们十分崩溃。我们通常会给自己一个最后的期限—如果这个人到这时还不能来,我们就再改方向,但一定争取到最后,反反复复。
前些天,我碰到一个制作人朋友,他说:“你们最宝贵的是真的在花笨功夫、下死力气。”他了解这些人是经过怎样的筛选和磨合才会出现在录制中。我们有一些原则:首先,在综艺节目中出现过的人我们很少用,因为他被消费过,他的面貌会含糊;其次,如果在近期的同为文化类的节目里出现过,我们就不用了,我们要保证观众有新鲜感。这个人出来了,观众会觉得“《朗读者》能把这个人请来”,而不是说“这个人我刚见过,他又来了”。其实,只是这一点用心,观众对你的好感和信任度便会增加,他们觉得你就是品质。所以我的一个良师益友,在第二季播出第二期还是第三期时对我说:“祝贺你,做综艺节目的爱马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别人没有的,或者别人做不到的。你去花笨功夫,把他“磕”来,再和他讲好,再让他读好,再后期打磨。
我们来算个时间成本。第二季的这些嘉宾,我们从2017年7月就开始找了,一直找到2018年6月10日。每一个嘉宾在确定之前,导演会与他有不下三次的采访,每次不少于两个小时,这样基本提纲才会清晰。这还不包括每一次导演采访完都要跟我开会的时间。采访的内容是什么?原定的方向还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或者走得通但不够,便再去补访,回来再开会。每一个人物的会,最少最少开两个小时,多的时候就要十个小时以上,因为路堵住了,就必须重新去开路。这样三次采访最少六个小时,开会最少最少六个小时,还不包括之前的筛选时间,这些前期工作中的时间成本都是无法衡量的。
当他终于来到演播室,可以和我面对面坐下来聊天了,一个人的录制不少于两个小时, 五个嘉宾就得十个小时,还不包括札记的拍摄,朗读亭的拍摄以及其他东西,拍摄完了就要进入后期。我跟嘉宾谈话谈了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就有一到两万字,多的、语速快的有三万多字,我们要从三万字里“扒”出三千字,大浪淘沙,取其精华。好多导演跟我说:“卿姐,咱是不是太傻了,咱就录半个小时行不行,半个小时也能剪十分钟。”我说:“半个小时剪出来的十分钟,和你跟他谈了一个半小时剪出来的十分钟含金量完全不一样的。”
什么叫奢侈品?所谓奢侈品,是你为它花时间。我只要最好最好的那个东西,要过心里的金线。画掉那两到三万字,没有两个小时根本完不成这个功课,有的時候连自己都被绕进去了,因为觉得每一句都说得太好了。画到最后,我经常会难过,因为我没有办法保留更多东西了。如果这是网络综艺,我可以推出无剪辑版。我可以自信地讲,我们的无剪辑版也会很好看,因为我们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非常完整,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内容扎实。只要稍微剪掉喝水、换镜头等动作,基本都可以保留。可能这也是《朗读者》这个节目个性的一部分了。
闫皓:您在去年(2017)掌嘘颁奖仪式上提出了“是文化类节目的春天真得到来,还是观众只是在看惯某类节目后换了口味”这样的疑问,可否请您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
董卿:做媒体的价值在于看你能影响多少你想要去影响的人,或者是影响多少有影响力的人。很多人认为“文化类节目的春天来了”,我倒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文化类节目本来就不该是一种很热的焦点所在,因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都是有惰性的,在更多时候希望被动地接受简单的东西。所以那些带图画的、短视频的文章在手机上传播更好。如果一张图都没有,全是文字,你可能一看就有点焦虑。对于文化节目本身,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它不可能一直在一个顶峰,但它可能一直在一个高原,因为它本身的地位和厚度摆在那里了,至于它能形成多少高峰,那就看你操作的能力了。
做节目跟做衣服是一样的,没有那么神奇,它也有款式和潮流,要看你的款式能不能符合大众的审美,你的款式能不能符合这一季的潮流。《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国家宝藏》之所以能在此时形成一股热浪,是因为在此前许多年中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像样的文化类节目了。大家对过去的形态已经感到厌烦,这时出现了一种制作精良的,有鲜明个性的文化类节目,它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所以,要做好静水深流的准备。文化类节目本身的手段是有限的,它不是那种很外化的东西,是内心的东西。可能是我个人比较热爱吧,我觉得文学还是有它得天独厚的地方,因为文和人始终是紧密关联的,它不会过时。经典的东西,几十年后可以读,几百年后可以读,而且还能读懂。《朗读者》第二季增添了几篇文言文,反响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做出的判断—敢不敢上文言文,就像第一季“敢不敢请老人家”一样。当大众阅读到达今天的高度时,偶尔出现的文言文读本刺激了观众的某种神经。我想很少有人现在没事时去读《礼记·大学》,读《留侯论》,读《牡丹亭》,可是当你温故知新时,会觉得老祖宗的东西很有深度,所以在一定的时间,按照一定的尺度,给大家一点点刺激便很好。但是,很关键的一点是,这道门槛观众一定要能跨过去。你如果是一堵墙,就会把人给挡住;你如果是平地,甚至比他低,他就会嫌弃你,他走过去就会忘了这个地方;你如果只是比他高一点点,他跨过去了会觉得被你带领了、进步了,他会记住你。
第二季节目刚过半,我们在喜马拉雅收听热度的TOP10里第三位是贾平凹陕西方言的朗读,第四位是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朗读《礼记·大学》,第五位是环境保护者黄鸿翔与珍古道尔隔空的中英文对读。我很庆幸,这就是我们第二季的增长点,是我们想要带领的方向,你会发现观众妥妥地都跟上来了,你会发现你点灯熬蜡、苦心孤诣、奋力拉的车大家都追上了。我们不要低估了观众的智商。
闫皓:请您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在当下的传播环境、舆论环境中,您心目中文化类电视节目应当具备的品质。
董卿:深厚,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朴素,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诚恳;如果你一定要我再加一个,我希望是智慧。深厚里包含着一定的思想性,我个人对思想性是有自己的癖好的,这可能是做主持人二十多年的积累。我真正的成熟是到中央电视台那年,我知道我到底要什么。说句俗的,我们媒体人是靠说话吃饭的,那么语言的功能是什么?或者说语言的价值是什么呢?它一定要达到目的,没有一种语言是没有目的性的,它之所以会产生也是为了某种更深的交流,需要达到某种目的,光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已经不够了,所以才会产生语言。因此,怎么样才能达到目的,是我始终在追求的,现在看来,整个团队也已经达成这样一种共识。
时间:2018年6月21日
地点:《朗读者》节目制作工作室
注:本文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的《中国电视:掌声·嘘声》一书,原文题目《精雕细琢,温故知新》。
(董卿,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朗读者》节目制作人、总导演、主持人。闫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