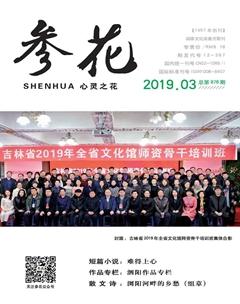王念孙《山海经》校本流传考
摘要:王念孙,字怀祖,号石臞,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山海经》校本递经名家收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将对该书流传过程进行考述。
关键词:王念孙 《山海经》校本 流传考
王念孙校本《山海经》为清康熙年间项絪群玉书堂刻本,书钤“高邮王氏藏书印”“淮海世家”“涵芬楼”“涵芬楼藏”“海盐张元济经收”“北京图书馆藏”等印。范邦瑾在《山海经笺疏补校·影印说明》中对校本的流传情况做了简要的说明。本文结合其他资料,对校本的流传情况再做梳理。
项絪本《山海经》为王念孙所得,以朱、墨二色进行批校,钤“高邮王氏藏书印”“淮海世家”二印。校本至迟在1891年已为盛昱所收藏,费念慈曾用明吴琯《古今逸史》本《山海经》过录王校。校本有费念慈题记:“光绪十七年二月既望,从伯羲前辈假读,用明吴琯本校临一过。武进费念慈记。”题记下钤“费”“君直”印。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伯羲”即盛昱之字。君直是费念慈的字或号。民国初年,盛昱藏书散出,傅增湘将校本为张元济购入涵芬楼,钤“涵芬楼”“涵芬楼藏”“海盐张元济经收”印。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校本,题“盛昱遗书,索十六元,壬子”。①傅增湘曾以吴琯本过录王校,该书现藏国图,跋云:“王石臞校本《山海经》,壬子出于盛意园家,余为收入涵芬楼。今春过沪,假来因循……取吴本就其朱笔先为过录……甲子七月十五日校毕。藏园记。”傅增湘在壬子年即1912年将校本为张元济购入涵芬楼。范邦瑾认为傅增湘在1911年为张元济购得校本,但未列证据,其说误。
之后的流传情况,张元济在给郑振铎的书信中有交代。
振铎先生大鉴:敬启者,前月徐森玉先生由京返沪,交到王石臞先生手校项絪本《山海经》一部。传谕系由赵君斐云入官之书籍中检得,因钤有涵芬楼印记,仍还旧主,由傅晋生君交森玉先生带到。弟一见书衣认为故物,不知何以散出在外。先是编《烬余书录》时,不见是书,故未列入。今合浦珠还,亟拟补撰提要附于录后。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四日。②
范祥雍《山海经笺疏补校》扉页有张元济撰、顾廷龙补的一篇题记,题记中也说明校本的流传情况。
去年冬日,吾友徐森玉归自北京,出示是书,云:郑振铎嘱其交还余手。称得自天水氏入官各书中。因有涵芬楼印记及余经收章,必系由涵芬楼散出。余一见书衣,即认为楼中故物。余编《烬余书录》,原有书目,遍觅不见,故于《录》中漏列,此必在日寇入侵以前即已散佚。楼中善本概不出借,不知何以入于天水手中?料必是典守之人胠箧而去者。又仅一册,故不易察也。是书为傅沅叔在京为余购得者,书中有石臞先生手校眉批旁注殆遍。朱笔字鉴秀整,墨笔行草朴质,又多渴笔,审已高年病癃之后,两校当非同时所为也。绎其校例,一以本经互校;一以它书所引,博稽异同,折衷己意。……诸如此类,考订精碻,为郝氏《义疏》所未及,可补《读书杂志》之遗。 一九五三年一月张元济。
菊生先生命拟提要,因得过校一通。此文前七行为先生原稿,后余所续貂也。龙记。
謇案:疑至“两校当非同时所为也”句止。此系为顾起潜兄跋语。雍案:天水氏谓赵万里。③
龙,即顾廷龙。“謇”即王謇,字佩诤。赵斐云即赵万里。傅晋生,傅增湘长子。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遭遇日军战火,此前校本已经散出在外。1952年,校本归还张元济。张元济“一见书衣认为故物”“合浦珠还,亟拟补撰提要附于录后”。《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子部列“《山海经》,王石臞校”,《补校》过录的题记,或即“补撰提要”。
傅增湘过录本《山海经》的题记写于甲子年,即1924年,此年王校本尚在涵芬楼中。1930年,赵万里时任北平图书馆中文采访组组长,曾至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参观涵芬楼书藏二日。④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陈钝为傅斯年过录王念孙校改的项絪本《山海经》,书有傅斯年1934年写的题记,云:“此赵斐云在涵芬楼所借怀祖先生校本,而骥尘为我过录也。”⑤据傅斯年题记,赵万里曾借阅校本;或因战事,未能归还。
校本归还张元济后,又有顾廷龙、王謇过录王校。顾廷龙因撰写提要而过录王校。王謇以《四部备要》本《山海经笺疏》过录王校。范邦瑾认为王謇从张元济处借得原书过录,但王謇过录了顾廷龙的题记,卷一又绘“廷龙校读”印,抑或是从顾处过录,此事有待进一步考证。后张元济又将校本捐给国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注释: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9页。
②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20页。
③郝懿行,笺疏,范祥雍,补校:《山海经笺疏补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④刘绍唐,主编:《民國人物小传》(第13册),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33页。
⑤汤蔓媛,纂辑:《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第1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版,第162页。
(作者简介:王志豪,男,硕士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语言学、文献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