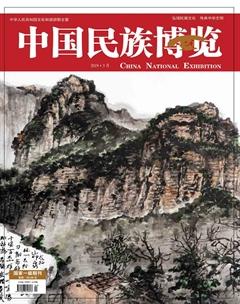黑泽明电影与文学的狂欢化
【摘要】黑泽明电影一直是亚洲电影界的一面旗帜,对世界电影发展都有过重要影响。本文从传统视角不同的方面切入,立足于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理论,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黑泽明作品中隐含的极其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黑泽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狂欢化
【中图分类号】J222.7 【文献标识码】A
黑泽明导演向来被认为是一个能够将日本风格融入电影艺术中的人,但他同时也深受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黑泽明自己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并非是出自臆测。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就描写了少年、青年时代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带给他的巨大冲击,他直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并且“直到今天我依旧崇拜他”。所以,他先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高尔基的《在底层》翻拍成电影。
通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技巧运用于电影创作中,黑泽明导演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在这些技巧之中,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狂欢文学创作观念对黑泽明的电影表现手法影响最大。
一、对狂欢化创作的概括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创作技巧之一,狂欢化的特点由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书中做出了相关的概括。
在表达方式上,狂欢化的核心是一个仪式:节日国王的加冕与脱冕仪式。这个仪式中蕴含着狂欢节的精神内核: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内核,毁坏一切并更新一切。这个过程包含着相对性,它是一种令人发笑的相对性。加冕,代表着现实中权力象征物的严肃形象的死亡中诞生出了一种戏谑而滑稽的形式,脱冕又是对于这样的形式的又一次加冕,它们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分割的两重性的体现,这使他们的象征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的否定,而这样的否定又是某种新的形势与象征所必须的前提,这种两重性的结构对于文学技巧的影响,使其赋予了人物两重性的特质,他们包含着一种危机与嬗变。
在主题的表达上,狂欢节中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狂欢节中的笑,这样的笑也包含着两重性的特征:讽刺和欢欣,讽刺是否定,目的是促进事物的新生,而欢欣是肯定的笑,它们两者隐含着对于秩序与权力的交替的含义。这里引申出对于讽刺性摹拟的探讨,讽刺性摹拟的探讨,关键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讽刺性摹拟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再与这样的同貌人的对比过程中,主人公临近死亡(否定),而在这样的贴近危机中,主人公才可能获得新生。
同时,这样的笑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狂欢化的笑是弱化的,它通过一种梦境式手法体现出来,在《罪与罚》之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梦见自己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时候就是将这样的凶杀以及无数人的狂笑场面相结合的,这样的笑并没有排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浓郁的阴郁色彩,相反,通过和完全有悖常理的凶杀与死亡的联系,使整个场面具有了一种狂欢地狱的性质;第二,群体性的狂笑通过与现实的严酷对比,将自命不凡的角色形象进行了脱冕,这使认知周围的环境限制溶解了,人们形成了内在的交往,使原本分化人的东西,给生活罩上一层严肃的假象的东西,变得只具备某些相对性的意义。
这样的笑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的感性表达,通过同貌人的媒介和人物的行为与对话,这样的笑排斥掉了任何严肃的抽象思想的表达,反而是立足于一种生活化的形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体验。它是一种实在的感性的生活体验,是一种蕴含着复杂情感的形式,它本身就是在对自己狂欢化的生活体验的死亡中体验一种新生。
二、狂欢化在踏虎尾中运用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传统能剧《安宅》:著名武将源义经在源平合战中立下战功,但受到自己兄长源赖朝忌恨和追杀,逃难途中他和部下途径一处重兵设防的要塞安宅关,在武藏坊弁庆的计谋下,一行人化妆成僧人,而义经化妆成一个脚夫躲过了守将的盘查。
黑泽明这个框架之下,完全摒弃了原作的悬疑内容。他立足于依靠语言对白和种种狂欢化的姿态来推动电影的叙事。于是,推动剧情的主角也从英雄式的武藏坊弁庆,转为原创的脚夫夏本,他与真正的主角,故意妆扮作脚夫义经,成了死亡之下的同貌人。
原剧中有着不低戏份的义经,因此在剧中仅有一句台词。他内心复杂的人性活动,完全借由夏本得以完成。当武藏坊等人向富坚介绍到:“我们六人是和尚,而他是脚夫”之时,映入眼帘的是去而复返的夏本,当富坚与武藏坊即将摊牌时,抱着装在箱子内的义经盔甲唯恐暴露的也是夏本,当武藏坊怒打源义经时,扑倒在义经身上的也是夏本。在肃杀的气氛中,夏本用自己低俗的语言与动作在压抑到极点的缓慢节奏中快速带动着叙事的铺陈与展开,成为剧本的核心,使矛盾与冲突富有动感而又不过于压抑。
他也使四周的配角也卷入了狂欢化的氛围之中,成为狂欢化的对偶。作为武士形象出现的武藏坊与富坚,一开始就围绕着义经产生了尖刻的对立,在夏本来到之前,富坚一直在以一种相对游戏的心态来看待这些连无知的脚夫都骗不过的“和尚们”,但在夏本的嬉笑作怪、插科打诨的情况下,他却开始用佛经这种全然非武士的语言和武藏坊开始一场关于仁与义的辩论。最终,游戏心态的富坚越发严肃和敬畏地看着这些俘虏,直到富坚以死相威胁,“和尚们”也坚定如故的时候,他最终动摇了。
当整个叙事走向结局时,黑泽明设计了一场意蕴深远的狂欢:脱险的几人遇见富坚差人送来清酒供大家享用,在开怀畅饮之后,喝醉的脚夫开始疯狂起舞,而他的舞步则是能剧《安宅》中武藏坊弁庆的舞步。正统能剧中严肃的英雄舞步,却是一个贱民在大醉之下胡乱地舞动着,人与人的间隙在此消融为一种跨越死亡的新生的喜悦,这种喜悦达到了电影叙事的高潮。此后,影片在如梦初醒的脚夫夏本在清晨的荒野中孤身醒来作结,只有身上披挂着一件只属于原义经的华服告诉他这一切并非是一场幻梦。
这样的手法给予电影叙事一种非情节化的推动特征,它拓宽了影片的感染力和叙事方式,在有限的篇幅和场景下纵深了电影思想上的层次与空间。
三、总结
黑泽明的诸多电影都具备上述特征,他注重人性却不试图批判的态度借由狂欢化的技法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正是这种复杂的技巧,使黑泽明的电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力度。其赋予了人物两重性的特质,将危机与蜕变融为一体,使原本很简单的剑戟片、警匪片都具备了相当的深度。比如在《野良犬》中,在连环杀人案中执着追查与自己同是退伍军人却命运迥异的警官,不断在博弈中认为对方只是另一个自己,而这个人也只在最后才显出真容,整部电影在紧凑的气氛中倒像是警官在追寻压抑的自己。《泥醉天使》中酒鬼医生和患肺结核的流氓相互将拯救对方看作是拯救自己。而在《七武士》中,坚守信义的七武士为了农民与沦为盗贼的武士的决战,最终两败俱伤之后,感慨道:输的是武士而赢的是农民。在《天国与地狱》中,穷人出身的资本家权藤在争夺公司的竞争中的不择手段,却最终因为仅存的善良被绑架犯逼得倾家荡产,而这善良又使本来冷眼旁观的警察全力以赴,设计将本罪不至死的亦是穷人的绑架犯银次郎判处死刑,当最终两人在死刑前见面时,崩溃的银次郎被警卫带走后,结局给了一个长镜头,展现出坐在狭小的探监室内的权藤和印在死刑犯窗口关上的玻璃门上的权藤的倒影,令人深思。
而黑泽明导演这种对文学理论进行创造性运用的手法,对文学研究者和电影研究者来说,或许都应该算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情。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里奇.黑泽明的电影[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2][俄]巴赫金,刘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日]黑泽明,李正伦.蛤蟆的油[M].海南出版社,2014.
[4][日]野上照代.等云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荣如德.白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6][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朱海观,王汶.罪与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谢钟磊(1988-),男,汉族,四川成都人,西华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文學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