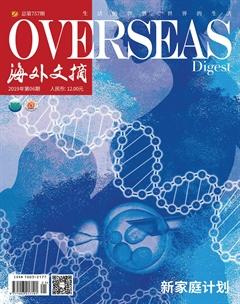堕胎是一种罪?
妮娜·珀尔肖 彦斯·柯尼希 约阿希姆·里恩哈特

对于马莱克·克鲁格尔来说,1月24日十分不同寻常。这天早上一醒来,她就想:“本来今天我就要当妈妈了。”她看着自己孕5周时的超声图像,上面有一块不规则的阴影。她清楚地知道,如果当时做了个不一样的决定,会意味着什么。她想:“天哪,我不想那样!”
马莱克·克鲁格尔选择了堕胎。
26岁的她在一家出版社工作,住在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个小城里,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眼里总是闪耀着光芒。她喜欢在阿尔卑斯山散步,也喜欢和闺蜜们一起聚餐。
那是5月初的一天,马莱克在一次派对上遇到了一位故友,他们之前就曾有过暧昧关系,两人都喝多了,安全措施没做好。4周后,看到验孕结果的马莱克大吃一惊——两道杠,她无疑是怀孕了。
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她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次谈话进行得十分艰难。她的父母说:“我们养大了我们所有的孩子。”但是他们也说,应该由她自己作决定。然而最后,马莱克还是决定尽快结束妊娠状态。
那时候她还以为,作出这个决定就已经是最艰难的一步了。如今她说:“最可怕的是我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发生的事情。在21世纪的今天,选择堕胎的我仍然感觉自己就像个罪犯。”
大部分人认为,在德国,孕12周内堕胎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毕竟相关法律规定已经前所未有的宽容。而且目前德国正在进行一项变革,将允许医生在遵守广告禁令的前提下指明自己提供堕胎服务。此外,很多不想要孩子的孕妇也确实得到了尊重,一些重视孕妇自主决定权的人对她们表示了支持。
“在21世纪的今天,选择堕胎的我仍然感觉自己就像个罪犯。”
但是,仍有很多孕妇备受指责,四处寻觅却仍找不到能提供帮助的医生。这些女性的数量将来还会更多,因为想做这份工作的医生越来越少了。在近年来右翼运动的鼓励下,那些极端“生命保护者”更加积极地展开了行动。做人流手术的医生遭到殴打,他们的住址被公布在如同血腥耻辱柱一般的网页上。这导致如今很多女人内心都十分矛盾:虽然她们不再认为堕胎是种禁忌,但一旦轮到自己身上,就会觉得备受指责和惊吓,有些甚至还会噩梦缠身。
自1995年以来,德国法律规定,在孕12周内堕胎不违法,如果有医学或犯罪学指征,该期限还可以延长。意欲堕胎的女性要接受专业咨询,在经过3天的等待期后方可堕胎。這是刑法第218a和第219条的规定,章节名为《反生命罪》。刑法第219a条认定,医生哪怕只是宣告自己提供堕胎服务,比如在他的网页上,都是触犯刑法的广告宣传行为。
似乎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严苛的规定,直到它于2017年11月走向崩溃。如今62岁的医生克里斯提娜·哈纳尔被吉森地方法院处以6000欧元罚款,因为她在自己诊所的页面上列出了“堕胎”这项服务。州法院的二审维持了原判。州法院法官遗憾地告诉这位医生:“您得将这项判决视作一种荣誉头衔,它见证了您为争取更好的法律而进行的战斗。”她从多方获得了支持,第218条法律再次引发群情激愤。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表示应找到一种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各党派都开始着手应对这件事。
但目前提出的方案也并非良策。医生们仍然不能在自己主页写明使用的堕胎方法、等候期长短或手术费用,只能挂上外链引领女人去咨询机构,或拨通家庭部的热线电话。而那些不想要孩子的女人希望尽快搜索到自己认识的医生能提供哪些服务。
在和父母谈过之后,马莱克·克鲁格尔决定向自己的家庭医生求助。她的妇科医生会不会帮她堕胎呢?由于广告禁令,他的主页上没有任何信息可循。她还记得那位妇科医生非常不友善的话语:“您会后悔的,会因此承受痛苦。”马莱克内心冰凉地离开了诊所。
接下来她去了卫生署,这是她所在小城中唯一合法的堕胎咨询机构,也是这里为做堕胎手术的医生颁发许可证的。工作人员给她的建议是,她应该生下这个孩子,将他送给别人抚养。“我感觉自己失去了自主决定权。”她说。根据《怀孕冲突法》,咨询师不允许下任何定论,但又必须保护未出生的生命——这种矛盾的规定导致在咨询过程中一些女人的内心受到巨大冲击。
| 诊所前的“生命保护者”|
马莱克·克鲁格尔开始寻找能帮她堕胎的医生。从咨询师那里,她得到了两个地址。一个在她所在的城市。那名男医生没有自己的网页,她记得他的助手如何在电话里朝她怒吼:“到底几周了?”听到这语气,她就放弃了去那里的念头。
第二个医生名叫弗里德里希·斯塔普夫,在慕尼黑行医,距离她的住处两个小时火车的路程。马莱克·克鲁格尔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他的报道。他只做人流手术,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女性自主决定是否保留孩子。约好就诊时间后,她继续在网上查找信息,发现全德国可能没有哪家诊所有斯塔普夫的诊所前聚集的“生命保护者”多。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和斯塔普夫的病人交谈,给他们看那些几乎已经可以存活的胎儿的流血照片,责备她们即将成为杀人凶手。斯塔普夫起诉了这些人,现在他们必须和诊所保持距离,但迄今没被赶走。这件事被闹上了欧盟法庭。马莱克·克鲁格尔准备避免被任何“生命保护者”搭讪,同时相信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医生。
弗里德里希·斯塔普夫是做人流术的先锋,对他的很多同事来说,也是最好别染指人流术的鲜活例子。斯塔普夫决定专注于人流术,是在60年代末。那时,在威斯巴登一家妇科诊所的人流手术室里,他看到几十名女性经受了最糟糕的人流术。就在他一年的实习期间,就有10名女性因此死亡。斯塔普夫的人流术当然是遵守现代医学标准的。他需要面对可怕而偏激的愤怒:在网页“婴儿大屠杀(babycaust)”上,他被称为“杀人专家No.1”和“流水线堕胎者”。他知道,敌视他的人越来越多。
目前,73岁的斯塔普夫还不清楚有谁能接他的班,年轻的医生们不想和这个手术扯上什么关系。2003年,德国还有2050家诊所提供堕胎服务,如今只剩1173家,减少了43%。对于这种缩减,妇科医生职业协会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显然,70年代的从业者们已经陆续退休,很多年轻的医生觉得没必要往人们愤怒的枪口上撞。“在如今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年轻一代的医生们都不再愿意从事堕胎工作,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件事。”协会主席克里斯提安·阿尔布灵谨慎地说。
大学几乎不教人流术,很多年轻一代的医生也不愿做堕胎手术,在一些天主教徒众多的乡村地区,方圆百里都找不到一个能堕胎的医生。
此外,大学几乎不教人流术,在为期5年的妇科医生专业教育中最多只是略有提及,只有自然流产之后也会进行的刮宫术是会正经教授的。对于抽吸术和药流是如何起作用的,也都闭口不谈。90年代美国医学生发起的名为“医学生的选择”的活动,如今也已经扩散到了爱尔兰、英国和德国。在私下组织的专题研讨会中,医学生们借助形状近似子宫的木瓜进行练习,用抽吸器将小小的核从木瓜中移除出来。
| 医院被牢牢掌握在教会手中 |
在上普法尔茨、下巴伐利亚、阿尔高——尤其是在天主教徒众多的乡村地区,有时候方圆100公里内都找不到一个能堕胎的医生,比如在富尔达或特里尔。
克劳蒂亚·赫尔特美思在特里尔的“支持家庭(pro familia)”组织做心理医生,她设计了一份传单,订了一间会议室,邀请医生和医院经营者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于3月8日在特里尔举办的这场活动以“我的肚子属于我4.0”为主题,这是70年代的女人抗争侮辱和诋毁时的呐喊。克劳蒂亚·赫尔特美思说,特里尔地区约有50位妇科医生,但没有一个能做人流术。在这个主教城市,医院被牢牢掌握在教会手中。人流?必定引发愤怒!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教皇是支持女人的,但就在不久前他还在罗马圣彼得广场表示:“杀死一个人是不对的,即使他还很小。这就像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雇佣一名职业杀手一样?”
“支持家庭”组织曾询问妇科医生,是不是至少存在药流的可能性,但没有人给出肯定的答复。
莱蒙德·卡托在离特里尔几百公里远的萨尔布吕肯工作。卡托是个化名,因为这位妇科医生担心再次成为“生命保护者”的箭靶子。每周五,他会在“支持家庭”组织在萨尔布吕肯经营的医学中心帮忙。卡托每年会在自己的诊所和医学中心做400~600台人流术。卡托为这些女性说明可以实施的人流方法及其风险。
手术室在走廊的另一侧,内有装着抽吸器的手术椅和超声装置。卡托说,在局部麻醉后将胚胎吸出的外科手术只需一分钟就能完成,那之后病人們就能起身去休息室了,有些当天就能回去工作。
| 复杂的感受 |
卡托收到了匿名的恐吓信。他有时候也会有道德伦理上的困扰吗?他说,问题的中心并不是他,而是那些女人们。“她们有保持健康的权利,我们必须提供医学帮助,否则她们就会像50年前的女人们一样落入犯罪分子之手。”
两周前的一个周日晚上,在著名主持人安娜·维尔的脱口秀节目上,从医几十年的医生克里斯提娜·哈奈尔和26岁的联邦议会议员、法学家菲利普·阿姆托尔相对而坐。阿姆托尔曾在一个电视短片中表示不应更改219a条款中的广告禁令,他支持基民盟的卫生部长延斯·史潘计划进行的一项关于“堕胎的精神后果”的研究。
这一切都让人想到五六十年代。那时,剥夺女人的自决权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而且被宣扬为对女性的关爱。女人是否经受得起一次人流术的问题早就有了答案。大卫·菲尔古松和他的团队进行了一项富有说服力的研究,他们对500多个女人进行了多次访谈,直到她们年满30岁。研究结果发现,堕胎几乎总是和强烈而复杂的感受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也会出现强烈的不适感。但是,当女人们30岁时被问到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时,给出肯定答复的比例高达89.4%。
马莱克·克鲁格尔和母亲一起来到了慕尼黑。当两人看到斯塔普夫医生时,诊所门前并没有“生命保护者”。她在监护病房休息,她的母亲陪着她,两个小时后她们就可以走了。马莱克·克鲁格尔很疲惫,但也很开心。
今天她说,那时她能很好地应对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在诊所时她被告知:像她这样不想要孩子的女人有很多,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很肯定,将来她会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到那时,她会真心期待孩子的到来。

约瑟芬妮27岁,开姆尼茨
我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是在孕4周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那时候我还不想要孩子。但是那之后的道路既漫长又困难重重,是我从来没有预料到的。我十分震惊,它居然会让我的生活变得如此艰难。我决定选择药流,这只在孕9周之前可行。我问了3家大医院,只有一家给我预约了时间,而且是在6周之后。我怀着疑问给医生打了电话,但是他们的回复十分不友好而且令人心碎。他们只是朝我怒吼:“在我们这里,您是别想了。”在“支持家庭”组织,我得到了一张联系方式列表。我拨通了上面的电话,但是其中一些医生只是告诉我,由于遭受控诉和威胁,他们早就不做人流术了。最后我终于联系上了一位友好有礼的医生,还好赶上了药流的时限。我本以为这种禁忌已经不复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作这个决定让我感到很糟糕,不只是因为那个未出生的孩子,也是因为不理解这个决定的社会。我觉得好像被剥夺了决定权,就好像生孩子是我作为女人的任务一般。

雅斯敏33岁,萨尔布吕肯
我打了两次胎,分别是在21岁和23岁时。第二次的经历十分恐怖。尽管用了药,胎儿还是没有打下来,医生给我看了超声图像。她说,孩子看起来很健康,“那里是他的心脏在跳动。”我觉得非常难受,也备受打击,震惊、悲伤和愤怒各种情绪杂陈。但是我很坚决,接下来又做了麻醉状态下的人流术。几年后,我迎来了新的人生阶段。再次怀孕时,我做好了要孩子的准备。然而到孕10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不太对劲,胎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失去了这个孩子。那太痛苦了,我崩溃地询问我的妇科医生,是不是之前堕胎的原因,他告诉我“是的”。我彻底绝望了。两天后我去医院刮宫。看到恐惧不安的我,那里的医生马上说,这不是你的错,孕12周内流产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那时候,我的生存意志也和这个孩子一起死掉了。而我周围的人继续将这一切归罪于我,让我觉得尤其糟糕。在和我吵架时,一个女性朋友说:“至少我没有杀死自己的孩子。”其他人认为:“你的状况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毕竟你是打掉了自己孩子的人。”好在现在我已经是一名母亲,我的女儿一岁四个月了。

茱莉亚29岁,柏林
我怀孕了,是因为我的宫内节育器脱落了。医生告诉我:“这事时有发生,这意味着您和男友之间的性生活十分和谐。”这让我十分震惊,也让我觉得愤怒。她无法想象我居然不想要孩子,尽管我之前正是因为如此才让她帮我放置节育器的。好在我找到了一家很好的咨询机构,几天后就得到了一位妇科医生的预约号。我决定接受人流术。问题在那之后接踵而至。有几天我感冒了,开始在网上搜索。在论坛上,我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人流手术后,何时才能喝酒或运动?但是我很快注意到,就连如此普通的问题都不能提,总有人留言骂你是谋杀犯。后来我陷入抑郁情绪,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然而我随即被导向了一个反对堕胎者的脸书页面。在那上面,我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女人在厕所里,她的肚子里有个胎儿,对话框里面写着:“我的妈妈马上就要杀死我了。”我想:这不是真的!这是我的私人领域、我的身体,但是一旦我怀孕了,我的身体就不再属于我了。

安娜(化名),30歲,基尔
实际上,在咨询机构时,一切都还挺好。刚开始,我的妇科医生大力地祝福了我。当我告诉他我不想怀孕时,他调戏我说:“那您怀他干嘛?”那时候我就觉得事情不对劲了。他对我带有偏见,充满傲慢,问我,我的伴侣对此是否知情。我诚实地回答了他,说这是一个错误,我的男友虽然支持我的决定,但也为此感到悲伤。而医生完全曲解了我的意思,向我描绘出这个决定的恐怖后果。他表示,生个孩子是其他女人最大的渴望;如果我的男友离开我,我不应感到惊奇。我就像在经历一次天主教的弥撒,一切变得越来越荒唐。检查完毕后,他说,他不做药流。我打电话给一家医院,他们也只能做人流手术。我又打给另一家,他们推荐我去另一所城市。那边给我的建议是,再打电话问问别家吧。最后我一共给十一二家医院打了电话,一直在害怕拖下去错过了药流的最佳时间。虽然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家,但是那时候的遭遇,那种绝望的无力感,至今仍然如同噩梦一般令我后怕。
各国女性堕胎权现状
在很多国家,选择堕胎变得越来越艰难。
在66个国家——其总人口占全世界1/4——都只有在妊娠威胁到女性生命安全时,才允许堕胎,其中包括一个欧盟国马耳他。
在其他国家,堕胎虽然是可行的,但是在很多地方都正变得越来越难。“在世界范围内,掌权的多是保守派政府,其中很多都认为,在生育的自决权上,女人应该受到限制。”纽约“生育权中心”组织的宝拉·吉伦说。
在法国,反对堕胎者聚集在以玛丽娜·勒庞为中心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曾经的“国民阵线”)中。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禁止堕胎。不久前,他还在讲话中表示鉴于目前国内形势,应要求禁止孕晚期堕胎。他举了个可怕的例子,表示纽约州最近通过的法律允许“将一个马上就要出生的婴儿在子宫中撕成碎片”。而这纯属谎言。在美国,虽然根据1973年最高法院的裁决,堕胎是合法的,但是女性自决权的拥护者们和“未出生生命保护者们”之间感情和理念上的斗争从未停歇,而这带来的后果是,在美国很多联邦州,女人需要突破重围才能接受人流术。例如在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或怀俄明州,分别只有一家医院能堕胎。在13个联邦州,女人会被告知,堕胎时胎儿会经受痛苦(尽管没有科学依据)。在32个联邦州,她们被医生要求堕胎前看一次她们胎儿的超声图像。仅仅在2017年,就有19个联邦州颁布了63条关于堕胎的限制性新规。在竞选宣传中,特朗普要求惩罚那些堕胎的女人。
意大利关于中断妊娠的法律规定和德国相似,对于这个主题的争议热潮前所未有。如今,能够中断妊娠的医院越来越少,约70%的妇科医生都拒绝做人流术。而这不仅出于伦理原因,医生们还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受到影响。在意大利,也有反对堕胎者在医院前示威。
就连在挪威,保守派也在试图限制已经实施了40年的《自由堕胎法》。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认为,堕胎法应变得更加严格。对她来说,保持权力似乎比女人的自决权更加重要。
而在爱尔兰,2012年,一位印度牙医不得不痛苦死去,尽管她腹中已经无法存活的胎儿正在毒害她,她也不被允许堕胎。自那以来,实现堕胎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接着,堕胎支持者们以相差悬殊的多数票赢得了全民公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