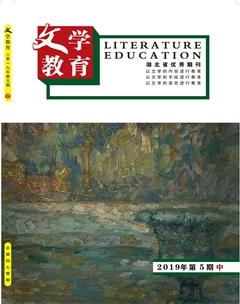《秀拉》中黑人男性的身份缺失
内容摘要:在《秀拉》中,生活在“天堂之底”的黑人男性在這个空间秩序充斥和种族疆域分明的权利异质空间中极大程度地遭受着社会他者身份的危机。在白人族群空间规训的威慑之下,他们的自我身份在社会空间的极度缺席中逐渐丧失和消解。同时,由于面临着“底部”社区中母性力量的崛起和抗争,黑人男性在暴力无序的母性家庭空间中逐步反成长为被异化被隔绝被驱逐的存在,因此,他们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限制和压抑。通过揭示“底部”黑人男性的所遭遇的空间规训和空间暴力,托尼·莫里森深刻而细腻地书写了他们在压抑空间中自我身份不断丧失的困境。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黑人男性 空间 权力 身份
一.引言
托尼·莫里森在罗伯特·斯特普托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有很强的地方感,这不是指某个乡村或某个州,而是指某个城镇或社区的一些细节,情感和气氛”(474)。带着这种强烈的地方感,莫里森在《秀拉》这部作品中刻画了一个充满冲突,死亡,创伤和异离的黑人社区——“天堂之底”。在这个被白人主流社会隔离和边缘化的他者空间之中,空间秩序和空间规训被严格遵守与实施。生活在其中的黑人男性被主流话语所拒斥,作为被定义为他者的少数族裔无法实现他们的社会在场身份。当黑人男性无法取得主流社会的在场身份时,他们选择成为家庭空间的主宰者和权威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底部”这个黑人族群空间中,面临着以夏娃为首的黑人女性竭力构建母性权威的对抗力量,黑人男性在这种女性话语模式的运作和挑战下逐步出现反成长迹象,最终身份被进一步消解。
二.空间秩序与疆域分界
空间,作为权力运作的基本场域,本身就充斥着权力规训与惩罚的运作方式。米歇尔·福柯指出,异质空间是一种集真实与想象,集空间、文化、历史于一体的空间形式,并且以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为特征(福柯,9)。异质空间作为一种充斥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包容性存在,它实际上富含了差异性和颠覆性。与主流的权力空间相对,异质空间由于它的差异和混合成为一种他者般的空间场域。在《秀拉》中,严密的空间秩序和清晰的疆域分界都在“底部”这个异质空间中确立和执行。与白人主流空间相对而言,“底部”成为一个异质的他者化空间,并且在这个权力异质系统中,空间成为标识种族社会关系的象征。
《秀拉》开篇,莫里森以一个关于黑鬼的笑话介绍了“底部”这个充满荒诞与创伤的社区的由来。一位白人农场主向一个黑奴承诺,只要他完成一件难办的事情,就会给予他自由以及一块低地。可是当黑人完成任务后,农场主同意给他人身自由,却不愿意交出原来承诺的底部的一块低地,而只愿意将山顶的土地给黑奴,并声称那是有着最好的土地的天堂之地。黑奴相信了白人农场主的话,终于得到了那块伫立在在山顶的却被称为“底部”的土地,却逐渐发现“那里水土流失严重,种子都会被冲掉,而冬天寒风又呼啸不已”(莫里森,5)。显然,“底部”并非白人农场主所声称的那般肥沃,它也并不是他所说的“天堂之底”。相反,它只是一块无比贫瘠难以耕作的土地。为了适应他自己的利益需求,拥有种族话语权的白人掌握着土地的所有权,并且可以任意歪曲事实从而按照他们的意愿划分种族空间。白人种族所拥有的绝对的空间话语权,而作为被奴驭的种族,黑人只能生存在“底部”这个异质的他者化空间。与白人居住的富饶繁华的梅德林镇相反,“底部”的黑人们面临的是无尽的贫穷,苦难以及无奈。高居在山顶,他们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被隔离在这边缘化的空间之中。“种族隔离所创建的是特权地理,特权地理不仅监管财富边界——构建不平等可再生的空间形式——而且同时建构和监管种族地理边界”(米切尔,255)。这种拥有特权色彩的种族空间秩序不仅将黑人群体从主流社会空间中分隔出去,更是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时刻提醒他们的他者身份。通过种族空间隔离,白人再一次确立并强化他们对社会空间的掌控权,在这种秩序化的种族空间中,黑人沦为他者。
三.空间规训与身份缺席
生活在特定空间之中,人类的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这个空间影响和规约着。“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Wegner,181)。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带着人类特有的标示,但与此同时,生活在其中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认知也不断被影响被规训。在《秀拉》中,黑人男性一直生活在“底部”这个权利异质空间之中,而这个充满权力与冲突的空间也反过来不断影响着他们作为黑人的身份意识和自我认同。在这个他者空间里,他们作为边缘者,面对着白人主流话语的空间规训,不得不接受和认同自己在社会空间中不在场的命运。
在种族空间秩序的规训下,维多利亚·布伦斯论述道,“底部有着一个受创伤的社区的所有特征。这是一种对创伤的公共反应,他们的创伤已经网结于社区生活中与种族化和性别化息息相关的一切事物之中”(117)。与如丰碑般的繁华的麦德林相反,黑人群体居住的“底部”充满了贫穷,灾难,疯癫,和死亡。被框限在边缘的他者空间之中,他们的生活被贫穷,苦难和无奈所充斥。他们被主流社会所隔绝,被异化为低于一等的存在,并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在提示着他们的他者身份,因此整个社群都被创伤网结着。莫里森写道,“底部”黑人的痛苦“它隐藏在眼睑下,在包头布或是软皮帽下,在手掌上,在商易磨损地翻领后,在肌腱的弧线里”(4)。他们的无处不在的痛苦和创伤,不止来源于种族空间分界后的无助和无望,更多的是因为无法在社会公共空间中获得存在感和价值感。由于他们的肤色和种族,他们在社会空间中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和白人男性相反,黑人男性无法从这种不在场的危机中突围出来。
裘德,李子,夏德拉克这些黑人男性都曾尝试打破他们的社会空间缺失状态,诉求自己的主体价值,但无不以失败告终。夏德拉克在未上战场前线之前,“他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嘴唇上回味着口红的味道”(莫里森,7)。可是当他从二战战场中亲眼目睹战友死亡并且自己受伤归来之后,一直活在狂躁,疯癫和恐惧之中,还成立了“全国自杀日”。在战场这个充满暴力,鲜血,和死亡的空间里,夏德拉克的自我意识和空间意识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当他回归“底部”这个他者空间后,他的自我意志逐步消解,他只能终生困于疯癫之中。和他类似,李子从战场回来后,开始变得浑浑噩噩,与之前那个“在从未间断的爱与关怀的包裹中游荡”的小伙子判若两人(莫里森,48)。从前的李子在爱与关怀中成长,但身为男性的他渴望在社会空间中寻得一片位置。年轻充满壮志的他希望通过参军来改变自己作为黑人男性的他者身份。然而,他作为黑人,就难以走出或者超越这个边缘者身份的框限。当时的美国政府积极号召黑人男性参加战争,并向他们许诺战争结束后的社会地位的改善。然而,当他们抱着满腔热血积极参加战斗渴望获取价值之后,迎接他们的却仍然是种族隔离和身为他者的社会身份。以夏德拉克和李子为代表的黑人男性都希望在战争中获得在美国这个社会公共空间中的认可和尊重,可是战争的残酷和血腥,回归后的社会空间缺失状态使他们所有的希望再一次幻灭。另一位一直生活在“底部”的黑人男性裘德也尝试走出被隔绝的空间从而实现自己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存在。当他听说城里要修一条路时,他渴望成为修筑这条路的一份子从而彰显自己的男性气质。急切地渴望进入这个社会空间,彰显自己的价值从而确认自己的男性气质的裘德却一次又一次失望。他只能眼看着工头们带走那些“细胳膊瘦腿的白人男孩,脖子粗壮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却避开有力气把马路翻个儿的黑人小伙子”(莫里森,87)。面对着这重重的挫败,裘德感到愤怒与不快。作为满怀斗志和年轻气壮的黑人男性,他却因为种族身份一次又一次地被主流社会拒绝和否定。深受创伤的裘德只能放弃自己的社会空间在场诉求而选择婚姻在家庭空间中塑造男性权威。
生活在“底部”这個他者空间里,以白人主流话语为主导的空间秩序以坚不可摧的方式压制着黑人男性的自我身份建构。“面临着来自白人社会无形力量所施加的的压力,黑人族群的主要生存策略只能是支撑住那些个人和社会都必须遵守的,严格且不可言说的,并且似乎不可渗透的边界规则”(布伦斯,126)。他们拒绝黑人男性进入到主流社会之中,并不断地限制着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存在方式。作为他者,黑人男性在这种如壁垒般地空间边界外,不得不内化这种规约和限制。在种族空间秩序和种族隔离的空间规训双重压制之下,黑人群体无法在社会公共空间实现自己的主体诉求,而只能在被规训的空间内生存。
四.空间暴力与男性反成长
空间作为权力运作的场所充满着暴力和规训。由于“底部”的黑人男性难以打破社会空间不在场的状态,他们选择在家庭空间中建构自己的话语权,重塑自己作为男性权威者的地位。然而,在“底部”这个充满差异和颠覆的权力空间里,以夏娃·匹斯为代表的黑人女性积极地通过空间改造来建构自我的母性权威,这种以杂乱和无语为特征的母性空间极大地威胁着黑人男性在家庭空间中的存在。在逐渐崛起并极具颠覆的母性力量的抗衡下,黑人男性在家庭空间中曾拥有的权威位置被否定,他们的优位也被驱逐。反叛的黑人女性在改造后的家庭空间中积极反抗着以父权秩序划分的空间秩序,并且她们通过实施空间暴力来进一步维护这种母性权威。在这种强大的对抗力量之下,黑人男性出现了反成长的迹象。
在《秀拉》中,在家庭住宅这个特定空间中,黑人女性渴望打破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虚无状态,她们通过实施空间暴力拓展女性疆域来建构属于自己的女性空间。在木匠路七号,女主人夏娃在这个充满女性能量的家庭空间中反抗传统的父权制性别政治模式,积极确认自我主导权。尽管身体残缺,夏娃对男性仍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并且这些男性“总是抬着头看着她:仰望着她两眼间宽宽的距离,仰望着她软而黑的鼻翼,仰望着她的下巴尖”(莫里森,35)。作为这个房屋的构建者和改造者,她成为了拥有至高权威的女性统治者。在她的监视和管控之下,生活在其中的男性成员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空间暴力,并都出现了反成长的迹象。
其中,来到木匠路七号久住的柏油娃娃每天都醉生梦死,如行尸走肉一般生活着。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来历,但“底部”的黑人群体集体意识到,他会在夏娃的房屋中逐渐死去。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名叫杜威的小男孩在被夏娃收养后再也没有长大过。由于夏娃夺取了他们各自原来的名字,于是他们便都成了杜威,慢慢地人们发现“他们用同一种声音说话,用同一个头脑思考”(莫里森,43)。显然,三个男孩的名字被夏娃同化后他们各自的个性也被消解。在夏娃的母性空间的暴力规训下,他们无法正常成长。除此之外,从战场归家的李子以被烧死的方式被夏娃规训。李子在战场上遭受和旁观着太多杀戮和暴力却仍然无法在社会空间中打破身份缺失状态,他选择回到“底部”。作为木匠路七号这个家庭空间中的唯一男性,他归家后自然而然会成为其中的权威者。然而,竭力建构和维护母性空间的夏娃无法容忍他夺取家庭空间控制权的潜在威胁。最终,李子被母亲夏娃以最暴力的方式活活烧死,他在家庭空间中的存在也被消除。
在男性主导的父权空间秩序下,男性在家庭空间中拥有优位权,然而,在“底部”这个异质空间里,以夏娃为代表的黑人女性积极地通过空间建构和空间改造来维护母性权威,因此,在这种具有颠覆性的对抗下黑人男性在家庭空间中的最高权威被消解。无法在社会空间中获得存在感的黑人男性在家庭空间中也难以突围,面对着来自母性力量支撑下的空间暴力,他们甚至被进一步异化被驱逐,他们的身份意识也不断被解构。
五.结论
作为一位对黑人民族的文化定位和身份意识深切关怀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深刻地了解黑人社群尤其是黑人在社会空间中不断被隔离,被规训,被湮没的状态。在她的多部作品中,黑人男性尽管处于叙述的边缘,但他们在压抑空间中的身份缺失问题也被有效地揭露出来。身份问题一直是黑人族群的核心问题,其中,随着黑人女性力量的不断崛起,黑人男性在空间中的存在也充满着冲突和变化。面对着持久的社会空间缺席,他们在家庭空间中的权威和主导也被逐渐消解。黑人男性在这种压抑空间中的生存困境也值得关注和探讨。
参考文献
[1][美]托尼·莫里森.秀拉[M].胡允恒译.北京.南海出版社,2007.
[2][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的空间[M].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3]Don Mitchell.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0.
[4]Stepo, Robert. Intimate Things in Place: A Conversation with Tono Morrison[J]. Massachusetts Review, 1977, 18, 437-489.
[5]Victoria Burrows. Whiteness and Trauma: The Mother-Daughter Knot in the. Fiction of Jean Rhys,Jamaica Kincaid and Toni Morriso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6]Wegner, Phillip E.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G] Julian Wolfreys.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P. 1994.
(作者介绍:黄依霞,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2016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