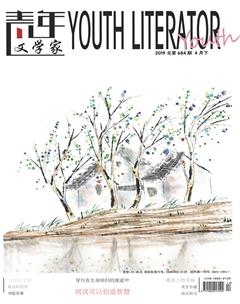论袁宗道的诗学观
摘 要:袁宗道是公安派的一位主要人物,对公安派的形成与发展,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其诗学思想中,开拓创新与保守持重互相错杂,本文着重考察其复杂多面的诗学观念。通过对袁宗道文章的分析,侧重稳健开拓的诗学观念,从文学通变观、真情与节制观、雅俗观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对袁宗道文章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深化对袁宗道诗学观的体认。
关键词:袁宗道;诗学观;稳健;开拓
作者简介:潘静雅(1995-),女,汉,江苏滨海人,扬州大学文艺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0-02
引言:
袁宗道身为家族长子、士人和士大夫,他肩有传统儒家士子的家国责任,也有心学、佛学等新思潮推动下士人向往自由创造的激情,这种矛盾同时体现在了他的诗学观念中。袁宗道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他的诗学观念体现出从传统士人矩矱中寻求创新突破的特点,在其诗学观中呈现出“稳健”和“开拓”并存的风貌。
(一)继承与发展的轻重权衡
袁中道在《石浦先生传》中描述袁宗道说:“二十岁举于乡。不第归,益喜读先秦、两汉之书。”[1]袁宗道对于古书是尽皆熟读的,但是袁宗道继承传统文学除了是爱好,更存在了一种必然性,袁宗道作为家族长子,担负着光耀门楣的责任,在古代“士农工商”理念的影响下,致仕是唯一出路,想要致仕必然要熟读儒家经典,可以说袁宗道前十几年接触的都是传统文学,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也不可能抹灭。除此之外,袁宗道还推崇白苏,他一度想要辞官归隐,便是受到他们的影响,白苏诗中表现出来的洒脱豪迈的精神,正是袁宗道求而不得的,所以他提倡学习古人的精神,汲取前人的文学观念。尽管如此,袁宗道却不是盲目拟古,而是取其长而去其短,因此,袁宗道强烈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驳斥了复古派的种种谬论,但是相对于宏道以及其他一些反對模拟文风的文人,袁宗道显得相对平和、公正。在人们将矛头指向七子的领军人物王世贞时,袁宗道却站出来为他说话:“弇州才却大,第不奈头领牵制,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时时露出,毕竟不是历下一流人。”[2]也对前后七子的文章做出了公允的评价:“且空同诸文,尚多己意,级事述情,往往逼真。”[3]袁宗道反对复古倒退,却不是盲目反古,对于有才学的人袁宗道还是会给予肯定,袁宗道真正反对的其实是那些盲目跟随前后七子的学子,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情感,这种风气需得到整改。
在继承古人精神的前提下,袁宗道也试图打破传统的束缚,提出了许多发展性的观念。首先,反对在语言上盲目拟古。因前后七子提倡“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4]他们的作品中多是佶屈聱牙的古代字语,读来晦涩难懂,所以袁宗道便在《论文》中讽刺主张拟古的文人:“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肴核之内也。”[5]批评前后七子的同时,提出“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6]的观点,认为语言与时俱进是必然趋势,不可倒行逆施。对于语言的运用,宗道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突破传统,提出了具有发展性的建议。其次,提倡内容决定形式,抨击王世贞、李攀龙为了迁就形式,不惜扭曲内容的荒唐做法:“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此一时遁辞,聊以解一二识者摹拟之嘲,而不知流毒后学,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理喻也。”[7]如果一味抄袭模拟,只知借用古人形式,套在如今的内容上,便只是不伦不类,既不能继承古文中的经典,对如今文学的发展也毫无意义。最后,提倡作家要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在作品中直抒胸臆,要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袁宗道在《论文》开篇中就提到:“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8]提出文章乃是表达心意之作,却多有辞不达意之困,需如孔子所说一般,言辞不需要太多华丽的修饰,只要能表达本意即可。由此可见,袁宗道习古却不泥古,遏制了文坛中的不正之风,帮助当时文人在继承还是发展的两难中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有助于当时文学的健康发展。
(二)真情与节制的两端取舍
袁宗道在《论文》中说道:“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9]这是说作家在进行创作实践时,必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自然流露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如若模仿抄袭,必然不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虚情假意,就如戏场中人,不过是角色的扮演者。袁宏道曾在《叙小修诗》中称赞袁中道:“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10]袁中道也提倡创作时应该流露真情实感,主张作家应独写“自家本色”,宏道也明确提出“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可见袁家三兄弟在创作观念上有相似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袁宗道受两位弟弟影响,转向性灵文学,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这与他狂放的性格相关,思维并不僵化,与时具进却不落俗套。同样受心学的影响,袁宗道一直标举学识,崇尚学理,在《论文》中说:“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拟不可得矣。”[11]他认为创作之所以能够抒发真实感情,就是因为作者具有独到的主观认识,只有具备了识别能力,学会进行思考,对创作对象和素材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才能创作出有自己风格的文章,具有自身的个性特点。袁宗道的创作流露真情,却不似宏道那般狂放恣意,任意妄为,会有意识地有所节制,这种创作中既有真情又有节制的特点可从以下两点来分析。
首先,从袁宗道的思想性格来看,他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出儒雅、平和的性格特点,在当时的热门话题“师心”还是“师古”中保持中立,可见宗道的文学思想有一定的保守成分。而且宗道推崇理学,喜欢用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来论情:“故曰致知在格物,此是初学下手吃紧功夫,千圣入门之的诀也。”[12]但是宗道推崇的“理”乃是真理,无论是评价他人还是创作作品,都要从事实出发。袁宗道不仅主张崇识尚理,还有“豁之以致知,养之以无欲”[13]的观点,这表明了宗道重德轻文的倾向,曾在《刻文中子序》中通过比较《庄子》与《文中子》的不同来提倡文学经世致用的作用。所以,袁宗道的经历导致其创作时不可能一味自由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是有意识往文学的实用方面发展。其次,从袁宗道的人生经历来看,袁宗道的一生受到了太多限制,他想要辞官受到家人阻止,想要享乐人生受到身体阻止,想要一心钻研佛学受到责任阻止,但是这些限制说到底都是他自己加在身上的,他不会不顾家人的反对,不会不顾自己身体的健康,不会不顾身上的责任,他的欲望是可以被控制的,可见其意志力之坚定。
最后,袁宗道能够分清创作与现实的区别。袁宗道在生活中追求功名利禄,可是在他作品中却是向往田园生活的。他在创作中保持情感克制,虽然看上去不如放任自然的情感来得酣畅淋漓,但是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艺术创作中审美情感的特性,他的诗文美学思想自有其合理之处,不可简单判定其保守落后。苏珊·朗格指出:“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但并不是象一个大发牢骚的政治家或是象一个正在大哭或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14]在朗格看来,审美情感与人的自然情感是有区别的,艺术家的审美情感虽来源于自然情感,以自然情感为基础,却不是自己真实的情感,这超越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意志和欲望,袁宗道的创作就是如此,掩盖了自己真实的欲望,这也可以解释為什么袁宗道欣赏真情洋溢,但是作品中的情感相对平和克制,确实别有一番特色。
这种创作时的真情与节制与公安派的整体方向不相一致,也与当时主流的文学革新运动相背离,尤其在公安末流那里,将直抒胸臆简单化,堕落为情感的粗鄙化。袁宗道能够力排众议,坚持己见,自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三)雅与俗的毁誉之间
明中叶后文学呈现新的风貌,描写市民的现实生活,表现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情感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在戏曲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汤显祖主张“唯情说”,而三袁与汤显祖交好,他们在与汤显祖的书信交往中表示了对其文艺观的认同。三袁也深受李贽的影响,李贽向传统儒学发出挑战,对于当时被视为俗文学的戏曲、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袁氏三兄弟中以袁宏道最为锋芒毕露,无所顾忌地对于传统文学进行了批判,对通俗文学推崇备至,而宗道同样受自己“稳实”性格的影响,并不能完全抛弃儒学正统,但他也试图突破传统文学空间的限制。例如《读论语》首句:“凡作于意用功夫时,真妄交争,理欲相乘,有照管有克治,有打点有考究等,俱费力生硬,不相谙习,厌苦不暇,何‘悦之有?时习之,十二时中,语默动静,相安相忘,不知不觉,妥妥贴贴,即此是悦。”[15]宗道对“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中的“学”和“悦”做出了不一样的解释,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局限,用新的学术思维来阐释传统文学,为公安派其他学者反传统的理论埋下伏笔。而且袁宗道也将自己的诗文向日常生活空间拓展,游记类散文多为我们细致描绘了当时壮丽的风景,而后回到现实,常发表自己的人生感悟,如《大别山》中先是惊叹“大别山隆然若巨鳌浮水上”[16],随后感叹“岂惟不识曹,亦不识衡矣”[17],讽刺世人过于推崇君子而不顾其是否拥有真才实学。又如《江上游记》中从描绘奔腾的长江中感慨百姓屡遭水患,为此忧心不已。宗道亦常常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作序,如《唐医序》、《李母寿序》、《顾使君考绩序》等,赠序、祭文、游记、尺牍在袁宗道的作品中占有一定分量,他将朋友逸事、山水风光、逝者恩德皆纪录在文中,虽是寻常琐事,却不拘一格,独抒性灵,这些文章虽不能流芳百世,却把明代的生活展现在了我们眼前,通俗易通,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较为深远。
结语:
袁宗道稳健开拓的诗学观念,以继承为基础,以发展为根本,继承中有发展,稳健中有开拓,既不会显得突兀,又有其开拓意义。放在公安派草创阶段的语境下看,这一稳健开拓之举,为日后袁宏道等人的淋漓发挥提供了空间,他的诗学观念是公安派诗学思想早期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公安派文学革新运动的先驱,在公安派的创立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注释:
[1]袁中道:《石浦先生传》,《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58页。
[2]袁宗道:《答陶石篑》,《白苏斋类集》,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3页。
[3]袁宗道:《论文下》,《白苏斋类集》,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5页。
[4]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第343页。
[5]同注释2,第285页。
[6]袁宗道:《论文上》,《白苏斋类集》,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页。
[7]同注释6,第285页。
[8]同注释6,第283页。
[9]同注释6,第285页。
[10]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
[11]同注释6,第285页。
[12]袁宗道:《读大学》,《白苏斋类集》,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13]袁宗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白苏斋类集》,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1页。
[14]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5]袁宗道:《读论语》,《白苏斋类集》,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
[16]袁宗道:《大别山》,《白苏斋类集》,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
[17]同注释14,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