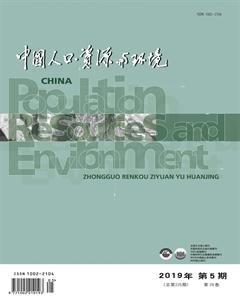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精准扶贫效果偏离的内在机理及实证分析
姚树洁 王洁菲
摘要 通过引入不对称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的经典信号博弈模型,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扶贫攻坚过程中,“普惠式”扶贫开发机制如何诱发贫困户机会主义行为。利用深度贫困的南疆四地州、六个县813户贫困家庭档案及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论证贫困户内生动力在扶贫开发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证明:①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主体和客体存在信息不对称,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诱发贫困户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使其更专注于贫困户身份的认定,不利于精准脱贫的可持续;②“短、平、快”的扶贫机制虽然能够快速帮助贫困户脱贫,但其保留效用较小,“益贫性”较低,导致贫困户对直接补贴产生持续依赖,进而失去主动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脱贫质量更低;③敏感性差异分析显示,长期受益于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陷阱”现象更为严峻,其扶贫开发对贫困户“扶志”的需求更为紧迫。以上发现是边疆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难点,也是贫困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点。新时代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扶贫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提高精准扶贫的保留效用。通过基础教育、国语教育、技能培训、外出就业指导服务等方式,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其自我发展、主动脱贫的意识,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关键词 不对称信息;精准扶贫;贫困陷阱;扶智及扶志;信号博弈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5-0165-12 DOI:10.12062/cpre.20181109
贫困治理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人心向背、国家政权稳固的政治问题。消灭贫困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更是人类文明及全球安全的重要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六年累计减少6 853万人。按照国家最新的贫困标准线计算,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 899万人减少至3 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1]。虽然中国贫困治理和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重点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国政府提出了更高标准、更高效率的精准脱贫目标。《中国农村扶贫发展纲要(2011—2020)》要求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证住房、医疗和就学)。201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对贫困家庭建档立卡,掌握全面信息,以便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实现全面精准脱贫。“三区三州”(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深度贫困地区是长期非均衡发展的产物,已然成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伴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解决刘易斯发展模式造成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和系列不平衡等问题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乃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深度贫困地区,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复杂,贫困问题与社会稳定紧密联系,是严肃的政治经济问题,精准扶贫成效不仅关系到绝對贫困的消除,更关系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尽管国家扶贫开发力度很大,持续时间漫长,但是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贫困深度仍然居高不下,已经脱贫人口因缺乏内生动力,返贫现象屡见不鲜,“贫困陷阱”(因缺乏自我发展动力与必要智力而致贫的现象)问题突出。因此,解决好边疆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是新时代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步骤。本文试图解答以下问题: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贫困户与村干部的动态博弈如何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受机会主义倾向影响的生产、生活决策对精准脱贫的影响如何;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贫困户的行为决策,在国家帮扶力度不同的贫困村,其对精准脱贫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扶贫政策措施。
姚树洁等: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精准扶贫效果偏离的内在机理及实证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 第5期1 文献回顾
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个科学动态的长效扶贫机制。世界银行曾把中国贫困治理成效归功于经济增长和公共转移支付的扩张,认为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实现了财富的二次分配,缓解了初次分配的不均衡。例如Birdsall等[2]研究发现公共社会支出在初等教育和基本医疗上的再分配既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又能高效减贫。樊丽明、解垩[3]通过对贫困脆弱性的测量,得出“输血式”的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户跨越贫困线作用显著,但是缺乏持续性和长效性。由此可见,许多学者已经在深入探究政府转移支付在扶贫攻坚中的作用。Fujii[4]运用Shapley值法将贫困进行了分解,提出政府要根据贫困源的变化相应调整扶贫政策,建立动态扶贫机制对精准帮扶的实现至关重要。贾俊雪等[5]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法”检验出小额信贷“造血式”式的扶贫机制对贫困户增收具有积极作用,而直接资本补贴效果很弱。所以当前扶贫机制应当由侧重于“社会他助”的普惠制,转向侧重于“个人努力”的差异性帮扶。杨娟等[6]发现义务教育是影响收入差距和代际流动性的主要原因,但是贫困家庭受预算约束的限制,对子女早期教育投入有限,进而高层次教育参与不足,导致非贫困家庭收入的差距持续扩大。所以教育是“扶智”的重要内容,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是消灭贫困和避免返贫困的根本保障。Ravallion等[7]将贫困程度描述分为四类,被调查者通过阅读对照自身生活水平,判断自己所处类别,其结果作为潜变量用来衡量贫困程度。Guagnano等[8]采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研究得出家庭经济特征和资本禀赋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贫困认知,进而影响主观脱贫动力。左停、杨雨鑫[9]通过梳理概念、理论和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建立主观贫困研究框架,重塑了主观贫困认知。可以看出贫困认定、研究已拓展到主观视角。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理性人(经济人)”,即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完全理性的。舒尔茨[10]认为传统的小农是“穷而有效率”的,在固定约束条件下其决策往往是一种理性选择。Robert Simon[11]也提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认为村民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必然会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从而陷入贫困。林毅夫[12]认为许多被认为不理性的行为,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向的人对小农所处环境缺乏全面了解而做出的论断,如果能设身处地看问题,则很多非理性行为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随着贫困维度的不断拓展,大量学者开始立足理性人视角,基于微观个体机会主义行为来探讨“贫困陷阱”。张新伟[13]则提出新“贫困陷阱”理论,发现贫困农户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由于选择贫困受扶要比自强脱贫成本小,并且一旦收入超过贫困线,就会失去政府帮扶,所以作为理性人,贫困户在博弈过程中会保持贫困状态,所以反贫困中的博弈现象极大降低了扶贫资源效率。傅晨、狄瑞珍[14]曾构建了一个贫困农户行为模型,分析得出贫困农户在扶贫过程中的“败德行为”,看似非理性,实则是机会主义倾向贫困户做出的理性决策。所以当前扶贫机制应当由侧重于“社会他助”的普惠制,转向侧重于“个人努力”的差异性帮扶。
上述文献对分析致贫影响因素和减贫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作用,但现有文献在分析受机会主义倾向影响的主观致贫因素对脱贫成效影响的研究乏善可陈,尤其是社会环境特殊、复杂的边疆少数民族特困地区微观视角贫困问题研究更为匮乏。这些特困地区致贫因子复杂、特殊,包括语言、文化、宗教、教育、医疗、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以及主观贫困认知等。所以在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边疆少数民族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是最关键、最困难的。
本文通过深入系统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家庭调研资料,构建信号博弈模型,探究贫困户内生动力对精准脱贫影响的理论机理。通过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贫困户机会主义行为对精准扶贫成效的影响。首先,基于新时代扶贫开发的要求,运用不对称信息动态博弈的信号博弈,构建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进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家庭堕入“贫困陷阱”,影响精准扶贫成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家庭微观数据,实证分析、论证“志”与“智”的不足对精准脱贫的影响。再次,结合Torazzi和Deaton [15]小区域用小样本分析以削弱异质性影响的主张,将样本分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贫困村与一般贫困县的贫困村,进一步剖析“贫困陷阱”在不同帮扶程度贫困村的差异性。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 理论分析框架
采用不对称信息动态博弈模型(dynamic gam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中的信号博弈,研究精准扶贫过程中“普惠式”扶贫开发机制可能助长贫困户机会主义行为,论证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对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信号博弈中,有两个参与人,假设贫困户为信号发送者的参与人1,共两种类型:客观贫困,即因个人、家庭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导致陷入贫困(θ=θo)和主观贫困,即因主观上缺乏勤劳致富思想,懒惰导致陷入贫困(θ=θs)。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两类人群各占1/2[16]。其中θ代表贫困户识别过程中所关注的致贫因子,除了易于观测的耕地面积、人均年收入、健康状况、务工状况等,还有很重要一部分是贫困户勤劳与懒惰,这通常难以直接准确观测。假设开展扶贫工作的村干部是接收信号的参与人2,也有两种类型:γ=γp(更注重脱贫数量)和γ=γq(更注重脱贫质量)。由于贫困户会口口相传村干部的履职经历、政绩表现,这使得村干部的类型成为易于观测的公共信息。相反,贫困户因人数较多,个体思想、生产生活条件差异较大,导致村干部难以准确把握每一个贫困户的类型,即贫困户和村干部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貧困户的类型θ∈{θo,θs}不为村干部所知。村干部要考察贫困户各项基本特征(生产、生产资料,家庭人口结构,收入来源及水平等)对贫困户身份予以判定,进而给予帮扶补贴。所以二者行动有先有后,村干部能够观测到贫困户的行动,包括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是否有工作,但不能观测其类型。因为参与人的主观行动是有类别的,每个参与人的行动都传递着有关自己类型的某种信息,后行动者可以通过观察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来推断其类型或修正对其类型的先验信念,然后选择自己最优行动[17]。贫困户(先行动者)将预测到自己的行动可能被村干部(后行动者)所利用,就会设法传递出对自己最有利的信息。博弈顺序如下:
(1)第一顺序行动的参与人(贫困户)的类型,不为第二行动的参与人(村干部)所知,假设村干部对贫困户类型判断的先验概率分别为P(θo)=μ、P(θs)=1-μ,(0<μ<1)。贫困户通过观察村干部类型γ后选择发出信号,M是信号空间,包括“M1=有工作、M2=没有工作”。
(2)第二顺序行动的参与人(村干部)试图从贫困户发出的信号M中观察、获取额外信息,并根据贝叶斯法则从先验概率P(θ)得到后验概率P(θ|M),增加其贫困识别和帮扶的准确性,从而选择自己的最优行动。N是村干部的行动空间,包括“N1=认定参与人1为客观贫困户并给予较多补贴,N2=认定参与人1为主观贫困户给予较少补贴”。
(3)假设村干部与贫困户的保留效用相等,则贫困户和村干部的支付函数分别为U=Uθ+A,U=Uγ+A。A是精准扶贫的保留效用 [18]。因为扶贫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医疗、教育事业等一定能为贫困户带来正向效用。相对的,无论村干部是注重脱贫数量还是脱贫质量,国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而投资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一定会使贫困村得到不同程度发展,进而摘去“贫困村”的帽子,所以精准扶贫总是一件喜事。即总效用为:TU=Uθ+Uγ+2A。
假设客观贫困户受健康状况、劳动技能、教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等限制普遍没有工作,故其信号成本为Co=0;而主观贫困户属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是懒惰的壮劳力,为获得贫困户补助,拒绝参加工作。假设劳动收入不仅取决于单位劳动力价格水平p,劳动时间T还与扶贫开发的保留效用A相关,因为村干部加强村里劳务输出、劳动技能培训、引进工厂企业增加就业岗位产生的保留效用对村民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则工作所获得的收入成为释放信号的机会成本w(p,T,A),且w(p,T,A)/A>0,同时也将获得闲暇所带来愉悦l,所以信号成本为Cs=w(p,T,A)-l。无论何种类型贫困户都希望能够获得政府的扶贫补贴,因此对村干部的平均预期为E(γ)=1/2(N1+N2)。图1是此信号传递博弈的扩展式表达。
图1 村干部与贫困户之间不对称信息动态博弈
首先,客观贫困户必定会选择M=M2,因为客观的自身和家庭条件导致其无法谋求工作,在国家精准扶贫中获得的效用为:U(θo)=1/2(N1+N2)+A。
然后考虑主观贫困户的情况,共有两种选择,M=M1和M=M2,对应的预期效应是:
U(θs)=A+w(p,T,A)-l (M=M1)
1/2(N1+N2)+A-[w(p,T,A)-l] (M=M2)
其它条件不变,若保留效用A增加,则w(p,T,A)增加,通过比较效用大小“主观贫困”户选择M=M1,获得的效用为A+w(p,T,A)-l,参与人之间实现混同均衡。其它条件不变,若贫困户对村干部的预期1/2(N1+N2)增加,则内生动力不足的主观贫困户会选择M=M2,其在精准扶贫中获得的效用为1/2(N1+N2)+A-[w(p,T,A)-l],即通过释放不工作没有收入来源信号,以获取贫困补贴资金。而村干部为了取得良好的考核结果,结合贫困户释放的无工作信号,修正先验概率,最终在β信息集上,γ=γ1类型村干部普遍策略是给予补贴(β→N1)(如图1所示),参与人之间实现分离均衡。
PE(混同均衡):
M(θ=θo)=M2,M(θ=θs)=M1
P(θ=θo|M=M2)=μ,P(θ=θs|M=M1)=1-μ,(0<μ<1)
P为村干部的后验概率
SE(分离均衡):
M(θ=θo)=M2,M(θ=θs)=M2
P(θ=θo|M=M2)=1,P(θ=θs|M=M1)=0
P为村干部的后验概率
由上述分析可得:
命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扶贫攻坚过程中,内生动力、劳动能力不同的贫困户可以通过发出是否拥有工作以获得稳定收入的信号,改进其在精准扶贫中的自身效用。
推论1:扶贫机制带来的保留效用较大时,即扶贫机制更注重公共卫生、教育、交通建设和劳动技能培训等,产生“益贫式”发展效应,则客观贫困户通过政府兜底补贴脱贫,主观贫困户则会参加能力范围内的工作,实现收入可持续,扶贫机制发挥“扶智”与“扶志”作用,此时形成分离均衡。
推论2:扶贫机制带来的保留效应较小时,贫困户则更关注村干部的类型,进而判断村干部“普惠式”扶贫机制带来效用的平均期望,扶贫收入若大于务工的劳动报酬,则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懒于工作赚取收入,实现其贫困户身份的认定,以期望获得扶贫补贴。
3 实证模型设定与分析
3.1 样本选择
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即“2010年标准”,按照当年价格每人每年2 300元),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4 335万,比上年减少1 239万;贫困发生率4.5%,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但是贫困人口在东、中、西部的分布依然差异较大(见表1),主要因为改革开放产生的要素区域间分配差异性,导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呈现出区域内收敛、区域间发散态势,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均衡[19]。所以,西部地区依然是贫困重灾区,贫困人口占全国52%,贫困发生率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新疆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的特殊边境地区,拥有27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3个自治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共3 029个贫困村。“三区三州”国家特困地区之一的南疆四地州因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封闭、自然环境恶劣、公共服务不足、人口素质低下等原因致使扶贫工作更为棘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未来脱贫攻坚主战场是14个连片特困地区,而南疆四地州不仅是连片特困地区,更属于“三区三州”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研究更为重要。基于此,本研究瞄准“三区三州”之一的新疆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贫困村。数据来源于南疆驻村工作队入户调查数据及2016年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信息。剔除残缺值和离群值后,本文选取南疆六个村813个贫困户及其包含的3 860个家庭成员作为研究对象(见表2)。
3.2 描述性统计
由表3可以看出,样本户主“年龄”50岁以上占比高达55.4%,这一年龄段的人群接受新鲜事物愿望、能力较低,扶贫难度大。样本户主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小学”“文盲或半文盲”占比高達72.6%,侧面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贫困户思想观念传统、落后,这也是深度贫困地区存在的共性问题。
表4显示,“健康”的贫困户占总数的85.5%,但是结合“劳动技能”指标看,“丧失劳动力”占比高达25.4%,因为除了存在“患有大病”“长期慢性病”和“残疾”的户主,还存在因年龄偏大无法从事生产劳动的户主。农业生产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传统家庭经营的农业耕作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所以“普通劳动技能”贫困户占比达72.1%。813个样本家庭中,2016年未脱贫的占76.8%,已脱贫的占21.8%,依靠政策脱贫家庭120个,占“已脱贫”样本67%。但是结合致贫原因分析,不难发现虽然生产要素稀缺是致贫的主要原因,但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是致贫的重要因素,占比高达36.4%。在访谈过程中,村干部介绍“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认定主要结合贫困户是否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技能培训;是否拥有耕地但却撂荒,拒绝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是否对村里开展的劳务输出活动参与度不高等。
3.3 模型设定及研究假设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的命题及推论,本文通过一手调研微观资料实证分析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对扶贫成效的影响。在研究中“贫困陷阱”被定义为:贫困户自身获得稳定收入的能力不足,靠自己的努力主动改变贫困现状的动力不强,故而严重依赖政府直接支持和补贴实现“短暂脱贫”,但存在极大返贫风险。所以不足的“志”与有限的“智”会致使贫困户堕入“贫困陷阱”。按照前文的命题与推论,贫困户堕入“贫困陷阱”的关键在于贫困户的身份可以实现其效用诉求,因此“等、靠、要”思想直接影响到精准扶贫成效。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智”与“志”是无法直接观测到的,所以结合访谈本研究选取“致贫主观因素”“外出务工时间”作为“志”的代理变量,“户主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作为“智”的代理变量,并在模型中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资料特征”三个维度的控制变量。众所周知,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获得公共财政支出的力度更大,为了观测贫困户“智”与“志”在不同程度政府援助支持下对精准脱贫影响的差异,文章将分别建立模型,进一步讨论。
Logit公式由Luce根据IIA(Independence from Irrelevant Alternatives)首次推导得出[20],是采用以Logistic随机变量的累计分布函数为基础函数形式来施加约束,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应用广泛。Logit模型是Probit模型发展产生的,都是二元响应变量模型,不同的是Logit模型假设误差项服从Logistic分布,Probit模型假设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因为贫困与非贫困恰好是一个二元随机变量,所以Probit和Logit模型在贫困影响因子研究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朱梦冰、李实[21]在研究农村低保政策瞄准效果中,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贫困低保户、非贫困低保户(误保户)和贫困非低保护(漏保户)致贫因素的差异性。Guagnano等[8]采用广义有序的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主观贫困认知的影响。在模型进一步分析过程中,Maddala[22]通过对Logit 、Probit和MDA进行比较,提出当解释变量并非服从正态分布时,Logit模型具有明显的优势。从研究的问题来看,贫困户个体“志”与“智”的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有两种可供选择:即要么对脱贫具有显著影响,要么对脱贫没有影响。本文采用离散型的二元选择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进行实证分析,即被解释变量取0为未脱贫,取1为脱贫,所以本文采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并使用对数最大似然函数对参数进行估计。
本文从微观个体特征视角分析扶贫成效的影响因素,结合行为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理论,提出一个总的研究假设H0:微观个体特征表现越好越容易脱贫。文章将围绕这一假设对贫困户个体特征如何影响扶贫成效进行分析。在总的研究假设基础之上提出模型限制条件假设H1:个体选择偏好具有同质性。区域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一致,微观个体属性越相似则脱贫的逻辑概率分布越一致,这与Torazzi 和 Deaton[23]提出的理论相一致。他们认为不同的社会环境,如基础设施的差异、耐用品拥有与否的差异会导致贫困预测的偏差。
Logit基本模型是:yi=xijβj+εi (i=1,2…n;j=1,2…m)
(1)
εi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服从Logistic分布(Maddala),βj为待估计参数单列矩阵,xij为(1×m)单行矩阵,y所有解释变量x的线性组合。进一步用概率形式表现为:
P(y=1|xi)=F(x,β)=exp(x′β)1+exp(x′β)
(2)
式(2)中,F(x,β)是“逻辑分布”(Logistic distribution)的累积分布函数。对(1)式和(2)式进行变换,加入关键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和控制变量后,得到以发生比表示的Logit模型形式:
Zi=lnP(yi=1|xij)P(yi=0|xij)=β0+β1educationi1+β2skilli2+
β3worki3+β4motivationi4+β5controli5+εi
(3)
对于二元响应变量Logit模型,被解释变量取值范围是(0,1),yi=1表示事件发生,yi=0表示不发生;关键解释变量“education(受教育程度)”、“skill(劳动技能)”是“智”的代理变量;“work(外出务工时间)”、“motivation(致贫主观因素)”是“志”的代理变量;“control”是控制变量集,包括个体特征(户主年龄、性别、民族、健康状况、大病医疗等),家庭特征(学生占比、病患占比、家庭劳动力人数),生产资料特征(耕地面积、住宅状况、饮用水状况、与村距离等)3个维度共14个控制变量。因为Logit是一个非线性模型,所以使用最大似然法進行估计。
3.4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贫困户是否脱贫是国家扶贫机制、生产生活资料、贫困户个体特征、贫困属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根据贫困户建档立卡信息与驻村工作队入户调查数据,再结合与村第一书记和贫困户的非结构式访谈结果,探究贫困户“智”和“志”的状态对扶贫成效的影响。表5列出所有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及对应的取值描述。
3.5 检验分析及实证结果
(1)多重共线性检验。一般的,对二元Logit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需要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文章通过VIF(方差膨胀因子)检测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VIF值越大则多重共线性问题越严重。结果显示:max{VIFedu,…,VIFsta}<10,VIFmean=1.34,故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6。
(2)模型稳健性检验。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的社会科学研究中,Logit模型应用广泛、优点突出,但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回归之前需要对模型稳健性进行检验。首文献中也有验证,朱梦冰、李实[21]根据CHIP2013数据计算、识别出“贫困低保户”比“贫困非低保户”收入更低。
先,分别使用普通标准误与稳健标准误进行参数估计,发现回归结果相差不大。其次,使用OLS进行线性概率模型估计,将其回归系数与Logit 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并非系数)比较,结果也相差不大[24]。最后,将模型二中关键变量“外出务工时间”替换为“是否外出务工”,估计时均使用稳健标准误以修正异方差影响,模型三的估计结果显示除了平方后的“户主年龄”,其余代理变量和各个维度控制变量显著性和系数估计值均未发生显著变化[25]。综上说明,该模型是稳健的,考虑文章篇幅,仅报告第三种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7)。
(3)内生性讨论。因为不知道是否所有未被观察的因子都被控制,而且遗漏变量偏误会导致内生性,对于截面数据,本研究通过纳入足够多体现个体异质性的控制变量,同时剔除具有明显反向因果关系的解释变量(人均纯收入)来处理这个问题。加之Logit和Probit模型能够自然避免映射问题导致的内生性,故进一步削弱内生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采用Stata15.0软件对813个贫困户样本使用稳健标准误进行Logit回归。因为813个贫困户样本中只有3户是汉族,所以模型剔除控制变量“民族”。由于样本为截面数据,所以模型一、二、三中的Pseudo R2(由McFadden提出)统计值表示估计结果都可以接受。模型二、三回归结果显示,除了“户主年龄”的平方项以外,其余各个变量的显著性及系数估计值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证明模型整体是稳健的。为了更精准地解释“户主年龄”对贫困户脱贫概率的影响,模型二加入了“户主年龄”的平方项,并将回归结果与模型一进行对比,用以检验脱贫概率与“户主年龄”是否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
(4)实证结果分析。模型二中关键解释变量“劳动技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为贫困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劳动技能需求较低,且“技能劳动力”样本仅占总样本的3%,导致贫困户劳动技能对扶贫成效并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时间”显著为正,“致贫主观因素”显著为负,说明贫困户“智”与“志”对精准脱贫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贫困户自我贫困认知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度越高,这不仅能够打破传统生产路径依赖,拓宽增收渠道,还有利于贫困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益贫式”增长。“外出务工时间”可以直接反映贫困户是否愿意“勤劳致富”,由于传统小规模农业家庭经营的投入产出比较低,所以主动脱贫愿望强烈的贫困户选择将土地转包他人,选择兼业或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来源。根据访谈了解,正常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可达3 000元/月,其年收入相当于40亩中等耕地丰年收益,政府采购服务(公益性岗位)也可达到1 200~1 500元/月(资料来源:喀什疏勒县牙甫泉镇访谈。公益性岗位例如村小队长、保安、保洁员等,岗位人数限制较大),但是受致贫主观因素的影响,相当比例贫困户并不愿意付出劳动、不愿意走出家门寻找新的增收渠道,“等、靠、要”思想严重,贫困治理过于倚重行政力量,导致“短、平、快”的扶贫措施成为村干部的首选。在我们的样本中,“未脱贫”和“返贫”的样本占比高达78%,说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依然艰巨。成功脱贫的家庭共178户,但是“享受政策脱贫”的家庭有120户,占已脱贫家庭样本的67.4%,说明南疆少数民族特困地区的扶贫成效主要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访谈中了解到,因为国家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巨大,所以村干部对贫困县摘帽信心普遍较大,直接给与补贴的“强制性”脱贫屡见不鲜,一旦政府直接性帮扶措施中断,享受政策脱贫群体极易返贫。所以,贫困户自身改善当前生活困境动力不足会极大降低国家、社会各界组织机构扶贫资金效率。
进一步分析贫困户致贫原因可以发现,“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缺土地”“缺资金”和“缺技术”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占比分别是36.4%、25.9%、11.8%和11.0%(见图2)。可以看出,“致贫主观因素”對精准脱贫成效影响极大。致贫原因中“缺技术”占比达11%,劳动技能单一、匮乏极大地缩减了贫困户增收途径。在样本中,半兼业农户不足1%,外出务工人员不到10%,相当部分贫困户不愿外出务工,但是传统农业生产易受自然、市场因素影响,致贫风险大。所以加大“扶志”力度,建立自主脱贫帮扶机制对高质量、可持续精准脱贫意义重大。
“户主年龄”与脱贫概率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为了寻找这一转折点,研究借助Stata15.0计算了“age=60”至“age=75”,16个观测点上处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age=72”时边际效应最大,在“age=73”时边际效应下降,户主年龄大于72岁对扶贫成效具有消极影响。
3.6 显著影响因素“oddsratio”值的测算与分析
上述非线性模型回归结果中,估计量β^j并非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s),不能直接用于度量各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作用。而“机率比”(oddsratio)可以用来解释脱贫概率对各个解释变量变化的敏感程度[20]。
假设educationi变为educationi+1,记P的新值为P*,则新机率比与原机率比的比率可以用公式(4)表示。
p*/(1-p*)p/(1-p)=
exp(β0+β1educationi1+…+β5controli5)exp(β0+β1(educationi1+1)+…+β5controli5)=exp(β^i1)
(4)
图2 致贫原因
这是第i个贫困户受教育程度增加一个水平至educationi1+1所引起机率比变化的倍数。oddsratio尤其适用于解释变量至少变化一个单位(如性别、婚否等虚拟变量,年龄、子女个数等实变量)的变动解释,exp(β^j)-1表示变动幅度,如果β^j较小,则exp(β^j)-1≈β^j。
根据式(4),我们估计各个与因变量有显著相关的解释变量增加一个水平(或单位)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列于表8。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非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贫困户脱贫概率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家庭脱贫概率的2.86倍,进一步证明主观脱贫动力不足是影响脱贫效果的重要因素。其它变量,特别是“大病医疗”,“饮水状况”,“贫困属性”,“户主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儿童上学”等,也都是影响贫困户能否有效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
3.7 国家级贫困县与非国家级贫困县敏感性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消除样本异质性,以观察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与一般贫困县中微观个体特征对扶贫成效影响的差异性,我们将样本分为两组:组一,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贫困村,包括和田县依斯拉木阿瓦提乡里青托尕依村、喀什疏勒县英阿瓦提乡安居尔村和阿拉甫乡尤喀克阿拉甫村,3个村,共485户;组二,非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村,包括和田市吐沙拉乡阿拉勒巴格村、阿克苏库车县硝尔库勒艾日克村和沙雅县阿牙克库勒达希村,3个村,共328户。分别进行稳健标准误Logit回归,由表9可以看出,模型四、五部分变量显著性较模型二发生了改变,进一步分析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贫困程度越高的国家级贫困县贫困村,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扶贫成效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样本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占比高达98%,差异较小;另一方面是边疆少数民族特困地区,受历史教育政策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不仅低,而且汉语教育严重缺失,沟通交流的障碍进一步加深了封闭性。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村户主“受教育程度”显著为正,说明教育产生的保留效用与贫困村贫困深度相关,在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教育依然是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
贫困程度越高的国家级贫困县贫困村,户主“外出务工时间”“致贫主观因素”与扶贫成效有显著性关系,结合“耕地面积”对扶贫成效没有显著影响的结果分析得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贫困户更难以打破禁锢,外出务工寻找新的增收途径。所以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村扶贫攻坚不仅难在生产资料匮乏,更难在贫困户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更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当下无论是政府的转移支付,还是“一户一策”的扶贫项目大多是普惠式的,贫困户“等、靠、要”的心理导致人人有份的扶贫方式虽然公平,但缺乏激励效应。不劳而获的福利使贫困户懒于提高个人生产增收的能力,可是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对口帮扶单位扶贫资金虽然能够直接增加贫困户收入,产生立即越过贫困线的效应,但却不能形成持续增收的效应,一旦离开补贴,脱贫人群立即返回贫困,这是目前边远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工作的难点所在,也是扶贫开发与“益贫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所在。所以,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扶贫工作,必须与“扶志”及“扶智”的体制机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破解我国的“贫困陷阱”问题。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信号博弈理论模型,我们梳理了懒惰、勤劳与扶贫效用最大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当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主观贫困”与“客观贫困”会通过工作状态发出传达自身“贫困程度”的信号,精准扶贫所产生的保留效用和贫困户对村干部的预期影响了贫困户的信号策略。其次,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边疆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对精准扶贫成效的负面影响。不管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结果,都证明了贫困家庭主观脱贫意识及能力,都是影响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其它的变量,包括户主的教育水平、劳动力人数、大病医疗保险、小孩上学人数、家庭生产条件、住房条件等,也都是决定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这与其它文献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实证研究方面,在控制贫困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资料特征后,我们用“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代表贫困家庭的“智力”,用“外出务工时间”和“致贫主观因素”代表贫困家庭脱贫的“意志”。实证结果证明这两组变量对脱贫的概率都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作用。
当把整个样本分为国家级贫困县和非国家级贫困县两个子样本进行分别回归以后,我们发现,“主观致贫因素”只是在国家级贫困县的子样本中对脱贫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在另一个子样本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另外,“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时间”等变量在两个子样本中的影响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异质性。辅以访谈资料我们发现,国家级贫困县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更为严重,一方面贫困户采取博弈手段隐瞒实际工作创收能力,以获取长期补助;另一方面,因为长期依赖政府慢慢地弱化了自我脱贫意志,并产生了懒惰思想。
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保留效用越大,则贫困户劳动技能的提升、就业机会的增加、薪酬水平的提高使其更倾向于自主脱贫。相反,若保留效用较低,贫困户对村干部给予直接补贴的预期越高,则更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滋生“等、靠、要”的思想。二是差异性的人口经济社会结构,使“短、平、快”的扶贫措施极易产生强制性脱贫,传统“授人以鱼”的财政扶贫模式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过度依赖直接财政补助脱贫,但其脱贫效率难以为继,故而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需要因地制宜、因户制宜、因人制宜、因产业和收入路径制宜。
三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导致政府“输血式”转移支付产生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相矛盾,尤其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贫困户更缺乏内生动力,即使投入再多资金,也很难实现高质量、持续性的精准脱贫效果。四是教育的缺位导致边疆少数民族特困地区贫困户观念禁锢、思想落后、语言沟通不畅,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依据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扶贫先扶志,降低返贫风险。政府要实现从救济型援助方式向发展型扶贫方式转变,从普惠的政策性补贴向激励生产的扶贫项目转变。处理好公平与激励的关系,建立动态激励的长效扶贫机制是激发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杜绝短暂性脱贫的保障。扶贫的公平在于建立贫困户精准判别机制,找到最需要扶持的人,配合最恰当的帮扶措施,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做到“扶真贫”。扶贫的激励机制在于优化扶贫资金配置,对于勤劳、生产动力足的贫困户给予更多生产性帮扶,实现持续增收,产生示范效应,做到“真扶贫”。
(2)治贫先治愚,加大扶智力度,嚴防贫困代际传递,巩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严控辍学率,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为特困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积极引导村民接受农业生产技能培训,转移家庭剩余劳动力至县、市务工,拓宽收入渠道,彻底摆脱“贫困陷阱”。
(3)因势利导,提高区域发展的“益贫”效果,增加精准扶贫的保留效用。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引导举家迁移和外出务工贫困户实现撂荒耕地合理流转,整合细、碎化土地,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因势利导,结合要素结构禀赋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如特色林果业。政府牵头,引进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加大产业专用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形成主导优势产业链,借助互联网开展电商扶贫,并对进入区域的先驱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26]。营造良好生产经营氛围,充分扩大当地就业,实现区域“益贫式”经济增长,真正解决扶贫与边远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 [EB/OL].2018-09-03. 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3_1620407.html.
[2]BIRLDSALL N, LONDONO J L. Asset inequality matters: an assessment of the World Banks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2): 32-37.
[3]樊丽明,解垩.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J].经济研究,2014(8): 67-78.
[4]FUJII T. Dynamic poverty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to the Philippines[J].World development, 2017,100: 69-84.
[5]贾俊雪,秦聪,刘勇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融合的政策设计——基于农村发展扶贫项目的经验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9): 68-89.
[6]杨娟,赖德胜,邱牧远.如何通过教育缓解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5(9): 86-99.
[7]RAVALLION M, HIMELEIN K, BEEGLE K. Can subjective questions on economic welfare be trusted? evidence for three developing countries[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3, 64(4):2-38.
[8]GUAGNANO G, SANTARELLI E, SANTINI I. Can social capital affect subjective poverty in Eur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8(2): 881-907.
[9]左停,杨雨鑫.重塑贫困认知:主观贫困研究框架及其对当前中国反贫困的启示[J].贵州社会科学,2013(9): 43-49.
[10]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
[11]ROBERT S. Measuring transaction costs: an incomplete survey[J].The Ronald Coas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1947(2): 1-16.
[12]林毅夫.小农与经济理性[J].中国农村观察,1988(3): 31-33.
[13]张新伟.反贫困进程中的博弈现象与贫困陷阱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1998(9): 22-27.
[14]傅晨,狄瑞珍.贫困农户行为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0(2): 39-42.
[15]TAROZZI A,DEATON A. Using census and survey data to estimat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for small area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statistics, 2009, 91(4): 773-792.
[16]CHO I K, KREPS D M. Signaling game and stable equilibri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02(2): 179-221.
[17]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8]方丽,田传浩.筑好巢才能引好凤:农村住房投资与婚姻缔结[J].经济学:季刊,2016(2): 571-596.
[19]YAO S J, ZHANG Z Y. 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diverging clubs: a cas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3): 466-484.
[20]科林·卡梅隆,普拉温·特里维迪,著.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与应用(英文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1]朱梦冰,李实.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农村低保政策的瞄准效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9): 90-112.
[22]MADDALA G S. A perspective on the use of limited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models in accounting research[J].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1, 66(4): 788-806.
[23]TAROZZI A, DEATON A. Using census and survey data to estimat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for small area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statistics, 2009, 91(4): 773-792.
[24]陳强,著.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5]崔红志.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8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5(4): 72-80.
[26]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苏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