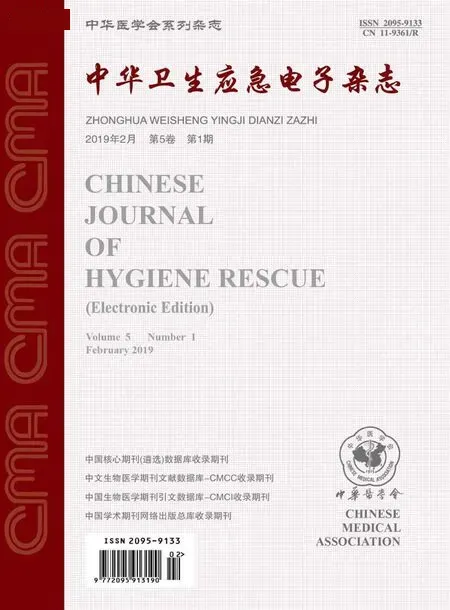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临床诊疗新进展
朱晓瓞 岳茂兴,2 郝冬琳 叶笑寒 徐君晨
运动神经元病(motor neuron disease,MND)是一组病因尚不明确,与上、下运动神经元(upper/lower motor neuron,U/LMN)选择性损伤相关的慢性进行性神经退行性疾病[1],主要累及脊髓前角细胞、脑干运动神经核和锥体束[2]。主要疾病类型包括有肌萎缩侧索硬化(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进行性肌萎缩(progressive muscular atrophy,PMA)、进行性延髓麻痹(progressive bulbar palsy,PBP)、原发性侧索硬化(primary lateral sclerosis,PLS)[3]。其特征在于隐匿性起病、进行性加重的肌肉无力以及运动神经元在电生理学检测中的退化表现。该组疾病的临床进程和预后取决于具体的疾病类型,存在较大的异质性。由于病因不明,且缺乏特异性的临床生物学诊断标志物,因此早期确诊困难,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无特效的治疗方法[4]。ALS是最常见的MND,PMA、PBP、PLS往往最终也会进展成为ALS。其患者病变同时累及多节段的UMN和LMN(ALS疾病早期症状局限于局部时可仅有LMN受损表现),以进行性加重的骨骼肌无力、萎缩、肌束颤动、延髓麻痹和锥体束征为主要临床表现,具有高致死性,无法治愈。ALS还与癌症、艾滋病、白血病和类风湿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五大绝症之一[5]。深入对该疾病的病因和治疗相关基础与临床研究对寻找快速有效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有重要意义,故现将2018年国内外ALS临床诊疗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以期为该疾病后续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一、概念与简史
ALS俗称“渐冻人症”,也被称为经典型MND(其他亚型称为变异型),是脊髓前角细胞、脑干与大脑皮层受累,以UMN和LMN变性损害并存为特征的神经系统非对称性、进行性、退行性疾病。发病年龄多在30~60岁,多数45岁以上发病,男性多于女性[6]。患者的生存期通常为3~5年,5年生存率仅为10%[7-8]。延髓起病患者的生存期更短,一般很少超过5年[9]。多数患者死于呼吸衰竭,部分患者死于营养不良和吸入性肺炎[10-11]。
这种疾病在1824年被首次报道,其症状与潜在的神经系统问题之间的联系在1869年由法国“神经学之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首先描述(因此ALS也曾被称为“Charcot病”),并由他于1874年开始使用术语“肌萎缩侧索硬化症”[12]。随着著名棒球运动员卢格里格和科学巨匠斯蒂芬霍金分别在1939年和1963年被诊断为ALS,该疾病开始被人熟知并逐渐影响了全世界[13-14]。自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以来,ALS也被称为“卢伽雷氏病(Lou Gehrig病)”[15]。在2000年丹麦举行的国际病友大会上正式确定每年的6月21日为“全球渐冻人日”,以引起世人对这种可怕疾病患者的诊疗和社会关爱的重视。2014年,“冰桶挑战赛”的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使公众对此疾病的认识得到了大幅度提高[16]。2018年5月11日,ALS已被列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5部门联合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17]。
二、易混淆的概念
国内常将“MND”“ALS”和“渐冻人”互相混用。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MND和ALS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英国、澳洲和部分欧洲地区,“MND”常被用以代替“ALS”,特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这一疾病。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以“MND”表示包含ALS在内的,存在UMN和(或)LMN损害的一组疾病。在美国、加拿大和南美地区,“ALS”则更为通用,有时也作为总称来使用。“渐冻人”一词则是为了帮助民众区分“运动神经元疾病”和“运动损伤所致疾病”,在1998年由中国台湾“渐冻人协会(中华民国运动神经元疾病病友协会)”第一届理监事会议讨论所得出的形象化名称,意指MND,并等同于ALS。目前,国际上尚未统一其命名,但世界神经病学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y,WFN)采用MND为总称、ALS为特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命名方式。此外,连枷臂综合征(FAL)、连枷腿综合征(FLS),ALS合并额颞叶痴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FTD)(ALS-FTD)以及孤立型延髓麻痹均代表不同表型的ALS亚型。
三、流行病学特征
2018年11月Lancet发表了基于1990年至2016年调查数据的全球MND疾病[调查囊括了包含ALS、脊髓性肌萎缩(spinal muscular atrophy,SMA)、遗传性痉挛性截瘫(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HSP)、PLS、PMA和假性延髓麻痹(pseudobulbar palsy)]负担结果:2016年全球共有33万例MND患者,造成平均926 090 (881 566~961 758)伤残调整生命年及平均34 325(33 051~35 364)例患者死亡,其中中国共有5.4万例MND患者(1990年至2016年的年龄标准化率增加18.6%),造成约10.7万伤残调整生命年及3 000例死亡。全球范围内全年龄组的患病率约为4.5(4.1~5.0)/10万,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增加了4.5%(3.4~5.7)。全球全年龄组年发病率为0.78(95% UI 0.71~0.86)/10万人。年龄标化患病率最高的地区集中于社会人口学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较高的国家,包括北美、澳大利亚和西欧,但亚太高SDI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患病率及发病率却低于预期。所有年龄段的男性患病率均高于女性;1990年男女年龄标准化患病率比为1.22(1.19~1.24),2016年则为1.25(1.23~1.28)。致死率在0~1岁组和70~74岁组两次达到峰值,在80~84岁时致残率稳步上升至稳定水平,且致残率远低于致死率,反映了MND的高病死率[18]。作为发病率最高的一种MND,该统计数据对评价ALS的流行病学特征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与欧洲相比,中国人群ALS的发病率、患病率以及家族性肌萎缩侧索硬化(family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fALS)病例比例均较低[19]。且我国ALS患者发病高峰年龄不仅早于欧美国家,亦早于日本:2009年由北京协和医院等国内10家单位组成的中国ALS协作组开展了多中心的登记注册研究(共纳入455名ALS患者)结果显示,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为52.4岁,男女患者的发病年龄高峰分别为55~59岁组和45~49岁组[20-21]。2010年至2015年北京市ALS的年平均发病率为0.8/10万人,男女比例为1.63:1,平均诊断年龄为54.11岁;首发症状至诊断的平均时间为14.8个月,诊断时的中位生存时间为49.4个月[22]。但目前暂无覆盖全国范围和系统性中国ALS流行病学统计数据报道。
四、典型临床表现
ALS患者的临床表现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通常与运动功能相关:局部或全身肌肉萎缩、肌束颤动、肢体无力、易疲劳、活动障碍,尿便功能障碍[23]、端坐呼吸、呼吸困难、构音障碍、咀嚼和吞咽困难、饮食呛咳、流涎等症状,以及腱反射亢进、病理征阳性、肌张力增高、强哭强笑、肌肉强直等体征,但眼外肌一般不受影响。还可合并肌痛[24]、营养障碍[25-26]、口干、睡眠障碍[27]、睡眠呼吸暂停[28-29]、情绪障碍(焦虑、情绪不稳定)和认知与行为改变(如影响语言流畅性、决策和记忆功能)[30-31]。患者的客观感觉功能通常不受影响,但可能伴有主观感觉异常(如麻木,刺痛感和温度觉减退等)[6,32]。5%~15%ALS患者表现有FTD[33-34]。其他较为少见的临床表现还包括眼球运动异常、锥体外系异常(动作迟缓、肌肉僵直)、共济失调等[35]。
五、ALS的病因及研究新进展
5%~10%的ALS患者与家族遗传有关,被称为fALS[36];其余90%~95% ALS患者没有明确的致病相关危险因素也无家族史,发病原因尚不清楚,为散发性肌萎缩侧索硬化症(scattered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sALS)。研究表明,sALS的发病原因也与遗传相关:sALS的兄弟姐妹发生ALS的风险为0.5%,其后代发生ALS的风险为1%;到85岁时,与无遗传背景的人群相比,sALS的兄弟姐妹发现ALS的风险增加了8倍[37]。除此之外,普遍认为sALS的发病还与神经炎性反应、自由基诱导的氧化应激、兴奋性氨基酸毒性、神经营养因子缺乏、异常蛋白聚集、细胞凋亡、钙超载、线粒体功能障碍、轴突运输受损、中毒、病毒、环境、创伤等相关[38-40],并提出了多种病因学说[41]。2018年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仍为遗传学病因,自然环境、生活行为习惯等流行性病学分析也是较为集中的研究方向,研究多聚焦于分子和细胞致病机制。
(一)遗传性病因
一直以来,遗传性致病因素都是ALS相关研究的热点方向。ALS的致病基因遗传方式遵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和X染色体连锁遗传,但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最为常见[42]。目前ALS相关的致病基因已有33种被定位(http://alsod.iop.kcl.ac.uk/Als/index.aspx),患者可因其中的任何一种基因异常致病,且根据致病基因的不同可分为不同亚型,临床表型也不相同[43-44]。25%~40%的fALS由C9orf72基因缺陷引起,其他突变基因还包括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Cu/Zn superoxide dismutase,SOD l)、肉瘤融合蛋白(FUS)与反式激活反应-DNA结合蛋白(TAR DNA binding protein,TARDBP)、Alsin、SETX、SPG11、囊泡相关膜蛋白相关蛋白B(vesicle-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associated protein B,VAPB)、血管生成素、TDP-43、FIG4、视神经蛋白(OPTN)、ATXN2、VCP、UBQLN2、SIGMAR1、CHMP2B、PFN1、ERBB4、HNRNPA1、MATR3、CHCHD10、TBK1、SQSTM1、UNC13A、DAO、DCTN1、NEFH、PRPH、TAF15、SPAST、ELP3、LMNB1等[42,45-53]。SOD1、TARDBP、C9orf72、SQSTM1、OPTN、TBK1等fALS致病基因也已在部分sALS患者中被筛查检出[54-60]。随着研究的深入,已被定位基因的新突变形式和新致病基因的相关报道始终在不断持续更新中。如最早发现且研究最多的一种fALS致病基因SOD1已报道了183种突变类型,在中国fALS人群中的研究已有19种SOD1基因突变、17个错义突变、1个插入突变和1个缺失突变被报道[43]。日本人群fALS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在HNRNPA1、TBK1和VCP中发现的新突变[61]。ARPP21[62]、ZNF512B[63]等均可能成为ALS候选致病基因。SETX基因突变可能是中国人群部分sALS患者的病因之一[64]。
ALS的遗传性病因主要与多基因致病有关,为多个罕见变异协同作用致病,最常见的遗传变异为缺失。可以通过TDP-43、FUS、ATXN2、TAF15、EWSR1、hnRNPA1、hnRNPA2/B1、MATR3和TIA1等编码RNA结合蛋白(RNA binding proteins,RBPs)基因的突变,使RNA代谢失调,RBPs胞内定位错误、应激颗粒动力学功能障碍以及突变体聚集倾向增加发挥ALS致病作用[65]。也可通过改变细胞或蛋白功能而致病:TDP-43突变介导的树突棘密度形态学改变可能是ALS的早期损害[62]。Fus缺失不足以导致运动神经元变性,但胞浆内Fus错位可触发运动神经元丢失以及运动神经元和邻近细胞的毒性反应而导致MND及额颞叶相关功能缺损[62]。qRT-PCR测定皮质、脑干、脊髓、肝、淋巴结、骨骼肌等ALS尸检组织中的miR-1825水平,发现其在ALS中系统性下调,且miR-1825的主要靶标提示了微管在ALS发病中的中心作用[62]。线粒体上Rab5的激活依赖于Rab5-GEF ALS2/Alsin,Alsin缺陷的ALS患者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生成的脊髓运动神经元在将Rab5重新定位到线粒体上存在缺陷,并且显示出对氧化应激的易感性增加:Alsin介导了Rab5在线粒体上的内吞机制,核内体对应激感知的缺陷对于ALS发病期间的线粒体质量控制至关重要[66]。错义形成的ALS2/Alsin无序高级结构变体可能是导致核内体定位功能和稳定性受损的原因,从而导致ALS2功能的丧失[67]。ALS的发生发展也可能与周围非神经元的基因型有关:在嵌合突变SOD1小鼠中进行的实验表明,突变表达SOD1的非神经元细胞包围的正常运动神经元表现出类似于ALS的病理学改变;而不表达突变SOD1的非神经元细胞能延迟神经元的变性并显著延长的基因突变运动神经元的存活时间[68]。
遗传因素同样影响ALS患者的病程进展:SCFD1 rs10139154与大量中国人群中ALS的风险缺乏关联,但这种变异可能调节ALS的发病年龄[69]。CHCHD10基因突变是中国人群中罕见的ALS病因,且其突变与延缓疾病进展和延长病程有关[70]。
(二)神经炎性反应
ALS中的神经变性伴随着中枢神经系统内的神经炎症反应,外周免疫细胞(特别是单核细胞)与ALS的发病机理有关[71]。fALS及突变基因携带者、sALS以及ALS-FTD的病程阶段均与患者脑脊液中的神经炎性标志物几丁质酶1(壳三糖酶)(CHIT1)、YKL-40和胶质原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有关:无症状的突变基因携带者中,三者水平无明显变化;ALS患者的脑脊液中CHIT1、YKL-40水平升高[72]。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在运动神经元毒性和ALS病程进展中均起重要作用[73]。
(三)细胞凋亡
一项以sALS、(FUS,TARDBP和SOD1)突变ALS患者为研究对象的完整转录组RNA-seq分析研究发现,共有87个mRNA在sALS患者中差异表达,受影响的基因与转录调节、免疫和凋亡途径有关[74]。C9orf72中的内含子GGGGCC(G4C2)六核苷酸重复扩增是C9ALS-FTD的最常见遗传原因,不同长度的G4C2重复可引起细胞凋亡。G4C2 RNA的重复相关非AUG(repeat-associated non-AUG,RAN)可翻译成5种二肽重复蛋白(dipeptide repeat protein,DRP):poly GA、poly GP、poly GR、poly PA和poly PR,且每种DRP在体外和体内实验中都被证实对鸡胚胎脊髓有一定毒性,其中poly GA毒性最大,其在体外细胞模型中的表达以剂量依赖性方式激活细胞程序性死亡和TDP-43裂解[75]。
(四)线粒体功能障碍
线粒体动力学及其轴突运输在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亨廷顿病和ALS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起重要作用,线粒体裂变和融合过程平衡的任何改变都会导致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生成障碍,其介导的活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可能诱导神经元中的脂质和蛋白质过氧化,造成能量缺乏并导致细胞死亡和神经传导障碍[76]。此外,通过两个离子型谷氨酸受体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ic acid,NMDA)受体和非NMDA受体介导的谷氨酸兴奋性毒性可致慢性线粒体功能抑制[77]。尽管线粒体是一种经过充分研究的调节细胞能量需求的细胞器,但其在ALS中的作用和关联细节仍需进一步观察与研究。
(五)轴突运输受损
FUS/Caz突变或过度表达可致突触线粒体减少、突触内钙离子浓度骤变、突触结合蛋白减少,特异性地破坏轴突突触小泡的运输并诱导过度兴奋[78]。ALS患者与正常对照受试者之间大约99%的轴突兴奋性变化差异可以通过被累及运动神经元细胞上所有离子通道的非选择性表达降低(离子通道和其他膜蛋白缺失)来解释:在中重度损害的神经-肌细胞中表现为动作电位阈值增加,在条件脉冲刺激下离子内流和外流减少以及更高的超兴奋性,改变幅度与损伤程度相关;严重功能损害的神经-肌肉单位中,轴突离子通道的变化还与精细运动功能的丧失相关[79]。当运动神经元功能进行性丧失时,存活的运动神经元轴突通过对去神经支配肌纤维的神经支配重建来部分保留肌肉的功能,至患者首次出现症状时,约60%~80%的运动神经元已经丢失了有效功能[79]。
(六)环境因素
ALS的环境致病因素在sALS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缺少系统和确切的论证。许多可能的环境和职业风险因素已见相关报道,如军队服役、吸烟、遭受电击和头部创伤,以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如有机溶剂、汞和铅等重金属、农药,以及蓝藻源性神经毒素β-N-甲氨基-L-丙氨酸(β-N-methylamino-L-alanine,BMAA)等][11,80-81]。
1.微量元素
有研究证明长期慢性接触无机六价硒可能会增加ALS和帕金森病的患病风险[82]。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硒参与了保护性抗氧化机制,对ALS患者具有功能保护作用[83]。血液中的铅是ALS的危险因素,但其他金属(镉、铝、汞、锰、铁、铜、锌、镁和钙)的水平暂未证实与ALS存在直接联系[83-84]。
2.生物因素
Torbick等[85]绘制了新英格兰北部面积大于8 ha(1 ha=10 000 m2)的4 117个湖泊的藻蓝蛋白浓度图,使用空间流行病学方法评估与ALS的关系发现:当平均藻蓝蛋白浓度为100 μg/L时,平均ALS风险增加约48%,蓝藻毒素增加了ALS患病的风险。饮用受污染水源和使用受污染海鲜等水产品是感染蓝藻毒素的常见途径。研究表明,自水体的气溶胶似乎也可能是蓝藻毒素暴露机制之一[86]。
3.职业暴露
一项纳入79项高质量流行病学研究的系统性文献回顾研究结果显示,过度体力劳动、化学品(特别是农药)接触,金属(特别是铅)接触等职业暴露将显著提高ALS的患病风险,其他可能的职业暴露危险因素还有电磁场工作环境和医疗保健等[87]。使用丹麦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数据对某些行业的就业者与ALS诊断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调查发现,从事农业,狩猎、林业或渔业的男性患ALS的概率增加;从事建筑工作的男性也有积极的关联,接触有毒物质的各种职业,如柴油机尾气和铅,以及与男性肌萎缩侧索硬度增加相关的剧烈体力活动;而在女性中,清洁行业就业显示出ALS保护性关联[88]。这些研究都提示关注收集有关某些体力消耗和毒物暴露的特殊职业详细信息应在未来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中予以重视。
(七)生活行为习惯
世界各地关于饮食习惯与ALS相关性的流行病学统计存在较大的差异,样本来源不同,调查的结果也不同甚至相反。吸烟、饮茶与ALS的患病风险的相关性未得到证实。饮酒可能与降低ALS患病风险相关,过量的体力活动可能与增加ALS患病风险相关[89]。有学者认为,肠道微生物群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其重要作用,细菌性生态失调可能导致不良的神经炎症状态,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ALS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增加[90]。意大利一项关于饮食习惯的研究表明,一些食物/营养素可能是ALS的危险因素和其他保护因素:咖啡和茶(OR=0.29,95% CI 0.14~0.60)、全面包(OR=0.55,95% CI 0.31~0.99)、生蔬菜(OR=0.25,95% CI 0.13~0.52)和柑橘类水果(OR=0.49,95% CI 0.25~0.97)可降低ALS的发病风险;红肉(OR=2.96,95% CI 1.46~5.99)、猪肉和加工肉类(OR=3.87,95% CI 1.86~8.07)使风险增加,高钠(OR=3.96,95% CI 1.45~10.84)、锌(OR=2.78,95% CI 1.01~7.83)和谷氨酸(OR=3.63,95% CI 1.08~12.2)饮食以及高总蛋白(OR=2.96,95% CI 1.08~8.10),尤其是高动物蛋白(OR=2.91,95% CI 1.33-6.38)同样是ALS的危险因素[91]。
(八)外伤
联合意大利、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塞尔维亚等欧盟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研究[92]显示,导致功能障碍或局限于头部的创伤史是ALS的风险因素,其中导致功能性残疾的创伤事件占主导地位且具有显著的梯度;在35~54岁发生创伤事件人群中发生ALS的风险几乎增加1倍;但损伤部位与ALS症状发作部位之间未发现关联。蒋金泰等[93]的研究也证实了头颈部外伤史是ALS的独立危险因素[OR=12.50(95% CI 1.21~129.40,P=0.03)]。
(九)疾病的播散
将ALS患者的脑脊液移植入正常成年大鼠的脑室内,可诱导大鼠出现与sALS相似的病理学改变:胱抑素C、转铁蛋白和TDP-43蛋白过表达以及细胞凋亡增加[94]。据此可提出ALS可通过脑脊液播散的推测。
六、诊断与鉴别诊断研究进展
由于ALS在疾病早期的临床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的临床表现,且缺乏特异性生物学诊断标记,因此诊断较为困难。ALS的诊断通常基于临床发现在脑干、颈段、胸段、腰骶段4个区域中存在UMN和LMN共同受累的症状和体征,结合家族史以及各种辅助检查的综合考量,多以排除法除外存在相同表现的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后予以确诊。
基于在1990年首次提出的El Escorial标准[95],ALS的诊断标准被修订了多次[96-97]。目前主要依据临床表现、体征或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所证实的侵犯范围,将诊断级别分为临床确诊、很可能和可能的ALS 3级(表1)。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于2012年提出了中国肌萎缩侧索硬化诊断诊断和治疗指南,指出ALS早期症状与多种病类似,缺乏特异的生物学确诊指标。医师常经过颈、胸、腰椎、脑部等多部位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与各科医师联合诊断,先排除其他各种可能的病变,最终结合详细的病史、细致的体检和规范的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才能确诊为ALS。并根据上述证据指示的累及范围,将ALS分为临床确诊、临床拟诊和临床可能3级[98]。见表2。

表1 Awaji-shima诊断标准与诊断分级[97]
注:ALS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UMN为上运动神经元,LMN为下运动神经元

表2 ALS诊断标准[98]
注:ALS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下列依据支持ALS诊断:一处或多处肌束震颤;肌电图提示神经源性损害;运动和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正常,但远端运动传导潜伏期可以延长,波幅降低;无传导阻滞[99]。
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特点,将ALS分为8种临床表型[9]:经典型、延髓型、FAL、FLS、锥体束体征ALS、呼吸型、单纯下运动神经元综合征、单纯上运动神经元综合征。各亚型在发病年龄、延迟诊断时间、合并FTD比率、生存期及3、5、10年生存率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伦敦ALS分期标准根据患者最近一次受累区域的不同,将其病程从发病到死亡分为5期[100]:1期为出现症状(第1区域受累);2期A为确诊时,2期B为第2区域受累;3期为第3区域受累;4期A为患者需行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percutaneous endoscopic gastrostomy,PEG),4期B为患者需要采用无创机械通气;5期为死亡或进行有创机械通气。各期平均存活时间及5 年生存率均不同。
(一)病史回顾与体格检查
1.回顾病史与家族史
隐匿性起病,病情呈进行性发展,表现为局部向多部位逐渐进展(多为非对称性发展)或局部症状进行性加重。部分患者可有类似表现的家族史(直系亲属或兄弟姐妹),应详细询问。对于有家族史的无症状患者也可通过基因检测进行筛选诊断。
2.症状与体征
(1)LMN:起于脑神经运动核和脊髓前角,止于骨骼肌的突触,其损伤主要表现为肌肉无力、萎缩和肌束颤动,常通过舌肌、面肌、咽喉肌、颈肌、四肢肌群、背肌和胸腹肌等主要肌群的体格检查和神经电生理检查获知损伤累及的节段[98]。
(2)UMN:是从皮质向下延伸到脑干或脊髓的运动神经元,其损伤主要表现为肌张力增高、腱反射亢进、阵挛、病理征阳性等,常通过检查肌张力、吸允反射、咽反射、下颏反射、掌颏反射,四肢腱反射、腹壁反射、Hoffmann征、下肢病理征,以及有无强笑强哭等假性延髓麻痹症状来判断损伤范围[98]。
(二)辅助检查
神经电生理检查结合脑和脊髓各节段的MRI仍是目前诊断ALS的主要辅助检查手段。但神经电生理检查存在偶然性和诊断滞后性,MRI缺乏诊断特异性和准确性,故仅作为诊断支持证据,而非确诊性信息。SOD1、C90rf7、TARDBP、FUS等主要致病基因以及关乎重要细胞结构和功能的CHCHD10等基因的检查可用于初筛部分幼年发病或具有家族遗传史的患者,但由于ALS多基因致病、突变种类繁多以及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致病基因有重叠的特性,以基因标记物作为诊断依据尚缺乏敏感性和特异性[101]。肺功能检查多用于呼吸肌受累程度的评估和机械通气指导应用指标。肌酸激酶、肌酐、同型半胱氨酸、超敏C反应蛋白、胱抑素C(cystatin C,CysC)和尿酸等血清学指标可能和疾病进展有关[9]。2018年,ALS辅助检查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神经电生理检查与ALS早期诊断、神经电生理检查与ALS病程评估/预测、MRI协助定位损伤部位以及血清及脑脊液中ALS生物标记物探索。
1.神经电生理检查
在ALS病程初期,患者常由于非典型临床表现而被误诊。当疑似诊断ALS或难以排除其他神经系统疾病时,早期行神经电生理检查可先于症状发现下运动神经元损害的征象[102]。神经电生理检查主要通过神经传导测定(运动神经传导、感觉神经传导以及F波)来诊断或排除周围神经疾病,通过同芯针肌电图检查以证实进行性失神经(正锐波、纤颤及束颤电位)和慢性失神经(运动单位电位时限增宽、波幅升高及多相波增多)的下运动神经元损害表现[98]。
(1)复合肌肉动作电位(compound muscle action potential,CMAP):同芯针肌电图作为判断下运动神经元损伤部位、范围及程度的重要检查,其结果的可靠性与肌电图医师的临床经验以及被检查者的配合程度有关。检查进行时的疼痛和不适也大大降低了患者的随访接受度,限制了作为病程评估的定期实施。因此,相对而言,数据收集一致度更高、客观性更强、患者配合度和接受度更高的神经传导成为了目前ALS神经电生理检查的热点。运动神经传导异常中最多见的CMAP波幅下降被认为是客观判断ALS病情严重程度的电生理指标,不同神经的CMAP波幅下降对判断颈膨大和腰膨大支配肌肉功能损害程度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改良功能评分量表(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functional rating scale-revised,ALSFRS-R)中各分项评分具有同等评估效能[103]。
(2)感觉神经传导:ALS患者的感觉神经传导通常正常,但有个别研究认为其出现轻度感觉传导异常时可表现为感觉传导波幅下降。
(3)F波:通常ALS患者的F波正常,但当肌肉明显萎缩时,相应神经可见F波出现率下降,而传导速度相对正常[104]。
(4)重复神经电刺激(repetitive nerve stimulation,RNS)波幅:ALS患者近端肌肉的RNS递减现象并不少见,但没有重症肌无力患者RNS递减幅度明显,对ALS患者伴乏力症状波动且RNS波幅递减阳性者可用于指导鉴别诊断[105]。
(5)神经生理指数(neurophysiological index,NI):NI由运动末端潜伏期(distal motor latency,DML)、CMAP和F波出现率综合确定,反映了远端运动神经功能及前角细胞兴奋性。袁宝玉等[106]分析完成单侧正中神经和尺神经检查的30例ALS患者NI与疾病进展速度之间关系,发现二者呈指数关系,且在相对晚期的疾病进展速度随着正中神经NI的减小呈指数增加,可用于ALS进展速度的评估和预后判断。
2.血清学与脑脊液检查
(1)CysC:Cys C是一种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也被称为γ-微量蛋白和γ-后球蛋白,广泛存在于各种组织的有核细胞和体液中。在人体内,脑脊液的Cys C含量高于血液。Cys C是Bunina体相关蛋白,和TDP-43共定位在路易体的透明包涵体中[107]。Nakane等[108]研究发现,ALS患者脑脊液中的Cys C水平低于多发性硬化和免疫介导的慢性多发性神经病变患者,且其水平的降低与临床UMN受累相关。Watanabe等[109]从脑室内注射重组人Cys C治疗SOD1突变ALS小鼠模型,延长了它们的存活时间。Wada等[110]通过体外实验证明Cys C与鞘脂激活蛋白原(prosaposin,PSAP)共同作用,参与了溶酶体酶调节和神经元变性。1项纳入纳入了16项研究的系统性评价和Meta分析研究显示[111],ALS患者脑脊液中的Cys C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但与若干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健康对照组比较,ALS患者的Cys C血液水平改变没有统计学意义。故而得出脑脊液中Cys C水平可能是ALS的辅助诊断生物标志物,但不是该疾病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虽然目前ALS患者脑脊液和血浆中的CysC水平变化尚存争议,多项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并不统一,但仍有研究者提出Cys C的脑脊液水平可能与疾病的严重程度预测和首发症状部位有关[101,112]。
(2)血清尿酸:血清尿酸是人体内表达丰富的天然抗氧化剂,与高血压、冠心病、肾脏疾病以及多系统萎缩、阿尔茨海默病、ALS和亨廷顿病等多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相关,与ALS的发病、自然病程时间、疾病进展速度以及生存率均表现出相关性[113]。美国的一项汇总5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病例对照研究中,纳入了319 617名提供血液样本的未诊断ALS受试者,其中275名在随访期间患有ALS,分析结果提示血浆尿酸盐的升高与ALS的风险呈中度负相关[114]。但二者间的确切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TLQP肽:TLQP肽是血管生长因子(vascular growth factor,VGF)的衍生肽,被证明可用于预防神经元细胞凋亡,TLQP-21也可通过参与新陈代谢增加静息状态下的能量消耗[115-116],TLQP-62与海马记忆巩固调节有关[117]。从疾病早期开始,TLQP肽就在ALS患者的血浆中减少(对照组的14%),并且在晚期也呈持续下降趋势(对照组的16%);与野生型小鼠相比,ALS小鼠的血浆和脊髓均在症状出现前就显示出了TLQP肽的减少(分别为约26%和70%)[118]。同样的TLQP肽下降趋势也表现在了体外实验中:在ALS成纤维细胞(对照组的31%)和用亚砷酸钠处理的小鼠运动神经元细胞系NSC-34(减少53%)中;此外,外源性TLQP-21改善细胞活力[118]。因此,在氧化应激下降低的TLQP肽可作为血液生物标志物。
(4)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病程较长和重度病情ALS患者的血清SOD、GSH-Px水平降低,且该指标的血清水平与患者的性别、年龄及起病部位无关[119]。
(5)神经丝蛋白轻链(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NFL)和磷酸化重链(phosphorylated neurofilament heavy chain,pNfH):NFL是一种结构性的神经蛋白,神经损伤后在血清及脑脊液中增高。研究者发现,NFL与ALS病程呈负相关,与疾病进展率呈正相关,且用于鉴别诊断的能力有限,但与正常健康对照组相比仍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NFL的血浆水平还可为ALS预后标志物[101]。在ALS患者脑脊液中,pNfH浓度会随着疾病进展而升高,区别于正常对照组的敏感性为97.3%,且与ALSFRS-R的下降速率呈正相关,其可作为ALS的预后标志。pNfH作为ALS的可靠生物标志物,与壳三糖苷酶(chitotriosidase,CHIT)组合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灵敏度为83.8%,特异性为91.9%)[120]。
(6)蛋白激酶CEpsilon(protein kinase C epsilon,PKCε):PKCε是引起运动神经元损伤的一个上游信号,可显著增强外周蛋白的聚集,促进星形胶质细胞中mGluR5激活的钙震动丢失,导致神经细胞凋亡,最终参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发生发展[121]。
3.基因诊断
可根据目前已定位的ALS致病基因对疑似ALS患者或由明确家族史的人群行基因检测来早期诊断ALS并做预防性干预措施。30%的幼年肌萎缩侧索硬化症(Juvenile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JALS)患者中发现了早期发病最常见的遗传决定因素——FUS变异,FUS变异体筛查将有助于发现早期发病的JALS[122]。ZNF5J2B基因中风险片段rs2275294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对评估ALS患者的预后有意义[123]:与ALS临床预后相关的ZNF512B基因片段rs2275294包括CC、CT和TT 3种基因型,C为风险等位基因,含有风险等位基因的患者(CC型+CT型)较不含风险等位基因的患者(TT型)生存率低,CC型与CT型患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意义。UNC13A中的遗传多态性rs12608932可能会改变sALS的额颞叶病变,对疾病的预后评估有一定的意义[124]。虽然尽早怀疑或确诊ALS可能无法阻止疾病的发展,但对已经诊断出患有ALS、FTD或ALS-FTD的一级或二级亲属进行基因检测必要的,这将有利于其早期诊断和防治。
4.影像学检查
颅及脊髓各节段MRI检查主要提供ALS鉴别诊断证据,同样是ALS诊断的重要辅助检查手段。枕骨大孔处的脊髓束横截面积与ALS的功能损害相关,而与全脑萎缩无关[125];MRI丘脑纵向扫描具有作为ALS中皮质功能障碍的非侵入性替代标记的潜力[126]。新的研究还提出ALS患者脑(皮质脊髓束)变性的文理分析[127]、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m,MEG)衍生的β振荡偶联[128]等MRI相关参数同样具备成为ALS诊断生物学标志物的潜力。还有有少量研究表明,采用影像学新技术[结构磁共振成像(structural MRI,sMRI)、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tensorimaging,DTI)、质子磁共振波谱、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RS-f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等[129-130]或MRI与结合其他检查手段有望在ALS疾病的早期提供诊断及病变定位依据。
(1)sMRI:主要用于研究大脑皮层局部萎缩和灰白质改变。王倩楠等[131]采集27例临床确诊ALS患者和27名健康志愿者的3D-T1W脑结构像,分别基于体素形态学(VBM)和表面形态计量学(SBM)方法对受试者的全脑结构进行分析:ALS患者大脑运动区和运动区域以外脑结构均有所改变,且BA4a区的灰质体积与患者的ALSFR-R评分呈正相关,有望作为生物学标记物用于监测病程的进展。此外,患者的灰质和白质变化也可用于ALS的病程监测[132-133]。
(2)DTI[134]:DTI依据组织的T1、T2弛豫时间和质子密度以及水分子弥散方向制图,是当前唯一的一种能有效观察和追踪脑白质纤维束的非侵入性检查方法。径向扩散率(radial diffusivity,RD)可能是检测ALS白质早期脱髓鞘的最敏感的生物标志物,RD和分数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均可作为ALS疾病严重程度评估的客观生物标志物:与健康受试者相比,非痴呆ALS患者的RD和平均扩散率(mean diffusivity,MD)升高、FA降低,主要沿皮质脊髓束和胼胝体分布;在两个半球的皮质脊髓束中,RD的增加比FA的减少更为明显;在受试患者左侧皮质脊髓束中,ALSFRS-R与FA呈正相关,与RD呈负相关;皮质脊髓束可能是非痴呆ALS中受影响最大的脑区。对于那些具有认知障碍的患者,MRI和认知分期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易于应用的认知功能障碍快速筛查手段[135]。DTI结合磁共振图像标记用于捕获舌肌在活动中的肌纤维结构,并首次提出了舌肌纤维收缩动态图谱绘制概念,为针对存在舌肌肉萎缩、构音障碍和吞咽功能的ALS患者进行评价和原因分析创造了可能[136]。
(3)RS-fMRI:沈东超等[137]应用分数低频振幅(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fALFF)和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法探索我国ALS-FTD患者的静息态脑功能特征的研究后发现,ALS-FTD患者存在运动区外(前额叶、前扣带回)的激活减低,且在对灰质体积进行校正后此种差异仍然存在。从而得出RS-fMRI有助于探索ALS认知功能障碍发生发展的病理生理机制的结论。
(4)全细胞3D图像中的细胞器形态评估:线粒体、高尔基体和内质网的细胞器形态的紊乱是疾病早期的表现,但对细胞器形态的可靠和定量检测十分困难且耗时多。Lautenschläger等[138]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机视觉算法,用于评估全细胞3D图像中的细胞器形态,可对细胞器结构进行定量描述(包括片段的总数和长度,细胞和胞核的面积/体积以及裂隙和分形等新纹理参数)。并应用于人类fALS转基因小鼠模型G93A hSOD1小鼠体外培养的运动神经元,证实了线粒体的网络碎裂、区段的数量增加和线粒体长度减少,管状线粒体数量减少和线粒体片段数量增加等改变,实现了再客观评估疾病相关的细胞器表型的同时,降低了检查者偏倚,可能有助于治疗新策略的细胞水平评估。
(5)高分辨率超声:高分辨率超声是一种新型的非侵入性工具,越来越多地用于筛查、诊断和辅助治疗疑似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也被用作神经肌肉疾病综合评估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需要整合临床评估、神经电生理检查、神经影像学检查、病理学和实验室辅助检查(如靶向基因检测)结果,通过准确描绘异常的特定区域或改变直接观察自发性肌肉运动以及监测其他相关病理,来补充临床和神经电生理学诊断。在ALS的无临床症状期或肌电图未见阳性发现时能增加10%~30%的阳性检出率,提高诊断效能[139-140]。ALS患者常见的超声异常为中等强度回波强度(echo intensity,EI)(↑↑)和肌肉厚度(muscle thickness,MT)严重下降(↓↓↓),最显著的特征是肌束震颤且EI异常(增加)多于萎缩[141]。下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筛查通常包括四肢骨骼肌、腹直肌、胸锁乳突肌、斜方肌、咬肌、第一背骨间肌和颏下肌,每块肌肉的扫描时间长达60 s[140]。ALS颅区的超声肌束震颤检检出率与肌电图相似,但超声检查更容易多次发现频繁的肌束震颤[140]。
5.其他生物学标志物
来源于脊髓V0中间神经元的轴突投射到α-运动神经元细胞体和树突近端的乙酰胆碱能C型突触终扣(C-bouton)控制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nAChR、P2X7受体、m2 受体、SK和Kv2.1离子通道、Sig-1R和NRG1等多种突触前后蛋白调控C-bouton的结构及功能,在MND的病理改变、功能异常以及运动神经元的电活动受损中起重要作用,影响肌肉的收缩特性。其中Sig-1R和NRG1等蛋白是参与ALS发生发展的重要因子[142]。
(三)鉴别诊断
ALS起病隐匿,缺乏特异性生物学标志物,早期临床表现与多种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相似,极易发生误诊和延迟诊断:从首发症状到明确诊断的延迟时间通常为10~18个月,约5%~8%的患者被误诊[143-145]。因此,应结合上述诊断标准和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实验室辅助检查来排除易混淆的疾病。见表3。

表3 ALS的鉴别诊断疾病[146]

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髓内胶质瘤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伴有脑脊液中的副蛋白血症和(或)寡克隆区带肺尖肿瘤综合征(Pancoast肿瘤综合征)伴有前角细胞受累的副肿瘤性脑脊髓炎僵人综合征物理损伤电击神经元病血管性疾病辐射诱发的神经丛病和(或)脊髓病动静脉畸形延髓内侧综合征中风血管炎其他神经系统疾病西太平洋非典型MND/ALS(关岛,新几内亚,日本纪伊半岛)加勒比非典型MND-痴呆-PSP(瓜德罗普岛)青少年发病的马德拉斯型MND/ALS(印度南部)伴有MND/ALS的额颞叶痴呆(包括伴有肌萎缩的皮克病)多系统萎缩橄榄脑桥小脑萎缩综合征原发性侧索硬化(与ALS无关的亚型)进行性脑脊髓炎伴僵直进行性核上性麻痹遗传性痉挛性截瘫(有远端肌萎缩的亚型)进行性脊髓性肌萎缩(与ALS无关的亚型)延髓性肌肉萎缩伴或不伴动力蛋白激活蛋白或雄激素受体突变脊髓性肌萎缩Ⅰ- ⅣBrown-Vialetto-van Laere综合征(早发性延髓和脊髓性ALS伴感音神经性耳聋)Fazio-Londe综合征(婴儿进行性延髓麻痹)Harper-Young综合征(喉和远端脊髓性肌萎缩)单纯性散发性脊髓性肌萎缩(良性局灶性肌萎缩,包括平山病)以运动症状为主的多神经性病变(如遗传性运动感觉神经病2型、遗传性运动神经病5型)家族性淀粉样多发性神经病变良性的自发性收缩肌纤维颤搐
注:ALS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MND为运动神经元病,CIDP为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HIV-1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TLV-1为人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
(四)病情评估
目前尚无针对与ALS的特异性病情跟踪及评估指标。ASLFRS-R是目前最常见的自我报告式功能丢失量表,其随病程进展的下降率是患者功能减退和死亡率最重要的预测指标,评分共分为12项,满分为48分[147-150]。ALSFRS-R随时间的变化,即疾病进展率(δALSFRS-R/△FS)被证实可以预测患者的生存情况[151-152],计算公式为:疾病进展率=(48-ALSFRS-R)/病程(月)[8,153]。其他常用功能缺失评估量表还包括EQ-5D、生活质量量表(amyotrophic lateralsclerosis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40,ALSAQ-40)等。快速词汇测验(rapid verbal retrieval,RVR)、韦氏成人智力测验(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WAIS)数字广度测验和额叶功能评定表(frontal assessment battery,FAB)评分可用于执行功能损害的评估[154]。此外,肺功能检查被认为是重要的生存率评价指标,其中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及一秒率(用力呼气一秒量FEV1/FVC)是提示呼吸机受累的重要依据[9]。
七、临床治疗及研究新进展
目前仍无针对ALS的特效治愈方法,大多数干预措施都是针对症状进行的处理和管理,多学科联合的模式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和护理效果。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用于ALS的药物为利鲁唑和依达拉奉。据调查,目前多数ALS患者在得到疑似或确定诊断后会选择使用上述两种药物来控制病情的进展。此外,辅酶Q10(coenzyme Q10,EQ10)、维生素E、复合B族维生素、甲钴胺、神经生长因子等抗氧化和营养神经药物也是常见的临床用药,但均未见明显的疾病预后改善效果。对于功能严重损害的晚期患者,机械通气和PEG仍是必要的支持治疗手段。国内患者还会选择采用中医药方法来改善症状和延缓病情发展。干细胞治疗、基因干预和多种研发新药仍处于研究阶段。
(一)药物治疗[155]
1.利鲁唑(Riluzole)
1995年,利鲁唑(50 mg 口服 2次/d)成为美国FDA批准用于ALS的第一种药物,该药通过尚未充分了解的机制干扰谷氨酸的突触前释放、摄取和突触后作用,降低兴奋性氨基酸——谷氨酸的水平、稳定电压门控钠通道的非激活状态,来减少对运动神经元的损害,临床试验表明可延长患者2~3个月的存活时间,特别是在延髓形式起病的患者中作用明显,但不会逆转已经对运动神经元造成的损害[38,98]。是目前我国ALS患者治疗的临床一线用药。最新的体外和体内研究揭示了其新的作用机制[156]:通过选择性降低“即刻释放小泡”(在病理生理刺激中首先被释放的小泡)的大小来降低谷氨酸能传递的效能,该作用与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依赖性Munc18-1磷酸化的抑制相关。老年患者、BMI偏大者及ALSFRS功能评分得分较高者服用利鲁唑的疗效更好;长期服用利鲁唑(诊断后服用>6个月,累计服药剂量>16 800 mg)可有效改善预后,而短期使用对生存率影响不大[157]。除ALS外,利鲁唑还被认为具有结肠癌、肺癌、黑素瘤、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一些抗肿瘤特性[158]。
作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一线治疗用药,与利鲁唑联合治疗的辅助用药也被进行了大量研究,以期增强利鲁唑治疗的获益或减轻副反应。(1)纳米结核蛋白:伊朗研究者取其抗炎和抗氧化作用进行相关研究,其提高利鲁唑治疗患者存活率和改善延髓症状的疗效和用药安全性已被证实[159]。(2)吡格列酮:噻唑烷二酮类胰岛素增敏剂,是高选择性的激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γ,PPAR-γ)的活化剂,可调节许多控制葡萄糖及脂类代谢的胰岛素相关基因的转录。3个独立小组报告了吡格列酮对ALS小鼠的有益作用,且作用机理与炎症介质水平的降低有关[160-162]。故利用其抗炎、增加体重的作用,被用作增加力如太(利鲁唑的商品名)疗效的附加药物进行了1项多中心分层平行组安慰剂对照的Ⅱ期临床试验(NCT00690118)[163],结果显示吡格列酮联合力如太治疗组的患者死亡危险增加了21%,与单独使用力如太的治疗组比较,患者的存活率、ALSFRS-R评分降低的程度及速度、生活质量和肺活量降低等情况均不受吡格列酮的影响,也无法改善无创通气率(吡格列酮:20.2%,安慰剂:26.6%)和气管切开率(吡格列酮:6.4%,安慰剂:4.6%)。(3)Mecasin:Mecasin具有神经保护和抗神经炎症作用,1项三盲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Ⅱ-A期研究已在韩国国家临床试验登记处登记实施(KCT0001984)。该试验纳入36例ALS患者进行利鲁唑联合Mecasin(1.6 g和2.4 g )的疗效、最佳剂量和安全性评估。患者将在经过12周治疗后,使用韩国版ALSFRS-R评分、简略健康调查-8(Short Form Health Survey-8)、医学研究委员会量表(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Scale)、疼痛视觉模拟量表、抑郁症汉密尔顿评定量表、疲劳严重程度量表、患者总体变化印象、肺功能测试(1秒用力呼气量及其与用力肺活量)、肌酸激酶和体重来总结评估结果[164]。
2.依达拉奉(Edaravone)
由于氧化应激被认为是ALS发病和进展的促进因素,消除自由基的药物可以保护运动神经元免受可能由自由基和氧化应激引起的损伤。依达拉奉是一种自由基清除抗氧化剂,于距利鲁唑获批后的22年(2017年5月)成为第二种被美国FDA批准用于ALS的治疗药物[165]。静脉滴注依达拉奉60 mg/d(30 mg依达拉奉溶于100 mL 溶剂静脉滴注,2次/d,每次输液时间为30 min。初始治疗周期为连续每日给药14 d,然后停药14 d;随后的治疗周期为在14 d内用药10 d,然后停药14 d)可减缓ALS患者33%的身体功能丧失速度。关于依达拉奉对ALS患者长期影响的回顾性研究证实ALSFRS-R评分低于基线水平,对6个月和12个月后的血清肌酐水平有显着改善,且依达拉奉组ALS患者的存活率显著提高[166]。它适用于病情较轻、FVC>80%预计值、病程<2年的患者。为减少静脉给药途径给治疗带来的不便,增加患者用药医从性,30 mg舌下含服片剂已被研发,但仍需进一步评估其生物利用度[167]。依达拉奉治疗ALS的获益和安全性尚存争议,现已有部分研究就此进行了验证:与未接受依达拉奉治疗的ALS患者以及安慰剂ALS患者组相比,24周治疗组间的ALSFRS-R评分的存在差异;不良事件或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8]。但在使用期间仍应定期复查肝肾功能损害情况并及时干预。
3.马赛替尼(Masitinib)
马赛替尼是口服给药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选择性抑制酪氨酸激酶受体集落刺激因子1R(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1R,CSF-1R)。在体外研究中证实能预防CSF诱导的症状性SOD1(G93A)脊髓的小胶质细胞增殖、细胞迁移和炎症介质表达;降低脊髓退化中异常神经胶质细胞、小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和运动神经元病理的数量,延长t瘫痪后40%存活时间。SOD1G93A大鼠模型研究中,马赛替尼诱导的肥大细胞减少导致神经肌肉接头去神经支配减少35%并且减少运动功能损害,巨噬细胞浸润正常化;在晚期麻痹大鼠中观察到施万细胞和毛细血管网络的退行性变化[169]。但也有个案报道显示马赛替尼治疗ALS时会引起急性重症肝炎[170]。马赛替尼用于ALS的治疗已进行Ⅱ/Ⅲ期临床试验,但目前暂未见相关文献报道。
4.替拉生替(Tirasemtiv)
替拉生替是一种快速骨骼肌肌钙蛋白激活剂,可使肌节对钙敏感,放大肌肉对神经肌肉信号输入的反应,提高肌肉收缩效率。在动物模型(B6SJL-SOD1 G93A)中显现出了增加小鼠前肢握力、网格悬挂时间、旋棒能力、隔膜力和潮气量的疗效[171]。对ALS患者功能和力量的改善效果呈药物浓度依赖性[172]。虽然该药物在ALS患者治疗中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得到了证实[173],但在后续进行的纳入700多例ALS患者的Ⅲ期临床试验(NCT02496767)[174-175]中并未达到主要终点或任何次要重点:与安慰剂组相比,在24周的时间内未见静态肺活量、肌力和功能均未见明显改善。
5.L-丝氨酸
2013年以来,已经有体外和体内研究报道L-丝氨酸具有针对于BMAA毒性的神经保护作用,可能成为ALS的潜在疗法[176-178],并提出其在体外和体内通过上调CHOP基因而不激活未折叠蛋白反应产生神经保护作用,表明L-丝氨酸可能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具有神经保护作用[179]。在一项纳入20例ALS患者(2次/d 0.5至15 g)的口服L-丝氨酸I期临床试验中[80],2例ALS患者因胃肠道副作用退出,3例患者死亡;余治疗患者的ALSFRS-R显示出与剂量相关的进展速率降低(斜率降低34%,P=0.044)。
6.瑞替加滨(Retigabine)
神经元钾离子通道开放剂,可增强神经元细胞中γ-氨基丁酸所诱导的电流,降低神经元兴奋性,临床上用于成人癫痫部分发作的辅助治疗。与利鲁唑组和安慰剂组相比,瑞替加滨显着降低了ALS患者神经元兴奋性实验的强度-持续时间常数(9.2%)和2 ms的不应期,提示其可急性逆转既往的异常变量,为评估其对疾病进展和生存影响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180]。
7.PDI蛋白家族
蛋白质二硫化物异构酶(protein disulphide isomerase,PDI)A1对表达SOD1突变体的神经元细胞中的内质网应激和细胞凋亡具有保护作用。PDI家族成员内质网蛋白57(endoplasmic reticulumprotein 57,ERp57)的过表达抑制包涵体形成、内质网应激、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功能障碍和细胞凋亡,并抑制原代皮质神经元中SOD1突变包涵体和细胞凋亡的形成;而ERp57表达的沉默增强SOD1突变包涵体形成、内质网应激和毒性[181]。而其作用机制与TDP-43的错误折叠有关。
8.ALS-内皮疗法(ALS-Endotherapia,GEMALS)
GEMALS由维生素、氨基酸和脂肪酸等小分子与多聚赖氨酸合成,是用于自身免疫、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增殖性疾病等慢性病的治疗新策略。基础研究证实对ALS大鼠(SOD1)模型起到延缓病情进展、延长生存期的作用[182]。研究者评估了31例ALS患者的应用疗效:在83.87%的患者中观察到了疾病进展的减缓,并且使患者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38个月;呼吸、行走、流涎、言语、吞咽和书写等运动功能也有所改善[183]。但结果还需在进一步的随机盲法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
9.辅酶Q10(coenzyme Q10,CoQ10)
CoQ10也称为泛醌,位于线粒体的内膜中,是电子传递链的组成部分,在ATP合成中起主要作用。该药物为亲脂性自由基的清除抗氧化剂,可保护线粒体和脂质膜免受氧化磷酸化过程中产生的ROS的影响。主要用于轻中度心力衰竭的辅助治疗,也用于肝炎、癌症的辅助治疗,在ALS转基因小鼠和ALS以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试验中显示出一定的治疗前景。但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期临床试验中,并未表现出由于对照组的ALSFRS-R改善[184]。但由于疾病的难治性,目前在国内仍将该药物作为辅助性治疗手段用于ALS患者的临床治疗中。
10.丁苯酞与甲钴胺
丁苯酞(dl-3n-butylpthalide,NBP)是我国自研的一种多靶点治疗急性脑缺血的药物,在局部脑缺血的动物模型中通过抑制线粒体损伤和神经凋亡,提升脑血流,减小梗死体积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在动物研究中证实有推迟发病时间、提高运动协调能力、延长生存期、增加细胞质内Nrf2、HO-1的表达等作用[185-186]。与利鲁唑联用则能获得更好的延长生存期疗效[187]。其作用机理可能是通过减缓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和腓肠肌运动单位的丢失,调节铁代谢来实现对ALS的神经保护作用的[188]。治疗ALS时甲钴胺与丁苯酞具有协同作用,可以显著增加丁苯酞治疗效果,降低丁苯酞的起效剂量,减少其用药量,长期应用降低其不良反应的发生[189]。但其应用还须通过更多的临床试验来加以论证。
(二)药物组合物及滋痿膏中西医结合疗法
岳茂兴等[190-192]将一种促进神经损伤修复的药物组合物(精氨酸1.5~5 g,异亮氨酸1.5~5 g,亮氨酸2.5~7.5 g,赖氨酸1.5~5 g,蛋氨酸0.25~1.5 g,苯丙氨酸0.25~1.5 g,苏氨酸1.5~5 g,色氨酸0.25~1.5 g,缬氨酸2.5~7.5 g,组氨酸1.5~4 g,甘氨酸1.5~4 g,丙氨酸1.5~5 g,脯氨酸1.5~4 g,天冬酰胺0.05~1.5 g,半胱氨酸0.05~1.5 g,谷氨酸1.5~5 g,丝氨酸0.25~2.5 g,酪氨酸0.05~1.5 g,L~鸟氨酸0.25~4 g,天冬氨酸0.5~2.5 g;维生素B11~2 mg,维生素B21~2 mg,维生素B310~20 mg,维生素B63~10 g;维生素C 1~3 g。药物的使用种类和剂量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方案制定)。配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个体化中药滋痿膏(主要成分:葛根、骨碎补、益智仁、山茱萸、柏子仁、五味子、地黄、玄参、丹参、麦冬、桔梗、防风、黄芪、黄芩、枳壳、赤芍、甘草等,国家发明专利号:ZL2011 1 0157186·8)用于治疗ALS和MND患者取得一定效果。部分ALS患者临床症状得到改善;治疗6个月,27.3%的患者ALSFRS-R评分上升,18.2%评分不变,且有72.7%的患者疾病进展率较治疗前下降;随访至首次治疗后1年,患者的ALSFRS-R评分上升、不变和下降的占比分别为18.2%、4.5%和77.3%,疾病进展率低于治疗前降低[(0.584±0.372)分/月比(0.716±0.440)分/月,t=2.706,P<0.05][190,193]。
该组合物的使用方法为:将各组分配制在1个三升输液袋内进行静脉滴注,1次/d,28 d为1个疗程,停药2周后行第2个疗程,依此类推,持续治疗时间≥4个疗程或6个月。于饭后2 h噙化或冲服滋痿膏,2次/d,吞咽困难患者可从鼻饲管(胃造瘘管)内注入。
研发者根据其经验总结得出“生命之源在于新陈代谢,疾病之因在于代谢紊乱,代谢之本在于底物、辅酶与强劲动能的支撑”的理论基础,通过该中西医结合创新疗法为患者提供机体新陈代谢的底物、辅酶与强劲的动能,从整体上促进人体血液循环、酶代谢、氨基酸代谢及免疫功能逐步恢复,使受损的脑、脊髓等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达到改善患者病情与临床症状,扼止危重状态进展并挽救生命的目的:一方面组合物中含有各种各样人体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氨基酸与丰富的B族维生素,在为机体提供合成蛋白质、核酸、激素、抗体、肌酸等含氮物质的重要代谢底物与强劲动能的同时,还能够将产生的有害二氧化碳及氨通过鸟氨酸循环代谢排出体外,从而使得肝内酶代谢逐步恢复;足够剂量的维生素B6应用,确保了肝酶代谢相关辅酶的充足供应和人体生命代谢活动被有效激活,其解毒排毒功效也起到一定增益。巧妙搭配的创新疗法在人体新陈代谢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使患者受损的脑、脊髓等功能得到一定程度地修复,增强了神经元的存活能力,从而改善患者的病情与临床症状,扼止危重状态的进展。另一方面中药滋痿膏可通过补益脾肝肾、扶元起痿、益气温阳、疏肝理气、养荣生肌、强骨抗痿、健脾祛湿、益气活血、双向免疫调节来改善患者的症状与病情。该疗法具有多途径、多靶点、多环节发挥治疗作用的特点,二者互补,临床证实可使疗效提高[190,192]。在综合治疗和全面护理的基础上实施该中西医结合治疗创新方法能取得更为理想的疗效[194-195]。但此疗法的确切作用机制还须被深入研究,重复进行大样本的临床试验以验证疗效也是必要的。
(三)细胞因子与反义寡核苷酸(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ASO)
ALS与中枢神经系统中神经营养因子的减少密切相关。目前基于腺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AAV)的SOD1和C9orf72重复扩增相关疾病的ASO疗法也在有关基础研究的推动下有了长足发展[196]。利用ASO进行内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补充和基因治疗将成为ALS病因治疗的一条新途径。
1.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 -1,IGF-1)
IGF-1具有强烈的保护线粒体免于凋亡的作用,并在ALS小鼠和细胞模型中上调线粒体自噬,这一研究结果提示“特异性保护线粒体功能”将有希望成为治疗ALS的新思路[197]。通过肌内注射和髓内注射途径转染编码IGF-1载体的方法在ALS小鼠模型中体现出了一定的治疗效果。通过静脉转染自体互补腺病毒(scAAV)载体途径开启了无创转染补充IGF-1的新思路[198],其相关动物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能减少90日龄SOD1-G93A ALS小鼠的运动神经元死亡和脊神经腹根部的髓鞘病变,延长SOD1-G93A小鼠的寿命。该项实验还发现IGF-1可通过下调p38和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N-terminal kinase,JNK)磷酸化来抑制脊髓中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JNK通路;通过上调凋亡抑制剂Bcl-2和下调凋亡启动子Bax、caspase 3和caspase 9来调控神经元细胞凋亡。此外,IGF-1处理后,促炎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减少。
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鞘内注射scAAV9-VEGF可减少ALS小鼠模型的小胶质细胞的数量并抑制了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炎症反应,同时可抑制巨噬细胞侵入外周神经系统,包括腹神经根,坐骨神经和肌肉[199]。
(四)干细胞
一些关于动物和I期临床试验研究的报道表明,将干细胞(干细胞来源主要包括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胚胎干细胞和神经干细胞)通过鞘内注射(一般为颈膨大附近或腰椎穿刺入路)或直接注射到脊髓腹侧角中可使神经细胞轴突和神经元髓鞘的再生,并可能成为治疗ALS的一条有效途径[200-201]。通过替代丢失的细胞、增强幸存神经元的存活、移植细胞旁分泌(生长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等)和基因修饰等方式达到损伤治疗的作用[202-203]。但干细胞用于治疗ALS仍需克服许多技术障碍:如何将干细胞引入脊髓而不损伤周围神经组织?如何确保其向运动神经元的定向分化?如何整合与局部的神经电信号回路?如何实现新轴突在成熟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生长与功能性桥接?如何矫正肌肉组织的正确轴突引导?如何形成成熟的神经肌肉接头?以及对必要功能活动的充分修整等[204]。且由于操作的损伤性,尤其是定位到脊髓腹侧角的精确注射需经多层椎板切除,限制了该技术的推广研究,因而目前多限于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尽管借助医疗机器人可以使脊柱内注射操作更快、侵入性更小,如MRI引导针定位系统SpinoBot[205],但相关技术仍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大量应用于临床。
(五)中医中药
ALS在传统中医学中没有相对应的疾病,但多认为属“痿病”范畴。自《黄帝内经》开始,历代医家根据其临床表现,对病症进行论述,辨证施治。现代中医医家基于临床经验,在中医古方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创新,希望用中国传统医学来改善ALS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延缓病情的发展。邓铁涛[206]主张以健脾益肾治本,熄风、化痰、祛瘀随症配用治标:自拟强肌健力饮、强肌健力口服液。裘昌林[207]辨识舌象论治ALS:依据舌体变化定脏腑盛衰、立治疗原则;以舌苔变化定夹邪病性,随症用药。其用药特点为:以补虚立论,扶正祛邪,补消相辅,阴阳互佐。王安琦等[208]对60例肺脾两虚的ALS患者开展了中医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观察组患者接受自拟的健脾益肺方治疗8周,结果显示,健脾益肺方对ALS患者上肢肌力及肺功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伊达伟[209]主张“治痿独取阳明”,肝脾同治,重视情志,配合心理治疗;“肺热叶焦”,治以甘寒。方用补中益气汤合柴胡疏肝散,以滋养肝肾的药物加减。石学敏[210]采用醒脑开窍针刺法配合华佗夹脊刺、经筋刺法等多种针刺法治疗ALS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赵立杰等[211]观察了温针灸对ALS的疗效:针刺以补法为主,配合平补平泻,总有效率达70%,说明温针灸可起到温脾补肾养肝、强肌健力起痿复用的作用。李晓艳等[212]的Meta分析显示,补益类中药延缓ALS进展的作用优于利鲁唑,但无法明显改善患者症状,也不能治愈ALS。郭颖等[213]研究发现,夹脊电针能够改善 ALS-SOD1-G93A转基因小鼠腰髓前角运动神经元形态学的变化,其疗效优于手针治疗,由此提供了针灸治疗ALS的动物实验依据。巫遥[214]给31例ALS患者施以强肾健脾方治疗3个月后,中医证候分级量化积分被改善,治疗总有效率为9.68%。
(六)高压氧
高压氧治疗ALS被认为是安全的,特别是对于累及呼吸肌出现起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的疾病晚期患者,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构音障碍、流涎、呼吸困难等症状,并且对患者的社交能力及情绪反应的自我评价中亦有积极影响[215-216]。但有关研究信息还有待补充。
(七)无创及有创机械通气
应定期检测ALS患者的重要脏器功能,及时发现急、慢性缺氧表现,尤其是存在缺氧的非典型表现(如乏力、咳嗽无力、强迫体位、失眠、烦躁甚至是不明原因的轻、中度意识障碍等)时应及时明确是否缺氧[194]。当FVC<80%预计值或用力吸气鼻内压(sniff nasal pressure,SNP)<40 cmH2O(1 cmH2O=0.098 kPa)时应考虑使用无创机械通气辅助治疗;当血氧饱和度<90%或二氧化碳分压>45 mmHg(1 mmHg=0.133 kPa)时,可以建议使用有创机械通气辅助治疗。机械通气辅助治疗期间应尤其注意呼吸参数调节和通气管道通畅性与清洁度的护理,防止管道脱落引起呼吸衰竭或管道污染引起呼吸道感染,当发现呼吸道感染征象时应早期甚至预防性抗感染治疗[194-195]。
(八)营养支持与PEG
由于ALS患者通常呈高代谢状态,营养状态似乎也是影响ALS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发现运动员体型和低脂肪储存者ALS发病风险增加,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与ALS发病风险呈负相关,BMI基线水平和下降速度也是影响ALS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11]。在动物模型中,挽救能量缺乏可减轻神经变性[217]。此外,中度肥胖[218]和高脂血症[219-220]与ALS的存活率提高有关,提示体重增加可能具有保护作用。意大利一项基于人口普查的时间依赖性变量的糖尿病与ALS发病关联的队列研究[221]显示,1998年至2014年登记有397名受试者发生了ALS,其中24名在ALS发病前已患有糖尿病,且糖尿病与降低ALS发病风险有关[风险比=0.30(95% CI:0.19~0.45)],因此研究结论支持糖尿病对ALS的保护作用。
ALS患者的膳食管理提倡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热量,且易消化;并指导患者及陪护人员建立规律饮食、均衡营养的膳食习惯[195]。在对患者进行营养支持治疗时,可参考2003年发布的《营养风险筛查表(nutrition risk screening,NRS)2002》评估结果,结合BMI、血清白蛋白(albumin,ALB)、血清前白蛋白(prealbumin,PA)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个体化的营养支持方案,合理应用临时或长期的肠内及肠外营养。对于食欲减退、消化功能不良患者,可适当予以促进胃肠蠕动的药物,同时注意调节肠道菌群[194]。对于咀嚼困难、吞咽困难的ALS患者,可留置鼻饲管,且应在呼吸功能不全发生前完成PEG[146],以免营养供给缺乏加速疾病进展。对于合并糖尿病的ALS患者,应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控制血糖,但不提倡严格的血糖控制[194]。
(九)心理干预
ALS患者常合并情绪障碍,加之疾病的难治性,极易出现较大的情绪波动,出现严重的抑郁情绪问题,且抑郁情绪与患者疾病病程、受教育程度、病情直接相关[222],需要及时进行干预[194-195]。借助眼控仪或研发生物-电子信息交流技术能帮助已完全失去言语和有效沟通能力的患者保持与外界的交流,降低其心理压力[223]。
八、预后
ALS患者的预后通常不佳,随着病程的延长,普遍出现局限性症状的加重或累及范围的规律和非规律性扩散,多数患者在确诊后3~5年死于呼吸功能衰竭及呼吸系统相关并发症,少数患者可在伴终生残疾的情况下存活较长时间。有较好医疗条件支持和家庭支持患者的生存期可能得到一定的延长。部分患者在自然病程中可存在病情的波动,出现短暂的症状和功能评估的好转。极少数ALS患者可在药物、康复或多方案联合治疗中收益,出现病情逆转,但关于病情逆转患者的报道多基于至少1个客观指标的持续改善,缺乏对患者本身抗病能力的评估以及指标改善与治疗方法间的关系分析[224]。
九、展望
(一)细胞模型建立
目前多数基础研究多基于遗传同质化的动物模型,探究复制人源性的细胞模型的方法进行体外研究,可正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基础研究的周期、减小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差异性,如人源诱导多能干细胞(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衍生的运动神经元的体外模型等[225]。
(二)动物模型的建立[226-227]
关于表达人SOD1突变的转基因ALS小鼠(hSOD1G93A、hSOD1G85R、hSOD1G37R等)建模方法的应用已较为广泛。Endo等[228]也设计并进行了腺病毒转染针对猴的FUS短发夹RNA(short hairpin RNA,shRNA),并通过立体定位注射成功建立了FUS基因沉默狨猴模型(Callithrix jacchus),获得了约70%~80%的FUS沉默效果。这都为ALS的病理机制研究和病因治疗打下了良好基础。但目前尚不清楚ALS遗传同质化动物模型的临床前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供人类病理学信息,大多数治疗药物在动物模型中的疾病改善效果尚未在患者中被复制。
(三)遗传性病因及基因治疗
fALS和sALS均被证实可受遗传因素影响而致病,目前虽已定位数十种致病基因,但缺乏共性研究,关于ALS的遗传病因仍众说纷纭,亦无法依据目前研究的成功研发出相应的特异性临床防治策略。因此,继续深入研究基于地域或种群性的共性遗传病因研究仍十分必要,以指导病因治疗手段的研发和基因防治策略的制定。在缺乏CX3CL1/CX3CR1信号轴(趋化因子CX3CL1主要表达于神经元,其受体CX3CR1主要表达于小胶质细胞)的末期ALS小鼠中存在神经细胞损失增多、小胶质细胞活化增加和SOD1聚集加剧,NF-κB通路被激活、自噬-溶酶体降解途径和自噬体成熟受损。CX3CL1/CX3CR1通讯通路具有抗炎和神经保护作用,在维持自噬活动中起重要作用,这可能会为ALS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靶点[229]。TDP-43表达下调降低了轴突中核糖体蛋白mRNA含量,导致轴突中整个核糖体功能抑制,过表达核糖体蛋白不仅减轻TDP-43缺失的皮质神经元中轴突延长的阻断,也抑制TDP-43转基因蝇复合眼的变性:提示提高靶向mRNA 的传输能力是治疗ALS和额颞叶变性的新策略[62]。但此类研究应尤其重视医学伦理学问题。
(四)分类诊疗
ALS患者表型变异性大,通过寻找不同表型的根本共同点来对ALS患者进行准确的归纳性分类,可能有助于在众多病因学说中找到与该亚型对应的独立病因,在此基础上进行病因诊断(体格检查、神经影像学检查和实验室辅助检查)与病因治疗的相关研究,或许能大大提高临床特异性诊疗技术的研发效率。
(五)康复训练与心理干预
ALS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已被广泛证实,如何进行切实有效的心理异常识别和干预尚未见系统性报道。随着病程进展,患者的全身功能进行性丧失,合理的康复训练能帮助提高一些治疗策略的效果,但过度运动或锻炼不足都有可能导致病情进展甚至加速恶化,相关研究也少有报道。因此,关于康复训练和心理干预的评估和策略也可能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十、总结
目前ALS仍是世界性难题,因遗传因素复杂、多因素致病、隐匿性起病与进行性进展的特点,其确诊、病因和有效治疗手段均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世界范围内,ALS有关的基础研究、技术手段更新、方针政策制定、新型药物研发等方面仍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理论也将被不断丰富和更新。研究的可重复性、结论一致性、创新性仍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