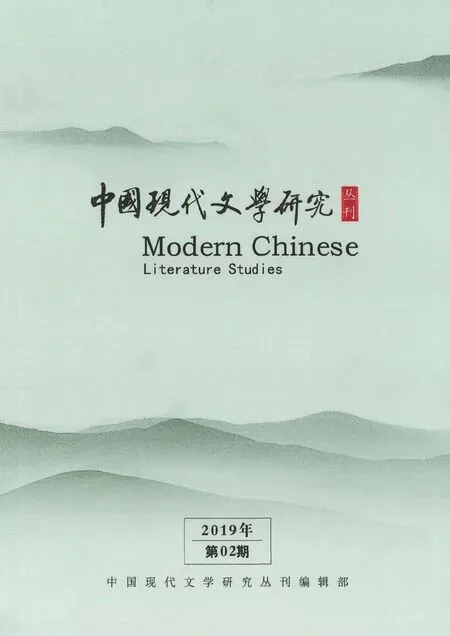移步换形的抗战书写与仓促换调的《清明前后》※
李永东
内容提要:“移步换形”是茅盾抗战书写的基本特征,也是考察《清明前后》创作过程的有效视角。《清明前后》面世后,评论界对作品价值的评判存在明显分歧。剧本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失衡,很大程度上缘于茅盾在特定情势和个人心绪的触发下,仓促地、大幅度地改变戏剧的最初构想。从《黄金潮》的创作大纲到《清明前后》,话剧的思想主题、人物性格、戏剧冲突等方面都有所调整,而关键性的调整是在第一幕已发表的情形下进行的,仓促更换主题造成了戏剧艺术的疏漏。由此可见,对抗战文学的研究,不能只聚焦最后完成的文本,还应关注文本的生产过程。
“八一三事变”之后,茅盾开始了战时流亡生活,在各个城市之间不断游走。游走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切换,也意味着创作立场的不时调整。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全面抗战时期茅盾的创作流变,那就是“移步换形”。移步换形本意指观看景色时,脚步移动,情景也随之变换。在本文中,“移步”指茅盾所处城市和观念立场的移动,“换形”指茅盾抗战书写的焦点、风貌、观念,以及所呈现的战时中国形象随之而变。对茅盾的抗战书写进行阐释,唯有察其“移步”,方能悟其“换形”,进而探究文本生产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了茅盾创作的风貌。
“移步换形”是一种权宜的写作策略,待到进入抗战胜利前后时局多变之时,茅盾的创作定位难免有些慌乱,以致仓促调整《清明前后》的构思,提供了特定语境下抗战文学的创作案例。
一 移步换形的抗战书写
茅盾的抗战书写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其倾向并非固定不变。在国内外形势和个人处境变幻莫测的抗战时期,茅盾随时随地调整着创作的倾向。浏览“七七事变”爆发后至抗战胜利前茅盾的散文创作,大致可以窥其概貌。
“七七事变”后,茅盾最早对中日交战做出回应的散文为《小病》,毫不掩饰对当局抗战工作的冷嘲热讽。接着发表的《爆竹声以后》一文,亦流露出对当局的严重不信任。1937年8月,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茅盾随即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同时发表的《站上各自的岗位》《写于神圣的炮声中》两文,满怀激情为民族抗战摇旗呐喊,但亦保留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把侵华的日本士兵当作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天真地认为“我们的战争负荷着解放自己和促进日本民众掉转枪口以自求解放的双重使命”①,从而“让亚洲两大民族达到真正的共存共荣”②。不过,在民族抗战叙事中掺杂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观念的写法,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茅盾就全副热情投入全民抗战的宣扬,完全站在民族国家立场,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诊断抗战中的问题,开诚布公,直陈建议,鼓舞斗志,对抗战的前途满怀信心。茅盾基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激情叙述,一直持续到1938年年底离开香港前夕。
1939年3月到新疆迪化后,茅盾散文创作的数量大大减少,也极少具体而微地谈论中国抗战问题,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国际格局,关心“帝国主义战争的新形势”③,以推崇的态度谈论苏联的状况。而1940年在延安的近五个月,茅盾几乎停止了文学创作。时空流转,在迪化和延安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茅盾暂时还没找到对战时中国发声的合适位置与方式。
直到1941年年初,在重庆,茅盾才找到书写战时中国的“在场”状态。这一次重返中国抗战的书写,茅盾的创作姿态和文本风格突然变了,由1938—1939年的民族国家立场转向了延安、左翼立场,叙事不再热烈明快(除了写延安的作品),冷嘲热讽的风格成了主调,所作多为杂感式的散文,大量地借用对比、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来装饰他对国统区的书写。这是1941—1945年茅盾散文创作的总体风貌。如果要看得更清楚,还需细分。1941年在重庆的散文创作,延安、国家、五四的立场相互兼容,以延安立场为主,这可以看作茅盾抗战书写的调整期。离开重庆到达香港后,茅盾对国民党的批判态度突然变得峻急。《“复活”》一文以尖锐的笔调揭露了国民党“信徒”的反动面目:他们表面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实则是希特勒法西斯的信徒;他们所作所为与“党义”背道而驰;他们开历史倒车,把陈腐的观念当作“总理遗教”。④茅盾两次在港期间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反差,1941年的茅盾开始集中火力对重庆当局进行“文化反攻”⑤,暴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和国统区的丑恶现实,提倡民主,寄希望于根据地民众的抗日行动。
1942年茅盾离开香港到桂林后,鉴于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暂时持观望的态度,对国统区的批判锋芒有所收敛,不大正面评析抗战现实,而是借古论今,指西说东。从系列散文《雨天杂写》的题目,就可以感受到茅盾创作的“火气”已大减。
1943年始,茅盾在重庆的散文创作,多少回到了民族国家抗战的书写立场,态度相对平和,对大后方社会文化问题的分析立足于“建设”,对民族抗战的前途抱有信心。其态度的转向见于《希望二三》《明年展望》《新年感怀》。第一次来到重庆,茅盾带着“先见”的延安立场,再次来到重庆,他的境遇、心态以及牵连的人事,就没有那么单纯了。所以,1943—1945年茅盾的抗战书写,是一种混杂的立场,国家、延安、左翼的立场不同程度地干预了他的抗战叙事。
概而言之,全面抗战的八年,茅盾散文对战时中国的叙述,其态度立场经历了多次调整,先后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民族国家立场,延安立场,国家、延安、左翼混杂的立场。抗战一结束,茅盾适应新形势,迅即转向延安立场。茅盾创作立场转变的幅度比较大,如果比较茅盾两次在港期间的抗战书写,比较两次在渝期间的创作,会有今非昔比、恍如隔世之感。茅盾立场的多次转变,唯有联系创作的时间、地点,方能看得更清楚,由此也能洞悉茅盾作品的意义生产机制。
全面抗战时期,茅盾的创作活动带有审时度势的色彩。在迪化,面临因言获罪的危险时,茅盾决定少说话,不创作。“皖南事变”前,茅盾在重庆主要发表了一些文论和散文,下笔比较理性,持论较为平和。其中《风景谈》是一篇向延安致敬的散文,但在地域空间的指称上,茅盾显得很谨慎。就字面意义而言,文中的“黄土高原”“北国”涵盖了西北大后方的广阔区域,并不具有排他性的党派立场,空间指向显得宽泛、含混。“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⑥的写法,让茅盾颇有几分自得,因为这让国民党的图书检查人员抓不到辫子。⑦其实,如果不持先入之见或定向思维,一般读者不会断然把《风景谈》归入对延安边区“风景”的描绘,而是可能看作对广阔的西北抗战大后方的书写。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篇散文也符合重庆当局的抗战宣传要求。“皖南事变”后,茅盾在重庆就“不再参加集会,也不写文章”⑧。茅盾以笔来回应“皖南事变”,描画重庆的丑恶,是在他即将离开重庆之时,《雾中偶记》写于1941年2月16日,九天后发表。除此之外,茅盾对国民党当局和国都重庆进行猛烈抨击的散文和小说,都发表于再次流寓香港期间,而且都发表在香港的刊物上。刊登于香港《华商报》副刊《灯塔》上的《如是我见我闻》系列散文,前五篇(《弁言》除外)创作于离开重庆前夕,后十二篇创作于香港,后面的十二篇对国统区政治批判的力度,明显加大。香港被日军攻陷后,茅盾把桂林当作“比较安全的落脚点”,暂留桂林,观察重庆方面在他“写了《腐蚀》等小说和杂文之后”的态度,“以便审时度势”,决定“今后的行动方向”。⑨
1942年年底,茅盾再次来到重庆。从香港到桂林再到重庆,发声的地点变了,发声的策略自当有所调整。那时,茅盾的两个孩子在延安,他离开香港为中共所安排,但他又是应国民党高层领导的邀请前往重庆,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委员。从国民党中宣部对茅盾“过去状况调查”来看,重庆当局似乎没有掌握茅盾1941年在港期间的创作情况,但非常清楚他一直站在左翼立场进行创作,并对之“示以优容”,试为“羁縻”⑩。在此情形下,茅盾在重庆该以何姿态进行创作呢?这个问题或许会让茅盾费些思量,让他感到“两难”[11],不免“踟蹰”[12]。茅盾的新一轮重庆书写,仍然秉持延安与左翼立场,只是换了一个套路。他的重庆想象,不再纠缠于国共冲突和党国卖国的问题,而是深入重庆的阶层状况,聚焦重庆社会的内部撕裂,描画权力人物的专横恣肆,表达普通市民的无望感,批判的重心由“假抗战”转向了“假建国”。
细加审察,茅盾此次抗战书写的态度,亦随个人处境和抗战形势的发展而有所调整,这从他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1943年创作的以上海工厂内迁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走上岗位》,调子比较明朗,表达了全民抗战的意识。由这篇小说可以看出,茅盾放弃了之前对抗当局的书写姿态,阶级观念有所淡化。茅盾与张道藩的“合作”态度和对统一抗战的宣扬,在“我们自己的朋友中”颇有“微词”[13]。实际上,茅盾新一轮的重庆构形,大致延续了之前的左翼立场。1943年创作的《委屈》《船上》这两篇小说,尽管收敛了批判的锋芒,但对国都重庆含沙射影、正反参差的针砭同样存在。此后两年茅盾创作的小说《小圈圈里的人物》《过年》《一个够程度的人》,所呈现的重庆形象则越来越灰暗,政治讽喻的色彩越来越浓厚。除了随时间而作的调整,茅盾对文体的选择比较谨慎[14],对作品发表的地点也有所考量。大致符合重庆方面抗战宣传口味的《走上岗位》,发表在张道藩在重庆创办的刊物《文艺先锋》上,而《委屈》《船上》《过年》则寄到桂林的《文学创作》杂志发表,以“避开重庆的图书杂志审查”[15]。
总的来说,茅盾第二次来到重庆的抗战书写,比香港时期要谨慎得多,已放弃了剑拔弩张的批判笔调,更多借助曲笔、转喻、侧面书写的策略,来为战时重庆造影。他对住处的选择——离市区三十里的唐家沱,也表明他在国共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倾向选择边缘的位置,以隐晦的话语发声。这也为他后来临时调整《清明前后》的写作思路埋下了伏笔。对照话剧《清明前后》的“大纲壹”“大纲贰”[16]和剧本定稿,辨析三者的人物性格、主题观念的转移和政治化,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会发现剧本“后记”、作者回忆录中的愤激之词与政治告白,更多属于事后的态度。《清明前后》无疑是体现茅盾“移步换形”“审时度势”创作姿态的典型案例。
二 “剧坛奇葩”抑或“公式主义的作品”
五幕剧《清明前后》是茅盾唯一的话剧剧本,创作于抗战胜利前后,茅盾试图通过对1945年3月底发生在重庆的“黄金加价舞弊案”的书写,“揭示官僚资本及其爪牙的卑劣与无耻,民族资本家的挣扎与幻灭,以及安分守己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又如何变成了替罪羊,从而向读者展示出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战时首都的一幅缩影。结论是:‘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17]。
《清明前后》可以看作《子夜》与《日出》的糅合,茅盾创作此剧所依凭的生活与艺术经验,更多来自1930年代,来自上海体验,只不过故事展开的背景为战都重庆。《清明前后》延续了茅盾所擅长的创作路子,如工业题材、经济视角、社会剖析、心理刻画。人物构想亦带有《子夜》与《日出》的痕迹,如民族工业家林永清有着吴荪甫的影子,亦官亦商的金澹庵的形象介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和流氓大亨金八之间,黄梦英形象与《日出》中的陈白露有些相似,陈克明形象则让人联想到《子夜》中的经济学教授李玉亭。《清明前后》的创作,茅盾大规模调用了上海时期的左翼文学经验,原本可能会写成“《子夜》的续编”[18],但在特定情势和个人心绪的触发下,剧本创作偏离了最初的构想,正是这种偏离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表达和价值评判。
关于《清明前后》最初发表的情况,诸多著述中的说法混乱不堪,错误百出,因此有必要先作一简单介绍。《清明前后》初版本1945年10月由开明书店在重庆出版,在这之前,话剧已在重庆《大公晚报》第二版的“小公园”副刊连载。1945年8月3日的《大公晚报》刊出了《清明前后》的连载预告。剧本8月6日开始在“小公园”副刊连载,至当年10月1日连载完毕。其中,8月6日刊登的是“开场白”,10月1日刊登的是“《清明前后》的后记”。各幕刊登的时间分别为:第一幕8月7日至8月22日,第二幕8月22日至9月2日,第三幕9月3日至9月16日,第四幕9月16日至9月24日,第五幕9月24日至9月30日。话剧连载尚未结束,《大公晚报》的第一版就开始刊登《清明前后》的演出广告,9月21日为演出预告,9月23日至10月21日几乎每天刊登该剧的演出广告。话剧由中国艺术剧社排演,赵丹导演,每晚在重庆的青年社演出(其中,民国国庆节10月10日增加日场)。话剧9月26日首演,10月21日结束,共演出31场。[19]
《清明前后》的剧本与演出,在重庆引起了广泛关注,收获了不少赞誉。话剧首演当日《大公晚报》刊登的演出广告称之为“划时代的盛大演出”[20],演出两周后,广告宣传道:“本剧被誉为近二年来剧坛的珍贵收获,本剧已突破今年度话剧演出之卖座纪录。”[21]多年后,茅盾的剧本被业界当作了经典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清明前后》,版权页有一段“内容说明”,指出该剧“文学性很高,一向被誉为剧坛奇葩”。黄会林主编的《中国百年话剧史稿》也对该剧作了专门介绍。
然而,《清明前后》公演后,在重庆文艺界引发了争论,争论围绕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关系展开。茅盾在回忆录中介绍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以王戎为代表,认为《清明前后》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的作品”;另一种意见“有何其芳、邵荃麟等许多同志”,认为艺术离不开政治,《清明前后》“攻击着、控诉着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和那些吃人的黑暗势力;同时,也明确的指出了如何才能求得生存的道路”。[22]在回忆录中,茅盾对王戎的意见很不以为然,并以“大多数”评论家的权威看法来确证作品的价值。不过,实际情形与茅盾所述有较大出入。确实,何其芳对《清明前后》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力作”,“这个戏有着尖锐而又丰富的现实意义”。[23]何其芳的赞扬,应该与他作为延安派到重庆主持文化界统战工作的身份有关。实际上,何其芳在1946年所写的《关于现实主义》一文中,隐约把《清明前后》归入“政治性高但艺术性……还比较弱的作品”[24]这一类。邵荃麟对《清明前后》的认可也有限,止于“比较有政治倾向”这一点,同时指出作品“在技术上有不足”,内容上“也有挖掘得不够的地方”,并存在“公式主义”的成分。[25]
1945年11月10日《新华日报》举行座谈会,集中展现了重庆观众对《清明前后》的不同评价。肯定性的评价,着眼于作品反映了战时重庆的社会现实,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而否定的声音,则认为《清明前后》在艺术上是失败的,戏剧布局乱,剧情散漫,线索不显著。[26]另外,J和S两位讨论者还指出,工业家的痛苦,包括不民主的实际情形,政府的统制管制政策怎样摧残工业等,只是借人物的口说了,并没有在舞台上用行动表现出来。[27]这些优缺点,也是剧本所具有的。其他报刊的评论,意见大致与《新华日报》座谈会的情形类似。即使对话剧多有肯定的评论者,如邵荃麟、梅子、刘西渭、夏丏尊等,也只是因为戏剧对现实的大胆表现而谅解了其艺术上的不足。夏丏尊一分为二地评价了话剧的内容与形式:“本剧是作者的处女作,以剧的技巧论,当然有可指摘之处,至于主旨的正确与反映现实的手腕,是值得敬服的。”[28]梅子指出茅盾“对于舞台技术不够熟悉”,但也理解“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茅盾先生写第一出剧本,缺点自然是免不了的”[29]。刘西渭尽管“不想就《清明前后》的艺术的形式多所饶舌”,但还是指出戏剧“近看雕琢,远看缺乏距离”,并认为戏剧第二幕的内容游离于主线之外,“冲淡了戏剧的浓度”,没必要单独成一幕。[30]景山在认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批评原则的基础上,愿意说“《清明前后》是抗战期间最优秀的剧作之一,因为它的技巧上还很有些问题,影响了全剧的艺术性,但政治性之高在本剧中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31]。
在抗战胜利之初的评论界看来,《清明前后》是一部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严重失衡的作品。他们几乎都是以政治与艺术二分的方式评价《清明前后》,肯定其政治的正确,原谅其艺术上的疏漏。但是,对于文艺作品而言,内容与形式原本不可分割,政治观念如果不能成为戏剧冲突的有机构成,就难免概念化。茅盾自己承认,“剧本的写作方法,我还没摸清楚”,“正像人家把散文分行写了便以为是诗一样,我把小说的对话部分加强了便亦以为是剧本了。而‘说明’之多,亦充分指出了我之没有办法”。[32]夏丏尊认为这句话是茅盾“老老实实的自白,并非自谦之辞”[33]。话剧《清明前后》确实未能摆脱小说创作的思维,关于人物性格与生活经历等方面的大量信息被置于出场人物的介绍中,这些信息并没有成为剧情的有机组成部分,也难以在舞台上呈现。不过,小说家第一次写剧本难免幼稚的说法,尚不是造成话剧艺术局限性的根本缘由。
《清明前后》作为一部政治正确而艺术上有明显缺憾的作品,仍然获得诸多赞誉,这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在重庆的传播,以及党的文艺统战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判断政治与艺术失衡的《清明前后》到底属于“剧坛奇葩”,抑或“公式主义的作品”,就不是单纯的文学评价问题。笔者想要指出的是,评论界对《清明前后》的价值评判,依据的是公开发表、出版的剧本,并没有注意其创作过程。王景山、刘西渭注意到戏剧存在两条故事线索,黄金案是一条,民族工业问题是另一条,这就造成了戏剧结构不紧凑。王景山甚至猜到茅盾“提笔时一定是想以黄金案为主题的”,然而,第二幕之后,“重心却逐渐完全移到了工业问题上”。[34]直到话剧的创作大纲公开出版后,才有学者立足于大纲与剧本的差异,从戏剧文体理论的角度,分析政治诉求如何带来林永清形象的修改、抗战胜利时间的误判如何导致“民主”主题的引入。[35]不过,《清明前后》的修改动因不是文体形式的问题,而是主观意愿的问题。《清明前后》的布局乱,剧情散漫,线索不显著,主题口号化,人物抽象化,这些弊病的出现,有着深层的现实原因。
三 从《黄金潮》到《清明前后》
《清明前后》艺术缺憾的肇因,很大程度上缘于作者仓促地、大幅度地改变剧本的最初构想。《清明前后》的创作思路经过了两次大调整。茅盾最初为戏剧拟的题目为《黄金潮》,在正式写作前,他制定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并对提纲做过大的调整,这样就形成了“大纲壹”和“大纲贰”。戏剧的明显破绽是在修改调整中出现的。从《黄金潮》“大纲壹”,到“大纲贰”,再到剧本《清明前后》,话剧的主题沿着激进化的路子越走越远,战时重庆的面孔也由情欲角逐转向了政治批判。
1945年8月3日《大公晚报》刊登的《清明前后》连载预告中写道:“茅盾先生在今年的五十大寿席上说,他要更加努力,如果看不到民主的中国出现,他死不瞑目”,本剧是他大寿后的第一本创作,体现了他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业绩。[36]演出广告则宣传该剧乃“推荐给工业界人士一部描写中国民族工业在抗战中的苦斗史”[37]。戏剧广告似乎表明茅盾有着明确的创作方向。其实,剧本最初的构思并未由民族工业的危机问题引出“民主”主题,“民主”主题是茅盾适应新形势临时添加的。
《黄金潮》“大纲壹”的创作思路,虽然前后有增补和调整,但人物形象、戏剧冲突和思想观念并无根本性的改动。“大纲壹”的剧情围绕黄金与女人展开,书写了充满投机和情色的重庆社会。戏剧冲突、人物关系和戏剧主旨,基本上依靠一个事件——黄金案,以及一个女性——梦英来结构。在“大纲壹”中,组织戏剧的核心人物不是工业家甲(林永清),而是梦英。甲(林永清)与甲妻(赵自芳)的家庭矛盾,因梦英而引发;“大亨”金(金澹庵)给甲(林永清)出难题,根源于两人都迷恋梦英;金(金澹庵)陷害乔张,是因为梦英与乔张关系亲密。而且,梦英还是剧中最重要的观念人物,作者赋予她高于其他人物的地位,扮演着道义裁决的角色,对卑劣无耻的重庆权势社会进行批判,对受压迫者进行声援。梦英同情发疯的卯妻(唐文君),为了解救乔张或卯(李维勤),想请金(金澹庵)出面帮忙;甲(林永清)办实业,有民族意识,故梦英对他“感想尚佳”[38],并为其筹备资金奔走,当甲(林永清)参与黄金投机,并向她炫富时,梦英开始鄙夷他;梦英把卯妻(唐文君)带到×主任(严干臣)家,且质问×主任;梦英戏掴“帮闲”寅(余为民)的脸,以发泄对他那套反苏反共理论的不满。依靠情色与权贵、大亨周旋的梦英,其人物性格比较复杂。她曾经是一位救亡青年,在剧中则是以交际花的形象出现。“大纲壹”这样描绘她的性格:
“七七”时期热情的余烬现在埋在她心深处,被玩世不恭的外衣厚厚地覆盖着了。但她在那个糜烂的上层社会中还是代表着一种爆炸力,一种不肯安于现状的激越的情绪,一种扑上光明的欲望。她痛恨自己目前的生活,但又不知道如何安排。她唾弃那些对她献媚的人们,但她离开他们又觉得闷;她需要玩弄这班人,在嘻笑唾骂中略感得一点生活味,倘连这一点也没有,她可真觉得自己是个活死人了。[39]
可以看出,茅盾依靠调用以往的经验——上海时期的城市体验和文学经验,来塑造战时重庆的梦英形象。梦英的性格是三个人物的杂糅,章秋柳(《追求》)+陈白露(《日出》)+徐曼丽(《子夜》)。《黄金潮》“大纲壹”主要的戏剧冲突其实不在黄金投机,而在情色。表现为金(金澹庵)、甲(林永清)、庚(陈克明)、乔张对梦英的争夺。第一幕的主要剧情就是甲妻(赵自芳)因梦英而争风吃醋。戏剧的情色化与政治化结合在一起,由情色进入权力和资本的压迫问题。如金(金澹庵)陷害乔张;金(金澹庵)给甲(林永清)出难题;梦英对甲(林永清)态度的转变;卯妻(唐文君)为了职业,“天天在上峰淫欲的眼光下讨生活”[40];寅(余为民)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为诱饵勾引玛(玛丽);金(金澹庵)为了占有梦英,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如此构思,乃是以都市情色作为戏剧的吸引力,在黄金投机事件中呈现民族工业危机重重,民族资本家歧路彷徨,政客、官商荒淫无耻、一手遮天,小人物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重庆社会。
《黄金潮》“大纲贰”的左翼色彩增浓。在“大纲壹”中,甲妻(赵自芳)与卯妻(唐文君)的关系为“从前中学同学”[41],而到了“大纲贰”,两人的关系改为抗战时期“在汉口办难民教育”时的同事。[42]这就为卯妻(唐文君)控诉重庆社会不公和当局抗战不力提供了政治依据。“大纲壹”的剧情概要中涉及的工业家有甲乙丙三位,性格各异:工业家甲(林永清)拿到借款却不用于生产,而是想通过黄金投机摆脱困境;工业家乙负债累累不以为意,“豪华如往时,意气洋洋”[43];工业家丙的心思尚在恢复生产上。由此可见,茅盾最初想写出重庆民营资本家的多副面孔。但到了“大纲贰”和剧本定稿中,工业家乙和丙这两个人物被删除了,工业家甲(林永清)成了联系各方的核心人物。由“大纲壹”到“大纲贰”的修改过程中,甲(林永清)自身的过错不断削减,越来越值得同情。在“大纲壹”中,甲(林永清)对办工业的动摇,其原因是他“着了一个女人的迷”[44],这个女人就是梦英,到了“大纲贰”中,甲(林永清)仍然迷恋梦英,但在两人的亲密关系中添加了另一重意味——梦英佩服甲(林永清)办工业的能力,尽量暗中帮助他,并联手对抗官僚资本家金(金澹庵)。与“大纲壹”相比,“大纲贰”通过重点渲染卯(李维勤)与卯妻(唐文君)的生活苦难,突显梦英与邪恶权势的对抗,锐化“可敬的人”和“可怜的人”的利益冲突,以加大对战时重庆的批判力度。不过,“大纲贰”的人物关系、矛盾冲突和思想主题,仍然围绕黄金投机案展开。尽管“大纲贰”的概念化初现端倪,但尚谈不上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明显失衡。
与《黄金潮》“大纲贰”相比,《清明前后》进一步增强了对阶级压迫的暴露和对重庆当局的批判。最明显的情节当属对卯(李维勤)夫妇悲剧的表现。在《黄金潮》“大纲壹”中,并没有写到×主任(严干臣)参与黄金舞弊案,也没有表现大人物逍遥法外的情节。即使到了“大纲贰”中,卯(李维勤)与妻子的悲剧也主要被归为社会与人心的问题,如收入的菲薄,债务的压力,医生的敲诈,公司的用人制度,卯(李维勤)的铤而走险,同事戊(方科长)的落井下石,归为一句话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而到了剧本定稿中,李维勤夫妇的悲剧则朝着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的方向加以阐释。例如,因为大批难民涌进重庆,剧本就借车夫的话说:“这是个人吃人的世界!”[45]剧本左翼色彩的强化,在戏剧冲突的重置上亦得到了体现。在《黄金潮》的创作大纲中,甲(林永清)与梦英的关系暧昧,引发妻子吃醋,也影响了金(金澹庵)与他的关系。《清明前后》则赋予林永清与金澹庵的冲突以新的意义,即民族工业的开拓者与商业投机者、官僚资本家的对立,男女私情故事演变成了政治冲突事件。由《黄金潮》到《清明前后》,戏剧的矛盾冲突发生了变化,由情色所引发的冲突转向了阶级、政党、经济所引发的冲突。阶级冲突主要体现在黄金案中李维勤与严干臣、方科长的不同遭遇及其引发的不平。政党冲突则表现为余为民的反苏倾向和陈克明教授对依赖美国经济的批判。经济冲突表现为官僚金融资本家金澹庵对民族实业家林永清的控制。
与《黄金潮》的创作大纲相比,《清明前后》的根本性修改在第三、第四、第五幕,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都作了明显调整。创作大纲中的甲(林永清)、甲妻(赵自芳)、卯(李维勤)、梦英各有其可怜可哀之处,而剧本的后三幕则把他们作为抗战事业的贡献者、不公社会的牺牲品、权势阶层的受压人物来处理。在“大纲贰”中,甲(林永清)等民族资本家作为“代表社会秩序”的人物,作为社会的压迫力量被卯妻(唐文君)控诉,[46]也作为“将失足”的“有用人才”而值得观众同情。[47]而在剧本中,民营资本家林永清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殚心竭虑,却被重庆当局的战时统制管制政策所压制,剧中的他被塑造成了受官僚资本压迫、主张政治民主的一个人物,由“伦理层面被批判的个体改写为政治上被肯定的集体代言人”[48]。在创作大纲中,梦英被塑造成以美色周旋于重庆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她既厌恨政客、资本家、帮闲的嘴脸,又离不开他们,而剧本第三幕对梦英的人物介绍,已删除了大纲中关于她的玩世心态的描述。[49]
正是《清明前后》后三幕创作倾向的大幅度调整,造成了剧本的诸多缺憾。就人物形象而言,梦英在剧本第三、第四幕的表现,与她在创作大纲中的形象有很大的出入,也与剧本第一幕中她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反差。在第一幕中,梦英处于幕后,并没有露面,其形象在赵自芳的评说中得以呈现,侧重表现其“魔鬼的笑”、令男人神魂颠倒的女性魅力。到了第三、第四幕,梦英以反抗压迫、伸张正义的形象走上台前,反转了她在第一幕中的形象,形象的刻意扭转和拔高,使得剧情显得突兀,后面的正义形象也解构了第一幕所设置的夫妻冲突,降低了读者对赵自芳形象的信任感。为之,作者不得不调整赵自芳的形象,突出其多疑、歇斯底里的性格,并在剧情发展中把第一幕有关赵自芳吃醋的剧情强行解释为误会,同时林永清与梦英的关系被去情色化。牵一发而动全身,作者仓促之下所作的连环修改,使剧本的政治观念得以加强,但多少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与真实感。概念化意味着思想观念不是从人物的性格命运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二者的对接不够顺畅。梅子在剧评中指出,“林永清那人物多少带有些抽象,仿佛有了黄金案才产生出林永清这一个人”[50]。周刚鸣亦指出,剧本中看不到林永清“这个人物的自私心的一点表现”,是不符合这类人物的性格的,而梦英形象的塑造,“太过夸张”,“过度神秘性”,有可能带来精神上的不健康影响。[51]梦英形象的修改,使得剧中的人物关系变得牵强,景山甚至认为“在全剧的发展中”,“实在是一个没必然存在性的人物”。[52]剧本后三幕的修改,弱化了对以梦英为中心的男女关系的表现,意在凸显权力的压迫,但用来控诉重庆“吃人”社会的相关人物,因身份信息的缺省,其行动功能显得有些可疑,人物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效应也大打折扣。剧本的第三、第四幕似乎想把梦英、乔张塑造成重庆权势社会的反抗者,暗示重庆当局对进步青年的迫害。但是,乔张为何被捕,剧中没有任何交代,梦英和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营救他,剧中也没有明确指出。当几个重要人物都因修改而形象力量减弱,戏剧主题的表达就只能依靠陈克明、余为民等观念性人物来补救,戏剧的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失衡也就在所难免。
《清明前后》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明显失衡,尤其体现在主题的调整上。《黄金潮》创作大纲的主题比较集中,围绕黄金投机案来揭露重庆社会的“矛盾,无耻,卑鄙与罪恶”[53],只有一句话捎带提及振兴工业“希望在民主”[54]。经过调整的《清明前后》的第一、第二幕还基本承续了创作大纲的主题,表现的重心为黄金案,而第三、第四、第五幕的表现重心却转移到民族工业的危机与出路问题,把民族工业的艰难处境归于政府的统制统管,并通过人物之口点出“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55]的主题。但是“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这一主题,在戏剧中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完全依靠政论式的对白来实现,并没有呈现为具体的“动作”“性格”和“事件”。而且,主题一变,剧本的第二幕就游离在主线之外,全剧的结构就乱了。由《黄金潮》到《清明前后》,因主题转移,剧本不得不增加两个观念性的人物陈克明和余为民的戏份。总之,“民主”主题的强势嵌入,不仅造成了人物形象的抽象化,而且带来了结构散漫,线索杂乱,思想概念化等弊病。
《清明前后》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明显失衡,与其说缘于茅盾话剧创作能力的不足,不如说是人为所致。
四 仓促调整创作方向的动因
为什么《清明前后》的构思、写作会越来越观念化,并因此留下诸多缺憾?如果注意到剧本构思创作的时间表,就会豁然开朗。
据茅盾说,重庆文艺界为他筹备五十寿辰祝寿活动时,他正忙着写话剧的“提纲”[56],时间是1945年6月,那时德国已投降,抗战已胜利在望。由南方局操办的声势浩大的“寿茅”活动,是党在大后方宣传、建构“人民文艺”战略的一部分,茅盾被确立为“人民文艺”的“旗手”。[57]因此,“寿茅”不仅是为茅盾做寿,也是给他“加鞭”[58]。这次祝寿活动对于促使茅盾调整剧本写作思路应起了重要作用。“《清明前后》正式写作时间不过两个月”[59],“刚写了两幕,敌人投降的消息来了”,尽管茅盾明知抗战胜利后,“经济界将有大变,我这题材有点过时了,而且又愈来愈觉得技术上不像个样”[60],但茅盾还是继续把它写完了。赵丹把剧本看了三遍,与茅盾交流演出脚本,是在9月初,话剧的彩排是在9月23日,9月26日正式公演。[61]也就是说,《清明前后》在1945年8月底已经定稿。按照茅盾所说的剧本的正式写作时间为两个月,可以推断,茅盾是在1945年七八月创作了这个剧本。戏剧第一、第二幕的创作时间为7月到8月15日左右,一个半月。后三幕的创作时间较短,大概半个月。
《清明前后》的仓促换调及其造成的缺憾,与剧本以连载的形式面世也有很大关系。剧本不是创作完成后再在《大公晚报》连载,而是边写边发表。由于剧本的第一、第二幕在抗战胜利前已写好,更重要的是,作为“展开全剧故事之线索,把几个纠纷的头都透了出来”的第一幕,[62]抗战胜利前已在报纸发表大部分,白纸黑字,不能更改。剧本的“开场白”表明,戏剧将讲述清明前后在山城重庆发生的一件事,即“黄金加价舞弊案”,表现几位“可敬的人”和两三位“可怜的人”的喜怒哀乐。[63]这显然是以黄金案为中心的构思,与《黄金潮》写作大纲相一致,剧本前两幕也确实围绕黄金案来写。但是,抗战胜利后创作的后三幕的表现重心,却转向了民族工业问题,这就造成整个剧本情节线索的枝蔓。甚至人物塑造也多少背离了最初的定位,例如,第一幕的人物介绍中说唐文君是“一位相当难以满足的太太”[64],就与后几幕中的唐文君形象不相符;第一幕详加介绍、重点推出的人物赵自芳,在后面的剧情中却变得无关紧要,成了“陪衬的人物”。[65]在第一幕已发表,第二幕也已写好的情形下,大幅度调整第三、第四、第五幕的写作,剧本的人物、情节和主题等方面,就不可避免出现前后不协调的情形。
茅盾之所以仓促调整剧本的创作方向,与1945年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快速变化以及茅盾个人境遇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和平、民主建国的呼声日高,政治站队显得尤为迫切。正是在此情势下,茅盾对剧本的人物性格、戏剧冲突和思想主题做了处理,“在一个重要的关头,恰当其时地喊出了广大人民的呼声”[66]。不过,所做调整并不一定使话剧内容更加贴近抗战胜利后的重庆现实,而是作者审时度势后的一种政治表态。茅盾的同乡,抗战时期在香港、重庆与茅盾有较多交往,并参加了“寿茅”活动的徐迟,断定“茅盾先生是认为他应该写这个戏而写了这《清明前后》。他并不是全部愿意的”,戏剧的弱点“来自创作过程的欠缺一致性”[67]。尽管没有资料表明徐迟是否了解《黄金潮》创作大纲,是否与茅盾有过关于《清明前后》创作过程的交流,但徐迟的说法多少触及了茅盾戏剧创作的心理动因:抗战胜利的庆祝之声中,茅盾并不完全“愿意”这样写,而是觉得“应该”写成这样。
迫切希望话剧尽快上演的态度,从侧面透露了茅盾修改话剧的心理动因。抗战甫一胜利,国共两党即紧锣密鼓地协商“重庆谈判”。谈判之初,茅盾正与赵丹交流话剧的演出问题。赵丹把修改后所形成的演出脚本带给茅盾,但茅盾觉得没必要看,只提了一点要求:赶紧排练,争取早日公演,“要趁现在毛主席在重庆的机会,把戏推出去”[68]。这句话道出了茅盾心中的隐秘。延伸来看,写于1945年9月20日的“后记”,茅盾的延安立场更为分明,对重庆当局的批判更为犀利。他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归功于“敌后军民”“敌后解放区”“苏联人民”,质疑民国政府是否有代表中国享受胜利荣光的权力,并把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看作极端“矛盾,无耻,卑鄙与罪恶”的地方。对照茅盾1943年至抗战胜利前的重庆书写,即可见出茅盾对重庆当局的批判突然升级了,又回到了香港时期的态度。
《清明前后》的意义生产过程,提醒我们考察茅盾的抗战书写,不能只聚焦最后完成的文本,还应关注文本的生产过程。只有不放松对其创作动因、书写语境的追问,才能深刻领会茅盾的抗战书写为何如此。
在抗战文学研究中,我们早已习惯于在文学中发现历史,并设想存在“一致性”的抗战历史与民族心理。我们也愿意相信作家创作的真诚,认为像茅盾这样的知名作家的抗战书写,必然近乎“写真”。况且,真实也是《清明前后》《腐蚀》等作品成为经典的基本前提。然而,茅盾移步换形、仓促调整的抗战书写,让文学史上的定见显得并不完全可靠。抗战文学研究要想有新的突破,不仅需要重新进入集体的抗战语境,也需要进入个人的抗战生活,不仅需要直接面对抗战文本,也需要探究创作的动因和生产的过程,如此方能对丛生的抗战文学做出恰如其分的评析。
注释:
①茅盾:《写于神圣的炮声中》,《呐喊》1937年第1期。
②茅盾:《站上各自的岗位(创刊献词)》,《呐喊》1937年第1期。
③茅盾:《帝国主义战争的新形势》,《茅盾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278页。
④茅盾:《“复活”》,《茅盾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6页。
⑤段从学:《夏季大轰炸与大后方文学转型——从抗战文学史的分期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7期。
⑥⑦⑧⑨[13][14][15][17][22][56][58][59][61][68]茅盾:《茅盾全集》第35卷,第396、396、405、455、493、494、494、548、552~553、547、539、448、550~551、550页。
⑩杨扬:《台湾所见“国民党特种档案”中有关茅盾的材料》,《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
[11]茅盾:《桂渝道中杂诗,寄桂友》,《茅盾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页。
[12]茅盾:《赠桂林友人》,《茅盾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页。
[16][38][39][40][41][42][43][44][46][47][54][62]茅盾:《〈清明前后〉大纲》,《茅盾全集·补遗》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142、100、99~100、106~107、93、113、90、93、123、109、107、108页。
[18][30]刘西渭:《清明前后(书评)》,《文艺复兴》创刊号,1946年1月。
[19]《大公晚报》1945年10月21日,第1版。
[20]《大公晚报》1945年9月26日,第1版。
[21]《大公晚报》1945年10月12日,第1版。
[23]何其芳:《〈清明前后〉的现实意义》,《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2日,第4版。
[24][66]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第4版。
[25]荃麟:《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6日,第4版。
[26][27]《〈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座谈》,《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8日,第4版。
[28][33]夏丏尊:《读〈清明前后〉》,《文坛月刊》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
[29][50]梅子:《关于清明前后(特约通讯)》,《月刊》第1卷第2期,1945年12月。
[31][34][52]景山:《读茅盾的〈清明前后〉》,《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
[32][53][60]茅盾:《〈清明前后〉的后记》,《大公晚报》1945年10月1日,第2版。
[35][48]江棘:《〈清明前后〉:从大纲到成文的叙述者位置》,《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6期。
[36]《大公晚报》1945年8月3日,第2版。
[37]《大公晚报》1945年10月7日,第1版。
[45][55][63][64]茅盾:《清明前后》,《大公晚报》1945年9月17日,第2版。
[49]删除的文字为:“她痛恨自己目前的生活,但又不知道如何安排。她唾弃那些对她献媚的人们,但她离开他们又觉得闷;她需要玩弄这班人,在嘻笑唾骂中略感得一点生活味,倘连这一点也没有,她可真觉得自己是个活死人了。”
[50]梅子:《关于清明前后(特约通讯)》,《月刊》第1卷第2期,1945年12月。
[51][65]周钢鸣:《论〈清明前后〉》,《文艺生活》1946年第3期。
[52]景山:《读茅盾的〈清明前后〉》,《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
[57]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251页。
[67]徐迟:《在泥沼中——向文艺界的朋友们和读者贺新年》,《新华日报》1946年1月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