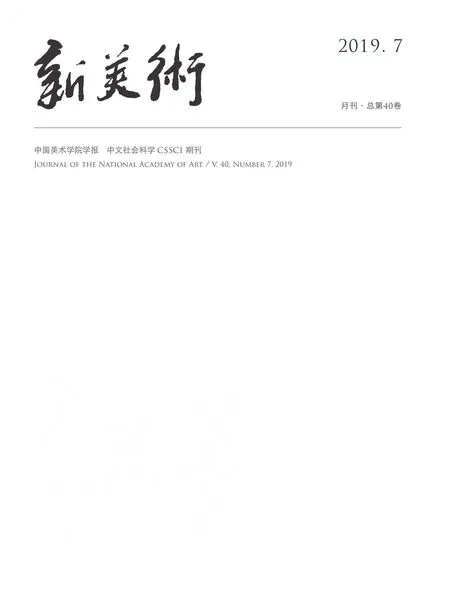王鸿绪尺牍考释* 管窥清代书画鉴藏史(下)
陆蓓容
一
王鸿绪(1645—1723)、顾维岳(生卒年不详)材料都很少。有此一信,即使它的写作时间不能最终确定,其中涉及的书画流传过程也无法全然考实,似乎也应该高兴和知足。但上篇花那些笔墨,却并不满足于泛泛钩稽一二线索。事实上,那些作品和这封信,至少反映出清初书画收藏活动的两类情况,而第二条又正是第一条的原因之一。
(一)藏品的消息很容易流传开来。藏品流转的速度也相当快。
(二)中间人,或者过去所谓“装裱匠”、掌眼者之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作用”,与学界过去理解的并不完全相同。
目前,清初书画收藏史个案研究有了很多成果,第一条论断早已不是新鲜话头。自明清鼎革起,至乾隆王朝开始之前,民间收藏发展了将近一百年。过去我们也讨论这种现象的原因,总说到权力洗牌导致的流通机会,政治气氛转变带来的崇文风气,以及数百年来未被征求过的“民间”,本来自有一份丰足的家底。从各种文献看来,只要地位够高,名望够大,即使并不专意于收藏,也颇有机会看到各家的藏品精华,王士祯(1634—1711)就是一个好例子。因此,原先我曾以为,相对而言,尽管康熙年间的上层文人书画圈子对外不易打开,对内却较为开放。1关于这些问题,我在博士论文中都有所讨论。参见《宋荦和他的朋友们:康熙年间上层文人的收藏、交游与形象》,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年。
王鸿绪这封信,能够部分证明我过去的观点。毕竟从友人处借得作品,靠的是他本人的社交关系,“昆山怀素《自叙》真迹,记得购于平湖”,或者也靠他自己的小道消息。可是“平湖昔年所收上乘,年道丈当无不知,巽老好佛典,书画非其所嗜,此时与言,尚可转移”“此外有何佳迹在平湖者,并希密示”,甚至“子敏前幸勿道破为祝”,却显示出过去没有条件,难以窥破的一面:个人的整体收藏规模,仍然是很难了解的。2王时敏作信与王翚,谈到张应甲向他求购关仝真迹与赵令穰《湖庄清夏图》时,就发出过“此迹藏之甚密,外人何以闻知”的疑问。这也证明,圈子即使存在,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人物都在同一个圈子里。被远人探知消息,仍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参见《清晖阁赠贻尺牍》,风雨楼丛书本,卷上,叶17。下引此书版本俱同。刘亚刚讨论清初书画作品流传之快,曾说“当时的情况来看,新的流转多发生在士大夫阶层内。在官方尚未大规模介入且没有新的收藏阶层形成的情况下,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们对彼此藏品的熟知”,本文将说明这个判断恐怕很不全面。参见刘亚刚撰,〈清初古书画“北移”现象之辨〉,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9期,第133页。
高士奇曾经写过《江村销夏录》,主动将大半生所藏的精华公诸于世,这部书刊行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下距其卒尚有十年。他和王鸿绪也算共过患难,颇有交情。即使如此,王氏仍旧不很了解故人究竟聚拢起多大一份收藏,其中又有多少好东西。
看来,王鸿绪相信,以高士奇的地位与能力,十年中足以聚拢许多新藏品。另外,不妨再作出两点推论。第一,收藏活动毕竟也有竞争性。即使有无数机会共赏书画,朋友之间,仍未必会亮出全部的家底。第二,关系总是时刻变化着的,命运拨弄之下,距离与心境都会随之改变。即使曾经是朋友,也不必相信对方没有藏私。
确实有一件“佳迹”,证明王鸿绪紧盯高氏遗藏,有所斩获。巧得很,高士奇的上家正是徐乾学,而顾维岳、吴升两家人也与此卷脱不了干系,几位老先生都从信中走到卷尾。那就是著名的欧阳询《仲尼梦奠帖》,2018年8月起,辽宁省博物馆将它打开展陈,拖尾题跋历历在目:
……顷从昆山传是楼得之,炎景杜门,静阅数日。所谓龙蛇飞动,矛戟森立者,良不虚也。唐彦猷得率更书数行,精思学之,遂以名世。余衰懒,不能动事临摹。惟于春秋佳日,出佐吟览。譬如人家有国色之姝,可以加餐,独旦老翁聊藉此加餐也。康熙庚辰七月十八日,秋暑未减,畹兰再发,书于清吟堂,江村高士奇竹窗。
庚辰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其时徐乾学下世已六年,因为一个“顷”字,确知高氏当时刚刚获得此卷。随后:
……细审是帖用笔之意,直与兰亭相似。宜乎唐人评论以欧书居褚河南、薛少保之右,不诬也。康熙五十七年岁次戊戌冬十月廿四日,横云山人王鸿绪题于长安邸舍,时年七十有四。
康熙五十七年是1718年,比王鸿绪写信的时间略晚。然而这段题跋只字不提购买时间与对象,作跋之日,倒还真未必是书卷入手之时。顾维岳的兄长顾复作《平生壮观》,说他亲眼看过《梦奠帖》。不过那是清王朝定鼎未久,冯铨(1595—1672)还当着相国的时候。那位子敏吴升,也在《大观录》里记录此卷,藏印只记到项元汴,题跋只录到杨士奇,过目时间不明。3《平生壮观》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而《大观录》成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
《梦奠帖》到高家时,《江村销夏录》已经刻成,因此只在《江村书画目》中现身。而康熙年间,《江村书画目》远未公开。也就是说,王鸿绪起初未必知道《梦奠帖》在高家,虽然最后很可能是从江村后人那里得到了它。可惜无法断然猜测是否顾、吴两家中的哪一位帮忙提供信息,牵线搭桥。
不过,当思考王氏从何获得消息时,尺牍与实物都在提示,那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人才有条件知道这一切——那也就意味着,什么人能够掌握一个藏家的整体规模?
唯有藏家始终需要的人。这些人出入各家,饱看真迹,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熟知每位收藏家的藏品数量,了解他们的需求;或者掌握“下游产业”核心技术,善于装裱作品,过手无数,知道原件的各种细节;或者拥有高超的临摹技巧,能提供下真迹一等的复制品……总之,只要收藏活动持续发生,而客观环境还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藏家的生活中总少不了他们,并且关系会长期维持。4关于这些人,本文不拟一一举例,可参见陆昱华撰,〈书画记人名考〉,载《美术史与观念史》,第14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2-428页。
今日条件有限,单独看每一条材料,都拼不起这样一个人的全貌。但如果把前辈学者们收集到的种种线索并置齐观,那么吴其贞、吴升、张黄美、陈定、王济之、顾维岳们,即使层次不同,侧重有别,所从事的活动毕竟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也常常彼此相识,互有竞争。杨小京曾言,“顾维岳是一位读书人,是一位收藏家,既收藏书画,也收藏古书,同时还是一位古董商。明末清初的一些读书人,身份不那么固定”5杨小京撰,〈默契神会,悟入真趣:清初鉴定家顾维岳事迹考索〉,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第140-150页。——不错,而我觉得上述这些人尽皆如此,不论能力高下,是否读书,有无藏品,都只在“成色”上有所区别。而且也必须提示,像王翚这样的人物,艺不压身,名闻海内,从事的活动更加复杂多元。他当然也做过类似的事情。6王翚也是与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都相识的人,他也为王氏提供鉴定意见。或许有人会问,本文讨论的密信会不会是写给他的?在此作一简单辩驳:《清晖阁赠贻尺牍》所录王鸿绪与王翚信,皆称其为“先生”。而本文讨论的信里,称对方为“年道丈”,语言习惯全然不同。另外,此书中收入一封龚翔麟致王翚信,说及刘松年、唐寅两幅画即将重新装裱,“应用何样款式,方为古雅,并恳先生-寄示”。这说明,王翚对装裱一行也不外道,不必只用“画家”的身份框住他。参见《清晖阁赠贻尺牍》,卷下,叶97。白谦慎与章晖曾经根据王时敏致王翚手札真迹指出,王翚在刊定此书时对事实多有删改。但一则无法找到所有的尺牍原件,二则本文所引都是与具体作品相关的具体事件,不涉及人物隐私,相信改动不会很大。更为直观地说:观察每一个具体人物,难免左支右绌,不见森林。集中讨论人们在为上层收藏家服务时的整体面貌,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类活动。7本文中的上层,与博士论文中的概念略有不同,指勋贵与重要文臣。品级较高或声望较大,均可视为“重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圈子是全国性的。我很乐意讨论次一级或“地方”的情况,但没有足够的文献来支持。过去我执着于区分“收藏家”与“鉴藏家”,现在已有所改观,本文统一称为“收藏家”;而讨论圈子时,则仍称为“鉴藏圈”。部分原因可以参见下文。另外,也必须说明:本文无意于抹杀中间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差异,也知道收藏家和他们之间可能只是“宾主”,也可以发展为“朋友”,关系非常不同。本文只是为了讨论这种活动的普遍性与重要性,才把他们的某些行为并置齐观。
二
中间活动直接影响了清初上层鉴藏圈的生态,也直接关系着怎样理解其中的众生相。现在先讨论其中两个方面:信息与鉴定。
翻阅顾维岳兄长顾复所著的《平生壮观》,董源《溪山行旅图》《龙宿郊民图》、米友仁《云山得意图》(书中名为《云山》)、怀素《自叙帖》全部赫然在目,只有柳公权《清静经》不曾入录。如前注所言,《平生壮观》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王翚也是与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都相识的人,他也为王氏提供鉴定意见。或许有人会问,本文讨论的密信会不会是写给他的?在此作一简单辩驳:《清晖阁赠贻尺牍》所录王鸿绪与王翚信,皆称其为“先生”。而本文讨论的信里,称对方为“年道丈”,语言习惯全然不同。另外,此书中收入一封龚翔麟致王翚信,说及刘松年、唐寅两幅画即将重新装裱,“应用何样款式,方为古雅,并恳先生-寄示”。这说明,王翚对装裱一行也不外道,不必只用“画家”的身份框住他。参见《清晖阁赠贻尺牍》,卷下,叶97。白谦慎与章晖曾经根据王时敏致王翚手札真迹指出,王翚在刊定此书时对事实多有删改。但一则无法找到所有的尺牍原件,二则本文所引都是与具体作品相关的具体事件,不涉及人物隐私,相信改动不会很大。92)。早在王鸿绪看到那些作品,写信求教之前,顾家兄弟了解它们已经快二十年了。这些人不只是以眼光而为大藏家所倚重,也未必只为一家一姓收买书画。既然圈子不全公开,人心彼此隔膜,那么,信息才是书画流通的关键。熟悉每一位“客户”的藏品,就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拥有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向每一位藏家提供他们感兴趣的线索,作品就顺势而流。下活一盘棋,正是中间人们对清初鉴藏活动最重要的贡献之一。8过去讨论清初书画收藏的大趋势,“南画北渡”是一个很著名的观察,刘金库甚至以此为他的梁清标研究著作命名,并强调了装裱师张黄美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可是,仅从本文涉及的几件作品来看,“北渡”并不如此普遍,王鸿绪看到它们时身在江南。何况,即使许多作品进入京官府邸,他们退休后仍会带回家乡。不要忘了,王、高、徐都是南方人。所以,可以说中间人促进了书画在鉴藏圈内的流通,但不必急于摹绘所谓的全局。近来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些情况并撰文讨论。刘亚刚认为所谓“南画北渡”的实质,是书画从明末以来旧族手里转入清初新兴贵族之家的过程。参见〈清初古书画“北移”现象之辨〉,第128页。
仅看作品上的钤印与题跋,或者会推断同时期的大藏家往往相识,有机会直接交易。但王鸿绪与高士奇的例子显示,并不全然如此。有时,书画在同时代的藏家间流传,可能是因为他们倚重同一位中间人。顾维岳本身就恰好能证明这一点:他帮高士奇补全藏品,也告诉王鸿绪“五字不损本”十分可贵,值得收购。是他穿针引线,直接促成了东西在几个家庭间流通。甚至有材料证明,有时收藏家会主动为中间人介绍工作——这也就等于帮助他们看到更多人家的藏品,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同时,可能也从侧面说明,这种经由中间人讲价来谈成交易的模式,是上下家双方都愿意接受的。有一封下款不明的尺牍,向宋荦介绍吴升,可以为证:
吴兄子敏少年绝技,且精于赏鉴,特命之一叩台墀。册叶无现成者,老长兄或以意授之,日内便可报命也。9原件收录在一套《宋牧仲家藏尺牍》中,西泠印社2016年春拍拍品。
这封信同时也提示我们:术业有专攻。有些知识,例如书画文献,只要已经刊刻,广为流传,则人人得而读之;对文人来说,检书尤其是本行中事。10但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在清初,许多重要的书画目录之属才刚刚刊刻,或者仅以抄本流传。另一些知识,譬如对作品本身材质的把握,对作品题跋与钤印信息“大数据”的记录,以至于对风格与水平的全面认识,他们就不一定都能擅长了。这些问题,看得越多,懂得越多。收藏家毕竟固守一隅,或者能通过权势,敲开一两家大门,遍阅其府库;或者能在自己不断扩充藏品的过程中锻炼眼力。可中间人有条件看到各家各户的藏品,或者至少把各家收藏信息并置齐观,这些经验弥足珍贵——他们不必一定拥有丰富的藏品,却在实践中获得许多经验,已经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鉴赏家”。所以,相对而言,他们是这类知识的生产者或传播者。11同时,我也认为,在理解《书画记》《装余偶记》这类笔记杂录与《庚子销夏记》《江村销夏录》那类书画著录的性质差异时,做这样的区分同样是有益的:他们的作者本非同一类人,关心的信息当然相当不同,想表达的内容也大有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前者几乎是一种工作手册,专门记录他们赖以生存的“行业信息”。甚至,这种技术能力和看问题视角的差异,也可以帮助理解何以《平生壮观》是如此独特的一部书。以后如有机会,这些问题都可以另外成文讨论。
即以王鸿绪此信为例,倘若顾维岳当年曾经有过答复,那么他需要详述自己对作品的看法,解释双钩、硬黄的边界何在,讨论割配题跋的可能性。至此已经没有实证,但还不妨鼓足勇气想远一点:他们所解释的技术方法,可能会成为小圈子里的共识。他们对名作真伪与优劣的判断,可能会成为它的附加信息,随作品一起不断流转。从而,他们的看法,实际上为“收藏活动成为一部历史”的过程推波助澜。
鉴定问题与此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谈论早期名迹时,常常提到它们如何流传有绪。清初距今已三百余年,当时重要收藏家的钤印和题跋,大多为作品的“真”,或者至少是“古”,提供旁证。也有学者拘泥于绝对的真伪,曾以现代信息条件下的新结论,批评某些大藏家眼光不佳。12我并不想做过分的推论,说收藏家在这些方面不过应声虫而已。只是,研究者立论之际,应当根据实情进行分析。遇到有中间人经手的买卖情况,须谨记“以孔还孔,以贾还贾”,不要把好话和坏话一股脑儿送给收藏家。
然而,回到当日的信息条件下,王鸿绪针对作品提出种种疑问,都期待顾氏给予解答。连他这样精于书法鉴赏,收藏过许多名作的人物,还要老老实实地求教。那么,今天通过题跋、钤印与著作看到的“清初鉴藏名家意见”,全然出自他们自己的认识吗?这个问题当然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不过,琢磨一下人们对中间人的描述,自有裨益。吴其贞说王济之:
际之善裱褙,为京师名手,又能鉴辨书画真伪,盖善裱者由其能知纸纨丹墨新旧,而物之真赝已过半矣。若夫究心书画,能知各人笔性,各代风气,参合推察,百不差一,此惟际之为能也。然只善看宋人,不善看元人;善看纨素,不善看纸上,此又其短耳。13[清]吴其贞著,《书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
说张黄美:
黄美善于裱褙,幼为通判王公装潢书画,目力日隆。14同注13,第441页。
这方面旁证甚多。例如,仍是《书画记》中记载的一位岳子宜,名声寥寥,只在地方上谋生,是一位“老裱褙,为嘉兴看书画得数者”15同注13,第542页。。这甚至提示:有大大小小的收藏圈子,也有不同层级、不同“主业”的中间人。但“眼光”,始终是他们谋生的看家本事之一。
退一步说,多数普通从业者,肯定没有机会锻炼出顾维岳、王济之那样的眼光,但他们也在以实际行动影响收藏家的鉴定结论。他们有的擅长裱褙,有的擅长拆配,有的擅长把零星作品集成全套。有的凭着高超画艺,在无数名公巨卿家频频出入,所见实多。收藏家倚重他们一天,与作品相关的认识,诸如真伪、优劣、鉴定方法等,就要受影响一天。16伪作很多,作伪手段很丰富,当然是常识,无烦外求,但眼力总要在实践中增长,这就需要讨论具体的作品。有时讨论可能是在中间人指引下完成的,有时则会不谋而合。王鸿绪给王翚写信,讨论一件《迂林优钵图》,双方在未经沟通之前,已经一致觉得画作本幅“尚有可疑”。参见《清晖阁赠贻尺牍》,卷下,叶78。不过,这并不代表王鸿绪眼力已经与王翚相当,注30、32、33所引诸条,都证明他还常要听取王翚的意见。只不过,面对不同水平的“客户”,中间人会决定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17陈定是我念念不忘的奇人,手段毒辣,风评不佳,但眼力应该不错。关于他的基本情况和藏品(其中部分可能只是过目作品)目录,参见注4,第415、425等页。章晖的研究指出,王永宁向王时敏购买藏物时,,“以陈定为眼”。周小英也提到,季振宜同样“藉陈定为眼”“与陈定胶漆”,要到王时敏家看书画。参见章晖撰,〈清初贵戚收藏家王永宁·下〉,载《新美术》,2010年第2期,第11-20页;周小英撰,〈烟客信札小疏:关于钱曾、陈定、张先三和唐光〉,载《新美术》,2012年第4期,第36-41页。王、季眼力平平,陈定就直接出手下判断了,这就是“授人以鱼”。当然,如果收藏家眼光太差,中间人自然有机会使诈,给他一条死鱼。
第三方面,尝试思考一下价格问题。王鸿绪的信里提到两个数目代词:“毛诗”和“名世”。它们分别是三百和五百的隐语,也就是说,董源《溪山行旅图》,本来要价五百两,王氏力请之下,对方松口,至少也要三百两才肯卖。王氏主动将这个信息告诉顾维岳。此处的价格不知是上家自行决定,还是由一位“上家的中间人”出面商谈。文献不足,且不多推论。不过,酌情定价确实是中间人的工作之一。有时,在传统上称为“掌眼”的那类活动中,已经可以看到为交易价格提供建议的情形。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通禹之鼎尺牍,上款不明。它恰好可以证明信息、鉴定、价格三者密切相关:
阅此画,似真,价不过雪花,多恐不当也。此轴乃耿三额驸所藏,非次等之物,谨复奉台裁,勿以鄙言为然也。18禹之鼎尺牍,文物号新00152035-11/22。
“雪花”仍是代指,不知是六两还是六十或六百两,总以贵者更为可能。禹之鼎说到,画是耿家旧物,来源可靠;加上质量很好,应是真迹,于是尽管谦虚,语气仍很笃定。若说到具体买卖中的定价问题,则有《清晖阁赠贻尺牍》中的几封信为例。王时敏与王翚诸信,频频提到“清河君”张应甲倚陈定为中介,到王家买画之事。其中一通说到张氏趣味陡变,忽然坚持要买“《曹娥》真迹”,可是“所许之值,不及陈生所言之半”,王时敏当然不肯。19《清晖阁赠贻尺牍》,卷上,叶22。张应甲也有信给王翚,全文曰:
昨赵舍亲回,展阅墨妙,苍古秀润,兼揽宋元之长。推为海内独步,非谀也。董北苑卷苍茫变幻,后半尤遒古胜前,自非法眼莫辨。思翁草书真而不精,惟画秀色可爱。石田大卷苍劲生动,仿米云山潇洒有致,稍以无款为憾。两陈书画虽不慊心,自是真虎。足征精鉴之不爽也。谢谢。庄淡老巨然《烟浮远岫图》议价二百金,恐稍增减,惟命是听可尔。20同注19,叶45。
这是王翚为收藏家提供鉴定服务的铁证21这种情况实在不少。《清晖阁赠贻尺牍》,卷下,叶71有王泽弘短简一通,最末曰,“顷有以赵卷求售者,其值甚昂,未知真伪,幸一辨之”。卷下,叶78,王鸿绪信也说,“兹有友人携鲜于伯几字卷、任子明画幅,大约是伪,惟祈法眼鉴定之”。卷下,叶111,张云章想请他鉴定自己最近几年收集的古书画。,同时,可能也反映出他在张应甲与庄冋生二人的交易中居间议价。如果张、庄两位可以直接讨论收购事宜,就不必将价格告诉王翚,更不用说“惟命是听”了。同类例证,可以再举吴开治信:
石田此卷颇费清心,不惮缕示原委,标举真确,可谓白石翁知己。既入法眼鉴定,自卓然无疑也……并以原卷价值托士奇兄交易,至送行图卷,亦希斟酌得之为快。如此韵事,仰藉韵人,感勒匪浅。22同注19,页54。
看来经过王翚鉴定,沈周一卷已无疑问,可以按照约定价格进行交易。而《送行图》一卷,还要王翚从中斡旋。从上下文看,这“斟酌”二字,很可能是指商谈价格。更直接的证据当然还要王鸿绪亲自来提供。他给王翚的信有好几封,其中有云:
书画一道,知音甚稀。时以古迹请示,非特评论价值高下,直以印证古今人心目也。23同注19,卷下,页78。
又有一次,王鸿绪遇到一套宋拓《大观帖》,无法决定买还是不买。于是他告诉王翚:
弃而不买,则爱其中仍有佳处;欲买之,则价甚重,而究是不全本,兼多损处。谨以奉览,幸先生教而酌之,果是宋拓否?索价囗百金,今还之百二,恐亦不能甚贱也。24同注23。本节引证的部分《清晖阁赠贻尺牍》材料,业师与杨小京在〈王翚与安岐〉一文中已注意及之,他们先于我讨论了王翚的鉴定眼光。此文收入《山水清晖:虞山画派精品特展作品暨研讨文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94-202页。
如此数例都说明,中间人往往从鉴定出发,顺势就参与了议价。即使不需要他们议价,收藏家也愿意主动告知价格信息,暗暗期待他们有所回应。现存的清初古书画价格材料很有限,有些标注在卷端的价格,甚至不知道是买入实价,还是卖出拟价。此外,清人购买书画的方式又很多样。这两个因素都导致眼下很难妥善地讨论书画的绝对价格,我本人过去的一些考量也未免胶柱鼓瑟。但是,换个角度,价格问题是认识的问题,它正是因此才与信息和鉴定息息相关:
在收藏史的无数故事里,像禹之鼎尺牍反映的那样,作品可靠度很高,来源清楚,品质又好的情况,是非常稀少的。多数时候,收藏家固然追求真迹,却也同样能够欣赏伪好物。可是,从真伪与优劣两个层面考虑,古书画至少有四个级别,25真而好,真而平常,伪而好,伪而平常。关于收藏家主动购买伪作的问题,同样有重要的尺牍材料为证,拟于另文讨论。价格当然与此挂钩。在理想状况下,一幅作品的成交价格,应该能够反映它的相对定位。26打个比方,晚明时期,沈周唐寅比荆浩关仝更贵,是受到好尚风气影响,没有道理可讲。可是两幅沈周之间、两幅唐寅之间的价格高下,却是由前述那些真伪、优劣之类的因素来主导的,仍可以相对比较。中间人越是掌握小圈子内的同类作品价格信息,就更有可能为一件需要定价的作品找准定位;经手的具体作品越多,对整体情况也就越“有数”。他凭着这些信息,要么在上下家两头打商量,要么为其中一头出主意,提供可资参照的市场价格案例。有时候,由他出面,恰恰是最得体也最有成效的方式。梁清标与宋荦一信曰:
承示二卷皆旧物,但王卷似南宋人画法,而阎卷又破损,无大意味。其索值太昂,愚意王卷不过七八十金,阎卷则三四十金耳。乞垂意确商之。如不便细讲,或呼王济之与商订,何如?27梁清标致宋荦信,见《宝鉴斋录存所藏宋牧仲存劄》,嘉庆郏志潮钞本,卷七,上海图书馆藏。
无论是因为上下家直接相识,不便讨价还价,还是考虑到士人对谈论价格之事多少有些介意,此处确实是主动请出中间人的例证。这说明,议价能力也是中间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至少,没有足够的眼光,没有“从业经验”,是很难做好讨价还价这件事的。同时恰好有一个反例,证明价格的公信力与鉴定眼光相关。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魏禧,是宋荦的前辈。宋氏不断送钱、送菜,照顾这位隐居不仕的老先生。他有信致谢,顺便帮自己的亲戚介绍文物。曰:
外沈画二十幅、题字二幅,舍亲欲得二金一幅。又,汉玉钩欲得五金。唯清鉴自别之,弟懵于识鉴,不敢一说低昂也。28魏禧致宋荦信,同注27,卷二,上海图书馆藏。
看来,“懵于识鉴”就无法帮着讨价还价。那么,考虑到真伪问题的复杂性,再考虑交易的普遍性,今天能看到的某些成交价信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作品的“看法”,而这“看法”,当然部分出自收藏家的“清鉴自别之”,而另外一部分,应当归于那些在鉴藏史上若存若亡,很难得到全面讨论的中间人。
三
从王鸿绪的信件出发,已经走得很远。现在是时候为上下两篇做出完整的总结。信件涉及的作品和人物都相当重要,它们反映出清初鉴藏圈的活跃程度。我认为这封信是写给顾维岳的。在清初的鉴藏圈中,有许多人像顾维岳一样,曾经在书画交易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不必纠结他们究竟是何身份,而应该关心他们从事中间活动的事实。
这些人出入许多收藏家府邸,过目既多,经验又足,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能够为合适的上下家牵线搭桥。同时,因为掌握的信息丰富,他们也是鉴藏圈内的知识生产者。今天看到的清初收藏家鉴定意见,不一定全然出于本人,也许还有他们潜移默化的功劳。信息与眼力使他们具备议价能力,理想状况下,为作品定价就相当于为它在艺术家的一生中找到定位。今日面对清初的书画成交价格信息时,不妨思考一下这些冷冰冰的数目字,是否可以理解为上下家与中间人达成一致的“看法”。
这些人活跃在从顺治晚期到康熙末的八十余年内,又在时世变化之后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是因为收藏风气渐渐趋于冷淡,大家不再积极记载这些人的故事,因为没有了那样的“时势”,也就不再会有这样一群“英雄”,还是仅仅因为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足够的材料,无法讨论乾隆时期及以后的书画中间人?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进一步讨论。
研究这封信及这些人群,并不只是为了厘清一点历史事实,而是为了引出我的观点:鉴藏史研究与其执着于讨论古书画的绝对真伪与优劣,纠结每一位收藏家或中间人的真实“鉴定水平”,倒不如梳理他们的活动方式,关心他们对作品的认识。显然,每一代人都在努力掌握信息,不断生产新知识,修正旧知识。这些知识的边界,决定了他们会如何评判书画作品,也就定义了当时的“鉴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