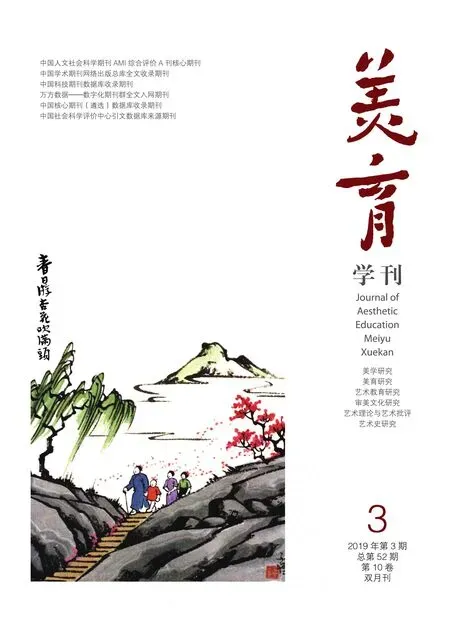试论金陵画派艺术风格的地域特征——以龚贤山水画为例
吴 婷,孙健环
(1.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2.昆士兰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以龚贤为首的金陵画派诞生于明末清初这一政治上极混乱、精神上又相当活跃的历史时期,是围绕于金陵这一地区的或深受其影响的以卖画或课徒为生的地域性绘画流派,其代表画家主要有龚贤、樊圻、邹喆、吴宏、叶欣、胡慥、高岑、谢荪等人。这实际上是一群籍贯、师承、风格及追求均不一致,常出入复社的画家,有人属遗民隐逸者,有人是文人,还有人属职业画家,他们之间唱酬往来,合作切磋,在艺术的道路上各显风采,有如画史所述“相互交游,以书画为酬答”,“面对尖锐的社会冲突,采取遁世的态度,沉湎山林,寄情书画,时人称为‘高士’”[1]。
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的环境历史学观点提到:“要想在自然界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之间划出一条简单的因果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它们互为前提,并且又都是对方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2]因此,作为地域性绘画流派,金陵画派虽然在师承及艺术风格的追求上各不一致,但由于其所生活以及所观察的客体都是金陵风貌,金陵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是影响画家进行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画家对于笔墨皴法、构图布局等艺术化的处理也都是师法金陵造化而来的胸中丘壑。对于金陵画家的艺术成就的研究,目前大多数都是集中于师承与创新、绘画理论、笔墨效果等角度出发,而忽视地域特征对于画家的影响;从地域特征出发来讨论金陵画派的艺术风格既有利于我们把握作品保持原创性的动力所在,也更能深入理解地域性绘画流派发展的方向。
本文即力图基于此角度,以代表画家龚贤山水画为个案研究,同时通过与其他金陵画派画家山水表达手法的比较,来探讨地域性绘画流派作品艺术风格中所独有的地域特征。
一、龚贤山水画创作背景
(一)龚贤于金陵的生平背景
龚贤(1618—1689),江苏昆山人,又名岂贤,字半千,又字野遗,或作野逸,号柴丈人。幼年迁居南京,青年基本在南京度过,晚年又回到南京。他在《溪山无尽图》后记自云:“余十三便能画。”但少时主要读“六经诸史”,主张“穷经致用”。他未成年时就与杨文骢、马文相识,这两个人是复社的活跃分子,他写下《赠友》一诗,回忆当年的生活:“江南六代风流地,白下多年翰墨场。”也写了《扁舟》一诗云:“短衣曾去国,白首尚飘蓬。不读荆轲传,羞为一剑雄。”大约在1644年,龚贤离开南京到扬州,清兵围扬州时,龚贤逃到泰州海安,在一户徐姓人家当了私塾先生,后来他又回到南京,在清凉山下弄得一小块田地,终于盖起了自己的一间宅屋,名为“半亩园”,在这里度过了20年左右相对平静的生活。金陵画家中的灵魂人物龚贤自秦淮结社以来,便“不幸以诗名”(龚贤《草香堂集·生日》),其实,他“十三便能画”,“垂五十而力耕砚田”(龚贤《溪山无尽图》),可见,龚贤诗画兼胜,晚年结识了《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并在扬州与石涛、查士标等人一起出席孔尚任主持的雅集,且与孔尚任互有诗画赠答。他身后的丧事还是孔尚任来料理的,而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与在龚贤的交往中完成的。
(二)龚贤山水画中的地域因素
长期的江南生活环境,使金陵山水都成为龚贤山水创作的素材,其山水画既注重在师古中创新,取法五代、北宋等传统精髓,又注重师法自然,在对景写生的创作过程中不断革新笔墨用法,发展了山水积墨画法,还形成别具一格的“黑龚”“白龚”的风格面貌。
“山水董源称鼻祖,范宽僧巨绳其武”,龚贤在其《云峰图》后如是题诗道。其师承关系一目了然,历代山水画师中,龚贤尤推崇董源、巨然、米芾、吴镇以及沈周等人,而这些人都以画江南山水见长,以自然为师,追求笔墨气韵皆是忠于自然实景的成功经验给龚贤带来很大的启迪。如方闻即指出董源皴法的地域特征:“董源的披麻皴在成为地道的带状书法性用笔以前,是表现南方丘陵土质山坡的最出色技法。”[3]董、巨对江南土质有切身的审美感受,他们以使用中锋为主,线条较柔,以接近平行的线条组合,这种松散舒展的线条可以表现江南丘陵绵延不断的起伏之态,反映土质疏松平缓的地貌,犹如披麻,故叫“披麻皴”。龚贤即一方面学习先人的笔墨技巧以更好地表现山石,另一方面也不断督促自己在学习中将古人作品与造化进行验证,乃言“心穷万物之原,目尽山川之变,取证于晋唐宋人,则得之矣”[4]41。在指导学生作画时更是反复提及“画泉宜得势,闻之似有声。即在古人画中见过,临摹过,亦须看真景始得”[5]129,“觉写宽平易而高深难,非遍游五岳、行万里路者,不知山有本支而水有源委也”[5]155。
在这样的观点中坚持着自己山水创作的龚贤,通过对金陵山水的反复观察以及对前人笔墨经验的总结,继承并发展了董源的笔墨语言以及米氏师造化和对生活感受的重视,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用墨技法(图1),其不趋时流的“黑、厚”面貌,不躁、不湿、不混、苍润秀美的墨色,通过对山石层层皴擦、积染,树丛近浓远淡,使墨色浓淡明暗变化丰富,画面层次饱满,表现出了秀润葱笼的江南景象,尤其烘托出那种山林雾气蒸腾,氤氲秀润的风格特征,成功地表现出在不同光线和水气笼罩下金陵一带山川景物微妙丰富的变化。

图1 龚贤 山水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除了笔墨效果,龚贤尤其擅长的“三远式”“半截式”画面布局的处理,不囿于平淡无奇的全景感,而是追求其所谓的“奇”而“安”,其审美趣味不仅对当时摹古之风盛行、程式化表现为主流的画坛来说具有超前性,其对自然实景的突破也是来自于金陵低山—丘陵特有的地域特征,这也是下文所要详细讨论之处。
二、地域自然因素对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影响
(一)地貌因素
“东尽钟山之南岗,北据山控湖,西阻石头,南临聚宝,贯秦淮以内”[6],《秣陵集》卷首《明都城图考》(图2)如是描述了当时金陵的地貌景观。从数据上来看,全市整体面貌主要是低山缓岗,包括占土地面积3.5%的低山,4.3%的丘陵以及53%的山冈,另外平原、洼地与河流湖泊占总面积的39.2%。山脉属以低山丘陵为主的宁—镇山脉,山脉向北凸起,耸立于长江的南岸,海拔不高。由是,南京自古就已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华南北的分界线,以及沿靠长江的独特地理位置,南京即已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中心,交通枢纽,经济中心。“在自然条件方面,南京除了有长江天堑,虎踞龙蹯的山川形式之外,周围地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六朝以建康为都正是看中其地的凭险可守与经济富庶”[7],孙中山就曾赞叹道:“南京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不难想见,无论是商周时期的吴国文化,春秋战国之际的吴越楚之城邑,还是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还是皆因南京这一“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的地貌而得以繁盛。及至宋代,山水画的兴起,这一只能用文字形容的地貌风景才开始成为可观的形象,进入我们的视野,此与其他地区所形成的地域差异,融入绘画的细节中,成为后代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源泉。

图2 明都城图
金陵画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出许多辨识度很高的富有金陵地貌特点并极富生命力的画作,或表现起伏绵延的山林,葱郁苍秀的树木,或表现岸汀水渚、江天空阔等浩渺之景,而有别于北方那种雄浑伟岸之山水。以金陵画派的代表龚贤为例,他的生活范围就是江南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地舆环境以江南水乡为典型,他的活动地带为江南、江北的平原及南京的山地,兼有江、湖、山色之美,而龚贤画中常见的题材就多描写水乡与平原、丘陵。同时也因其地处北亚热带温润气候,使得山间云雾蒸腾,湖上烟霭缥缈,冬季昼夜温差大而使水面易生烟气,夏季则暑气漫漫,常现水雾升腾,水天相连之状,因此我们既有幸闻得杜牧诗中“烟笼寒水月笼沙”的诗意,又更能理解画家笔下烟雾缭绕的金陵山水景貌,皆是师法造化而来的真实体察。
(二)地质因素
从地质方面来看,南京属于江苏省宁镇扬丘陵地区,地处低山丘陵为主的宁—镇山脉的西段,在地质构造上处在下扬子段裂凹陷带的一块,长江自西南向北流经市境中部。2亿年前,这里仍是一片海洋(下扬子海),石灰岩与碎屑岩相间排列出现,构成南京山地的物质基础,“主要由震旦系三叠系岩层构成,主要为灰岩、砂岩、页岩,经长期风化、侵蚀和断裂活动,呈现出峰顶浑圆,坡度平缓的特征;山前坡麓和谷地普遍掩覆着下蜀系黄土,是黄土岗地分布最广的地方;在流水切割下,岗地破碎,大都形成岗、塝、冲交替排列的特点”[8]。现今南京山地地形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地层岩石性质控制,另一个节制因素是地质构造,二者共同塑造了南京的山地。在这样的山地中,石灰岩便造成了浑圆的山链和浑圆的露头景观,“石灰岩形成的山,具有两种景观:从外轮廓来看,石灰岩山由于表面被熔蚀而形成圆浑的山形;从内轮廓来看,石灰岩地层的露出往往呈圆形的露头,露头周围有风化土覆盖,其上为植被(草、小树、灌丛)”,这两种景观“正是龚贤山石造型特征的原形,换言之,龚贤笔下画的是宁—镇山脉复背斜构造的两翼次一级石灰岩链地形”。[9]此外,还有侵入岩(如花岗岩、闪长岩等)的球状风化以及中、新生代的红色岩层可以出现圆形轮廓线。比如,蒋庙、岔路口的圆包形低丘,以质地松软的红色砂砾岩为基岩的清凉山,形成外形为圆包形的丘陵等,都成为龚贤等画家的一个创作参考。南京一带的气候、湿度及其对云气、光线的影响,特别是地形地貌的特征,也对重师造化的各家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带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貌,历经风化与水蚀,高处渐被削平,成为与安徽黄山、白岳所不同的岗峦起伏,更因山头风化土的覆盖,其多泥被草之状更有别于北方山水的石骨峻险。至于长江之外的湖泊水流,又是扬子江冲积平原的一部分,这些都成为忠实于大自然的画家的天然粉本,从而影响了绘画的面貌。
有学者提出“山水地质学”探讨龚贤绘画特点及与金陵自然环境之间关系,分析龚贤的雨点皴、豆瓣皴等多次积墨法,最能表现花岗岩表面粗糙的风化特征,以龚贤60岁时画的《龚贤山水精品》(图3)为例,在24幅山水画中,写平原景观的就有9幅,占37.5%,其作品中槐树形态的树木是扬子江冲积平原中最常见的,故称龚贤是“描绘扬子江冲积平原山水的第一位高手”。[9]龚贤将搜寻万物的目光集中到城郊蜀宁镇山脉的丘陵和沟壑,视之胜过古人,曾自谓“我师造化,安知董、黄”,虽则如是说,“但龚贤也是自相矛盾的,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会自题仿某某古代大师,可同时又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谓,而在我们目睹了《千岩万壑图》(图4)一类的画作之后,乃知其言并不为过”[10]。从山水地质学的角度分析龚贤的山水画特点,我们可以观察到其主要是低地、丘陵、平原三种形态。他的《夏山雨过图轴》(图5),“画的是金陵山地层峦,一坡一壑,山坡高拔,气势雄伟,雨后云气冉冉升起,前景是华滋的茂林,这种景色可以在栖霞山一角找到模式”[9],龚贤巧用“截取法”,他的画常常看不到山顶,也看不到山脚,即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半截式”山水,这一手法更是能衬托金陵低山丘陵性质的特征,取山地之一截,变低山为万仞,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9],例如《山居图》《云居图》《独庐》。由于南京的山地多为圆包状的山石和山冈,从扬子江畔到华南低山,常见丘陵地形景观,所以龚贤的山水画中,一山一水轮廓线均为圆浑曲线,不见方硬的转折,查士标说:“昔人云,丘壑求天地所有,笔墨求天地所无。野遗此册,丘壑笔墨皆非人间蹊径,乃开辟大文章也。”[注]查士标跋“龚野遗山水真迹”。龚贤描写的岩石地质构成,地表形貌如畦状,用中国人的说法,如皴折般。
三、地域人文因素对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影响
地域对山水绘画的影响不仅存在于自然因素对画家的视觉刺激,还有更为复杂深层的影响,就是地域的人文因素,即“这一地理空间内所留存的共同的、相似的精神传统和文化特质”[11]。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指出:
“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既可分析其静态,也可考察其动态。这样,文艺活动的社会现象就仿佛是名副其名的一个场……作品后面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地域概括了这个群的活动场。”[12]因此,从地域的人文因素来讨论金陵画派画家们的艺术创作是更为深刻和必须的,金陵特殊地貌所带来的士人的集聚、文化氛围对书画交流活动的推动以及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时代氛围,都对金陵画家对金陵山水的表达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金陵地区的文化氛围
明初南京就被确定为首郡,这里是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兴衰往往与政权的更替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六朝古都,经历了六朝、南唐和明清之际的三次文化高潮,文化底蕴尤深,绘画艺术也渐至繁盛。尤其是在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中,南京的地位更为瞩目。首先因为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会在此处举行,得以聚集一批文人,文风盛行遍及秦淮,且因皇亲国戚等位高权重之人的存在,为艺术提供了持久的赞助;又因国变之际,国势衰微,南京成为明代故都和故国的象征,也聚集了晚明各种有正义感和有识之士,他们结成复社,参与了各种活动,文人群体居多,金陵画派的画家几乎都参复社的活动。例如龚贤参加过“百二十人”的诗社,与东林党人、复社成员来往密切,一时间南京文化气氛特别活跃。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是旅游风气的盛行,出现各种旅游诗歌以及图文并茂、有导览功能的旅游书籍。因为时有被派去远方任职的官员,故士大夫间常有“宦游”的传统并进而推动旅游活动的发展,而明代的水陆交通也为这些活动提供了便利。在金陵,更是有“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彼此更相觑为景”[注]王士性撰《广志绎》卷二“两都条”。,“二月携酒游山,城南雨花台最盛,谓之踏青,每日游人晚归如蚁,迄三月终无间日”[注]王诰、刘雨纂修《江宁县志》。这样的情景。旅游作为士大夫间的一种文化活动,不再仅仅只是简单的娱乐休闲,它甚至成为一种身份区分和品位塑造的方式,文人们或品题吟咏,或以图绘加以表现,以金陵为例,就催生了许多“金陵胜景”题材的画作。
金陵的绘画传统悠久,这里的风光曾深深感动过董源、巨然。董其昌任礼部尚书时,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继承其传统的杨龙友、马士英至清初仍活动于此,同时在弘光的朝廷任都宪的邹之麟也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南京特有的地位,它自然成为安徽、娄东、杭州、江西各地书画家的集散地。安徽、武林各派的画风都因为人员的流动带到南京。南京在收藏书画上也已成规模,从黄琳开始,收藏家便成了画家最殷勤的接待者与资助人”[13]。周亮工弟子黄虞稷在周亮工《读画录·吴子远传》所收的一首诗中指出:“金陵昔时饶盛事,承平人物如菁莪。美之富文聚圆史(黄琳美之,有富文堂),姚公市隐来轩车(姚淛秋涧市隐图)。唐寅文璧座上客,髯仙秋碧人中豪。后来茅杨亦大雅(茅止生、杨龙友),诗坛画社相矜夸。”[14]而黄的老师,便是著名的收藏家周亮工。他始而宦游来此,继之在康熙己酉罢官定居于南京。龚贤说他因“有画癖”,“结谈画楼,楼头万轴千箱,集古勿论,凡寓内以画鸣者,闻先生之风,星流电激,惟恐后至,而况先生以画召,以币迎乎”[注]周亮工原藏《集名家山水册》之龚贤题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周亮工不仅以收藏之富吸引了画家,而且为卖画者提供了经济报偿,他积极与画家交友,组织诗画雅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京画坛的繁荣与艺事的交流,据《读画录》吴子远条记载,在己酉年末,周亮工曾“邀诸公为大会,词人高士,无不群集,数十年来未有胜事也”。[注]周亮工《读画录》卷四。龚贤也曾说:“画至今日,金陵可谓极盛矣。前此,文、沈、邹、董皆产于吴,比之三君八龙。一时星聚而至钟山之阳、淮水之滨含毫吮墨者,不啻百家。加以宦游、寓公,指不盛屈。”[注]周亮工原藏《集名家山水册》之龚贤题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看来南京画坛的兴盛,既有因为传统承接,又因为有不少流寓于此的画家加入南京的绘画行列,此间以金陵八家为代表,他们承继发扬董其昌松江派的传统,却在娄东、虞山之外自成面目。八家分别师承董、巨和宋、明人传统,从不同侧面融合吴门画派、武林派乃至浙派的传统,创造长于描写地方风光的不同面目。尤其吴门画派注重以温润的笔墨对实景山水的反映,指引他们把取景的视角转向金陵城郊的山野等地。清初的南京画坛,并不曾像安徽那样形成比较接近的审美内涵,也未产生像蒌东、虞山等派那样异中有同的画风,但是,南京特有的历史、地理和人文条件,画家或以画隐或以画为生的创作目的,却也导致了下述特点:以画为隐的优秀文人画家,大多不以笔墨谴情为皈依,也不表现安闲自在的贵逸之气,而是在个性鲜明的风格中,表现不受拘役的自由精神。以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不仅往往兼工山水、花鸟乃至人物,而且长于描写南京一带的地方风光,从中透露出牧歌式的情味。
(二)改朝换代的时代氛围
公元1644年前夕那一段岁月,农民起义,清军入关,晚明政权岌岌可危,最后以崇祯皇帝在煤山的自杀而宣告了这一王朝的覆灭,民众深陷“山河破碎风飘絮”之中,难逃身体的颠沛流离和精神上的无所归依。用石守谦的话来概括:“这一段日子里的金陵,基本上是风月繁华与政治倾轧、国事如麻的混合体。”[15]332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志士更是重复叹息着金陵的破败,借以怀念往日繁华,“王气消沉石子岗,放鹰调马蒋陵旁”等与金陵实景密切相关、感怀故国的诗句不绝于耳,可以想象生活在其中的金陵八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也难免没有自身情感的渗入。龚贤即作了《燕子矶怀古》感怀:“断碣残碑谁勒铭,六朝还见草青青。天高风急雁归塞,江回月明人倚亭。忆昔覆亡城已没,到今荒僻路难经。春衣湿尽伤心泪,赢得渔歌一曲听。”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期,画家们是如何处理情感与创作的关系,甚至为何还有“金陵胜景图”这种看似毫无伤感情怀之作的出现?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为金陵八家之画家,樊圻、叶欣、吴宏等对金陵山水的怀旧忆写尤为典型,石守谦即提到“他们在进行此种怀旧风格之制作时,总是以金陵的某些实景为基础,除了清丽的描绘之外,再加上一层如诗化之处理,将金陵地景与‘断草荒烟孤城古渡’之淡淡凄迷感叠合在一起。”[15]339叶欣在其所作的《山水册》第七开《亭台游春》(图6)就采用这样的手法,画面以清丽之色给人一种诗意的浪漫,却因画面中的几处孤枝独木以及低平空阔的野水转化为清冷萧瑟之感,连画面下方那游走在“断草荒烟”中的两人都让觉得仿佛在感慨故去的繁华,流露不舍之情,隐含着“艺术家身处其中的无力与孤独”。
这一时期“金陵胜景图”的出现是否就说明画家的心情与所画之景是矛盾的?为何当时的文学作品多是感伤情怀的咏叹,甚而龚贤的“槖驼尔何物,驱入汉家营”也体现了内心的不平,在绘画创作上却似乎没有直接标明感怀故国之作,却只能从极隐晦的意象上让后人来揣度画家的心境。对此,姜斐德做出过相关解释:相较于口头传播,视觉图像会带来更大的危险,人们相信图像会像符咒一样传播开来,吉祥的图像会带来好运,而一幅残破的图像会促使人们把图像当作现实场景的反映,带来不幸。[16]就如艺术史家巫鸿所述,厌恶描述破败景象也许是因为这些图景表示不祥与危险,“他们震撼了他们的观众,因为他们记录、描述、保留或模拟了’毁灭’——作为暴力和凶残的代表的毁灭带给一个人、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是受伤的肌体和心灵”。[16]因而,我们可以理解樊圻在他所作的《青溪游舫》(图7)中,同样表现秦淮河的画面时,并无诗歌中所言的“枯井颓巢”“砖苔砌草”之萧索枯寂,而是通过相对较高的视角以及稍显明丽的色彩,很显然这不是对当时实景的描绘,更似对往昔胜景的追忆,通过今昔之对比,更能引发遗民的感伤怀旧之情。

图6 龚贤 亭台游春图

图7 樊圻 青溪游舫图
此外,吴宏、龚贤等人选择的倒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吴宏在其作《燕矶》中就表现了多处惨败倒塌的山墙,《莫愁旷览》(图8)更是真实再现了莫愁湖“鬼夜哭”般的衰颓,通过萧索的寒林、零星的村舍、破败的湖心亭等建筑遗迹、倒塌的院墙,唯有两名孤独的文士遥望着空寂辽阔的湖面等情景,直接给观者带来了持久的震撼与叹息。

图8 吴宏 莫愁旷览图
同样处理这一问题时,龚贤的画作《千岩万壑》(图4)石守谦认为“很精彩地显示了龚贤这个与感伤相连的复古行为”。它的风格甚至可以追溯至金陵绘画传统之根源,他在处理岥石虚实与云水之间抽象式的交互嵌置效果可见于魏之璜的《千岩竞秀》(图9),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动态气势。画面中的奇峰,块面的分割与突兀的柱锥状造型并行处置,与稍早期的吴彬有相通之处,更主要的影响仍来自于五代的董巨传统,尤其是山水受光照而产生的强烈的光影效果。此卷除了表现他向传统的回归,亦包含了他对所处时局产生的深刻感伤,画面中“只见群峰不见天”的构图处理,全轴中各种物象相互挤压而产生的逼人的压迫感,正是来源于作者的内心,正如他自己所说“千山万壑一人家,白石为粮酿紫霞。尚尔逃尧犹未出,避秦若个向云涯”。将感伤与复古相连,既充满对今昔的无奈又满怀着对往日追忆的深情,竟真从这看似冰冷的山石间弥漫出来,感动了画外之人。

图9 魏之璜 千岩竞秀图
(三)西方绘画技法的影响
以前述龚贤《千岩万壑》(图4)为例,它除了表现出技法处理上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它还吸收了当时由西方传入的铜版画的影响,高居翰在《气势撼人:17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中分析得尤为详细。17世纪的金陵正是多种思想交织活跃之时,此时欧洲传教士抵达此地,传教过程中携带着有关西洋国土的图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急于探索突破的金陵画家们,它不仅为中国绘画提供了新的再现技法,也为传统笔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帮助山水画家们突破了传统的成规,从有限的山水类型中解脱了出来。龚贤用明暗交替手法表现有深度感的连绵山峰时即可能受到了欧洲版画的影响,他在处理岩穴组成及岩穴周围的岩块时就类似布劳恩与霍根贝格编纂的《全球城色》中的圣艾瑞安山景图,岩穴虽是中国画中的传统题材,但其表现的岩穴两侧垂直地面,渐行渐窄,并渐入山间岩道的处理方式以及明暗技法,很明显是来自于西方。同时他的《千岩万壑》与《全球史事舆图》中的《田蒲河谷》(图10)也颇有相似之处:由右下角向左上角的对角线构图,强烈明暗对比造成的戏剧性效果,溪流、山径、云雾等交错纵横之感,画幅顶端触手可及的云层以及如角型塔一样的山峰构成和排列等。而这些处理方式,大都来源于西方的山石构造和周遭景色,在龚贤画笔下宛如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图10 田蒲河谷图
四、结语
由此观之,无论是别具质感的金陵山石,还是龙盘虎踞的风貌,抑或是繁华过后的旧都,守望在这一方的画家们,都或以皴笔勾勒,或以墨法氤氲,或以布局置胜,让我们照见了古代的画家们是如何“师法自然”,在尺方天地间再塑金陵的真实风貌。在研究区域性流派的画家时,通过对地质地理和具体画面的比较也为我们打开了更多的思路。金陵的画家流传下来的作品有很多,集中了江南风景的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渺远寂寥……其旨都在于体现真实的山壑气势。正如龚贤所言“古人之书画,与造化同根、阴阳同候,非若今之人泥粉本为先天,奉师说为上智也”[4]41,即要理解众多自然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且要以目所能及的可视形象把握其运动变化的势态,用真实的造化去检验笔端的意象,实为后人所应学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