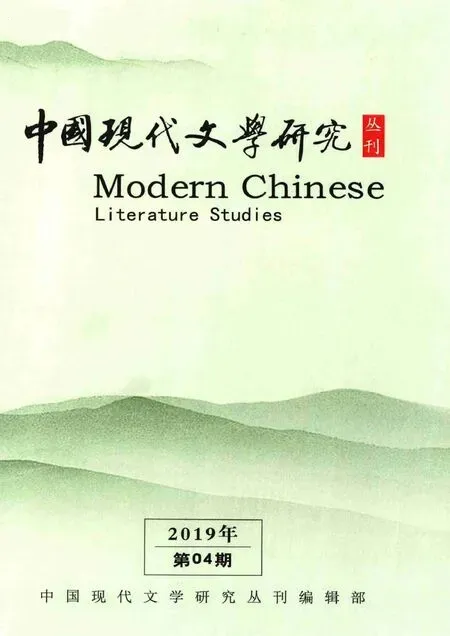《老同志》与沈从文创作转型的努力
李 斌
内容提要:短篇小说《老同志》是1949年后沈从文重新开始小说创作的第一次试笔之作,通过对劳动模范的歌颂表达了沈从文靠拢人民文学的真诚努力。但对于具有成熟创作理念和技法的沈从文来说,这个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小说充满了意义缝隙。沈从文努力书写劳动,但对劳动性质缺乏分析,文字也较为浮泛。通过魏同志和小花猫的情节,他发挥了书写农民“把生命谐和于自然”的特长,却跟他“管理生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相矛盾。他意图融入思想改造的主题,却将农民置于思想改造施动者的位置。沈从文无意于去弥补这些缝隙,这成为他既努力融入新的时代,又保留较多积习的症候。
沈从文在近年来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对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行做文物研究,学界多有惋惜,且居多将原因归结为政治压力,而对于其转行的过程缺乏更细致的探究。其实,1949年后,沈从文通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和参加内江土地改革,对新政权表示了由衷的认同,他渴望发挥自己的特长,以小说创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多次尝试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出能为当时批评界所接受的作品。短篇小说《老同志》正是他试图改变风格的第一次尝试。
《老同志》初稿于1950年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间,其后数易其稿,现在收入《沈从文全集》的是他1952年1月14日在内江完成的第七稿。沈从文对这篇小说十分重视,在家信中多次提及修改情况,并请妻子张兆和代为投稿,但没有成功。1952年5月,他又亲自寄到某报编辑部,3个月后被退回。他随即将稿子寄给丁玲,表示不拘刊物大小,甚至可以不署他本人姓名,只求能够发表;如果不能发表,他也渴望丁玲指出缺点。现在已不清楚丁玲是否回信,《老同志》在当时没有发表出来。学界对于沈从文这次重要的创作尝试尚未展开讨论。本文拟通过对《老同志》的分析,探讨沈从文向新的人民文学靠拢的努力情况及龃龉所在,以丰富对1949年后沈从文基本从文坛消失这一重要文学史事件的认识。
一
《老同志》取材于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生活,以炊事员老同志、魏同志为主人公,歌颂他们在服务学员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热爱劳动、厉行节俭的优良品质。《老同志》“十分中有八分是写实(十分九分),特别是那猫儿的关系,工作神气,以及当事演说后大家的情形”。①此言非虚,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包括两位炊事员、教育长、学员以及叙述者“我”,都能在革大中找到原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由于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对干部的需求量增加,加上很多从国统区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需要思想改造,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各新解放区纷纷成立人民革命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于1949年2月,属中共华北局管理,有北平本部和天津分校两处校址。本部校址在北平西郊万寿山湖畔的西苑,校舍原为清代的大营房。校长刘澜涛,教育长侯维煜,学员9000余人,分为四部。第四部为政治研究部,招生对象为党外民主人士和旧社会的上层分子,学制6个月。1949年年底,政治研究部第一期学员60余人毕业,有数人留校执教。1950年2月6日,刘少奇批示说:“革大政治研究班已在党外人士中建立了一些信仰,拟继续扩大办下去,各地高级军政旧人员及知识分子愿来学习者,可以送来。”②
1949年8月,大病初愈的沈从文由郑振铎介绍,人事关系转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1950年3月2日,也就是刘少奇关于革大扩办的批示之后,沈从文由组织推荐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多月后,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并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部,沈从文随着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部第二期学习。
华北革大所设课程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当前各种政策,共产党的建设及其历史等四大部分”。学校为学员配备了当时中共党内较强的师资队伍:“薄一波同志的政治形势,黄敬同志的人生观问题,安子文同志的介绍中国共产党,杨献珍同志的唯物史观,艾思奇同志的社会发展史,冯文彬陆平同志的建团报告,还有马列学院许多同志的班联课,宋平同志的介绍苏联青年团,刘宁一同志的世界各国情况,和中国革命胜利对于世界的影响及郭沫若先生演讲介绍苏联等。”③政治研究部第二期的学员既包括中共一大代表、前国民党内政部参事包惠僧,前国民党第53军少将副军长赵镇藩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包括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张舜徽等著名学者,刘天怡、刘健康、彭清源等留学归国人员,还包括刘国光这样的曾在西南联合大学上学,现在中国科学院任职的属于沈从文学生辈的年轻学者。
沈从文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表明了新政权对他的接纳。沈从文也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所长为新政权服务,于是创作出了《老同志》。这篇小说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题材,既没有写在该校授课的教师和教学情况,也没有写沈从文那些大名鼎鼎的同班同学,而是选取了在学校中相对边缘的食堂炊事员老同志为主人公。如此选材,体现了沈从文在发挥创作优势的基础上靠拢人民文学的努力。
《老同志》开篇写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部开学典礼上教育长的致辞:
……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比如我们这里一字不识的炊事员,因为出身是劳动人民,立场坚定,就容易领会马列思想和唯物论精义。同学应当向他看齐……④
教育长致辞中提到的炊事员给小说中的“我”和同学们以很深的刺激。“大家情感上不免受了点刺激,思想上有点儿迷乱。”对于这些大知识分子来说,“学习第一课碰上那么一个题目,自然想不通”。⑤小说以此逆入,开始对炊事员老同志的书写。
这名炊事员是有原型的,即当时著名劳动模范刘洲。《人民日报》1950年3月5日(即沈从文进入华北大学的第四天)第6版刊出通讯《第三次当选模范——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特等模范炊事员刘洲同志》,通讯表扬了炊事员刘洲“忠诚老实、吃苦耐劳,对同志团结友爱,对工作力求精简节约”的品质,并举出具体事例及周围人对他的评价。
教育长让学员向炊事员学习,《人民日报》表彰劳动模范刘洲,都继承了陕甘宁边区的新传统。延安整风后,各级政府有意塑造各个行业的英雄模范,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解放日报》刊文指出:“一线工作中出了一个或几个这样的英雄与模范,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就可以把一项工作做好。”⑥陕甘宁边区塑造的模范人物有赵占魁、吴满有、刘建章、杨步浩等人。《解放日报》1942年发表社论《吴满有——模范公民》,1943年又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提出了“吴满有方向”,号召大家向吴满有学习。丁玲在1943年2月延安文化界举行的欢迎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三位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上说:“过去总有些感伤的性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⑦3月9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整版发表了艾青歌颂英雄劳模的长诗《吴满有》。表现英雄模范人物,已经成为人民文学的新传统。
1949年后,一直以丁玲为榜样的沈从文对这一人民文学的新传统应该是了解的。《老同志》表彰劳动模范,体现了沈从文融入人民文学的努力是真诚的,也是极富智慧的。这篇小说在题材选材上的成功,还体现在它符合沈从文的创作经验和在华北革大的生活体验。
厨子是沈从文小说中的重要形象。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在《我的教育》中,沈从文叙述道:“兵士一有了机会,就又把从上司处所记下的新颖名词加到火夫头上了。火夫则只能互相骂骂,或对米桶,水缸,汤杓,痛切的辱骂。照例被骂的自然是没有做声。”⑧但这些伙夫却有着沈从文所欣赏的忠厚善良的品质。《灯》中的老兵原是军中厨师,他来到城市,尽心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叙述者对他满含深情:“我望着这老兵一个动作,就觉得看见了中国多数愚蠢的朋友,他们是那么愚蠢,同时又是那么正直,那最东方的古民族和平灵魂,为时代所带走,安置到这毫不相称的战乱世界里来,那种忧郁,那种拘束,把生活妥协到新的天地中,所做的梦,却永远是另一个天地的光与色,我简直要哭了。”⑨如今厨子以老同志的身份再次出现在沈从文笔下。
沈从文“进入革大学习是怀着压力进去的”⑩,他对于革大的群体生活很不适应。华北革大主要由教员、学员和工作人员组成。沈从文对教员并无好感。“初到华大,听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倒只为他着急。因为不像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只感觉国家一定还有困难,不然怎么会这么来领导新教育?除了共产党,从各方面工作,爱这个国家的人还多!即不是党员,牺牲了自己来爱党的也还有人!这种讲演要的是什么效果?华大如真那么办下去,那么领导下去,照我理解,对国家为无益。”⑪对于革大的学习活动,沈从文也不大喜欢。“半年学习,理论测验我大致常在丙丁之间,明白政治水平十分低,而且明白那么出问题回答的反复测验,慢慢的,把一点从沉默中体会时变,有自主性、生长性,来组织文字写点小说的长处,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耗蚀了。”⑫沈从文坦言,在革大期间,“对同学关系,我作的不算好”。这些学员在《老同志》中虽然并没有表现出如沈从文在1930年代小说中所批评的都市人的特征,但诸如“娇气”等词仍然出现了。小说中,有位学员对老同志说:“老同志,你怎么不去看戏?今晚戏好得很!还有北京城里来的魔术,对口相声,不容易见到,快看看去!”⑬这偶一闪现的学员业余生活状况,在沈从文的书信和日记中受到很多批评。沈从文在华北革大期间的日记中写道:“吃饭时几人谈‘风流’。极离奇。有些人似乎不找些无意义话谈谈,即不能过日子的。从谈话中也可见出一个来源不一的群,只有用一些不相干而又有共同性的闲谈,方能联系。除谈这种闲话外,即玩牌、玩球、玩棋等。唱京戏也是一种,不过这种走群众路线的玩意儿,对我实在毫无办法。”⑭在给亲戚的信中,他又说:“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方式,我总觉得格格不入。”⑮
沈从文较有好感的,是远离课堂和学生集体生活的厨房的八位伙夫。“在那里只八个厨师傅还像是朋友,从他们学的可能比从小组学的将来用处多。”⑯“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也有价值得多。老同志似乎寂寞得很,昨早天未明即见他蹲在煤边敲煤,晚上去倒水,又见他独自靠在饭厅外木撑架边。几个年青的都上学去了,还未回来。问他‘怎么不休息?’说‘还不想睡。’每天吃烟半包,每包值八百……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比起听同组空谈有意义得多。有教育性得多。”⑰“对工作干部,由上到下,只和炊事员接触较多。他们沉默服务的态度,必然对我有长远影响。”⑱
沈从文习惯于在小说中表现厨子,在革大期间又跟炊事员接触得最多,对他们也最有感情,以此为题材创作小说对他来说是比较自然的。
二
小说中的老同志五十七岁,来自北京西郊青龙桥红山口北村。他长期在家务农,家里两亩地,屋前有枣子树,农忙时常给地主家打短工。解放军到北京西郊时,他加入革命队伍做人民勤务员,华北革大成立后调入革大做炊事员。
虽然正如沈从文所说,《老同志》贯穿了“反浪费、应节令”⑲的时代主题。与《人民日报》所报道的刘洲先进事迹相似,老同志“烧火加煤就得和绣花织布一样,格外细心。敲煤时照例块子都不大不小,骨牌片儿有个一定分寸,送到炉中去,火力才又猛又停匀”。⑳在老同志的努力下,食堂用节约下来的煤炭钱添置了二十五张桌面。但老同志最突出的品质,是对劳动的热爱。他“手足贴近土地辛苦勤劳五十年,性情成了定型,沉沉默默,只做事,少说话”。“每天只是一声不响的低头把事情作下去。”㉑“平时极少说话。一天有大半时间,都蹲守灶炉边工作。”㉒
沈从文从老同志对劳动的热爱中找到了共鸣,因为他本人在革大期间也热爱劳动。他疏离于同学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闲不下来,“看来看去,只毛房没有人打扫,就不经许可,当成我的业务之一了”。㉓据同学回忆,有一次放假,学校中“大约有几十年没洗涮干净的小便池里又臭又厚的积垢,都被刮洗得干干净净,十来个池子,个个如此”。经过大家调查,原来是沈从文干的。“呆在这里,没有事干,就用刮胡子的刀片(单面的)慢慢地一个一个池子刮,花了整天的时间,总算大致弄干净了。”㉔这件事,沈从文在给亲友们的信中也多次提到,他认为这也是学习,“这种学习并不使人堕落,只会更加爱这个国家的。劳动创造了人是事实,天下事总得要人从劳动来解决,来推进”。㉕
劳动问题也是华北革大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华北革大学员何兆武回忆说:“社会发展史上说劳动创造世界,我们有个女同学四十来岁,是基督徒,课堂上发言,坚持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我觉得‘劳动创造世界’这句话确实有问题,应该改成‘劳动创造文明’。”㉖政治研究部学员谢晋日记也记录到,他们讨论了“先有劳动还是先有思想?二者关系如何?”这次讨论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坚持思想在先,劳动在后的一方,堡垒没多久就被打垮了,纷纷举手投降”。㉗尽管沈从文认为与其空谈和进行空洞的理论学习,不如实实在在去劳动,但从何兆武的回忆和谢晋的日记来看,《老同志》以“劳动”为主题却体现了革大理论探讨对沈从文的影响。
热爱劳动是新社会的道德伦理,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老同志》没有区别对待不同时代的劳动性质。老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热爱劳动,他被军阀地主欺侮,“只是在无望无助中熬,干一顿湿一顿不成个生活”㉘,热爱劳动和他的忍辱负重并行不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热爱劳动依然是他可贵的品质。沈从文没有弄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两种劳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老同志之前实际上“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劳动产生的价值被无偿占有了,如果他对这样的身份没有自觉,对这样的处境没有反抗,则他的劳动是不值得歌颂的。“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㉙因此,只有在老同志翻身做了主人之后的劳动才是值得歌颂的。沈从文对这两种劳动的性质没有区别,跟他在革大理论测试常在“丙丁之间”有关。由于没有分清劳动的性质,《老同志》对劳动的歌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距离。
在沈从文写作和修改《老同志》时,思想文化界正在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日报》社论认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㉚这篇社论发表后不久,沈从文就写了《〈武训传〉讨论给我的教育》,他说他没有看过《武训传》,“但事先却看过李士钊的画传原稿,是在革大时,记得曾经还要我写点序,没有写”。所以他对这件事并没有太多感触,却在文章中批评了“近两年来文教政策”的“偏颇”和“陷于主观”㉛。毛泽东发起《武训传》的讨论,是希望知识分子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评判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包括郭沫若等很多知识分子都结合这次讨论做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老同志在军阀地主的欺负下“在无望无助中熬”和武训行乞兴学在性质上相差不远,老同志的勤劳可能会被认为和武训的勤劳一样,在旧社会不仅不会是高尚品质,反而是不具反抗精神的“奴颜婢膝”。但沈从文并没有能够从《武训传》讨论中汲取思想资源,去辩证分析老同志的历史和现在,区别对待老同志忍辱负重的劳动和为人民劳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
沈从文在内江修改《老同志》时曾批评当地诗人说:“特别是不会写平凡时,不会写静,不会写家常,因之写特别事,写动,写变故,也无个对比,易失于夸,而得不到准确生动效果。”㉜无论是热爱劳动,还是厉行节俭,《老同志》都是几句话就写完了,对此的表现很浮泛,并不符合他对好作品的要求。但沈从文又说,《老同志》的“毛病可能还是‘太细’。但如果翻译成英文,照例要细到这个样子,才够小说条件的”。㉝这里的“细”突出表现在魏同志和小花猫的情节上。
魏同志午休时,小花猫和他一起睡。“有时睡不着,即在床上地上跳来跑去,抓抓咬咬自得其乐。偶尔在魏同志坦坦荡荡大腹上吵闹,人被搞醒后,魏同志必细声细气,充满父性情感。”小说还模拟了魏同志和小花猫之间调皮而又亲热的对话。“小花猫的年龄,适和个六七岁生命活泼孩子一样,虽通达人性,不免稍稍顽皮。自己既不想睡,就把身子尽挨着魏同志肩脖和宽脸,憨憨的十分亲昵。并且像是还有些不成熟意见,不提出憋在心里不好受。一切行为让魏同志在迷糊中感觉到毫无办法。”㉞
魏同志和小花猫的细节在《老同志》中像是意外之笔,跟小说对劳动和节俭的赞美没有关联,也和他对业余时间的规划相矛盾,但熟悉沈从文小说的读者对此却并不意外。表现底层人物与小动物的和谐相处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主题。在发表于1929年的《牛》中,大牛伯因为打小牛打重了,造成一幕生活的轻喜剧。大牛伯给小牛抓了药。“回到家来他望到那牛,那牛也望到他,两个真正讲了和,两个似乎都知道这脚不是一天可好的事了,在自己认错,大牛伯又小心的扳了一回牛脚,看那伤处,用了一些在五月初五挖来的平时给人揉跌打损伤的草药,敷在牛脚上去,用布片包好,牛像很懂事,规规矩矩尽主人处理,又规规矩矩回牛棚栏里去睡。”到最后,“牛伯因为体恤到伙计的病脚不敢悭吝自己的力气,小牛也因为顾虑到主人的原故,特别用力气只向前奔,他们一天所耕的田比用工人两倍还多。”“回到了家中,两位又有理由做那快乐幸福的梦了。”㉟在《会明》中,主人公伙夫会明在前线阵地上养了一群鸡,“他喂鸡,很细心的料理它们,多余的草烟至少能对付四十天,他是很幸福的”。㊱二十多年后,大牛伯和小牛、会明和鸡在沈从文笔下演变成了魏同志和小花猫。
在写于抗战时期的《虹桥》中,沈从文认为,革命者和农村问题研究者“所知道的就只是农村生活贫苦的一面”,“只知道他们缺少什么,全不知道他们充足的是什么”,而在他看来,“充足”的是“农民的生活平定感,心与物实两相平衡。增加财富固所盼望,心安理得也十分重要”。“信仰简单,哀乐平凡”,“把生命谐和于自然中,形成自然一部分的方式,比起我们来赏玩风景搜罗话本的态度,实在高明得多!”㊲大牛伯和小牛、会明和鸡、魏同志和小花猫正是这种“把生命谐和于自然”中“心安理得”的重要例子。
在《老同志》中,这种“把生命谐和于自然”“心安理得”的例子随处可见。夏天的厨房十分炎热,“但在炊事员一面,却从这种高度服务热忱下,说着冰呀雪呀的快乐笑话,把个三伏天满不在乎的打发走了”。老同志“生命的火和大炉灶中的高热炉火,俨然融合而为一”;“到月头发薪时,就把应得工薪捎回去,给侄儿补贴家用。顺便买点米花糖给孙娃娃。平时很欢喜两个孙,回头即和他们到地里去,看看地中生长的菜蔬,捉捉虫,浇浇水。间或还带点新成熟的茄子黄瓜四季豆,回学校添配到菜里去,给同学尝尝新。”㊳只是在小说中,沈从文不再使用“谐和”“古民族和平灵魂”这样的词语,而是用了“素朴和忠诚”,并将其上升为“无产阶级高贵品质”㊴。
“把生命谐和于自然”,体现的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的尊重,和沈从文规划的“管理生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是矛盾的。沈从文当时提出:“凡土改后的区域,人的双手都从束缚中得到了解放,但解放后的双手,如何去使用他?”他觉得应该发起“管理生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㊵。斯达哈诺夫是苏联的采煤工人,1935年,他“在熟练的技术基础上,合理地组织了生产过程中的每一动作,使每一分钟的生产时间也不浪费,打破了旧的生产定额”。他的做法得到肯定和仿效,苏联掀起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要求工人们大家开动脑筋,在工作中找窍门、挖潜力,以最少的劳动和最短的时间,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生产品”。㊶对于斯达哈诺夫运动,《解放日报》也有过介绍。沈从文要求向这种运动学习。每个人办公时间不能浪费,“办公以外的私时方面,调查统计一下他的用途,是些什么样耗费方式,且分析一下他的效果作用”,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国家计划经济实施中,先把人的生命时(或剩余劳动力)统统计划一下”,“或者使之生产物,具体的物;或者使之储蓄为能,可以在另一时转化为物的能”。㊷他所喜爱的那些“把生命谐和于自然”的细节,并不能够超克自然时间去生产物或储蓄能。这一矛盾沈从文没有能够解决,体现了他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节。
三
老同志不识字,学员问他:“老同志,你可学习马列主义?”老同志回答说:“同志,我不认字!人老了,记性不好。自己姓名也不会写。”这位不懂“马列主义”的农民,却对学习过马列主义的某学员进行“启蒙”:“我们没有知识,一天就烧火做饭。学校好多事情要人做,大家都在忙!我的事情容易做。敲敲煤,放放水,帮他们做点杂务,不费力气的。上月里抗美援朝,好多同学都报了名,去朝鲜帮朝鲜人民打美国鬼子,把鬼子赶下海里去,多好。打仗可不容易!事情不论大小,大家齐心合力作,就好办!”这些学员,在小说开篇对教育长表彰老同志,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的话是想不通的:“学习重联系实际,不以读书多少为准,一时难行通。学习马列不读书,图书馆那些大本本马列全集怎么来的?印出来又有什么用?”㊸某学员经过老同志朴素话语的“启蒙”之后,联系老同志平时的表现,突然醒悟了:“觉得话语浅显意思深,满有道理。比起几次小组讨论道理似乎还明确深刻。以为恰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结合国际主义最好的注释。可是想起老同志最后问他的几句话,不免打了寒噤,不住骂自己混蛋狗屁,用来惩罚自己在美国大学念博士学位,多年来升官发财往上爬的糊涂思想和卑鄙打算。”㊹
这其实体现了沈从文对思想改造认识的不足。《老同志》的初稿还没有突出思想改造的主题,在第四稿后,小说的主题则越来越明确。在第七稿完成后,沈从文在家信中说:“今天已把革大那个《老同志》故事改写完成,似走了样,主题转到知识分子改造去了。”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当时的大事,政治研究部的主要目的正是让国民党上层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改造他们的思想。改造思想的施动者,当然是艾思奇等革大教员。但在《老同志》中,“马列主义”是可以不学习的。小说中提到的“小组讨论”是革大的重要学习方式,“由班主任、班干部开列题目,学员分头准备,集中发言和交流讨论”。㊻学员在准备工作中,则需要仔细阅读消化马列主义书籍。而老同志的简单几句话,比这些“马列主义”都要深刻。也就是说,《老同志》的隐含台词是:一个没有学过马列主义的“自然人”反而比学过“马列主义”的学员更能理解“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真谛。这固然是呼应了小说开头教育长的训导,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沈从文自述《老同志》重“解释”。他在完成第四稿后说:“在事情行进中,言语中,还要多一点,解释还要删节点,就对了。”㊼第七稿寄给妻子张兆和未获消息后,他又写信自嘲:“事少解释多,方法不大好。”㊽所谓“解释多”,就是叙述者的声音特别突出,叙述者在小说中是政治研究部的学员之一,他熟练操纵“马列主义”“劳动”“改造”“群众路线”等新词语,属于改造得比较好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于某学员被老同志启蒙一事,叙述者“解释”说:
马克思列宁一生关心注意的,讴歌赞美的,对之抱着深刻信任和希望的,特别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认识得极深刻,理解得极透彻,而在一个崭新的光荣伟大时代中,为了完成中国历史任务,要求于万万人民对于劳动热情的新道德品质,老同志所保有的,恰是一个全份。㊾
出身农民的“老同志”不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完全同领袖要求的“新人”形象一致,而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还需要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貌似符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其实不然。毛泽东针对的是改造之前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不及工人农民干净,而正在进行或者已经被思想改造过后的知识分子,是否应该直接接受“自然人”农民的“再教育”,则是值得追问的。
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比较特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农民“代表着文明内部的野蛮的那个阶级”,“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既笨拙又狡猾、既奸诈又天真、既愚蠢又精明,是经过权衡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诞绝顶的时代错乱,是世界历史的嘲弄,是文明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㊿。马克思对于农民的革命性显然是保留的。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不够强大,必须依靠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同盟者才能进行革命,“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51中国革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将工人农民并列,这容易给人造成农民是革命领导者之一的错觉。但在毛泽东看来,农民需要分成很多阶层。《老同志》中的老同志,有两亩地和枣树,算不上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这样的农民也需要改造:“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我们国家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面就有改造农民的任务。”52农民只有经过改造,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这跟马克思的论述是一致的。
关于农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革大学员有过激烈讨论。有些学员认为,共产党不能称为工人阶级的党,而应该称为农民党或者工农联盟的党,因为中共党员中农民占80%。何兆武就回忆说:“讨论党的性质时,有个农民出身的人说:党代表最大多数人,中国农民最多,那么党就是代表农民的。”53这些观点出现后,华北革大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学员进行公开辩论,校长刘澜涛在总结报告中认为:“农民出身同志的根本缺点,是思想上的片面性、狭隘性,缺乏历史唯物观点,看进步不看生产力,不了解农民只是一个过渡的分化的阶级,不易分清出身和入党、农民和共产党员、单纯农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分,因而常常片面地夸大农民的优点和估计农民在革命中的功劳,断章取义地了解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思想。”54
沈从文在华北革大学习期间,每次测验成绩都在丙丁之间,这说明他并没有理解校方在有关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的辩论中对他们的引导,而是根据自己的积习认可了校方所否定的“农民党”的观点。老同志可以归入沈从文塑造的湘西朴素健康的农民形象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沈从文塑造的这些“自然人”农民形象,以乌托邦的形式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讴歌这些处于政治规训之外的农民形象,虽然主观上想向人民文学靠齐,客观上却并不符合思想改造的目的。
余 论
《老同志》是沈从文在1949年后重新开始小说创作的试笔之作。他选择《人民日报》和革大教育长表彰过的炊事员刘洲为原型,表现了他融入人民文学的真诚努力。小说语言脱去了他先前那种文白夹杂的特点,而出以洗练清新的白话文,表达了他对来自左翼文坛批评的接受55,对小说服务人民功能的认可。
沈从文虽然有着靠拢新的意识形态的主观诚意,并在创作中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像他这样的有着成熟创作理念和技法的作家,这种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他的试笔之作充满了意义缝隙。一方面是赞美劳动,讴歌老同志等人努力工作,但表现劳动的文字却较浮泛,对劳动的性质缺乏分析,体现了沈从文对书写劳动的陌生。另一方面,小说对人的自然状态进行了诗意呈现,这是沈从文长期以来所擅长的小说技法,但这种技法却和他当时提出超克自然时间的“管理生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相矛盾。而且,劳动和休闲呈现出了较大的意义缝隙,并不能够形成意义整体。不仅如此,沈从文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较多误解,他认同中国革命领导人在工农并举中对农民革命作用的肯定,因为这契合了他与农民一贯的亲近感,但他不明白农民有其阶级弱点,他笔下的农民虽然能够说出新的时代的语言,但终究是未经改造的“自然人”。如果将这样的“自然人”置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施动者位置,这就必然混淆革命的性质和目的。沈从文无意于去弥补小说文本呈现出的诸多缝隙,这恰好成了他既努力融入新的时代,又保留较多积习的症候。但从另一角度来说,沈从文对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把生命谐和于自然”的呈现,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弥补了主流文学对日常生活越来越激进的规训,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可能引起注意。
注释:
②刘少奇:《对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主要情况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949.7—1950.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③林洪:《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访问记》,《人民日报》1949年6月23日。
⑥《郑重准备边区建设的“总检阅”》,《解放日报》1944年8月1日。
⑦李向东、王增如编:《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⑧沈从文:《灯》,《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⑨朱洪涛:《思想·心态·立场——华北革大时期沈从文述论》,《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