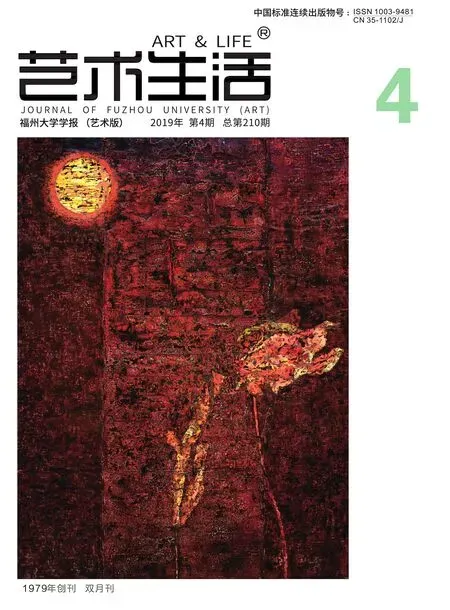论羌族图案形式的法则与秩序
王李羊
(南通开放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6)
图案作为“有组织意义”的对象,通过视觉作用于人的感知,使审美主体受到感染,与此同时,它适应人的视觉系统的选择,给人们带来心理的快感。基于羌族图案艺术的形象系统,形式直接面向人的知觉呈现,它既能够存储羌族的知识和记忆,也是读者和观众进行审美消费的对象,即审美再创造的起点。
羌族图案是羌族人集体记忆的体现,它是一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民间艺术符号系统。羌族图案的核心之一是线条,其形态决定了结构图式;色彩调配表达了审美风格;位置经营彰显内部要素美的规律……羌民使用诸类形式要素表现事物的量感、质感、空间感和运动感,创造性地生成了羌族特征的图案造型。接受美学认为:“‘具体化’是‘作品被理解的具体形式’……具体化是与原作保持同一性与读者创新的变异性的统一。”[1]14羌族图案构成简单,其显现形式及存在方式的属性,是分析研究羌族图案造型特点的“密码”,是接受者识别体验的直接关联物。
一、形式媒介
无论哪种民间手工艺,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借用多样化工具去突破材料的限制,以实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检验人的智慧能在多大程度上战胜客观物质。不同的材料需要安排不同的方式、手段、技法去加工其形式要素,好比带着镣铐的舞蹈,越难应对的材料越有成就感。羌族图案的构图形式,与中国传统纹样的常见组织方法具有相似性、一致性,主要类型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纹样、四方连续纹样、适合纹样等。图案创造可以采用不同属性的材料,如纺织物、彩纸、竹子、木头等。羌民对这些材料的属性非常了解、烂熟于心,甚至进入到集体无意识直觉层面,能克服材料的局限性并保留其自然属性,能从技术手段上保证战胜材料的自然属性,并对其精心雕琢,以刺绣、雕刻、彩画、拼接等方法,构成真正符合其精神的形式,实现图案艺术形象的“形”与材料的交融。
在图案造型的创作上,羌族刺绣图案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从游离状态到形成体系的过程,达到形式结构和装饰材料的精密结合。在绣制过程中,以纺织物为载体,与其交织融合、彼此渗透,呈现出图案的艺术效果。“经纬线本身就是一种图案,而手工艺人可以按照意愿自由选择不同的方式对图案进行修改,用不同的线条、不同的交织法织出各种复杂程度不一样的图案。”[2]75在羌族刺绣手工艺中,图案造型受到材料本身的“图案”限制,选择相适应的几何法则后,依靠“添加”的图案,进行绣制图案的加工、完形。除了制作这种二维空间“平移”图案的之外,还有羌族口弦三维空间“旋转”雕刻的“装饰”图案(如图1),不仅具备二维空间图案的美的视觉特征,且具有一定的三维立体性。因此,主体在视觉感受的基础上,可以去感知图案本身的质地形体。观赏者则可以站在不同角度,从不同层面欣赏同一图案,获取多方位、多层次的美感。

图1 羌族口弦(王李羊摄,理县蒲溪,2016 年)
羌族理县蒲溪的休溪羌寨制作的口弦为管状细小竹节,上面有立体感的“旋转”雕刻图案。制作过程中,在“旋转”有形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浮雕”的雕刻手法,以凸起来的结构与凹下去的纹理,营造出三维实体的造型美。“图形”与“基质”产生“虚实相生”“有无相关”的艺术效果,彼此形成对比,又互为填充对象,相互激荡,相辅相成。再加上天然材料的自然美,这种图案与材料的处理达到最完满的对应和契合,形成微妙的图案艺术的和谐之美,给人以亲切感。
绵阳平武县平通镇阳明村山区里发现的清代羌族“绘画”图案更是精妙(图2)。从现存的图案看,全图采用场景式的叙事法构图,画中的人物有释比、药王、龙王、判官、文书、兵员等。民间传说故事在布卷上娓娓道来,可谓是姿色各异,集中又详尽地再现了羌民的民情风俗和宗教信仰。图案中的线条轮廓及色彩块面经历数百年依然比较清晰,可见天然矿物质颜料更容易渗透纺织物,颜色保存更持久,晕染程度更小,这些是纸张不具备的属性……作为图案的物质基础,“材料的任何变形同时也就是形式本身的变形,每种材料都有自己最美的形式,也有自己不合适的形式……”[3]P186只有挖掘材料的最美形式,创造最适合材料的形式,材料被精当地和谐组合,与图案形成有机的统一体,二者水乳交融,才能突显出图案的自然美感。

图2 “卷卷神”(案子,清代)(王李羊摄,绵阳平武,2017 年)
二、形式色彩
色彩诸要素是最具感情特征的因素,而界定形状的轮廓线,则是眼睛从区分几个亮度和色彩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区域时推导出来的。羌族图案丰富多样,其形式结构可依赖色彩和亮度来区分。图案的形状与颜色相互渗透、融二为一,形成一个有机体,是图案艺术美的重要视觉因素,它对人的视觉冲击力、影响力远胜于线条,极具艺术张力和感染力。用于区分图案的亮度和色彩,不只是以几何形态的象征方式暗示了创作者的情绪,更能唤起欣赏者的情感,并去体悟、解读图案意义。图案借助材料本身色彩,在光影的作用下,透过其纹理也能显现出颜色的微妙差异。然而,严格说起来,色彩与形状是两种互相区别的对象。在识别图案信息的过程中,外在造型要比色彩更有效,因为形状能够建构出大量互不相同的式样。但是从视觉要素来看,图案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色彩是比形状更为原始的审美形式,足够活跃而又有视觉冲击力,能更多地唤起人们情感上的反响和共鸣。某些情况下用色彩赋予图案以表情达意时,会别出心裁,从而胜出形状一筹。因为我们在感知形状时,“首先必须积极地审视眼前的物体,然后又要确定它的结构架构,最后还要把它的各个部分与它整体联系起来”[4]130。颜色造就的形状在图案结构上是另一种样式,它的美有其物理因素,也有色彩生发的情感体验。普辛曾经说过:“在一幅画中,色彩从来只是一种吸引眼睛注意的诱饵作用,正如诗歌那美的节奏是耳朵的诱饵一样”[5]369。因为人对色彩的视觉反应强于形状,那种能使图案形状放射出光彩的色彩具有极强的刺激作用,使图案的表现力更加强烈,与人的情感和个性紧密关联。因此,当色彩与图案造型交织在一起时,可以使物体更加引人入胜。
图3 为图2“案子”中的局部,它的色彩有效地加强了线与线之间的界域,区分了几何形态,形成具有块面感的形体,不仅突显人物形象,还赋予人物性格以特定含义。蓝色服饰与画面流露出的镇定自若的面部表情相对应,妥帖的颜色表现出形象的身份、地位和个性,进而反映出当时社会背景下整个文官阶层的生活面貌。
色彩为形式注入更深邃的意义。色彩的干涉功能减少了几何图案中存在的纯形式关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对色彩的偏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羌族图案中,可以只用一种颜色来强调图案的造型,也可用色彩组合打破“素”的静态。“素”色图案间的相同之处比多色图案要多,“素”色沉寂和“彩”色多姿都各具特色。图案色彩中的“同”或“异”打破了原来的死板秩序,出人意料地生发出各式各样的和谐关系,增添了图案艺术生命的跃动感。

图3 “案子”局部( 清代)(王李羊摄,绵阳平武,2017 年)

图4 几何形点运用(王李羊摄,西南民族大学首届“非遗”培训班羌绣成果展,2016 年)

图5 羌族装饰品图案局部(王李羊摄,四川汶川,2016 年)
三、形式组合
任何图案都包括点、线、块、肌理等“形”的基本元素,对它们进行提炼、归纳与整合,有助于形成视觉线。在调动审美者艺术想象力的同时,还能实现创造主体情感和构思的流畅表达。
在羌族平面图案构成中,“点如果没有大小,便无法被人所单独感知,所以二维空间中的可见点是有大小和形状的变化的”[6]24。在羌族图案中,点是视觉停泊站,“几何形中的点有圆形、三角形、矩形、半圆、梯形等多样形态”[7]131,常被羌族妇女用作图案的点缀或装饰。图4 中的花蕊,其几何形点呈圆形,是视觉跳动的踏板,也是图案得以延伸的线、块、肌理等其他因素的起点。点的无方向性,也正是图案跃动的开端。
如果图案空间内,点被群化为一组,或是点之间形成定势的重复移动,将会产生线。“线”具有方向、长短、倾斜角,影响图案的周围空间。“(线)是构成物体视觉形象最基本的要素,是表现物体最直接、最明确,也是最富有概括力的艺术手段。”[8]126羌族图案中线条所构成的形式美是多种多样的,有加速度、减速度,流畅的线、弯曲的线、交织的线、重叠的线等,这些线彼此交替,相互作用,其内在张力呈现出图案的运动轨迹,流淌出创作者的情感意绪和审美情趣。图5 是羌族刺绣装饰品的局部,主要运用“线”的形式来描绘风景,通过线的方向、长短、倾斜角的变化,构成树、亭、山、人物等意象,营造出空间维度——“咫尺亦有千里之趣”。相较其他元素,“对它的感受、领会、掌握要间接和困难的多,它需要更多的观念、想象和理解的成分和能力”[9]28。
羌族图案形状由不同形态的线构成,线条的起伏节奏变化以及“色彩”的晕染,形成了空间维度的块面,无论以什么样的工艺方式呈现,图案中块的体态会留下创造者的制作痕迹。图6 飘带上的“四方花”图案,不同色块自成一体,但成为整体图案的一部分后,单独成分的局部特征消失了,各个部分的色块组成以出人意料的形式,使图案呈现出神奇效果,部分与整体相映成趣,符合美的规律。
不论图案以何种形式存在,它都不是想象中的事物,而是被想象具体化、物态化的事物,从而成为可见、可触的实物。赋予图案以肌理,透露出手工艺的自然之美。不同工艺手段造就羌族图案肌理的多样性,笔触在画布上的留下肌理,木、竹、石等材质上雕刻出的肌理,纺织物与剪纸拼贴组合的肌理等,共同构成“附属的”艺术形式,它们增加了图案的厚重感。整体而言,肌理的“形”是构成图案最终形态的基本要素之一,它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只有把它们与其他要素综合起来仔细揣摩、玩味,才能悟出图案的秩序和意义底蕴。

图6 飘带“四方花”(王李羊摄,茂县叠溪,2016 年)

图7 圆菊花图案(王李羊摄,四川成都市图书馆,2016 年)

图8 团花图案(王李羊摄,茂县,2016 年)
四、形式秩序
“韵律或节奏就是有规律性的运动的反复,即使在似乎不规则的自由运动的延续当中经过细心观察也能发现韵律的存在。”[6]55羌族图案的各组成部分有秩序地“排列”在图案整体中,正是这种秩序营造了图案的韵律,而这种秩序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常常“干扰”我们对图案的把握。羌族图案是按照连续、渐变、起伏、交错、对比等秩序原则,巧妙地将各个要素贯穿融合,连接成一个整体,通过图案的外部秩序表达内在的意蕴特征。
(一)连续韵律
羌族图案色彩、结构和形式上的对照以及重复、发散等方式的运动状态,使观者顺着物体暗示的视线移动,以“惯性”冲破图案物体的局限,扩宽“可视”范围,在超然的空间中无止境地连绵变化,达到王维所言“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方寸之内,纳寰宇之姿”[11]135的辽阔境界。图7 飘带上由连续“卍”字纹围合的边框及内里的圆菊花纹饰所构成的图案,以连续的方式排列。借助其秩序,读者能假想式地“看”到被遮挡的内容,这是连续的图案韵律造成的。图案本身受到空间的严格限制,但当观者去面对这种变化的构成时,却发现它不再是图案的具体化表现,而是由统一的内容与形式秩序所展现出的规则而连续的运动轨迹,形成富有韵律的空间艺术效果。
(二)渐变韵律
羌族图案中的渐变韵律失去了连续韵律的稳定感,其形态的某一造型依照另一种秩序演变,欣赏者在渐变过程中观察并感受到图案的韵律。渐变方式如直线般引导着视线由始至终,若不依循这种顺序,很难直观“看见”图案所要表达的内容意义。图8 是一方由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团花图案正方形手帕,由四瓣花变为以一叶花瓣为纹饰的花瓶,再到插有花朵的花瓶,最后形成团花图案的整体统一。观者视线被牵引着作规律而有序的运动,像钢琴跳跃的律动节奏,给人生动流畅的感觉。
(三)起伏韵律
秩序变化犹如波浪或规则或不规则的韵律,在人的期待范围内,时而增加时而减少所要传递的信息,图案静中有动,使人产生余味无穷、耐人寻味的审美效果。图9 是羌族茂县坪头羌寨建筑的墙体局部,是运用黏土与纤维物巧妙生成的特殊肌理效果,圆形的起伏变化不同于螺旋形的自然现象。这种趣味的起伏韵律,会让观者调动其主观因素作出响应,产生一连串的“寻找”反应,以满足较大范围的预期,从而实现境外之意的艺术体验。

图9 羌族建筑上的肌理(王李羊摄,坪头羌寨,2017 年)
(四)交错韵律
图案中的点、线、面等要素在一定的规律下的交织融汇,色彩的对比与和谐间的无限张力,不同材质属性间的交相呼应……以上要素相互作用制约,时隐时显,依靠内在的秩序表现出有组织的变化,营造出特殊的文化氛围。图10 团花图案中颜色与形状二者交错组合,或是由深至浅、由暗及明的颜色变化过程,或是形态各异的几何形体的变化,给观者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凹凸感,这是每个排列分明的块体形象产生出的层次秩序,整个图案由此产生立体感。图案上的文字对图案有限定作用,有的内容明朗,有的含蓄复杂。图案内容与文字的交错律动也给观者留下回味空间,引导他们去体验其中蕴藏的生活经验。

图10 团花图案(王李羊摄,茂县,2016 年)
结语
羌族图案的内在审美意蕴是由凝练概括的典型性图案,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来实现的。羌族图案的审美特征在形式审美法则下得以显现,其外在形式既具备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又蕴含着内在的精神性。我们通过寻觅图案形式构成的基本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体察深藏于作品内部的精神或灵魂,这也是图案审美价值的实现过程规律。学界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艺术学、设计学、美学、图形学等学科系统理论加以抽象解读,总结出系统的形式规律,让当代设计从中汲取养分,创新性地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血脉,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