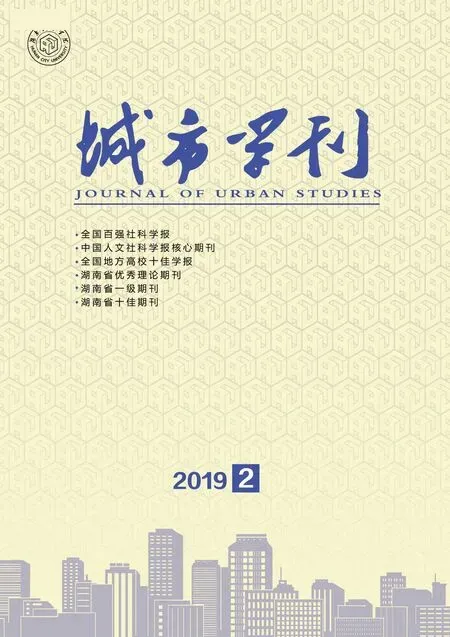宋代词学中的词体风格论
向 娜
宋代词学中的词体风格论
向 娜
(湖南城市学院 人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从“辨体”的角度来说,词的文体风格是词学中的核心问题。词学中明确辨体思想的出现,始于北宋中后期的李之仪、陈师道等人。宋代词体风格论中涉及的主要风格特征,主要包括“绮艳”“含蓄”“清”几种。其中,“绮艳”比较贴近唐宋以来创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宋人极少有从正面肯定其为词的文体特征者。“含蓄”则是词的文体特征中的核心规范。“清”是文人雅趣在词中的反映,也是词体由俗趋雅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最终形成了张炎的“清空骚雅”说。宋代词学中提出的几个关于词体风格的要素,基本成为后来词体风格论中延续的核心要素。
宋代词学;辨体;绮艳;含蓄;清
词体风格论,讨论的是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风格上所具有的独特性的问题。“文章以体制为先”,[1]“辨体”在古典文学的创作和理论中都是具有首要地位的话题。而对于词这种兴起于诗歌之后,且与诗歌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体来说,辨析其体性更具有在文学体系中寻求其独立地位的特殊意义。词之为词,其体制上的特征诸如长短句的形式,格调韵律上的严密要求等,固然极为重要。但独特的风格特征是更重要的因素,正如缪钺先生所云:“抑词之别于诗者,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律,而犹在内质之情味意境。外形,其粗者也;内质,其精者也。”[2]这种内质,也即词的审美风格特征。因此自宋代起,对词体特性的讨论便已多集中在风格上。
一种文体的文体规范与特征,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这些作品在质与量方面都有了丰富的积累以后,文字组合便逐渐显示出一定的规律和结构,形成了‘法’。”[3]因此对一种文体的认识,也往往需要在其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之后才能逐渐形成。词自隋唐时期开始兴起,之后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人从文体的角度对其体性进行辨析。唐五代及北宋初期对词体的认识,一方面以其为小道不足为论,另一方面由于词兴起之初在体性上与诗歌具有相似性,也往往存在诗词不分的情况。如欧阳炯《花间集叙》从音乐文学的角度,将词与“南朝之宫体”“北里之倡风”[4]相联系;宋初潘阆《逍遥词附记》谓诗词“其间作用,理且一焉。”[5]708都说明当时对词的认识尚未关注到其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特性。
但是,当词的创作成为一种无法被忽视的文化现象,对其进行文体定位就成为一种需要。因此到北宋后期,出现了对词的文体特征的集中讨论。李之仪的“自有一种风格”说、晁补之与陈师道的“当行”“本色”说,都明确地指出了词在体性上应区别于诗,这也意味着词学辨体思想的确立。稍后的李清照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词“别是一家”之说,并对词的体性及其与诗的差异都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在此之后,虽仍不免有混淆诗词的观念出现,但宋代词学对词体的辨析总体是向着深与细的方向发展的。虽然最终还没有形成兼顾词体独特性与其在古典文学体系中独立地位的词体观念。但是我们今天提及较多的几个词体风格的核心要素,在宋代都已经出现,并有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一、以“绮艳”为核心的词体风格论
“诗庄词媚”“词为艳科”是今人习以为常的观念。从创作来说,绮艳确实是唐宋词的主要特点之一,后人评唐宋词尤其是唐五代北宋词,也常以此类特征形容之。但宋人自己其实极少以“绮靡”“纤艳”一类特征来要求或评价词体、词作。有之,也多出于否定的态度。然而这种否定,毕竟也从反面说明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词确实是以此类风格为主要特征的。因此,对于词体中绮靡一类特征,需要结合唐宋词创作之实际与理论批评两个方面来认识。
“艳”,本意指美好,常被用来形容女性之美,如《左传》云“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6]《楚辞·招魂》曰:“美人既醉,朱颜酡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王逸注云:“艳,好貌也。”[7]又扬雄《方言》谓“美色为艳”。[8]则“艳”似偏指外在之美色。另,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释“艳”云:“容色丰满也。”[9]则其所指对象在风貌上应偏于秾丽而非淡雅。综合以上几点,文学作品的“艳”一方面指题材内容以女性的容色或者男女之情为对象,一方面指作品色泽上的鲜明秾丽。常与“艳”连用而具有相近意思的,还有“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谓缯之有文者也,文者,错画也。……缯为交错方文。”[10]引申以指文词之繁丽者。刘熙《释名》云:“绮,欹也,其文欹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11]故于文学批评中,绮常与艳连用,指带有狭邪意味的作品。常见于绮、艳一类的词语,则有绮艳、绮靡、浮靡、艳冶等。
宋人鲜少从肯定的角度以“绮艳”一类词来评价词人词作,直接以“绮艳”为词的文体风格特征的更是不多。较早指出词体以绮靡为特征的,是南渡时期的郑刚中,其《乌有编序》云:“长短句……余每有是焉,然赋事咏物,时有涉绮靡而蹈荒怠者,岂诚然欤?盖悲思欢乐入于音声,则以情致为主,不得不极其辞,如真是也。”[12]指出由于与音乐的关系,词在体性上以情致为追求。既追求抒情的极致,则自难免有流于绮靡荒怠处,这就将绮靡的特征与词的体性联系了起来。
明确标榜词体特征之“艳”的,则有南宋晚期陈模与沈义父,陈模《怀古录》云:“然作词亦须要艳丽之语,观此,诗之高者,须要刮去脂粉方是,此则其不同也。”[13]明确指出词要有脂粉气,并以此为诗词差异所在。沈义父《乐府指迷》云:“作词与作诗不同,纵是咏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然多流淫艳之语,当自斟酌。如只直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14]281所谓略用“情意”,即后面所说之“艳语”。认为没有“艳”的成分,便非正宗之词,也即强调了“艳”作为词的核心风格要素。但他也承认艳语毕竟易流于淫亵,因此指出应自斟酌,在艳语与淫艳语之间设置了一个微妙界限。不过,像这种从正面标榜词体绮艳特征的词论在宋代是比较少见的,更多的是从批判中透露出其时绮艳词风的创作倾向。典型的例子如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所云:“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词家争慕效之,粉泽相高,不知其靡,谓词固然也。”[15]其批判之意非常强烈。出现这种倾向,主要因为绮靡、绮艳一类风格特征,在正统文学中一直属于被批判的对象。一方面其辞彩的秾丽往往意味着对形式的追求与雕琢,因此不符合古典文学的传统创作取向,如刘勰《文心雕龙》在其列举的八种风格中,就唯独对“轻靡”“新奇”二体“稍有贬义”,谓“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16]而且从审美心理来说,中国古代文人在色彩上也更偏好淡雅而非秾丽。另一方面,因与女性容色或男女恋情的密切关系,绮艳风格的文学作品往往容易流于淫亵,《文镜秘府论·论体》就曾说:“绮艳之失也淫……艳貌违方,逞欲过度,淫以兴焉。”[17]因而此类风格极少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在宋代这样一个理学大盛的时期更是如此。也因此,即便早期唐宋词的创作确以绮艳为主流,但一旦进入理论探讨范围,就只能被否定、批判。
相对而言,宋人更偏好与“艳”相近的“丽”,“丽”与“艳”在形容美这一点上有共通之处,但又没有“艳”所包含的指向低俗淫亵的一面。因此用“丽”来论词,既能贴合词体的精美特征,又不违背士大夫的审美习惯。宋人虽没有明确提出词以丽为特征,但在评论词人词作时,却极愿意以具有丽的特点来褒扬评论的对象,譬如陈世修论冯延巳词“思深辞丽”,[5]332黄庭坚谓王观复词“清丽不凡,今时士大夫及至者鲜矣”,[18]陆游肯定唐五代人“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19]等等,皆对词中具有“丽”的特征表示出极大的赞赏之意。这也反映了宋人在反对艳冶特征的同时,对于词体精美的一面是认可的。
二、以含蓄为核心的词体风格论
“含”,“嗛也”,含蓄即蕴含而不露之意,在文学艺术中,含蓄的风格所追求的审美特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蕴的丰富性与深长性,即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与浅白相对;二是表达上的温润不过度,与直接、生硬相对。对于委曲含蓄的追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大多数文体都以此为重要的标准,其中诗歌尤甚。但于词体而言,此类特征则具有更为核心的意义,甚至成为分别于他种文体的核心标准。梁启勋云:“词及近体诗,大都以婉约为正宗,盖一则上承三百篇之遗风,而格律之拘束亦有以致之也。汉魏乐府,无篇幅之制限,长言咏叹,了无拘管。唯近体诗则以二十字至五十六字为限,若不采含蓄蕴藉之技术,取弦外之音,纳深意于短幅,则作品将薄为寡味矣。唯词亦然,且以其格律愈谨严,故婉约之技术亦愈巧。”[20]词体在进入文人手中时,以小令为主要创作体式。小令字句少,容量小,因此需要以有限的字句表达更多的内容,含蓄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而另一方面,由于词在兴起之初的创作、功能都与女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以“柔”为特征,这也决定了其在表达上以温润而非激烈生硬为尚,刘师培先生就曾说:“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柔者以隐秀为胜。凡偏于刚而无劲气风格,偏于柔而不能隐秀者皆死也。”[21]所谓隐秀亦即含蓄之意。而词学中对委曲含蓄的要求,也确实是自宋代开始就不断被强调的。
北宋文人在评价他人词作时,已经常常表达出对含蓄蕴藉的肯定,如陈世修《阳春集序》谓冯延巳词“思深辞丽”,所谓“思深”,一方面指情思的幽深、深厚,另一方面也指表达上的幽隐而不直白浅露。苏轼《祭张子野文》谓其“微词宛转”[22]、朱敦儒评曹勋《谒金门》:“还古风之丽则,宛转有余味也”。[23]皆将宛转含蓄作为论词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含蓄的要求与对韵致的追求有关,而从辨体的理论在词学中开始出现,韵致就是核心的要求之一,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论词之“自有一种风格”,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韵”的肯定。而其末几句:“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24]310虽只是针对词的结尾而言,但对言、意、情的关系的表述,已经体现出含蓄的追求,只是还没有将其作为词体的要求而已。到南宋的王炎,则正式提出了婉转特征在词体中的核心地位:“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不溺于情欲,不荡而无法,可以言曲矣。”[5]793不仅将婉转妩媚视为得词之体的首要特征,而且提出了更详细的标准,“不溺于情欲”,强调抒情之“度”,是内容上的含蓄;“不荡而无法”,则强调表达上的规范得体而不过分,属形式上的婉转。
关于词的婉转含蓄,沈义父论述得最为丰富详尽,其《乐府指迷》论作词之法,与含蓄相关的规则就占了两条:“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14]277明确将词体含蓄的要求落实到“深长之味”和“柔婉之意”两个方面,并进入到字句等细节的讨论,指出实现意蕴丰富深长与词意柔婉的具体途径。关于词之字面的含蓄,《乐府指迷》还特别强调应避免生硬:“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14]277-278之所以肯定融化唐诗中字句,而认为用经史中字面则显生硬,源于诗歌与词在追求“韵致”上面具有一致性,而经史以叙事明理为目的,置于诗词中,则锋芒过甚而有失生硬,缺少含蓄柔婉之致。
在字面上与含蓄委婉相对的还有直接,沈义父对于这一点亦极为强调:“炼字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咏书,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箸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往往浅学俗流,多不晓此妙用,指为不分晓,乃欲直捷说破,却是赚人与耍曲矣。”“词中用事使人姓名,须委曲得不用出最好。”[14]280-282前面一段话往往为人诟病,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25]此种批评,确实深中其病。但其本意并非为了避鄙俗,而是为了避浅直,是希望以暗示性的替代语取代直接的描述,从而赋予词作以联想性,这也是实现词意的多层次性即含蓄的途径之一。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说:“用字不可太露,于是每用代字……如用之适当,自具蕴藉含蓄之妙。惟用之不当,往往流于晦涩。”[28]844刻意使用典故代字,确实可能有雕饰晦涩之弊,但避免直接的描述指称,也确实更适合诗词在语意的丰富性含蓄性方面的要求,更能见作者体物之功力。
词的意蕴的丰富性,亦往往通过结尾的处理来实现:“结句须要放开,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尾最好。”[14]279李之仪曾提出词体之妙见于卒章之余味,而沈义父则从指导创作的角度更为具体地指出了实现这种余味的途径。以景结情,可避免将情说尽而流于质直、浅露,因“景语含蓄,较情语尤有意味”,[26]855由情语转入景语,亦可形成转折动荡之势,增加词意的层次。
宋人论词虽然尚未明确标举“含蓄”之名,但在讨论词体之具体特征时,已经触及了含蓄的多种内涵。不仅从高下优劣的角度表现出词以委曲含蓄为尚的观念,也已经出现了明确将“含蓄”作为词体的规范性特征的观点。
三、以“清”“雅”为核心的词体风格论
“清”这种审美特征,似乎很难与词这样一种被视为“艳科”的文体产生联系,但事实上,对“清”的崇尚几乎是伴随着整个词史而存在的。在词学发展的源头,“清”这一风格范畴就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所标举的词体风格取向,除“艳”以外,最突出的就是“清”,其中一再表示对“清”这一审美风范的崇尚,“从开头部分的‘金母词清’到晋朝诗歌的‘清绝之词’,欧阳炯对‘清’的审美观念的崇尚是清晰可感的。如果再把序中提到的历史典故,如《白雪》的‘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等对勘,则清美意识更是洋溢在序文的字里行间。”[27]
如果说绮艳是词体与唐宋时期娱乐文化的关系在风格上的体现,那么“清”则是文人雅趣的反映,“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典艺术的终极审美理想相联系。”[28]也因此,相对于绮艳,“清”是唐宋人在讨论词体及评价词人词作时使用得更多的一个范畴,对“清”的称扬贯穿于整个宋代的词评、词论中。宋初陈世修评冯延巳《阳春集》,已经称其“真清奇飘逸之才”“飘飘乎才思何其清也”。[5]332此后“清”更成为宋代词论中极为常见的评语,如:
(王晋卿)作乐府长短句,踸踔口语,而清丽幽远,工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
黄庭坚《跋王晋卿墨迹》
安定郡王……时时游戏于长短句中,妙丽清壮,无一字不可人意。
周紫芝《书安定郡王长短句后》
今观中行所书便面长短句,凡六解,清而婉,不减唐人风味,盖平生得意语也。
张元幹《陈中行宣事乐府跋尾》
(仲殊之词)盖篇篇奇丽,字字清婉,高处不减唐人风致也。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梅溪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者也。
张镃《题梅溪词》
就词论所呈现而言,虽然在张炎之前明确提出词应具有清的特征的比较少见,但从两宋词家在论词评词之时流露出对清的崇尚肯定,可以认为清是比艳更为唐宋人所接受认可的一种属性。宋代词论中以清为核心构成的评语主要包括清奇、清丽、清远、清婉、清新、清逸、清劲、清淡、清壮等,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则是清丽、清新、清婉几种。这也说明“清”这一概念,更多还是与偏于柔的词语连用,也就是说宋人对具有清的风格特征的追求,并非是要在词体的委婉特征外另立一宗,而是以委婉为基础。另一方面,唐宋词家对清的肯定,也确实具有脱离绮艳淫靡的低级趣味而体现文人雅趣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清”可以算作沟通词体的艳与雅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审美特征,正是因为对“清”的肯定与追求自始至终存在于唐宋词人的意识中,才使得“雅”的要求能够真正适用于词这一种文体,而非脱离词体发展的渊源本质,仅仅以诗道之骚雅要求来反对绮艳淫靡特征。
相对上述几种词体特征而言,“雅”是后出的一种观念。宋代词学中尚雅的要求,就其出发点而言,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在不忽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的前提下提出雅的要求;二是出于诗教的立场,将词置于诗歌乐府的发展脉络中,以诗教中的雅正思想对词提出要求。
以雅论词的现象在北宋中后期大量出现,不过多仍出现于对词人词作的评价中,如黄庭坚谓晏几道词为“狭邪之大雅”。[29]晁补之亦谓其:“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自是一家。”[30]黄庭坚明指其为狭邪,晁补之所举例证也是典型具有词体特征的句子,可见这两家论小晏词之雅,也是在词的范围内,在区别于诗的前提下给予“雅”的评价的。更典型的则是李之仪,其《跋吴师道小词》云:“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24]310明指其为余力游戏之作,而风流闲雅的评语也显然是照顾到词体的特征,乃是风格上的评价,而非思想上的雅正。以上诸家词评,说明词体趋雅的进程,其实在北宋开始。且以上所举的词人,也都是坚守唐五代词传统的本色词人,这也就是说词体的雅化,并非如一般所说是经过苏轼等人以诗为词之后才开始,而是进入文人手中后的自然趋势。
不过,两宋词学中对雅的提倡更多的是出于忽视词体独立性的立场,将词视为诗歌的一脉并直接以诗教的观念衡量词体。较早表现出这种观念的是北宋后期的黄裳,其《书乐章集后》评柳永词云:“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31]64以典雅论柳永词,并将其比于杜甫诗,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黄裳其实并没有将词视为诗之外的另一种文体,因此仍是以诗的思维在评价柳永的词,“盛世之黼藻”显然是论诗之语,也与当时词体的创作状态有一定差距。又其《演山居士新词序》谓自作之词乃:“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以协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舞蹈以致其乐。”也显然并未在诗词间有所区分,甚至是直接以诗之六义论词,因此自谓其词“清淡雅正,悦人之听者鲜。”[31]791虽提出雅正之说,但因其并未予以词体独立的地位,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算作针对词体的尚雅之说。但是这种以诗教立场对词提出雅正要求的态度,却成为词学史上始终存在的一种观念,其中第一个集中出现的时间段即稍后的南宋。
词学的复雅是南宋词学的一个显著现象,但这一时期所倡之雅,主要是内容上的雅正。因此在论述的方式上基本都是从诗乐传统入手来反对此前词史中出现的淫靡倾向。如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云:
迄于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淫乐,而明宗犹溺于夷音,天下薰然成俗。于是才士始依乐工拍但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尊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

宋末诸词家所提倡之雅,又开始回归与文人雅趣及反对俚俗淫靡等低级趣味的高雅,在张炎之前,对雅讨论得比较多的词家是沈义父,其《乐府指迷》开篇论作词之法,第二条即为论雅:“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14]277将雅作为词体区分于坊间所唱之曲的关键因素,《乐府指迷》屡屡表示词应区分于乐工所唱之俗词的意思,无论字面、用意、腔调,皆反对教坊乐工所代表的俚俗之气。论字面则反对市井气、鄙俗语,如肯定周邦彦词:“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批评康与之、柳永词:“音律甚协,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语。”论孙花翁词:“有好词,亦善运意。但雅正中忽有一两句市井句,可惜。”对诸家词之褒贬,可见市井俗气是词应极力避免的特点,则其所论之“雅”,也主要是与这种市井俗气相对,加上其肯定施岳词得益于唐诗,故能淡雅,则可看出其论词所尚之雅,与教坊乐工之词保持距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提倡的主要是文人之雅趣,表现为风格上的高雅。
最后看张炎的清空雅正说,从以上所述宋人对雅词的崇尚讨论,可知其中涉及雅的两种意义,一种是儒家诗教的雅正思想;一种是体现士大夫情趣的高雅风格。而张炎所说的“雅”则两者兼而有之。其讨论雅正,一是认为词之抒情应有度,发乎情而止乎礼义:“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14]266主要表现为对词中流于淫亵之意的反对,但不同于南宋前中期复雅诸家尚雅而纯以诗教论词,张炎只是强调词体抒情之“度”,却并不限制其所述之情的具体内容,赋情条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如陆雪溪《瑞鹤仙》云……辛稼轩《祝英台》云……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故其宴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州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14]264首先就对词在抒情方面长于诗的特性表示肯定。最后列举的情感类型,也多是与个人生活相关,而并未强调思想上的正确,或要求词具有“通政事、考风俗、正得失”等社会政治的功能。所以其雅而正的要求,说到底还是针对唐宋词中存在的流于淫亵之失,属于风格上的雅洁,与从诗教方面讨论其意旨的雅正有一定的差别。
张炎论词之“雅”的主要含义,是体现文人雅趣而脱离尘俗、世俗的高雅,就这个意义而言,雅是与清互相联系的两个概念。《词源》卷下论词之雅正,而举标出秦观、高观国、姜白石等数家,谓诸家词:“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14]255以“清新之意”作为雅词的关键因素,并与词的靡曼之失相对,也说明清新确实是雅词的一个关键因素。关于这一点,陆辅之表述得更为明确:“造语贵新。纤巧非新,能清而新,方近雅也。”[14]301很明确地指出语意的清新是雅词的必备因素。又论秦观词云:“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14]267以淡与雅连用,又强调秦词“清丽”的特征,也可见其所申之雅,更重于格调之清淡。前文提及唐宋人对清的提倡,是文人雅趣在词中的反映,也是词最终避俗艳而趋雅的内在动力。张炎对这两个方面的讨论,可以说正是这两方面最终结合的总结性表述。而其中最突出地体现这一点的则是“清空”这一风格范畴的提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唐多令》)此词疏快,却不质实。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耳。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14]259以清空与质实相对,但首先强调古雅峭拔,因此并不止反对质实所带来的晦涩之感,更重要在于与质实相联系的“密丽”词风,在色泽上过于秾丽密集,因此不符合清雅的审美观,其讽梦窗词如七宝楼台,首先也正在于其色泽之秾丽。而“清空”的审美趣尚,在词的色泽上,应是以“清”为核心,取淡雅而偏于冷色调,此处以白石词为例,而清刘熙载以“幽韵冷香”评价白石词,[34]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宋代词学中关于词的文体风格的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因词兴起的环境、功能等早期因素而产生的以绮艳为核心要素的词体观;二是在词的发展过程中,因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逐渐占据主流的以清雅为主要特征词体观。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对含蓄委婉的要求都是一致的。这几个特点,也基本成为后来词学史上对词的文体风格界定的核心特征。
注释:
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云:“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二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见《文心雕龙注》, 刘勰,著. 范文澜, 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07页
②镇词,近人潘飞声评其“格高气远,情致绵邈,而才足以运之,为宋代词家特出。”又评其《念奴娇》咏茉莉词云:“赋物小题,而托体高华。”可见其词确实颇有骚雅之趣的。见《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第171页;第二卷第一号,第126页
[1] 倪思语, 王应麟. 玉海·卷二百二[M]//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94.
[2] 缪钺. 缪钺说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2-3.
[3] 龚鹏程.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论本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72.
[4] 赵崇祚. 花间集校注[M]. 杨景龙,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01.
[5] 王鹏运. 四印斋所刻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6]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83.
[7]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10.
[8] 王智群, 谢荣娥.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M]. 王彩琴, 协编. 华学成, 汇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00.
[9] 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94.
[10] 许慎. 说文解字注[M]. 段玉裁,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648.
[11] 王国珍. 《释名》语源疏证[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154.
[12] 郑刚中. 北山文集·卷十三[M]// 丛书集成初编第1964册.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172.
[13] 陈模. 怀古录校注[M]. 郑必俊,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57.
[14] 唐圭璋. 词话丛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5] 林景熙. 霁山集[M]// 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111.
[16] 刘勰. 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505-507.
[17] 遍照金刚. 文镜秘府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151.
[18] 黄庭坚. 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1193.
[19]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徐小蛮, 顾美华,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614.
[20] 梁启勋. 曼殊室随笔[M]. 正中书局, 1948: 490.
[21] 刘师培. 程千帆.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37.
[22] 孔凡礼.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943.
[23] 曹勋撰. 松隐文集·卷三十八[M]// 嘉业堂丛书.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657.
[24] 李之仪. 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丛书集成初编[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25] 彭玉平师. 人间词话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15.
[26] 唐圭璋. 词学论丛[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844.
[27] 彭玉平师. 《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J]. 江海学刊, 2009(2): 179-187.
[28] 蒋寅. 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1): 146-157.
[29] 晏几道. 二晏词笺注[M]. 张纫草, 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603.
[30] 赵令畴. 侯鲭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84.
[31] 黄裳. 演山先生文集[M]// 宋集珍本丛刊第108册b. 北京:线装书局, 2004.
[32] 谢维新.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M]// 文渊阁四库全书941册. 511.
[33] 刘克庄. 刘克庄集笺校[M]. 辛更儒, 笺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183.
[34] 刘熙载. 艺概注稿[M]. 袁津琥,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13.
The Stylistic Style of Chinese Peom ofLyrics in Chinese Song Dynasty
XIANG 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The stylistic wrinting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oemwhich is a kind of Chinese poem is the core topic inlyrics. The emergence of the idea of distinguishinglyrics from other genres by style began in the mid-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960-1279). The main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style in the Song Dynasty including the “sensual and exquisite”, “implicit style” and “Qing”. Among them, the peom of “Qi Yan” is accor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ut few reviewers affirm it positively as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lyrics. Impliciting style is the core criterion in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lyrics. Whil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interest of the intellectuals but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ofstyle from vulgarity to elegance, and it finally formed the typical style that defined by Zhang Yan: clearing and emptiness. These elements oflyrics style are put forward instudies of the Song Dynasty that becomes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continuation oflyrics theory.
theory oflyrics in song dynasty; stylistic; sensual and exquisite; implicit style; Qing(green)
2018-07-22
向娜(1986-),女,湖北恩施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 207.2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9.02.015
2096-059X(2019)02–0089–007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