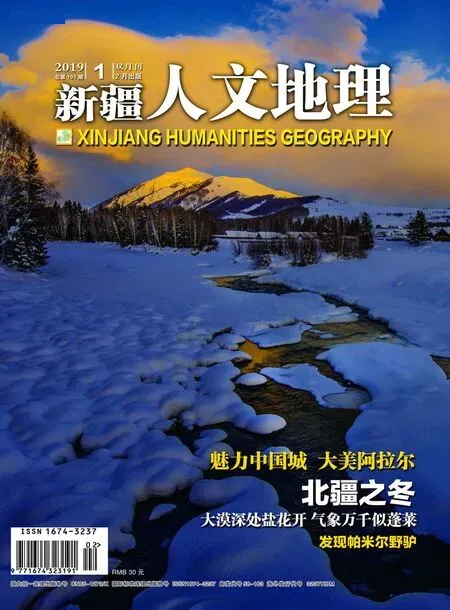西域秘境哈密魔鬼城
撰文/田蓉红 摄影/周生国
绿洲哈密,西部往西,几十万年以来,风贴着大地飞过,切割出了绵延百里的雅丹地貌,人们叫它魔鬼城。
黛青色的戈壁曾经是一片瀚海,孕育着诸多远古的生命。而今,它们和大地躺在一起,骨骼变成岩石,血肉变成砂砾,魂魄变成云烟。侏罗纪,一个已经走远的时代,带走了古生物时代的恐龙和始祖鸟,而石炭纪的珊瑚已失却了曾经的鲜艳。一年又一年,只剩下不羁的西北风在天山山谷中蜿蜒盘旋,然后呼啸而出,冲向广阔平坦的戈壁,在魔鬼城的西部形成了新疆风速最大的百里风区。风,经年累月地卷向这些裸露的砂土岩层,雕琢出气势壮观、千奇百怪的雅丹地貌。
艾斯开霞尔,一座在风中死去的城,几千年前,它曾扼守着古丝绸之路中道,南来北往的人群在这里汇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被不同肤色的人同时传播于一座荒漠中的绿洲上。后来,他们沿着白杨河流域行走的身影和足迹渐渐被黄沙掩埋,他们掩藏在胡杨木下的尸骨最终被风掀开。
没有什么是可以永久隐匿的,几千年后,一位牧羊人独自站在一座业已破败的城堡面前,在惊异之余,把艾斯开霞尔的名字传给了世界。许多人,追寻那座城堡的影子和传说而来,试图拂去黄沙,还原艾斯开霞尔本来的面貌,但是一切依旧扑朔迷离。

而比这更久远的远古时代,一片湖泊滋养着大地,树木,养育着大型哺乳类动物和鸟类,它们自在栖息,生殖繁衍。后来,湖水消弭,喜马拉雅隆起,两亿多年的地质变迁,哈密盆地经历了由海盆到湖盆、湖盆到陆盆的沧桑巨变,生机勃勃的古生物天堂变成了今天面目斑驳的魔鬼城。穿行期间的风,是试图将那些逝去的身影永久雕琢吗?瀚海神龟、金陵石虎、神女峰、千佛山、狮身人面像、布达拉宫、鳖盖梁、彩石滩,人们凭借自己的想象为自然的杰作安放一个恰当的名字,它们像魔鬼城的前世,隐藏着某种预言,被风慢慢地破译而出。昂首的恐龙驻足不前,展翅的鸟儿欲飞还留,一座时间的迷宫在风吹雨蚀的洗礼之后,独处一隅,无语静默。
在魔鬼城,我们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风起的时候,我们听风,雨落的时候,我们观雨。电闪雷鸣的时候,天空被撕开一个裂缝,我们来不及觊觎,便立刻被缝合。日升月落,斗转星移,魔鬼城被时间遗忘在大西北的荒漠中,带着史前的神秘,独自迎接最纯净的日出,独自目送最悲壮的日落。

行走在魔鬼城,举步之间,恍若从现代的文明中跌落回这个星球最初的荒洪。流云四合,狂风骤起,闪电在空中交错,光怪陆离中的雅丹上演着无人能参透的剧目——城堡,谁曾留恋于你,夜夜笙歌?殿堂,谁曾醉卧于你,狂歌当哭?佛塔,谁曾面对于你,无语膜拜?碑石,谁曾踟蹰徘徊,留下一个无字的空碑?魔鬼城,又是谁用无形的手铸造了一个有形的你?
或许正是因为这久远的秘密,这片雅丹才有了久远的引力,迎接着四面八方探究的目光。哈密西部,一座以魔鬼的名义命名的城堡因此被聚焦在目光中,被定格在镜头中,被锁定在人们的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