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歌与寓言
——重读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
◆胡传吉
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和《无字》先后获得过第二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张洁的创作一开始就能够脱颖而出,固然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学潮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她有着非常强烈的美学自觉、情感诉求与人文意识。这使张洁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具体时代及文学思潮的局限,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其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太阳》《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四只等着喂食的狗》,中短篇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场》《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七巧板》《关于……情况的汇报》等,散文《挖荠菜》《捡麦穗》《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游记《域外游记》等,皆有不被时势席卷而去的自我意识及生命感觉。《沉重的翅膀》是张洁文学创作的重要起点,重读这部长篇小说,既有助于认识张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期的审美趣味,也对理解她在1986年之后的转型有所裨益。
《沉重的翅膀》发表及出版后,相关的评论及研究是多元而丰富的。其中,有两个方面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版本研究,二是译介研究。两者皆能牵扯出相关的历史问题及不同的研究趣味。《沉重的翅膀》于1981年发表于《十月》杂志第4、5期,在单行本出版前又几经修改。修改的主要原因,跟小说发表后引发的各种议论有关。在《文艺报》《文学评论》《十月》等报刊组织的讨论会上,与会者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指出其缺点和不足,一些评论文章、读者来信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张光年的日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读者和批评家对作者的影响:1981年10月16日,“下午吴泰昌带张洁来访,要我谈看了《沉重的翅膀》后的意见。断断续续看了,记不清了,还是率直地谈了印象和感想,指出思想上、艺术上加工不足,议论过多,许多议论是不妥当的,甚至错误的,表现了偏激情绪。她取去了我划了记号的两本杂志参阅”。1981年12月13日,“翻阅张洁送的小说散文集。看了《忏悔》,重阅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及《漫长的路》第二篇,感情是纤细的。黄秋耘一篇评论,称赞她的‘痛苦的理想主义’,张洁把它放诸卷首代序。从这点来看,《沉重的翅膀》到底突破了那个细致的茧壳,未见得不是好事”。1981年12月14日,“韦君宜来电话,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根据多方的意见改了一百多处,纸型上作了挖改,她将在今天签字复印,是否同意。我说这不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我认为可以出版。下午,翻阅张洁小说集,看了其中《有一个青年》《含羞草》《非党群众》三篇,这些,连同《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都比较明朗,并不都是‘痛苦的理想主义’,可见,她也是很受批评影响的”。《沉重的翅膀》的修改过程,既对应了历史的重大变迁,也反映了美学趣味逐渐突围、获取相对独立的地位。于作者而言,这种修改,是妥协之举,也是写作艺术的打磨。这短暂的三四年间,关于《沉重的翅膀》的争议,折射了批评趣味的剧烈变迁。
与版本相对应的,是译介研究。在张洁的作品里,《沉重的翅膀》是被重点译介并产生过后续影响的小说,曾被译为德、英、法、俄、美、巴西、西班牙、荷兰等国语言。它是第一部被译成德文的中国当代小说,译者为阿克曼,曾获1985年“卫礼贤文学翻译奖”一等奖,德文译本影响较大。戴乃迭的英译及葛浩文的英译,亦广为人知。戴乃迭的英译,有一些技术性处理,可能启发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葛浩文的英译,相对来讲更忠实原文,其呼应的可能是西方人的另一套话语体系——借助中国文学了解中国,能满足西方人对所谓“真实”及历史的认知欲。此外,译介研究也注重语料库等方面的研究。译介的趣味及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了版本变化后面的历史与评价趣味。从这个角度来看,版本及译介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
顺着版本研究及翻译研究,今人有机会探讨后续的学术问题,即《沉重的翅膀》,究竟有没有经得起修改经得起翻译的内容,有没有哪些内容是修改及翻译都无法更改无法动摇的。经得起修改,经得起翻译的内容,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及诗学的辨析。《沉重的翅膀》发表至今,已接近38个年头。今天再回看《沉重的翅膀》,可以得出许多诗学上的启发——无论是修改还是翻译,都有诗学及伦理层面的完善及再生的可能。这是一个奇特的文本,“痛苦的理想主义”,能让人“看到”过去,亦能让人“洞察”未来。在面向过去时,《沉重的翅膀》是挽歌,在面对未来时,《沉重的翅膀》是寓言。
《沉重的翅膀》书写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美德:高尚与善意——受“相信”感召的高尚与善意。同时,也无意中为这些美德唱出了挽歌。之所以说是挽歌,一方面,往后的写作者,再难呈现当时的美德:无论是叙事还是语言,都很难再现那个时代的人之真诚、热情以及忘我。另一方面,不同时代,“高尚”与“善意”的内涵会有所改变。时光与激情不再,属于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可能就会走向终结,从这个层面看,《沉重的翅膀》更像是真诚岁月的余韵。这里的“高尚”,往往表现在对事业的忠诚与献身。事业不同于职业,职业对应的是生计、专业、生活,在事业这个范畴,个人与其所追求的理想是合为一体的,其献身精神以忘我乃至牺牲自我的方式完成,属于世俗生活的那部分“自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沉重的的翅膀》的题记是:“谨将此书献给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人。”这个题记,既可以对应理想,也可以对应极具时代特色的高尚(忘我)。但如果只有理想和高尚(忘我),《沉重的翅膀》就很难写出“翅膀”的飞翔意味,张洁的过人之处在于,她还写出了善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是隐藏在生活深处的秘密,想要把日常生活长久地继续下去,善意必不可少,但善意又是复杂的。一方面,不加节制的善意,有可能成为干涉或控制他人生活的工具,另一方面,合宜的善意,是对高尚的完善、对不近人情的弥补。《沉重的翅膀》写出了高尚与善意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沉重”(现实)和“翅膀”(通往理想)均得以呈现。《沉重的翅膀》之所以能在时代中脱颖而出,高尚与善意是其伦理思想资源:如果只有沉重,没有翅膀,人就飞不起来,“理想”就会化为乌有;如果只有高尚,没有善意,个人价值及日常生活会灰飞烟灭。说到底,是个人价值与日常生活使高尚与善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平衡。但反过来看,假如没有高尚与理想的召唤,个人及生活就容易庸俗化、物质化、娱乐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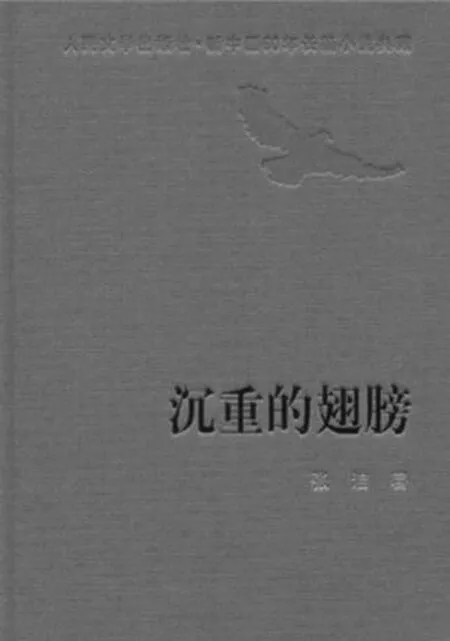
《沉重的翅膀》除了有挽歌意味,还有寓言的意味。其寓言意味在于,张洁很早就看到了个人生活的庸俗化、物质化、娱乐化。战争时代是通过献身的方式来抵达高尚和理想,那么到了和平年代,个人及生活又将如何克服庸常,这同样是“沉重”的内容。如果说挽歌是面向过去的,那么,寓言就是面向未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沉重的翅膀》借助了爱的失意、婚姻的绝望、人的庸俗等来隐喻未来。但无论是挽歌还是寓言,《沉重的翅膀》中是有“相信”的——“相信”什么?“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正因为有“相信”,才有理想主义,才有与理想主义密切不可分的美德。
《沉重的翅膀》里的“事”是透过“人”带起来的,时代的美德,也在“人”身上得以呈现。所以,读《沉重的翅膀》,还是得“读”人。叶知秋、陈咏明、郑子云等是努力让“翅膀”飞起来的人。记者叶知秋仿佛是“文眼”,小说透过她的眼与笔,去为那些能承载时代理想的英雄们立传。英雄——勇往直前的唐·吉诃德们,无一不是对事业抱有崇高理想且有献身精神的人。叶知秋是记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与书写者。叶知秋自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新闻战线上工作,她的工作信条是,“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对求真与求实的追求,使她对理想社会有虔诚的信念。信念使叶知秋对郑子云这样的改革家寄予厚望,也使叶知秋对脚踏实地的工作者充满了敬意。张洁有意让叶知秋在小说的尾声充当救急者,当郑子云心肌梗塞时,叶知秋以专业的急救知识,为郑子云赢得救命的时间,同时发出真诚而强烈的呼声:“天,这个人绝不能就这样地去了,这样优秀的人,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对理想社会的信念,仅有求真及求实精神是不够的,它需要真诚情感的投入。叶知秋的时事采访,最终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呈现,纯粹的新闻报道容纳真实,报告文学却能容纳真实后面的情感。郑子云是改革家,他的使命是什么?用小说中一句话来讲就是,“一定得让老百姓像个人那样活着”。郑子云主持专案组工作、经济工作等,都围绕这个使命来进行。“郑子云没有更多的‘野心’”,“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年轻时的许多抱负,到如今只剩下这一点: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历史到来的时期,根据他多年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实践,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提出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郑子云是有信仰的人,也是实干家,他要为历史还债,为现实开创新局面。曙光汽车厂厂长陈咏明,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要解决生产亏损、职工房子及福利、政策能否落实、职工待业子女就业等问题。在郑子云等人的支持下,陈咏明的工作取得实效,但同时也遇到了阻力,付出了一些代价:“有人要查我的账,说我胆子太大了,一定是扣了应该上交的利润给工人盖房子、盖养鸡场、挖鱼塘”,“如果不让这么办,国家就拿出个解决的办法来。我给国家上交的利润一个不少,还超额了呢,能犯多大的法?在现行体制下,采取一些‘变通’办法,解决厂里的主要矛盾,有什么不可以呢?”除了胆子大,还有使命感,陈咏明的更大心愿是,“成立一个联合汽车公司,把所有的协作厂组织起来,大家在管理上取长补短,统一管理、组织生产,使散兵游勇式的生产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竞争力”。
叶知秋、郑子云、陈咏明等人,在“为公”这个层面,可以说是问心无愧,配得上“高尚”这一美德。但同时要看到,在“为公”的前提下,“为己”的空间很有限。从世俗眼光来看,叶知秋的个人生活是狼狈的,“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头发,又粗、又多、又硬,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怪,……活像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肩膀方方正正,就像伐木人用斧子砍倒的一棵老树的树桩。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这个“顶丑”,不仅是相对婚姻视角的丑,还是俗气之人眼中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丑。郑子云的个人生活同样狼狈,他跟妻子夏竹筠貌合神离,完全无法交流,“他们结婚四十年了。每每郑子云越是细细地打量她,便越是感到陌生”。陈咏明的个人生活,看似美满恩爱,但与妻子郁丽文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郁丽文是“一个以丈夫为中心的傻女人”,而他则是一个会忘掉自己有两个儿子的男人。以贤妻良母搭配实干家,这是为事业献身的另一种形式。为事业献身而生活狼狈,很大程度恰是因为“公”压缩了“私”的空间。
对“公”的强调,是人类对私欲的警惕。“人既是一种精明的动物,亦是一种格外自私而顽固的动物”,“因此,立法者及其他智者为建立社会而殚精竭虑、奋力以求的一件最主要的事情,一向就是让被他们治理的人们相信:克服私欲,这比放纵私欲给每个个人带来的益处更多;而照顾公众利益亦比照顾私人利益要好得多”,“再野蛮的人亦会为赞扬所陶醉;再卑劣的人亦绝不会容忍轻蔑”,“他们便利用这部令人着迷的引擎,……将千种荣誉加在人类心灵的理性上,说人类依靠它们的帮助,才取得了那些最高尚的成就”。但也正如曼德维尔所说,“私人的恶德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转变为公众的利益”。“私人的恶德”很难明确界定,但若强迫他人牺牲,高尚就有可能变为恶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代发生剧变,“公”“私”之间的关系变得可以讨论、可以协调,很重要的原因是,与高尚紧密相关的善意得到释放。忘我的、牺牲式的高尚,其理想指向是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这一理想带有强制性,那么,美德就有可能演变为恶德,但若有合宜的善意制衡,高尚就会有所节制。
善意得到释放,未必完全归于良心,有时候是迫不得已,有时候是因为历史偶然性,有时候是因为时间对生命的统治。《沉重的翅膀》看到了一个关键性因素:“穷”。现实中的“穷”激发善意,进而改变高尚所追求的理想。没有哪一个理想社会以“穷”为目标,“穷”无法证明制度的优越性。历史剧变,历史中的善意,是从现实中的苦难而来的。小说花了不少篇幅来暗写贫穷,除了田守诚、夏竹筠等人之外,其他人的生活都是窘迫不堪的,刘玉英、吴国栋、吕志民等,汽车厂的工人,没有哪一个人在经济上宽裕。所以,小说会发出这样的追问:“现在,工人阶级变成了社会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为什么仍然处在这种只能维持和延续后代的经济地位上?他们所创造的那些财富,是不是正常地发挥着它们应有的积累和公共福利的消费作用?”经济上的变革是时代最大的善意。它缓解了事业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对不近人情及强制他人的习气有所劝喻和修补。虽然私人的恶德无处不在,但是,受理想主义感召的高尚与善意仍然随处可见,这些善意改善了日常生活。
《沉重的翅膀》中那些关于时事的描述,对政策的阐述,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因而有其时效性。但是这些由时代造就的美德,经过时间的洗礼,今日在文学里回望,其内在伦理关系又别有趣味。《沉重的翅膀》里有琐碎不堪的庸常生活,但骨子里是积极求变的,这跟虚无、颓废及厌倦的趣味是不一样的,跟“新写实小说”里的“一地鸡毛”,也有大的差异。属于那些时代的美德,激发了文学的无比真诚与巨大热情,《沉重的翅膀》在为时代写下证词的同时,也无意中为时代的美德写下挽歌。
正因为有不乐观,所以挽歌才能既追忆光荣的岁月,也记下不幸的寓言。《沉重的翅膀》很容易让人联想古希腊神话里的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相传雅典的代达罗斯是“建筑家,雕刻家和石雕工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虽然代达罗斯艺术水平超群,他在艺术方面的为人却又自负又嫉妒,正是这种人格上的缺点诱他犯罪,使他遭受苦难”。他杀害了天分比自己高的外甥塔罗斯,之后被判有罪,逃至克瑞忒岛,成为国王弥诺斯的朋友。但当代达罗斯完成为怪物弥诺陶洛斯修建的迷宫后,又决定逃离这个专制国王。他用羽毛和黄色的蜜蜡做成翅膀,带上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一同飞离克瑞忒岛,飞离之前,他警告伊卡洛斯,“亲爱的孩子,要永远在中间的航线上飞”,“如果你飞得太低,翅膀就会擦到海水,变湿变沉,你就会掉到大海里去。如果你飞得太高,你的羽毛就会因为离太阳光太近突然着火。要在海水和太阳之间飞,永远沿着我的航线飞”。伊卡洛斯由于过分自信,飞离父亲的航线,“但可怕的惩罚也立刻降临。更加靠近太阳后,太强的光线烤软了粘合翅膀的蜜蜡”,翅膀散了,他很快“被碧蓝的海涛吞没了”。
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的翅膀,奇妙地暗合了《沉重的翅膀》里的变革。但变革中的人,都是凡人,他们甚至没有代达罗斯的能耐,而且有着更多的“人格上的缺点”。与伊卡洛斯有别,《沉重的翅膀》里那些变革的力量,不是飞得太高,而是飞得太低(根本无法飞到中间的航线),致命的力量来自海水,而非太阳。什么是太阳?是借时代美德呈现但又面目模糊的理想主义。什么是海水?一方面,海水是贪婪、嫉妒、怨恨、庸俗、傲慢、损人不利己、不可理喻、愚蠢等未经“妥善管理”的“私人的严德”。高官田守诚是贪婪的:见风使舵、专权弄权、贪得无厌、善于钻营、唯利是图,任何时代都能身居高位而不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的“海水”,遍地皆是,郑子云有再大的本领,也斗不过他们。对此,张洁内心很清楚,所以小说的结尾,郑子云心肌梗塞发作,尽管小说留了个伏笔,称“放心,他不会死的”,但毕竟,田守诚笑到了小说的最后,“田守诚比往日更加庄重地坐进小汽车,即使在这深更半夜他也衣冠楚楚,像去赴一个盛大的招待会”。那些百般刁难变革者的人,有怨恨有杀心,有的可能是出于嫉妒,有的可能是出于天生的斗志。变革的翅膀再硬朗,也会被这样的海水所困。父亲代达罗斯的航线,实际上难以完成,因为伊卡洛斯还没有被“罪”预设,他在人间还不具备抗争命运的基本能力。《沉重的翅膀》里,代达罗斯式的航线是缺席的,所以,对于年轻人郑圆圆和莫征来讲,除了年轻和生命力之外,他们似乎别无所有,他们能不能飞离大海,去到想去的地方,未知。另一方面,海水也象征凡人的命运。凡人必在由爱情与婚姻构成的日常生活里生育繁殖,现代凡人经不住爱情的诱惑,亦难逃婚姻对生命的消磨。郑子云与夏竹筠四十年婚姻下来,如同陌路。美德里有没有凡人的命运?正如郑子云反思的那样,“高、大、全的形象又是为什么?难道在为事业而献身的后面,没有一点对个人功名的追求吗?……哦,他怎样地为自己描绘着一张圣徒的像啊,为了头上那道光圈,他抛却了一个人的真情实感”。郑圆圆和莫征可以更新爱情的内涵与定义,但是,假如跟时代造就的美德失去亲缘关系,这样的爱情能否飞翔起来?现代凡人终身要面对物质的诱惑,难逃欲望对肉身的消耗。最有象征意味的,是郑子云与夏竹筠之间的关系:郑子云为事业献身,夏竹筠被物质奴役,郑子云对夏竹筠存有道德上的嫌恶,但他并没有阻止并约束夏竹筠在物质上的贪婪。他的遭难,一如代达罗斯,“他自己度过的却是忧伤苦闷的晚年”。这一切,都跟“人格中的缺点”直接相关。“翅膀”的隐喻,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将其置于“海水”与“太阳”的神话里,更显“沉重”之意味。
《沉重的翅膀》通过挽歌和寓言,为现在和未来设下悬念,这是小说经得起回看的重要原因。相关的答案,也许要从《无字》中求得。
注释:
[1]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308页,309页。
[2]Gladys Yang:Leaden Wings.London:Virago Press.1987.
[3]Goldblatt,Howard:Heavy Wings.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好多年前,聂华苓(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创办者)跟出版社说,应该找葛浩文来翻译张洁的小说。我译后给出版社的老板,老板说不怎么样嘛,看德文版时觉得小说好得不得了。但德文版完全不是翻译而是译者自己写小说了。出版社老板说,你稍微妥协一点点,改改语气。我做了一点点,最后他还是说英文的不如德文的好读”(葛浩文),《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谈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学——读者爱故事评论家重批判》(记者刘婷采访),《北京晨报》,2013年 10月 18日。Goldblatt,Howard的译本问世后,PublishersWeekly,Booklist,Library Journal,LA Times,The 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Elle,Inquirer,Times-Republican,The San Francisco,Wisconsin State Journal,Indianapolis News,The New York等媒体都登载了相关的书评及报道。
[4]【荷兰】B.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312页。
[5]【德】斯威布:《古希腊神话与传说》,高中甫等译,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