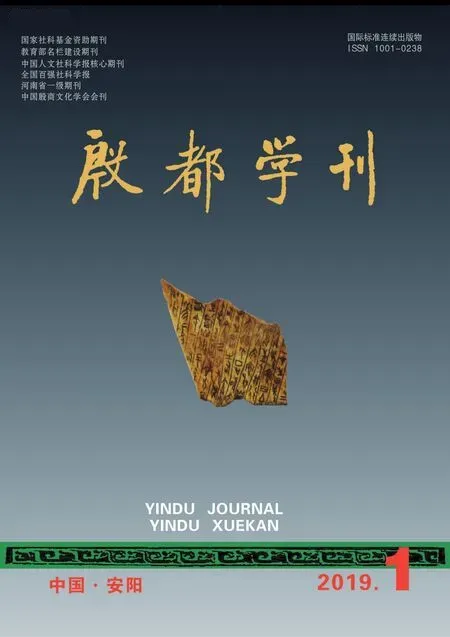说甲骨卜辞中的“省牛”“刍”
——以商国家结构为视角
黄 旭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呼和浩特 010000)

一、关于“省牛”与牛田、牧田
贞乎省专牛。(《合》9504正)
丁□卜,□,贞王往省牛于□。(《合》11173)
贞王往省牛。(《合》11174正)
贞□其□。贞王往省牛。(《合》11175)
贞王往省牛。贞勿往省牛(《合》11176)
丙午卜,宾,贞乎省牛于多奠。贞,勿乎省牛于多奠?(《合》11177)
贞……省牛。(《合》11178)
□卯卜,宾贞……省牛(《合》11179)
……勿乎……贞勿往省牛。(《合》11180)
贞王往省牛于敦。贞王勿往省牛。(《合》40181)

陈梦家以“敦”之地望在淇县沫邑朝歌以南以衣为中心的沁阳田猎区内。[8](P259-260)“敦”之区域在远野,可从牧野证之[注]《周语》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商牧”即商之牧野乃武王伐殷之处,《牧誓》谓“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牧野连接商之近郊,帝辛都淇水沫邑朝歌。牧野之战后,帝辛辗转于鹿台(南单之台)而终为武王擒,事俱见《古本竹书纪年疏证·周纪》、《初学记》卷二四《居处部》晋束皙《汲冢书抄》、《太平御览》卷一七八《居处部》引《郡国志》等书,鹿台乃朝歌之郊,在牧野北,与牧野相近不远,《逸周书·克殷》云:“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牧野乃沫邑之郊外之野,《尔雅·释地》谓“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说文》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处今新乡北卫辉一带,黄河故道在其南,沁阳田猎区犹在其南。,则“敦”与“多奠”之位置处王畿远郊之郊甸,此区域在国家结构当中相当于《载师》所谓远郊之地。《载师》兹录于下:
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
郑司农云:
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养公家之牛。赏田者,赏赐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10](P725)
按《载师》,“省牛于敦”、“省牛于多奠”之区域似周制所谓“牛田”、“牧田”之区域,按郑玄注,“牛田”乃“以养公家之牛”,“牧田”乃“牧六畜之田”。孙诒让《正义》:“江永曰:牛田、牧田,兼用先、后郑之说,皆是授民以田,而为公家畜牧。”按此注与“敦”、“多奠”在国家结构中之位置,连劭名便引《周礼·地官司徒·载师》、《周礼·地官司徒·牛人》,认为关于省牛于敦、多奠之性质乃巡省为公家饲养官牛之“牛田”或为公家畜牧之“牧田”,此公家之牛即由牛人、牧人专门负责饲养,专门饲养牲畜之官员即卜辞之“刍”。[5]
司农云“牛田者以养公家之牛”,后郑不从者,若是养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税?故后郑亦为牛人之家所受田也……司农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农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后郑不从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税乎?故后郑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10](P725-726)
按贾公彦疏,牛田、牧田乃周制,郑注其义即乃牛人、牧人家人所受田,按贾疏,此非公家放牧之地,故税之。所谓牛田、牧田非全为公家性质。由于资料缺乏,“省牛”之区域不宜用周人“牛田”、“牧田”来套,二者是否全为为公家放牧之田尚存争议,且目前较为通行之说法认为《周礼》成书于春秋末或战国早期到晚期之战国说,与春秋前之西周时期亦相去较远,体制如何变化已难探知。
载师者,乃掌地力之官。牛人,按《周礼·地官司徒·牛人》,掌管国之公牛,涉及与祭祀有关的“享牛”、“求牛”,与宾客有关的“牢礼积膳”之牛,与“飨食宾射”有关的“膳羞”之牛及与军事丧事有关的用牛,凡“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而“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簝以待事”。郑注:“职读为樴。樴谓之杙(木桩),可以系牛。”凡所堪祭祀之牛,由牛人授以职人以刍之,刍即饲养,饲养者乃职人,当祭祀时,由饲养者供牛于牛人,牛人“与其盆簝以待事”。《周礼·地官司徒》又有“充人”而无“职人”,“充人”乃“掌系祭祀之牲牷”,“充人”即所谓“职人”。贾疏训:“职”即“枳”,“凡官皆有职,直云职人,无所指斥,但职枳声相近,误为职,故读从枳。充人置枳, 入地之时,枳枳然作声,故以声名其官也。”又,“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选入牧人。临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系养之。今若即以枳人为充人,则隔牧人,故连牧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10](P723-724)按此,充人即系养公牛之人,亦即牛人所授刍之的职人,乃直接负责饲养公牛之官员。卜辞有:“贞,执雝刍。贞,勿执雝刍。”(《合》122)“贞,弗其执雝刍。四月。”(《合》127)某族刍养牲畜的人或奴隶,胡厚宜以其乃某族刍养牲畜之奴,即《周礼·充人》中郑注“养牛羊曰刍”、《孟子·梁惠王下》赵歧注“刍者,取荛薪之贱人也”,则刍乃刈草饲养牲畜之奴。[11]按此,“雝刍”即雝族方刍养牲畜之奴,“刍”指某族方刍养牲畜持有低贱身份之奴(“刍”在卜辞里兼具多义,亦不能一概而论,参下文)。所谓“刍”乃专门饲养牲畜的类似牛人具有职官性质的人员,似当商榷。卜辞有专门负责管理祭祀用牲及生活消费之官员“刍正”,专司刍之管理。郭旭东亦涉及了这种专门人员,商王朝设立了专职官员“刍正”,专司“刍”的管理,“正”,即官长,亦略涉及了其他具体牲畜的官员“牛臣刍”、“司羊”等。[12]“刍正”等或即周牲畜管理制度之渊源。
鉴于卜辞所用牛骨作为卜骨主要来源之一及商代祭祀用牲之法的普遍性,其性质应至少与王室生活或祭祀有关。由敦、奠之位置知王都以外的郊甸到王畿外围地带的这一块区域,不仅有很多的农业生产区(甚至设了很多储存谷物的粮仓)、田猎区,还有不少饲养牲畜之饲养牧业区。其中原因,如郭旭东所论“商王朝在极为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对其传统的畜牧业并没有偏废,相反还是非常重视的,畜牧业生产在商代的经济生活中还占有相当地位,它与农业生产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12]
二、“刍”、“省牛”与商国家结构
单独地分析卜辞“刍”之本义或引申义并无意义,试以商国家结构为视角与所总结的有关“刍”等卜辞几个特点结合在一起分析。
商存在着以王畿为中心的呈同心圆结构分布的国家结构,殷统治架构具有多层次的同心圆特征。一般认为商国家结构是:商王朝的王畿区是以王邑为中心,王邑之外乃东、南、西、北四鄙之近郊,次之以东、南、西、北四奠,奠即甸服,甸由王田区而起名,并连同宗族邑聚及农田区一起构成了王畿区,再次之以四土、四方,四土周围之边地即四戈,乃边侯之地,王畿区为内服之地;四土乃外服之地,四土之外为乃邦方之域。[13](P27)[14-15]陈梦家考内外服认为《召诰》、《酒诰》所谓殷制“侯甸男卫邦伯”,《酒诰》谓之外服,邦伯乃外服诸侯,但介乎邦伯与国邑之间亦存在着许多边域诸侯[注]陈梦家认为《酒诰》之殷制诸侯乃外服,《大盂鼎》“殷边侯田”在内外服之间,即在边域“四戈”,侯本义即斥候,伺望,乃为殷守边,侯、田由戍边斥候引申为诸侯,《君奭》所谓“小臣屏侯甸”乃商邦国之屏藩,《殷虚卜辞综述》,第328页。,在殷邦内外及其边域上,有许多大小邦的诸侯,称其君长乃诸侯,称其地方乃族邦。[8](P325-332)林欢在陈梦家基础上有过分析。[6](P31-32)简单来说,畿内分布着不少数量的邦内诸侯,四土四方至商国家边境“四戈”、“四戈”外围分布着众多殷边诸侯侯田、外服小邦,更外为以战争分离为常态的多方。在此结构下,虽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控制的不断强化,“使许多方国部族的政治独立性日益减弱,其首领成为商王朝的臣属官吏,王朝与诸侯、方国之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支配和从属关系”[16],但整体上商由政治宗教核心区为核心的王畿向四周的影响力处于减弱状态。刘桓仔细分析了商时期作为商政治关系不同层次集中体现的服制与各层次的邦内贵族、族邦、殷边侯田、方国等纳贡之间的相互关系。担任王邦各级“臣”、“亚”、“射”等职务的邦内族邦贵族对商有为应对岁祭的岁贡等入贡活动,而政治关系益疏浅则入贡种类与次数亦少。[17](P15-44)卜辞中可以明显察觉到:政治关系益发疏浅的邦方或方国以分离为状态的战事、抓取敌国俘虏等事益增加,载除战争等以分离为特征的活动之外的事务或活动的频率亦随之减少,与商的政治联系处于递减状态。刘桓之研究亦从侧面反映了该问题。因此,处在内服邦内诸侯及藩屏之诸侯封国,与商地理位置更近,政治宗教等联系更加密切,包括诸侯封国对商的入贡献祭种类更多(助岁祭、陟祭、御祭等)、向商呈报多方军情、从商征伐、代王祭祀、频繁入商、入职为官、联姻、以商之名义替王处理地方事务(巡省或出使诸侯、巡视商边、征伐监视镇抚多方、征收牲畜等等)等。王震中称商为复合制国家结构,尤其是担任商“亚”、“射”、“师”、“子”等官职爵位的族邦贵族与商政治宗教联系最为密切。而那些地理位置更远且相对远离商政治中心的族邦方国则与商之间的政治、宗教联系益发薄弱。进一步分析:
(一)刍牧卜辞与国家空间分布特征、土地开发
贞于敦大刍。(《前》4.35.1)
贞奠臿以刍于丂。(《合》101)
戊戌卜,雀刍于教。(《甲》206)
……唐刍……(《合》145)
庚申卜,宾,贞朕刍于斗。贞朕刍于丘索。贞朕刍于斗……(《合》152正)
贞曰氐来,迺往于敦。贞于敦大刍。(《合》11406)
贞刍于旬。(《合》11407)
……奠弜刍于□。(《合》11408正)
贞刍于奠。(《合》11417正)
“刍”乃本义,“芻”,《说文》训为“刈艸也,谓可飤牛马者,象包束艸之形”[18](P44),《甲骨文字典》谓“象以手取草之形。罗振玉曰:‘从又持断艸,是刍也。’”[3](P55)是以《说文》不确。“淫刍荛者”(《左传·昭公十三年》),“禁刍牧采樵”(《左传·昭公六年》),“刍莝养马”《越绝书·外传本事》,本义,刈草,故王国维谓“疑即刍荛之刍”[19]。“刍”,亦作吃草之牲畜,如“某来刍”。赵诚以“刍”乃“从又从断草,象以手将一草折断之形,即刍字……其本义近似于现代口语里所说的‘打草’”,但若直接训为“割草”,则给人一种“用刀割而排斥用手抓拿”之感觉,此“可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完全吻合”,上几辞之“刍”乃放牧(即是将牲畜赶去吃草,当是所谓的放牧)之引申义[20]。
关于商代方国地理、族邦方国地望分布,学者已诸多考证:


结合学界关于“刍”本义之研究及刍牧地点地望之分析可知:
上述将某族邦、商王“刍于某地”并列,“某族邦名或邦君名刍于某地”应是族邦之邦君而非该族邦之族人或国人,“雀刍于教”即邦君之雀。 “刍”之本义乃刈草,引申为放牧,王、诸侯邦君刍于某地,结合所涉及之地名:各族邦邦君刈草放牧于直属商的畿内或王畿附近的王室牧场,非各族邦的私有牧场,性质乃王与族邦贵族牧于或刍于畿内某地,是一种主持开展放牧活动的表现,并夹杂着一些放牧礼——或先由王或邦君进行象征性的刈草以刍喂牲畜之活动(一种象征性的主持开展刈草放牧活动政治典礼),并负责主持该地畜牧活动,相关管理人员再组织众人或一些奴隶进行放牧。“王或族邦邦君刍于某地”放牧之性质非同于身份较低群体专门饲养或放牧人员的放牧活动。
直属于商王邦的牧场不仅大量分布于王畿内或王畿附近,甚至广及外服诸侯区域。此种在外服族邦区域开垦牧场的活动在卜辞中能找到相似内容。林欢论商外服的属地分类之第二类即在附属国族势力范围内通过垦田建立占有的土地[6](P55),在晋中南诸国区域建立的“南牧”、“北牧”等直属于商的牧场,乃通过放牧于诸侯区域而占有的属地。在外服诸侯邦境周围分布有直属商的牧场,是商在二者存在服属政治关系的条件下,对诸侯族邦周围土地进行的一种占有与开发,构成商属地之一部分。此种开发方式类似“裒田”,“商朝后期,商王朝除了在王畿内开垦农田、设立牧场外,还把田庄和牧场扩展到了周边部族和方国境内”,如“癸已卜,宾,贞令众人取(趋)入羊方裒田。”(《合》6)“壬戌卜,争,贞乞令曼裒田于先侯,十月。”(《合》10923)[16]如后述,各诸侯族邦在境内亦有属于族邦、但在义务关系上需献祭大邦商的族邦牧场,而畜牧区作为野或甸常分布于政治实体之外围,它们与属于大邦商控制的直属于商的牧场交错分布于诸侯国境周围,结合成势力圈。这种刍牧场所的分布特征,正是商外服属地与王畿外围的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诸侯族邦的犬牙交错特征在经济范畴的体现。

(二)对其他刍牧卜辞、“省牛”卜辞之分析
与“某族邦刍于某地”不同者,即在“刍”前加一族名作名词:
取竹刍于丘。(《合》108)
勿取夫刍于〔隹〕。(《合》109)
贞乎取羞刍。(《合》111正)
贞乎取何刍。(《合》113正甲)
勿乎取何刍。(《合》113正乙)
贞取克刍。贞取般刍。(《合》114)
戊申卜,宾,令吴取析刍。(《合》118)
此两类卜辞,前者“某族邦刍于某地”之“刍”是动词,后者乃名词。“取某族方刍”之义,或乃某地、某族的刍,即该地、该族刍养之牲畜,“取某刍于某地”即取某族在某地饲养之牲畜[注]于省吾持此观点,其从罗振玉“从又持断艸,是刍也”之训,甲骨文刍作名词或动词用,一则刈草,二则读作牲畜之畜,畜、刍为通谐,《楚语》有“刍豢几何”,韦昭注“草食曰刍”,甲骨文之畜字不作牲畜用,“取某刍”,“刍”上一字加方国名或地名,表明乃某方国某地之畜,见《甲骨文字释林》,第264页。。与“取某族之刍”性质相近或相同者,即取族邦之牛或马等,盖刍莝养马而草食曰刍,如:
弗其取弜马……以才(在)易。 (《合》170)
贞取马。(《合》8798)
□□卜,贞……取……牛(《合》8799)
乎取牛。(《合》8801)
贞乎取牛于吴。(《合》8806)
贞乎取羊。(《合》8813反)
勿乎取方骨马。(《合》20631)
或“氐刍”、“氐某族邦刍”、“取某族邦刍氐”,如:
贞吴率氐网刍。(《合》95)
允叶率氐骨刍。(《合》97正)
贞侯氐骨刍。(《合》98正)
氐侯刍。(《合》100)
□□卜,争,贞令雪氐牧刍十。(《合》409)
乙未卜,宾,贞氐武刍。氐武刍。贞弗其氐武刍。(《合》456正)
庚子卜,亘,贞乎取工刍刍氐?(《英藏》757)
“氐”,郭旭东训抵达义或致送义[注]“氐”,郭旭东训致送义,并对与“取某族邦刍”类似的贞问地方族邦所致送之“刍”(氐某族邦之刍)、派人前往“网刍”等等曾加以简单讨论,见《从甲骨文字“刍”、“牧”论及商代的经济生活》,第146-147页。,与“取某族刍”义相近,某人将某族之刍氐商,即将向某族征取或某族入贡之刍致送于商,谓“氐某族刍”。《合》95即吴将网来之刍入于商,所网之刍或系属于畿内商牧场,亦或族邦牧场,性质不明。

诸侯、族邦方国的邦君入贡之牲畜或备商征取的牲畜、马匹、犬、龟甲等,与族邦邦君所俘获多方俘虏及多方刍养牲畜等物共同构成了诸侯、族邦方国众多入贡或征贡的内容,性质同。它是商王畿周围众族邦依附于大邦商的国家结构并划分彼此权力义务之结果,是宗主国与从属族邦的政治相互关系在职贡范畴的体现。

卜辞中所见诸侯族邦境内的刍牧地名或某族所氐之刍、来刍、供商征取刍,这些牲畜之饲养区域,因资料缺乏,不好直接武断地认为该些区域皆系直属于大邦商之牧场。各族邦在各自族邦附近应分布有一些隶属于族邦的畜牧点,产物除自己使用外,亦选作入贡之物或被商征取一部分。多奠、敦、丘索等隶属于商或商王室的畜牧区域集中在畿内或王畿附近,部分散布于外服诸侯区域。居于王畿内部的商与王畿外部族邦拥有各自的畜牧点,彼此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二者地理上存在交错分布特征(商牧场穿插在诸侯国境周围:直属于商王室的牧场部分分布于诸侯国境周围或境内),又存在政治关系从属下的入贡关系——族邦的刍养区域之牲畜带有向大邦商贡刍或由大邦商派人前往领取该族在某地饲养之牲畜以备祭祀之用的助祭性质的入贡义务。

“王往省牛于敦或多奠”结合“刍于敦”、“刍于多奠”,敦、多奠是商众多牧场之一(其他还有丘索、斗等地)。敦、多奠或有专门刍养牛等牲畜之奴隶,或还有其他放牧人员。当商燎祭、沉等用牲之祭祀及宫廷生活资料时,呼多奠等地供牛,如《合》8938甲:“贞勿乎共牛多奠。”“戊申……亘贞……乎共牛多奠。”因此,“王省牛”,即前往巡省省视牛之放牧,亦巡视放牧之牧地,亦巡省刍养牲畜之奴隶或相关人员。王“省牛”之区域具备特殊性,王“省牛”多限于敦、其次为多奠,可见作为商众多牧场之一的“敦”作为多重性质之区域,乃王亲自参加的象征性的刈草放牧的政治性典礼牧场区域之一,亦乃巡省礼的构成部分。实则“敦”乃商王众多政治性礼制的集中区域,不仅仅涉及刈草放牧、省视牧场之牛,如后期伴随敦地附近大规模游猎活动的兴起,成为了与商王田猎并行的“省田”(观看巡视田猎)礼的集中区域。
(三)刍牧卜辞反映了商与居于国家结构中不同层次的族邦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商向附属诸侯族邦索求财物时,卜辞中除部分载向某族某处地畜牧点进行直接征取外(上述《合》108、109、119诸例),多仅载取何族邦之刍、氐何族邦之刍、取何族邦之牛羊马匹等物。有的卜辞则载某族邦“来刍”或商派人前往某族(或具体到该族邦某些畜牧点)进行征取,却未见商贞“该族邦邦君+刍于+某地”。进一步对有关“刍”卜辞进行分层的分析,其原则按政治宗教联系与亲密程度来排列。

因此,商有权从畿内贵族、殷边诸侯、外服小邦等族邦征取他们在某区域所刍之牲畜,这些族邦亦有向商敬献所刍之牲畜或供商派人征取之义务。商国家结构中不同层次的畿内诸侯、边境诸侯等族邦方国均有将自己所养的包括牲畜在内的物品入贡大邦商之义务。这些属邦虽在国家关系上被置于商复合制国家结构中而依附于大邦商,但拥有一定的政治实体地位(存在商将某些土地册封给诸侯封国之现象)。不过,某族邦性质一致的来刍、来马、入龟甲、来羌,或商取某族刍、马等,或氐某族刍、马等,性质上仍不能断定入贡或征贡的牲畜饲养区域是属于大邦商官方在该地区设置的王室牧场或商王邦的官办牧场,或某族邦在某地设置的专门用来履行入贡大邦商或备大邦商征取之义务的助祭入贡牧场。


因此,大邦商以亲密族邦贵族代王主持放牧事宜之性质,应类似于笔者上述列举事务之性质,其构成了亲密族邦贵族代王或在商之名义下执行某项特定职能的政治事务的内容之一,乃一些族邦与商地理更近、关系更为密切的表现之一。
戊申卜,宾,令吴取析刍。(《合》118)
己亥卜,萑(观)耤。己亥卜,贞令吴小耤臣。(《合》5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