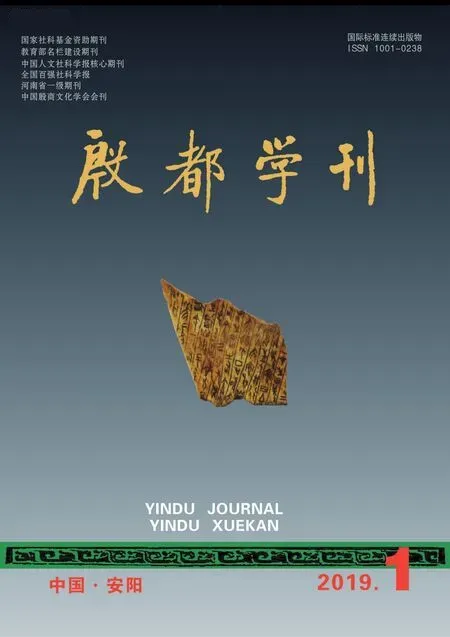从北朝的佛教造像记看女性的造像活动和社会地位
李林昊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引言
《魏书·临淮王传》有言:“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1](P491)这是北朝时期妇持门户、女子妒忌之风盛行的反映。这一时期,女子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她们不再仅仅是夫权的附庸,反而更趋向人格独立,甚至可以左右夫婿纳妾。《魏书·长孙道生传》载:“罗年大(长孙)承业十余岁,酷妒忌。承业雅相敬爱,无姬妾。”[1](P725)长孙承业先后出仕北魏、西魏,并被封为上党王,却因为妻子善妒而不敢纳妾。北朝女子的善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北魏孝文帝就曾为此大发感慨:“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1](P393)由此可见,北朝女性的家庭地位是相当高的。
除了传世文献外,此时期的佛教造像记亦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反映。风靡北朝的佛教信仰及其带来的造像风潮打破了阶层、性别、年龄等的限制,女性作为重要群体参与到造像活动中,她们不但可以参与家庭和社会群体的共同造像,还可以作为造像主体,或为自己造像,或为亲人造像,或为发愿祈福而造像,因此出现了种类众多的女性造像记。女性造像记的出现,为我们研究北朝女性的生活、心态、宗教信仰、社会活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和视角。本文拟从现存的北朝佛教造像记切入,探析当时女性在造像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和女性地位提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造像活动的风行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于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盛行一时的宗教。随之而来的是北朝造像之风的兴盛。隋末唐初的高僧法琳在《辨正论》中提到,隋文帝时代“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海内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许躯”。[2](P509)可见隋代之前的北朝造像数量之巨。佛教在北方的普及使得造像活动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参与造像。一时之间,造像活动蔚然成风,参与佛事活动也成为北朝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朝时期的墓志亦数量众多,但其只是权贵豪强阶层才能享有的特权。北朝重厚葬的社会风俗和儒家对于“三不朽”思想的提倡,使得贵族和士大夫阶层颇重功名,死后也希望名传千古,因此镌刻墓志、树碑颂德在上层社会风靡一时。康有为曾云:“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3](P134)墓志实际上是为墓主记事立传,对于墓主的生平事迹、功业成就进行介绍和评价,故而多请有文采、有名望之士,如著名文学家庾信就是当时撰写墓志碑文的名家。北周王族公卿的墓碑墓志,大多请托庾信撰写。《周书·庾信传》有载:“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4](P734)

墓志有千古留名、润色功业之用,大都富有文采,如若请名人名家撰写,则需要花费重金,非一般平民家庭所能承受。而佛教信仰和造像风潮打破了阶层、性别、文化程度等的限制,贵族、平民、男女、老幼皆可自由造像。造像记有着固定的套语句式,信众可据此于石像上镌刻佛法、经文,发表内心之祈愿,这就为造像记的镌写提供了便利。信众造像的根本目的就是发愿祈福,对于造像者、造像对象、造像题材等信息往往一笔带过,字数相比于墓志要少。而且造像记没有文采方面的要求,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就可以撰写,即使目不识丁的平民请人代笔刊刻造像题记,费用也不是很高。再加上平民造像尺寸较小,造像的经济成本较低,平民家庭完全有条件供养佛像,因此造像记得以在广大平民百姓中流传开来。
关于造像记的套语和结构类型,日本学者佐藤智水在《北朝造像铭考》中将造像记分为A、B两种形式,并进行了详尽阐释,目前学界多采用佐藤氏的观点,此略不赘。[注]佐藤智水将造像记分为A、B两种类型,A类造像记直接表明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造像对象、祈愿内容等;而B类造像记则首先阐释造像之佛法意义,再揭示造像者身份、造像者、发愿动机、造像对象等内容。具体参见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铭考》,收录于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需要强调的是,有了固定形式的撰写套语,即使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平民来说,撰写造像题记亦非难事。如刻于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的《阿鹿交村七十人等造像记》:
大齐河清二年,岁次癸末,二月朔,十七日辛巳,阿鹿交村七十人等敢□天慈降尊,惠泽洪深,其唯仰凭三宝,可□皇恩下述□心矣。故知宝璧非随身之资,福林获将来之果。人等深识非常,敬造石室一躯,纵旷东西南北,上下五尺。中大佛、大菩萨、阿难、迦叶、八部神王、金刚力士,造德成就,佛法兴隆。皇帝陛下、臣僚百宫,兵驾不起,五谷熟成,万民安宁。复愿七世父母,阖家眷属,边地众生,普蒙慈恩,一时成佛。[6](P223—224)……
北齐的武成皇后胡氏作为贵族阶层的代表也曾参与造像活动,可将其留下的《武成胡后造像记》与平民造像记《阿鹿交村七十人等造像记》进行比照参看。
盖力士慈悲,施□畏于六趣,菩萨弘护,恣神通于三有。皇心所以翘仰,圣意所以殷勤。皇太后以武平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敬造观世音石像一区,以此胜善,仰资武成皇帝升七宝之宫殿,皇帝处万国之威雄,傍兼有心之类,一时俱登圣道。[7](第9册,P390—391)
按照佐藤智水先生的分类方式,《阿鹿交村七十人等造像记》属于A类造像记,《武成胡后造像记》属于B类造像记。而《阿鹿交村七十人等造像记》虽为A型,亦带有一些B类的特点,其造像题记中包含发愿动机、造像者对于佛法意义的体悟和阐释。仔细比较皇后造像记和平民造像记,发现《阿鹿交村七十人等造像记》的文采及对于佛意的领悟并不亚于《武成胡后造像记》,这说明平民中的佛教信众亦会造出有文采、有价值的造像记。佛教以包容的姿态吸收了各个阶层的信众,将宗教的狂热渗入到北朝民众的生活之中。
二、北朝佛教造像中的女性造像
北朝佛教造像记中出现了大量的女性造像记。从女性在造像记中的身份来看,她们主要以造像者或造像对象的面貌出现。所谓造像者,就是造像的主体;造像对象就是造像的人物对象,即为谁而造像。北朝造像记中,以女性为主体的造像类型复杂多样,出现比较多的主要有三种,即夫妻互相造像、夫妻共同造像和母亲为子女造像。
夫妻互相造像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丈夫为妻子造像,即丈夫作为造像者,妻子是造像对象;第二种是妻子以造像者的身份出现,丈夫是造像对象。如北齐天保十年(公元559年)的《成犊生造像记》,就是佛教信众成犊生为其亡妻而造:
唯大齐天保十年,岁次己卯,三月戊□朔,廿六日癸丑,胶州高密郡琅琊县人成犊生,为亡妻敬造卢舍那像一躯,上愿国祚永隆,万民宁泰,亡者升天,现存寿福,居家大小,常与善□。[7](第9册,P40—41)
而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的《张元祖妻一弗造像记》,则属于妻子为丈夫造像的类型:
太和廿年,步举郎张元祖不幸丧亡,妻一弗为造像一躯,愿令亡夫直生佛国。[7](第3册,P296—297)
北朝是一个全民信仰的时代,佛教深入民间,家庭全部成员信仰佛教的现象很普遍。众多家庭的夫妻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加入同一个佛教团体,一起参加佛事活动。在这种信仰自由和社交自由的环境下,加上佛经教义“众生平等”的渲染,为女性在家庭中拥有与丈夫平等对话的地位奠定了思想和话语基础。共同的信仰追求往往会促进夫妻之间的感情。当妻子亡故后,丈夫更倾向于用一种宗教的仪式感来表达对于亡妻的悼念和祈愿。
夫妻共同造像是夫妻二人皆以造像者的身份共同造像。这一类型造像对象范围比较广泛,有夫妻为父母造像,有夫妻为子女造像,也有夫妻二人只是单纯地出于祈愿的目的而造像,还可以是为自己造像。夫妻共同造像类型中,为子女造像的比例无疑是最高的,如造于北齐乾明元年(公元560年)的《欧伯罗夫妻造像记》,是夫妻为女儿造像的代表:
唯大齐乾明元季,岁次甲辰,七月庚戌朔,十日己未。

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的《丁辟邪造像记》是夫妻为自己造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给家人祈福,希望能得到佛祖的保佑。该题记言:
孝昌二年,五月廿三日,丁辟邪为自身夫妻,居眷大小,法界众生,敬造无量寿供养。[7](第6册,P12—13)
母亲单独为子女造像也很普遍。有的平民女性在亲人去世后无所依靠,出家成了比丘尼,即使已遁入佛门,但是她们的尘缘并未割舍,比丘尼为自己亡故子女造像的事例不在少数。这恰恰反映了北朝时期的宗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与民间、信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佛像上镌刻的文字无不体现出母亲的舐犊深情,母爱的伟大和宗教的虔诚在造像记中同时得以彰显。如:
正光四年九月十五日,清信优婆夷李,为亡女杨氏王神英敬造无量寿像一堪,愿亡者离苦得乐,普津法界。[7](第5册,P220—221)
孝昌元年,八月八日,比丘尼僧达,为亡息文殊造释迦像。愿亡者升天,面奉弥勒,谘受法言,悟五生忍。现在眷。常与善居。七世父母,三有四生,普同此福。[7](第5册,P331—332)
上述两篇造像记分别为《优婆夷李造像记》和《僧达造像记》。《优婆夷李造像记》是佛教女性信众李氏为其故去的女儿所造。《僧达造像记》的造像者是比丘尼僧达,造像对象是其去世的儿子。北朝的俗字和异体字数量繁多,《僧达造像记》中的“息”其实就是儿子之意,现在日语的汉字词中仍保留“息子”一词,指的就是儿子。因此,从“为亡息文殊造释迦像”可以判定出这是比丘尼僧达为自己的儿子造像。
需要说明的是,夫妻互相造像、夫妻共同造像和母亲为子女造像三大种类的女性造像记,大部分都是造像者为自己已经亡故的亲人进行的造像活动,在表达深沉悼念、哀思的同时,又寓含着对于亲人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造像者通过造像为亡灵进行超度和祈愿,不仅意寓着造像者的情感,更有一种浓厚的宗教仪式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民众逐渐接受了“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理论学说,认为世间众生无不在轮回之间流转。六道有“善道”和“恶道”之分,死者生前所造之“业”,决定了轮回后的去向。除了生前广结善缘以外,倘若亲属举行各种佛事活动,为亡者追福,死者便能往生善处,由此导致社会上追荐之风的盛行。[8](P26)从这个层面来讲,佛教造像记不仅仅是民众一心向佛、记录宗教活动的一种形式,也是民众祈福、发愿的重要载体,是民众真诚朴素的情感表达。
三、北朝女性造像活动的社会参与
北朝文学家刘昼在《上高欢书》中云:“尼与优婆夷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许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矣。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9](P668)《上高欢书》作于东魏时期,刘昼在文章中提到,当时的僧尼有二百多万人,数量甚巨。僧尼人口的剧增,随之而来的造像之风日炽,女性信众群体自然不会缺席。从北朝现存的造像记可以看出,北朝女子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在造像活动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女性信众或与僧尼合作造像,或与家庭成员一起造像,或以宗族、村落为单位进行造像,更是出现了女性团体结成佛社造像的情况。北朝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从女性造像活动中一窥端倪。
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的《逢迁造像记》是女性参与家庭造像的一个典型例子。佛教男性信徒逢迁为亡妻造像,造像主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妻子和女儿以及亡妻的父母、姐妹都参加了此次造像活动。参与者中包括了多名女性,她们还都留下了名字:
大齐武平四年,岁次十一月癸亥朔,八日庚午,佛弟子逢迁为亡妻赵伯姿敬造观世音石像一区,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一切众生,咸同斯福。
逢略,妻董伏;逢遵,妻树妃,女妙;逢陁,妻杨臱;亡人父赵桃树,母成贵,姉令光,妹明光,妹□光,妹神光。[7](第10册,P28—29)
北魏正光二年(公元521年)的《锜麻仁造像碑》也是众多女性参与宗族造像的典型,碑文如下:
母朱女炽,祖亲李苌命、祖亲柳娉,祖君锜光、父锜元伯、叔父锜□□。
姪锜□□、弟锜灵□、□锜胡奴、兄锜文庆五郡宗主、弟锜燕石、弟锜双胡、锜神敬。
……
姪女(要胜、姪女李男朱、姪女阿小、清信女□化、清信女老□、清信□阿火。
夆妻公孙□□、汉妻王兆□、□妻□□、□妻□□、首妻李真朱、洛妻魏三好。
……
神欢妻魏花女、放阳妻孙合姜、女香映、女姿方、孙女阿眇、孙女香综、女香好、女□□、孙女小香。
……

该造像题记是锜氏家族129人的共同造像,囊括了男女老少等几代人。古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较低,受到儒家礼教制度的家庭乃至所在宗族的约束。宗族、村落是以男性为核心的,女性处于附庸地位,古代女性是没有资格参加家族祭祀活动的,而造像记中却反映出女性可以参加宗族组织的造像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宗族对女性活动的限制。《锜麻仁造像碑》记录的人物中,像女儿辈和孙女辈等年纪小、辈分低的女性竟然都可以参与宗族举行的造像活动,说明此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
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女性邑社组织,它的出现意味着拥有共同信仰的女性群体可以较为自由地结成佛社,一起组织、参与佛事活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社,称为邑、邑义的最多,法义次之。这里的“邑”字,不是地域概念,而是指某一地域内信奉佛教的人结成的宗教团体。[10](P90)这一时期,女性可以不受束缚地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除了参与佛事活动之外,还可以在佛社中进行社会交往。
造于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的《刘凤姜等四十九人造像记》对于女性信众的结社有充分反映:
大魏武定三年,岁次乙丑,四月己酉朔,五日癸丑,清信女刘凤姜率领同壬四十九人等,敬造弥勒下生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群僚百官,及七世父母,现在眷属。愿愿从心,所求如意。
该造像记中的佛教邑社有49名成员,“清信女”指是受三归五戒、持清净信仰的女性佛教徒。由“清信女刘凤姜率领同壬四十九人等”可以推断出这是一个女性群体组成的佛社,且刘凤姜是该佛社的领导者。
从邑社组织的形式来看,除了由女性集体组成的邑义外,还有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混合邑义,比如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的《元氏法义三十五人造像记》就是男女混合的邑义造像。造像记中的女性在宗教活动中的表现是相当活跃的,有的女性在男女混合的邑社中还充当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北朝时期,墓志也风靡一时。但是墓志属于高官权贵才能拥有的“特殊产品”,因为墓志造价过高,单单邀请名人名士撰写墓志时的“润笔费”就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担的。女性墓志也有很多,但能够拥有墓志的女性或为贵族女性,或为官吏之妻,我们很难从墓志中看到平民女性的身影。如果说墓志是贵族阶层的小众化产品,那么造像记则是深入到平民阶层的大众化产品。造像记深入民间,一方面说明佛教和造像的世俗化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因为与此时期同样盛行的墓志相比,造像记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按照碑文惯例和汉民族的礼法、习俗,妇人皆称氏而不名,女性碑文的具体书写形式多为某某妻某某氏墓志,大都有姓无名。当然也有一部分女性墓志对于女性墓主的名字有详备的记录,但总体上比例不高。而绝大部分造像记不但镌刻了参与造像活动的女性的姓氏,同时还有详细的名字。在造像活动中,无论女性是作为造像者出现,还是以造像对象的身份出现,哪怕只是在群体造像中充当不起眼的角色,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佛像旁。贵族女性,亦或是平民女性,她们的姓氏、名字都能够通过造像记这一载体而得以流传下来。平民女性进入造像的行列,更是跨越了墓志作为贵族女性特权的局限。相比于墓志,造像记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其对于平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反映。
四、北朝女性社会地位较高的历史镜像问题
北朝女子地位较高的现象是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它就像北朝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投射在镜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共同构成了北朝宏大的历史镜像。
(一)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强大母权制度的延续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其王朝建立之前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属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氏族制的遗风使得北魏政权延续了部落联盟时期强大的母权制度。《后汉书·乌桓传》有言:“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计谋从用妇人,唯鬭战之事乃自决之。”[11](P2979)从中可以看出乌桓仍然保留有氏族母系社会的残余,且女性在乌桓族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后汉书·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11](P2985)鲜卑和乌桓同属于东胡族,言语、习俗皆相同,因此乌桓部落强大的母系力量在鲜卑族中同样存在。
北魏建立以前,拓跋部刚刚脱离母系社会不久,母权制的遗风仍在延续。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妇女能够干预部落联盟议事和王位继承。从北魏前期实行的子贵母死制度就可以看出女权强势的端倪。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的第一章《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对于鲜卑政权母族强大的实力有精彩论述。从神元帝力微到昭成帝什翼犍的100多年中,是后权支撑皇权,拓跋家外部家族支撑拓跋部,嗣君得立,一般都有赖于强有力的母后和强有力的母族。文帝兰妃两次为子孙争得君位;桓帝祁后三次为子孙夺得继承权,先后立君四人五次;平文帝王后则先为平文的庶长子翳槐夺得继承权,后又以己子什翼犍继承长兄翳槐君位。[12](P15—30)北魏帝国的开创者拓跋珪就是什翼犍的孙子,而拓跋珪也是凭借其母族贺兰氏的强大力量才夺得继承权的。由此可见,鲜卑族部落首领的更迭与继承,其背后必然有一个或数个强大的母族来施加影响,母系一族甚至具有左右继承人的力量。
女性干预政治贯穿北魏一朝。早期有常太后的干政,中期有冯太后的垂帘听政,后期有胡太后的专权。掌权女性在政治上的作为和影响,将会使女性群体在政治上的地位更为凸现,贵族妇女之间的社交往来蔚然成风,她们自由地拓展个人的社会交际圈。鲜卑政权女性地位较高的古老风俗为后宫干政提供了便捷,一旦出现一位强力的太后,她的政治行动势必会影响到朝局乃至国家政权的各个层面,她在提升自己地位的同时,其代表的女性利益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会水涨船高。从贵族阶层到平民阶层,从鲜卑族扩散到北方汉族广大群体,其影响是自上而下的。同时,女性干政又使得古老的母系氏族遗风得以延续,从这个层面上讲,早期的鲜卑风俗和后期的太后专政是相辅相成、双向促进的。
(二)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
《颜氏家训·治家》有云:“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13](P51)这说明南北朝时北方的女性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北方政权更迭的频繁,战乱、兵灾导致人口锐减,尤其是男丁数量的减少使得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广大平民女性必须走出“闺房”以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也要承担更多的生产劳动来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
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1](P3107)“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1](P3108)与均田制相适应的租调制,“其民调,一夫一妇出帛一匹,粟二石”。[1](P3109)均田制与租调制本质上皆是以一夫一妇的小家庭为授田纳租单位的,这就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每位女性可以分得二十亩露田和五亩麻田,这在古代历史上实属罕见。妇人分到了田地,也就有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北魏政府以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授予妇女一定数量的土地,这就使得妇女享有较高的经济权利。有了土地这一经济基础的支撑,女性自然就有了经济独立权,生活上也就有了自主权,可以做到不依附于男性而独立生活,这就使得女性对于男性的人身依附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也便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改善而提高。
(三)不同民族文化的互渗作用
自两汉起,我国确立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迅速下降。北朝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逐鹿中原,他们不单单依靠强大的军事武力征服北方汉族人民,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对于北方汉族以全方位的冲击。在胡汉融合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也不断冲击着汉族儒家伦理体系中的“男尊女卑”观念。
北魏孝文帝时期进行的改革,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移风易俗,全面实行汉化。但由于孝文帝英年早逝,其后相继出现了胡太后专权、六镇起义和尔朱荣之乱,北魏政权在孝文帝去世三十五年之后就灭亡了,这就导致少数民族在思想文化层面汉化得不够彻底。加上孝文帝颁布的均田制和租调制为女性的生产生活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因此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反而趋向稳固。
鲜卑族政权汉化的进程中对于北方汉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就在少数民族汉化的同时,北方汉族亦在被“胡化”。比如东魏的奠基者高欢,隋朝的建立者杨坚,以及唐朝的开创者李渊的先祖,全都是鲜卑化的汉人。因此鲜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也深入到汉族民众的生活之中。《颜氏家训·治家》载:“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 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13](P48—49)颜之推描述的“河北人事,多由内政”正是女性掌家现象的反映,这在北朝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北朝是女性社会地位较高的一个历史节点。五胡乱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断冲击着汉族的文化体制。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后,其母系氏族遗风随着统治的不断加强,势必影响并渗入到平民生活之中。胡化汉人高欢建立的北齐和鲜卑人宇文泰建立的北周,在北魏构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框架上基本保持不变,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着其经济基础的日益牢固,在达到较高的水平后趋于稳定。
北朝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她们拥有参与社会活动的自由,经济上的自主为女性进行造像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佛教风行于北朝的盛况下,女性信众的结社造像活动亦从自发走向自觉。她们或三两结对造像,或与僧尼协作造像,或结成群体共同造像,这就直接催生了北朝数量众多的女性石刻造像。统观北朝佛教造像,女性造像的数量并不亚于男性,女性在造像活动中的多元化参与也成为北朝佛事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女性笃信佛教,女性作为佛教信众的重要群体,在佛教活动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分女性在佛社团体中成为组织者、领导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结语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4](P177)北朝女子走出闺阁,可以像男性一样拥有信仰的自由、社交的自由,不再受到夫权和礼教的强力束缚,女性地位空前提高。北朝女子的社会地位之高在古代历史上实属罕见,因此北朝是属于女性的“黄金时代”,它上承魏晋的个性解放之风,下启唐朝女性的“红妆时代”。
就北朝女性社会地位提高这一问题,可从出土文献造像记和部分传世文献中管窥一二。文学创作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因此,北朝民歌《木兰辞》的出现及其所反映的女子从军的现象,应当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现实土壤之上的。造像记可以将北朝历史镜像中的女性地位、佛教邑社、宗教信仰等问题反映出来,把一度被历史遮蔽、传世文献未记载的事物较为完整地勾勒出来,使得原有的、微小的、不为人关注的现象和问题得以呈现。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证中,我们的研究会更贴近历史的真实。
北朝女性造像记的重要价值,在于将女性这一群体的社会活动和宗教信仰记录下来,除了贵族女性外,广大平民女性的姓名、家庭、社会活动等多个方面的资料也通过造像记得以流传。造像记是学界研究北朝风俗、宗教信仰、佛徒结社、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正史是贵族的历史,而不是平民的历史。国家的兴衰,贵族阶级的荣枯,英雄人物的悲喜,大都在正史中得以呈现。而大部分平民百姓则因为默默无闻,难以得到史官群体和文人群体的关注。造像记则以其独特的方式,将不同等级、阶层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宗教活动完整地记录下来,使得原本不受重视的平民阶层,尤其是作为北朝民众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群体,也获得越来越多地关注,其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