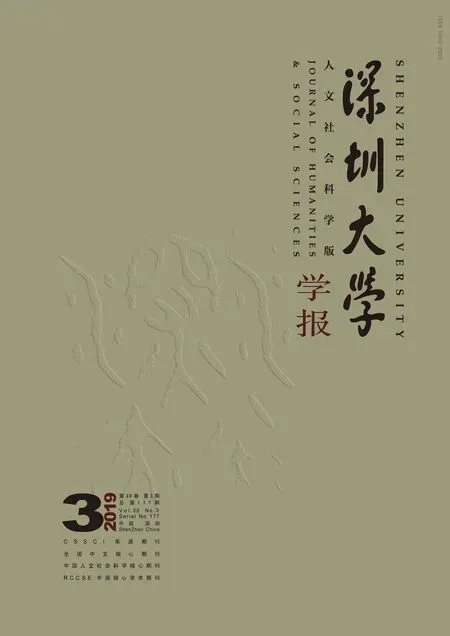以情致用:特朗普政治劝说话语中的恐惧驱动模式
毛延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一、引 言
作为一种常见的交际行为,劝说可以看作是一种通过话语表达来改变他人态度的行为[1]。从语用学的角度讲,作为指令性言语行为的一种,劝说就是通过既定的语言结构来影响或者改变对方的信念或行为方式的交际策略[2];也可以看作是试图影响对方自主判断的一种语用策略[3]。用话语学家Perloff 的话来说,劝说就是语言使用者试图借助语言表达来改变个体或群体的信念、态度或行为的一种活动[4]。就其本质而言,劝说就是悄无声息地在精神上征服别人而不留任何胁迫的痕迹[5]。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还是古希腊时期的诸多先哲,都对劝说话语的功能予以重点关注。特别是随着语言研究逐渐迎来“话语转向”,一些语言学家所说的“只是掌握语法并不能实现有效地交际,日常交际中还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约”[6]逐渐成为现实。相应地,劝说话语的语用研究开始回归其政治原型语境,一方面便于更好地控制相关变量,另一方面可以定点观测社会规约对于劝说话语影响的共时与历时对比[7](P5)。以往有关劝说话语的研究多见于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例如,有学者认为,劝说行为涉及的语用关联对于理解其言语行为本质意义重大[8],特别是其所涉及的跨文化对比视角[9]以及不同文化对于面子的理解差异尤其值得重视[10],这也是后续劝说研究必须予以关注的重点,更是系统认识劝说行为语用普遍性的重要保证[11]。不可否认,上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学界对于劝说话语的认识,但是其共性缺陷在于关注的研究对象都是单一劝说话语的句法性与建构性,而没有关注到劝说行为的语篇序列性以及文化语用性特征[12],这也可以看作是以往言语行为研究的不足。特别是在公共话语领域当中,劝说行为的实现往往是以语篇的形式实现的,这也是古希腊时期修辞学得以萌芽、发展和勃兴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重新思考公共话语中劝说话语的实现形式与驱动理据是探讨全球政治领袖领导力建构过程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一方面,结合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政治话语来分析其劝说模式,可以回溯经典政治语篇劝说模式从信度(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维度出发而诠释语用理据的多层表征[13];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扩展传统言语行为研究的可应用性外延——在提升观察充分性与描述充分性的同时,寻求经典言语行为理论范式批评与改进的潜在突破点,最后提升言语行为理论的解释充分性。有鉴于此,我们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劝说话语为例,从文化语用学视角出发来探讨公共话语空间之内劝说行为的实现形式与驱动理据。这一方面可以观察公共空间当中的文化语用因素如何为政治领袖的劝说话语建构提供理据性支撑,另一方面可以透视公共话语空间当中文化语用视角对于政治领袖个人话语特征、执政倾向以及政治理念解构的解释力。更进一步讲,这对于认识公共空间之中当代政治领袖话语的文化属性与政治本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也可以揭示政治领袖领导力的建构与提升当中从“存量”到“增量”转型的相关参数。
二、政治劝说话语中的情感元素溯源
情感在政治劝说话语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但孔子的《论语》中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亦强调政治话语的劝说力来自其对受众内心的情感影响力。例如,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控制了民众的情感,就等于控制了对方的心智,进而可以左右其判断[14]。也正是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的劝说策略涵盖了三个部分:理性论证(logos)、言者信度(ethos)和内心共情(pathos)[1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内心共情”不但可以增加既定政治目标的实现可能性,更可以提升交际双方之间的政治认同关联度。正如Reddy 所言,政治本身就是情感控制,这一过程涉及既定政治语境下哪些情感需要凸显,哪些情感需要压制[16]。同样,美国著名政治文化学者Kitchens & Powell 指出,如果想弄清楚为什么有些政治信息可以高效地传播给受众,而有些信息则中途夭折,就必须知晓四类支撑美国政治话语传播的心理状态,其中一个就是有关情感元素的“恐惧(fear)”[17](P1-2)。用他们的话来说,美国是一个生活在恐惧当中的国度。实际上,在美国只要提到“恐惧”一词,一定会想到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件演讲中所说的“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所畏惧”①。从 20世纪初对于一战的恐惧,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大萧条的忧惧;从1941年对珍珠港事件的恐惧,到二战以及朝鲜战争时期的恐惧;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核武竞赛的恐惧,到70年代以越南战争为代表的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从80年代里根时期的对星战计划的恐惧,到2011年9·11 事件带来的恐慌,从中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一直到现在美国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现实的或者想象的“恐惧”魔咒。
因此,恐惧也成了美国政治系统中最为常见的词语[17](P7),并且也是美国学术界的焦点话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在“通过不安全而实现治国理政”[18]。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现有政客对此不但认同,而且亲身实践:美国选举过程参选者所建构的负面攻击性话语就是让选民知道其他候选人有多么可怕,其结果就是美国的政治选举被恐惧所包围[19]。相应地,恐惧驱动的话语模式也成了美国政治劝说话语的重要表现形式。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话语同样也不例外,特别是其有关移民问题的公共话语可以看作是美国政治劝说话语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恐惧驱动的话语建构模式。换言之,美国人有关政治和政府的集体意识中的恐惧情感可以看作识解美国政治话语的关键。实际上,支持针对公共话语领域的情感元素展开分析的还有著名的话语学家Piotr Cap。以当代美国以及欧洲的政治话语、医疗话语等公共话语为研究对象,Cap 认为:当代公共话语中的恐惧建构与表征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催生恐惧以及社会焦虑是现代公共话语的重要特征,其目的在于论证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决策的正确性与正义性,并引导公众避免恐惧背后隐藏的威胁[7](P10)。由上分析可见,公共空间中政治语篇背后的情感因素是理解政治信息、解读政治取向以及了解政治领袖执政思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文献为我们从文化语用学视角出发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政治劝说话语的“恐惧驱动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佐证。下面我们就以特朗普有关美国如何看待移民问题的公共话语为例,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予以论证。
三、特朗普劝说话语的“恐惧驱动模式”
作为美国政治文化中最为常用的概念之一,“领导力”一词往往与“强势”和“有效”等修饰语相关,并且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统)身上得以彰显。按照美国总统话语研究的权威学者Neustadt 的观点:总统的权力就是劝说的力量[20]。因此,美国历任总统都颇为重视自身领导力的塑造,特别是公共话语操控能力的提升。这不但关系总统作为政治领袖形象的塑造,更是关乎政治政策的传达、解读与执行的有效性。作为塑造与提升领导力的重要手段,政治劝说话语可以说是美国各个阶层政治领袖的必修课,其中也包括美国总统。因此,民间和学术界都非常关注作为政治领袖的美国总统如何在政治话语中通过劝说来表征与传播“CHANGE”——美国文化最为看重的就是“与众不同(to be different and to make difference)”,这也是“个性主义”在美国文化群落里最直白的表现。因此,美国人对于总统执政期间的劝说能力往往寄予厚望。那么,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劝说话语是如何运作来实现这一语用期望的呢?我们的观点是,特朗普政治劝说话语以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为支撑,主要贯彻了恐惧情感驱动的劝说话语建构模式,这在其有关移民问题的公共话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有关具体论证模型,我们参照的是Kitchens & Powell 在《政治之四根砥柱》一书中所提到的政治话语传播的四个主要维度:恐惧、自恋、消费主义和信仰。他们认为这四根支柱可以看作美国民众态度、信仰以及价值观的坐标,这四个维度将美国文化的诸多信念和理想提纲挈领地盘织成网,并在美国人的心智世界和话语层面上予以表征[17](P3)。因此,任何的政治话语传播、评价、认同与批评都必须依赖这一文化语用网络,否则,就会出现信息传递的不对称以及文化语用期望落空,这就是美国政治领域里为什么一些候选人一败涂地且不具领导力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社会判断理论看来,人们往往以自身的内在情感支点和自我情感介入为基础来判断某个信息的可接受度[21]。因此,情感维度是既定社会成员形成自己的观点与判断的重要参照系,其在具体社会群体选择性认知与表现中的作用不可忽视[22]。就第一根支柱“恐惧”而言,他们提出了四条具体的恐惧所指对象:(1)罪犯袭击家园(Attack on my home from a criminal);(2)恐怖分子袭击社会(Attack on society by terrorists);(3)孩子可能发生不测(Something could happen to my children);(4)个体可能失业(I could lose my job)。通过具体核心语义分析不难看出美国人的恐惧感涵盖了国家(第2条)、家庭(第1 和3条)和个人(第4条)三个层面,由此形成了我们分析特朗普政治劝说话语的恐惧驱动模式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综观视角。下面我们就以特朗普2016年8月31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作的有关移民问题的部分演讲为例(后文不再赘述具体出处),分析论证其政治劝说话语中的恐惧驱动模式。
(一)“国”之恐惧:特朗普移民话语中情感劝说的宏观维度
情感往往会影响文化信念,文化信念反过来又会唤醒既定情感。换言之,既定语境当中的情感反应会带来文化信念的激活、运作以及改变[23]。例如,9·11 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将这次恐怖袭击描述为“与美国为敌的战争”,将其背后的动机看成是对于美国民主政治的情感——憎恶(hatred),将其性质定性为一种针对情感的战争——“恐惧之战(War on Terror)”,而不是“恐怖主义之战(War on Terrorism)”,也不是 “恐怖主义分子之战(War on Terrorists)”。正是基于情感和文化信念之间的关联性,美国总统布什的政治话语通过使用情感词汇“恐怖”来激活美国民众内心深处的安全与自由等文化信念。当布什总统告知“美国公民的敌人”是一种情感——“恐惧之感”时,其实就是在号召美国民众为了国家的自由与安全而团结战斗。可见,恐惧作为美国政治实体用来操控公共话语进而影响民众的重要工具,并在公共话语领域有所体现并非偶然。同样,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劝说话语在宏观国家维度上也体现了对于情感元素的文化调控。例如,在特朗普有关移民问题的演讲中,他多次提到了具有身份属性划定的话语。
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作的有关移民问题的演讲中,特朗普首先给美国涉及的移民问题予以定性:这是关系到美国人民福祉的核心问题(the well-being of the American people)。通过文化指示语“美国人民”,特朗普有效地把移民和美国人民对立起来,从而为后面的劝说做好铺垫——我们来自两个不同身份的阵营,我们美国人才是自己人,而那些移民都是外人。紧接着,特朗普以希拉里为攻击对象,提到了“恐惧(fear)”这个关键词:希拉里担忧与恐惧的是作奸犯科的外人 “移民群体”家离破散,而非担忧自己人“美国人”因为移民涌入而导致的生离死别。然后,特朗普再次重申所有的公平、公正与热情应该受益的是自己人“美国公民”,进而猛烈抨击奥巴马和希拉里所奉行的“外人优先”政策(特朗普多次细数当下政府移民政策的诸多过失)的“不合情(they support the release of dangerous criminals from detention)”、“不合理(surrendering the safe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o open borders)”与“不可信(catch-and-release on the border)”,分别对应了内心共情、理性论证、言者信度三个维度。
此外,特朗普基于诸多事实(例如:开放边境而危及美国安全、边境罪犯即抓即放、移民签证过期停留、高危罪犯不再收监而是释放,以及违宪执行特设、保障非法移民的社会安全与医疗保险、承诺不控制低技能移民数量以及未来四年接收海量难民等等),将奥巴马和希拉里对于移民的态度定性为渎职。通过上述与美国民众群体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的诸多移民议题的罗列,特朗普进而从理性的角度让民众自行推理奥巴马和希拉里的上述行为和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进而从感性的角度建构一种恐怖分子可能随时袭击美国社会(Attack on American society by terrorists at any time)的恐惧心理,最后从可信性角度达到说服听众相信自己并支持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语言背后的文化信息及其关联的文化语义情感网络是政治信息建构与传播的重要前提。
从宏观上看,特朗普的上述话语暗示:当下的美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进而向美国民众渗透一种信息:像希拉里那样和“罪犯”讲道理是不理智的,也是行不通的。如果说前面诸多事实的罗列是特朗普在建构一种“现实性恐惧”的话,那么这种背后的信息则在更深层次上激活了一种“想象性的恐惧”。实际上,特朗普非常熟悉美国民众骨子里对于美国文化归属感(American people/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citizens)和安全性(open borders/ catch-and-release/ visa overstays/unconstitutional executive amnesty/ illegal immigrants/620,000 new refugees)丧失的恐惧,并且借助自己政治劝说话语而在两个层面去激活美国民众内心的这些负面情感,最后为己所用。这充分说明了劝说话语的情感性往往存在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并且直接与其传播取效息息相关[24]。特朗普有关移民演讲的字里行间都在传递当下奥巴马和希拉里政府的移民法案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会造成严重威胁的重要信息。虽然字面上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劝说美国民众支持自己,但是上述话语处处触动着美国人对于丧失国家安全的恐惧神经,因此取得的传播效果比直接劝说更好。这一点在特朗普移民话语中情感劝说的中观维度也有体现。
(二)“家”之恐惧:特朗普移民话语中情感劝说的中观维度
美国文化对家庭观念的信奉十分坚定,在日常语言中也是随处可见。例如,“I care”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文化中家庭成员之间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恐惧和冷漠(I don’t care);美国幼儿园和小学时常安排Doughnuts with Dad(和爸爸一起吃多纳圈)、Muffins with Moms(和妈妈一起吃松饼)、Mom and Son Day(妈妈和儿子亲子日),Dad and Daughter Party(爸爸和女儿亲子日)等活动来一起建构家庭温馨记忆。这些与美国当初以清教价值观立国不无关联,因为大多数人觉得传统的婚姻家庭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这在美国历届总统大选中“婚外情”与“不顾家”等劣行往往成为竞争对手攻击的把柄就可见一斑。因此,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都主打“家人牌”,夫人、子女纷纷出马发表演说、拉选票,力图塑造自己丈夫(爸爸)是好丈夫(父亲)的角色,从而提升他们在选民心目中的信任度。反过来讲,凡是危及美国人家庭幸福、稳定与和谐的任何负面举动都会带来一种恐惧感,因此就会遭到美国民众的极力抵制。有鉴于此,特朗普的政治劝说话语有意涉及到家庭维度,特别是通过陈述移民问题对于普通美国家庭的潜在威胁(Something could happen to my children),进而在公众心里激活一种对当下移民政策的恐惧和否定,最后劝说美国民众认同并支持自己。
情感自身的社会传承性往往与家庭熏习性和关联性密切相关[25],演讲中通过一个活生生的移民杀害美国学生Sarah Root 的个案来凸显当下移民政策过于宽松而给普通美国民众带来的极大危害。通过这种恐惧驱动的共情话语策略,特朗普就能够在攻击希拉里的同时,交代这种恐惧背后的威胁得以解除的具体进路——控制移民量、美国人优先。可见,特朗普在有关移民的政治话语中通过植入生活故事,把恐惧叙事和美国民众的现实生活有效地勾连起来。为了激活恐惧叙事的相关语境,特朗普已经通过身份对立(例如,移民群体和美国本土公民)而完成铺垫,进而增强恐惧叙事的真实性——这种威胁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事真的会发生。特朗普通过演讲中渲染Sarah Root 被残酷杀害而罪犯却被释放并逍遥法外的真实恐怖实例,意在激发听众对于奥巴马移民政策纵容这种恶性事件的“愤怒”,将听众对于类似事件可能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的“恐惧”潜移默化地引导到把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希望”寄托于特朗普本人身上(we could provide one million at-risk students with a school voucher)。由此可见,情感在话语维度的表征不仅仅是说话人对于当下语境和切身利益的认知与关注,还可以看作是说话人按照既定文化意识形态设定从现实利益商讨出发而做出的相应努力[25]。鉴于权力是所有政治劝说话语中情感元素的最终所指,因此情感元素的真假、强弱以及是否被接受决定了权力认同的成败与程度[26]。特朗普通过激活美国民众的恐惧来进一步刺激他们内心的愤怒,通过情感元素的强化而为后续民众的政治认同与赋权做好铺垫;然后,强调自己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最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值得民众信任的人(例如,特朗普特意强调自己“我曾亲见过萨拉美好的一家人 I’ve met Sarah’s beautiful family”所隐含的亲力亲为,而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精髓)的同时,把 “黑锅”甩给了奥巴马和希拉里政府——他们才是罪魁祸首,这样给美国普通家庭带来伤害、愤怒和恐惧的人值得谁去相信?这种恐惧驱动的话语策略直指关乎普通美国公民家庭平安幸福的政策,因此其劝说效果不言而喻。此外,对于真实发生的Sarah Root 被杀案以及其严重后果加以合理的重复,以及重点列举威胁和恐惧的发生主体涵盖美国公民的男女老少(例如:21 year-old convenience store clerk in Mesa,Arizona;Kate Steinle gunned down in the Sanctuary City of San Francisco;90 year-old Earl Olander,who was brutally beaten and left to bleed to death in his home)、个体与群体(例如:illegal immigrants and other non-citizens in our prisons and jails together had around 25,000 homicide arrests to their names),这种恐惧感的认同就会得以强化,从而获得更深、更广的民众感同身受的共情支持。
(三)“人”之恐惧:特朗普移民话语中情感劝说的微观维度
情感元素是劝说话语中的核心要素,并且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正如Worsham 所言,劝说中的情感元素是一种个体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情感性体验,由此社会个体成员才能完成个体身份归属感的集体性建构[27]。正是抓住了情感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体验性关联,特朗普往往借助情感维度来实施自己政治话语的劝说功能,并在具体的微观话语维度有所表征:其政治劝说话语中会触及美国公民比较恐惧的 “个体可能失业(I could lose my job)、公民的社会保障与保险都会受到威胁”等等个人体验性最强的问题。
【例1】

美国文化对于公民个体经济能力的重视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美国实用主义的文化本源——实用就是有用。作为信奉实用主义文化的美国人给自己的定位一定是“有用的人”,“有工作、有事干”就是最为直接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重视来自于20世纪初期经济大萧条时期心理恐惧的集体记忆。相应地,公共话语空间中的经济失业话题就会导致美国民众个体内心的恐惧与焦虑,因为“个体事业”否定的不只是经济实力,还意味着个人主义文化信条层面的“实用主义精神(照顾家庭、服务社团、造福社会)”的脱落以及自身社会价值、家庭价值和个人价值的丧失。正是基于普通民众对于个体价值的担忧,特朗普不断提及美国当下政府所采取的移民政策会直接影响美国民众的就业率与薪金(例1a 中的黑体部分)。通过特别点出“非洲裔和墨西哥裔工人”的特殊身份及其对普通美国民众所带来的经济挑战,从而将美国民众拉到自己的阵营并获得对方的政治认同。特朗普通过倡导亲力亲为地倾听一线普通美国民众的心声(例1b 中的黑体),并且强调当下移民政策对美国民众个人生活多个维度的全方位冲击(例1b 中的黑体部分),让美国民众生动地“想象”当下奥巴马政府和希拉里所宣传的移民政策对于每个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会有多么严重并让人恐惧的影响。特朗普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基于普通美国民众认可的恐惧心理(经济安全感)来攻击竞争对手的弱点,然后建构自己获得美国民众支持的政治话语策略。由此可见,政治劝说话语中的情感控制,一方面可能是源自现实中的威胁,一方面也可能是来自想象中的虚拟性忧虑[28]。
(四)“勇”者无惧:特朗普移民话语中恐惧劝说的整合分析
既定社会团体内部的人际交往是以主体化事件为核心元素的话语交互作用的过程,是社会成员之间实现社会目的、建立互动关系、达成社会理想的最主要的途径。此间,文化元素不仅会指引互动的方向,还会驱使语言使用者去完成既定的语言选择,以确保交往得以正常进行,最终保证社会意志和理想的顺利建构[29]。特朗普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语用准则而不断尝试借助恐惧驱动的劝说话语来影响受众群体。鉴于文化指示是文化得以向话语渗透,实现其现实人际社交价值、社会价值以及自身重构、复兴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特朗普往往借助一系列的文化指示来实现恐惧认同以及政治认同[30]:一方面让受众从国家(例2a 中的“边境危机”)、家庭(例 2a 中“恐怖主义危机”)和个体(例2a 中“失业危机”)三个维度了解到当前移民政策对于美国公民在国家、家庭和个体等层面上的威胁与恐惧,另一方面将罪名(例2b 中黑体部分)加在竞选对手身上(例2a 中黑体部分)。
【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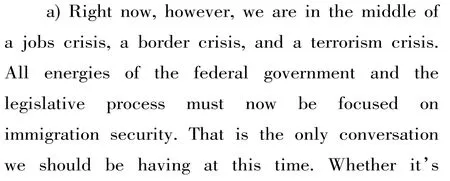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政治蓝图,完成自己政治纲领的立论奠基,并且尝试通过政治劝说话语把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从奥巴马政府移民政策的烂摊子转移到特朗普自己的政治计划之上——美国复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具体表现为后文例3 中一一回应美国民众所关心的如何消解国家、家庭和个体三个维度的恐惧,最终特朗普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勇者无惧”的问题解决者与领导者形象(例 3 中四个“Let’s…”的排比使用)。从文化语用信息传递的角度看,特朗普上述言辞不但将美国所面临的“被威胁”的虚拟恐惧语境予以前景化处理,更重要的是凸显过往美国政策的灾难性错误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通过负载恐惧情感的公共话语策略,特朗普将自己建构为一个与美国及美国人民利益一致的解决问题与扫除恐惧的“英雄形象”,这十分符合美国文化中的无畏精神;与之相反,将其竞争对手则刻画成恐惧制造者与麻烦制造者,以此建构“自我与他者”的鲜明关系,从而实现自我政治领导身份的情感认同。从传播效果上讲,特朗普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对于美国民众恐惧情感的多维调动有效地激发和唤起了普通民众的共情认同,因此其所倡导的政策主张更易于被认定为合理化、合法化,最终实现领导力的有效建构与操控。
【例3】

四、结 语
基于美国文化对于恐惧情感的特殊认识以及情感是理性的重要前提,特朗普的政治劝说话语建构路径完全与众不同:当希拉里还是采取理性思路建构自身政治话语来实现民众劝说的时候,特朗普选择的是打“恐惧驱动”牌,以“情”动人地刻画当下美国的窘境,同时又技巧地塑造了自己独特而又负责的领导人形象。这种对比鲜明的公共形象塑造完全是遵循美国文化的基本信条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十分容易触动美国民众。美国总统作为国家的政治领袖,其公共话语输出除了个人获得认同的私人目的之外,同时也肩负着传承自己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重任。有趣的是,特朗普选择从情感上建构共鸣,完成政治劝说,最后获得美国民众支持,体现出文化价值信念的政治属性与价值,可以说其话语输出和建构别具风格。以上我们针对特朗普移民话语而展开政治劝说话语的恐惧驱动模式分析,充分验证了政治权力不仅仅存在于静态的宪法文献当中,更多的时候在鲜活的政治话语中发挥具体功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政治领袖的美国总统的权力性情感输出可以看作是其政治劝说建构的重要理据,更可以看作是其政治领导力建构以及权力话语边界调控的标记。
此外,本文针对特朗普移民话语中劝说行为的文化语用分析表明:从说话人的角度讲,了解目标受众的文化价值体系与敏感认知网络是保证政治信息传递、认同、赞许与执行的重要前提,否则可能导致“鸡同鸭讲”的尴尬,甚至误国误民;从听者的角度讲,了解言者话语背后的文化信息架构机制与识解关键点是保证政治信息感知、解析、理解与应对的必经之路,否则可能出现“依文解意,谬以千里”的误解,导致战略失策,这在国际关系研究、政治领导力分析以及国际舆情检测等领域均是如此。最后,我们借用Hitler 的话来总结全文:“大多数人之所以被争取到某个阵营,靠的多是‘口之言’而不是‘笔之语’,并且任何一个了不起的政府机构都将其成长归功于杰出的演讲者而不是伟大的作家”[31]。虽然目前还不能说特朗普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至少特朗普通过运用恐惧驱动的负向政治劝说与竞选话语已经成为政治话语研究当中独具特色的一类[32]。
以上本文从文化语用视角出发所做的诸多探讨权作引玉之砖,希望引起国内相关领域学者的的重视以及进一步追问。后续研究可以考虑结合特朗普自传分析法、读者反应分析法和库助情感分析法来进一步尝试交叉检验与论证本文的初步发现。
注:
①英文的原文是:We have nothing to fear,but fear itself.1941年,在美国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观念。四大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中前两项仍然属于传统的权利法案的内容,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而后两项则为后来第二权利法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