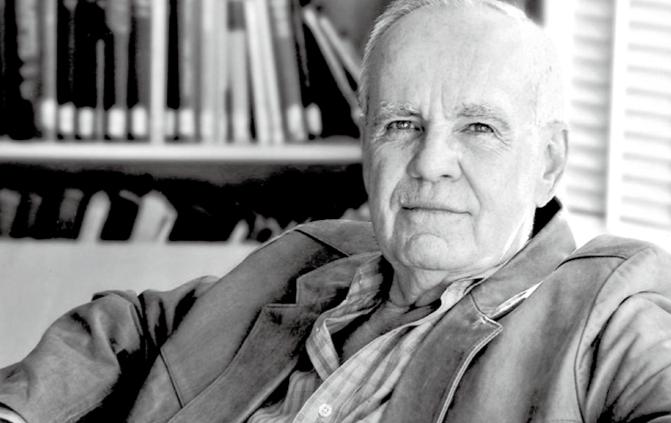麦卡锡《路》的电影叙事元素
王晓燕
《路》(2006)是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海明威与福克纳唯一的后继者”的科马克·麦卡锡(1933— )创作的一部小说。小说通过一对父子面对被灾难毁灭的家园而南迁的旅途经历,展现了灾难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以及生态破坏给予人的警示,人性的善恶是作品探讨的重要内容。而小说在叙事方面,通过运用一些独特的电影元素和电影叙事艺术,如蒙太奇、画面、色彩等,来表现小说深厚的主题思想,体现了麦卡锡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追求。

一般而言,蒙太奇在电影中主要指的是镜头的剪辑。由于镜头与镜头之间在故事、情感和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蒙太奇反映的是“镜头之间的一种辩证法”。在小说创作中,蒙太奇的运用则主要指情节之间的分割与重新组合,是小说情节展现的一种重要手段。麦卡锡是一个深谙小说情节结构设置的作家。小说《路》中的情节看似简单、平实,实则凌乱琐碎,在梦境和回忆的穿插中,往往给人以迂回曲折的阅读体验。而这些恰好与蒙太奇的艺术效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故事以一对父子的旅程为主线,叙事时间基本上是按照他们的旅行时间进行的。但麦卡锡在这简单的整体情节中,通过描写大量的梦境和回忆,将小说直线的故事主干分派出若干小的叙事片段,并将这些小叙事片段重新拼凑出来,形成一个小而完整的叙事单元。所以,当情节顺势发展时,作者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笔锋一转,便开始写一次回忆或者一个梦境,从而打乱并延宕了故事的整体叙事时间。小说开篇写“男人”与“孩子”在幽暗的森林里过夜,之后便上路了,他们走过一座旧的水泥桥,跨过河流,穿过小溪,越过山脉,之后穿越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城市。紧接着便是对这一城市的场景进行详尽的描写:“这座城几乎已全被烧毁。没有生命迹象。街上的汽车蒙满灰尘,每样东西都布满了灰尘。干结的泥泞中镶着车轮印子。一处门洞里,有具死尸干成一张皮。”这看似没头没尾的流水账似的叙述,既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感,也设置了一个悬念;作家转而叙述多年前他在叔叔农场度过的一段日子。之后再次跟随主人公的旅程开启新的叙述,并在此过程中不时地通过回忆和梦境来展示“男人”对他妻子的记忆。由于这些梦境和回忆都是零散、琐碎的,致使故事的整体叙事脉络也被割裂得支离破碎。麦卡锡的这种对小说情节不着痕迹的打乱与重组无不与电影表现中的镜头剪辑与重组相似。同时,小说中大量跳跃式的蒙太奇表现手法,将现实与虚构的镜头拼凑在一起,形成一种虚实相间的叙事效果。比如写到“男人”在某栋楼的办公室抽屉里找到一套扑克牌时,镜头一跃便开始写他脑海中出现的关于妻子“她”的记忆;当写到“男人”和“孩子”的一次对话时,镜头一转开始诉说“妻子”自杀的故事:“她走了,只留下一片冰冷作为最后的遗赠。她可能是用一种黑曜石了结的。他曾亲手教过她。尖利如钢。边缘薄如蝉翼。”小说中除了这种现实与梦境的、现实与记忆的对比外,还有远景与近景的对比,远到这片土地已被切割、侵蚀,变得荒芜空阔——“死去的生物的残骸横七竖八散布在干枯的河床上。一堆堆不可辨认的垃圾杂物。田野上村舍的油漆已经消磨殆尽,护墙也挽着上翘了。一丝影子都没有,万物失去了个性。路向下穿过一片枯死的葛草丛。一片低沼地,蔫蔫的芦苇泡在水中。大地的尽头悬挂着阴郁的烟霾,正如头顶上的天空一样。”近到脚下刚踩过的路——“道路上,流浪者沉下、跌倒、死去,荒芜、皱缩的地球颤抖着环绕太阳,日复一日,与远古那不知名的姐妹世界一样,没有履痕,没有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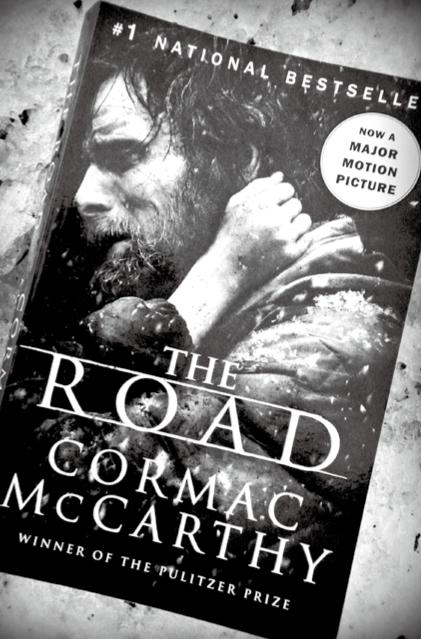
另外,前进式的蒙太奇也是《路》中常见的叙事类型之一。它主要是指把镜头移动起来,由远而近或由大到小。小说中最经典之处体现在对灾难场景的描写上,比如写到路上的一家老式药店内的陈设,先写“里面有一个黑色大理石柜台,还有艳黄色的高脚凳”,然后再突出写“柜台尽头的罩铃下吊着个人头。风干了。戴着顶球帽。干枯的眼球悲伤地凹陷下去”。作者正是通过蒙太奇的艺术技巧,将小说深厚的内涵与动感的电影表现手段相结合,既深化了主题,又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能力,拓展了小说艺术表现领域。
麦卡锡的《路》中有大量新奇独特的画面,这些画面既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推动了情节发展,又给读者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
小说中画面技巧首先体现在对画面符号元素的运用上。小说对时间的描述就是通过这种画面元素体现出来的。故事以父子二人的旅程为主线,时间开始于何年何时、结束于何年何时都是未知。但通过麦卡锡设置的一系列意象和场景画面,可以看到时间的痕迹。比如,“褪色的岩石城”“布满灰尘的房间”“超市上了年头的红花菜豆”“干得皱巴巴的杏脯”“泛黄的栅栏”……这些古旧破败的物象都打着时间的印记,带着陈旧的气息,“每种物体的硕果仅存的一个带着它这一族走向毁灭”。在这些看似无意的时间画面中,引导读者化无形为有形,感受作品中时间的荒凉与无尽,因此也更加突出了灾难主题和悲凉阴暗的审美意蕴。
同时,在小说的空间设置中,麦卡锡也擅长运用丰富的画面来强化叙事功能。小说以“路”命名,人物大部分的活动场景都在路上的自然处所,像荒野、森林、峡谷、溪流、山地、洲际公路等。每一处场景都有与其特征相反的景致配备,比如森林到處都是烧焦的枯木而非翠绿成林,峡谷里河流是灰色而非透亮的,等等,这些具有张力的画面描述,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一幅构图阴暗而又鲜明的画卷。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些对人文空间的画面描绘更是凸显了主题,比如废墟一般的游乐场“遍地是木乃伊般的死尸。肌肤和骨骼分得一清二楚,韧带缩得又干又细 ,恰如绳索。死人干枯萎缩得如同现代版的沼泽林干尸,脸皮像煮过的床单,一排牙如同泛黄的栅栏”。
其次,小说中的镜头元素运用也是其画面技巧的重要手段。镜头在电影艺术研究中主要体现为 “视角”问题,即观看者“看”的维度。通过镜头的角度、镜头的运动,观看者可以看到角色所处的现实场景或者梦境、回忆等。在《路》中,麦卡锡很注重从多个角度去选择画面,他常常使用远景、中景、近景以及特写镜头来突出灾难之后社会环境的险恶,渲染残酷恐怖的气氛。比如写到“男人”的一次梦境:
很久之前了。一个灰蒙蒙的日子里,国外某个城市,他站在窗边,望着下面的街道。他身后的木质书桌上,小灯亮着。也有书、报纸。天下起雨来,街角拐出一只猫咪,穿过人行道,端坐于咖啡厅雨篷里。桌边有个女子,双手托着下巴。数年之后,他站在焦黑的图书馆废墟中,烧黑的书本就那样泡在一摊一摊水里。
这段描述中,首先是心理的虚景:很久以前,他站在窗边,下面的街道,他身后的书桌、小灯,桌旁的女子。其次是现实的近景:数年之后,他站在废墟中,在水里的焦黑的书本。麦卡锡似乎手执摄像机,用镜头拍摄下一系列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这种远近、虚实画面的对比,来突出灾难的毁灭性。同时,在小说的叙述中,麦卡锡还常常会将某些意象从周围的背景或环境中凸显出来,用特写镜头将其放大。巴拉兹曾说过:“一部优秀影片可以通过它的特写来揭示我们的多音部生活中最隐蔽的细节……优秀的特写都是富有抒情味的, 它们作用于我们的心灵, 而不是我们的眼睛。”
再次,小说中的造型元素和色彩艺术的运用也是画面技巧的独特呈现。《路》中对造型艺术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小说宏伟的叙事背景设置上:一场未知的灾难之后,世界暗无天日;动植物绝迹,幸存者同类相食;主人公父子二人为求生踏上旅途,寻找南方。作者通过这样宏大的背景设置,深刻揭示了人类在末日面前的真实生存处境;通过这两个人物的旅途经历,塑造了一对朝圣者的形象,并深刻探讨了上帝的存在与救赎问题。
小说中,不同的色彩对于小说基调氛围、空间场景及人物形象塑造都有着重要作用。《路》的总体色调是灰暗的,集中体现在对雪景的描写上:一片“灰白的雪花撒落下来,接在手中,看着它融化,就如基督徒的最后一片圣饼”。“雪花”与“圣饼”除了夸张展现了二者之间相似性的外表,还带有一种上帝最后对世人关照的隐喻。“灰白湿润的雪花从虚空中旋转飘落而下。道路两旁是污浊的融雪。”“灰白的积雪上,有一层薄薄的血红……又下雪了,柔软的雪花从黑暗中飘落……尘埃落在雪地里,将其染成黑色。”潔白圣洁的“雪”在作者笔下却是“灰白”“污浊”“血红”的,这是对常态下“雪”的陌生化重塑。这种对色彩的颠覆性处理颇具张力,夸张性地隐喻了主人公生存环境的恶劣和残酷。而作者笔下“废墟般的娱乐场所”“幽暗的地下室”“布满灰尘的超市”“焦黑的土地”等,也如同主人公的心一样是灰色的,从而更加凸显出小说“灰暗”的基调,让读者深刻体会色彩带给人的弦外之音,像作家一样进一步反思生命,探讨人性善恶,寻求人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