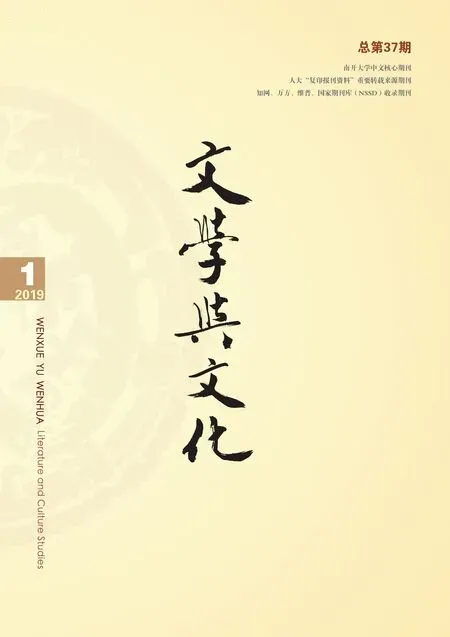近三十年《红楼梦》作者新说述评
崔 淼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红楼梦》作者的争论持续发酵:有人坚持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有人认为另有“原始作者”,曹雪芹仅做了增删工作;更有人认为《红楼梦》完全与真实的曹雪芹无关,书中的“曹雪芹”只是个化名。因此,出现了众多的作者新说。本文在全面梳理本时段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描述、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总结近三十年来《红楼梦》作者新说的研究路径、文化传统、新变及局限,反思作者研究之于《红楼梦》这部传统小说经典的价值所在,并引入基于“阐释循环”理论的理想作者研究模式。
作者研究是《红楼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与“红学”四个分支: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密切相连。因为要弄清《红楼梦》的作者,就要关注曹氏家族(根据不同的作者新说,也可能是其他家族),要考虑《红楼梦》各个抄本、刻本间的关系,要对“脂本”的价值作出判断,也要关注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关系。这也使得作者研究成为红学中较为复杂、争论不休的话题。近三十年来,出现了众多曹雪芹之外的《红楼梦》作者新说。这些新作者或是曹氏族人,或是明清之际的其他文士。但无论新说如何之“新”,总的来看,这些作者研究的范式仍然不出索隐、考证二途。其思维模式、研究路径、所使用的材料,往往与前辈学者有着呼应关系。但同时,这两大范式也在进行着内部革新,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
一 文献:考证派的困境之源

如果往前回溯,这种思考的角度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戴不凡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就已经基本成型。其在寻找外证时,一是依据对脂批的分析,如认为脂批严格区分“石兄”和“作者”:前者指底本《风月宝鉴》的作者,后者指对底本进行“批阅增删”形成《红楼梦》的曹雪芹。二是依据裕瑞《枣窗闲笔》等文献的记述,如“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而内证除了指出雪芹年龄偏小这一总纲外,又引第一回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语,并指出小说存在掺杂吴语词汇、贾府兼有南北因素、时序倒流、大小宝玉等问题。据此戴圈定了作者的范围:不应是曹寅嫡亲孙辈或堂弟曹宜之子,而只能是其胞弟曹荃诸子中的一位,最后确认为其次子“曹竹村”。由于这两篇文章在新时期第一次否定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引起广泛争论。


而有关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过程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一些新发现的文献从论证角度看也并不有力。多数研究者还是围绕脂批和第一回的“楔子”展开符合自己需要的诠释。我们暂且假设脂批和“楔子”指向的是《红楼梦》真实的创作过程(不管楔子是否使用了“烟云模糊”法),那么这些文字的含义应该是唯一的。然而现在研究者却从“经验作者”所用的词语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自由的语义联想”,并在这一过程中掺入索隐之法。如赵国栋引甲戌本脂批“凡例”中“作者自云”一段与宝玉经历相对应,以证明“作者”即宝玉原型,这固然是考证派家法。但当其分析“脂砚”包含宝玉及石兄二义时,认为“脂”暗指“红”,砚(研)乃“石开”(即“石兄”),以证成“脂研不但是怡红公子,还是书中的那位‘石兄’。所以“脂研”既是作者,又是贾宝玉之原型”之观点,则分明具有索隐色彩。鲁歌也结合谐音拆字法,推断出小说的原作者为曹寅之侄、曹荃之子曹硕。其理由一是吴世昌根据曹寅《和竹磵侄上巳韵》诗,认为磵(同“涧”)出于《卫风·考槃》“考槃在涧,硕人之宽”,推断出竹磵名“硕”;二是“硕”与“石”音、义可通;三是“硕”可拆成“石”、“页”,即“石头”,也即宝玉、作者。
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都反映了考证派作者研究面对有限文献的困境,而本就有限的文献自身尚有若干混乱龃龉之处。如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云:“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云:“此书乃康熙间江宁织造曹练亭之子雪芹所撰。”然而敦诚《寄怀曹雪芹》“扬州旧梦久已觉”句下却有“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的小注,另如清宫档案对曹寅家世的记载相互间也颇多出入。这些文献对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重要性及其相互间的矛盾,使得研究者们开始思考其中是否存在真伪问题。其中要紧处在于脂批的真伪,因为曹、贾之对应关系,很大程度上来自脂砚斋以“事皆亲历”者的身份所作的批语,如果能证明脂批为伪造,那么在考证《红楼梦》作者时,不就不再受这种对应关系(“自传说”或“叔传说”)的限制了吗?于是欧阳健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脂批乃出于刘铨福伪托的观点,后又主张目前脂本外唯一提到过脂批的文献——裕瑞的《枣窗闲笔》亦出于伪造。此后有关此书真伪的争论愈演愈烈,2014年黄一农发表《〈枣窗闲笔〉新探》一文,运用“E考据”的方法,推断《闲笔》为裕瑞手稿。主要证据是裕瑞于《闲笔》自序末所钤“淒香轩”朱文印又见于其为佘嘉惠《临罗两峰鬼趣图》册页所题诗后(图册上还另钤“淒香轩”白文印一枚),同时用《长白艺文志》中有关《闲笔》的记载、《闲笔》与裕瑞其他自录诗文集笔迹的对比、新发现的《闲笔》收藏者裕颂庭的住址等作为证据来加强结论的可信度。此说一出,立即引发争论。反对者有欧阳健、吴佩林等,赞成者有高树伟、刘广定等。《闲笔》真伪直接关系到脂批伪造说是否成立,因此欧阳健撰长文,从佘临《鬼趣图》上的裕瑞印乃后添、《闲笔》书法水平低下、文物专家鉴定不可靠、《闲笔》上没有裕颂庭收藏印迹、《闲笔》篇数及内容与《长白艺文志》中所记不符等方面证《闲笔》之伪,认为现存《闲笔》乃经与胡适有矛盾的李祖韩篡改,李捏造了《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一文置于首篇,又篡改次篇《〈后红楼梦〉书后》,目的就是“确立曹雪芹‘身胖头广’的形象”,并批驳胡适的“自叙传”说(《闲笔》所持为“叔传说”)。此文对现存《闲笔》真实性的一些质疑是有力的,但若说李祖韩仅仅因为胡适没有肯定其所藏的曹雪芹画像手卷而蒙受经济损失,就如此费尽心力的将《枣窗闲笔》改头换面,只是为了“以防他(胡适)继续散布对画像不利的言论”,此动机似难令人信服。而黄的回应文章《再论〈枣窗闲笔〉之真伪》及高的《裕瑞〈枣窗闲笔〉新考》则提出了更多文物上的证据。黄举出裕瑞钤于佘临《鬼趣图》上的若干枚印与新发现的裕瑞为《蝶仙图》《梅石犬戏》题跋所钤印,以及裕瑞一些写刻诗文集上所钤印相似,故佘临《鬼趣图》上的“淒香轩”印亦属裕瑞所钤,并认为裕瑞在这些画作上的题跋“书写风格与《枣窗闲笔》颇一致”。而高文举出最有力的证据则是其在稿本《枣窗闲笔》(缩微胶卷)的首页书眉和末页左下角发现的两枚裕颂庭印,使《闲笔》的递藏情况得以明晰。
通观这些争论,《枣窗闲笔》文献上的真伪判断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文物鉴定方面的工作,而有些研究者(特别是证伪一方)又对文物专家的鉴定表示强烈怀疑,于是争执不下。现举双方对《闲笔》字迹的鉴定为例:黄一农曾在《闲笔》(图中A行)和裕瑞自录诗文集(图中B行)中各选取相同的十五字,以两者书法上的相近证明《闲笔》出于裕瑞之手(此法并不一定科学,此处只用来做讨论案例)。吴佩林则又在《闲笔》(图中C行)和裕瑞自录集(图中D行)中找出这些字的其他写法,欲通过CB、AD、CD间的字形差异证明《闲笔》与裕瑞自录集实出二手。但其所认为的差异,有的是行书写法的不同(如“佳”C与“佳”B),有的是草书与行书或草书与楷书的不同(如“有”A与“有”D、“明”C与“明”D等),这种差异完全可以出现在同一书家笔下。这正回答了吴佩林的疑问:“若这15个字(指黄在《闲笔》中所选者——笔者注)几乎均可找到相近的字体(指黄在裕瑞自录诗文集中所选者——笔者注)是因为‘同一人的习惯性写法’,那么,这15个字在裕瑞自录诗文集中还分别有多种不同字体,又说明了什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佳”B与“佳”D的不同正是书体不同所致,“窗”B与“窗”D则是“窗”字的俗、正两种写法。这种性质的字形变换可以避免作品呆板,亦可视作书家普遍的“习惯性写法”。这个案例说明文物鉴定由于其复杂性,尚需可靠的专业人员参与。

A行是黄先生从《枣窗闲笔》选的15个较具特色的字,B行是黄先生从裕瑞自录诗文集中找到的此15字的相近字体,原图见《二重奏》第572页;C行是本文作者所选《枣窗闲笔》中此15字,D行是本文作者所选裕瑞自录诗文集中此15字。
二 “近史而悠谬”:根植于文化传统的索隐派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这一关于《红楼梦》作者写作意图和写作手法的论断,几乎代表了古今索隐派的研究总纲,直接影响到当前索隐派的作者研究。本事即历史政治事件,小说文本成了本事的“障幂”,有待读者去拨云见日。近三十年来,以索隐派思路另寻作者的研究日趋活跃,其基本倾向是:仍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曹雪芹只是“批阅增删”者,或干脆是作者的化名,真正的“原作者”另有其人。正如蔡元培所云:“故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由于此派多认为小说隐写的是明清易代之际或康、雍两朝的历史,因此也多把新作者的生活年代定于明末清初,相继提出了洪昇说、吴伟业说、李渔说、冒襄说、顾景星说等作者新说。
洪昇说由土默热于新世纪初提出。此说认为洪昇的经历与小说甲戌本凡例中“作者自云”所显示的作者创作《红楼梦》的思想基础完全相同,而根据书中指向南明历史和明珠家事的情节,以及小说中若干诗词的主题,也应将作者的写作时间设定在明末清初。此说的证据还包括,金陵十二钗的原型是杭州“蕉园诗社”的十二名女性成员,她们是洪昇的姊妹;洪昇故乡西溪的若干亭台楼阁是大观园的原型;传抄《红楼梦》,为其命名、作序的空空道人、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人皆为洪昇师友。至于曹雪芹,只是因洪昇将手稿遗落在曹寅处,被其得到,而做了“批阅增删”的工作。此说认为洪昇初期创作《红楼梦》是为了表达“悼明反清”的遗民情绪,“不过洪昇后来把《红楼梦》改写为以自己和姐妹们亲身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但原来描写改朝换代的内容未删除干净,客观造成《红楼梦》明写‘家难’、暗写‘国仇’的效果。”
吴伟业说由傅波、钟长山于2006年提出。此说认为《红楼梦》由吴伟业初创,创作动机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是一部以言情为表象,暗寓明显政治倾向的小说”。其根据是第一回文中及脂批提到的吴玉峰、孔梅溪、棠村暗含“吴梅村”三字;吴的传奇、诗词中有与《红楼梦》的书名、人物、情节相契合的内容;吴具有写作《红楼梦》的经历、文学功底和思想基础。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序、脂砚斋批语、一百二十回与八十回文本的区别及小说中的提示都显示了雪芹并非原作者,曹雪芹(并非与二敦相交的“北京曹雪芹”)只是对小说进行了增删,“揉进了康熙朝的政治事件和若干好友的经历(如纳兰明珠家和曹寅家的事,贾宝玉有纳兰性德和曹寅的影子)”。
李渔说由朱江兵于2011年提出。此说认为红楼梦的成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顺治晚期,李渔根据自己创作、编删、批评的《肉蒲团》《金瓶梅》《十二楼》《连城璧》等书重新创作而成《石头记》,此书是其生活与思想的反应。出版时由吴玉峰改题《红楼梦》,孔梅溪的批评本则题名《风月宝鉴》,由棠村作序,李渔芥子园书铺出版。第二阶段为康熙壬午(1702)前数年到康熙末期(1710),高景芳改编《风月宝鉴》形成《金陵十二钗》前八十回和其后的故事框架,“全面描述靖逆侯府的全貌和各个人物的心理”。其夫张宗仁以脂砚斋为号进行批评,名为《脂砚斋评石头记》,未出版。高景芳《红雪轩稿》及张宗仁家事与小说内容的多处关联,被此说认为是“高景芳改写脂批本《红楼梦》的重要的直接的证据。亦符合脂砚斋批语‘《红楼梦》亦有传诗之意’的提示”。第三阶段为乾隆晚期,程伟元邀请高鹗根据多种脂批本整理成为百二十回《红楼梦》,刻印出版。
冒襄说由冒廉泉于2012年提出。此说认为小说中的服饰、器物、剧目等皆出自明代,因此将作者生年提前到明末。又列举小说存在如皋独有的方言,冒襄与董小宛的爱情与宝、黛类似等七十三条证据,推断《红楼梦》作者为冒襄,曹雪芹为其笔名。此说认为《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是“冒辟疆一生的实录”,并否认曹寅有一个名为曹雪芹的孙子。与二敦相交的北京曹雪芹,只是恰好与冒襄的笔名相同而已,并没有对小说进行“批阅增删”。


索隐法的缺陷曾被众多研究者指出过,笔者亦举一例。前文提到,顾景星说认为小说中多处出现“虎头”一词,是判定作者为别号“虎头”的顾景星的有力证据。照此逻辑,小说第二回所举禀正邪掺杂之气而来之人中尚有陶潜。第三十八回林黛玉所作《咏菊》《梦菊》皆有“陶令”二字,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作诗,亦提及其人。潜一字元亮,经查,清代字或号元亮者有周亮工、王奂曾等四人。特别是周亮工,不仅字元亮,又号陶庵,慕陶之意显然。他由明降清,亲历清军镇压汉人之种种;幼年和晚年均居于南京,又曾在北京为官;不得志于南明小朝廷,被清廷重用却又两次下狱。如以索隐派隐指姓名、关涉政治的思路来看待这些因素,周亮工是否也可作为《红楼梦》作者的又一人选?

虽然索隐一法有着诸多弊病,但其在《红楼梦》作者研究中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实与中国某些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首先是“《诗》无达诂”的经学诠释传统。这种诠释方式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注重发掘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不过,在红学研究中,被索隐派“索”出的小说的言外之意更像是符号学家艾柯所定义的“本文意图”而非“经验作者意图”(即小说作者的本意),但索隐派往往认为他们才真正抓住了“经验作者意图”。
其次是“退史入子”的观念传统。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小说内涵宽泛,并不专指今天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在早期反而与史书更为贴近。李剑国先生指出:“两汉乃至于以后的大量杂史杂传,常常介于小说和史书之间,以至于使目录学家普遍感到分类的困难。”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时对史部的清理就是一例:“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因此历史上始终有人坚持小说的“实录”属性。小说第一回空空道人即云《石头记》是“实录其事”。因此,索隐派持续不断地想从“虚”的小说背后找出“实”的“本事”。
复次是美刺比兴和“隐语”传统。关于美刺比兴,蔡元培已经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也就是说,有些文学作品确实有“言外之意”,特别是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而“隐语”,蔡元培所举有曹娥碑和古民谣的例子,其实就是拆字谐音一类的方法。中国文化中流行的谶语、离合诗、藁砧诗、灯谜等也都是这种隐语传统的体现。这一传统也影响到小说的创作,《文心雕龙·谐隐》云:“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红楼梦》也确实在局部运用了这种手法来暗示情节和人物命运,比如判词和灯谜等。只不过索隐派将比兴上升为比附、局部上升为全局,把“隐”作为作者结构全书的最主要手法。
三 “自叙传”:索隐与考证的合流
除上述两派作者新说外,另有孔祥贤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曹頫说、霍国玲等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曹天祐说在研究思路上较为独特。

曹天祐说认为曹颙的遗腹子曹天祐创作了《红楼梦》,目的是为自己及所爱女子竺香玉立传,隐写雍正一朝的历史和两人合谋害死雍正的全过程。此说认为小说隐写历史的根据是:脂批视《红楼梦》为“野史”、称曹天祐为“史公”;小说曾名《风月宝鉴》,曹天祐和脂砚斋都提示读者要“反照”小说;戚蓼生序的提示;宁国府的建筑与祭祖方式与清宫相同等。此说运用“分身法”、“合身法”等方法,推断甄、贾宝玉,贾琏,秦钟等隐指曹天祐,而贾敬、贾珍、贾蓉、贾瑞、贾雨村等隐指雍正,林黛玉、晴雯、妙玉等则隐指竺香玉。贾宝玉的原型也不止一人,“作者在他身上既写了作者本人,又夹写了香玉,偶尔还承担着雍正的部分角色”。
此二说在对小说性质的判断及具体研究方法上符合索隐派特征,如认为小说影射历史政治事件,使用分身、合身法等。但又呈现出考证派的思维特征:认为小说作者是曹氏族人,且影射之事件与作者有密切关系。因此小说在具有影射性的基础上又兼具了自传性。正如陈维昭所云:“此前的《红楼梦》索隐都反对‘自传说’,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其本事的当事人,只有这样才能对顺治朝或康熙朝的政治进行索解。霍著充分利用‘自传说’,利用胡适以来红学界对于曹雪芹身世与家世的研究成果,把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作为《红楼梦》的本事。”本文第二部分所列举的索隐派作者新说也几乎都具有兼顾影射性与自传性的色彩,其中冒襄说更是影射色彩甚微。当前索隐派作者研究大量使用向来作为考证派重要文献的“脂批”,正是因为脂砚斋对于作者生活“事皆亲历”的实录口吻符合索隐派的“自传说”转向。索隐派对脂砚斋的身份也作出了新的定义:有人提出脂砚斋与正统红学中的北京曹雪芹没有关系,而是新作者的身边人,脂批指向的是新作者的事迹。如洪昇说认为脂砚斋是洪昇的妻子黄蕙,李渔说则认为是高景芳之夫张宗仁;有人则提出脂砚斋就是新作者本人,曹雪芹是其化名,墨香说、施廷龙之妻说皆持此观点。可以说,当前索隐派出现了向考证派靠拢的迹象,同时又在研究方法上对考证派有着渗透。
综上,当前的考证派和索隐派,大都将《红楼梦》作为作者的“自传”来看待。只不过考证派认为小说是作者家庭生活的记录,而索隐派则认为其中还包含作者参与历史政治斗争的内容。本来,小说的虚构性是其基本的文学特征之一。金圣叹指出小说有“因文生事”的虚构性特点,作者有“临文动心”的创作心理,未必需要事皆亲历。韦勒克也认为:“也有另一种相反的观点使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严肃对待小说,即把小说当成文献或个人档案,或由于小说的真真假假的效果或它有时的自我宣称,使我们把它当成某人的自白,当成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成某种生活及其时代的历史。”但《红楼梦》的作者研究正如韦勒克所批评的那样——过分强调了小说的“实录”色彩而忽略了作者的艺术虚构与创造,拼命地“以子证史”。他们似乎忘记了俞平伯于1925年便提出的应从“自叙传的文学”与“历史的小说”而非“自叙传”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红楼梦》的观点。
四 “阐释之循环”:超越“偏枯”的诠释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
持曹雪芹作者说的研究者认为,“旧有”的“有”,“哭成”“未成”的“成”,“撰此书”的“撰”等字皆是“写作”之义;而持“原作者”说的研究者则认为“有”是“藏有”之义,“成”乃“批阅增删”之义,“撰”的对象乃“诗词”而非小说文本。对“一篇楔子又系谁撰”数语是否能证明作者为雪芹,双方的理解也截然相反。此外,小说第二回“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侧有脂批“‘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不同的研究者也都把这个“西”字与自己推断的作者相联系。这些争论的出现不能不说与由“志”通“文”的诠释方式有很大关系。
这些诠释由于未能形成“阐释之循环”而显得“偏枯”,但作为“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研究乃至于其过程中产生的争论仍具有价值。索隐派作者研究虽然在方法上多不被学术界所认可,但研究中搜集的大量历史材料可以让人们了解更多与《红楼梦》有关的信息。而考证派中否定曹雪芹作者地位的观点虽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因其需要否定指向曹雪芹著书的相关文献(如脂本、《绿烟琐窗集》《春柳堂诗稿》《枣窗闲笔》等)的真实性,使人们加深了对文献问题的思考。如对脂本的质疑促使人们反思脂批在作者研究乃至《红楼梦》研究中所处的绝对主导地位。如果脂本确属伪造,那么脂批在文本诠释上对读者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引导”。而即使脂本真是乾隆年间的“文物”,脂砚斋、畸笏叟等就一定如批语所显示的那样,是曹雪芹生活的亲历者吗?即便如此,作为读者,他们也不过同你我一样,只是小说文本的诠释者之一。“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但即使是再高明的“笺”,对“作品意图”也只是一种推测,若据此便认定《红楼梦》作者将家事与小说内容一一对应,正如艾柯所言:“经验作者的私人生活在某个程度上说比其作品本文更难以追寻。”也就是说,摆脱机械的“自叙传”说,并不一定要以脂本的证伪为前提,进而废除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此外,即便脂本早出,程本就毫无价值了吗?方广锠曾提出敦煌遗书“废弃说”,钱钟书论版本亦云:“且本之‘胜’否,依文义而不依字体。”皆不必盲从早出版本之意。再考虑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多有在传播中逐步完善的情况,程本自有其意义。而对《风月宝鉴》“原作者”的追寻,则引发人们对《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关注。这一连串的思考,都和《红楼梦》作者的讨论有或深或浅的关系。
而对于作者研究中发现的丰富材料,若仅仅用来推断《红楼梦》的作者身份及其家世,未免有些可惜;但如果用来一味比附小说内容,更不能说真正发挥了其价值。而如能不去盲目预设文本之“志”,而是对这些材料与小说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加以发掘,找到作者身上的“文化血脉”,对文本之“文”形成更准确的理解;同时,“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便可形成“免于偏枯”“义解圆足”的“阐释之循环”。如同样是“宝玉挨打”这一情节,陈洪先生将其放在白话小说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观照,指出其与《金瓶梅》“李衙内挨打”一节高度相似。据此,则《红楼梦》的一些情节很可能出于对此前若干文学作品的借鉴,若一一坐实为作者生活的实录,未免刻舟求剑。又如,敦敏的《题芹圃画石》和雍正的《朱批谕旨》通常只是被用来进行“曹学”研究,但陈先生据此看到了作者个性与小说中“顽石”象征意义之间的关联,又进一步指出《红楼梦》中的关键词——“木石”的“碍语”性质,为曹雪芹著《红楼梦》提供了新视角。张培锋先生则通过对脂批中“悬崖撒手”一词佛学内蕴的解读,讨论了宝玉是否出家的问题。而如果按照考证派的旧思路,则势必要看看小说作者是否真做了和尚。这些观点都从机械的“自叙传”说以外的角度肯定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如果《红楼梦》的作者研究能够避免卡勒所说的“要想在此研究领域取得成功、要想出人头地,其首要条件是必须不断创新,不断标新立异”,而采取上述态度与方法,则一定会为这部经典小说的诠释注入更多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