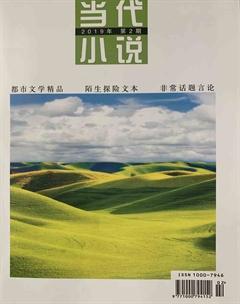二人转
周树莲
路上,肖文觉得有人跟踪她,她几次回过头去看,却都不见人。再走,还感觉有人跟在后面,她没有再回头,而是加紧了步子,匆匆地往家赶。到了家,关上房门,她长吁了一口气,终于甩掉了那个跟踪者。可是,走在屋子里,她仍然感觉有人跟在后面,她回头去找,一个人也没有,可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是那种被跟踪的感觉。她把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都找遍了,就连床底下、柜子里都没放过,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她背靠着墙壁神经绷得紧紧地冲着屋子大喊,谁?是谁在屋子里?话一出口,她激灵一下醒了,按住怦怦乱跳的胸口,许久才平静下来,却再也睡不着,直到天将放亮的时候,她才迷迷糊糊睡去。
醒来天已经完全大亮,她拉开窗帘,天空灰蒙蒙的,房屋、树木、道路以及匆匆过往的路人全部湮没在雾霾之中,倘若不是刚起床,她真有些分不清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又是一个严重雾霾的天气,这几年北京的雾霾天气越来越多,动不动就红色预警,弄得人出门都要戴上口罩遮住半张脸将自己隔离起来。她对着窗外的灰蒙蒙伸个懒腰,双手习惯性地在脸上搓了搓,这时候,门铃响了,她一愣,问,谁?门外传来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大姐是我,开门。
小齐!她脱口说道,这时她才想起今天约了小齐来打扫卫生。
她打开门,小齐穿着一件灰色大衣,肩上扛着一个工具筒,筒里包裹着她外出做活的工具,一只黑色的大口罩罩住了小齐的半张脸。
快进来。她把小齐让进屋里。
大姐,这都几点了,你还没起床?小齐摘掉口罩,露出俊俏的一张脸,站在客厅门口望着蓬头垢面的她。来北京几年了,小齐虽说的是普通话,但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重的乡音。
起晚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姐夫呢,也没起呢?小齐探头往卧室里望了望。
他今天值班,不在家。她说。
小齐放下工具筒,脱掉大衣顺手放在门口的衣架上,你们城里人真是轻闲,周末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哪像俺们大周末的也得出来干活。小齊边说边拿出工具走向阳台。
不歇会儿?她的目光追着小齐的背影问。
不歇了,累了再歇。
看着小齐瘦小的身子去了阳台,她转身进了卫生间去洗漱,小齐来她家做保洁已经是第十次了,不用她交代任何事情,小齐会把所有该收拾的都收拾干净,这点小齐很让她放心。
洗漱完,草草地给自己弄了点吃的,吃完人便去了书房。书房只有十平方米,原是女儿的房间,如今女儿去南方一所大学读书,很久不回来,她便把女儿的房间当做书房。在摆满书籍的书架上,她的目光在每一本书上掠过,最后拿出那本买了很久说看一直没看的《佩德罗·巴拉莫》,翻看起来。
小齐在阳台上擦着玻璃,边擦边哼着家乡的小调,早上不到六点,小齐便爬起来,今天是她到肖文家做保洁的日子,这在一周前就约好了的。小齐热了点剩饭扒拉了几口,便匆匆赶往汽车站。前些年,小齐撇下幼小的儿子,跟着老公来北京打工,老公在一家建筑队盖楼,她则找了份打扫卫生的差事。老公盖楼的地方今天换明天换,辗转在北京各个城区,开始小齐跟着老公跑,老公所在的建筑队到哪里,他们的家就安到哪里,后来,这样折腾实在太累,为了省钱,他们便把家安在了大兴,这样少了一个人折腾也省了不少事。只是遇到城里的活儿,小齐就得早起早出门,这样才能按时赶到客户家里,倘若不是老客户,一般城里的活儿,她是不接的,同样的价格,她不如接离家近些的活儿,这样节省了路上的时间,她还能多接一单活儿。因为跟肖文熟悉了,她觉得肖文人很好,便接了肖文的单。为了省钱,她没有坐地铁,而是选择了公共汽车,离她住得不远的地方就有一路公交车直达城里。她打出的时间是有富余的,可是路上却堵了车,公交车走走停停,像只不堪重负的老牛,半个小时了,还没出一站地,还在北京城边趴着。她在心里抱怨北京的车多,抱怨归抱怨,她没有任何办法。
窗台上一盆绿萝的枝蔓拖了地,绊了小齐的脚,大姐,你这绿萝应该吊起来,小齐躲过绿萝的枝蔓冲屋里喊。
听到小齐的喊声,她走出来。
你看这绿萝叶子都拖地了,你也不给它挂起来,耷拉在地上碍事不脚的,小齐埋怨道。
她这才注意到绿萝的枝蔓真的是太长了,她喜欢养花,但仅限于那些绿色植物,她不喜欢那些过分妖娆充满香气的花朵。她得承认这两年她养的花大不如从前了,阳台上除了那盆绿萝,其他的几盆都已近枯萎。
大姐,你是什么命?小齐望着那些将死的花问。
什么命?她一时被小齐问住了,她还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命。
金命和火命的人,都不适合养花,只有水命、木命和土命的人才适合,我猜大姐你是金命或火命。小齐按照她的逻辑想当然地给她下了定论。
你的理论还挺多。她笑笑将绿萝吊在衣杆上面,猛然想起还没给小齐沏茶,便转身回屋去沏茶。
沏茶的工夫,小齐说,大姐,你家姐夫怎么周末老不在家?
他单位忙,得值班。她说。
也不能哪个周末都值班吧?我来你家不下十次了,只有一次他在家。小齐将脏了的抹布扔在筒里,换了一块干净的抹布在满是水渍的玻璃上擦起来。
单位忙,没办法。沏完茶,她在沙发上坐下来,自顾低下头,眼睛盯着书中的文字:“不,我问你的是这个村庄,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仿佛被人遗弃了一般……”这段文字没看完,小齐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大姐,你说姐夫去值班了,你信他真的去值班了吗?
她从文字中抬起头望着小齐,目光中满是疑问。
我没别的意思,小齐说,我是说男人要是总值班,你就得留点神,说不定他拿值班当借口去干别的了。
你怎么知道?小齐的话让她一怔。
你别多想,见她不安,小齐说,我只是提醒你注意,反正男人要老值班就准有事。小齐说着换了一块玻璃擦起来,就像我一个朋友,就老值班,当然他不是单位里的人,他那也不叫什么正经的值班,就是拿值班当幌子。
你朋友是干什么的?她问。
商场库房收拾废品的。小齐说。
她点了下头,等着小齐往下说,小齐却专心致志地擦起了玻璃,一点没有了要说下去的意思。她收回目光接着看书,看了二十几页,小齐收拾完阳台,走进来挨着她坐下,随手擦了一把额头上的一层细细的汗珠。
歇会儿吧。她倒了杯茶递给小齐,重又低下头去看书中的文字。
小齐接过茶,眼睛看着她强调说,大姐,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可得重视。
她嗯了一声,眼睛并没有离开书上的文字。
大姐,我跟你说话呢,你认真听了吗?小齐用一只手捂住书上的文字,阻止她往下看。
你说吧,她被迫抬起头,摆出一副认真听的样子,实际上她对小齐的话题并不感兴趣,她的心思只在书上那个叫佩德罗的人身上。
我刚才跟你说,我那个朋友拿值班当幌子,我是想跟你说——小齐停顿了一下,算了,还是不说了。小齐低下头去喝茶。
见小齐止了话,她有些不解,平日里小齐是个爽快人,今天说起话来却有些吞吞吐吐,完全像换了一个人。小齐不说,她也不便问,只得低下头接着看书,然而书却有些看得不踏实,她用眼睛的余光瞥向小齐,看到小齐的目光在客厅里徘徊,尔后又将目光落在她的书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她几次抬起头去看小齐,小齐却又不接她的目光。她不再看小齐,安心地去看书,刚看进去,小齐却沉不住气了,吞吞吐吐地说,我那个朋友说值班的时候,其实……都是和我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短暂的愣怔之后她问,小齐的话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我那个朋友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小齐一口气说完忙低下头,眼睛看着浸在杯子里花瓣一样盛开的茶叶。
你是说你和你那个朋友好上了?她惊愕,疑惑地似又求证似的望着小齐。
我们好了有一年多了,小齐抬起头,去年,他阑尾炎住院,他老婆在老家来不了,让我帮忙照顾。
你认识他老婆?
我和他老婆是一个村子长大的,算是发小吧。刚开始我也不情愿,虽说平时我对他印象不赖,可你想我一个女人伺候一个不是自己男人的人多不方便啊,可是既然答应人家了那也得去啊,我硬着头皮去了,谁知道伺候他一个多星期,他出院后,我们的电话就勤了,他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一打就说起来没完没了,有一次,他说买了个壶给我,让我去拿。我那时烧水的壶正好坏了,想去买还没买,他就替我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我在电话里无意间跟他说过,也许是他去我家里发现的,我弄不清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好饭菜,正在等我。那天我也是真饿了,上桌就吃,我们边吃边聊天,吃完了,我拿壶想走,他却上来一把抱住我亲我,说他喜欢我。我当时真有点蒙了,怎么推也推不开,我又不敢喊,院里住着那么多人,让人知道了算怎么回事。后来推不开我就不推了,索性让他抱着,可能潜意识里我也喜欢让他抱吧,那天晚上我没回家,我老公那些天在昌平的工地上不回来,我也不用跟谁请假。那之后,我们就好上了。
听着小齐的叙述,她不由得想起了肖丽和马克。
她和肖丽是双胞胎,母亲生她们的时候死于难产,父亲一个人照顾不了两个孩子,就由奶奶做主留下她,把肖麗送给了姑姑。三年前,也就是女儿考上大学那年,肖丽离婚后没地方住,便住进了她的家里。就住在女儿的这个房间,且一住就是两年。
作为姐姐,她没有理由不让肖丽住进来,毕竟肖丽遇到了难处。她把女儿的屋子清理干净,换上了新的床单被褥,迎接肖丽的到来。
肖丽住进来,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每天下班,买菜做饭全是她,肖丽从来没有下过厨房。那时候,为这马克还对肖丽颇为看不惯,夜深人静的时候,马克拥着她,摸着她稍显粗糙的手指埋怨道:你这个妹妹,怎么这么不懂事?怕马克嫌弃肖丽,那时候她还替肖丽说好话,为她辩解。直到肖丽搬进来的那年10月25日,马克给她们姐妹俩过生日,她才从此不再为肖丽辩解。
那天是在鲜鱼口的便宜坊烤鸭店,因为她对酒精过敏,饭桌上喝酒的便是肖丽和马克,这么多年不在一起,她不知道肖丽竟有那么大的酒量,她看着肖丽和马克嘻嘻哈哈地打酒官司,一瓶45℃的牛栏山竟不知不觉地被两人喝光了。肖丽晃着空瓶子还想喝,她怕肖丽喝坏了身体忙伸手制止,不想肖丽却瞪着眼睛说,你别管,你泡在幸福堆里怎么知道我的苦楚。
她被肖丽无来由的话说愣了。
肖丽指着她,为什么当初他们不把你这个姐姐送人,而把我这个妹妹送出去,你在家里享受爷爷、奶奶、爸爸那么多人的疼爱,而我什么也没享受到。
肖丽的话让她很吃惊,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姑姑对肖丽像母亲一样地爱着,而自己却从来没有享受过母爱。
她说,姑姑不是很疼你吗?
姑姑有她自己亲生的孩子,我不是她的孩子,肖丽站起来,身体跃过桌面,将头伸到她的眼前看着她,而你,却是爷爷、奶奶、爸爸的唯一。
肖丽恨恨地盯着她,她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了,好了,今天咱就到这儿了。看她面色苍白地僵在那里,马克在一旁打着圆场。
出了酒店,马克扶着肖丽在酒店门口等她,她去开车。车开过来的时候,她看见肖丽整个人都倒在马克的怀里,口里不依不饶地叫嚷着。
应该说,自从马克给她们姐妹俩过完生日后,马克对肖丽的态度就变了,他不再挑肖丽的毛病,每次都是以同情的口吻说,肖丽不容易。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马克对她的穿着开始挑剔,跟她说,别老往老处打扮自己,学学肖丽,也给自己化化妆。
那个生日之后,每次过节,马克给她买礼物都买的是双份,她一份,肖丽一份。款式颜色都一样,即便他们结婚纪念日出去都要带上肖丽。她和马克除了关起门来在一张床上,除此之外,没了私处的时间。为此,她曾提醒马克,不要上哪里都带上肖丽,我们夫妻得有独处的时间。马克却说,肖丽一个人怪可怜的,带上她省得她寂寞。再说,肖丽也不是别人,是你妹妹,你不能连自己的亲妹妹都容不下吧。让马克这么一说,好像她是成心无理取闹。
大姐,你在听我说吗?见她走神,小齐问。
我在听,她被小齐的问话拉回来,你和他好,你发小知道吗?稍做平复,她面向小齐问。
我也不清楚,现在我发小也从老家来北京了,在一个公司打扫卫生,我每次去她家,我们就一起聊聊天,有时候,他也带着我们去看电影,他们超市旁边是工人俱乐部,那里就放电影。看电影的时候,黑灯瞎火的,他就偷偷把手伸过来攥我的手,那时候,我就害怕,怕被我发小发现。
听小齐说起看电影,她忽然又想起那次马克带着她和肖丽一起去看电影的情景。那天的电影是一部美国片《肖申克的救赎》,进影院之前,肖丽嚷嚷着要吃爆米花,马克便给她们姐妹俩买了一筒爆米花,肖丽的座位本来是挨着她的,可是进了影院肖丽却一屁股坐在了马克的左边,这样她和肖丽坐在马克的一左一右,爆米花放在马克的双膝上。当时,肖丽还开玩笑说,姐夫,你要把爆米花放正,不能因为肖文是你老婆你就偏向她。马克说,哪能呢,我要偏向你姐,不显得我们俩欺负你吗?就这样马克抱着爆米花,她和肖丽边吃边看,电影看到安迪得到一把鹤嘴锄的时候,她伸手去拿爆米花,却触到两只手,当时她也没在意,以为是恰巧马克和肖丽都去拿爆米花两只手碰到一起,现在想来,当时马克和肖丽的手是攥在一起的,因为她的手的突然介入,才使得那两只手分开,或许,那个时候,他们彼此就有了爱意,只是她被蒙在鼓里。
想到马克和肖丽让她顿生不悦,几次站起来借故去卫生间,有意打断这个话题,她不想再就这个话题说下去。然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小齐却不明就里,完全向她敞开了心扉,说起来滔滔不绝,以致她不得不重新坐下来耐着心思听小齐叙述。
有一次,我和他正在一起,我发小来电话,把我和他吓一跳,他怕被我发小发现,没接,由着电话响。后来,电话断了,一会儿工夫,我手机又响了,我一看是我发小打来的,像被烫着了似的扔了手机不敢接。他说,你得接,你要不接她就得起疑心。怕我发小怀疑,我硬着头皮接了。我发小问我干嘛呢,这么半天不接电话?我说,在人家干活呢,没听见。我发小说,晚上你来家吃饭吧,我买了你爱吃的元宵。我说,我不去了,你们吃吧。我发小说,那怎么成,元宵是我专门为你买的,一定得来啊。我发小正说着,他突然打了个喷嚏,尽管在打之前他用双手使劲捂着鼻子和嘴,喷嚏的声音还是被我发小听到了,我发小问,谁呀,你跟谁在一起?这声音怎么听着有点耳熟。没,没谁,是客户家的老爷子感冒了,我吓得捂着手机语无伦次,赶忙跟他使眼色让他离远点,他知趣地捂着嘴悄悄地躲到了门边。我发小在电话里噢了一声,说,干活时注意点,别着上感冒,便挂了电话。我发小一挂电话,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那次可把我和他吓得够呛,虽说过了这么长时间,可一想起来就后怕。
她看着小齐心有余悸的样子,不禁联想到前年夏天,她出差的那个晚上,马克和肖丽的那一幕与小齐的叙述竟然十分相似。
前年七月,她出差去外地开会,晚上没事她给马克打电话,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她又打过去,电话通了,马克在电话里有些慌乱和烦躁,声音里夹杂着粗重的喘息,她还听到听筒里面一丝轻微的女人的喘息,因为声音太轻,她听不清是谁的,但凭着女人的直觉,她怀疑那声音是肖丽的。
那次出差,她没有按原定的时间回来,而是提前一天回到家。进了家门,站在客厅里,头一次,她觉得家是那样的陌生。沙发上扔着马克的臭袜子和一件揉皱了的白上衣。肖丽的房门大开着,床上堆得乱七八糟,像几天没睡过人。她来到她和马克的卧室,床上是干净的,那条乳黄色的竹纤维毛巾被晾在阳台的衣杆上。床头柜的烟缸里卧着十来支抽剩下的烟嘴和烟灰,那两只玫红色的枕头并排躺在床头。就在她准备离开卧室的时候,她看见两只枕头之间一根半露的头发,她弯下腰,伸手捏起那根头发,头发很长黑黑的打着卷儿。她把那根头发捏在手里看了一会儿,放回原处。
自从开始怀疑他们,她内心极度恐慌,养大了女儿,葬了双方老人,二十年,按说她的婚姻应该是牢固的,应该一直走到终点才对,可是肖丽来了,四十几岁,人到中年遭遇婚姻危机,这是多么令人尴尬和痛苦的事情。那晚,马克和肖丽回到家,见她端坐在沙发上,吃了一惊。马克说,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不是明天吗?
你跟我来。她站起来把马克叫到卧室,用拇指和食指夹起枕边那根头发举到马克眼前。她想让马克给她一个解释。可是马克却说,床上怎么会有长发,是不是小丽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在这里休息了?说着就要喊肖丽过来被她制止了,她不想看着他们两个给她演双簧,有马克一个人撒谎还不够吗?她盯着马克的脸,一字一顿地说,别忘了——你的身份。
第二天,下班回家,见肖丽躺在她和马克的床上,眯着眼晒太阳。她心里立刻就有了不悦,她板着脸对肖丽说,以后你不能再躺在这张床上,毕竟这是我和你姐夫的床,你应该懂得避嫌。她一脸的严肃。
我哪有姐夫呀,我只有哥。肖丽在床上打了一个滚,拧了拧身子下了床,甩着长发走了出去,床上一片褶皱。
想到马克和肖丽对她的伤害,她的心口立刻像堵了一块大石头,让她难以喘息。小齐和那个男人的故事简直就是马克和肖丽的翻版。
小齐并没有注意她的变化,而是还在满面春风地自顾述说着,我和他在一起,除了怕接到我发小的电话以外,我们有很多幸福的时光。他不光给我买东西,还经常带我去公园,北京城里的公园我们几乎都去遍了,去公园游玩的人除了本地居民,剩下的都是天南海北的游人,誰也不认识谁,我跟他在公园里是放松的,我们无所顾忌地手挽着手,看公园里的美景,像一对恋人一样别提多幸福了。小齐把身子靠在沙发上,扬着头,望着房顶上那盏方形的羊皮灯罩,一脸的幸福陶醉。
她叹息一声,将手里的书重重地放在沙发上。
马克和肖丽也经常出去约会,只是他们不会去公园,公园里人多眼杂,他们开车出去,去更远的没有熟人的地方,他们比小齐他们更聪明,更知道保护自己,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肖丽前脚刚走,她便在马克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那时候马克正在卫生间,她听到马克的手机震了一下,便拿起来看了。短信上说,老地方等你。
等马克从卫生间出来,她拿着手机问,谁在老地方等你?
你说什么?马克一把夺过手机看了一眼,快速地删除了那条短信,朋友约我有事出去。说着穿上衣服就往外走。
你说清楚再走,她一步跨到马克跟前,忽然变得歇斯底里地喊道。
不是说了吗,是一个朋友,你这人真是不可理喻。马克推开她,房门在她眼前砰的一声关上了,差点碰到她的脸。等她换了鞋子追出来,早已不见了马克的影子。
那天她憋了一天的火,等马克回来,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和马克大吵起来。
大姐,你怎么了?不高兴了吗?听到她叹气,小齐扭过脸看着她。
没有,看到小齐投过来的探询的目光,她一怔,猛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态,为了掩盖住自己的失态,她随手端起茶壶为小齐的杯子续水,你和他好,考虑过你发小的感受吗?
这个……我也想过,小齐垂下头,脸上的红晕逐渐退却,每次去他家,看我发小为我们做饭,我就觉得对不住我发小,就想跟他断,后来我就不去我发小家了,也不接他的电话,他几次找我,我都躲起来没见。有一天,我发小给我打电话,问我这段时间怎么没去她家,我说忙没顾上。她说,再忙不是还有休息时间吗?怎么休息的时候也不来?明天晚上你来我家吃饭吧。我说不去了,累了一天哪儿都不想去。我发小不高兴了,说,明天你一定得来,明天你生日,出门在外不容易,你来,我给你做面条。我发小这么一说,我才忽然想起明天是我的生日了,怕负了我发小的一番好意,也怕我发小怀疑,我只得去了。到我發小家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我发小和面,我洗菜。他回来的时候饭正好熟。两个多月没见,他明显瘦了,人也苍老了许多,见了我,他一愣,显然他不知道我会在家里,他跟我客气地说了几句话,就没了下文。吃完饭,我发小送我出来,我问我发小,你老公怎么这么瘦,是不是病了?我发小说,你也看出来了,你要不问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他最近瘦得这么厉害,我担心他得了癌症,人不都说人得了癌症就瘦得厉害吗,让他去查,他也不去,你看看要不哪天,你跟他去查查,这医院里好多事我也弄不明白。我发小恳求地望着我,我也担心他真得了癌症,就答应了我发小。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说陪他去看病,他却说,我没病,看什么看,我得的是心病,医院治不了。我以为他在说气话,就跟他急了,我说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话,下午必须去,我在区人民医院门口等着你,之后就挂了电话。
小齐说到这里,肖文的手机响了,她起身去接电话,电话是女友打来的,约她明天晚上去长安看戏。女友是京戏迷,北京各大剧院的戏票她都能弄到手,票多了,就叫上她。她呢,没事就去看。她跟女友说话的工夫,小齐去了厨房。
后来呢?他查了没有?挂断电话,她本想接下去看书,可是双脚却不由自主地似有什么东西牵着她让她走进厨房。
查了,小齐仰着头正在费力地擦油烟机。
是癌症吗?她问道。
不是,查了一溜够,除去血有点稠,什么毛病也没有,小齐说,就是心病。
后来,你们──她看着小齐没有把要问的话说出来。
还能怎么样?小齐反问了一句,他的心病是因我而生的,只能我治,我治的办法只能是接着好下去。说实话,我现在都怕见到我发小,见到我发小我就心虚,我越来越不愿去我发小家了,我发小打电话我就找种种借口推托,跟他这样,我没脸见我发小。小齐停下来,看着她,有时候,我真盼着我发小知道,盼着她知道了,狠狠打我一顿,那样我的负罪感就少了,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小齐叹了口气,将手中的抹布翻过来叠成方块,把油污的一面叠在里面,手上肥大的黄色橡胶手套让她做这些动作时有些笨拙。
看着小齐,她的眼前又划过肖丽的脸,就在昨天晚上,她接到马克的电话,说他值班,不回家了。她没有问他到底是不是值班,实际上问了也没有意义,很多次马克跟她说值班,结果她打电话过去,他根本不在班上,所以她便不问。前几天,马克跟她说,肖丽那里的水龙头坏了,让他去给换换,说他已经答应去给她换。既然他已经答应她,那么他跟她说也只是通知她一下,没必要征得她的允许。
大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明知道这事不对,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她走神的工夫,小齐擦完油烟机,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一脸无助地望着她。
你想怎么办?她回过神,反问小齐。
小齐一愣,说,我也不知道。
她看着小齐,小齐看着她,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客厅墙上的石英钟嘀嗒的声音在两人耳边划过。小齐转过头,一声不响地去擦灶台上的油污。
她从厨房里退出来,走进客厅,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拿起书,可是她却怎么也看不下去,眼睛盯在书上,目光却游离了文字之外,满脑子都是小齐和那个男人,是马克和肖丽。她索性放下书,拿了块抹布,去擦茶几和电脑桌,这些东西每天都用,有什么可擦的呢,她只是想给自己找点活干,只要身体动着她心里就会好受些。擦到衣柜的时候,她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是个小巧的女人,细眉细眼,皮肤白皙,她不敢说自己有多漂亮,但起码不是个难看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她很瘦,如今有些发福,腰有些粗,小肚子也有些凸起,笑起来眼角生了细细的纹路,像鱼的尾巴。突然,在黑发间她看到一根粗硬的竖起的白发,她扔掉抹布,对着镜子去拔那根白发。
擦到柜子,她又想起柜子里那些自己不穿的没来得及处理的衣服,她想让小齐拿走。那些衣服,实际上也包括马克给她买的那些和肖丽一模一样的衣服,她不想穿了,那些衣服她也没穿过几回。那些衣服对她来说,有的款式她并不喜欢,有的颜色并不适合她,而每一件衣服穿在肖丽身上竟是那样的合适,让她感觉好像都是马克专门给肖丽买的,而她仅仅沾了肖丽的光。
她打开衣柜的门,开始清理衣服,她先把马克给她买的和肖丽一模一样的衣服找出来,那些衣服质地都很好,有的上面的吊牌还没剪掉,她摸着那件粉红色的吊带儿睡衣,就像摸着自己刚刚洗浴过的身体一样光滑。这件衣服她只穿过一次,是马克买来的第三天,晚上她去卫生间,发现肖丽正穿着和她同样的睡衣从卫生间出来,肖丽看见她没说话,径直在她眼前走了过去。她看着肖丽的腰像摆动的柳枝一样路过客厅飘进了自己的屋子。
她把那些衣服放进几个手提袋里,堆在沙发上。客厅里,白的地板砖反着亮光,她把目光落在一块方格的光影里。
自从她警告了马克和肖丽后,两个人对她有了明显的疏远。很少在家呆,休息的时候家里往往剩下她一個人。
去年八月的一天,肖丽突然搬走了,说是在外面找到了房子,她想很可能是马克帮她买的,或者马克给她租的。她和马克的钱都是自己掌握,马克到底挣多少钱,她也不知道。肖丽搬走后,表面上看她是清静了,实际上她更闹心,肖丽搬走后,马克值班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马克爱上肖丽是毫无疑问的,或许从马克对她有了挑剔那天起,马克就爱上了肖丽,只是碍于多年夫妻情分,不愿表露出来,她相信马克在背叛之初,内心肯定做过挣扎,也对她产生过愧疚,这一点从第一次他跟她撒谎时,他不自然的表情里就能看出来。渐渐的随着撒谎的增多,他开始变得淡定,对哪次外出都开始做到从容不迫。
肖丽爱不爱马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或许肖丽真的爱上了马克,想把他从她手里夺走,否则肖丽是不会搬出去。平心而论,马克是很招女人喜欢的那种男人,虽然四十多岁了,仍旧风度翩翩,体形一点没变。倘若他们彼此之间真的有了爱,像小齐和那个男人一样难舍难分,她该怎么办?她闭上眼睛,脑子里不断闪出这个问题。
这时,小齐放在包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吓了她一跳,小齐扔下工具,奔过来,手套都没来得及摘下便拿起手机,电话里一个瓮声瓮气的男人的声音传出来,小齐看了她一眼,拿着手机去了卫生间,她听到小齐压着声音说,你小声点,我在人家干活呢,什么?给我买了条围巾,什么颜色的?紫的,喜欢……小齐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温柔,温柔中带着撒娇的成分。或许怕她听到,小齐把普通话改成了家乡话,虽然不能完全听懂,直觉告诉她小齐是在用家乡话和那个男人说情话。
她站起身,走向阳台,打开窗户,一股冷风吹进来,让她不由得打了个寒噤,窗外阳光微弱,无数的颗粒物在空中悬浮着,使得天空模糊一片。楼下是条单行线的马路,车不多,偶尔驶过一辆,眨眼就不见了。马路对面的胡同里是个小学校,将近中午放学,校门口聚集了一堆的家长等着接孩子。
大姐,清洁剂没有了。小齐一只手将电话放在耳边,一只手举着一瓶空了的清洁剂,从卫生间探出头来。
她关了窗子,穿上外套,下楼去买清洁剂。
外面的雾霾小了许多,太阳躲在雾霾里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发着惨白的光。一阵风吹过,她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心里倏地轻松了许多,她望望天空,心中的波澜渐渐退却,迈步走进小区外面的超市,在每排货架跟前她有着极大的耐心,时不时地,她会拿起琳琅的商品左看右看,直到把上面的说明文字看到剩下一个句号为止。最后,在厨房用品的货架前,她拿了一瓶威猛先生,付过款,提着威猛先生出了超市,面色坦然地走进雾霾里。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