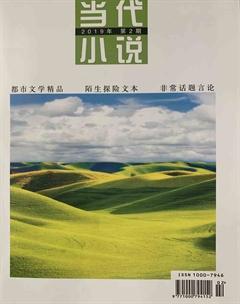岁月静好
张宝中
1
这里是丘陵地区,少数山岭突出丘陵之上。104国道从连绵的群山中穿过。李家庄在104国道边上,一大片红瓦白墙的院落。再往里二三百米就是山了,依稀能看见山上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庙宇。村头国道边高高地耸立着一个长约十六米、宽约九米的巨幅广告牌。广告牌左边一半是四幅小照片,内容是山间的绮丽风光;右边一半是一幅十分醒目的大照片,是一位老太太的半身近景肖像。老太太照片的空白处有一行金色魏碑体大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神泉宫欢迎您。”好像这句话是她说的。
照片上这位老太太看上去七十岁左右,一头雪白的卷发,戴一顶黑色羊毛呢圆顶礼帽、一副白框茶色太阳镜,穿一件大红色高领羊毛衫,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细长的烟卷,冲每个看她的人微笑。她神情安详、从容、沉静、亲切,虽然两腮的几条竖纹清晰可见,但仍不失雍容、华贵、优雅、端庄。看相貌、神情和气质,很像老年的美国好莱坞著名女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那些开车匆匆路过的人们,也许会把她当成某位一下子想不起名字的中国老一代表演艺术家。但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她名字叫王葵花,就是国道旁边这个李家庄的;还知道她的三个儿子都死了,她是天底下受苦最多的人。
李家庄现在居住很集中,五排院落七十多户人家都紧靠公路,距离公路最近的不到五米。但在五六十年前,104国道还没修建的时候,还有十几户人家零零星星地住在山上。因交通不便等原因,104国道建成后,这十几户人家陆续搬迁下来。王葵花家的房子在104国道建成前四五年才盖起来,还很结实,不舍得搬,山上就只剩下她一家。她和丈夫李凡昌经常下山到村里的代销点买煤油,点灯照明。
王葵花有三儿一女,最小的是女儿。她的三儿子四岁那年死于火灾。
那年深冬的一天,王葵花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下山,到村里的代销点打煤油;李凡昌去上海看望他生病的老姑。三个儿子都在家里,其中老三有点感冒,正躺在被窝里熟睡。屋门后头堆放着一捆晒干的玉米秆。老大老二在屋里烧红薯吃,不小心把那捆玉米秆给点燃了。火苗很快就蹿到了玉米秆的顶部。屋顶盖子是高粱秸,窗户是杨木窗棂。玉米秆顶部的火苗瞬间烧到了屋顶。直到屋顶落下土来,两个小子抬头一看,才知道失火了,急忙从屋里跑出来,吓得蹲在院子里大哭。听见老三撕心裂肺地哭,这才想起老三还在屋里。他们想把老三抱出来,但看着一股股黑色的浓烟像老绵羊一样从屋门往外冲撞,都吓得不敢进屋。
最早发现失火的,是一个在附近山里打野兔子的中年人。他扛着枪跑进院子时,屋顶已塌下去锅盖那么大一块,窗棂也已烧掉了大半扇子,红色的火苗像某种巨兽的舌头,从屋顶和窗户伸出来。中年人听见屋里有小孩的哭声,那哭声像狼叫一样,都没有人腔了。他想冲进屋把孩子救出来,可每次到屋门口,巨大的气浪就把他推一个趔趄,根本冲不进去。他对着山下“砰——砰——”连放了两枪,又声嘶力竭地大声吆喝:“失火啦,失火啦……”
山下村里有人听见了枪声和喊声,这才看见山上一股股浓烟像狼奔豕突一般,马上报告给了大队支书。大队支书跑到村中的大槐树下,急促地敲响了上工铃,并大声吆喝李凡昌家失火了,请老少爷们马上去救火。村里的拖拉机手开着拖拉机,用三只氨水桶拉了水上了山。几十个青壮年提着水桶和脸盆往山上跑。王葵花抱着女儿,也跌跌撞撞地往山上跑。
当大家赶到时,大火已烧了半个多小时,屋顶全烧没了,只剩下四面焦黑的土墙。屋内的大床、橱子、衣物以及檩条、椽子等等,所有可燃物都成了黑色的灰烬。几麻袋麦子、玉米、地瓜干也都烧焦了,发出刺鼻的焦糊味。只有两根屋梁还没烧尽,但都断成了几截。几只老鼠“吱吱”地叫着,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老大老二早已哭哑了嗓子,缩在院子角落的鸡栏前,张着嘴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火被澆灭了。大队支书带人找来棍子,在废墟中扒拉着寻找老三的遗体,只找到了一块比较完整的大腿骨。大队支书叫王葵花过去看一眼,王葵花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算了算了”。她看上去十分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和难过。她抱着女儿,和几个人一起在院子里寻找有用的东西。在院子角落找到两把铁锨和两把锄头,用白色尼龙绳编织的鸡栏里还有七只鸡。那个打兔子的中年人钻进鸡栏里,从腰间解下一个尿素袋子,把七只鸡装进去。
王葵花让两个儿子分别扛着铁锨和锄头,她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提着那只尿素袋子,对打兔子的中年人说:“大哥,你看我抱着孩子,要不就给你磕个头了。”打兔子的中年人咧了咧嘴,眼红了红,转过脸去。王葵花对大家说:“天快黑了,大家都回家吧。”她慢声慢语,那语气像是她得了感冒,不好意思麻烦这么多人来看望她。声音也不高,像是怕吓着正在怀里熟睡的女儿。
王葵花和大家一起下了山。大家不时回头往山上望一眼,王葵花一次都没回头。
2
经大队安排,王葵花一家住在一栋废弃的学屋里,算是安了家。这栋学屋在村西头,盖起来已经十五六年了,孤零零的三间屋子,没有院墙。墙基是石头砌的,再往上是土墙,屋顶是蓝瓦。里面空空荡荡的,除了墙上贴着“马恩列斯”的大幅画像,什么都没有;地上积了一层白花花的浮土。
公社拨给王葵花二百元救济款。大队给了她一些粮食,还发动村里人捐了些锅碗瓢盆和被褥、衣物等日常用品。她的两个娘家弟弟和两个姐姐也帮衬了一些。日子总算能凑合着过下去。后来又垒了院墙,盖了厨屋,这个家才慢慢有了一个家的样子。
从这年冬天开始,三十冒头的王葵花抽起了旱烟。李凡昌不抽烟。烟叶是王葵花跟娘家弟弟要的。来年立夏后,她赶集买了几十棵烟苗,种在院子里。大暑前后,烟叶成熟落黄,她摘下来摊在高粱箔上曝晒,直到焦黄,然后装在布袋里搓碎。烟叶上的青筋用菜刀切碎,再在蒜臼子里捣软。
王葵花抽烟不用烟袋锅,是卷纸烟。她从大队部拿回家一些报纸,用剪刀剪成比扑克牌略窄一些的纸片,很厚的一沓,用细绳扎着。随身带一小沓,用皮筋扎着,和火柴装在一侧的口袋里;烟叶装在一个荷包里,荷包装在另一侧的口袋里。她卷烟的时候,抽出一张纸片,用食指和中指捏一小撮烟叶放上面,卷成一个长约八公分的细长的圆锥体。粗的一头比筷子略粗,细的一头比火柴杆略细。手指来回捏捏、捋捋,使细碎的烟叶均匀分布,不留空隙。然后舌头轻轻舔一舔纸边,粘合烟卷。再然后,像包包子一样把粗的一头拧死,用尖利的指甲盖把细的一头掐下来一小截,再捏扁。这时候,一支烟卷就做成了。
她抽烟的时候,是右手架着烟卷,同时左手抱在胸前。抽完了烟,左手从胸前放下来,两手同时抄在裤子口袋里。她不抽烟的时候,如果手里没拿东西,就把两手抄在褂子或裤子口袋里,好像不抄口袋里就没地方放似的。
那个年代都穷,王葵花家里格外穷。只在过年的时候,她才买半斤猪肉包饺子。那半斤猪肉挂在院子树上冻半透,然后切成黄豆粒大小的肉丁,一个饺子里放三块。全家五口人,包八九十个饺子。三个孩子每人二十个,剩下的二三十个,两口子再分。即便这样,两人还舍不得都吃了,总是再分给孩子们几个。正上小学的大儿子冬天没有棉裤,里里外外穿了五条打补丁的破裤子。二儿子去县医院治病,在病房里闻见其他病人滴了香油、放了香菜的挂面的香味,馋得牙齿打颤,脑袋“咚咚”地撞墙,额头上鼓起一个鸡蛋大小的包。
秋收秋种之后,地里没有多少活儿了。李凡昌和两个亲戚结伴去山西挖煤,出苦力挣钱。按照多年的惯例,黄河复堤也是在这个时节。各家各户要么出一名男劳力当河工,要么出一些钱。王葵花想都不想,就报名当河工。女人当河工,大队支书不敢做主,就汇报给了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知道王葵花家的情况,就和带工的县武装部部长商量。县武装部部长二话不说,破例批准了。王葵花在工地上做饭,和本村的十几个男人住一个窝棚。她睡在窝棚的一个角落里,一领破席子固定在两根木桩上,和大家隔开。好在只有十天左右,也不算太难熬。县武装部部长说,王葵花是参与这一浩大工程的唯一一名女河工,本县没有,外县也没有。
冬闲时节,王葵花宰狗卖狗肉。她的一个娘家弟弟干这营生很多年了,来钱比较快。她戴着男式的绿色“火车头”棉帽子,穿着黑色的皮裤子,围着黄色的皮围裙,带着皮鞭和麻袋,骑着笨重的“大金鹿”自行车走村串户收狗。回家把狗宰了,炖了肉到集上卖。她本来不会骑自行车,为了收狗、卖狗肉,硬是学会了。她在村头的晒场上学骑自行车。一开始不会上,也不会下。先跐着一尺多高的矮墙骑上去,在晒场上骑几圈,下来的时候一头撞在麦秸垛上,那样摔不疼。她本来鸡都不敢杀,却硬逼着自己宰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宰狗之前先把一口黑色的布袋套在狗头上,不看狗的眼睛,那样攥刀子的手才不会哆嗦。她是村里唯一一个会骑自行车的女人,也是人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敢宰狗的女人。
“天冷饿不死瞎家雀儿。”日子那么苦,慢慢也熬过来了。
转眼间,两个儿子都到了成家的年龄。两人都高大健壮,品行端正,一表人材。但因家里穷,一个上门提亲的都没有。又过了几年,大儿子二十八岁了,二儿子二十五岁了。别的这个年龄的人,孩子都好几岁了。
要想给儿子娶媳妇,必须先盖屋子。王葵花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又从娘家借了一些,总算给大儿子盖起了屋子。托媒人给大儿子找了个媳妇,长得倒不丑,个子也不矮,但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嘴唇发乌,脸色发紫,只能在家里洗洗衣服做做饭,不能下地干重活。大儿媳还提了一个条件:婚后不领婚前的饥荒,盖屋子欠下的那些债她一分都不承担。
二儿子也是二十八岁那年才找上了媳妇。和大儿子一样,也是借钱盖屋子,也是婚后不领婚前的饥荒。二儿媳倒没什么病,看起来很精明,也能说会道。但长相很一般,身材瘦小,脸窄窄巴巴,小鼻子小眼小嘴。
两个儿媳妇各生了两个闺女。
3
老大结婚后,承包了村里的鱼塘,每隔一段时间就蹬着人力三轮车去镇上的饭店送一趟。钱慢慢赚了一些,在院子里盖了三间配房,几年后又买了拖拉机。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村子里算是中等偏上。基本上想吃什么都能买来吃,吃了也不内疚。老大隔几天就给王葵花送一条大鲢鱼。后来王葵花不要他的鱼了,让他卖钱。老大还瞒着媳妇攒了一些钱,偷偷拿给王葵花,让她偿还那些债务。王葵花拒绝了,她说:“既然早就说好了我来还债,就不会要你一分钱。你吃你的鱼和肉,我吃我的糠和菜。丁是丁卯是卯,不能马虎。”
老大对自己的日子还是很满足的。可是,他的好日子只过了十几年就到头了。
这年中秋节前,老大媳妇回了一趟娘家,在那里住了几天,迷上了法轮功。有人告诉她说,如果信法轮功,她的先天性心脏病就会好起来。从娘家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摞关于法轮功的书籍和油印材料。小学都没毕业,斗大的字识不了一麻袋,却认真地看起那些书来了,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家里墙上贴着宣传画,一天到晚用收录机播放着一种经声佛号般的音乐。还挨家挨户动员大家信法轮功,把那些人领到自己家里来。家里每天都乌乌泱泱很多人,站都站不开。两个孩子写作业只能跑到厨屋里,在板凳或锅台上写。该做饭了也不做饭。两个孩子中午回家吃饭,经常拿个馒头就回学校了。
老大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下去了。怎么劝都不听,老大语气就有些急。没想到媳妇的语气比他更急,上来就说要离婚,干一番大事。老大弱弱地说,现在日子好过了,还要一起过下去。媳妇说:不离婚也行,但你不能管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给你做饭就不做;你要是管我,我一天都不和你过。
后來老大媳妇不把那些人往家里领了,她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一出去就是一个多星期。回家住两三天又走了。村里经常有人看见她提着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站在公路边上等短途汽车。老大也不敢问她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她回来就是洗衣服、拿衣服、拿钱,凑合着做几顿饭。孩子缠着她和她说话,她就皱着眉头,很不耐烦的样子,说她们“恶心人”,真不该生她们。
有一天上午,老大媳妇从外面回家了。中午,老大和两个孩子都没回家,在王葵花那里吃饭。老大媳妇吃了一碗鸡蛋面,从抽屉里翻出存折和结婚证,用床单包着自己的衣服,背着走了。走到村头的河边,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家门钥匙扔进河里。有人看见她在村头公路边等车,过去好几辆短途汽车都没上,最后上了一辆看起来很豪华的长途汽车。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家。
老大的鱼塘承包期到了。他想继续承包,却被一位村干部的弟弟承包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老大经常一个人在家喝闷酒。他的脸色越来越蜡黄,胸腔经常隐隐作痛。到医院一检查,肝癌。医生建议他动手术,但那要花费二三十万元。他没有那么多钱;有也舍不得花,还要留着给两个女儿置办嫁妆;他的两个女儿都高中毕业了,在县城的工厂打工。他只接受保守治疗,每隔三天就从村头坐汽车去市里的医院,打一种美国进口的针剂,一针就一万多元。此外每天还要吃三十多种西药。
那段时间,老大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家。两个女儿都住在县城工厂的集体宿舍里,谁歇班谁回来陪他,给他做饭。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到了饭点,他就去父母家拿一个馒头回来,就着咸菜吃。女儿联系她妈,可是包括舅舅在内,谁也不知道她妈在哪里。
三个月后,老大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不再去医院打针了,也不吃药了。他瘦得一把骨头,脸色发灰,眼窝深陷,端一杯水都累得出虚汗,去趟厕所都得拄两根竹竿。两个女儿轮流请假回来照顾他。
老大的日子不多了。有人劝王葵花去看最后一眼。王葵花不去,她说:“他得的是治不好的病,我又不是个神,我去看他也好不了,我难受他也难受,这是何苦呢?”王葵花不光自己不去,也不让李凡昌去。老两口每天都搬着小马扎,在院门口面对老大家的方向坐着,一坐就是一天。王葵花脚边的烟头和烟灰一大堆。李凡昌几年前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和白内障,视力几近于无,吃饭的时候坐在饭桌旁,碗都看不见,只能摸索着吃。自从知道老大得了癌症,他每天都止不住地流泪,不到半个月两眼都彻底瞎了。
直到老大被火葬厂的面包车拉去火化,王葵花都没去看一眼,也没人见她掉一滴泪。
4
老二媳妇嫌家里穷,在外面跑起了传销。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住两三天又走了。老二不懂传销,问媳妇出去在哪里干什么。媳妇不说在哪里,只说能挣很多钱。这个家她基本上不管了。在外面跑传销两年多,挣了一万多块钱,存到了一个存折上。一次,她把那些钱都取出来,准备作为投资赚更多的钱。没想到被传销组织骗到了广西桂林,和上百个南腔北调的陌生男女关在一个废弃的工厂车间里,那一万多块钱也被没收了。一个星期后,传销组织给每人发了回家的路费。
老二媳妇不跑传销了,又跑保险。在哪里跑保险,她不说,老二也不问。回家的次数更少了,一两个月一次,住两三天就走。据她说挣了一些钱。但到底挣了多少,老二不知道,因为她把存折藏起来了。倒是经常给老二和两个女儿买衣服。她虽然不算漂亮,却很会打扮,看上去像个城里人。一件看上去几十块钱的衣服就上千元。她身上还总有一股很好闻的香水味,闻了头皮一麻一麻的,像裂了很多纹一样。
老二媳妇的脾气越来越怪,越来越大。如果她在家,老二从地里干完活回来必须换衣服和鞋,还必须在进屋门之前换。如果老二坐在床沿上换了衣服,她会把老二坐过的床单扯下来,填进锅灶里烧掉。必须洗澡、刷牙才能上床;鼻毛不能长出鼻孔;指甲盖里不能有泥,如此等等。老二赶集卖花生算错了账,少卖了一块多钱,她就喋喋不休地骂了一个下午,说他是没用的窝囊废。老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咂巴咂巴嘴,咽几口唾沫,一声不吭。
老二的大女儿高中毕业后在市里打工。媳妇这些年跑保险挣了一些钱,在市里贷款买了一栋八十多平米的商品房,和大女儿一起住。母女俩两三个月回来一次。二女儿高职毕业,她长得像老二,很漂亮,很白净,个头也高——大概有一米七三,在北京当“车模”,每年只过年的时候回来一次。平时老二一个人在家。他慢慢学会了做饭,会蒸馒头、煮面条、炒白菜、炖土豆等等。
老二一个人种十口人的地。每天早晨,他用一只破旧的黑色人造革提包带八九个馒头和一块腌萝卜咸菜,用一只盛花生油的塑料桶带一桶白开水,去地里干活。一干就干到天黑,有时候晚上还打着手电筒干。实在累极了,就躺在地头的草丛里歇一会儿。王葵花有时候蒸了包子,去地里给他送一些。他一天一天不说一句话,沉默得像哑巴。隔两三天就去父母院子里站一站,不进屋,就在门口站着,抽着烟。王葵花问:“吃了吗?”他说:“吃了。”如果灯泡该换了,或缸里没水了,王葵花会告诉他,他就把灯泡换了,把水缸压满水。如果王葵花什么都不说,他瞅瞅鸡栏,看看羊圈,抬头望望屋顶,站一会儿就走了。
這年夏天特别热。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达41摄氏度。下午两三点钟,有人把鸡蛋磕在太阳曝晒的石板上,眼看着蛋清成了饼子。屋顶和路面上方的热空气像火苗一样跳跃,都能看见形状了。几天时间里,镇卫生院接收了七八个热死的人。昏迷后送过去,实施抢救已经晚了。医学上的说法,是死于中暑或热性痉挛、热晕厥。
下午四点以前,没有人在庄稼地里干活。尤其是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空气就像固体一样,往鼻子里吸不动,憋得喘不上气来。在里面待几秒钟,浑身的衣服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指甲盖大小的干爽的地方都找不到。整个村子几百口人,在玉米地里干活的只有老二一个人。玉米长得很旺,玉米地里的各种杂草长得也很旺,撒了除草剂也不管用。因玉米太茂密,锄头也抡不开,只能蹲着用铲子除草。头天傍黑,老二在父母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王葵花劝他说:“天这么热,上午下地干活早点回家,下午就别去了,别跟个傻瓜似的。”他没吱声,站一会儿就走了。这天他打算干一大天,一直干到天黑。
可是他没干到天黑,下午四点多被人发现死在了玉米地头。他趴在那里,浑身只穿了一件湿透的三角内裤,眼睛瞪着,嘴张得很大,两手深深地抠进泥土里,白色和棕色的玉米须粘满了后背。
王葵花没过去看一眼。她出了一些钱,请村干部张罗老二的后事。天太热,遗体不能停,当天下午就火化了。老二媳妇和两个女儿都还不知道。没人知道她们的电话号码,没法通知她们。
老二死后,一连半个多月,李凡昌每天躺在床上,用床单蒙着头,不住地“哎哟——哎哟——”地长吁短叹。那声音很像某种剧烈的肉体疼痛引起的压抑不住的呻吟。大热天,他的身体凉得像冰块。王葵花每天晚上都抽着烟,去村头的公路上来回转悠。天热,村里很多人都在胡同口乘凉,半夜了还没睡。他们隐约看见有个人下了公路,右手架着烟卷,左手抱在胸前,知道是王葵花。王葵花走近了,大家都不吱声。她主动和大家打招呼,爽朗地笑着说:“还是大路上凉快。”大家都附和说,还是大路上凉快。她在村子里转悠了一会儿,大家以为她要回家了,她却又向村头走去。凌晨四五点钟,村里有在二十多里地以外的制药厂下夜班的人,看见她还抽着烟在公路上转悠。村里人希望她能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但没人见她掉过一滴泪。
5
王葵花的女儿叫素云,长得比较漂亮,个头也不矮。但她患有先天性哮喘病,咳嗽得很厉害,脖子都快咳没了,脑袋像长在了肩膀上。直到二十六岁,都没人上门提亲。王葵花托媒人给她找了个三十五岁的光棍。长得不算丑,人也不笨不傻,脾气也好,只是家里很穷,彩礼都拿不起。
据说某些娘胎里带的病,生了孩子就好了。素云生了个儿子,果然再也不咳嗽了,先天性哮喘病好了。她的儿子很乖巧可爱。家里虽然穷了些,但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她觉得日子还是有盼头的。
女婿有个不良嗜好,爱喝酒。喝了酒也不打人不骂人,爱嬉皮笑脸地缠着素云嘟嘟囔囔说个没完,一句话能说三十遍,半夜都不让她睡觉。儿子上小学一年级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女婿又喝了酒。都凌晨一点多了,还缠着素云说说说。素云掰了一天玉米棒子,很累很困,眼睛都睁不开,就抱了一个枕头和一件床单,跑到西厢房去了。西厢房里有一块宽约半米、长约两米的石板,架在两摞砖上。素云打算在石板上躺一会儿,等女婿睡着了再去床上睡。可是,她躺在石板上睡着了,一直睡到了天亮。她想起来做饭,这才发现身体不能动弹了,腰有些酸,下半身就像通了电一样发麻。她心想坏了,她曾听人说过,凉石板寒气太重,上面不能睡人,不然身体就“塌”了,重的会死,轻的会瘫痪。
女婿开着拖拉机把她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她的病情很严重,需要针灸治疗,一天一次。治疗效果好的话,一年半年就能治好;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十年八年也不一定能治好。治疗费用一年需要两万多元。而他们家一年的收入还不到五千元。王葵花每年有六七千元收入,但她还要还债,不能帮女婿。两口子一商量,就放弃了治疗。素云嫁出去不到十年,哮喘病好了又瘫痪了。
素云脑子是清醒的,但下半身没知觉,大小便都在床上,吃饭要喂。女婿要挣钱养孩子,不能伺候她,就把她送回了娘家。头四五年里,女婿还经常带着儿子来看看,后来就不再来了。王葵花知道,女儿这辈子砸在自己手上了。
6
自从老二死后,王葵花就把十口人的那十几亩地包给一个邻居,每年得些粮食和蔬菜。她每年那六七千元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卖鸡蛋和羊奶。她养了十几只鸡,每隔十天半月赶集卖一次鸡蛋。那些鸡蛋她一年只吃两个,过生日吃一个,端午节吃一个。养了三只大奶羊。每天早晨五点左右,镇上奶粉厂的车来收羊奶。那六七千元三个人花,年底还能攒下两千元,用于偿还债务。二十多年前的钱“结实”,王葵花参照后来的物价和消费水平,执意十倍偿还。
后来,王葵花的四个孙女收入都渐渐高了,每年都给她一些钱。前三个孙女每人一两千元;最小的,也就是在北京当“车模”的那个,收入最高,每年都偷偷地给她一万多元。王葵花后半辈子一直在还债,直到七十七岁那年,所有的陈年旧债终于都还清了。为了犒劳自己,她花一千多元在镇上一家口腔诊所做了一口假牙。这也是她这辈子花在自己身上最大的一笔钱。
可是,这时王葵花仍不能松一口气,她头上还有一座山压着。她想给素云治病。她打听了很多人,得知县城一位从大医院退休后开私人诊所的老大夫能治瘫痪,就请那位老大夫给素云做针灸。至于能不能治好,老大夫说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老大夫三天来一次,一次收费二百元。县城太远了,四十多里路。老大夫还不会开车,需要儿子开车拉他来。来一次最少需要三个小时。如果计算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二百元真是亏大了。如果不是可怜王葵花,一次五百元他都不来。每年光是给素云做针灸,就需要两万四千元。四个孙女给的钱一分不花都不够,她还得继续养鸡养奶羊,继续省吃俭用。
几乎没人见过王葵花买什么东西。但她爱赶集。别人赶集是要买东西或卖东西,她如果不卖鸡蛋,赶集只是为了看新鲜。有的女人赶集,遇到卖苹果的尝一个,遇到卖西红柿的尝一个,光尝不买,中午回家的时候吃得饱饱的,午饭都省了。王葵花从不尝人家的东西,人家请她尝她都不尝。她打定主意什么都不买,所以什么都不尝,连一粒瓜子都没尝过。集上有卖香瓜的,她拿起一只放在鼻子下面,使劲吸气,一副很陶醉的样子。卖香瓜的拿起切好的一小块香瓜请她品尝,她“咕咚”咽了一大口唾沫,使劲摇了摇头说:“我不买,也不尝,就是想闻闻味儿。”说着就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香瓜是从外地运来的。王葵花年轻的时候,因物流业不发达,从没见过香瓜;现在集上有卖的了,她却舍不得买一个。她只知道香瓜闻着香,却不知道吃起来有多甜。集上那些吃食,油条、豆腐脑、胡辣汤、白吉馍、灌汤包、麻花、肉馅饼、羊肉汤、烧饼、兰州拉面、煎饼馃子等等,她一辈子都没尝过一口。
7
三十多年来,王葵花一直接受亲戚和邻居们捐赠的旧衣物。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农村越来越富了,没人手工做衣服了,大人小孩都买着穿,淘汰的旧衣服也越来越多。那些亲戚和邻居有了旧衣服,就给王葵花送过去。王葵花有一台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的“工农牌”缝纫机,是她的弟媳送给她的。不合身的衣服,她就用缝纫机改一改。
王葵花穿过的衣服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穿过年轻女孩花花绿绿的裙子,穿过男式西装、风衣、牛仔裤、运动鞋,还穿过陆军迷彩服。她穿衣服只需遮体和御寒,完全不讲究好不好看,就没有她不敢穿的衣服。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穿着男士风衣、西装上衣和牛仔裤,走在乡村大街和集市上,右手架着烟卷,左手抱在胸前;不抽烟的时候两手抄在裤子口袋里。用时髦的话说,简直酷毙了。
王葵花那个最小的孙女穿剩的衣服,也都一股脑地打包邮寄给她;有时包裹里还有文胸、礼帽、太阳镜等年轻女孩用的东西。“车模”的衣服很时髦,有的还是“韩版”、“限量版”,村里的年轻女人都不敢穿。王葵花只要穿着合身、舒适,就穿着出门。后来她竟然渐渐喜欢上了那些时髦衣服,倒是农村老太太常穿的那些衣服怎么看都不顺眼了。“车模”的时髦超过了北京大部分女孩。王葵花穿著“车模”的衣服,如果到了巴黎、伦敦、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大概也是个十分时髦的老太太。
村西山上有一座不知建于什么年代的“老庙”,庙里有大大小小七尊石头塑像。附近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破破烂烂的古建筑。老庙旁边不远有一座深约九米、宽约七米、高约三米的大山洞,常年泉水淙淙,大旱之年也从不间断,数九寒冬也不结冰,被称为“神泉宫”。几年前,县旅游局和一些民间机构投入巨资,把这里开发成了“神泉宫景区”。那个大山洞前面立了一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山下建了几家“农家乐”饭店。春暖花开和秋高气爽的时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游人前来观光。小轿车、越野车在山下的路边排成了长队。
春天,王葵花从山上挖一些野菜,荠菜、马齿苋、婆婆丁、苦菜等,挎着破旧的柳条篮子去景区里卖。她坐在石碑旁边一个树墩子上。这个地方人总是很多,因为来景区的人都会以石碑为背景照张相,下山的时候也路过这里。王葵花的那些野菜很快就能卖完,能卖三四十块钱。春天风大,她就戴上小孙女的礼帽;阳光太刺眼,她就戴上小孙女的太阳镜。她抽着自己卷的烟,打量着来来往往的人。那些游客以石碑为背景照完相后,离开时都像欣赏一幅名画那样打量她一番,有的还窃窃私语。
这天上午来了一个看上去六七十岁的老头儿,秃顶,矮胖,戴眼镜,穿了一件满是口袋的灰色马甲,脖子里挂着一架像炮筒子一样笨重的专业单反相机。他对着石碑“喀嚓喀嚓”拍了幾张照片后,蹲在王葵花身边,和她聊了起来。老头儿问王葵花多大岁数了,王葵花说八十二了。老头儿惊讶地“啊”了一声,连声说:“不像不像,看着六十五都不到,比我还小好几岁。”老头儿问王葵花身体还好吧,王葵花说:“从三十多岁开始,五十年了一次感冒发烧都没得过,从没吃过一粒药,兴许是老天爷不叫我生病吧。”老头儿问王葵花有什么养生秘诀,王葵花哈哈大笑,说:“哪有什么养生秘诀,下来玉米吃玉米,下来红薯吃红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是狗肉和鲢鱼。”
闲扯了几句,老头儿沉吟着问,能不能给王葵花照几张相。王葵花说,随便照。老头儿问,能不能站起来走两步。王葵花就站起来,在石碑前走来走去。她右手架着烟卷,左手抱在胸前。烟抽完了,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蹍碎,同时两手抄进牛仔裤口袋里,继续走来走去。她身材高挑挺拔,细腰,大屁股紧绷绷的,分明是三十多岁的女人的身材。老头儿端起相机,撅着屁股,对着她一阵“喀嚓”,一头一脸的汗。
王葵花坐回树墩子上。老头儿还不走,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王葵花,说:“老大姐尝尝这个。”那种烟细长得像圆珠笔芯,过滤嘴也是白的。王葵花笑笑说:“我抽五十年烟了,只抽自己卷的旱烟,别的烟一口都不抽。”老头儿有些着急,用乞求的语气说:“老大姐就抽两口嘛,做做样子就行。”说着,另一只手“啪”地摁着了打火机。王葵花迟疑了一下,笑了笑,接过烟抽起来。这种烟有一种淡淡的薄荷味,绵绵软软的很没劲,但抽起来嘴里凉嗖嗖的,倒是很清爽。她仔细品着这种烟的味道,对老头儿微笑着。老头儿单膝跪地,端起相机又是一阵“喀嚓”,又是一头一脸的汗。
最后,老头儿说那些野菜他都买了,问王葵花多少钱。王葵花说,三十块钱吧。老头儿掏出三百块钱塞到王葵花右手里,抓着她的左手使劲握了握,提着篮子转身就走。王葵花愣了:三十块钱,难道老头儿听成三百了?她卖的是野菜,可是老头儿把她的篮子也给提走了,哪有这样买东西的?篮子扔大街上都没人捡,但下次还要用呢。她站起来,想叫住老头儿。可老头儿已沿着石阶下山了,“哧溜哧溜”走得很快,好像那一篮子野菜是他偷的。脑袋锃亮锃亮的像个灯泡,在上山的人群中一晃一晃的,越来越小。
那个老头儿是市里的退休干部,是个摄影爱好者。他给王葵花拍的那些照片,其中一幅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摄影大赛,荣获一等奖,在摄影界反响很大。后来,“神泉宫景区”管理处把那幅著名的摄影作品做成了大幅广告牌,悬挂在村头的国道边,以招徕游客。
那幅获奖摄影作品,标题叫“岁月静好”。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