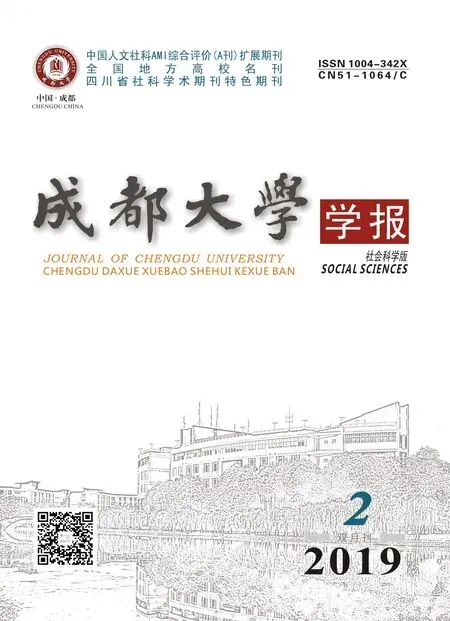中国流动老人研究现状及展望*
廖爱娣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逐渐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促成史无前例的流动人口浪潮。我国流动人口已从2000年的1.2亿增加到2016年的2.45亿,约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流动人口,虽自2015年流动人口总量开始下降,但仍保持较大比重。2005年,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 408万人,约占总人口(130 756万人)的11%,其中流动老人有276.6万人,约占老年人口的1.92%。2015年,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2 200万人,占总人口(137 462万人)的16.1%,其中流动老人为1 778.4万人,占老年人口的8.01%,占总流动人口的7.2%[1]。十年间,老年人口由总人口的10.85%上升到16.1%,流动老人由老年人口的1.92%上升到8.01%,流动老人数量由276.6万人增长到1 778.4万人,十年间增长了1 501.77万人。由此可见流动老人是一个庞大的不可忽视的群体。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家庭养老观念的偏重,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以及城市化的普遍趋势,可以预测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由于种种原因加入到流动人口的行列中。流动老人兼具老年和流动两种特征,相对于一般流动人口,流动老人处于生命历程的后期,在城市生活、融合等方面存在更多问题。相比一般老年人,流动老人的生命历程具有断裂性、不连续性,这种双重特征使得了解流动老人的流动行为、社会排斥和融合等显得非常迫切[2]。但是,不管在政策视野还是学术研究上,流动老人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可以说,中国流动老人问题尚属新课题,也将对我国公共服务政策、社会福利制度设计提出新的挑战。
一、中国流动老人研究的文献概况
流动老人,亦称老漂族、“候鸟型”老人、外来老年人口、流动老年人口、随迁老人、流动老人,常用名词为“老漂族”“随迁老人”“流动老人”,虽然定义有所不一,但都是研究处于流动或者迁移状态中的老年群体。其中“老漂族”一词最早出现,特指人到老年,还要离开故土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生活的那些老年人[3],经常出现在报纸与杂志上,多为浅显描述。学术界对“随迁老人”与“流动老人”的定义虽有不同,但都是将流动老人定义为没有办理户口迁移而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外地生活的老年人,不同的是对流动老年人年龄的划分,有的将流动老人简单定义为60岁以上,有的根据退休年龄将流动老人分为60岁以上男性人口和55岁以上女性人口(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2004;王世斌[4],2013)。芦恒,郑超月[5](2016)根据“是否获得居住地城市户籍”以及“是否照看孙辈”两个维度,进一步将“老漂族”划分为“双漂型老漂”“民工型老漂”“保姆型老漂”“受养型老漂”。有关流动人口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迄今为止关注的对象主要有劳动年龄人口、流动儿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流动妇女等,而由于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比例较低且已经完成了生命过程中的生育、就业以及受教育阶段,容易被当作没有特殊问题的一类人而受忽略(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2004)。因此,对流动老人的研究甚少[6]。
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文献数量来看,以“流动老人”为主题的文献总共17篇,以“随迁老人”为主题的文献55篇,以“老漂族”为主题的文献81篇,总共153篇文献,其中期刊占比61.4%,报纸占比19.6%,硕士论文占比18.4%、中国会议占比0.6%,拥有基金支持的占比仅18%(2017年11月13日21点10分),而从文献出处来看,在《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经济》等国内代表性期刊上发表的数量并不多。文章通过对我国流动老人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分析,以期较为全面地呈现我国流动老人的全貌,并提出相关展望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中国流动老人研究现状
(一)流动老人流动原因、特征及影响研究
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是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仍有23%的流动老人因务工经商而流动[7]。根据“推—拉”理论,迁出地的环境、家庭成员的缺乏、健康原因、退休等被视作是推力因素,而家庭支持、低生活成本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等被视为迁入地强有力的拉力因素[8](刘佩瑶,2015)。家庭因素是促使流动老人流动的主要动因,包括迁入地子女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可观的经济基础、与父母的关系密切、家庭中有婴幼儿需要照顾等等;但城乡户籍流动老人流动的原因却有比较大的差异,城市户籍的老人受家庭因素驱动更大,主要表现为想为子女照料孩子,而农村户籍老年人的迁移原因更加多元化,比如说丧偶、需要子女经济扶持、身体照料等(张伊娜,周双海[9],2013)。
在流动特征方面,流动老年的人口学特征表现为以迁入到家庭户为主;以女性老年人的迁入或流入为主(女性老人更加擅长抚育小孩和做家务,而男性老人要留在家乡经营土地);以非户籍流动为主;以户主的父母或岳父母等“被抚养类关系”为主;迁移决策的主体主要为子女,有65%的老人是子女邀请而来;受教育程度以未上过学为主,上过初、高中的老人寥寥无几,但是也有研究(基于北京)表示流动老人多为年轻老年人口,自身文化素质较高,并且以前从事的职业多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多数人都有相当可观的退休收入(周皓[10],2002;苗瑞凤,2012[11];孟向京,姜向群,宋健,2004)。另外,流动老人与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呈现同构特征,将经济发达地带、大城市作为主要迁入地,原因在于流动老人迁移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务工经商,另一方面是为了投靠子女;从迁移观念来看,目前我国流动老人自主享乐型迁移非常少(张伊娜,周双海;2013)。与国外相比,因独特的户籍制度、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流动老人在流动行为上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除为了家庭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外,更主要是帮子女照看孩子,料理家务,与西方老年人口迁移流动模式并不一样(宋健[12],2005;孟向京,姜向群,宋健,2004)。
针对流动老人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对迁入地而言,老年人的迁入会刺激迁入地相关服务人员的需求,带动各种老年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如医疗、交通、服务行业。另外,有养老金的老人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会增加该地区的消费和市场发展的潜力。一份关于“养老型”住宅购买意愿的调查显示,在上海月入8000元以上的人群中,过半数愿意购买“养老型”住宅。但是,流动老人流入地过于集中,不仅是造成当地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也会对流入地的社会医疗服务设施等构成巨大的压力,而对流出地则会起到释放压力的作用(刘燕飞[13],2009;张伊娜[14],孙许昊,2012)。
(二)流动老人健康、幸福感以及居留意愿研究
1.健康状况
对流动老人健康状况的研究并不多,且主要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使用的主要数据为“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流动老人医疗卫生服务专题调查”。通过对不同特征流动老人自评健康进行比较,发现男性自评健康状况好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参加体育锻炼的老人自评健康较好,得到的社会支持较强、朋友较多的流动老人健康自评状况则相对较好,有医疗保险的流动老人自评健康相对好于没有医疗保险的流动老人,有配偶支持的流动老人自评健康相对较好,在流入地没有朋友的流动老人健康自评状况普遍较差,年龄层次越高自评健康状况越差(聂欢,潘引君,2015;陈宁,石人炳[15],2017)。关于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老人更看重社会环境以及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配偶影响最大,其次是朋友,最后才是子女[16]。另外,流动老人自评健康状况比一般老年人更乐观,因为外出(流动)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要求。
此外,流动老人离开熟人社会,配偶分离,交际圈变小,主要的情感依托为子女或孙子女,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精神健康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与一定的社会因素相关联。从人口学特征来看,性别、年龄、婚姻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其精神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影响其精神健康的因素是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而非绝对社会经济地位,迁移行为(语言不熟)产生的压力对流动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可以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性质不同的影响[17]。流动老人相比一般的老年人口,在新的环境更加需要寻找精神支撑,而有关流动老人的精神需求、慰藉途径等研究是严重不足的。
2.幸福感研究

3.居留意愿研究
流动老人居留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有两种结论,一是流动老人的总体城市定居意愿并不强烈,超过一半的流动老人不愿意在城市定居(陈盛淦,吴宏洛,2016),二是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比劳动年龄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侯建明,李晓刚,2017)。整体上,学界认为流动老人是否居留是基于实现整个家庭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定居意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城市子女的要求、流动老人的配偶有定居意愿、流动老人的其他子女没有要求流动老人与其共同生活、流动老人与城市家庭的关系和谐越好、女性“高龄者”生活自理能力差,语言沟通较强,需要对孙辈照料[21],则城市定居意愿的可能性较高。流动老人是否居留与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时长、流动原因均显著相关,而流动老人预期在农村的收入越高,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可能性则越低(侯建明,李晓刚[22],2017;陈盛淦[23-24],吴宏洛,2016)。此外,有学者从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建立自己的框架,从经济资本(成年子女的经济状况、家乡资产状况)、文化资本(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流入地居住时间、现居社会参与、好朋友数量等)三个角度出发研究资本对老年人居留意愿的影响(李芳,龚维斌[25],2016)。
(三)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社会参与相关研究
为探索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融入(合)、适应等状况,现存文献主要从社区融入、城市融入、社会融入、社会融合、城市适应、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支持几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将城市融入界定为内心感受、闲暇时间安排、邻里关系、社区情感认同四个维度(文仁兴,赫艳杰,2016)[26];其次,社会融入界定为经济适应、文化接纳、社会交往、心理融入[27]或经济层面、文化层面、行为整合、心理层面[28]四个维度(程首一,2015;瞿红霞,2012)或经济层面(经济来源、消费水平)、居住状况、社会福利保障、文化融入(语言交流、日常生活状况、价值观念)、社会融入(闲暇时间、社区参与状况、心理融合)五个维度[29];再者,将社区融入界定为社区交往(主要事务安排、生活适应、闲暇安排、与亲友交流、与社区居民交往、利用公共设施与社区参与)与身份认同(经济支持、未来打算)两个维度(刘亚娜[30],2016),居住内外环境、社会支持网络(与子辈关系、孙祖关系、朋友关系)与社区的融入主观感受[31]三个维度,或闲暇时间利用、社区居住意愿、社区活动参与度、社区情感认同四个维度[32];此外,将社会融合界定为心理认同、家庭融合、社会融合、区域适应(经济适应、文化适应)、制度包融五个方面[33]。维度的界定多样化,未达成统一意见,且多是从流动人口相关的研究中直接借鉴过来,未考虑流动老人的特殊性。
在社会参与这一方面,流动老人和户籍老人在参与志愿服务和社区活动方面意愿都比较低,流动老人参与社区志愿活动更显“惰性”(王世斌[34],2015)。影响流动老人社会融合最大的是家庭情感支持,其次是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支持和医疗服务支持,再次是政府提供的老年福利和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周红云,胡浩钰[35],2017)。在社会支持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支持主体疏离,血缘支持单一,地缘支持缺位,业缘关系匮乏;社会支持内容缺失;社会交往支持的非持续性;社会支持体系碎化。通过梳理会发现流动老人社会融入、社会融合、城市适应、社区适应等概念的定义比较模糊,维度界定也没有达到共识,且均是直接借用劳动年龄人口社会融入(合)、社会参与等维度的界定,并没有考虑到流动老人群体的特殊性。
(四)社会工作介入
现存文献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比较多,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小组工作介入、个案介入、社区介入,一般在某个社区选取几十位流动老人作为案主,采用的理论主要有:小组动力学理论、社会适应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团体动力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同辈群体支持、家庭网络支持、社区工作人员支持)、社会活动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社会撤离理论、赋权理论等。童晔珏认为老年人同样有着活动的愿望,只是活动速度和节奏放慢了而已,即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因年龄的增长而减少[36]。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各种环境系统都会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环境系统与个体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要改变流动老人的现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从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围系统、宏观系统进行解答[37]。“增权”理论认为可以通过给流动老人提供融合的机会,鼓励其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通过活动的参与提高自信心[38]。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不能一味只重视介入、强调为弱化的老年群体赋权,更重要的是具有效益地解决问题,通过初级防御和二级防御的方法来创造良好的环境[39]。
从社会工作角度出发对流动老人的研究,涉及的对象仅仅为流动老人本身,无疑会将流动老人和本地人口进行隔离,即使融合也只是一种同阶层的融入,研究深度也有待提高。
(五)流动老人社会保障及政策研究
流动老人处于生命周期的晚期,身体素质远远不及以前,但其对卫生服务利用却明显不足,慢性病管理存在严重缺失(聂欢欢,鲍勇,2016)[40]。相对劳动年龄人口,流动老人更加迫切需要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但是由于户籍政策的限制,这些老人无法享受“同城优待”(杨芳,张佩琪[41],2015),政策地域差异较大,医疗报销政策统筹层级低,各地报销药品目录不一,生存认证手续麻烦,养老金领取转接不够人性化是目前面临的最主要、最迫切的问题。而外来务工者有社会保险政策、住房政策及落户政策等,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有入学政策、医疗政策等,但是流动老人社会保障这一部分研究不足,也没有单独针对他们开放的社会保障或福利政策(刘晓雪[42],2012)。芦恒,郑超月(2016)提倡从治理理念上的“静态的公共性”转换为“流动的公共性”,彰显流动的跨越性、制度化的个体主义、多方联动等优势。同时,需要针对“老漂族”自身的复杂性配之以类型化分析,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着力点,建构不同侧重点的流动公共性。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据以上分析,目前我国流动老人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虽取得一定成果,对往后的研究具有较大借鉴,但存在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方法、数据、区域单一
首先,目前国内对流动老人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使用深入访谈,定量分析非常有限。其次,绝大多数是选取几十位流动老人作为研究对象,而缺乏大数据分析,对流动老人整体的把握不够全面。再者,现有文献对流动老人调查的区域范围比较小,一般为一个社区、街道、城市或省份,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福建等),全国性调查很少。
2.缺乏学科碰撞,深度有待挖掘
从研究范式上看,现存文献主要从社会学、社会工作的角度进行探索,缺乏多学科的碰撞与交叉研究,理论视角过于单一,且理论挖掘有待深入,缺少宏观的理论框架指导,在实证调查中更是如此,其理论预设不足,只是简单就事论事,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扩展。总体而言,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共性,即流动老人流动的特点、流动原因、现状。
3.研究对象一刀切,可加强精细化研究
现存文献主要是将流动老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缺乏流动老人内部异质性研究,可引入性别、年龄、区域等视角,比较男性与女性流动老人,高龄、中龄、低龄流动老人,城—城、城—乡、乡—城、乡—乡流动老人,户籍与非户籍流动老人等各类群体在流动原因、动力、特征、健康状况、社会适应、社会融入、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异同。
4.研究内容不够丰富,需集合“流动”与“老人”双重特性
流动老人研究内容比较单一,不够丰富,除去流动老人的流动原因、特征、影响因素、健康状况、幸福感、居留意愿、社会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等状况,还可以关注流动老人生活方式、婚姻状况、社会保障、社区照料体系、空间分布模式、闲暇时间安排、消费观念、养老方式、服务管理、健康教育等等。可以参照流动人口的研究,但是不能仅仅止步于此,需要结合流动人口与老年人的双重特性,不断丰富流动老人的研究内容。
6.缺乏流动老人政策研究
流动人口问题的本质特征是我国户籍制度及依托之上的公共管理及社会服务制度的不合理而导致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劳动力市场和公共管理及社会服务体系中难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和获得平等的地位[43]。但是,流动老人政策研究尚属盲区,目前文献仅仅分析了流动老人的特征、原因、影响因素或仅对迁移老人的社会适应性问题进行描述,并未进一步对流动老人的社会适应背后的养老需求与养老资源供给进行深层次探讨。此外,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现行政策主要涉及流动儿童、育龄妇女、农民工群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有关流动老人的专门性文件尚属空白,甚至在文件中提到流动老人的省份也是寥寥无几。
(二)展望
基于目前流动老人研究的不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首先,今后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调研应加入流动老人群体,丰富流动老人数据库,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还可以加强各区域流动老人的比较分析,比如“东部、中部、西部流动老人在社会融合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流动老人在超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生活状况是否存在差异及影响因素是什么”等方面的研究。
其次,需要重视流动老人的双重属性,即“流动性”“高龄化”。研究表明能够进行流动的老年人,其身体状况均好于非流动老人,因此不能将其视为仅仅需要照料的老年人群体。但是,相对青年流动老人,其身体机能相对较弱,更加需要医疗卫生服务。因此,今后有关流动老人的研究可以基于或参考流动人口的概念界定、指标测量、研究内容,但是不能够止步于此,应该多一些探索符合流动老人实情的概念、指标、测量等等。
再次,流动人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分层性(杨菊华[44],2015),不同年龄、性别、户籍的流动老人各不相同。因此,需加强对流动老人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关注,为其提供分类化与精准化的服务。比如,可以加强对“流动中的老年人口与非流动老年人口的差异比较”“男性流动老人与女性流动老人的特征分析”等研究。还可以关注未发生流动、配偶分离留守农村的老年人生活状况。
最后,倡导多学科碰撞,重视理论指导。在分析流动老人现状、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制度、体制以及公共服务管理。目前研究往往重视现状及问题的研究,不重视对策的提出。今后需要尝试提出全面的、细化的、静态的政策建议。此外,流动老人处于生命周期的晚期,对医疗卫生服需求更大,从长远看需关注流动老人背后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