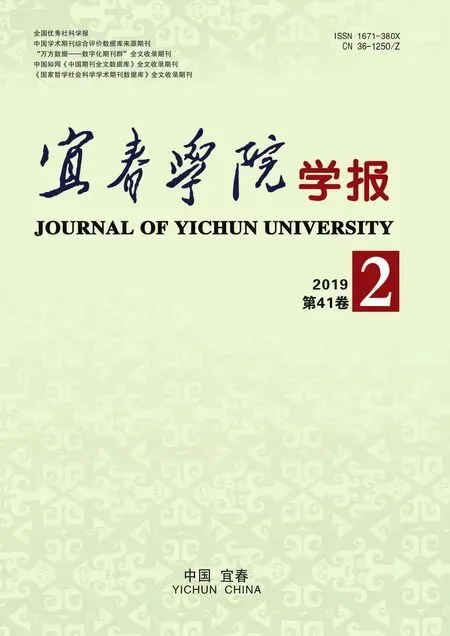梨花沉吟,海棠轻语
——对话理论视域下的小说《洛丽塔》与《甜蜜的房间》
马雪宁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作为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1]通过一个死囚的独白,用绮丽、绚烂的语言,结合暗指、巧合、戏中戏等手法,叙述了一名中年男性与其未成年的继女不为伦理所容的恋爱经历。随着该作品的传播,如今“洛丽塔”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情结。而森鸥外长女,日本作家森茉莉多数作品都围绕父亲,其中《甜蜜的房间》[2]一作让她被称为“写作的洛丽塔”。在《甜蜜的房间》中,她终于直面她这一生惟一不断书写的主题,赤裸裸描写父女间的浓烈情感,被三岛由纪夫誊为“性感杰作”。创作这两部作品的作家生卒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纳博科夫是俄裔美籍,一生流离,森茉莉生在日本,但是其父崇尚德国文化,家居布置、生活习惯高度德化。巴赫金曾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3](P340)这从侧面揭示了对话研究的其价值与意义。森茉莉笔下的藻罗是否代表被物化的、沉默的“洛丽塔”原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两部作品对于欲望各自做了怎样的加工处理?两部作品超越了地域、民族、性别的隔阂在什么层面上达成了怎样的对话?
一、“小仙女”原型考——“问题少女”珀耳塞福涅们[4](P68)
“使我失去理智的是这个小仙女的二重性——可能也是所有小仙女的:我的洛丽塔身上混合了温柔如梦的孩子气与一种怪异的粗野,是从广告和滑稽画片上那些狮子鼻的扭捏作态学来的;是从“旧时代”(弥漫着碾碎了的雏菊和汗味)故作名士派头的年轻仆役身上学来的;是从地方妓院里那些已经足够年轻,却还要装成孩子的妓女那儿学来的;而后,所有这一切又与白玉无瑕无与伦比的温柔混杂在一起,渗入麝香味的草丛和泥土之中,渗透尘埃和死亡。”[1](P32)
“藻罗体内同时住着小孩和恶魔,这就是她可爱的源头。甩着尾巴的恶魔和小孩,像小狗一样相互嬉戏着,很难分出胜负。其实,每个孩子原本都是这样,但平凡的父母会扼杀恶魔的部分,也会扼杀孩子的部分,却因为无法彻底扼杀,所以孩子和恶魔的部分都变得十分丑陋、愚蠢,残留在子女的身上。长大以后就变成只会动坏脑筋的大人,或是墨守成规的人。”[2](P175)①
以神话、仪式为基础的原型概念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逐步渗透到社会、宗教、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在弗雷泽和荣格原型理论的影响下,加拿大文化学者弗莱确立了原型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手法的地位。原型批评旨在探寻文学中某些反复出现的意象的由来已久的原始意义以及它们是如何保存在文学经验之中。
希腊神话中,少女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哈迪斯诱惑、绑架,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因为这场无妄之劫成为了冥王的妻子。从安提戈涅到亚瑟王传奇中的王后格温娜维尔,从梦游仙境的爱丽丝,到奥菲利亚,自然还有广为人知的“小仙女”洛丽塔和森茉莉笔下的“小恶魔”藻罗,这些文学形象无一不传承着珀耳塞福涅这一脉传统。
珀耳塞福涅们生活无忧无虑、平安喜乐。她们觉察不到世间险恶,热衷于猎奇和冒险(正如洛丽塔在夏令营期间和同学之间进行的性方面的探索游戏,或年幼的藻罗在不止一名男子身上验证自己的魅力)。她们习惯依赖别人(正如洛丽塔会因为经济原因一度陷入亨伯特的控制,或藻罗习惯了养尊处优,连走路都不能直起身来)。她们厌恶道德、责任或任何形式的控制(正如洛丽塔会主动按照她理解的成年人那一套诱惑亨伯特,或藻罗对于散发着道德味道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厌恶)。
珀耳塞福涅们喜欢玩耍、派对,时常显出纯真温柔的一面。她们敏感,甚至通灵,不太会为自己的言行负责,需要他者的关注和照顾。缺乏耐心,容易恼怒,自私自利。所以当珀耳塞福涅的人生境遇不利于其性格发展时,就会成长为“问题少女”——本文分析的洛丽塔和藻罗或多或少带着“问题少女”的影子。“问题少女”失去控制,甚至沉迷于玩乐、派对、毒品和性。她们不在意学校的纪律和自己的成绩,因为她们不在意未来。她们可能被诱惑与人发生性关系,过后并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问题少女”时而觉得世界让人抑郁、厌倦、幻灭的同时,常希望通过卖弄风情控制他人。
洛丽塔在亨伯特杀死情敌奎尔地并被绳之以法后死于难产,藻罗对婚姻不忠,其丈夫遭到背叛后去世藻罗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两位“问题少女”,两种结局,无一不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问题少女”人物形象的塑造,能把更多矛盾冲突带入叙事中,增加作品的张力,通过和“问题少女”的接触,淋漓尽致地揭示各个人物的性格。与此同时,“问题少女”这一原型还具备较其他女性文学形象相比更多的复杂性——积极、进步的意义就蕴于这种复杂性中。
纵观东西方文学传统,女性人物形象是两极分化、二元对立的——要么是贤淑勤劳、温文尔雅的“屋子里的天使”[5](P22)(如《奥德赛》[6]中的珀涅罗珀,或《沙恭达罗》[7]中的沙恭达罗),要么是冷酷无情、为非作歹的恶魔(如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或《吉尔伽美什》[8]中的女神伊丝塔)。无论是神圣化还是妖魔化,都是对女性角色的边缘化甚至物化——女性角色缺乏丰富的内涵,缺乏性格变化,呈现出非此即彼的扁平化、脸谱化特征,并在情节推动中缺乏能动性。这种种现象,反映着在文学传统中女性——无论是女性作家还是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集体失声。而“问题少女”这一原型在不同作品中的不断生成、演进,某种程度上以鲜活的生命力对抗着这种男权的传统——她们不是单纯、无力,坐等命运摆布的少女,她们对自己的美丽有明确的自知,并时常挑衅伦理、规则,玩一些危险的恶作剧;与此同时,她们也不全然是心狠手辣的恶魔,她们天真无邪,对自己所作所为可能会导致的后果并不知晓,连她们的自私和乖戾都是孩子式的,无辜的,让人不忍责怪的——“问题少女”提供了除天使和恶魔外的第三种女性形象,也提醒着更多种女性形象存在的可能性。
二、欲望的食物链——蝴蝶与幼兽
罗兰·巴特在《文之悦》一书中提到,“父亲死了,这会使文学丧失许多悦。倘若父亲不复存在了,还讲故事作什么呢?每一种叙事不就都要复原成俄狄浦斯么?”[9](P58)拉康则在20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父亲是一种隐喻”,并在其理论构建中将父亲视为一种能指符号。
按照画族谱的方式画出《洛丽塔》和《甜蜜的房间》两部作品中呈现出的关系图,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例如:洛丽塔与藻罗都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母亲;洛丽塔与藻罗都和父亲曾经某位已经去世的情人之间具备较高的相似性;洛丽塔与藻罗都有一位情人被其父亲/情人在实际层面或象征层面杀害。

图1:《洛丽塔》中主要角色关系图(死亡角色用灰色表示)
Figure 1:The main role diagram in Lolita (death character is shown in gray)
从拉康的视角,这两部作品主人公的成长境遇里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共同点——母亲的缺席(死亡)。不同的是,作为洛丽塔度过童年、进入青春的背景环境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在亨伯特闯入她的生活之前,父亲是缺失的,而“心怀不轨”的亨伯特以继父的身份介入后,洛丽塔的母亲又在发现真相的悲痛中意外死亡。而藻罗年幼丧母,母亲角色的缺失,让藻罗将自己人同为与父亲同一,并眷恋这种状态——生活在“甜蜜的房间”中,和父亲成为彼此欲望的客体。这种状态本应由于母亲的介入被压抑,进而使得藻罗向母亲认同,向菲勒斯认同,可是藻罗由于母亲的缺失,没有走出想象界进入象征界接受菲勒斯,而是始终停留在与父亲共同的“甜蜜的房间”中。

图2:《甜蜜的房间》中主要角色关系图(死亡角色用灰色表示)
Figure 2:The main role diagram in Sweet Room (death character is shown in gray)
无论是对于洛丽塔,还是对于藻罗,这个“父亲的形象”都曾发挥类似于镜子的作用——通过这个形象确认自己的存在,确认自己青春、甜美又不乏性感。不同的是,亨伯特为洛丽塔写下的是墓志铭,而藻罗从父亲林作手中获得的是通行证。
如果将洛丽塔和藻罗当做两个行动元提取出来,我们又不难发现,在各自的故事、情节中,洛丽塔是被动的,如同被逐猎的蝴蝶,而藻罗是主动的,如同食肉的幼兽。
如同《洛丽塔》开篇处亨伯特所言,“你放心,杀人犯总能写出一手妙文。”[1](P3)作品通篇是亨伯特自己洋洋洒洒的陈述,而洛丽塔,只是一个被抹去了声音的符号,一个理想的欲望客体。而《甜蜜的房间》中,几乎听不到父亲林作的声音,他是真的在父爱之外对藻罗怀着深深的爱恋,抑或这一切不过是藻罗近乎神经质的幻想,实际上我们都无从知晓。
尽管亨伯特无疑也曾作为洛丽塔欲望的客体存在,但是那只是洛丽塔一次叛逆的冒险,一次对自己魅力的确证。后来洛丽塔接受亨伯特作为自己的情人,更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她别无去处。随着成长,她对继父亨伯特的怨恨也逐渐积累起来。洛丽塔开始认识到,即使是最可悲的家庭生活也比这种乱伦状况好。她交往其他男性,并借机逃离。与此同时,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欲望,更接近一种早年创伤经历后固着的情结——他“青梅竹马”的恋人阿娜贝尔因病夭折后,他为之痴迷的欲望对象便一直都是十岁左右的“小仙女”。他紧紧攥住“生命之光”、“欲念之火”,以抗争阿娜贝尔的死亡,以及正在发生的他的衰老和必然发生的他的死亡。在对洛丽塔的渴望中,亨伯特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他是满心溺爱的慈父,是无视伦理的恋童癖,也是忧伤的、蠢蠢欲动的少年情人。而这种复杂性洛丽塔不愿承担也无法承担。对于洛丽塔而言,亨伯特是一个合格的供养者,同时也是侵犯者和控制者,她挑衅的态度渐渐变为反抗、逃避。
而藻罗身上更多地体现着较之男性更为复杂的女性俄狄浦斯情结。在父亲肯定的目光中,她获得了某种骄傲。并且伴随着这种骄傲,以及不安,她去讨众多男孩,甚至成年男士的欢心,并将这些她认为足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新生的女性具备性魅力的战利品展示给父亲,引起父亲的嫉妒,从而挑逗起其兴趣。而藻罗的父亲林作与亨伯特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相似:他的妻子,藻罗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不难理解他将对妻子的爱转移,并倾注到和妻子最接近的人——女儿藻罗身上。只是藻罗和母亲之间存在着固定的血缘上的相似,而洛丽塔和安娜贝尔之间只存在着“年幼”这个共同点(这个“年幼”实际上体现着亨伯特的情结),并且林作和藻罗之间存在着不但是法律、伦理层面上的,更是血亲层面上的父女关系,所以较之林作的克制,亨伯特表现出的爱欲更加疯狂、肆无忌惮——当然也可以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故在个体欲望的层面上,洛丽塔是消极、被动、不作为的,而藻罗的声音并不是对亨伯特的回应,更多地是对自己的野心闪烁其词、遮遮掩掩的陈述。
三、微观权力的战场——“父亲之名”的变奏两种
更值得注意的是,透过爱情和性的表象,两部作品中展现着两种耐人寻味的权力关系。福柯即强调权力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在权力运作的网上,个体不但在流动,而且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同时又运用权力。”[10](P28)权力是微观的、毛细血管状的,性、家庭、学校、军营、精神病院、监狱甚至人文科学的形成,无不体现着这种权力的运作。
在这两部作品中,权力从以往与之密切相关的宏观叙事中逃逸出来,父权不再体现为类似于君权的绝对的否定、压抑和禁止。
在有性欲的地方就有权力。性同时是进入身体生命和人种生命的通道,因此性要求最高级别的对待,因此性成了抵达权力中心的通道,同时也成了理解权力的依据。
如同小说《你好,忧愁》[11]中女主人公塞茜尔竭力阻挠鳏居多年的父亲和其女友的婚事一样,叛逆、任性的少女洛丽塔虽然和母亲关系紧张,但是至少也达成了一种平衡。所以面对不速之客亨伯特的闯入,洛丽塔最初是拒斥的——接纳一个知识分子做派的中年男子作为母亲的配偶、自己的父亲,意味着原本闲散的生活很可能要被一种新的秩序统摄。所以洛丽塔对初来乍到的亨伯特看似漫不经心的撩拨实际上是对这种权威的挑衅。当她意识到亨伯特很可能被自己征服时,产生的是一种旗开得胜的自喜。但是随后,母亲的意外身亡,让她从这场游戏中回到了残酷的现实,她意识到这种“父亲的权威”不但确凿存在,而且自己在性上被享用,经济上被控制,无处可逃——徒有风情的自己根本不是亨伯特的对手。与此同时,《洛丽塔》的文本却处处在诉说着洛丽塔的残忍、无情和她对亨伯特的百般折磨。“但我软弱,我不聪明,我的女学生小仙女让我甘心为奴。伴随着人类生活环境的缩小,只能是温柔恋情和痛苦在增加;而对此,她是占尽了便宜。”[1](P145)可见在这里,权力不是单向的。与此同时,权力以其创造性,孕育、生成着亨伯特和洛丽塔各自的性格特质。
而在《甜蜜的房间》中,藻罗从一开始就深谙父亲林作的权威是如何存在,如何运作。并且藻罗在逐步学习向这种权威靠拢,把自己逐渐同化进去。关于“食肉的幼兽”的比喻揭示了藻罗本也并未加以掩盖的野心——父亲爱我,我便可以(像父亲一样)呼风唤雨。只是比起父亲——一个中产阶级的中年男子——藻罗更渴望处处去验证这种权力。最初是欺负家里的佣人、家庭教师,在父亲的庇护下与她们身上那种虚伪的道德斗争。实际上,由于在家中她拥有几乎是绝对的权力,所以她完全可以无视任何形式的道德训诫。进而在学校从老师、同学的拥护中确证自己的这种权力离开了家依然能够生效。藻罗过早地了解到自己在外形上的出众之处,并诱惑同龄的男孩,钢琴教师,家里喂马的男仆,后来成为了她丈夫的天上,度假时偶遇的男青年多米多里……藻罗的出轨和丈夫的死亡,是这种权力运作达到了巅峰的标志。在丈夫天上去世后,也就是文本接近尾声处,有一段通过藻罗为数不多的女伴爱莎的视线对藻罗的描写:“藻罗的嘴唇轻轻闭着,眉毛已经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但比以前更加强烈地发散出一种异样的粘稠东西。她一双湿润的眼睛没有焦点,茫然地看着半空。原来,这才是藻罗。爱莎情不自禁地出神地看着藻罗。藻罗的脸像可爱的魔鬼一样,爱莎从藻罗的脸中,看到一个伟大男人的影子。那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男人,看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被自己打死时的错愕表情。在错愕表情中,连带着害怕——原来,这才是藻罗。”[2](P453)
权力顶端无雌雄。藻罗凭借向父权的极力靠拢,与之同化,一步步成长为爱莎眼里那个“可爱的魔鬼”、“只关心自己的男人”——而那个被藻罗击败的男人,她的丈夫天上,反而成了“被打死的无足轻重的女人”。在尤其是东方的文化传统中常常是三位一体的父权、夫权和男权中,藻罗通过借用前者,将后两者踩在脚下。而她对此似乎并不自知,甚至还错愕中连带着害怕。
“又出现了一个牺牲者,这次,终于要了他的命。”[2](P458)这是藻罗的丈夫死后,父亲林作的自言自语。耐人寻味的是得知这个死讯后,林作脸上浮现出来的笑容——“那是没有一丝忸怩,毫无顾忌的恶魔的美丽微笑,那是一个肆无忌惮,简直让人怀疑是从林作的细胞转移到了藻罗的细胞里;那是面对整个社会的叛逆笑容,叛逆的欢喜。”[2](P456)
个体对他者拥有权力,最不容辩驳的证明就是,他者的生死由该个体决定。支配林作和藻罗形成的共同体行动的,不是邪恶,而是实际上无关善恶的权力。
权力是关系。在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从洛丽塔的角度看,这种对抗针对的是父权,从亨伯特的角度看,这种对抗针对的是时间和死亡。这种对抗让双方都受到了无法逆转的损耗,亨伯特身败名裂,沦为阶下囚,洛丽塔颠沛流离,贫困潦倒,最终死于难产。而在林作和藻罗之间存在着的更近乎一种秘密的契约,这种契约关系甚至高于一切,远在他们之间的父女关系和隐晦的情人关系之上。藻罗是林作的得意之作,是他生命的寄托和延续,更是他实现对世界的野心和叛逆的最佳渠道。藻罗对父亲的渴望比起情欲更接近于对权力的欲望。
四、梨花对话海棠——两重声部的错落交织
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2](P947)尤其是在读者的阅读。感知过程中,任何文字都是跨文本的,任何文本都产生于其他文本之上的“二度”结构,文本的意义源于文本间的相互作用。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洛丽塔》、《甜蜜的房间》这两个文本在创作过程中发生过彼此的影响和渗透。然而由于对相同母题的涉及、贯彻,以及主人公在人物原型上存在着同源性,使得这两个文本在被接受过程中产生了跨地域、文化的,内在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两个文本叙述的故事,都发生在道德和非道德的边缘,传统的穷途末路中,伦理的风口浪尖处。所以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方的“耻感文化”之间的区别。《洛丽塔》中多次出现的“罪恶”、“灵魂”、“乱伦”、“忏悔”、“救赎”等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字眼,而在《甜蜜的房间》中情节类似的位置这些字眼并没有出现——《甜蜜的房间》中一切以一种更加隐晦、更加暧昧的形式,隔着一层网纱影影绰绰呈现出来。耐人寻味的是发生在时间轴最末的“情敌的死亡”——亨伯特杀害奎尔第带有一种“决斗”后同归于尽的意味,而藻罗的父亲林作,他并没有亲手杀死情敌,只是在情敌死后,他意味深长地露出了微笑。但是抛开这种文化差异对叙述造成的影响,从情感意蕴的角度观之,《洛丽塔》文本在道德的断裂处触发悲悯,而《甜蜜的房间》更多的是关乎野心、权欲的暴力美学。
两个文本的空间构建耐人寻味。《洛丽塔》是典型的“公路小说”,在洛丽塔的母亲意外死亡后,亨伯特驾车载着洛丽塔沿着公路旅行,在路边的汽车旅馆投宿,寻欢作乐。中途虽然也曾短暂租下房子停留,然而随着叙述,亨伯特又一面追逐逃离的洛丽塔,一边沿路颠沛下去。而《甜蜜的房间》一开始就把背景设定为藻罗“甜蜜的房间”——她和父亲林作拥有的一幢宅院,这是一个近乎封闭的空间。随着藻罗成长,步入婚姻,她离开了“甜蜜的房间”,却无法也不愿和父亲相互割舍。直到藻罗的丈夫去世,她又被父亲接回“甜蜜的房间”,回到了叙述的起点。将时间这一维度纳入视野后,不难发现,两个文本的时间和各自的空间之间存在着同构的关系。克里斯蒂娃曾提出一种新型的时间模式——“女性时间”[13]。她认为,由于女性自身的特点,女性主体性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测定概念,一种从本质上来说具有“重复性和恒定性”的测定方式。与(男性的)线性时间不同,这种时间体验突出了循环往复,强调了回归——一种螺旋式回归。这种“循环式和纪念碑式”是《甜蜜的房间》提供的感官盛宴背后铺设的不可思议、无限复杂的时间感。较之而言,《洛丽塔》中的时间绵延正如同笔直的公路,虽然饰以大量倒叙、嵌套、回环往复,但是本质上是线性的——这种一往无前或也掺杂着些许悲壮的况味。
看似巧合的是,纳博科夫和森茉莉都有文学创作之外的迷恋,纳博科夫是收集、研究蝴蝶,森茉莉是制作、品尝甜点。
纳博科夫对蝴蝶的分类、变异、进化、结构、分布、习性感兴趣,并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一些关于蝴蝶的论文。当被问及这与他的写作有什么联系时,他表示“一般来说是有联系的,因为我认为,在一件艺术品中,存在着两者之间的某种融合,即诗的精确与纯科学的欣喜这两者的融合。”[13](P10)森茉莉也在《甜蜜的房间》后记中类比过小说写作和甜点的制作。事实上,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我们相信《甜蜜的房间》这一文本比起甜点的制作过程更多地来自于森茉莉和父亲森鸥外之间甜蜜、复杂的情感。如同纳博科夫表示在《洛丽塔》的构思阶段,自己有意识地关注新闻中的性犯罪、凶杀等刑事案件,并把它们拼接到《洛丽塔》中。
显而易见,这两部作品是独立于作者存在的——这就为我们将之作为研究客体,并研究其彼此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只有在沉思中将文本与作者之间粗而韧的脐带剪断,尊重文本的独立自足性,才能进一步在文本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放眼更大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
注释:
①原文为繁体中文,引用时转化为简体,其他来自此书的引用同
——《洛丽塔》的成长小说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