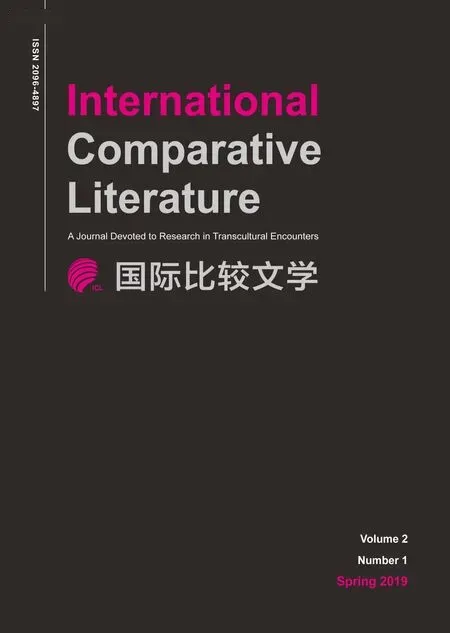从“八五新潮”到图像-资本时代
——论守望丹青与中国书画家的博物学知识学养*
杨乃乔 复旦大学
一、黄宾虹的书画学养及为黄宾虹造像的视觉观念生成
“1985”,那是一个让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怎得也无法忘却的年代!198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下简称“上人美”)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合编出版《黄宾虹画集》,一位沉寂多年的“书画宗师”重新进入了编辑们的视野,当时是由“上人美”美术读物编辑室主任范志民亲任责编,身为同一科室的理论编辑邓明也感受经历了这部“画集”的编辑与出版过程。在我与邓明的交谈中,我们都提及自己对优秀的绘画作品秉有一种长久凝注性品鉴的审美心理,我们往往会对自己所致敬的绘画作品给予长时间的品鉴性注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再或多次品鉴于长时间的凝视,以便让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完全融入作品的本质性意象中去。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一直存有“南黄北齐”之说,黄宾虹的辈分很高,李可染、林散之等也曾是他的学生。然而长时间以来,黄宾虹的绘画作品在艺术市场的价格并不高,公允地评判,黄宾虹的绘画学养含量高峻,深藏不露,不像齐白石的花鸟鱼虫,一眼撩人喜爱到底。
的确,我一路地把黄宾虹的绘画品鉴下来,感觉黄宾虹的笔墨及设色,从“白宾虹”向“黑宾虹”转型所形成的“黑、密、厚、重”之画境,在积墨深涩的风格上是拒庸常之辈于理解之外的,所以黄宾虹的笔墨意象特别经得起品鉴者的长久凝视,且依然深不可测。《黄宾虹画集》在编辑室的编辑过程中,使得邓明有机会对黄宾虹的一幅幅作品给予长久的凝视,这种对黄宾虹笔墨及设色内涵的摄入性凝视,对邓明来说是一种难能所属的进入性体验,他完全融入了黄宾虹深涩的笔墨意象中陶冶着自己,从而收获了丰沛的养分。
而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机遇,则把邓明又带入了对黄宾虹信札及其画论思想等最为切近的体验性接触与阅读中。
198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把《黄宾虹书简》列入发稿计划,范志民直接把书稿移交给邓明,确定由他担任责编。据邓明当下的回忆,在编辑出版的程序上,这部“书简”应该是在当年发稿的,即1985年。由于邓明在1986年初担任“上人美”的副总编,手头担任责编的《中国美术全集·石刻线画》《刘海粟艺术文选》《黄宾虹书简》及五六种《中国画家丛书》正处在发稿后的校样阶段,这些出版事务仍然需要他来负责,故《黄宾虹书简》直到1988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
我在翻阅《黄宾虹书简》(第一版)时,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这部《黄宾虹书简》的《前言》是由著名的大翻译家傅雷先生所撰写的,而落款时间却为1962年11月。傅雷《前言》落款的时间与这部“书简”付梓的时间有着如此久远的历史逆差,这让我很震动,我下意识地感觉到其中可能隐含着难以言说的历史苦涩。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邓明,他告诉我:“这部《黄宾虹书简》是‘文革'前所留下来的一部老稿子。”
我明白了!
中国美术界皆知黄宾虹生于1865年,于1955年因病作古。从傅雷《前言》的最后一段陈述,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这部“书简”编辑出版的往事踪迹:
本编既有汪己文倡议,复独任征求、收集、编辑之劳,可谓终始其事。至克观厥成,则宾虹先生友好及各方之支援赞助莫不与有力焉。付印之日,汪君嘱缀一言,因述编辑大旨及经过如上。
从傅雷的陈述中,我们不难见出,汪己文把这部“书简”编完后,即嘱傅雷撰序,那至少是在1962年11月之前的事了。当然,我们还可以把汪己文准备且开始编辑黄宾虹“书简”的时间,再往前推若干年,三年或五年,或假设性地推至于黄宾虹离世的1955年。
历史总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书写那些让人不可忘却的记忆。“文革”是于1966年5月16日正式爆发的,从1962年到1988年,中国历史经历了“十七年”的最后5年,又经历了十年“文革”,再经历了“文革”终结之后改革开放的11年,一部个人“书简”的出版在时间的延宕中整整耗去了26年!历史总是在不可预测中跌宕起伏,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谁也不愿意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就是说,至少时隔26年,这部由傅雷撰序的《黄宾虹书简》才得以付梓,以告慰35年前作古的中国书画大师黄宾虹先生,而更让人苦涩的是,撰序者傅雷先生在“文革”初期不堪凌辱含恨离世也过去了22年。
专业书画界与艺术市场在质性上应该分属为两个不同的空间,艺术市场对黄宾虹是不公允的,然而专业书画界在把黄宾虹尊称为“书画宗师”时,也并不见得公允到哪里去;因为绝大多数专业书画家与美术史论家依然忽视了黄宾虹背后的深厚学养,而邓明与我都坚持地认为除此“书画宗师”尊称之外,黄宾虹更是一位学养积重的学问家,是中国书画界难得的一位博物学家(naturalist),启用另外一个术语表达,也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黄宾虹书简》共收集了黄宾虹的信札170通,他在日常的信札中所讨论的话题不仅关涉了中西绘画史论,还涉及了中国书论与金石文字等相关考据学的艰深问题。关于这一点傅雷在其《前言》中曾给予了准确的评价:
黄宾虹先生不仅为吾国近世山水画大家,为学亦无所不窥,而于绘画理论、金石文字之研究,造诣尤深。或进一步发挥前人学说,或对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态度谨严,一以探求真理为依归,从无入主出奴之见掺杂其间。
我在这里无意于展开性地讨论黄宾虹的书画境界及其笔墨风格,当然,也不想多谈他关于金石文字的考据,主要是担心那些错字连篇的所谓“书法家”不懂金石考据,因此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只想说邓明作为责编为了编辑好这部“书简”,他不仅细读且校对了黄宾虹的全部信札,也扩展性地借阅了大量关涉于黄宾虹及其信札的相关背景文献和研究材料。
从《黄宾虹画集》到《黄宾虹书简》的编辑与出版,这项工作不仅让邓明颐养于黄宾虹的书画境界,而且也更让邓明陶冶于黄宾虹的中西美术史论思想及其金石文字的考据学养中;所以在视觉体验与思想知识的两个维度上,邓明得以心游于对黄宾虹的通透性整体把握,作为一代“书画宗师”的黄宾虹也必然在邓明的敬拜心理中油然矗立起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呼之欲出的内视形象,且鲜活地向他走来。恰恰不同于普通的出版编辑者,邓明本人是书法家与画家,是一位美术史论家,也是一位颇有学养的出版家,用水墨丹青为黄宾虹造像的视觉观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默然生成了。
那年是“1985”。
1991年,邓明出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对该社美术、摄影及连环画出版的发展思路给出了拓展性的规划,因而不久劳累致病。1993年,因肝病久治不愈,出版局同意他去职养病。对于邓明来讲,养病虽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赋闲,这却让他更为专注地沉浸于从1985年以来对黄宾虹的书画体验及其画论思想的回顾中。对黄宾虹长久的凝注、阅读与思考,这一切最终全部淤积为邓明于一瞬间所希冀表达的审美期待,也正是如此,他毫不迟疑地以黄宾虹的“五笔”“七墨”为黄宾虹画了一幅水墨丹青肖像——《黄宾虹先生像》(4 cm×24 cm,1993)。他试图完成一个观念性的尝试:以操用黄宾虹的笔墨风格为黄宾虹造像,他想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向黄宾虹表达敬意。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一个偶然的行为其背后必然蓄势着经年积久的沉淀,也正是这幅蓄势成形而涌出的黄宾虹水墨丹青肖像,开启了邓明用中国水墨丹青为中国水墨书画家造像以写史的观念,这就是《守望丹青》成书的最初历史缘由。《守望丹青》是邓明于2017年出版的一部在观念上集诗、书、画、论于一体的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邓明的《黄宾虹先生像》做一次视觉及其笔墨风格上的细读。邓明以水墨丹青为黄宾虹造像,其绝然不是一般画家画人物肖像的形似之笔,邓明的《黄宾虹先生像》不仅仅是达向一种形神兼备的水墨造像,而更是在形神兼备的交集维度上,把黄宾虹早期与晚期的两种笔墨风格给予提炼,且集纳于造像中一并合力出场,即集纳“白宾虹”与“黑宾虹”两种笔墨风格为黄宾虹造像。我私下以为,这大概是水墨画家在为水墨大师作水墨肖像时所刻意表现的一种崭新观念了。
邓明的黄宾虹水墨造像从其棉袍右下半身蔓延于双脚之鞋,其笔墨的铺染所遵循的笔法是黄宾虹早期的画风:干笔淡墨,从这一局部的表现,我们可以见出邓明是藉由特定的笔墨风格叙述早年黄宾虹对“新安画派”的承继,以在视觉形塑中表现被中国美术史界所尊称那个“白宾虹”;除此之外,在造像的笔法上,邓明大面积地定格于黄宾虹晚年黑密厚重的风格:积墨浓染,以在视觉形塑中表现被中国美术史界所尊称的那个“黑宾虹”。邓明刻意总纳黄宾虹绘画生涯之早期与晚期的两种风格为其整体造像,这的确呈现一位美术史家的用心及刻意拣选的眼光。
邓明的《黄宾虹先生像》不是一幅简单的水墨造像,而是在一幅水墨造像中,用黄宾虹的笔墨风格及其气象记忆与表现黄宾虹一生的书画生涯。实质上,仅从这幅作品成像的视觉观念来看,邓明即是以水墨丹青造像为黄宾虹撰史。因此,邓明的《黄宾虹先生像》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绘画与美学的含量是非常丰沛的。而我所担心的是,邓明的良苦用心难免会被那些只考虑资本与商业市场运作的浅薄之人所不可识读,因为,当下视觉艺术市场在运作的方式上已为资本所操控(manipulation),艺术的本质及其审美意旨已然被这个商业社会所绑架,拍卖与收藏只是为了资本的炒作,所以收藏一幅视觉艺术作品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资本在艺术收藏的商业性运作中攫取最大化的增值:即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
思考到这里,我还是要把自己的思路转向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那里去,谈一下文学艺术与资本的逻辑关系问题。
布尔迪厄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与文学艺术批评家,在我看来,他的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理论在体系的构成上过于精制化,充满着适用于法语历史文化语境下展开批评的学院气。多年来,我始终把他的理论看视为法兰西学院派批评家的思想游戏,其中不断地闪烁着精制的理论想象性,然而中国学者恰恰不可以把他的理论直接译入汉语学界使用,因为他的理论及批评取向在法中双方语境下所指向的历史文化形质不一样。我们应该把布尔迪厄的理论译入汉语学界给予修订性与丰富性的使用。
坦言而论,布尔迪厄关于“资本”(capital)、“场”(field)、“习性”(habitus)、“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与“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这几个重要理论观念的思考,可以说,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应该是具有跨语际的启示性的。特别是布尔迪厄把资本诠释为一种权力形式,当下中国美术界就是受动于资本的权力性操控而形成的一个被构成性的艺术生产场。在这个艺术生产场,从康德(Immanuel Kant)与黑格尔(G.W.F.Hegel)以降的任何对美及艺术本质的普遍性定义,全然失效,成为了理论的幻像,并且对进入资本市场的艺术作品及行为丧失了合法化的解释权。
在这里,我不想旁涉当下艺术市场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只想接续言谈一种艺术观念的生成:用邓明的话说即“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的视觉观念。可以说,从当下来看,这种视觉观念的生成具有相当的前卫性,但是,转换历史的另外一个维度来评判,在“1985”,其又遮蔽在本土主义(localism)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色彩之中。无疑,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二律背反(antinomy)。我们只需把历史发展的时间逻辑带入于反思中,即可以感知这种二律背反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境遇中所存在的逻辑自洽性。如上所述,邓明的这一视觉观念是在1985年生成的,我想在这里设问的是,在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历程上,“1985”又是怎样一个让学界的良知者不可忘却的年代呢?全球化的当下是一个文学艺术遭遇不测的图像-资本时代,从“1985”到“2018”,在这30多年的历史间距中,审美价值与文化观念所发生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绝然有必要回到“1985”给予重新的反思,因为对文学艺术的批评必须要回到历史的本体境遇中,才可以求取那些曾经存有过的真值性历史现象。
二、从“伤痕”“反思”“寻根”到“八五新潮”
对于“50后”的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批当下依然在从事文学艺术批评的“50后”学者来说,回顾1985年,那是在我们这一代良知者的集体心理深层结构中召唤一种激动无比的文化记忆。
我们不妨让自己在时间轴上退出当下,以追溯发生在30多年前那个时代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场景。
“文革”终结后,民众在瞬间的价值真空中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只能从众般地从一种广场政治迅速向另一种广场政治集体移动。民众一旦解禁于长久的思想蒙昧,反而像无知的孩童那样不知所措,他们在惊愕中惶然地迟疑着,随后便在开放的惊喜中接受了政治震荡的价值替换。概而言之,从1977年至1985年,在又一个八年里,中国学界在灵魂破碎重组的震荡中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寻根文学的精神洗礼。倘若说,在“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一切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政治策略调整之态势中,而时至1985年,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走向了百废俱兴。
凡是在思想的介入性摄取中真正体验过这一历史时段的学者,他们都不会忘却:诸种新旧思想与不同政治信念的相互挤压及碰撞,在这八年的文化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板块间的推挤、错动、破裂与重组,不同思想能量消长的张力向碰撞的极限性递增,终于导致了在1985年这个临界点快速地释放,其终结就是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引起了一次思想大地震——“八五新潮”。
的确,1985年,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发生了太多的事件。此次思想大地震——“八五新潮”所波及的范围之广之深,其瞬间席卷了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与舞蹈等领域,并且引发了太多的次生性文学艺术行为及其艺术思潮运动。至少“1985”“八五新潮”“八五美术新潮”“八五新潮文学”与“八五音乐新潮”,这五种表达已作为专业话语被定格在新时期至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史的诸种教科书中,成为了五种使用频度极高的专业术语,并且从未被中国当代学术史所遗忘过。实际上,从历史意识形态的本质来判定,究其“1985”的思潮震源,其还是导源于“十七年”与十年“文革”所淤积而来的那些意识形态板块在解禁后的冲突与碰撞,也导源于新时期前八年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异化、人性、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等大讨论的争鸣。
可以说,在历史的时间坐标系上,“寻根思潮”是点燃“八五新潮”爆发的最后一个导火点。反思到这里,我们还是要在系谱与地图上追溯一下伤痕文学的崛起。
卢新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的本科生,十年“文革”的苦难历史拣选了他成为小说《伤痕》的被动书写者。随即美术界也引发了联动性的无缝跟进,尚辉在《“伤痕美术”的历史记忆》一文回忆道:
为人熟知的“伤痕美术”是从陈宜明、刘宇廉和李斌创作的《伤痕》连环画开始的。……作为“伤痕美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枫》由刘宇廉等三位画家在1979年创作完成的。
从1978年《伤痕》刊发于《文汇报》至1985年,我们可以浓缩出这样一个理论表达式:在咀嚼伤痕的苦涩中探索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之根,那个时代的学人于集体心理结构中始终在鸣响着一个沉重的设问:中国,你怎么了?中国传统文化,你怎么了?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为从近代到当代以来的中国及这个民族所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怎样的文化心理积淀?现在回想起来,有两种思潮依然在我脑际清晰无比地萦绕着,也正是这两种思潮成为触动“八五新潮”爆发的前奏曲:一是对本土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怀疑,二是对外域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全盘接受。
回顾中外文学艺术发展史,文学以其文字的抽象编码易于表达思想与理论的出场,所以其在思想的启蒙与批评的呐喊上,一般是走在美术、音乐、戏剧、电影与舞蹈等艺术表现形式之先的。当然,这也是文学艺术形式本体论及其形式审美表现的一个技术性问题。在这里,让我在文献极简主义(minimalism)的观念下,来浓缩式地检索在“1985”所发生的那些重大文学艺术事件,以提醒当下还在思考的中国学人“千万不要忘记”。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关于事态的发展,一切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中国作家》在1985年第2期刊发了王安忆的《小鲍庄》,紧接着,《人民文学》于1985年第6期刊发了韩少功的《爸爸爸》,当然,在创作的主题上还有其他同频共振的作家作品也同时出场了。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掀动的寻根思潮,让王安忆与韩少功等成为质疑中国传统文化怎么了的“共谋者”(conspirator)。王安忆讲述了捞渣,韩少功刻画了丙崽,他们以讽谕性寓言体(the style of satiric allegories)的书写符码形塑了这两个质性顽钝的荒诞形象,以追问一个根源性的历史原因:是怎样一种根源性的民族文化心理情结从千年积淀而来,从而尘落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到“文革”之封闭与落后的历史成因。这种呐喊于历史寻根思潮中的质疑,在本质主义的反历史传统之激进上,把愚昧、落后、封闭与惰性等民族文化之负面元素统统归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生性品质,李泽厚等相关学者把这种原生性品质带入西方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分析心理学维度,使其被界定为是原发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等。上述来自于创作、批评与理论的三种复调声音合力推动了寻根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的否定及彻底怀疑。
文化寻根思潮的崛起标志着第二次启蒙思潮达向了顶点。同期,韩少功又在《作家》1985年第4期联动性地推出了他的那篇文章《文学的“根”》,这是一篇在理论上为寻根文学摇旗呐喊的宣言性文章:“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的作家有一个‘寻根'的问题。”韩少功进而论述道:
他们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1985年7月6日在《文艺报》的第二版,阿城也发表了他那篇论述文化寻根的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以对寻根文学观念的蜂起推波助澜:“湖南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既是对例如汪曾祺先生等前辈道长中对地域文化心理开掘的作品的承认,又是对例如贾平凹,李杭育等新一辈的作品的肯定,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学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之中的端倪。”与此同时,贾平凹、张承志、阿城、李杭育、路遥、郑义与李锐等都曾先后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卷入了寻根思潮,我在这里恰恰愿意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借喻两部经典中的两句经典表达,以总括寻根思潮与“八五新潮”的联动。《周易·系辞上》言:“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文心雕龙·原道》接续论述道:“《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无疑,从创作、批评到理论,寻根文学思潮以其鼓天下之动的文辞书写深度地推动了“八五新潮”的到来。我曾以自己的青春在生命的体验中经历过那个历史时期,所以完全可以判定,寻根思潮从创作、批评到理论在复调性思想的共谋上无疑是点燃“八五新潮”爆发的最后一根导火索,甚至就是“八五新潮”的前奏及所属部分。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鼓辞论道”的时代彻底到来了。
反思近两百年来中外文化运动,那些文学艺术重大事件的肇事,从来就不是在单一的逻辑上孤立地发生与发展的。势态的发展远不至此,更为令人振奋的是,在彻底怀疑中国传统文化时,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对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及其文学艺术思潮的全盘接受也亢奋为一种激进的偏执姿态。
这,还是发生在1985年!
《人民文学》在1985年第3期刊发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刘索拉是中央音乐学77级作曲系的本科生。在小说创作的身份上,与卢新华一样,刘索拉也是一段历史的被动书写者。然而具体地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不同于卢新华的是,刘索拉则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央音乐学院校园西方先锋音乐思潮生存境遇的被动书写者。《你别无选择》惊世骇俗地宣告了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思潮在汉语本土的正式出场。回忆当时的场景,事态发展得如此之迅速,事隔仅仅四个月,《人民文学》于1985年第7期再度推出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这两部小说在汉语语境下书写的虽然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那些人与那些事,而在创作观念和美学风格上所演奏的却是地道的西方现代派思潮的荒诞。当然,还有其他同道作家作品在其他文学期刊上的摇旗呐喊。
回顾到这里,我必须要提及几句关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及其文学艺术思潮著作的翻译与接受问题。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二次启蒙思潮中,中国学人在思想界开始了为摆脱政治蒙昧的集体大逃亡,这个民族的一代学人把求知的视域不约而同地集体投向西方,力图以寻找欧美异域的那些思想来回应淤积于中国本土的文化问题。从70年代末至1985年,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心理学及文学艺术理论著作被急迫地翻译为汉语译入语。时至“八五新潮”的崛起,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批评与理论三种维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及其先锋派思潮于中国在地学人接受的思想急迫上,已酿成不可阻挡之势,招摇为一种盲从鲁迅“拿来主义”的照单全盘接受,在相当的程度上,形成了西方现代文学艺术思潮在中国本土的先锋化与合法化接受,“保守”与“保守主义”是那个时代学人耻于被粘贴的标签。
我愿意借用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中那句著名的题词以接续我的表达:“1985”,是一个思想者与激进者崛起的年代,一切如此让人留恋。在“伤痕”时期,他们曾是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而在历史的转型中,他们又成为了引领思潮的先锋一代,也成为了过于放纵的一代。他们喧哗且躁动于文学艺术的公共广场,集体狂欢着,无疑,那是一个思想协同激情燃烧的岁月。非常令人深思的是,王安忆与韩少功笔下的荒诞涂染着寻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愚昧且落后的顽钝性,而刘索拉与徐星笔下的荒诞则蒸发着受西方现代派思潮影响的先锋性,而在本质主义上,无论是中华民族寓言式的顽钝性之荒诞,还是西方现代派的先锋性之荒诞,两者藉凭于中国与西方不同区域文化价值观念的书写,合力达向的是一个共谋的思想目的——“八五新潮”。在某种程度上,“1985”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铸就了那个书写文学艺术宣言的激进年代。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小说的虚构世界与现实历史之间所存有的那种暧昧性指涉或悖反性指涉的隐含关系。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英国左翼作家,1949年,他推出了自己的反乌托邦经典小说《1984》(1984
);乔治·奥威尔以其政治寓言式的书写,在小说中虚构了于1984年瓜分世界的三个极权主义国家,而1985年,则是中国新时期文学艺术史程上一个能够自由且接续地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异化、人性与人道主义的自由时代。乔治·奥威尔为“1984”的极权主义所虚构的政治寓言,似乎于阅读的逻辑上在遭遇中国的“1985”时破产了。无论如何,“1985”,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彰显为一个显赫的时代性专业术语,从当下看,“1985”在教科书中以专用术语的书写符码记忆着那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时代。
三、“八五美术新潮”及对中国画的否定与守望
然而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在于,30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完全没有把“1985”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现象来给予整合性的全面研究,并且在偶然的片断性回顾与讨论中,相关学者总是因为学科过于精细化的分类,把“1985”割裂为一个个破碎的学科分类空间,即文学、美术与音乐等均从自己所属的学科孤立地言说“1985”。这种学科割裂式的破碎性讨论,把新时期文学艺术在合力中所推动的整体历史发展解构为学科碎片,散落涂地。无疑,这是非常可惜的!还原历史地讲,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与舞蹈作为文学艺术的总类,它们是一个维系紧密的审美共同体(aesthetic community),从伤痕文学与“《星星》美展”肇事以来,文学艺术同步深度地推动了“1985”,尤其是文学与美术的共谋。在“文革”终结前后的那个历史时期,一批蛰伏于民间的思想者为国族的命运在思索着,他们以文学艺术爱好者的神圣名义走到一起来,有思想且无纲领地集结在一起,激情于诗歌、小说、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自发地以觉醒者的姿态躁动着。
在那个历史时期,他们的行为虽然只是蛰伏于民间社会的微不足道,但他们的思考焦虑于“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却让他们显得格外的神圣。究极而论,民刊《今天》与“《星星》美展”就是由这批蛰伏于民间社会以文学艺术为生存信仰的觉醒者共谋发起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回到《今天》的创刊号,去阅读北岛、芒克与黄锐等在其首页《致读者》中所表达的宣言,他们使用的一个重要术语就是“文学艺术”:
“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
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与黄锐等在北京三里屯亮马河畔的一间民宅里共谋创刊了民刊《今天》,当代文学批评界妇孺皆知北岛与芒克,但很少人知晓黄锐也是《今天》创刊的主谋者,黄锐本身即兼有画家与诗人的二重身份。1979年9月27日,黄锐、马德升、曲磊磊、王克平、严力、阿城、李爽、薄云、杨益平等又共谋了策划了“《星星》美展”,黄锐既是手刻油印版《今天》创刊号套色封面的设计者,又是“《星星》美展”的首席主谋者。用黄锐的话讲,《今天》的诗歌朗诵会与他策划“《星星》美展”有着直接的内在精神关系。关于“《星星》美展”受限后的活动,诗人北岛又是率先走在那些画家前面的引路者,而当代文学批评界也很少有人知道“三王”的作者钟阿城又是“《星星》美展”的策划者及参与者之一。我们应该来阅读一下当时钟阿城在《〈星星〉美展部分作者谈艺术》一文中的表述: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涉及艺术了,活活[编者按:应为“生活”]对于我曾经是如此沉重,而且是整整的十年。
可恰恰是生活,真实的生活,使我觉得我必须用我的画笔说话。深刻的艺术产生于真实的生活。苟有隐瞒,画笔就会变成煮熟的猪舌头。
我的笔顺着那些被阳光、被风、被尘土、被劳动、被泪和汗水弄得粗糙的表面刻划[刻画]。我希望纸上出现的是灵魂,是那些被侮□与被损害的灵魂,那些乐观的灵魂,是那些善良的灵魂。
值得提醒当代文学艺术界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天》的第6期。这些珍贵的文献被尘封得太久了,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我的论文书写中给予引用。当代文学批评界无论怎样也不会想到那个年代的阿城首先是一位画者,他早期是用画笔来排遣整整压抑十年之沉重的心绪的,而发表处女作小说《棋王》则是1984年的事了。
既然我讨论的是上个世纪70年后半期冲破“文革”铁幕觉醒而来的民间文学艺术行为,我就应该回避使用在当下流行的诸种“后主义”(postism)理论等给予过度性诠释,而使用与“文革”前后那个历史年代在学理上有所互涉的理论思想来给予分析,即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市民社 会(società civile/civil society)与文 化霸权(egemonia culturale/cultural hegemony)理论。书写到这里,我们必然首先涉及到了一个翻译的问题。我们在把意大利语“società civile”转码为汉语译入语概念时,至少可以有四种翻译:“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或“民间团体”,关于英文“civil society”的翻译也是如此,因为两者均属于印欧语系下的同源语言。
葛兰西是意大利的作家及政治理论家,“società civile”这个概念是他在《知识分子与文化组织》(Gli 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
)一书中最早提出的,后来他在《狱中书简》(Lettere dal carcere
)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述。谙熟葛兰西理论的学者均知他在国家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给予了很高的期待,相对于保守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把行使文化霸权的知识分子在阶层的属性上定义为有机知识分子(l'intelletuale organico/organic intellectual)。在《葛兰西狱中札记选集》(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章中,他郑重地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deputy),以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政府的下属功能。”并且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在民间组成的社会团体即隶属于市民社会——“società civile”。他继而提出这种市民社会是一个“超级结构性”(due grandi piani superstrutturali)的存在,有机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化霸权的组织者与决策者。当然现在看来,这只能是葛兰西在那个历史时期作为理论家所构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他本人作为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在监狱中囚禁而死的。仔细地阅读葛兰西,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知识分子的市民社会与文化功用的论述又持有诸种质疑,《知识分子》一章记录了他对知识分子及其团体性质所投射的疑问:“知识分子是一个自治(autonomous)与独立(independent)的社会群体吗?或者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拥有自己特殊的或专属的知识分子分类吗?由于知识分子不同分类形成的真正历史过程至今依然呈现为多种不同的形式,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随后,葛兰西对自己的设问给出了长篇的回答,并且指出:“因此人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功能。”其实在中国,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非常有趣的是,从“società civile”或“civil society”翻译过来的四种汉语译入语概念虽然都可以成立,但是,在汉语概念的字面书写上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异性修辞表达的意义,学术思想的构建在出场于书写的修辞择取上从来都是如此敏感。倘若把“società civile”翻译为“公民社会”,好像这个概念在汉语语境下有点装腔作势,一般不被大众市民所使用。
在本篇文章所讨论的话题与语境下,我愿意把葛兰西讨论的“società civile”这个概念借用于汉语语境下,为我修订性与丰富性使用。我把这个概念翻译为“民间团体”,以指认《今天》与“《星星》美展”那批民间知识分子的市民社会功能。在理论诠释的一个维度上,他们的存在及其社会身份不同于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所讨论的“die Zivilgesellschaft”(市民社会),其更贴近于葛兰西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所阐释的向度。虽然他们只是民间知识分子,不是黉门知识分子,但他们更是以觉醒者的姿态与社会总体结构发生交往。在社会阶层的身份上,他们是具有意识形态批判性的有机知识分子,然而他们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更谈不上是文化霸权的决策者与行使者。所以他们只能借驻于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领域,以集结为一个具有思想同质性的民间团体,并且相当松散,全然没有葛兰西所言说的“超级结构性”。其实,我们转换一个修辞表达,他们就是一个松散的市民社会阶层。从团体的社会性质上来分析,这种由觉醒者自治且独立源起于民间的文学艺术行为,充其量也只是有组织而无纲领的“società civile”,其不可抵抗的宿命必然是瓦解于成员内部的无休止争吵,最终分道扬镳。但是无论怎样,《今天》与“《星星》美展”的那些人与那些事确然在历史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踪迹,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可歌可泣。
2007年,陈丹青在《仍然在野:纪念星星画展28周年》一文中有着赤裸到原始的真切回忆,他把“民间”称之为“在野”以反讽体制内的画家,他的情绪与修辞依然在未老的亢奋中充斥着这位画家习惯于咆哮的野性张力,并且陈丹青又理性地指出:“文革后首次在野画展不是星星。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黄浦区文化馆举事的《十二人画展》才是头一回。”栗宪庭也多次确认了这一点。确然,从上海的《十二人画展》与北京的“《星星》美展”到弥漫于全国的“八五美术新潮”,新时期当代中国美术界发生了太多的事件,其悉数记录于高名潞等撰写的《'85美术运动》与《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两部读本中,当然,还有吕澎、易丹的《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等。
就“新潮”与“八五美术新潮”这两个术语的率先使用,栗宪庭在《85美术新潮——栗宪庭访谈》曾给出过确定性的回忆:“‘新潮'一词最早是刘骁纯说的,他连着几篇用了‘青年美术新潮'。后来惯称叫‘八五美术新潮'。”我必须在当代文学艺术史的发展系谱上确定地指明,“八五新潮”这个术语是由当时的美术批评界主将刘骁纯、栗宪庭、高名潞等先于当代文学批评界提出且给予论述的,从新时期当代文学艺术史料学所存有的文献来考据,“八五美术新潮”是先于“八五新潮文学”所使用的一个术语。并且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怀疑与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全盘接受这两个维度上,冠名于“八五美术新潮”之下且肇事的那些人与那些事,统统喧哗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偏激。
高名潞在《'85青年美术之潮》一文中曾记忆了“1985”的思潮场景:“八五年是艺术观念更新口号最为强烈的一年。这是中国艺术面临如何走向现代的一种思索,它首先出现在理论和评论界,随之画家(包括老、中、青画家)也为之倾心。”毫不夸张地说,在“1985”前后,汉语中国本土的文学艺术空间几乎沦陷为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及诸种先锋思潮的异域实验工厂。在当代汉语本土文学艺术界,从“伤痕文学”到“八五美术新潮”,美术创作及其批评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接受,是走在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前面的。事态还在继续发酵着,李小山在《江苏画刊》1985年第7期发表了那篇全盘否定中国画的檄文:《中国画之我见》。至此,李小山事件把裹挟在“八五新潮”或“八五美术新潮”中热议的反传统文化话题推向了极致。
那年,还是“1985”!
当年,李小山是南京艺术学院国画系的硕士生,李小山可谓是祸起萧墙的中国画专业的叛逆者。关键在于,一位专攻中国画的硕士生,相当专业地全盘否定中国画,这需要一种怎样的智慧与勇气?!
从李小山在这篇文章肇事的第一句,我们即可以一眼抓取那句偏激的表达——“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其实,这种偏激观念的持有并不是李小山个人的自作多情,而是喧嚣于当时中国美术界的一种“时髦说法”:
“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这个说法,成了画界的时髦说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这个看法的人是真正这样来认识中国画现状的。事实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些。
确然,事态发展至1985年,新时期美术界对中国画及其书画大师进行袪魅(disenchantment)的批判性言说已蓄势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喧哗。我想从那个历史时期走过来的学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与舞蹈学院系科分类的等级差异感:学油画的在感觉上一定优越于学国画的,吹长笛的一定高于吹竹笛的,学中国民族舞的不如学西方芭蕾舞的。李小山对中国画及其书画大师的袪魅性批判是相当意识形态化的:“传统中国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它根植在一个绝对封闭的专制社会里。”把“中国画”与“封建意识形态”链接在一起,这是李小山的批判逻辑,他的表达在修辞上依然残存着“文革”时期的政治术语色彩。然而,李小山在《中国画之我见》一文中指出中国画在笔墨观念上的保守,这的确是一种偏激的思想闪光:“可以说,中国画笔墨(由于强调书法用笔)的抽象审美意味愈强,也预示着中国画形式的规范愈严密。随之而来的,也就使得中国画的技术手段在达到最高水平的同时,变成了僵硬的抽象形式。这样画家便放弃了在绘画观念上的开拓,而用千篇一律的技艺去追求意境——这是后期中国画中保守性最强的因素。”
“1985”,这是一个国人蒙昧于长久的意识形态封闭,渴望在改革开放中拓新生存观念的年代,因此,矫枉过正地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以影射“十七年”与“文革”,及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成为共和国历史在这一年所遭遇的必然。“八五新潮”是新时期文学艺术思潮走向灿烂的一年,追求新的美学观念成为学人呼喊的时代性口号,然而仔细地考量,我们又不难发现,这是新时期文学艺术界一次源起于民间且被体制放纵的合法化“洋务运动”。从骨子里讲,我很欣赏“1985”的李小山,无论怎样,他搅动了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史。
述评到这里,还是让我们的思路回到《守望丹青》及其作者那里去,回到邓明在1985年介入编辑出版《黄宾虹画集》与《黄宾虹书简》时所形成的视觉观念那里去。在“八五新潮”或“八五美术新潮”狂飙突进的激进观景下,邓明没有随波逐流,在李小山们宣称“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他却生成了以中国古人笔墨为黄宾虹及中国水墨书画家造像的视觉观念。这,确然是另外一种独立自由的处世姿态。关于这一姿态,我们至少可以给出如此以下的价值判断:一是在不识时务的反潮流中呈现出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二是对中国画的传统笔墨观念给予公然的守望。然而,历史的发展要比天真的知识分子们想象的复杂得多,30多年过去了,邓明在“1985”所持有的保守主义姿态,在视觉艺术的美学观念上则转型为一种当下的前卫。
历史就是在如此的反讽中大浪淘沙,面对着历史只有历史地评判一切!
四、历史的周期率与“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
历史的钟摆总是在回荡往复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呈现出历史的周期率,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文革”终结前后于坊间私下传递的那句表达:“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在延安曾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向毛泽东请教王朝兴替的历史周期率现象。我们知道,黄炎培的请教本身所依据的就是中国夏商时期的一个历史典故,其典出于《左传·庄公十一年》的“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无论夏禹和商汤怪罪自己,还是夏桀和商纣怪罪他人,历史被史学理论总结为就是如此宿命般地在周期率中往复循环地敷衍着。这是一个曾引起中西历史学界所讨论的重要历史现象。当然,黄炎培向毛泽东设问的是一个大历史的问题,而文学艺术史的发展也存在着自身所不可规避的历史周期率,这是一个逻辑从属性的小历史问题。
倘若我们以“八五新潮”为时间坐标系,向其前后推至若干年,我们可以清醒地看视到在十年“文革”终结后,历史转型生成了一个十年新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思潮轨迹。而时至1989年,中国再度遭遇了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也恰然在这个历史转捩点之后,曾在80年代高涨的人文思潮悄然散尽,被90年代迅速崛起的经济大潮在摧枯拉朽的裹挟中所全然取代,中国开始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与资本快速积累的时代。这无疑是一种在人文思潮退却中的前行,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文学艺术作为小历史,其必然是依附于大历史而行动的。
90年代裹挟着经济大潮到来,让沉湎于审美的感性中诉求思想深度的文学艺术及其批评遭遇了不情愿的重创。客观地评判,文学艺术及其批评失去了在80年代的轰动效应后,其不再执著于对异化、人性、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与自由等话题的深度性探索,放弃了以讨还真理从而彰显创作主体与批评主体的哲学性思考,迅速跌向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平面化与碎片化,把压抑在人文精神诉求中的现代主义焦虑,释放为一种对浅表形式观念的炒作性诉求。尤其是美术界的当代艺术更是惶然放弃了对人文深度的追问,伺机而起,把攫取资本的积累作为衡量作家作品成功的唯一性目的。
在这里,我不想展开地论述从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期所沉落的那些历史细节,一切都过于碎片化了,不堪收拾。但是我至少可以给出三种简约的历史性判断:一是80年代的人文中国转型为90年代的经济中国,资本成为文学艺术追逐的风向标,尤其是视觉艺术;二是在对西方哲学、美学与文学艺术思潮的接受方面,人文学界依然持有的是全盘拿来主义的姿态,只是汉语本土文学艺术及其批评界在80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接受,转型为在90年代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炒作;三是学界把文学艺术及其批评高涨的80年代定义为新时期(new period),而把文学艺术及其批评转型后的90年代定义为后新时期(post-new period),随即在学界也生成了一系列同频共振的术语,以标识着90年代这个由经济与资本操控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如后新时期文学(literature of post-new age)、后新时期艺术(art in post-new era)与后新时期文化(culture in post-new period)等等。当然,术语的背后是思潮在行动,我们不可能给虚无的历史贴上一个空洞的标签,所以新时期与后新时期的代际性差异也就如此被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界分开来了。历史在时间的发展逻辑上又开始了另一个新10年的轮回。
让人困惑与深思的焦虑是,往日喧哗且躁动于80年代的那些广场公知,在遭遇90年代经济大潮的席卷时,被资本冲击得茫然不知所措;同步生成的逻辑是,文学艺术及其批评在美学的观念上也遭遇了最大的颠覆性转向,历史的钟摆在回荡往复中,让得到的失去,让失去的得到,只留下让弄潮公知惘然若失的伤感。不错,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当代文学艺术及其批评的小历史现象,虽然是从属性历史现象,但其在本质上则是对大历史的背景性投影。
再三强调的是,邓明生成用黄宾虹的笔墨为黄宾虹造像的观念是在1985年,较之于上述我所描述的关于“八五新潮”前后若干年的历史背景,邓明在当时所持有的确然是一种守望与承递传统的绘画观念。思考的逻辑行走到这里,我们不妨撮录及阅读李小山在《中国画之我见》中的一段表达,那就更有意思了:
传统中国画发展到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的时代,已进入了它的尾声阶段(人物、花鸟、山水均有了其集大成者)。尽管当代中国画家并没有放弃继续在中国画园地的辛勤耕耘,但所获的成效甚微。当我们看到一大批富有才能的艺术家还在捍卫显然已经过时了的艺术观点,并且的确在实践中浪费了那么多的精力时,只能深深为之惋惜;当不少自认为“清高”的国粹派画家——特别是某些名重一时的老画家——以轻蔑的目光投向现实的艺术革新运动时,我们只认为这不是清高,而是糊涂和懒惰。不清不高,企图充当现代堂吉诃德角色的人,只能贻笑后世。席勒说,危险的威胁,是透顶的庸俗。而最可恨的庸俗是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艺术的实质就是不断地创造,否认这一点,就将使艺术变成手工技艺和糊口的职业。
在这篇檄文中,李小山至少对八位以上名重中国美术史的大师给予了偏激的批判与否定,如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傅抱石、李苦禅与黄胄等。然公允而论,李小山的一些观点即便是在当代艺术恶性泛滥成灾的现下来看,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历史绝然不是由一种人、一种声音、一种立场与一种文化观念给予操控性推演且书写完成的。恰然是在“1985”,当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出版《黄宾虹画集》时,在视觉的设计上定位于一种大型画册的版式,并且每张大尺寸的反转片都拍摄得如此精美,这让范志民与邓明如同面对原作一般,老少两代美术编辑同时身临其境地进入了黄宾虹的水墨气象中,震惊不已。
我曾问过邓明:“你当时对‘八五美术新潮'及李小山的《中国画之我见》是否有着深度的了解?”邓明回答说:“那是我经历过的时代,当然非常了解,我不同意李小山的观点,我依然钟情黄宾虹及中国传统水墨的气象与意境。‘守望丹青'是我始终坚持的观念。”现下的青年学者很难理解,在“八五新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性否定及全盘西化的一边倒中,邓明对传统国画观念的守望必然会被定性为一种不识时务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黉门知识分子,大都是在极端的敏感中持有自己的尊严,且爱惜自己的羽毛,被定性为“保守”,普遍地来讲,这是学界任何人不愿承担的名誉代价。我始终认为,李小山的偏激是“八五新潮”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应势产物,从事隔30多年后的当下给予理性地评判,其恰然是顺应了那个时代总体思潮的一种正常性偏激。在那个时代,不偏激反而是不正常的。但是,随着历史的逝去与发展,历史的钟摆周期性移位了,评判历史的价值视点转换了,邓明在那个时代对传统国画观念的守望,表现在当下,其恰恰可以被诠释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偏激与前卫。人,面对着历史永远是一个被动的价值担当者,历史的周期性更替可以让真理变成谬误,也可以让谬误变成真理。历史对人及事件的评价从来就是如此,这也是不可规避的历史周期率。
邓明在1985年生成了这一水墨观念后,时至1993年才得以在践行中画了《黄宾虹先生像》,其中除却邓明肩负的出版任务与行政事务繁忙之外,更多的是,邓明又沉潜了8年的时间,全方位地走进中国水墨丹青史及其相关文献中,其中包括深度地阅读黄宾虹与体验黄宾虹的意境,最后完成了以黄宾虹的水墨笔法及其气象为黄宾虹准确地造像。我特别注意到邓明书写于《守望丹青》之《后记》的开场白:
予幼习丹青,性亲写意。好奇黄宾虹学说,试以五笔七墨为图其像,不意一稿而成,乃知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可行。我对邓明在《守望丹青》中所画的从沈周至黄胄一百位明清近现当代以来的水墨书画大师的肖像,一一进行了仔细的品鉴,我个人始终认为,其中黄宾虹的水墨肖像是画得最好的一幅。在文学艺术创作的空间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往往第一个作品恰恰是作者最成功的作品。
邓明完成这幅《黄宾虹先生像》后,其思路并没有终结在黄宾虹那里,他随后接续形成了以中国水墨笔法为一系列中国水墨书画家造像的观念,即如邓明所言:“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可以说,退出“1985”,站在1993年中国本土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景观下来看,这居然是一种相当前卫的美术观念了。“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的观念形成后,邓明并没有立即动笔进行一系列水墨书画大师造像的践行,而是再度沉淀了十几年,也就是在2009年退休后,他又启动了这项工作。至于他完成第二幅陈洪绶的水墨肖像作品,历史已走到了2010年,用邓明的话说:“正式启动‘守望丹青'的创作是2010年,一下子画了陈洪绶、徐青藤、八大山人、石涛、虚谷、蒲华、吴昌硕与齐白石等八位,他们都是早就想画,且笔墨特征比较明确,容易把握的几位大家。”
全球化的21世纪是一个操控于大数据的网络时代,不幸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也生成了一个求数量及其背后的资本积累而不求质量的快捷年代。客观地讲,无论是对一位文学艺术家来说,还是对一位学者来说,人,一生做不了多少像样的事。尤其是对那些专注于精品推出的文学艺术家与学者而言,这更是如此。一位作家一生硬性地挤出几部或十几部小说,一位画家一生可以涂抹出几百或上千幅画,一位学者一生用电脑码字码到著作等身,我必然怀疑其质量的伪劣性。人的才智与精力都是一样有限的,谁也比谁高明不到哪里去。邓明是在“八五美术新潮”时期生成了“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的观念,而一部228页的《守望丹青》直到2017年才杀青正式出版,时间整整过去了32年。需要补上一句的是,其中还缺失他抄录自己一百首画外“题画诗”的书法作品。为什么《守望丹青》耗时32年才得以问世?我想有些细节及所经历的时代背景还是值得在此谈一谈的。
时值2010年,邓明投入全身心精力来完成这部《守望丹青》时,关于这部画册于体例上的构成已经在他的思考与观念中完全成熟了。据邓明回忆,2011年1月21日,他去画院交徐青藤与陈老莲的造像,以参加本年度的上海中国画院迎春画展,在画院签收时,他第一次明确地注明系列作品的题目为“守望丹青”。而实质上,“守望丹青”这四个字在他的观念中已酝酿了很久,其思路可以追溯至“1985”。我一直在想怎样给《守望丹青》这部文本的体例构成下一个定义,由于这部文本是在跨界中完成的,其艺术、美学、文化及学术的含量多元且丰富,涉及到了中国画、中国书法、中国美术史论、诗歌创作及“以诗论画”等美术批评的综合性元素,我想在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知识的意义上,其应该可以被称之为一部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关于这一点,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多个层面来分析这部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及其博物学内涵的价值所在。
五、《守望丹青》和图像时代契合的美学观念
《守望丹清》遴选了从明代、清代、近代、现代至当代的一百位中国书画家,如从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仇英、八大山人、吴昌硕、康有为至黄宾虹、齐白石、刘海粟、李可染、启功、石鲁、吴冠中、程十发、黄胄等,其可谓都是名重中国书画史的大师。在表现的视觉观念上,邓明是以中国水墨笔法及其意象为从明代至当代的一百位中国书画大师造像。然而倘若我们仅仅把邓明的意图与行为理解为单纯是“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那就小视了邓明。就我看来,邓明在观念上是要完成一部表现中国书画大师的水墨丹青视觉图像史。书写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度反思一下历史在这一时期转型的背景。
我曾在上述指出,80年代的人文中国在历史的形质蜕变中转型为90年代后新时期的经济中国,而历史走向21世纪,我们迎来的又是一个新10年协同资本发展的高科技中国。我依然记得千禧年前后若干年聒噪于人文学界所讨论的那些命定于“postism”下的主流话题,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工业文明与后殖民批评等,其中一个热点话题就是焦虑于后现代工业文明打造的图像时代的到来,广场公知惟恐失去印刷时代的守成性词语及其背后蓄意掀动的意识形态冲突。1989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一书被翻译为汉语,这部读本一时曾在90年代中国本土学界产生了巨大的渗透性影响。透过丹尼尔·贝尔理论描述的图景,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文学者似乎都获取了这一种感受:全球化的态势协同于资本的全球化弥漫于当下,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在逻辑跨越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不可遏制地向中国本土漫延,经济、高科技协同资本同步发展,所有的迹象让国民大众必然面临着资本运作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国际互联网与新媒体铸成了大数据时代,国民大众在遭遇消费社会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应对海量信息的压迫,开始娱乐性与习惯性地接纳了把视觉读图的简单方式作为提取生活信息的快捷通道。知识分子在理论上的喧哗与国民大众在日常娱乐生活中的媚俗性趋同,无奈,图像时代协同着消费文化来临了!特别值得学界注意的是,理论跨国族的翻译与借用,往往会产生一种悖反的效用,在理论的取向上,美国的丹尼尔·贝尔是一位从左翼知识分子转向文化保守主义的介入性公知(interventional public intellectual)。非常有意思的是,面对图像时代的到来,黉门知识分子像以往每一次面对历史参加文化运动的站队一样,自然划出了两种人:一种人是保持广场公知的介入性批判,他们撰文对图像时代及其消费社会的到来进行了理论上的抵抗与批判,守护自己从“八五新潮”以来所宣讲的人文精神。我们都不会忘记,在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后新时期,汉语本土人文学界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学者关于图像时代讨论的理论著作及文章,并且本土相关学者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以批判图像时代及大众消费文化什么的。另一种人则是顺应“图像时代”及其消费社会的到来,相关学者不失时机地接受了历史潮流的蜕变,群起而应之。
令人深思的是,早在1988年4月,于新奥尔良“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Featherstong)提出与讨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个话题,而时隔十几年后,后新时期的相关中国学者把这个话题带入汉语学界,以庆典图像时代的到来,从而讲唱大众文化消费审美心理的合法性与普世性,以消蚀纯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等级距离什么的。关于这个话题于中国本土学界的那段热议,我在此无意多论,只想陈述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对学术讨论介入的一波风潮。每一个时代总会承奉一批应时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相关学者不失时机地编纂了多部关于中西文学史、中西历史、中西哲学史、中西艺术史与中西电影史等的图像读本,究其目的而言,他们恰如其分地配合图像时代的到来,是为了把高深的学术研究著作降解为大众性普及读物,当然,在降解中其迎合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媚俗性阅读也必然带来了出版码洋的增加,这也必然同步带来了资本运作的附加值。
我想指出的是,历史在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后新时期转型了,不可遏制地遭遇了普世性的图像-资本时代,从而构成了绝然不同于“伤痕”“反思”“寻根”到“八五新潮”时代的文化形质。学界在理论的需要上一厢情愿所定义的那个后新时期果然且彻底到来了。让我们的思路再度回到《守望丹青》的绘画观念那里去。我们不能不承认,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评判,过来后站在当下的立场看视,邓明在“1985”生成以中国水墨笔法为中国水墨书画家造像的观念,是非常前卫的,而恰然又是这一观念让邓明接续生成了要完成一部为一百位中国水墨书画大师造像的水墨视觉图像史。在这里,我有必要做一个解释,不同于上述所提及的中西文学史等媚俗性图像读本什么的,《守望丹青》是一部以中国水墨笔法及其意象为中国水墨书画大师造像而完成的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其恰然是在美术领域生成的一种崭新的视觉艺术史观念,这部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不仅贴合于图像时代的到来,在本质上,又不同于把中西文学史等降解于图像阅读的媚俗性。的确也是如此,我们不无遗憾地感觉到,图像时代的到来让在80年代曾经引领思潮的文学彻底边缘化了,而美术这类视觉艺术则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审美表现形式。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一直深陷于一个理论的误区,相关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当代历史只是在走进了中国学者理解与解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时期,才获有足够的理由讨论视觉文化与图像时代的那些问题。实事上,中国汉语学界关于视觉文化与图像时代的讨论也的确如此。其实,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专设《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一章,他恰恰是讨论西方在现代主义时期所遭遇的视觉文化与读图时代的那些现象。准确地分析,西方与中国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从现代主义文化向后现代主义文化过渡的历史进程。在西方,从现代主义文化向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过渡经历了一个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渐进的有序发展逻辑,其背后的资本运作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也同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递进性过渡历程。而“文革”终结后的中国门户开放,对西方资本经济与工业文明的接受,则表现出一种因长期封闭而解禁后的饥不择食,因此文化形质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在中国本土来得太快且过于密集,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学术理论上的过度性推动,以至于在“八五新潮”时期,弥漫学界的现代主义思潮还没有来得及让中国知识分子过把瘾,历史就在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与接受中,迅速转型为后现代大众文化及读图时代的商业性消费社会。
从1977年“文革”终结至2017年,40年过去了,凡是经历过这40年历史的“50后”人文学者,都会不胜伤感地遭遇这样一种失落的现象且被其触疼:在图像-资本时代,作为美术的视觉艺术——当代艺术于审美的形式上碾压且取代了当代文学,成为后新时期历史的主流艺术表现形式;在80年代一路引领时代思潮的当代文学批评也被彻底地边缘化了,失落了在审美意识形态领域产生轰动效应的话语权。读图-资本时代抛弃了当代文学,同时,也抛弃了当代文学批评!关于这一现象,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视觉文化》一章中也有所论述:
在高级文化(high culture)范围内关于大众社会影响的辩论,忽视了这样一种理解——因为这种辩论是由人文主义者形成的,他们的高级文化概念主要是由文学(literature)构成的——所以这种辩论无法面对大众文化之本质最为重要的方面,即作为显在事实的一种视觉文化。
事实上,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蜕变为一种视觉文化(a visual culture),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a print culture)。
在这里,丹尼尔·贝尔给文学与视觉文化划分了一个等级序列:文学归属高级文化,而视觉文化属于大众文化。而我想指出的是,丹尼尔·贝尔所讨论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时期的视觉文化,讨论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时期文学作为高级文化在大众社会边缘化的现象。关键是历史及其文化形质在转型换代的时期,其必然要淘汰一种守成的审美表现形式及审美风格,而选择另一种更贴合于这个时代的审美表现形式及审美风格。的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与审美风格,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无论怎样,在图像-资本时代,当代文学失宠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周期率。
问题是,在这40年的前行历程中,中国的资本经济、科学技术与文化思潮的发展起跑得极为迅速,并且过度密集,呈现在文学艺术领域,诸种躁动的思潮与视觉观念也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再或各领风骚三五天。尽管是那些短命的思潮与视觉观念炒作者,他们也要竭尽相互轻蔑之能事刷一次瞬间的存在感,现下碾压当代文学的当代艺术就是如此,其流派林立却无持久的立场。韩愈在《原道》嘲讽了一种“入主出奴”的宗派投机者:“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而邓明关于“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的观念从生成到完成《守望丹青》,却坚守了32年。客观地讲,我们仅从美术的表现技术上来评判,无论是中西绘画还是中国书法,现下在技术上表现还不错的人的确是较多的(当然平庸者更多),但大多数书画人还是捆绑于“艺”,在骨子里是有技术因无学养而缺失灵韵(Aura)的匠气十足者,他们成不了艺术家,充其量也就是艺人而已。历史已经走到了应该给“艺术家”重新下定义的时代了。而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恰恰不在于“艺”——技术,而在于灌注艺术作品中经得起历史检阅的厚重学养及不可复制的、此时此地的唯一性灵韵及其气象格局。
邓椿是宋代的藏书家与画论家,其实早在那个时代,邓椿于《画继卷第九·杂说·论远》中对此即有着精辟的论述:
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著意。张彦远所次历代画人,冠裳太半。唐则少陵题咏,曲尽形容;昌黎作记,不遗毫发。本朝文忠欧公、三苏父子、两晁兄弟、山俗、后山、宛丘、淮海、月岩,以至漫仕、龙眠,或评品精高,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难者以为自古文人何止数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将应之曰:“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
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虚深鄙众工,谓“虽曰画而非画者”。盖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而若虚独归于轩冕、岩穴,有以哉!
多年来,中国美术史论界在讨论中国书画与学养互为浸润的逻辑关系时,总是相互照抄地搬引邓椿在此表述的第一句“画者,文之极也”,谁也不愿切实地翻阅《画继》这部原典,让自己从此句之后深入地阅读下去,以获得更多的启示。事实上,邓椿关于画与文之关系的精辟论述,恰然在其后两大段的完整语境中,这两大段文献为中国美术史论界遗失得太久了,我愿在此把邓椿的完整语境给予引出,以飨读者。中国美术史论界在撰写论文及引用文献时,应该再讲求一些学养。邓椿对张彦远于《历代名画记》“所次历代画人”多为衣冠贵胄的官宦士绅,给予了鄙视,相反邓椿在此论画所举诸家皆为唐宋两代之文学大家,且以为“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这就是张彦远与邓椿在格局和品味上的差距。我特别建议当代中国美术界相关画人与画评人能够放下架子,切实地品味一下邓椿的此句表达:“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学界基本不是如此。邓椿在这里讲求的“传神”与“气韵”即是因学养而浸润于绘画作品中而超拔脱俗的唯一性“Aura”——“灵韵”。
在这里,我认为特别有必要在艺术社会学的理论上递进地补谈一点。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德国哲学家与艺术社会学家,“Aura”是他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社会学三论》(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Drei Studien zur Kunstsoziologie
)一书中所操用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我们可以把德语“Aura”这个概念的语源追溯到拉丁语的“aura”(breeze, wind, the upper air),还可以再往上追溯至古希腊语的“αǔρα”(breeze, cool breeze, air in motion)。从上述两个古典词语的英语释义,我们可以见出“Aura”在词根的原初意义上与“气”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传统上,“气”是一个抽象的精神概念。需要提及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概念,“Aura”是19世纪由英国神父查尔斯·韦伯斯特·李德彼德(Charles Webster Leadbeater)在讨论宗教唯灵论(spiritualism)的问题时给予普遍性使用的,隐喻圣像的光晕,后来“Aura”被艺术批评与理论借用过来,以指涉蕴涵于艺术作品中种种精深微妙的审美精神。无论是德语、英语还是法语,“Aura”都是从拉丁语与古希腊语所借用过来的一个词语。实事上,“Aura”的修辞本身就是一个敞开的概念,在西方也被不同领域的学者在修辞的意义上赋予细微的差异性以解释丰富的精神现象。中国学界把“Aura”翻译为汉语译入语时,绝对不应该认定只有一种固定的译法。如果相关学者认为“Aura”只有一种规定性的译法,并偏执地视其为正确,在学理上,这不仅是封闭了“Aura”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内涵,同时,也封闭了蕴涵于艺术作品中魅力无穷的多元审美精神。如邓椿所讲求的“气韵”是就“Aura”的一种现象,而“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的艺术观念恰然就是沉淀于《守望丹青》这部文本中的“Aura”,这里的“Aura”在汉语修辞上最为恰切的翻译应该是“灵韵”,而不能翻译为“气韵”。也就是说,“Aura”的翻译也必须视其汉语译入语的修辞目的而定。
再让我们的讨论于逻辑上链接到本雅明那里去。本雅明在讨论以技术工艺对原创经典艺术作品进行复制时,涉及了其中灵韵凋谢的讨论:“人们会通过灵韵的概念关注到艺术复制品所失去的东西,并且会说:在艺术作品技术工艺复制的时代所凋谢的,正是艺术作品的灵韵(Aura)。”简而述之,本雅明把原创艺术作品在特殊场域的此时此地所表现的唯一性存在诠释为灵韵,认为以技术对原创艺术作品进行完美复制的工艺品,其中必然消蚀了原创艺术作品唯一存在的审美意义与趣味,即灵韵的凋谢:“即便是在最为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有一种元素也是缺失的:即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性——它是一个特殊场域中的唯一性存在(einmaliges Dasein)。”在此,我无意于专论本雅明的灵韵及其相关艺术社会学理论,我的意图旨在借助本雅明的“Aura”改写且引申出我在当下汉语学界的思考。
事实上,被技术工艺所复制的艺术品——工艺品在进入资本流通市场时,其原创必然都是人类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在现代时期还是在后现代时期,被技术工艺批量复制品的原创经典作品也必然是经过资本市场所拣选的,那些庸常之作是不会被技术工艺所批量复制而进入资本市场的。所以那些庸常之作尽管是原创作品,但其本然就是缺失灵韵的,所以没有被技术工艺所复制的价值。我们从本雅明的艺术社会学理论进行逻辑反推,“Aura”必然是指涉原创经典艺术作品在特殊场域的此时此地所表现的唯一性审美意义与趣味,灵韵是原创经典艺术作品的唯一审美本质属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审美的唯一本质属性上秉有灵韵的原创艺术作品能够成为人类美术史上的经典。那么,当下中国美术界又有多少作品具有可能成为原创经典的唯一性灵韵呢?
需要申明的是,我无意于讨论《守望丹青》及其水墨书画的技术性问题,我只是希望能透过这部文本及其作者反思中国书画界的整体学养及博物学知识结构的问题。让我们的思考再度走下去。我想郑重指出的是:邓明在“1985”生成“用黄宾虹的笔墨观念为黄宾虹造像”,到随后自觉形成“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的视觉观念,这一观念从经历“八五美术新潮”到读图-资本时代的当下,从保守到前卫,其前后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而这一切是在32年的历史发展中被证明的。这,对于一位书画家来说,是一种怎样执著的守望?
在相当的程度上,“观念”是决定视觉艺术之高下性与差异性的一个重要美学元素。现下的那些当代艺术行为者或书画者,他们大都热衷于挖空心思发掘新的视觉观念以炒作自己的另类身份,而没有人注意到邓明“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之观念,在32年中,以不变的守望立场所经历的从保守到前卫的两种价值判断历程。一幅书画作品究竟如何评判?一种视觉艺术观念应该怎样评判?我想还是应该交给历史去慢慢地证明。当然,我不是一位唯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可以说,在这32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及其行为者为蓄意制造一个又一个另类观念的出场,搅动了太多的轰动性效应,绞尽脑汁地推出了太多耸人听闻的艺术行为与艺术现象。由于见惯了太多的噱头及那些恶俗的反社会伦理现象,我反而欣赏这种在沉默中为一种笔墨观念从保守到前卫的执著性守望立场,我对哗众取宠者不感兴趣。
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把《守望丹青》带入晚近40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史的背景中,以其作者个人恒持32年不变的水墨观念做参照,抓取一个恒持不变的立场为视点,去透视与读解40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所经历的多变轨迹,为这40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流变的主脉描绘一幅系谱性地图。近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位沉稳的学问型书画家:对艺术观念立场的守望,可以从“八五新潮”通贯于当下而恒持不变,并且这位书画家低调且中正,不曾为资本的获取而出卖过自己的灵魂,在声誉上干净且无争议,不趋附于任何时髦的当代艺术思潮,也必须持有厚重的学养及博物学知识结构;然而,大多书画家受资本的诱惑都太过于功利性,且在观念上应时蜕变得太快,或者卷入太多的争议而“名气”过大,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文化修养都没有,不要说学问与博物学知识结构了。我无法把这种人提取出来作为一个不变的参照,以反思40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流变。
就我看来,邓明就是这样一位学问型的书画家,也是一位讷于言、敏于思、践于行的慢热型学者。有一个思考点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如丹尼尔·贝尔所界定的读图时代的雅文化与俗文化,中西文学图像史等必然属于满足于媚俗性阅读的俗文化,而《守望丹青》作为博物学知识意义上的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则属于雅文化。这个思考点非常有意思!
最让人无奈的是,李小山在“八五新潮”所宣称的“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之表达,被后新时期的中国历史所嘲讽了,全球化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广泛交流与深度对话,中国文学艺术能够走向世界的恰恰是那些具有中华民族性的国货,我清楚地记得在后新时期至晚近当下,国学、国画、国乐、民族舞等突围于80年代的全盘西化,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定位,在“八五新潮”中被批判的附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文学艺术现象反讽般地转身,成为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一路贴向国际文学艺术圈的民族性标签。中国画非但没有走向穷途末路,反而走向了国际美术界被西方画家所关注,连北岛与高行健在国外也以涂染中国画为生存手段之一,当然其中有他们各自的实验性尝试作为表现手段。
在“八五美术新潮”时期,李小山对“国粹派画家”依然捍卫“过时了的艺术观点”给予了批判与惋惜,认为他们所坚守的“清高”只能是一种“糊涂和懒惰”。而我们在当下理性地透过历史的周期率评价“八五新潮”,评价那个时代相关弄潮学者对西方哲学、美学与文学艺术思潮接受的全盘西化,我们只能说:历史的转型无情地嘲讽了一个时代的学者,李小山所批判的中国画是一种“过时了的艺术观点”在后新时期“过时了”。一个人及一种艺术观念究竟应该怎样被评价,还真的必须搁置在历史的发展中走着瞧!知识分子是作为个体思想的智者,他们面对着历史的前行往往是缺失有效价值判断的失尊严者,历史转型的周期率就是如此让前卫褪色为保守,让保守蜕变为前卫。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守望丹青》这部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与图像时代所契合的观念意义。这一观念意义恰然不同于中西文学史等图像读本谄媚读图时代的媚俗性,而李小山在“1985”所批评的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傅抱石与黄胄在当时就被《守望丹青》选入给予造像,而后新时期又被资本市场所复魅(re-enchantment),他们还是中国美术界所尊崇的国画大师。
六、书画家的博物学知识学养与资本对文学艺术的异化
《守望丹青》不是一部纯粹的水墨丹青画册,倘若如此,我也就没有必要把其带入我的论域,借其在以静观动的参照中反思近40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蜕变的历史轨迹。当下业已出版的画册林林总总,可谓是汗牛充栋,平心而论,绝大多数也就是兑现书画者个人出书的愿望而已,没有太多的艺术价值,更谈不上学术价值。我一直在想,应该怎样给《守望丹青》的多元性体例下一个定义,或许应该称之为一部跨界且具有博物学知识的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在体例上,《守望丹青》的体例构成应该含有以下四个层面:1、在“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的视域观念下,形塑一百位中国书画家的水墨丹青肖像画;2、遴选被造像的每一位书画家的一幅书画代表作品;3、就每一位水墨书画家及其代表作撰写一段史论评述,以评价其笔墨观念、风格气象及表现技法等;4、就每一位书画家及其代表作的风格及表现技法撰写一首七言绝句,“以诗论画”,从而营造一种诗性的画评意境。从《守望丹青》体例的四个构成部分,我们不难见出其作者秉有丰厚的博物学知识学养,也是一位学问家。
多年来,我周遭有一批书画家与中西美术史论研究者,也有一批附庸风雅且习作中国古体诗的学人,但他们几乎都是把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投放在一生专注的那一亩三分地。书画家往往偏执于那点表现技术上的事,对中西美术史论知之甚少,或不懂中西美术史论,更不要说他们对沉淀于中西文化传统背后的文史哲又有多少切近性的了解;中西美术史论研究者做不好书画,或完全不会画画与写书法;当然,在书画家与中西美术史论研究者中,能够吟写中国古体诗者更是寥寥无几,且不要说让能够吟写中国古体诗的学人去画画、写书法及通晓中西美术史论了。并且以吟写古体诗而论画造境与单纯吟写古体诗造境,其还是两种不同的格调与境界。实话实说,学界都知道,在资本的推动下热闹浮华的当代艺术与新水墨画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窘态就是没文化或文化水准低下。说到底,在相当的程度上,当代艺术及新水墨画者就是一批没有文化的人干有文化的事,当然还包括那些错字连篇及观念恶俗的书法人。
我为什么欣赏《守望丹青》?这部文本所负载的整体价值恰恰就在于作者沉淀于其中的这种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学养及灵动于其中的艺术观念。邓明书画的童子功很好,而我个人认为,他的书法比绘画功底还要好一些。幸运的是他于1980年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在“上人美”任职期间,他与他的同仁一并策划、编辑与出版了一批在国内外美术界很有影响的中西美术史论之书籍及画册。在中国美术出版界,“上人美”是一种份量。历史的偶然性选择往往可以成全一个人,也可以弃置一个人。我想指出的是,如果当时邓明没有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现下他也就淹没在那些参差不齐的书画家的群落中了,因为30多年来,“上人美”的策划、选题、编辑、校稿等出版工作让他得以沉淀下了丰富的文史功底。而这恰然不是一位纯粹的书画家有所幸经历的,正是书画家与“上人美”出版家这两种身份在整合中,铸就了具有博物学知识结构及艺术修养的邓明。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反思晚近40年来中国美术界的乱象杂生,特别是当代艺术与相关新水墨画在观念与形式上的某种低俗性“创意”,其到了必须要强调文化与学养的危机时刻了。
在中国水墨书画的发展历史上,那些曾被历史所记忆的书画大师,哪一位不是学养积重的文豪及博物学家?中国书画源起与发展的本质就是在博物学意义上所成就的视觉气象,王岳川也提出国学高度决定书法之美。
思考到这里,还是让我尊黄宾虹为例给出以下的接续性论述。我建议当下的书法家与画家不妨去恭敬地拜读一下《黄宾虹书简》、《黄宾虹文集》与诸种“黄宾虹年谱”等,以检讨自己在知识与学养上的缺憾。在这里,还是让我援引傅雷对黄宾虹的评价:
黄宾虹先生不仅为吾国近世山水画大家,为学亦无所不窥,而于绘画理论、金石文字之研究,造诣尤深。或进一步发挥前人学说,或对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态度谨严,一以探求真理为依归,从无入主出奴之见羼杂其间。
仅就“金石文字之研究造诣尤深”与“从无入主出奴之见羼杂其间”两句评价,当代中国书画家谁又能够担当得起?前者是厚重知识学养的评价,后者是独立之人格境界的赞誉。
黄宾虹的确是“为学亦无所不窥”的百科全书式的书画家,他的朴学功底极为厚重。黄宾虹15岁开始读许慎的《说文解字》,一生与其交游者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大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吴昌硕、邓实、黄节、蔡哲夫、陈去病、柳亚子、李叔同、苏曼殊、谢觐虞、高剑父、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刘海粟、潘天寿、何香凝、陈叔通、王济远与俞剑华等,于此我不再更多地举例。黄宾虹一生参与主持编辑了多部重要的刊物,如编辑《神州国光集》,与邓实、黄节编辑《国粹学报》,与邓实合编《美术丛书》,49岁任《神州日报》主编,应康有为邀请主编《国是报》等。他不仅是一位书画宗师,更是一位学养积重的出版家与学问家。他的金石学功底令人敬重,王国维和罗振玉两位大师也曾与他讨论过金石学的问题,让我们来阅读王中秀在其《黄宾虹十事考·贞社时代》一文中的陈述:
这次陈列大会后不久,在6月21日另一次例行古物陈列会上,当时任广仓学会著撰的王国维无意间看到黄宾虹收藏一方“匈奴相邦”玉印,大为诧异,以为于学术研究关系甚大,便向黄氏索取印拓二纸,并写信给罗振玉,专门申述了他的看法,还附去该印印拓一纸;王氏据此印拓,写成一文,收录在他的《观堂集林》中。黄宾虹捐赠的朋友信牍中,存有一封王国维1918年的信,大概是秋天写的,内容是切磋金石文字之学的。
我想提醒中国美术史论界注意的是:这是早在1921年发生的事。
我特别建议当代中国书画家及美术史论家应该去阅读一下收入在《黄宾虹文集·金石编》中的69篇关于金石学研究的文章,如《叙摹印》《滨虹藏印记》《金石学略说》《金石书画编》《古印概论》《虹庐笔乘》《周秦印谈》《阳识象形商受觯说》《古印文字证》与《宾虹艸堂藏古玺印释文》等。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见出黄宾虹作为一位中国书画家的学养所在。对这些文章的阅读也可以让那些在技术上还能写几笔与画几笔的自负书画家羞愧于自己知识与学养的薄浅,从而心悦诚服地谦卑下来,也可以让聒噪于学界的美术史论者安静下来。在此,我特别想设问的是,当代书画家是否能够有点学问与学养?为什么当下中国美术史论界如此缺少有学问且有学养的关于书画及其史论研究的厚重文章与著作?为什么相当一部分美术史论的文章与著作充满了如此多的病句、错别字及标点符号的错误?不要说中西文献引用的规范性出注与理论带入的错误了。事实上,当代艺术批评所面临的问题比当代艺术还要严重。
学界皆知黄宾虹关于中国书画的论述深湛且博旷,但是在美术观念上,他又绝然不是守旧于中国传统书画观念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他对西画的论述也极到位。我特别建议当下的画者与画评者不妨去阅读一下黄宾虹的《新画训》,这是一篇美术观念极为前瞻的长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篇长文是于1918年8月26日连载于《时报·美术周刊》迻译栏的。平心而论,从“《星星》美展”到“八五美术新潮”,那些于中国本土讲唱西方美术思潮的前卫者,在西方美术观念的接受上较之于这篇文章,已然落后了大半个世纪。
不啻如此,中国美术界还没有注意到黄宾虹兼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45岁那年,黄宾虹不仅撰写了《滨虹论画》,并且赴南京文艺学堂讲授公羊学;公羊学是今文经学的主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见思想的学脉,从黄宾虹在那个历史时期讲授公羊学的隐喻立场来看,他在思想上也是一位关注国族意识形态的介入性公共知识分子(interventional public intellectual)。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黄宾虹的博物学知识结构及其学养给出更为深入的评讲。
论述到这里,有一种旷日持久的尊重在敲击着我的心脉,有两位学者是我在此必须提及的:一位是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先辈学者张元济,另一位是曾任中华书局总编的傅璇琮,此两位学者出类拔萃的身份都是以出版家丰沛的博物学知识结构所铸就的杰出学问家。书画的本体一定不是玩弄技法所刻意制造的形式观念,而是颐养于书画家人格结构的深厚学养及从中澄明出场的精神气象。多年来,在市场资本的功利性驱动下,无论是体制内书画家还是在野书画家,大多数人往往被挤压于技法及其形式观念的偏执中相互争奇,说到底在本质上,这还是文化底蕴贫瘠的表现,更谈不上什么学问与学养。
在太多的书画策展上,我们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某位书法家错字连篇,某位画家操用水墨及设色在表现体道或参禅的观念时,让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学者一眼看上去实在是牵强附会或浅薄无知。资本驱动的时代把一批当代书画家剥离于起码的文化知识,成为资本及剩余价值的唯利是图者,当然,还包括那些当代艺术行为者。在资本运作的经济时代,资本已成为推动文学艺术创作的第一生产力。在这里,我们还是以书画艺术为例,当下书画作品的拍卖天价已完全背离了艺术本然所含有的非功利性审美价值,成为艺人、策展人、拍卖人与收藏人在预付的可变资本中追求剩余价值的商品。实际上,艺人所获取的天价利润还只是上述后三种人获取暴利后的一个部分。文学艺术被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后,在资本及剩余价值碾压审美的时代彻底地异化(alienation)了,我无法忘却马克思关于“资本”论述的那句著名表达,其详见于《资本论》(Das Kapital
)第1卷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Der Akkumula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的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Die sogenannte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Wenn das Geld, nach Augier, „mit natürlichen Blutflecken auf einer Backe zur Welt kommt,“so das Kapital von Kopf bis Zeh, aus allen Poren, blut-und schmutztriefend.)当代书画市场的天价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在追求暴利性剩余价值的资本操控下,书画及书画市场又怎能不裸露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这里我所要提醒学界注意的是,在布尔迪厄的文学艺术理论场中,他所论述的“资本”——“capital”在外延与内涵上是一个更为宽阔的概念,汉语学界必须要区分清楚。美国学者兰德尔·约翰逊(Randal Johnson)在为布尔迪厄编辑《文化生产场:艺术文学论文集》(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时,曾撰写了一个较长的《编者前言》(“Editor's Introduction”),以对布尔迪厄的理论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概述。客观地评判,兰德尔·约翰逊的概述较之于汉语学界相关学者介绍布尔迪厄理论的文章更为简要与准确,更为接近法国本土的原版布尔迪厄理论。关于资本的性质,兰德尔·约翰逊阐述得非常明晰,不能把文化资本化简为经济资本:“具有圣名声望的权威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象征(purely symbolic),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布尔迪厄把这个观点发展为他的实践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的概念是建基于不同的资本形式(diverse forms of capital)之上的,并且这里的资本不能化简为经济资本。”据我统计,布尔迪厄关于资本的论述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布尔迪厄扩大化且精制化地论述了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学术资本(academic capital)、语言资本(linguistic capital)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等。并且他在具体论述文化生产场时,申明有两种资本特别重要,即符号资本与文化资本。布尔迪厄把文化资本界定为一种知识形式(a form of knowledge),艺术作品就是文化资本的符号性代码,并且认为艺术作品对于拥有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人才秉有意义与趣味,艺术作品是代码(code),是拥有文化能力的人参与其中给予意义与趣味的编码(encode)。当然,我认为这里涉及的拥有文化能力的人,应该包括艺术家、艺术批评家与艺术收藏家什么的。而我在这篇文章所讨论的“资本”不完全等同于布尔迪厄的理论,主要是指涉操控市场的“经济资本”。
再让我们的思路回转于中国美术界去。我们只有真正地了解资本操控艺术市场所带来的乱象与迷雾,才知道要寻找到那种洁身自好且有知识学养的书画家是怎样的困难了。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美术出版界有两位学者是应该提及的:一位是北京的程大利,一位是上海的邓明。程大利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他的山水画有着笔墨缘发于心的文人气韵,而邓明在书法上更胜一筹;邓明攻瘦金体与苏体,其笔墨章法透露出文人孤高耿介的骨气。30多年来,程大利与邓明以自身逐年沉淀的博物学知识结构,对书画史论之典籍与画册的出版起到了重要的策划人作用,并且他们又都是博物学养积重的书画家。这一点就很难得了。当下我们所倡导的是一位优秀的中国书画家应该秉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学养,否则愧对颐养历代中国书画家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七、黄宾虹的古印训释及其古典学的知识含量
中国书画家及批评家对文史、金石及篆刻等多少应该有些修养,可是当下的中国书画家又能够知之多少呢?赏玩古印历来是中国书画界与收藏界的雅好,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黄宾虹赏玩古印的学问及学养深度。在《宾虹艸堂藏古玺印释文》这篇文章中,黄宾虹就一方古印“高身”进行了释义:

从学术研究史的宏观背景来考查,虽然黄宾虹在这里仅是对一方古印印面上“高身”二字进行释义,但是其中就“身”字的训释,最终在训诂学、文献学与经学方面涉及了对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周礼》注的指谬,其堪称了得!
郑玄是东汉末年通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一代大师,他遍注群经,在中国经学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曾给予郑玄以极高的评价:“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吴冠中曾放言:“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严格地讲,由于吴冠中没有设定参照系,齐白石与鲁迅没有可比性(comparability)。然而我客观地评判,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天平上,一百个齐白石、一百个李可染、再加上一百个吴冠中也压不起一个郑玄。
我想在这里还是应该就黄宾虹的释文及对郑玄的指谬给出一点必要的解释,以便让当下中国书画界及书画史论界了解黄宾虹对一个字的释义,其究竟涉及了怎样的学术含量,触及了怎样深度的历史问题。

然而,问题绝然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从黄宾虹的释义可以见出,他接受了许慎在小篆文字系统中对“身”释义的文字观念,并且也接受了郑玄因声释义的训诂学方法论。黄宾虹认为“身,从申,申即信之古文”,正是在这样一个释义的逻辑上,他判读“文王受命惟中身”之“身”应该释义为“信”,那么“中”即通“忠”,“中身”即“忠信”,从而黄宾虹指出郑玄把“中身”释义为“中年”是错误的。以下还是让我们来阅读一下《尚书》的原典及郑玄的注释。《尚书·无逸》载:“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郑玄的《尚书郑注》在“文王受命惟中身”一句下释义曰:“中身,谓中年。受命,谓受殷嗣王立(位)之命。”关于“中身”即“中年”的释义,事实上时至清代,经学家与书法家孙星衍在撰著《尚书今古文注疏》时,依然追随且引用郑玄的解释:“郑康成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谓中年。'”但是,黄宾虹则坚持“中身”应该释义为“忠信”。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黄宾虹作为一位水墨书画家,他在这里对郑玄的指谬,其不仅涉及了对《十三经》注疏传统及相关文字义理的勘定问题,也涉及了训诂学的问题与中国经学诠释学的问题,还涉及了上古时期文王在位的重大历史判断问题。
这,就是黄宾虹,而现当代中国书画家谁还可以做到这一点?
关于“申”通“信”的释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信”下释义曰:“古多以为屈伸之伸。”当然,这里的“伸”通“申”。我们注意到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躳”所给出的如下解释:“‘侯执信圭',伸圭人形直。‘伯执躳圭',躳圭人形曲。”在段玉裁注的释义逻辑上,“信圭”即“伸圭”。而黄宾虹释义言:“按身圭人形,直;躳圭人形,曲,经均假‘信'为之。”在黄宾虹的释义逻辑上,“信圭”即“身圭”,“身圭”之“身”字是假借“信”字所为之。段玉裁注与黄宾虹在此所言指的“侯执信圭”与“伯执躳圭”,在文献的溯源上可以追问至《周礼》。
“圭”是上古时期朝觐的礼器,其上刻有“象以人形”的瑑饰,《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侯执信圭,伯执躬圭”一句下,郑玄注曰:“‘信'当为‘身',声之误也。身圭、躬圭,盖皆象以人形为琢饰,文有粗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长七寸。”原来郑玄在注《周礼》时即把“信”声训为“身”的假借字,而“身”是本字,认为“信圭”即“身圭”。的确,在古音中,“信”与“身”可以音通互训。唐代经学家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也释音曰:“信圭,音身。”在《周礼注疏》中,唐代经学家贾公彦以疏之解经体例对郑玄的注给予了更为详尽的诠释:
[疏]注“信当”至“七寸”○释曰:郑必破“信”为“身”者,古者舒、申字皆为信,故此人身字亦误为信,故郑云“声之误也”。云“身圭、躬圭,盖皆象以人形象致饰”者,以其字为身躬,故郑还以人形解之。云“文有粗缛耳”者,缛,细也,以其皆以人形为饰,若不粗缛为异,则身、躬何殊而别之?故知文有粗缛为别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则约上下圭为义,既以人身为饰,义当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侯伯守之”是也。
从许慎、郑玄、陆德明与贾公彦一路释义的逻辑上,我们可以见出黄宾虹关于“身,从申,申即信之古文”的释义,在训诂学上是秉承因声释义的方法论。
训诂学之因声释义的提出与使用在解经中最早见于郑玄,后盛行于清代古文经学家关于“五经”或《十三经》原典及其传、注、笺、疏与正义等之勘定与整理。从一个字的释义,我们可以见出黄宾虹深厚的训诂学功底及其学养所在而引发的学术问题。但困惑在于,既然郑玄在《周礼·春官·大宗伯》注中已经把“信圭”之“信”因声释义为“身”,那么,郑玄在《尚书·无逸》注中又为什么把“中身”之“身”释义为“年”,以至把“中身”诠释为“中年”呢?其实,郑玄必然知道“信”与“身”音通互训。这是从黄宾虹对“高身”的释义中所引发出来的问题。
如果我们再说得细一点,黄宾虹关于“身,从申,申即信之古文”的释义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学术问题。许慎把小篆“身”判读为一个形声字:“身,从人,申省声”,“人”是意符,“申”是声符。从汉字造字结构的“六书”上讲,“申”只是声符,其并不应该携带“身”之意义出场,只是表声而已。因为黄宾虹的释义也认同了“身”是一个形声字,所以他在“身”——“申”——“信”之间的互通释义缺少了一个意义的链接环节,这个意义的缺环正是存在于“身”与“申”之间。其实,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训“申”为“身”有一个总纳性的解释,并且就这一解释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这就是书画家黄宾虹因一方古印其一个字的释义所带出浩瀚学术含量!
让我们思路来到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那批战国竹简那里。清华简《保训》也记忆了文王为政五十年的问题,其第一句曰:“惟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保训》是文王写给武王的遗嘱,其在简牍的书写中四次使用了“中”这个字。关于《保训》“中”的理解与解释,近年来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李学勤把“中”释义为一个表达思想观念的书写符号,他在《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由此可见,‘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这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与传流,无疑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注意到李学勤在另外一篇文章《重说〈保训〉》中也坚持这一立场:“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保训》所说文王传的宝训的确是中道,与《论语·尧曰》《礼记·中庸》等儒家文献有一定联系,也正是后世儒学道统说的滥觞。”我翻阅了近年来多位学者对《保训》篇“中”字的理解与解释,在学理上还是认同李学勤的释义。如果我们顺延李学勤的训释逻辑,黄宾虹把《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之“中身”释义为“忠信”,我认为可以把“中身”释义为“中信”,因为“中”“中道”“中庸”与“中信”是沉淀于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
其精彩在于黄宾虹就一方古印之“身”字的训读,在本质上触动了学界对上古历史及后世儒家经典注疏的一个重要的争议性问题:究竟是周文王因“中信”(忠信)受命而在位五十年,还是于“中年”受命而在位五十年?非常有趣的是,在《周文王遗言》《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与《重说〈保训〉》三篇文章中,李学勤在解读清华简《保训》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为“中道”时,却坚持文王“中年”受命而在位五十年的立场。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了!当然,关于这些问题的考释是史学界、经学界、文献学界与考古学界的事。黄宾虹因声求义把“中身”诠释为“忠信”,这一定不是“确诂”,其在文献上还需要更多的书证。但我只想在此指出的是,黄宾虹关于一方古印的诠释,其可以引发出的中国古典学知识含量究竟有多大?黄宾虹作为一代水墨书画家,他背后的博物学功底和学养就是如此的厚重渊博!
在这里,我必须要多说一句,我们从黄宾虹关于古印之“身”字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理解与解释,其势必涉猎到中国诠释学的实证性研究问题,而那些空谈建构中国诠释学的学者更应该走进文献学与训诂学的底层,以证明自己的专业身份,空谈建构中国诠释学没什么意义。这是黄宾虹对一方古印的训释所给我们的启示。
八、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美术史”
让我们的思路再回到《守望丹青》及其体例结构观念所引发的反思中来。
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在西方崛起以后,迅速弥散于国际视觉艺术界,且一直影响至当下。显而易见,“concept”“idea”与“notion”成为了当代艺术行为者趋之若鹜所追求的新奇表现尺度。1967年,《艺术论坛》夏季卷(Art Forum
, Summer)发表了美国艺术家索尔·莱维特(Sol Lewit)的文章《观念艺术卮言》(“Paragraphs on Conceptual Art”),这篇章中,索尔·莱维特就“观念艺术”的本质与形态第一次给出了论述:我把我所设身投入其中的艺术称为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在观念艺术中,观念的想法(the idea of concept)是作品的最为重要方面。当一位艺术家使用一种观念艺术的形式时,这意味着全部的计划与决策是事先安排好的,执行只是一件随后完成之事而已。想法变成了一种制作艺术的机器。这种艺术不是理论化的,也不是对理论的解释;这种艺术是直觉性的(intuitive),与思维过程中的诸种形式有着关联,并且是无目的性的(purposeless)。观念艺术通常摆脱了艺术家作为一个工匠对技艺的依赖。
确然,在观念艺术中,“idea”或“concept”是作品须臾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方面。特别是当代行为艺术者为了呈现一个特立独行的想法,可谓是绞尽脑汁地实验了一个又一个危言耸听的视觉表现观念。但遗憾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制造一个个“观念”的出场时,其绝大多数俗不可耐。那些耐不住寂寞的画者以为可以投机取巧于玩观念艺术,以便如此让自己在短期内成名,这显然是没有在美学的本质上理解观念艺术。平心而论,玩好一个观念介入性先行的行为艺术或装置什么的,不比画画容易,甚至还要难。
的确,“观念”界分了一个时代差异于另一个时代的历史本质,“观念”的前卫性也构成了学者的价值判断立场。“我们的观念不同”,这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立场性与宣示性的表达。关键的逻辑点在于,《守望丹青》在体例结构的四个层面上涉及了重写中国美术史的新观念。在形式本体论上,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与舞蹈等虽然分属于各自不同的审美表现形式,然而特别是在现代与后现代时期,它们必然是在全球化的共时历史语境下发生的文学艺术现象;只是学科研究分类的细化恰恰把它们分解于各自的领域,脱离于他们发生的整体历史背景,结果也促导他们共同所属的完整历史遭遇了破碎,我们之所以在跨界的语境下把文学与艺术给予整合性的思考,在本质上,也是为了于思考的研究中还原其背后的完整性历史景观。当然,这是我的研究立场。
需要提醒学界注意的是,布尔迪厄在其一系列文章与著作中,始终都是把文学艺术整合为一体,共置于文化生产场中给予思辨性论证的。《文化生产场或逆转的经济世界》(“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一文是他的代表作,凡是在原典阅读上真正进入过这篇文章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在开篇第一句布尔迪厄即宣称了他把文学艺术整合为一体的研究立场:“较之于艺术与文学,很少的领域能够如其那样清晰地展示交互思考的启发性功效。”他继而论述道:“文学或艺术场不仅是一个动力场(a field of forces),另外其也是一个对动力场进行改造或守望的斗争场(a field of struggles)。”
既然如此,就让我协同着布尔迪厄的研究立场,把晚近40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整合于一个文化产生场中,以反思这4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是在怎样的改造或守望的斗争场中推动历史发展的。
其实,学界是无法忘却这样一个学术事件的。
“八五新潮”所裹挟的思想震动在持续性地发酵着,激发了一代学人在“重写文学史”的观念上对“体制文学史”及其历史价值观提出了挑战。依然是在198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黄子平与陈平原以“三人谈”的对话形式,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思考命题。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关于这个命题的提出初步涉及了“重写文学史”这个重大学术观念的讨论话题。他们在198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强调了文学史研究者对同时代文学发展的介入性:“文学史的研究者凭借这样一种使命感加入到同时代人的文学发展中来,从而使文学史变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此次发生在1985年的思想震动从那个历史节点强势性地持续了若干年,时值198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思和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晓明,联袂在《上海文论》第4期开始设置“重写文学史”的专栏,在观念的前卫性上拉扯起“重写文学史”的大旗,这一学术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呼唤“重写文学史”的观念在理论的讨论上走向了自觉。
我们必须要清晰地体察到,任何一部“体制文学史”及其结论都是为其背后那个时代的历史价值观及国族意识形态所界定的,因此在本质上,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是在历史的价值重估与批评主体立场的调整上所涉及的一次重大的学术观念转型。我这里无意于细化地分析发生在“重写文学史”前后的那些人与那些事,我只想说,“重写文学史”的观念在“1985”以后的历史发展境遇中也必然波及到了美术界与音乐界等,直至弥漫了整个艺术界。
美术界关于“重写美术史”口号的提出,在学理上,毫无疑问是受到文学界的影响,当然,尽管这个口号的接受与提出迟到得有些晚。在这里,我不想再从当代文献系谱上考证美术界是谁最早在哪一年接受性地提出“重写美术史”的口号,我只想援引陈丹青在《无知与有知:答〈边缘〉杂志许宏泉问(节录)》一文中的表述就足够了:
陈:他俩不在行政美术界之内,你在整个行政美术史找不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只有一个办法——重写美术史。上海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张爱玲、沈从文、胡兰成,在文学史里面吗?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里根本没有这几个人。可是行政文学史的许多大角色,出全集,几百万字,谁爱看?黄宾虹早就说过要“画史重评”。可见,历来如此,中国很多的历史都是实用的,功利的。
在这里,“他俩”指代的是“玉渊潭画派”与“无名画会”的赵文量与杨雨澍。在陈丹青的个人评价系统中,赵文量与杨雨澍是两位值得他尊重的在野画家,他们在“文革”时代抵抗政治,在资本时代抵抗市场。陈丹青认为由于他们两位在“行政美术史”上的缺席,所以呼吁美术界应该重写美术史。
陈丹青一贯以犀利的表达臧否人物,给坊间留下一种误解:他在“老炮”的年龄假装生存得很“愤青”;而我认为,他实质上认真地读了不少书,且有自己的思想:“上海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张爱玲、沈从文、胡兰成,在文学史里面吗?”这句表达还真的不是那些名声显赫的当代书画家与美术史论家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所能够储存的知识信息。请注意,这是陈丹青在现场的采访中脱口而出的,当然,陈丹青还即席引经据典地支撑自己的表达:“黄宾虹早就说过要‘画史重评'”。在陈丹青的即兴表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视到文学批评在跨界中对美术批评有着不可遏制的渗透性影响,陈丹青所言说的“行政美术史”就是文学界以重写的姿态所抵抗的“体制文学史”。
再请注意的是,陈丹青为两位在野画家叫嚷“重写美术史”是发生在2004年的事,而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掀起众声喧哗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于1989年第6期随着历史的转型而终结了。值得回味的是,在历史行动的深处,事态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文学界五位肇事者的预判。文学界在“八五新潮”及后来若干年所提出与争论的“重写文学史”,其绝然不仅影响了美术界,可以说,是在新时期历史向当下发展的全方位层面上深度波及了整体艺术界;从“重写文学史”大旗的扯起与争论到当下,艺术界先后接受性地提出了“重写美术史”“重写音乐史”“重写戏剧史”“重写电影史”“重写舞蹈史”与“重写雕塑史”等口号。不啻如此,时值2002年,李学勤把自己推出的论文集也定名为《重写学术史》,也有相关学者回应性地提出“重写国史”等等。
令人遗憾的是,学科之间划分的过细必然会导致学界盲目地构筑“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科壁垒,学科壁垒也必然铸成某些知识分子癖恋学术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的狭隘心态。无论是文学界还是艺术界,如果双方学者都没有从文学艺术的整体背景俯瞰提出“重写……史”所依凭的总体历史格局,那么历史一定会被学科研究的壁垒及单边主义立场所解构得破碎一地。事实证明,所有的迹象也确然如此。不错,我们应该把文学艺术还原于在本质上具有普遍联系性的整体历史景观,以给予反思与重写,这必然也是我书写这篇文章的主旨观念之一。
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依然存有相关学者在叫嚷重写西方美术史或中国美术史什么的,但较之于“八五新潮”至1988年的文学界,他们的集体发声在思想的批判性与理论的建构性两个维度上要逊色得多。这种现象与美术批评界在理论的知识结构上落后于文学批评界有着本质性的逻辑关系,所以他们的声音在指涉历史价值观及意识形态所亮出的批判思想已经不是那么具有说服力了,除去美术批评界那些常态发声的贬损话语之外(如把“美术史”唾骂为“美术屎”什么的),他们似乎开始靠近一种在学理与文献上更为接近历史本体的“重写美术史”。
我在这里只想谈一个现象,为什么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美术史”等,知识分子从思想的张力性批判跌落于集体失声的惘然若失?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八五新潮”前后高涨的人文精神已经远离当下,逝去得过于久远了,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中淡化了。历史在发展中的转型让大众把媚俗作为日常生活的审美趣味,大众在娱乐至死的抚摸下相当舒适地接受了图像时代与资本时代的彻底到来。历史向后新时期彻底转型了,我们可以在形质上把后新时期界定为一个图像-资本的时代。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学批评在遭遇图像-资本时代的最后命运就是迅速地边缘化,以语言为思想出场的抽象性书写符号被图像及其背后的媚俗性阅读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艺术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视觉艺术在资本推动下的迅速发展最为恰切地迎合了图像时代的历史形质。这就是为什么美术会成为图像-资本时代的主流艺术表现形式,当然,其次还有在资本推动下的电影与电视。思考点在于,资本对图像时代美术创作及其批评的市场性介入,进一步推动了书画作品成为资本积累及剩余价值获取的商品,而文学作品在形式本体上全然没有资本介入的收藏价值,音乐也是如此缺少资本收藏介入的形式本体。
在这里,让我们注意两种具有前卫性“观念”之间的差异性。从“1985”到当下,“重写……史”在思想观念上的突破从众声喧哗到平静后的一般性学术讨论,其无论怎样也持续了30多年,然而无论是“重写文学史”与“重写美术史”,还是“重写……史”什么的,在观念的思维方法论上还是滞留在以语言的抽象符码“重写……史”,而《守望丹青》在“重写美术史”的观念上则更为前卫性地递进了一步。我在上述指出与分析了《守望丹青》在体例构成上的四个层面,其中特别是“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与“以诗论画”两种观念的介入,让这部文本绝然不同于以纯粹抽象的语言符码“重写美术史”,《守望丹青》是一部在新观念下完成的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作者正是以此介入到同期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中来了。
《守望丹青》在体例的观念构成上不仅贴合于图像时代,也吻合于美术在资本时代凸显的主流地位,然而其恰恰又不是那种具有媚俗性的“图像文学史”等通俗读本。我们只有把“重写文学史”“重写美术史”或“重写……史”一路地反思下来,才可以在互为参照的观念反差上看视到《守望丹青》的美学观念及其历史价值所在。并且我把以下三个年代的数字于此再度强调,学界便知晓这一观念生成与行为的前卫性了:邓明“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的观念是在1985年生成的,也是在1993年完成的,而建基于这一观念之上“重写美术史”行为是在2010年启动的。
“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以构成一部从沈周到黄胄的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这不仅是在中国绘画观念上的突破,也是在重写中国美术史观念上的突破。突破点在于,邓明不是操用他本人的笔墨观念为这一百位中国书画家造像,而是操用每一位书画家的笔墨观念为每一位书画家造像。我把邓明的笔墨造像观念剖析到这一深度,真正的画家与画评家应该理解其前卫性与难度性所在了。《守望丹青》遴选了从明清近现当代以来的一百位中国著名书画家,他们都是名震历史的书画大师,在笔墨、设色、格局与书法风格上各成一家,可谓是气象繁华。作者要准确地把握这一百位书画家各自的笔墨观念及蕴涵于其中的气象、意境、格局与风格,为这一百位书画家造像,可以说,作者的造像观念及其行为的历史含量、美学含量、技法含量与学养含量是非常宏大且厚重的。也就是说,“用黄宾虹的笔墨观念为黄宾虹造像”“用八大山人的笔墨观念为八大山人造像”与“用吴昌硕的笔墨观念为吴昌硕造像”等,其谈何容易?!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再做几例造像观念的细读,以剖析邓明在造像的笔墨观念上所投入的良苦用心。八大山人是有其画像传于后世的,后世的画家多据此本为八大造像,当然邓明也是。但是邓明在观念上是更为自觉地取用八大简约的笔墨风格来为八大造像,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八大的画像,如邓明所言:“我原先是为八大画手画衣袖的,然而总感觉不对,感觉还缺少什么,仔细思量后发现原来缺少的正是‘缺少',于是在笔墨上就做减法,减到减无可减了,也就非他莫属了。”我想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在观念上理解了邓明笔墨下那幅极简主义的八大造像。
邓明也是刻意地把吴昌硕的笔墨观念其中蕴涵的气象、意境与风格渲染于他为吴昌硕造像的观念中。在与邓明的多次谈聊中我得知,吴昌硕造像是2010年邓明正式启动“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计划的首批八件作品之一,他很早就想为吴昌硕造像了,在邓明看来吴昌硕的笔墨特征比较明确:“缶翁意笔前无古,画印诗书冶一炉。”吴昌硕是诗书画印自成一家体系的宗师,在画风上导引了清末以来上百年的大写意绘画风气。邓明总是强调齐白石所讲求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其直接源头就是吴昌硕。吴昌硕笔墨的核心观念是“以气驭形”,可谓“老缶写气不写形”,所以吴昌硕画牡丹与芍药不分,也没有人去较真,也不可以较真。除黄宾虹外,邓明特别喜爱吴昌硕,因此邓明在吴昌硕的造像中灌注了包括焦墨、渴墨、泼墨、淡墨、光感与金石味线条在内的几乎所有吴门技法,一如邓明所言:“特别是吴昌硕马褂的墨色处理,其丰富性与合理性,我至今认为是到位的。当然,重点是吴昌硕的气质,低调而有分量。”
邓明为一百位中国书画家造像,其每一幅造像笔墨在观念上都力图透向每一位书画家的笔墨气象、意境与风格的内在审美神髓,这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有多处是在诸家笔墨观念极为细致的表现中见出为诸家造像之境界的。
邓明为明代画家陈淳造像时,在笔墨观念的细微之处可谓是取其风格的内在神髓。邓明在《守望丹青》陈淳评传中言:
(陈淳)文徵明弟子,擅写意花卉,一花半叶,淡墨欹毫,自有疏斜历乱之致,画史将其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足见其在水墨写意花卉上的成就。
在邓明看来,同在“青藤白阳”的誉称下,徐渭更奔放一些,而陈淳更内敛一些。陈白阳的写意花卉是控制于静态中所绽开的一种惬意,要在笔墨观念中造境出这种惬意,用笔与用墨都需要沉潜于从容中而透向沉稳,在定力中疏解火气,并且操持书法性的用笔必须贯通终始,一写到底:衣领两笔,袖口两笔,帽三笔,衣纹于形体若即若离,舍此则境界尽失。这是邓明为陈淳造像时所达向的神髓境界,当然,境界背后沉浸的是笔墨观念的渲染,用邓明的表达来解释:“我用了一段雍正旧墨画陈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把邓明为一百位中国书画家的造像及其不同的笔墨观念一一给予诠释。当然,我在这里要指明的是,邓明的这一百幅作品也不是每幅都成功的。把一百位书画家的笔墨观念要准确地呈现于一百幅造像的形神中,其在具体的造像行为中又是否可以一一兑现呢?如花鸟大写意画家的笔墨观念是否适用于人物的造像,又应该怎样造像?还有多位书法家的笔墨观念又怎样恰如其分地表现于人物造像的观念中?邓明在笔墨观念的操用中对上述现象又是怎样理解与驾驭的呢?其中也有可商榷之作。然而较之于几十年来那些知识贫瘠且人格低俗的某些观念艺术,我所欣赏的不仅是邓明“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之观念生成的前卫性,更欣赏的是邓明在这一观念表现中所沉淀的一位博物学者的深厚学养。
九、画外“题画诗”和书画家通修诗文的功底
“以诗论画”也是《守望丹青》体例构成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其也是表现一位书画家具有博物学深厚学养的标识。在《守望丹青》中,作者吟诵了一百首七言绝句对他遴选的一百位画家进行了品鉴与述论,他的“以诗论画”必然在书写的文体构成上涉及了“题画诗”这一概念。多年来,中国美术史论界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对“题画诗”这个概念有所争议:即“题画诗”究竟是题署于画面之内以构成诗情画意之融合的书写,还是撰写于画面之外以形成对绘画及其作者给出“知人论世”的评述?我认为“题画诗”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能指应该秉有两个所指,即画外“题画诗”与画内“题画诗”。
在此,我无意于介入这个话题的讨论,也不想追问“题画诗”在文献上最早源起何时与何人,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常识。我只想还原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原典文献中,在“题画诗”的源语逻辑上承继性地使用沈德潜的这个概念,清代学者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一书中有如下所言:
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又如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出登临凭吊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拈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广之,才是作手。
沈德潜在这里主要是以论诗而涉及论画,文学与艺术的确无法切割为两个壁垒相望的场域,中国传统诗画更是如此。沈德潜在这里所使用的“题画诗”这个概念是指称杜甫22首品鉴与议论水墨丹青的诗作。杜甫曾吟诵歌行体《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与四言体《画马赞》两首诗,非常有趣的是,这两首诗虽然同源于杜甫,却对唐代画家韩干画马给出了悖论性的评价。关键在于,这两首诗都未直接题署于画面,而沈德潜恰然把其称之为“题画诗”。这也就是我所定义的画外“题画诗”。
我们必须注意在沈德潜的表述语境中,他所言说的画外“题画诗”之“题”有“发论”与“议论”之意,并非是“题署”之意,并且强调“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沈德潜也借势把孟子“知人论世”这个文学批评立场带入自己的表述中。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内编三》也言:“题画自杜诸篇外,唐无继者。”这里的“题画”应该视为一个具有动宾结构的独立话语:即“论画”与“评画”。而需要指谬的是,学界较多的学者在使用胡应麟的这段文献时总误衍了一个“诗”字:即“题画诗.自杜诸篇外,唐无继者。”一个“诗”字之“衍”,在语感上遮蔽了“题画”在画外“论画”与“评画”批评姿态,而把读者误导于“诗”的书写形式本体上。无论怎样,邓明吟诵的一百首七绝是“以诗论画”的画外“题画诗”。
2016年6月,邓明把一百幅作品完成装裱以后,便开始为《守望丹青》撰写评传与七言绝句。我在这里不谈评传的问题,只想谈一下他“以诗论画”的七言绝句。邓明在中国古体诗的平仄、粘对、对仗与押韵等方面有着很好的学养,并且熟读盛唐七言绝句,他在这方面颐养的博物学知识不是一般书画家可以比肩的。可以说,他的一百首七言绝句“题画诗”能够严格地遵守定型的格律,首首合辙押韵;精妙之处在于,他在“题画诗”吟诵的意象上也能够突围于七言绝句的形式本体,以营造一方诗境,对一百位书画家及其作品的表现风格等给予准确且有见地的评述。我一路地诵读下来后特别注意到,其中只有吟诵钱松喦画境的一首在一个“常”字的使用上有失对之处,我做事情偏执于逻辑的严谨上求自洽,因此曾就这个字的入诗与邓明讨论,然而,此字入诗的失对也在邓明知识结构的掌控之中。当然,我们就这首绝句讨论的话题还涉及了其他问题,所以我愿意在此拈出这首诗来给出一个分析。
众所周知,钱松喦是新金陵画派的代表画家,邓明对他的品鉴与议论是凝思于这样一种诗境中的:
石涛水法髡残墨,老笔纷披写陌阡。
三远亦随时代走,红岩镜泊常熟田。
这首七言绝句在格律上属“首句平起不入韵式(平起仄收)”,其格律图示如下: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遵七言绝句格律的要求,其首联对句的脚节应该是以平声入韵,而“阡陌”是钱松喦于1963年创作《常熟田》所渲染的一个重要的视觉风格,这也是钱松喦代表新金陵画派为中国传统山水画注入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即鸟瞰“阡陌”纵横的万顷平畴,以表现当时江南水乡的丰饶气象。邓明择用“阡陌”这个修辞且携带其构图景观入诗,以品鉴与议论钱松喦在咫尺画面上拓展的千里之势,这是非常准确的。然而“阡陌”的韵律是平仄,倘若邓明带“阡陌”直接入诗,则破坏了首联出句脚节与对句脚节前后平对仄与仄对平的格律,即失对。而邓明在修辞上把“阡陌”颠倒为“陌阡”入诗,便应和了出句与对句前后平仄相对的格律,所以邓明落笔为诗曰:“老笔纷披写陌阡”。“老笔”在修辞的借代上隐指钱松喦在创作《常熟田》及其后于墨法上所铸就的老辣之笔。
我接续要谈下去的是,邓明不仅是在平仄与粘对上恪守格律的定型,也更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的格律与修辞之典故上为自己寻找理据。在邓明看来,为什么可以把“阡陌”颠倒为“陌阡”入诗,因为南朝梁代诗人吴均在其乐府诗《行路难》第三首中已有此用:“君不见西陵田,从横十字成陌阡。君不见东郊道,荒凉芜没起塞烟。”我想只有把典故追问到这等深度再做诗,那便是学问了。谙熟中国古体诗的学者应该一眼看出,在尾联的出对两句中,对句腹节的“常”与出句腹节的“时”失对,按照七言绝句“首句平起不入韵式(平起仄收)”,尾联出句腹节与对句腹节应该是平对仄,出句腹节的“时”是平声字(阳平),而对句腹节的“常”也是平声字(阳平),就格律而言应该使用仄声字,因此失对。就这个“常”字的失对,我请教邓明后,理解了他的用意,他在格律上是非常清楚的。
邓明的一百首画外“题画诗”,首首有诗眼,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尾联对句“红岩镜泊常熟田”就是此首七言绝句的诗眼所在。在我与邓明的交谈中得知,此句在诗眼的意境烘托上以隐喻浓缩了三幅作品作为诗句:即《红岩》(1965)《镜泊湖水电站进水口》(1961)与《常熟田》(1963)。为了格律的粘对与押韵,邓明打破了三部作品的创作年序,分别入韵且入诗,以“红岩”为顶节,以“镜泊”为头节,以“常熟”为腹节,以“田”为脚节,这自然便是一种作古体诗的讲究了。
其实,“熟”在吴方言保留的古音中是一个入声字,但是“常熟”是一个既成的地名,所以邓明无法像颠倒“阡陌”那样,把“常熟”颠倒为“熟常”以求出句腹节与对句腹节的平仄相对,即便颠倒如此,“熟常”在对句中也是有韵无意。在中国古体诗创作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即允许诗人因照顾诗面字义而出现个别失粘与失对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明以“常熟田”完整的字义入诗,呼应于“红岩”与“镜泊”形成诗眼。也就是说,在尾联中,对句腹节之“常”与出句腹节之“时”的失对,其完全在邓明知识结构的掌控中,这无疑是一种学养。我想顺便在这里提醒诸家的是,遵七言绝句的格律与粘对,尾联对句腹节的“熟”于此只能读为现代汉语的阳平,如果刻意炫耀地读为入声,反而失对成错。
在中国书画传统上,那些被历史所记忆的经典书画家在气韵上从来都是得益于对文史博物知识的承诺,说到底,“画学高深广大,变化幽微”,就是要多读书以颐养人格气象。唐岱被康熙赐称“画状元”,在《绘事发微》一书中,唐岱专门著有《读书》一篇,我愿意把此篇的完整语境引出,以敦促当代中国书画家了解一下应该读哪些书:
画学高深广大,变化幽微,天时、人事、地理、物态无不备焉。古人天资颖悟,识见宏远,于书无所不读,于理无所不通,斯得画中三昧。故所著之书,字字肯綮,皆成诀要,为后人之阶梯,故学画者宜先读之。如唐王右丞《山水诀》、荆浩《山水赋》,宋李成《山水诀》、郭熙《山水训》、郭思《山水论》、《宣和画谱》、《名画记》、《名画录》、《图绘宗彝》、《画苑》、《画史会要》、《画法大成》,不下数十种。一皆句诂字训,朝览夕诵,浩浩焉,洋洋焉,聪明日生,笔墨日灵矣。然而未穷其至也。欲识天地鬼神之情状,则《易》不可不读;欲识山川开辟之峙流,则《书》不可不读;欲识鸟兽草木之名象,则《诗》不可不读;欲识进退周旋之节文,则《礼》不可不读;欲识列国之风土,关隘之险要,则《春秋》不可不读。大而一代有一代之制度,小而一物有一物之精微,则二十一史,诸子百家,不可不读也。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立身画外,存心画中,泼墨挥毫,皆成天趣,读书之功,焉可少哉!《庄子》云:知而不学,谓之视肉。未有不学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自能超越名贤者。彼懒于读书,而以空疏从事者,吾知其不能画也。
中国书画不同于西画及其技法的表现性,中国书画的格局、气象与意境等在笔墨丹青的展开与精微之处皆是知识学养的沉淀与流露。的确,对于任何一位书画家来说,“读书之功,焉可少哉!”邓明一生在“上人美”从事编辑工作,读了不少书,他的一百首画外“题画诗”所摄入的书画历史典故与文史知识含量是相当丰沛的。在一定的程度上,邓明的一百首“题画诗”浓缩了一部中国书画史的多维断面。在书写的要求上,作为七言绝句的画外“题画诗”,其不同于一般状写自然景观或抒发个人胸臆的七言绝句,也不同于画内“题画诗”,邓明的画外“题画诗”是“知人论世”的“以诗论画”,并且还要营造一方诗境。“石涛水法髡残墨”其隐含的叙事语境是指涉钱松喦在水法与墨法上受石涛和髡残的影响,“三远”作为画论典故取用于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提出的“高远”“深远”与“平远”:
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
郭熙的“三远”恰恰没有涉及从山上往下鸟瞰的散点透视图景,而钱松喦在创作《常熟田》时,登常熟虞山鸟瞰江南万倾水乡良田,其咫尺画面在构图上突破与发展了“三远”的散点透视法,拓构出另外一种气象宏大的俯视格局,所以邓明在画理上认为钱松喦的这种俯视格局推动着“三远亦随时代走”。从一个艺术流派的整体表现风格上来评述,这种在咫尺画面所渲染的鸟瞰式的宏大视觉精神也是新金陵画派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共铸的水墨风格。
我想可能也正是新金陵画派的整体时代风格给邓明带来了一个整体的记忆,因而产生了作品的混淆,《镜泊湖水电站进水口》不是钱松喦的作品,而是新金陵画派另一位大家傅抱石的作品。当我指出这一点时,邓明坦然地说:“惭愧,惭愧,记错了,匆忙了!”邓明的爽直让我恰然感受到一位学养积重的书画家所秉有的谦卑气度。当下中国美术界,多少人为饾饤之异见互不服气,互怼互骂,全无修养,更不要说学养了。说到底,还是格局太小了!我建议邓明在此首七绝的修订中择用钱松喦的《爱晚亭》入诗,这幅作品创作于1979年,是钱松喦晚年的气象隆盛之作,即“红岩爱晚常熟田”,以“爱晚”替换“镜泊”,前后呼应颇得诗意,并且“爱晚”均为仄声字。邓明也欣然接受,这是学者的坦诚之交。
坦白地讲,在邓明的一百首画外“题画诗”中,吟诵与评述钱松喦的这一首不是最好的,其只是我随机提取的一首,这样做是为批评的公平。我认为其中最好的前十首是吟诵郭诩、唐寅、董其昌、傅山、八大山人、黄宾虹、齐白石、于右任、傅抱石与黄胄的“题画诗”。多年来,我读过一些当代学人附庸风雅所拟作的中国古体诗,其格律不算严谨,大多为择辞刻意精致且过度矫揉的无病呻吟之作,充其量也就是表现酸腐的个人小时代情调而已。邓明的画外“题画诗”是“以诗论画”,固首首可以见出他通观历史与当下中国绘画的批评立场,如邓明在绝句中批评美术界对吴冠中“笔墨等于零”的误读等:“笔墨千年诚有用,还须植入画图中。”这一百首画外“题画诗”是《守望丹青》一书重写中国断代美术史的一个重要体例及观念构成部分。
诗文、书画与金石篆刻是中国文人与书画家的通修学养。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传统上,很多书画家的诗文功底深厚,很多文人的书画也表现得极佳。在当下的图像-资本时代,相关书画家的作品被资本市场非理性地炒作到天价,而作者本人在知识学养与人格气象方面却贫困得相当落魄,这种反差向学界提出一个设问:在图像-资本时代,文学艺术究竟何为?从邓明的一百首论画绝句,我自然想到了《启功论书绝句百首》。启功作为一位当代书法大师,曾以一百首格调古雅醇厚的七言绝句通论书法,每一首绝句都在高古的意境中通幽于中国书法美学的神髓,同时,启功又以法度悠然典雅的小楷一一誊录。启功先生的这部书法手稿曾被朋友以赏读而骗走,在香港卖给台湾商人,后又被启功自己以高价买回。多年来,我始终以为这是中国书画艺术界无人可以复制的格局与学养。
我想设问的是,当代还有哪一位书画家可以做到此等境界?我还想,那些在当代中国美术界为名利而争其位的书画家,面对启功与《启功论书绝句百首》应该心悦诚服地放下身价,保持谦虚与沉默。还是在“八五新潮”前后,邓明曾多次拜望启功先生,而《守望丹青》有一点却让我感到遗憾,邓明本身也是优秀的书法家,甚至我认为他的书法在他的绘画之上,可他为什么不把他的一百首七言绝句以书法的形式誊录出来,邓明的回答还是“匆忙了!”
2018年3月23日至4月8日,“守望丹青:邓明画坛胜流肖像展”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展出,邓明完成且补上了一百首七言绝句的书法作品,至此在观念上集画、书、诗、论于一体的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得以完成。《守望丹青》作为邓明个人的一部通约诗书画论的博物学文本,从在“八五新潮”形成观念到2018年的最终完成,真的是几乎经历了一生。并且其中还有一点隐密之处让我感佩,邓明是一位对书画资本市场断然拒绝的书画家与美术出版家。这部文本在观念的构成上虽然契合了图像时代,但是对资本市场却完全保持着一个干净的距离。
结语 对资本的抵抗与无界的思考
从1977年“文革”的终结到当下,40年过去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在这40年上演了太多的惊心动魄,历史也到了必须对这40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进行总体反思的时刻了。如果让我从心底透露出一句话,我想言说的是:看惯了在这40年的喧哗与躁动中领尽风骚的那些人与那些事,我欣赏的则是一生守望一种文学艺术观念及学术理想不变且低调行走的谦卑者,这是一种不起眼的人格魅力,即便是挑剔的学者也无法从他们的灵魂中打捞起一丝无知的傲慢。此刻,我到想起《庄子·天道篇》中的一句表达:“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可惜的是,基本上黉门知识分子或书画家都功利得很,大抵做不到这一点。
就我看来,在这40年里,“十七年”与“文革”以来的左倾政治对文学艺术的钳制,被资本与文化生产场的潜规则操控所逐渐替换,文学艺术在看似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自由下,事实上,跌落于另外一种非自由的功利性异化中。从后新时期以来,被资本与剩余价值绑架的文学艺术,较之于被左倾政治碾压的文学艺术是一样的卑微,因此,文学艺术家在资本时代抵抗市场保持人格的洁净,如同在“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抵抗政治一样伟岸。对于文学艺术批评家来说,也是如此。问题是,又有多少文学艺术家及批评家做到了这一点?如果历史向他们设问,谁又敢说自己从不为资本的趋利而拒绝出卖良知?当然,还有一种人,他们以策展的方式伙同书画家一起炒作资本市场,而又回过头来咒骂资本,关键在于,他们还往往把自己称之为著名艺术评论家或著名美术评论家。其实,就当下的文学艺术场之发展态势来看,抵抗资本比抵抗政治还要困难!
关键在于,资本对当下中国艺术市场的操控,是完全无法带入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给予对应性的分析与思考的,当下中国艺术市场的资本操控及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论述的现象来得还要简单且粗暴,甚至原始到连《资本论》在理论上都无法给予解释。在当下中国美术界,无论是守成的书画家,还是当代艺术家,他们私下时时都在企盼着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艺术市场被资本拉动到一个想象的天价,以便让交易后的剩余价值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并且资本对当下中国艺术市场的权力性操控,是相当原始的,也是相当非理性的,甚至不需要布尔迪厄论证的文化再产生逻辑环节,其中完全缺失艺术在非功利性的审美意义与趣味上所沉淀的纯粹与高贵。不要说视觉艺术作品是在符号的代码上显现文化资本的一种知识形式,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艺术批评家与艺术收藏家是缺失文化能力的人,更不要说他们在百分之一、二的程度上是否具有黄宾虹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知识学养了。在某种意义上,视觉艺术作品的存在不是为了审美之意义与趣味的非功利性体验与品鉴,只是为了在市场的交易中掠夺资本的原始积累及剩余价值的获得。很多“艺术收藏家”在身份上是非常暧昧的,说到底,他们也就是纯粹获利的商人与职场官员什么的,他们不懂艺术,也没有知识学养,更没有艺术信仰,他们介入艺术场只是为了资本的获取,当然,还有那些缺失知识学养的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的推波助澜。因此,资本不再是操控艺术生产场的一种隐蔽权力,而是一种显性的符号暴力。
我特别欣赏布尔迪厄在《权力场、文学场与习性》(“Field of Power, Literary Field and Habitus”)这篇文章中把艺术场划归为一方信仰的领域:“艺术场是一个信仰的领域(The artistic field is auniverse of belief
)。文化生产把自己区别于最为普通的物体生产,在其中,文化生产一定不仅生产出具有物质性的实体,并且还生产出了物体的价值,那就是对艺术合法性的认同。换言之,艺术家或作家的产生与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艺术家或作家是不可分离的。关于艺术家特质之意义的反思就是如此。的确,“艺术场是一个信仰的领域”,在这方领域中,文学艺术家是价值的创造者,这里的价值不是指资本,而是指文学艺术创造者沉淀于其中的非功利性审美体验,文学艺术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纯粹与高贵的文化资本,是人在自由的审美信仰领域中所获取的权力。《守望丹青》是一部低调的中国图像断代美术史,作者以其守望丹青32年不变的艺术观念作为一种信仰投入其中,经历了从保守到前卫,荣辱不惊,到头来既契合了图像时代,又抵抗了资本市场。这种为一个艺术观念不变的朴素守望使得让我以静观动,能够有效地反思40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在喧哗与躁动中所跋涉的逻辑轨迹。当下艺术市场为了资本的暴利性攫取把相关书画炒作到天价时,这部文本在低调中反而以其丰厚的博物学知识学养引起我的瞩目。因为,当下中国美术界缺少的不是资本,而是博物学知识学养。
多年来,我把中国学界诸家关涉中西美术史论的文章一路地看下来,由衷地感受到还是钱锺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与《读〈拉奥孔〉》写得最佳,其的确是缜密博旷的大师之作,我心里充满了佩服。多年来,我反复拜读了钱锺书的《管锥编》《谈艺录》与《七缀集》等,在学科意识上,才真正地领受到比较文学就是汇通古今中外的博物学,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确应该是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者。近年来,在欧美比较文学系与东亚系等,太多的学者跨界于文学研究之外,把美术、音乐、戏剧与电影等艺术现象摄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全球化的时代,把文学与诸种艺术现象还原于他们本然共存的整体历史语境下,给予跨界(transboundary)的互看与思考,这已成为了主流趋势。关于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艺术批评的书写及其相关理论体系的构建,其领导思潮者恰恰不是那些在本行当下从事专业批评的写手,而是从哲学、美学、文学或社会学跨界过来的学者,其实,从康德、黑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和伯明翰学派(School of Birmingham)诸家学者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有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与布尔迪厄等。
究其时代的本质而言,文学艺术研究的无界(unboundary)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谈“跨界”的合法性什么的。在这个无界时代,如果学人依然把自己的研究闭锁在自己那方狭小的一亩三分地,那就是公然宣称自己落伍于这个时代。在比较文学专业下,有一个跨学科研究,也可以称之为比较艺术学,我也只是在跨学科研究方向下寻找一位在艺术观念上的持久守望者,以一个低调的守望视点,对40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做一次思潮性的互看与反思;因为知识分子大都顺时应变,经不起功利性的诱惑,所以坚守不渝者太少了。由于书写文本空间的有限,我也只是更多地落实在文学与美术的交集场域无界地谈谈而已。
Bibliography 参考文献
Bell, Danie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8.Benjamin, Walter.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Drei Studien zur Kunstsoziologie
. 40 Jahre edition suhrkamp.Frankfurt:Suhrkamp, 2003.Bourdieu, Pierre.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Randal Johnson.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3.Gramsci, Antonio.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2.Lewit, Sol.“Paragraphs on Conceptual Art.” InConceptual Art:A Critical Anthology
.Edited by Alexander Alberro and Blake Stimsonthe.Cambridge:MIT Press, 1999.Marx, Karl.Das Kapital
.Bd.I.Siebenter Abschnitt.Berlin:Dietz Verlag, 1968.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路文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文论选(1949—2000)》,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
[A-Cheng.“Wenhua zhiyue zhe renlei” (Culture Restricts Human Beings).InZhongguo dangdai wenxue shiliao wenlunxuan (1949
-2000)
(Selected Wor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49-2000]).Edited by LU Wenbin.Beijing: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2006.]北岛:《青灯》,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BEI Dao.Qingdeng
(Blue Light).Nanjing: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8.]陈丹青:《无知与有知:答〈边缘〉杂志许宏泉问(节录)》,见陈丹青:《退步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CHEN Danqing.“Wuzhi yu youzhi:DaBianyuan
zazhi Xu Hongquan wen (jielu)” (Ignorance and Knowledge:Answering Xu Hongquan's Question inEdge Magazine
[Excerpts]).In CHEN Danqing,Tuibu ji
(Regressive Collection).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仍然在野:纪念星星画展28周年》,《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2日,第24版。
[——.“Rengran zaiye:jinian xingxing huazhan 28 zhounian” (Still Be Out of Power:Commemorating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he Stars Exhibition).Nanfang zhoumo
(Southern Weekend
), November 22, 2007:24.](宋)邓椿撰,(宋)刘道醇纂:《画继·五代名画补遗》卷第9,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刻本。[DENG Chun, LIU Daochun.Huaji:Wudai minghua buyi
(Painting Succession:Supplementary Works of Five Generations).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Chen Taoren's bookstore in Lin'an Prefecture of Song Dynasty.]邓明:《守望丹青》,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
[DENG Ming.Shouwang danqing
(Protecting Chinese Painting).Shanghai:Shanghai Dictionary Press, 2017.]高名潞:《'85青年美术之潮》,《文艺研究》,北京:中国艺术研究主办,1986年第4期。
[GAO Minglu.“'85 qingnian meishu zhichao” ('85 Youth Art Tide).Wenyi yanjiu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 4 (1986).](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GUO Maoqian.Yuefu shiji
(The Collection of Folk Songs and Ballads in the Han Style).Vol.3.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宋)郭熙、郭思编:《林泉高致》,明刻百川学海本。
[GUO Xi, GUO Si, eds.Linquan gaozhi
(The Elegance of the Bamboo and Spring).Block-printed edition ofBaichuan xuehai
of Ming Dynasty.](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庄子》,见《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缩印浙江书局光绪初年汇刻本。
[GUO Xiang, LU Deming.Zhuangzi
(Chuang-tzu).InErshier
zi
(Twenty-two Masters).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1985.]韩少功:《文学的“根”》,吴义勤主编:《韩少功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HAN Shaogong.“Wenxue de ‘Gen'” (The “Root” of Literature).InHan Shaogong yanjiu ziliao
(Research Materials of Han Shaogong).Edited by WU Yiqin.Jinan:Shando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唐)韩愈著:《原道》,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HAN Yu.“Yuan Dao” (Origin of Dao).InQuan tang wen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the Tang).Vol.3.Edited by DONG Gao.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1990.](明)胡应麟:《诗薮》,清广雅书局丛书本。
[HU Yinglin.Shi sou
(Poetry).Series Edition of Guangya Bookstore in Qing Dynasty.]黄宾虹:《黄宾虹文集·题跋编·诗词编·金石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HUANG Binhong.Huang Binhong wenji
(Anthology of Huang Binhong).Shanghai: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1999.]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HUANG Ziping, CHEN Pingyuan, QIAN Liqun.“Lun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sanren tan
(Three Persons Talking abou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8.]《今天》编辑部:《致读者》,《今天》(创刊号)1978年第1期。
[Editorial Department ofThe Moment
.“Zhi Duzhe” (To the Readers).Jintian
(The Moment
) (first issue) 1 (1978).](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本,1980年。
[KONG Anguo, KONG Yingda.Shangshu zhengyi
(Annotations onShangshu
).InShisan jing zhushu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Thirteen Chinese Classics).Edited by 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李小山:《中国画之我见》,《江苏画刊》,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7期。
[LI Xiaoshan.“Zhongguohua zhi wojian” (My Opinions of Chinese Painting).Jiangsu huakan
(Jiangsu Pictorial
) 7 (1985).]李学勤:《周文王遗言》见于《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第12版。
[LI Xueqin.“Zhou wenwang yiyan” (The Last Words of Wen Wang of Zhou State).Guangming ribao
(Guangming Daily
), April 13, 2009:12.]——:《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第6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Lun Qinghua jianBao Xun
de jige wenti” (Several Issues on the Bamboo Slips aboutBao Xun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Wenwu
(Cultural Relics
) 6 (2009).]——:《重说〈保训〉》,《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31卷第1期。
[——.“ChongshuoBao Xun
” (Re-comment onBao Xun
).Shenzhe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 31, no.1 (2014).]栗宪庭、Art World:《85美术新潮——栗宪庭访谈》,见于“艺术档案网”http://www.artda.cn/view.php?tid=5222&cid=23,2011年5月12日检索。
[LI Xianting and Art World.“85 Meishu xinchao— Li Xianting fangtan” (85 Art Trends:Interview with Li Xianting), http://www.artda.cn/view.php?tid=5222&cid=23, (May 12, 2011).]
(南朝)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LIU Xie, HUANG Shulin, LI Xiang, YANG Mingzhao.Wenxin diaolong jiaozhu
(Annotations onWenxin diaolong
),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刘心武:《班主任》,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LIU Xinwu.“Ban zhuren” (Head Teacher).Renmin wenxue
(People
's Literature
) 11 (1977).](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
[LU Deming.Jingdian shiwen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Vol.1.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5.](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Max, Karl.Ziben lun
(Das Kapital).Vol.1.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孟子注疏》,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本,1980年。
[Mengzi zhushu
(Annotations onMencius
).InShisan jing zhushu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Thirteen Chinese Classics).Vol.2.Edited by 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PI Xirui.Jingxue lishi
(A History of Confucianis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秦牧著:《艺海拾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QIN Mu.Yihai shibei
(Sea of Art).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清华简《保训》,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西书局,2010年版。
[Tsinghua bamboo slipsBao Xun
.In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Vol.1.Edited by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Unearthed Document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LI Xueqin.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0.]尚辉:《“伤痕美术”的历史记忆》,见于《上海艺术家》,上海:上海艺术研究所主办,2005年第5期。
[SHANG Hui.“‘Shanghenmeishu' de lishi jiyi”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Scar Art”).Shanghai yishujia
(Shanghai Artist
) 5 (2005).](清)沈德潜:《说诗晬语》,清道光青照堂全书本。
[SHEN Deqian.Shuoshi zuiyu
(Commentaries on Poetry).The Full Version of Qingzhao Tang in Daogua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SUN Xingyan, CHEN Kang, SHENG Dongling.Shangshu jinguwen zhushu
(Annotations onShangshu
's Modern and Ancient Texts).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清)唐岱撰:《绘事发微》,亁隆刻本。
[TANG Dai.Huishi fawei
(Explain the Subtleties of Painting).Block-printed edition in Qianlong period.]汪己文编:《黄宾虹书简》,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WANG Jiwen, ed.Huang Binhong shujian
(Letters of Huang Binhong).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88.](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本,1980年。
[WANG Bi, KONG Yingda.Zhouyi zhengyi
(Annotations onZhou Yi
).InShisan jing zhushu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Thirteen Chinese Classics).Vol.1.Edited by 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清)王引之著:《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道光七年刊本。
[WANG Yinzhi.Jingyi shuwen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al Meaning).Nanjing:Jiangsu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85.]王中秀著:《黄宾虹十事考·贞社时代》,王中秀编:《黄宾虹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WANG Zhongxiu.“Huang Binghong shishi kao:zhenshe shidai” (Huang Binhong's Ten Things:Zhenshe Age).InHuang Binhong nianpu
(Chronicle of Huang Binhong).Edited by WANG Zhongxiu.Shanghai: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2005.]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
[XU Zhongshu, ed.Jiaguwen zidian
(Oracle Bone Text Dictionary).Chengdu:Sichuan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 1989.](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影印经韵楼藏版。
[XU Shen, DUAN Yucai.Shuowenjiezi zhu
(Annotations onShuowenjiezi
).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1988.]曾镇南:《让世界知道他们——读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读书》1985年第6期。
[ZENG Zhennan.“Rangshiije zhidao tamen—Du Liu Suola de ‘Ni biewu xuanze'” (Let the World Know Them:Read Liu Suola's “You Have No Choice”).Dushu
(Reading
) 6 (1985).](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卷第一,明刻津逮祕书本。
[ZHANG Yanyuan.Lidai minghua ji
(Records of Famous Paintings of the Past Dynasties).Vol.1.Block-printed edition ofJindai mishu
in Ming Dynasty.](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本,1980年。
[ZHENG Xuan, JIA Gongyan.Zhou Li zhushu
(Annotations onZhou Li
).InShisan jing zhushu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Thirteen Chinese Classics).Vol.1.Edited by 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东汉)郑玄注,王应麟辑,孔广林增订:《尚书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
[ZHENG Xuan, WANG Yinglin, KONG Guanglin.Shangshu Zhengzhu
(Annotations of Zheng onShangshu
).InCongshu jicheng chubian
(Preliminary Edition of Series Integration).Edited by WANG Yunwu.Shanghai:Commercial Press, 1937.](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本,1980年。
[ZUO Qiuming, DU Yu, KONG Yingda.Chunqiu Zuo zhuan zhengyi
(Annotations onChunqiu Zuo zhuan
).InShisan jing zhushu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Thirteen Chinese Classics).Vol.2.Edited by RUAN Yu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