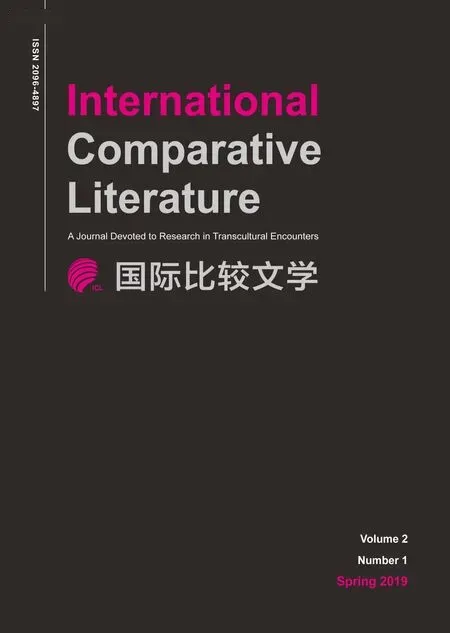巫 鸿:《 “空间”的美术史》
《“空间”的美术史》一书记录了巫鸿在OCAT研究中心的系列演讲,包含“空间与图像”“空间与物”和“空间与总体艺术”三部分内容;也是他对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总结。无论是作为一种概念还是研究方法来说,“空间”都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巫鸿强调“空间”其实是想开拓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其言说目的主要是在反思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发掘空间概念在艺术分析中的方法论上的潜能。
一、图像、器物与总体艺术中的空间表达
在“空间与图像”一讲中,巫鸿反思了西方传统美术史研究中使用“空间”概念的两种基本方式,即“图像空间”与“视觉空间”。前者将空间理解为构成图像意义的一个因素,后者则将空间视为视觉感知及再现的内涵和手段;前者沿袭图像学的思路,后者则属于形式分析和心理学的系统。而那些立足于西方艺术的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分析。中国古代艺术作品呈现出的也是基于特殊目的的选择性表达,故而要对这种表达进行合理且有效的阐发,就需要以对作品本身的分析为基础,进而剖析不同空间表现模式的内在逻辑与文化脉络。他对东汉晚期画像砖、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武梁祠画像等作品的分析,无不体现这一思路。
“空间与物”这一部分是从反思“空间”在视觉表现中的基本含义开始的,着眼点从图像扩大到了器物。他认为“如果说平面图像中的空间是由图像本身构成的话,立体形象则不但构成空间,而且与空间共生、并存和互动。”故而研究者既要考虑不同器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又要考虑每个器物与空间的互动。他以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古代重“器”的历史传统与艺术表现,认为中国古人对“器”的执着与古代礼制有关。说明引进“空间”的因素来研究“器”,有助于发现“器”的实体与空间的共存和协商关系,及因此而呈现出来的外在形制与文化符码的关系。
“空间与总体艺术”一讲又进一步将图像和器物纳入了建筑和行为的空间中去讨论,也对美术史中的空间概念进行了协调和拓展。他认为视觉和物质的空间、知觉空间和经验空间递进综合而成了一个“总体空间”,此种空间所对应的是整个城市、地区或文化网络,具有整体性特征。保存较好的建筑、器物、绘画和装饰的综合体(如保存较好的墓葬)方能体现出此种总体空间的特质。
二、对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反思
若说《“空间”的美术史》与巫鸿以往的文章、著作略有不同,便是其对研究方法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探讨,如他在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强调对“关系”“整体”及差异性的把握。此外,他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体现出较强的方法论意识和科学分析倾向。
(一)对“整体”与“关系”的把握
此书在总结美术史研究方法的时候,比较重视对“整体”与“关系”的把握,认为当我们面对一个画面,把握它的总体空间结构和基本视觉逻辑是首要的,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不同视觉语言的空间关系,从而真正理解其表达逻辑。如其在讨论空间与物的时候,以青铜器铭文、棺材、枕头等为例,分析了器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辩证关系所呈现的表达效果与承载的文化内涵。又以镜子、椅子等为例,分析了特定空间中物性与主体的特殊关系,及此种关系是如何被呈现的。
他在讨论敦煌艺术的时候也强调敦煌作为一个实际社会空间的完整性与多元性,认为莫高窟只构成了这个地理和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因此,佛教艺术不可能是一个独立而封闭的艺术传统,而是与其它文化和视觉传统并存的。建筑、图像、器物等各种艺术形式所呈现出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整体,而不只是简单化的意义联系。如其所言:“当我使用‘总体空间'的概念重新考虑美术史的资料时,我们很自然地突破‘佛教美术'和‘墓葬美术'等传统研究领域和学科划分,转而考虑这些资料的相互联系以及对于理解真实历史环境的作用。”此种对关系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与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等人的思路是一致的:海德格尔认为空间就是人与世界相互关联形成的结果,列斐伏尔则认为空间与社会之间充满了互动关系。
(二)对差异性的重视
注重中西的差异,及不同时期、不同属性艺术形式的差异也是复杂空间得以被剖析、重建的一个重要条件。把某一艺术传统作为先例去衡量其它艺术传统,以一时期之标准衡量另一时期之艺术,以绘画的特质去框定建筑的特质等等行为,皆无助于准确而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如中国绘画中并不缺乏对三维空间的表现,只是其使用的手法与西方不同。又如巫鸿提到的“重屏”构图、“正反构图”等皆是中国古代绘画中较为常见的非线性透视的空间表现方法。他强调古代画论中“经营位置”与西方艺术中“构图”的区别:认为后者隐含了西方绘画中散点透视等概念;而前者强调的是画家基于创作意图来安排绘画形象的位置,并不暗含透视等技术性的构图方式。他在分析晚唐时期莫高窟壁画《劳度叉斗圣变相》与变文的关系时也指出,变文是一种时间叙事,而绘画是空间叙事,故而要真正理解壁画的内容,就必须从其整体的空间布局与视觉逻辑出发,而不是依赖变文时间逻辑和故事顺序的佐证。
(三)对理论与方法的不同态度
巫鸿的研究中体现出了对理论和方法的不同态度,认为“理论总是带有某种终极的意味。而美术史不是做这个,不是追求或证明某种理论。美术史是解释美术,通过解释美术理解历史,它不是做理论的。所以我多用‘方法'这个词,因为方法是工具,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艺术和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一观点并非否定理论本身,而是强调对具体材料与形象分析的重视。他强调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对“空间”的表现,而非中国古代的“空间”概念。概念和理论的抽象性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将存在的物质属性遮蔽,而要通过解释美术理解历史和文化,就不能离开具体作品和它所处的时代环境。只有接近具体才能充分发掘历史研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双重丰富,才能实现方法论的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实际研究。而“空间”作为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图像、雕塑、器物和建筑这些美术史材料的传统分类划分”,“可以帮助我们将视点从孤立的图像和作品转移到图像间和作品间的关系上来”,“可以帮助我们连接和综合书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前者为艺术品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后者为艺术品产生和展示的条件和环境”。
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将研究落到实处之外,巫鸿还比较讲究经验式或实证式的分析,强调从视觉方面更清楚、有条理地分析画作,而不是一来就跳到解释层次。这三场讲座以及作者的其它作品,对分析方法的运用无处不在。他也提到了“这个讲座的主要目的是开始建构一种分析语言”。
三、“空间”方法在不同分析层面的尝试
从该书观点来看,“空间”方法的逻辑出发点和重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将空间视为具体图像或作品的实际存在形态,分析作品的内容、形式、产生的缘由与展示的环境等;二是,在更深的层面,将空间视为“由图像或作品建构起来的结构性联系”。前者是顺着作品给出的逻辑进行阐释,研究内容如“表达什么”“如何表现”“有何影响”等,此种研究有利于读者深入地解读文本及与文本相关的内容,但却难以真正将文本视为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整体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这样的研究可以很细致,但往往缺乏深度。后者则尝试摆脱作品的逻辑进行阐释,在第一种研究的基础之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作品建构起来的结构性联系是隐藏在作品逻辑之下的,是更深层面的,毕竟作品空间性的叙事是如何完成的有其自身言说的逻辑;要对其进行有效挖掘,就不仅要会“顺着说”,还必须学会“打破逻辑地说”。后者和前者相比,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拓展,更意味着思维的变革。
巫鸿对美术史研究方法的探索是深刻而富于创见的,但在建构起方法论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每一个具体案例的研究中,“空间”到底指向什么。巫鸿讨论“空间”似乎更强调其方法性,即在作品本身呈现出的和暗含的各种关系之中,空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以之为切入点有助于穿透文本逻辑。故而巫鸿所强调的还是作为一种方法的空间,而作为问题的空间往往是更具有意味的。其次,此种所谓更为深广的空间方法和传统的图像研究或形式研究究竟是否存在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如何实现摆脱作品的逻辑进行阐释,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巫鸿在本书及他的其它作品中通过对诸多案例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阐释策略。再次,不同种类的空间概念如何在综合性的研究中解释和使用,如何将不同领域的空间探讨置入带有普遍性的空间分析框架之中,使其不仅具有理论生成性,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历史作品的空间分析的有效性如何得到印证?作品是以怎样的形式展现出特定的空间结构,空间又是如何作为一种表达产物实现其作用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者们不断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