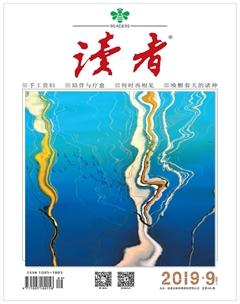没有答案的生命选择题
傅志远

重症监护室里有一位老太太,做完手术后由于呼吸衰竭,一直无法脱离呼吸器,也拔不了管,已经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30多天。
病人本身已经因中风而卧病在床多年,这次又因为长期使用呼吸器而衍生肺炎和败血症,目前处在败血性休克与多重器官衰竭的状态。最后一线(临床上将抗生素分为三线:一线抗生素非限制使用,第二线抗生素限制使用,第三线抗生素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抗生素已经用上,强心剂也已使用,但休克依然没有改善,预计死亡率近100%。家属已有心理准备,也签署了“临终放弃急救同意书”,不再对病人施以于病情无任何积极意义的电击与心脏按压等急救措施。
“病人从昨夜开始,血压越来越低,请问还要不要增加强心剂的剂量?”查房时,护士向主治医生报告前一天的状况。“不用了,再调剂量也没什么用,维持现状就好。”主治医生边说边走,脚步完全没有停下来,显然,他想快点结束对这个病人的查房。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10个小时没有小便,值班医生给病人打过两支利尿剂,还是没有反应。”护士接着说。
“这是正常的,血压太低,所以肾脏的血液不够,当然不会有小便,这个病人的肾脏已经衰竭了。”主治医生依然淡淡地说。他很快走向下一个病人,对这个病人的病情变化既不发表意见,也不做任何处理。
“不用做点什么吗?他就这样走了?”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似乎对于主治医生什么都不处理的态度不甚理解。“虽然家属已经同意放弃急救,但不代表什么治疗都不用做吧!我实在不能接受,身为主治医生竟然什么都不管!”主治医生的身影已经远去,但护士似乎仍无法释怀。
“难道你也跟他一样冷血吗?就不能再替这个老太太想想办法?我觉得病人很可怜。”当时我还只是跟在老师后面学习的实习生,主治医生一走远,这个护士便看着我。可惜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决定权。
面对生死难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我也尚在学习中,不敢对谁是谁非骤下论断。但我相信,在她的价值观里,任由病人自然死亡,有违医生的职责。
“从医疗的角度来看,是应该再把强心剂的剂量调高些,甚至要考虑帮病人洗肾。”我自言自语。但我也不知道对一位临终病人是否真的應该这么做,况且,我还只是实习生,我不能、也不敢违背主治医生的命令。
又过了一天,病人虽然没有起色,但也不好不坏地撑过这一天。
第二天,主治医生查房看到这个病人时,眉头皱了一下,说:“嗯?她还没死?”
听到主治医生这么说,护士气得拍了桌子:“你这样说真的太过分了!身为病人的主治医生,你怎么可以诅咒病人死亡?”
主治医生不理会她的怒吼,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那你觉得她会活吗?”
激动的护士一时为之语塞,但看得出她相当不服气。
眼见气氛越来越僵,为了缓和这种剑拔弩张的场面,我赶紧来打圆场:“我想护士没有恶意,或许把药物做些调整,再联系肾脏科的医生来帮病人洗肾,说不定老太太可以撑得久一点。”
这时候主治医生看了我一眼,很严肃地告诉我:“你自己也说了,多做治疗只是‘撑时间罢了,病人已经撑了一个月,难道还不够吗?你觉得再多撑几天,意义何在?你可知道家属已经照顾得心力交瘁?既然死亡是预料中的事,早一点发生,对病人、对家属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或许主治医生之前的那句话不怎么厚道,但听完这番解释,我也觉得他这么做似乎没有错。
一般来说,这类病人临终前,血压会越来越低,接着心跳会越来越慢,直到停止。家属对治疗最后的决定,是让这个状况自然发生、自然结束,以不增加病人的痛苦为原则,不做多余的电击与心脏按压。
虽然我们预期病人的败血性休克应该撑不了太久,但什么时候会死亡,也真的很难准确预测。接下来的几天,在没有任何积极治疗的情况下,病人的血压低到量不出来,本人也早已进入弥留状态,但预期中下一步的变化始终没有发生,心脏依然靠仅有的一点强心剂顽强地跳动着。
其实大家都知道已经没有治疗可做,换个更直接的说法:病人正在“等死”。既然家属已经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医疗人员的态度也会相对消极,原先对主治医生的态度颇有微词的护士,也不再发表意见。
主治医生甚至连病情解释都免了,他认为应该给家属多点空间与时间,让他们与亲人做最后的相处。
“把强心剂停掉吧!”某天早上,主治医生突然下了这个命令,这让我们大感惊讶。
“您确定吗?这样真的好吗?”虽然在他面前我只是个学生,但也忍不住发出质疑。
“我再强调一次,很多事情该来的还是要来,病人的死亡并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加速了中间的过程,这也是在减少对病人与家属的折磨。”主治医生态度很坚定地一字一句说出他的想法。
在强心剂停掉后没多久,病人便去世了。主治医生到场确认了病人的死亡,也确认家属对整个治疗过程完全了解,没有疑义。
送走病人之后,我继续随着主治医生查房。“你觉得我无情吗?我带你去急诊室看一看。”主治医生带着我去急诊室看其他的病人。
“目前急诊病人等待住院的状况如何?”
“还有三个病人在等重症监护室的床位,其中一个待床已经超过72小时。”
急诊总医生向前来巡诊的主治医生回报。
我跟随老师看过这三个病人:一个是急性心肌梗死,一个是严重外伤患者,还有一个甚至因为心肺衰竭已经使用了体外维生系统。每个病人的情况都相当不稳定,都急需转进重症监护室,可惜重症监护室床位有限,因此,虽然病情危急,但也只能继续躺在急诊室。
“这几个病人,每一个都比楼上那个老太太更需要住进重症监护室。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有义务做合理的分配。”老师的这番话启发了我。
“我们要救的不是‘哪一个病人,而是‘这一群病人。
“一个注定早晚会死亡的病人,我们不应该投入太多资源做无效医疗,反而应该把资源集中分配给更需要的病人。
“就像在战场上,当我们资源有限时,我们该救最严重的,还是该救最有机会存活的?
“在医疗上我是你的老师,但医疗以外的伦理问题,请你自己想一想。”
多年过去,现在的我,在医疗能力上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实习生的水平,而医疗以外的伦理问题,在看尽生死之后,我也有了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