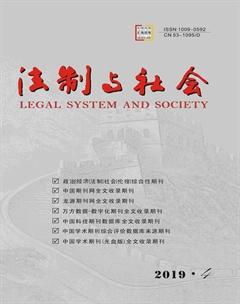盗窃他人未激活信用卡并透支之行为定性
摘 要 我国《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罚。盗窃他人未激活信用卡,将之激活后透支的行为是否也应认定为盗窃罪。本文对“信用卡”的范畴及该条规定的;立法本意作了探讨。
关键词 信用卡 盗窃 冒用信用卡
作者简介:郑阁林,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4.024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被害人王某至A公司工作。工作期间,A公司为王某办理了一张银行信用卡,后王某因离职未能及时领取银行通过邮件寄送给其的信用卡。2013年1月,犯罪嫌疑人任某(系王某同事)未经过王某许可,擅自领走了上述邮件。之后,犯罪嫌疑人任某冒充王某,按照邮件中步骤激活了该张信用卡。嗣后任某将上述信用卡用于个人消费,截至案发时共拖欠信用卡本金人民币10370.20元无力偿还。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于任某的行为进行定性是否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办案人员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任某主观上明知邮寄给王某的邮件中的物品为王某离职前所申领的信用卡,仍然擅自领走,将卡占为己有,系盗窃行为。虽然盗窃时信用卡尚未激活使用,但卡片寄送时附随的相关材料中已写明了激活该信用卡所必需的要素,因此该信用卡系处于“准有效”的状态,只要按照邮件中指示的步骤激活后随时可以开卡使用,该信用卡已具有价值属性。任某虽然窃取的是他人未生效的信用卡,可其之后有效的激活了信用卡并使之功能生效,并将之用于透支消费,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构成盗窃罪。还有一种意见则是认为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所规制的“信用卡”的范围应当限定为已生效的信用卡,排除了尚未被激活的信用卡。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任某所窃得的信用卡尚处于未激活的状态,不具备有消费、提现等信用卡所应有的支付功能,因此不属于刑法上对信用卡的界定范畴。任某激活信用卡后再使用的行为是一种冒用行为,因此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争议,主要是因为对于信用卡概念范畴的理解不同,刑法所规范的“信用卡”是否应包括尚未被激活的信用卡。要正确对该行为进行认定,有必要对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重新进行理论梳理,明晰立法原意。
二、刑法意义上“信用卡”的概念与界定
尚未生效的信用卡是否属于刑法上所规范的“信用卡”的调整范围?目前关于“信用卡”的法律定义主要如下:199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所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2004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颁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2010年7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这三部法律规章中,数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颁布的立法解释法律效力级别最高,而且是从刑事法律范畴对信用卡的内涵外延予以界定,笔者认为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应依据该解释去认定信用卡。首先,信用卡的载体是电子支付卡;其次,其发行主体只限于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最后,其功能具有特定性,限于消费、信贷、存取款等。对照以上要素,我们可以发现未激活的信用卡不能满足第三点,也就是其还没有完成激活步骤,不具有信用卡必须具备的功能属性,因此不能符合刑法规范对“信用卡”内涵及外延的要求。
三、刑法中关于盗窃信用卡后又使用信用卡规范的法理分析
关于盗窃信用卡后又使用该信用卡的行为该如何定性,早在198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答复中首次对盗窃信用卡又使用的行为作出固定,认定盗窃一罪 。之后在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规定》,重申了窃取他人信用卡并予以冒用的,依照盗窃罪的条文处罚。1997年在修订刑法的过程中,立法者对以上答复以及《决定》的内容予以全盘接受,增设条款直接明确盗窃信用卡后予以冒用的以盗窃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虽然立法已对窃取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有了明确规定,但理论界对此如何定性及其适用分歧并未停止,主要反映在以下几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也就是说无论法条是否做出这样的规定,行为人盗窃并使用的,理所当然成立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该款规定属于牵连犯,因为窃取信用卡后使用的行為侵犯了两个客体,其手段行为(盗窃)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构成盗窃罪,其目的行为(冒用他人信用卡)侵犯国家金融层面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该定盗窃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吸收犯的处罚原则,虽然行为人实施了数个不同的行为,但以盗窃作为主行为吸收冒用这一从行为,所以应定盗窃罪。 同时,也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将该行为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理由是窃取了信用卡并不意味着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行为人是通过冒用信用卡从而获得他人财物,因此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冒用的规定,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
在上述处理结论中,笔者认为前三种皆有不尽完善之处,而当下的立法规定亦不十分妥当,上述行为应当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理由在于:
首先,批复将窃得他人信用卡后又予以使用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其所依照的是刑法上“事后不可罚行为”原则,将盗窃后使用窃得的信用卡的行为定位成盗窃犯罪的延续,行为人在非法窃得被害人名下的信用卡时即已触犯盗窃罪,其后的冒用信用卡不过是先前盗窃信用卡的继续,是盗窃罪的事后不可罚行为。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注意到盗窃并使用信用卡和“事后不可罚行为”之间在构成要件上所存在的差异。理论上“事后不可罚行为”的适用,存在两个阶段,一是先前行为,一是继起行为。先前行为是一个能够在刑法里独立评价、构成犯罪的行为。即使未发生后续的行为,我们仍可以对先前行为进行单独认定。就一般盗窃行为而言,盗窃对象的价值必须要达到法律规定的一定数额方能构罪。回到盗窃信用卡本身,盗窃对象信用卡实质上系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凭证,其自身的财产价值微小,持卡人信用卡被盗后其损失的只是一个挂失成本,并不会直接导致账户内财产受损。作案人即使窃得他人所有的信用卡,他并非能够直接获得信用卡账户里面的资金。其非法获利必须依靠之后的冒用行为才能实现。因此,一般来说光窃取信用卡并不能满足盗窃罪对犯罪金额的要求,必须依赖冒用的情节。既然盗窃行为无法单独够罪,事后不可罚又从何谈起。
其次,以牵连犯处断的方式也有所不妥。刑法中的牵连犯针对的是数个行为,且每个行为之间相互牵连。如前所述,先前窃取信用卡并不一定满足盗窃罪对定罪金额的要求,即使随后的冒用行为能构罪,也不符合牵连犯的构成要件。退一步说,即便窃取信用卡的行为满足盗窃罪对犯罪金额的要求,根据牵连犯择一重处的通说,我国刑法上同一犯罪数额下,信用卡诈骗罪的最高量刑高于盗窃罪,对该类行为也应该从重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处罚而非盗窃罪。
再次,该条规定同其他关于信用卡的司法解释之间存在冲突,立法规制导致了罪责刑的不一致。2009年,高法院、高检院共同发布了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根据该解释,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如信用卡账号、密码,之后通过互联网、手机等终端使用的行为属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即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该解释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之间存在较大冲突。虽然两者从行为对象上看略有不同,一个是实体卡,一个是信用卡信息资料,但实质都是通过窃取行为实现了对他人的信用卡帐户的掌控,进而通过使用行为实现目的。但由于立法冲突,导致了不同的法律适用结果。通过比照法定刑、起刑点,可以看出盗窃罪同信用卡诈骗罪在量刑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样是“数额较大”的情形,假设是冒用型的信用卡诈骗行为,犯案金额在人民币5000元到50000元范围内,对应的主刑是有期徒刑五年以下或者拘役;而盗窃金额在人民币1000元到3000元范围内,对应的主刑仅为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拘役或者管制。
最后,对窃取信用卡后又冒用的行为规定为盗窃罪,不仅忽视了国家金融体系对信用卡管理制度的保护,还会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造成困扰。比如说,行为人窃得信用卡后在冒用中,因为一些意志外的因素介入而未得逞,应成立盗窃罪的未遂还是信用卡诈骗罪的未遂?依照当前刑法规定,应认定为盗窃罪对未遂形态,但实际上其盗窃行为已实施完毕,只是其后的冒用信用卡诈骗活动未遂,显然不合理。但如果对该行为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则不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注释: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6年11月3日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王平盗窃信用卡骗取财物如何定性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
张明楷.支付用Card犯罪的现状、立法对策与研究课题//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任景辉.信用卡诈骗罪之“冒用”行为定性分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陈明华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8页.
马小平、谭智华.金融诈骗犯罪通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