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博物院藏元青环耳花匜 相关问题研究
文/李 湘

图一 元 青花折枝灵芝纹环耳匜 安徽博物院藏

图三 山西北峪口壁画墓备茶图
匜是先秦时期礼器中的水器,质地以青铜为主,用于祭祀祈祷前净手,以示对神灵的尊重。此外也用于宴飨。匜最初造型为椭圆形器身,一侧置流,对侧设鋬,底部有三足或四足防止倾倒。春秋战国之后,青铜匜渐少,出现原始瓷、金银、漆等质地的匜。唐宋之际,陶瓷匜大量出现,元代尤其多见,并出现标志性匜器——环耳匜。
安徽博物院藏有一件元青花折枝灵芝纹环耳匜(图一),为1977年安庆市一处元代窖藏出土。该器高4.3、口径13.2、底径8厘米。方唇、芒口、弧形腹,腹部一侧开长方形小槽,置流,流下为卷云状环形耳,砂质平底。整器施白釉,半透明状;器内底部绘折枝灵芝纹,内、外壁近口沿处饰卷草纹一周,釉下青花呈色素雅,构图别致,是国内窖藏环耳匜中的稀世珍品。特别是流下带有元代标志性装饰——卷云状小环耳,给人一种浓厚的异域风情。该器为景德镇窑烧制。

景德镇型环耳匜与龙泉窑型无耳匜对照表
元代瓷匜的种类
元人使用的匜器有两种类型(见表)。安徽博物院藏青花折枝灵芝纹环耳匜属其中一种,即景德镇窑型环耳匜,它是元朝人使用频率最高,也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器具。其特点为薄胎、平底,口沿及底部不施釉,口腹部壁上向外开口,置槽形短流,流下有云形小环系。保定窖藏、高安窖藏、萍乡窖藏、昌平区城关旧县村元墓、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所藏瓷匜亦属于此型。另一类型是龙泉窑型无耳匜,其特点为侈口、厚胎、卧足,平底碗形器身外接槽形短流,流延伸部分上翘,高出口沿。器身与槽形流相接部分未切去,二者之间有小孔相通,流下无环形耳。如元铁可父子墓、汪世显家族墓、新安海底元代沉船、石家庄后太保村元代史氏家族墓出土、台北故宫所藏瓷匜均属此型。上述两类元匜在装饰风格上略有区别:龙泉窑型注重胎装饰,多为印花、刻划花,施青釉,少数饰斑块状褐色铁彩。而景德镇型注重彩装饰,为釉下青花或釉里红,多绘折枝花卉、双凤、兔纹、雁衔芦纹样等,外壁常绘变形莲瓣纹,也有蓝釉描金、卵白釉以及青白釉印花瓷匜。元灭亡后,此类匜销声匿迹。
匜与元人的茶酒生活
据文献记载,商周时期,匜还有一种辅助功能,即作为酒器使用。“《句读》、《义证》、《通训定声》皆云‘匜’是古人沃盥时的注水器,也可兼做注酒之用的酒浆器”,到元代,环耳匜作为酒器的功能被延续下来,在墓葬和窖藏中环耳匜多与玉壶春瓶、台盏等配套使用。如浦城元壁画墓备酒图(图二):高桌上置环耳匜、玉壶春瓶、劝盘,盘中置酒盏,侍者立于桌旁。又如山西洪洞水神庙壁画上的备酒图以及元刻平话插图,画有一或两位侍者,一位手持玉壶春瓶,一位手捧劝盘,盘中置酒盏,桌上有环耳匜、酒樽或梅瓶、酒杓。在这些画面中均不见宋金时期十分流行的注子、温碗。
元人对作为酒器的环耳匜有专门的称谓。如元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二:“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研究者将上述器物与景德镇出土饮食类实物对比发现,这里“盂”即“匜”。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下“古无器皿”条:“古人吃茶汤俱用,取其易干不留津,饮酒用盏,未尝把盏,故无劝盘。今所见定劝盘,乃古之洗。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胡瓶及有嘴折盂、茶钟、台盘,此皆外国所用者,中国始于元朝,汝定官窑具无此器。”文中所说的“有嘴折盂”就是有流的盂,即匜。另据《元史》志第二十八《舆服一》载:庶人“酒器许用银壶台盏盂镟,余并禁止”,可见,在元代“匜”被称做“盂”、“有嘴折盂”、“盂镟”,元人饮酒的必备组合已由宋金时期的注子、注碗、台盏变为银壶(玉壶春瓶)、台盏、盂镟(匜)。
另外,在元代壁画墓里,我们还发现元人使用一种形似无耳匜的容器搅拌和调制膏茶。如山西北峪口壁画墓备茶图中(图三),左侧两位侍女带小孩立于桌旁,桌上有劝盘、台盏、汤瓶,高桌另一侧的两位侍女,一位手持台盏,另一位右手持茶筅在左手托住的带流容器内搅拌;山西屯留元代壁画墓M2东壁的侍女备茶图(图四):壁画上绘有高桌,上置酒樽、盖罐、碗、盏托等器物,右侧侍女同样持带流容器并以茶筅在器内做搅拌状,该容器局部放大,一侧有短流,形似无耳匜,左侧侍女左手托、右手持注子做倾倒状,注子流嘴朝向右侧侍女,似乎是要在其搅拌的时添加注壶中的液体,她们身后有一方石磨盘。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壁画墓备茶图剥落比较严重,部分画面不清楚(图五)。该壁画上绘一位男侍,左手环抱一容器,左手手掌似乎紧紧攥住容器上凸出部位,右手执棒状物在容器里捣鼓。他身后的桌上放绘花盖罐、汤瓶以及三个倒扣的茶盏。有的学者认为该男侍在碾茶,笔者认为不妥。首先,侍者左手环抱容器擂茶不便发力;其次,从画面上看容器内食物容量超过该容器的三分之二,同时侍者手中的棒状物也有一部分没于食物中,若是碾茶,擂棒上下运动恐怕茶末会溅洒出来。最后,从侍者怀中的这件器物形状来看,腹壁曲线缓和,器腹不是很深,器口微敞,既不好碾茶,也不便倾倒茶末。所以,结合山西北峪口、屯留等壁画墓中壁画备茶图情景,笔者认为该男侍者应使用棒状物正在容器内搅拌调制膏茶。可惜男侍左手手掌与容器相接部位模糊不清,推测这件器物应该是带流的,否则制好的糊糊状茶膏不易倒出。
上述壁画墓中添汤、搅拌、调制膏茶的情形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元《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己集“诸品茶”条谓“兰膏茶,以上号高茶。研细一两为率。先将好酥一两半。溶化倾入茶末内。不住手搅。夏月渐渐添冰水搅。水不可多添。但一二匙尖足矣。频添无妨。务要搅匀。直至雪白为度。冬月渐渐添滚烫搅。春秋添温汤搅”。元《饮膳正要》中多处有“酒调一匙头”“温酒调下一匙头”“酒调服之”“以酒一杯和匀温饮之”的记载。由上述文字可知,在调配兰膏茶时,需要有容器装盛茶末及特殊方法提炼的膏、油等,按不同时节分别与冰水、温汤、暖汤等各类酒水调和搅匀。无耳匜的口径约在5-18厘米,在搅拌和调配膏茶时小型无耳匜适合使用者捧在手心、口径大者需一手环抱并攥住其短流,匜口为广口,便于目测膏茶与不同液体混合搅拌的情况,一侧带流便于倾倒出制好的膏状物。

图四 山西屯留元壁画墓M2备茶图(及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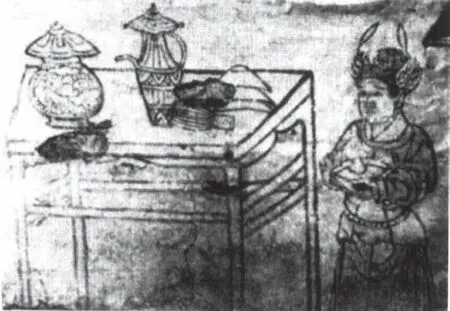
图五 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壁画墓备茶图
装烧之谜
此类景德镇型青花环耳匜芒口而涩底,且口沿部位为一个不封闭式圆形。它不像龙泉窑型匜器口为封闭式圆形,底部刮釉并留有环形垫烧痕迹,说明该器使用环形垫圈仰烧而成。假如环耳匜也采用底与底或口与口一正一覆入炉烧造,如果受力部位为底部,那么涩底应与其他物体紧密接触,平底外侧为受力面,则会留下其他器具的垫烧痕迹。而环耳匜底部并没有装烧痕迹。若受力部位为口沿,从力学角度上分析,圆形器口本身就不具有稳定性,虽然口沿周长不变,而圆弧却容易发生变化。再加之环耳匜的一侧开口置流,口沿的稳定性就更差,外置短流在烧制过程中还会产生向外的拉力。环耳匜在仰烧的情况下器物口沿会产生变形。
从这件青花匜的外部造型可以看到,该器口沿有装烧受压的痕迹,不封闭式圆形口沿几乎处于同一个水平面,没有发现仰烧时器物口沿两头翘呈船形的状况,种种迹象证明,这件器物采用了单件覆烧工艺。
结论
安徽博物院藏元青花折枝花卉纹环耳匜是元代最具特色的器类,从窖藏、考古发掘出土品器物组合以及元代壁画内容,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一种温酒器具,而另一种无耳匜则是用于调制膏茶或食物的容器。青花环耳匜芒口、底涩,且口沿部位为一个不封闭式圆形,这种特殊的造型为其装匣入炉烧制造成了难度,而景德镇工匠以惊人的智慧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