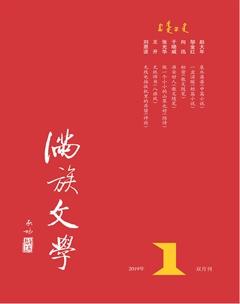淮安好人(外一篇)
于晓威 1970年生,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人,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优秀专家,一级作家,油画家。毕业于上海社科院首届全国作家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第四、第二十八届高研班。曾获第九届全国“骏马獎”、第一至六届辽宁文学奖、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奖等。著有小说集《L形转弯》《勾引家日记》《午夜落》《羽叶茑萝》,长篇小说《我在你身边》《遍地野草》。作品被翻译日、韩等多种文字。曾参加第六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韩国首尔日、韩、中三国作家笔会、台湾纪州庵文学交流会、第61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等文学活动。
少年时学画,曾入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受训,后转入专业文学创作。2015年秋天始,写作之余重拾画笔进行丙烯画创作,其美术作品以强烈的个人生命感受力和独特的审美思考、不拘一格的笔法,受到文学界和美术界许多好评和推介。入展福建省文联“百位著名作家书画展”中国现代文学馆“多民族作家书画展”以及意大利贝纳通“多彩中国”国际画展等。至今已有近百幅作品被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人士购藏,并被权威的中国美术出版社《油画》杂志以及《上海文学》《中篇小说选刊》《文艺报》《莽原》《广州文艺》《南方文学》《新疆文学》《海燕》等诸多杂志发表和报刊媒体推介。
近些年,说不好是怎样一种心境或原因,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实在不可免的,哪怕是旅游,要么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去,要么独自一人行走。
这次到了淮安,我是比会期提前半天到达。现在想想,可能不仅是因为不想让航班跟开会时间弄得太促迫,我是想给自己半天时间,看看淮安。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因我本来就是一个对地理没有概念、也不感兴趣的人,对一切所谓大好自然风光也心不在焉的人——也许是因为多年前,在杭州还是无锡,面对缓缓流淌着的京杭大运河,我问身边人,从这里还能坐船通向北京么?——竟无人能答——我要解脱那份郁结和可笑吧。
婉谢了会议方的盛情陪伴,我一个人走出酒店。此时是下午三点半,我在宽阔的大街上等待出租车,竟寻觅了半个钟头而不见,倒是有时常路过的封闭篷厢的机动三轮车,突突而过。不忍继续耽误时间,我拦住一辆机动三轮,问他:“我要去看就近的大运河,多少钱?”
“十块。”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衣服油渍麻花,寸短头发,黑红面庞。即使端坐在驾驶室,也给人佝偻着腰身但却精明的感觉。
我上了车,他帮我关好后门。但是发动机声音响起,我就思忖:他拉我倒是拉我了,可是到了大运河,我是要下车仔细转转的,他岂能等我?既不等我,街上如此不好打车,我又如何回返?但是要他等我,岂不又窝他的工?于是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下午的时间跟着我,我可能要仔细看看,耽误你一些时间,回头你再拉我回来,我给你一百元车费?”
他扭头“突”的一下笑了,说:“哪里用得上那么多钱?”
看着街道边林立的现代高楼,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这里有老街么?”
“老街?唔,有着呐!叫河下古镇。”
“拉我可好?”
“那先看河下古镇,顺路,回头再拉你看运河。”
在街道上左拐右拐,他拉到的真是好地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抬头一看:连通无数商铺的巷子的迎面处,大牌坊上写的三个字是:估衣街。
我喜出望外地下了车,跟他交代:在此地等我,我转转就出来。然后就一头钻进了估衣街。
我以为街子很短,没想到好深。鳞次栉比的全是淮扬风格的古旧建筑,让我目不暇接。河下古镇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估衣街是淮安最早的商贾繁盛地带,名人辈出。我漫步流连着,不仅是巷子里许许多多外观建筑让我喜不自胜,连了许多内宅和庭院,我也要扒门再三探看的。可笑的是,偶尔见了老宅门上贴了自来水公司的催费通知单,我也以为是什么宝贝,细细地通读一遍。试想,几百年前的估衣和晾衣胜地,说不准这是哪家状元或名商大户,如今被催了水费,怎敌今夕是何年啊。
天空轻雨似有还无。巷子莫名幽深,但是所来无人。真个是岁月如流,伊人情无反顾。窗棂古意斑驳,青条石绵延不绝。正适合我瞻旧的心情。估衣街现时还居住着许多居民,甚至保不准还有许多当年原住民的后代。路遇了两位街坊间彼此串门的老妪,我去搭话,她们给我讲了半天估衣街往事。谈唠间,我依稀间看见老妪身后的墙上,悬挂着醒目的标志牌,与我以往阅读习惯很不一样。但凡各地的老街,只要被保护起来,均是要书写“行人须知”或“游客须知”,规范的是外地客人,但是这个代表估衣街的标牌上写的是:“非机动车和原居民进入来往,给您的行走观览带来不便,敬请多谅”。
估衣街,河下古镇,仅明清两代,就诞生过《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以及上百名进士、举人、翰林和状元的文士麇集之地,它的谦抑与文润之风,着实让我触面可感。
再往里行,巷子越发纵横扩大,蛛街密布。看看时间,已不知觉耽搁快一小时了。我不敢再走,担心巷口等候我的三轮车师傅疑我小人,而他又兀自走掉。于是止步回返,临近巷口,无意间向右手边的一处玻璃店门里望了一眼,目光竟被惊艳了一下。一个女子,应是店子的主人,坐在桌前,煞是美丽,旁边相依而坐的是一个男子,亦为端庄,两个人正在低头专心看着什么,见我走过,一起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回身望了一眼上方的匾额:“淮味楼”。我不敢回头,边走边想,敢情是我入巷时未曾留意这个店子,再想那对男女,许是夫妻,许是姐弟,亲人一定是了。单是他们双双抬头看我的表情,我是打扰了他们低头专注的什么事体呢?一定是在同看一本书了——如果是他俩在看手机,抬头相迎我的目光断不会那么沉静和雍容。
还想起,我透过玻璃看里面摆设时,不像饭店,好像是经营一些地方佐料或药材。这样想来,“淮味楼”与我想象的况味倒是深契了。
……三轮师傅在我身后浅笑。我这才回过神,原来我大踏步走过了他和他的守候。于是上了车,他拉我去运河。
他先拉我去的是里运河,也就是最古老的运河,两岸酒肆喧腾,似乎康乾两帝昨天还来过。后来,又拉我去大运河,让我在河边好一顿流连,直到夜幕降临。顶着一袭历史的古老风尘,我尽兴而归。穿梭在灯光流离的大街上,我跟他起了争执。我的意思是,除了车钱照付,我想请他吃饭,而他坚决不肯。我诚心觉得耽误他几乎两个小时的时间,将近六点,又没有吃饭,而他一再谢绝,坚持拉我回酒店。争执了大约几个回合吧,恰巧我手机响了,是朋友已在催等我吃饭。三轮车师傅正好跟我说:快去快去。
到了酒店楼下,我只好拿出两百元钱递给他,他大声喊:“给我这么多干什么?我只要三十块钱。”
我说,耽误你太久时间,你少赚了钱,又不吃饭……
他干脆发动油门要走,我赶紧求饶。又是争执再三,终于和平谈判,他无奈地接过了我递上的一百元钱,跟我再三道谢和道别。
清代崔旭有首《估衣街竹枝词》:“衣裳颠倒半非新,挈领提襟唱卖频。夏葛冬装随意买,不知初制是何人。”
淮安,古老运河犹在,如今估衣风新。
在松桃
这次来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有一个想法是,能去拜谒一下欧百川故居。
此前,我们曾专门驱车,迤逦爬上了松桃境内盘信镇的旧时抗战公路。
這条公路在七星山脉上,蜿蜒盘旋,陡峭险峻,据1939年国民政府出版的《西南公路路线状况示意图》得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这是由松桃至铜仁最早的一条公路,再由铜仁至重庆,是抗战时期物资运送的重要公路之一。而今早已废弃不用了。
因为这条抗战公路有几十道“胳膊肘弯”, 当年彻夜负责运送战时物资的汽车兵们,每年翻车坠下悬崖的现象时时发生,更兼公路旁有一处自然垂挂的崖泉,据老人们讲,这条泉水是运输兵们饥餐渴饮的救命之水,所以我竟一直以为它就是当年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之一。因为,之前我一知半解所知的“史迪威公路”之“二十四道拐”经典路段,不仅战时背景和大体描摹形态如此,不仅每年有大量运输兵坠入山崖,而且也有半路之中的“救命泉”。
关于“史迪威公路”的“二十四道拐”,据查还有这样一段史闻。1945年3月,美国随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在中国行军途中,无意中拍摄了一张照片——在一座大山的背景下,数十辆军用卡车盘旋行进在犹如蛟龙而直插云霄的公路上,这条公路从山脚到山顶,共有二十四个“S”形弯道,令人震撼。这张照片发表后,引起世界关注。
“史迪威公路”连接滇缅公路,但是因为该照片没有注明拍摄的具体地点,而且是黑白照片,难以参照其它标识,所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引无数人在云南境内寻找,却对这段道路遍寻不得。人们感叹:“它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直到2002年,中国一位研究二战史的民间专家经过横跨数省,跋山涉水,反复比对,终于来到“二十四道拐”的现场,并冒着生命危险攀上悬崖,拍摄到了与当年那位美国记者拍摄的角度和内容一模一样的照片。原来,世界著名的“二十四道拐”不在云南,而是在贵州!
是在贵州的晴隆县境内。二战时期,美国的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二十四道拐”的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二十四道拐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运输任务。——而我眼下所来到的这条抗战公路,虽则也在贵州境内,却不是历史上那条著名的“二十四道拐”。这是我回来后才知道的事。我不知我的内心是否稍许有些遗憾。
下山后,来到欧百川故居。
欧百川故居建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这是一座坐西北朝东南,由门厅、正房和两厢组成的四合院,占地面积200平方米。正房面阔3间,通面阔12米,进深8.1米,穿斗式悬山青瓦顶。欧百川在这座四合院出生的时候,正是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
我恒久地在故居的院子里穿梭和凝望。感觉时间似乎风干了,用力地拧它,还能渗出一些湿意。
欧百川1920年加入国民党黔军,历任排长、事务长、营长,团长,1926年毅然率全团到铜仁投奔贺龙,出任贺龙麾下第一师独立二团团长,自此与贺龙成为莫逆之交,其后又成为师长,并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在抗战中,又屡建奇功,建国后,出任贵州省副省长。1957年,被打成全国著名的六大少数民族右派,文革中继续惨遭迫害,1970年含冤去世,直到1979年被平反。
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在松桃县走出来的抗战名将,除了欧百川之外,仅是少将师长级以上的就有罗启疆、毛定松、曾元三、吴峻人、龙骧、文安庆、涂传德、杨恩贵等等,连、团级的抗战勇士和无名战士更是不计其数。松桃县为当年抗日战争贡献的有生力量几乎支撑了黔军的半壁江山。我还想起,在此前登临松桃抗战公路的时候,有一处即将进入铜仁地区、却又能俯瞰松桃全境的平台,被称为“望乡台”,据说是当年无数松桃将士开赴前线时最后一眼可以回望家乡的地方。
我当时在那里伫立了很久。历史的烟尘覆盖了半个多世纪,我似乎还能听到队伍在日光下,在暗夜中,战士们脚步的卟卟声。
是啊,就像此时此刻,虽然我站在欧百川的故居里,缅想他的战绩,但是又有多少跟欧百川一样的松桃将士们在历史上为民族的自由而奋争啊。于是我又想起,松桃的抗战公路,虽则不是我其时感知到的“史迪威公路”之“二十四道拐”,但是谁能否认,那不是每个鲜活的生命在历史上汇入到巨大抗战洪流中的个体之途呢?
松桃,以后的传说必将还被传说。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
近些年,说不好是怎样一种心境或原因,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实在不可免的,哪怕是旅游,要么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去,要么独自一人行走。
这次到了淮安,我是比会期提前半天到达。现在想想,可能不仅是因为不想让航班跟开会时间弄得太促迫,我是想给自己半天时间,看看淮安。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因我本来就是一个对地理没有概念、也不感兴趣的人,对一切所谓大好自然风光也心不在焉的人——也许是因为多年前,在杭州还是无锡,面对缓缓流淌着的京杭大运河,我问身边人,从这里还能坐船通向北京么?——竟无人能答——我要解脱那份郁结和可笑吧。
婉谢了会议方的盛情陪伴,我一个人走出酒店。此时是下午三点半,我在宽阔的大街上等待出租车,竟寻觅了半个钟头而不见,倒是有时常路过的封闭篷厢的机动三轮车,突突而过。不忍继续耽误时间,我拦住一辆机动三轮,问他:“我要去看就近的大运河,多少钱?”
“十块。”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衣服油渍麻花,寸短头发,黑红面庞。即使端坐在驾驶室,也给人佝偻着腰身但却精明的感觉。
我上了车,他帮我关好后门。但是发动机声音响起,我就思忖:他拉我倒是拉我了,可是到了大运河,我是要下车仔细转转的,他岂能等我?既不等我,街上如此不好打车,我又如何回返?但是要他等我,岂不又窝他的工?于是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下午的时间跟着我,我可能要仔细看看,耽误你一些时间,回头你再拉我回来,我给你一百元车费?”
他扭头“突”的一下笑了,说:“哪里用得上那么多钱?”
看着街道边林立的现代高楼,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这里有老街么?”
“老街?唔,有着呐!叫河下古镇。”
“拉我可好?”
“那先看河下古镇,顺路,回头再拉你看运河。”
在街道上左拐右拐,他拉到的真是好地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抬頭一看:连通无数商铺的巷子的迎面处,大牌坊上写的三个字是:估衣街。
我喜出望外地下了车,跟他交代:在此地等我,我转转就出来。然后就一头钻进了估衣街。
我以为街子很短,没想到好深。鳞次栉比的全是淮扬风格的古旧建筑,让我目不暇接。河下古镇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估衣街是淮安最早的商贾繁盛地带,名人辈出。我漫步流连着,不仅是巷子里许许多多外观建筑让我喜不自胜,连了许多内宅和庭院,我也要扒门再三探看的。可笑的是,偶尔见了老宅门上贴了自来水公司的催费通知单,我也以为是什么宝贝,细细地通读一遍。试想,几百年前的估衣和晾衣胜地,说不准这是哪家状元或名商大户,如今被催了水费,怎敌今夕是何年啊。
天空轻雨似有还无。巷子莫名幽深,但是所来无人。真个是岁月如流,伊人情无反顾。窗棂古意斑驳,青条石绵延不绝。正适合我瞻旧的心情。估衣街现时还居住着许多居民,甚至保不准还有许多当年原住民的后代。路遇了两位街坊间彼此串门的老妪,我去搭话,她们给我讲了半天估衣街往事。谈唠间,我依稀间看见老妪身后的墙上,悬挂着醒目的标志牌,与我以往阅读习惯很不一样。但凡各地的老街,只要被保护起来,均是要书写“行人须知”或“游客须知”,规范的是外地客人,但是这个代表估衣街的标牌上写的是:“非机动车和原居民进入来往,给您的行走观览带来不便,敬请多谅”。
估衣街,河下古镇,仅明清两代,就诞生过《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以及上百名进士、举人、翰林和状元的文士麇集之地,它的谦抑与文润之风,着实让我触面可感。
再往里行,巷子越发纵横扩大,蛛街密布。看看时间,已不知觉耽搁快一小时了。我不敢再走,担心巷口等候我的三轮车师傅疑我小人,而他又兀自走掉。于是止步回返,临近巷口,无意间向右手边的一处玻璃店门里望了一眼,目光竟被惊艳了一下。一个女子,应是店子的主人,坐在桌前,煞是美丽,旁边相依而坐的是一个男子,亦为端庄,两个人正在低头专心看着什么,见我走过,一起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回身望了一眼上方的匾额:“淮味楼”。我不敢回头,边走边想,敢情是我入巷时未曾留意这个店子,再想那对男女,许是夫妻,许是姐弟,亲人一定是了。单是他们双双抬头看我的表情,我是打扰了他们低头专注的什么事体呢?一定是在同看一本书了——如果是他俩在看手机,抬头相迎我的目光断不会那么沉静和雍容。
还想起,我透过玻璃看里面摆设时,不像饭店,好像是经营一些地方佐料或药材。这样想来,“淮味楼”与我想象的况味倒是深契了。
……三轮师傅在我身后浅笑。我这才回过神,原来我大踏步走过了他和他的守候。于是上了车,他拉我去运河。
他先拉我去的是里运河,也就是最古老的运河,两岸酒肆喧腾,似乎康乾两帝昨天还来过。后来,又拉我去大运河,让我在河边好一顿流连,直到夜幕降临。顶着一袭历史的古老风尘,我尽兴而归。穿梭在灯光流离的大街上,我跟他起了争执。我的意思是,除了车钱照付,我想请他吃饭,而他坚决不肯。我诚心觉得耽误他几乎两个小时的时间,将近六点,又没有吃饭,而他一再谢绝,坚持拉我回酒店。争执了大约几个回合吧,恰巧我手机响了,是朋友已在催等我吃饭。三轮车师傅正好跟我说:快去快去。
到了酒店楼下,我只好拿出两百元钱递给他,他大声喊:“给我这么多干什么?我只要三十块钱。”
我说,耽误你太久时间,你少赚了钱,又不吃饭……
他干脆发动油门要走,我赶紧求饶。又是争执再三,终于和平谈判,他无奈地接过了我递上的一百元钱,跟我再三道谢和道别。
清代崔旭有首《估衣街竹枝词》:“衣裳颠倒半非新,挈领提襟唱卖频。夏葛冬装随意买,不知初制是何人。”
淮安,古老运河犹在,如今估衣风新。
在松桃
这次来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有一个想法是,能去拜谒一下欧百川故居。
此前,我们曾专门驱车,迤逦爬上了松桃境内盘信镇的旧时抗战公路。
这条公路在七星山脉上,蜿蜒盘旋,陡峭险峻,据1939年国民政府出版的《西南公路路线状况示意图》得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这是由松桃至铜仁最早的一条公路,再由铜仁至重庆,是抗战时期物资运送的重要公路之一。而今早已废弃不用了。
因为这条抗战公路有几十道“胳膊肘弯”, 当年彻夜负责运送战时物资的汽车兵们,每年翻车坠下悬崖的现象时时发生,更兼公路旁有一处自然垂挂的崖泉,据老人们讲,这条泉水是运输兵们饥餐渴饮的救命之水,所以我竟一直以为它就是当年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之一。因为,之前我一知半解所知的“史迪威公路”之“二十四道拐”经典路段,不仅战时背景和大体描摹形态如此,不仅每年有大量运输兵坠入山崖,而且也有半路之中的“救命泉”。
关于“史迪威公路”的“二十四道拐”,据查还有这样一段史闻。1945年3月,美国随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在中国行军途中,无意中拍摄了一张照片——在一座大山的背景下,数十辆军用卡车盘旋行进在犹如蛟龙而直插云霄的公路上,这条公路从山脚到山顶,共有二十四个“S”形弯道,令人震撼。这张照片发表后,引起世界关注。
“史迪威公路”连接滇缅公路,但是因为该照片没有注明拍摄的具体地点,而且是黑白照片,难以参照其它标识,所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引无数人在云南境内寻找,却对这段道路遍寻不得。人们感叹:“它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直到2002年,中国一位研究二战史的民间专家经过横跨数省,跋山涉水,反复比对,终于来到“二十四道拐”的现场,并冒着生命危险攀上悬崖,拍摄到了与当年那位美国记者拍摄的角度和内容一模一样的照片。原来,世界著名的“二十四道拐”不在云南,而是在贵州!
是在贵州的晴隆县境内。二战时期,美国的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二十四道拐”的滇黔线才能送到前线和重庆。二十四道拐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运输任务。——而我眼下所来到的这条抗战公路,虽则也在贵州境内,却不是历史上那条著名的“二十四道拐”。这是我回来后才知道的事。我不知我的内心是否稍许有些遗憾。
下山后,来到欧百川故居。
欧百川故居建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这是一座坐西北朝东南,由门厅、正房和两厢组成的四合院,占地面积200平方米。正房面阔3间,通面阔12米,进深8.1米,穿斗式悬山青瓦顶。欧百川在这座四合院出生的时候,正是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
我恒久地在故居的院子里穿梭和凝望。感觉时间似乎风干了,用力地拧它,还能渗出一些湿意。
欧百川1920年加入国民党黔军,历任排长、事务长、营长,团长,1926年毅然率全团到铜仁投奔贺龙,出任贺龙麾下第一师独立二团团长,自此与贺龙成为莫逆之交,其后又成为师长,并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在抗战中,又屡建奇功,建国后,出任贵州省副省长。1957年,被打成全国著名的六大少数民族右派,文革中继续惨遭迫害,1970年含冤去世,直到1979年被平反。
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在松桃县走出来的抗战名将,除了欧百川之外,仅是少将师长级以上的就有罗启疆、毛定松、曾元三、吴峻人、龙骧、文安庆、涂传德、杨恩贵等等,连、团级的抗战勇士和无名战士更是不计其数。松桃县为当年抗日战争贡献的有生力量几乎支撑了黔军的半壁江山。我还想起,在此前登临松桃抗战公路的时候,有一处即将进入铜仁地区、却又能俯瞰松桃全境的平台,被称为“望乡台”,据说是当年无数松桃将士开赴前线时最后一眼可以回望家乡的地方。
我当时在那里伫立了很久。历史的烟尘覆盖了半个多世纪,我似乎还能听到队伍在日光下,在暗夜中,战士們脚步的卟卟声。
是啊,就像此时此刻,虽然我站在欧百川的故居里,缅想他的战绩,但是又有多少跟欧百川一样的松桃将士们在历史上为民族的自由而奋争啊。于是我又想起,松桃的抗战公路,虽则不是我其时感知到的“史迪威公路”之“二十四道拐”,但是谁能否认,那不是每个鲜活的生命在历史上汇入到巨大抗战洪流中的个体之途呢?
松桃,以后的传说必将还被传说。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