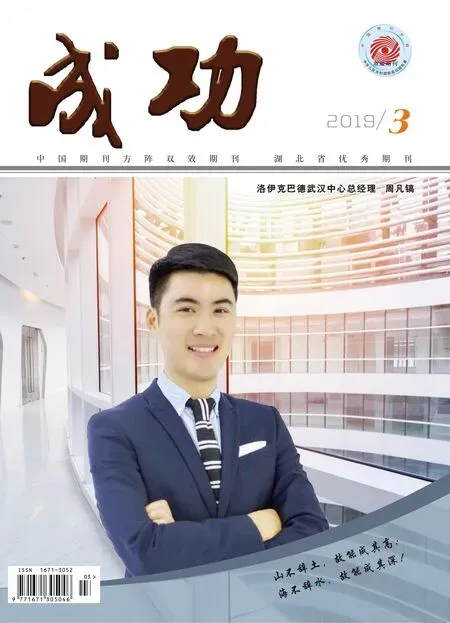浅析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黄沁茗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梁启超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美育思想大家。在他的美育著述中,“情感教育”、“趣味教育”、“艺术教育”等概念均使用过,从基本内涵看,它们都可以理解为美育,但就侧重角度和所处地位而言,还是有所分别的:情感教育侧重于美育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艺术教育”侧重于美育的主要途径和方法,而“趣味教育”在梁启超看来就是审美教育,这显然更接近美育的内在本质。在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中,“趣味教育”是核心范畴,“情感教育”、“艺术教育”是对于“趣味教育”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因此,以“趣味教育”为切入点更能把握他的美育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首先,“趣味教育”的内在本质
梁启超曾明确地宣称:“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第12页)他还说:“问人类生活干什么,我一点不怀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人若生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2](第22页)可见,“趣味”、“趣味主义”不仅是梁的审美理想,也是他的人生信条,由重“趣味”、重“趣味主义”到重“趣味教育”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
梁启超说:“趣味教育”这个名词不是他创造的,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他则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梁启超这一改动,就将趣味提升到了审美的高度,意义十分重大。“拿趣味当手段”,是“有所为而为”,总要以另一件事为目的,其结果是目的达到,手段抛弃,“趣味”也就没有了。而“拿趣味当目的”,却是“无所为而为”,“为了趣味而趣味”,像小孩子游戏一样,没有其他目的,这里“趣味”已成为一种超功利目的的情趣、乐趣,也就是美感愉快。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他进一步指出,“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3](第13页)可见,梁启超所倡导的“趣味教育”中的“趣味”,不是一种形而下的感官愉快和低俗享乐,而是一种超官能欲望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愉悦。在《学问之趣味》中,他更明确指出:“趣味”就是“快乐”、“乐观”、“有生气”,“趣味”的反面是“干瘪”、“萧索”,趣味具有健康向上的情感意味和生命意味。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趣味是一种超利害得失、超生理欲望的审美愉快即美感,这样,梁启超所谓的“趣味教育”在本质上就成为审美教育、美感教育。
梁启超极力弘扬趣味、审美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为“趣味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审美的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而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4](第24页)这就是说,人虽然具有审美的本能,但生活中的趣味和美感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进行有意识的培养训练,即通过一定的手段,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审美活动,不断提高感官的审美能力,把感官从麻木的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有趣。他特别指出,尤其是人生在幼青年时期,趣味是最浓的,整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入下等趣味不可。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趣味”之有无和“趣味”之高下都与“趣味教育”息息相关。
二、其次,“趣味教育”的主要途径
“趣味教育”之必要性在理论上已如此,那么“趣味教育”在现实中如何可能呢?梁启超认为,现实的和理想的生活为趣味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善于感受、善于想象,随时随地都能受到美感教育。在梁启超看来,趣味的源泉有三: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三,“他界之冥构摹进”。总之,无论是外部自然、社会生活还是艺术的形式都是引发美感的重要“机缘”。“趣味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充分利用这些审美因素,有意识地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让人们拥有一双会看形式美的眼睛和会听音乐的耳朵、拥有一颗热情敏感的心灵。
虽然,在梁启超看来,天下万物都有趣味,人生生活于趣味,只要有生活、有事做就有趣味,然而对于“趣味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即他所谓的“趣味的主体”,他还是有严格界定的。经过多方比照,梁启超列出了四项趣味的主体:劳作、游戏、艺术、学问。在劳作、学问主要还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手段的条件下,趣味毕竟是有限度的,游戏中所产生的趣味又往往稍纵即逝;而艺术比之劳作、学问游戏却具有更为普遍、更为持久的影响力。因而在这四项主体中,他最看重的又是艺术教育。而在艺术教育中,他尤其推崇音乐、美术、文学。他说:“美术的功用”,“是把那渐渐坏掉了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令他常常吸受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康健。明白这种道理,便知美术这样东西在人类文化系统上该占何等位置了。”[5](第24页)在梁启超看来,文艺的本质就是趣味、就是审美。因而,艺术教育在整个美感教育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并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所以,他说,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
艺术教育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威而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这是因为在梁启超看来,艺术教育主要是一种“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比之理性教育,在人的审美心理的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到的越发少”,而“用情感来激发人,好象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吸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时间占领了他心的位置”。[6](第71页)这是梁启超对于艺术情感教育特征的极具本质性和独创性的阐发。他认为,艺术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加以浓缩、物化,通过塑造的美的形象来感染人,触动人的情感,对人的心灵加以“熏”“浸”,如春风化雨,点滴滋润,天长日久,铭心刻骨,它对人的影响是深透、久远的。由此,梁启超称艺术是“情感教育的最大的利器”,说“音乐、文学、美术是情感教育的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并说“艺术家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它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7](第72页)。
三、最后,“趣味教育”的根本旨归
在梁启超看来,“趣味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既含真善又超越真善的理想的人生境界。梁启超说:“若就美术家自身说,他们的趣味生活,自然更与众不同了。”“假使‘人生生活于趣味’这句话不错,他们(指美术家)的生活真是理想的生活了”[8](第24页),可见,梁启超所理想的生活就是如同美术家那样的“趣味生活”。“趣味生活”的实质是什么呢?在梁启超那里,“趣味生活”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首先,“超味生活”是美与善的统一。梁启超说,“我平生最爱用用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9](第28页)。他还说过类似的话:“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件事情做我的生活资料,我觉得很是合宜。”[10](第60页),“责任心”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情感,“趣味”、“兴味”主要是一种个体性的审美情感,责任心制约着趣味,趣味又引导着责任心,既超越个人利害得失又不失快乐愉悦,显然是一种美善合一的理想境界。
其次,“趣味生活”还是美与真的统一。梁启超特别推崇美术家的生活,他说“他们的美感,比我们敏锐若干倍,我们领略不着的趣味,他们都能领略……”而美术家“所以能成功地创造趣味的生活,全在观察自然之美,而怎样才能看得出自然之美,最要紧的是观察自然之真,能观察自然之真,不难美术出来,连科学也出来了”。[11](第6页)他还说过,“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首先从求真入手”[12](第8页)。总之,美术家的生活是美真合一的趣味的生活。
最后,“趣味生活”本质上是精神与物质相调和而成的生活。梁启超说:“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人生观”[13](第23页)梁启超“悬”的理想即是“趣味主义”的理想,只有这种理想才能将物质与精神即他所说的“物界”、“心界”调和结合而成一种生活。不难看出,他所说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是物界被心界加以改造编织而成,所以这种生活本身具有审美的性质,是既会真善又超越真善的理想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