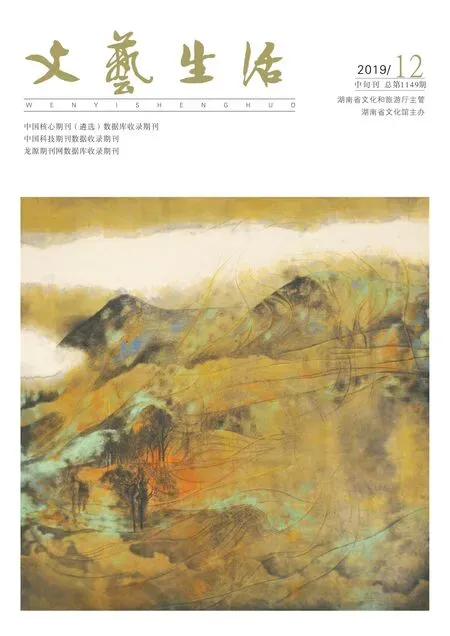浅析艺术作为再现符号的困境
陈 妍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
一、艺术是否可纳入符号学研究范畴
关于艺术是否为符号,以及艺术作为符号,它自身的性质与类型,是艺术是否可以纳入符号学研究领域的争论焦点之一。对于艺术作为符号这一命题是否能够成立,学术界对此尚存在争议。20世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F.)在其相关论述中首次提出了关于“符号学”的理论的相关构想。提出了“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聚合”等二元区分概念,这一系列的二分的概念也是索绪尔符号学的核心思想,奠定了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学研究基础。索绪尔在其论述中强调符号的任意性。符号是依靠区分性原则运作的,符号其内部存在着结构规律而构成的存粹形式关系结构。符号总是指向系统内部的其他符号。由此出发,艺术理论中的“模仿再现”,则有悖于索绪尔的符号学论调。显然此理论对于艺术作为符号学研究来说具有局限性。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哲学家皮尔斯(Pierce,C.)以认识论为基础,提出了不同于逻辑学意义上的再现论符号学。皮尔斯再现论符号学理论将符号划分为,由再现体、对象、解释项构成的三分结构。“解释项”的概念,为艺术作为符号提供了阐释能力与基础。推动了艺术符号的发展。根据此理论,可以将艺术作为一种再现符号,并将其划至“像似符号”的范畴。
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提出,应该把“人定义为符号语言”,并且,他认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苏珊·朗格(Susanne.K)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她将艺术视为符号,认为艺术的意义与一般符号的表义规律有所不同。由此造成艺术符号研究领域所谓的“朗格难题”。从而让诸多学者对“艺术是符号”这一命题产生质疑。
因为艺术符号的表义规则与符号的一般表义规则不同。学术界对于艺术是否可以视为符号也有诸多观点。如文艺理论家与符号学家,诸如雅格布森、穆卡洛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均将文学艺术视为“符号”。表现主义美学代表克罗齐与科林伍德等人,则反对将艺术视为符号,认为艺术是语言而不是符号。
综其上述符号学理论的内容,诸多学者对艺术符号是否成立这一命题,探讨的理论基础,究其实质是因为各自持有理论参照不同所致。否认艺术符号成立,主要以索绪尔符号学理论为研究基础。反观认为艺术可以作为符号,则是以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为依据,并认为,制约艺术成为符号的“朗格难题”,其实质是由于持有索绪尔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学理论在解释艺术作为符号问题上是具有局限性。而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为艺术作为符号提供了基础。
二、艺术作为再现符号的困境
艺术作为再现符号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于当代语境的挑战,同时也来自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本身。皮尔斯的符号概念看似一个三分结构,即“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三者又相互存在着制约关系,在这个制约关系结构中,我们最终将发现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其实质为一个新的二元区分概念:“再现体”与“解释项”作为“符号”与“对象”的替代,皮尔斯符号学本质即为符号再现论,再现论符号的的核心即为“替代”。
根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皮尔斯将符号划分为“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symbol)三个部分。在皮尔斯看来,绘画、雕塑以及艺术的其他表义形式均可隶属于“像似符号”的研究范畴。认为艺术可以作为符号的学者也是秉持着一论述作为研究基础。将艺术作为符号去研究最大的困境在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本身。皮尔斯符号学实质是用“再现体”与“解释项”作为“符号”与“对象”的替代。“解释项”是皮尔斯符号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解释项”这一概念的介入,使得符号与对象关系复杂化。
在皮尔斯符号学视阈下,符号、对象、解释项三者可以分开,用以代表或替代某不场对象的再现体,同时也可以被其他的相似再现体所替换。因此再现体不再具有唯一性。在皮尔斯符号学视野中,符号即为一种载体与工具,其自身不再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假使表达的意义达到,符号存在的必要性将消失。显然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作为解释艺术符号并不恰当油画,雕塑,电影等艺术作品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它的存在并不只是传达意义的虚拟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