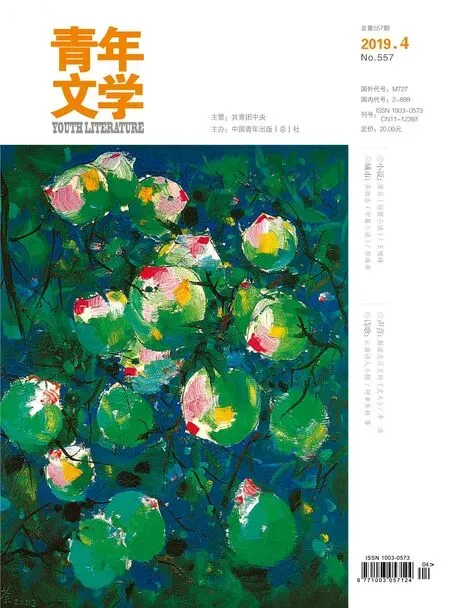白鹇坑旧事
⊙ 文/全秋生
那时还没有公路,人们要去县城只有沿着修在河边的石砌古道逆流蜿蜒而上,翻山越岭,横跨一座名叫梅岭的大山。山坳上有座古老的书院,即梅山书院。自从梅山书院有一年出现凶杀案后,过往行人就免不了提心吊胆起来。加之早出晚归,途中常有毒蛇出没,咬伤人畜也就在所难免。故而小路上的行人日渐稀少,路边各色草木也就趁机疯长起来,小路越发无人问津,要到县城,便只好从水路乘船,于是白鹇坑便有了一艘乌篷渡船。
两个船工是堂兄弟,因为在生产队上不安心挣工分,开始死缠烂磨直至舞刀弄棒、半是哀求半是威胁终于让生产队队长做了让步,谋到了一份撑船的副业,这可是一份当时人人羡慕的美差。虽说每年要上交生产队一笔数目可观的利润,但懒于种田锄地的船工兄弟却自有打算:每逢进城便偷偷捎几担木柴卖给城里人,回家时再捎带一些村民所需的日常用品,日子竟然比生产队队长家过得还要富裕。因为长年在外穿街过巷,走村串户,见闻也就格外丰富,各种下流和不入流的绯闻趣谈便由他们的口中滔滔不绝地流淌出来,使沉闷的小山村增添过许许多多热闹而快乐的气氛。
乌篷渡船是一种两头窄、中间稍宽的船,宽的地方最多也就是四五丈左右,刚好够搭起一个能住人的大篷,大篷前后都各有一扇小木门,大篷用竹篾和做斗笠用的箬叶编织而成,大篷与前后小门框上的空隙要用干稻草扎紧塞好,这样就成了一个夏不热、冬不凉的安乐舱。据世代流传下来的迷信说法,只有用这种材料做的大篷船能防备晚上各式落水鬼的进攻。
在家乡,船有许多种类别,单是乌篷渡船就有两种:一种长约两丈,通常用来摆渡,叫渡船,所谓“百世修来同船渡”的船就是这种;一种是长约四五丈,通常用来运送货物的叫货船。这种乌篷渡船与别的船最大的区别是船头上竖有一根高大的桅杆,上面有一面很大的用白布做的帆,不用时就收起叠在舱顶上,通常能载五六千斤东西。船工兄弟撑的就是这种大货船,每逢夏秋两季运送公余粮的时候,乌篷渡船就跑得格外频繁,村子里的人有事没事也常常搭船进城去看看热闹。船舱里面床铺被子油盐柴米一应俱全,几个人在船上可以吃住几天而不用担心。船上还备有鱼叉、鱼钩、渔网,一有机会,船工兄弟便撒网捕鱼,倘若运气好的话,进城的人便能吃到香喷喷的油煎鱼。那个年头村民想要吃鱼除非自己下河去捕,花钱去买鱼吃的人家是没有听说过的,倘有这种人,那肯定是村民们所深恶痛绝的“懒汉、二流子”。
八叔便是这种“懒汉、二流子”中的一分子。四十多岁的年纪仍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平常生产队出工了,他总是拖到最后才到场,钟声一响(生产队的田地里有一口从古庙中得来的大铜钟,吊在一个木质高架子上,队长用锄头一敲,便是上工、歇昼、散伙的指令),他转眼就不见踪影。不是躲到别人菜地里摘黄瓜解渴,就是偷挖队上的红薯充饥,为此没少惹麻烦,最后队长也懒得跟他计较,把他的工分定得和村上的妇女们一样低,任由他迟到早退。偏偏八叔毫不介意自己工分的高低,一干活便混到女人堆中去干轻活,于是他又有了一个绰号“妇女队长”。说来也奇怪,好吃懒做、没有念过几天书的八叔却天生一副好嗓子,能唱一肚子从老人们那里学唱来的山歌。平常他唱得最多的要数这首《十五看情郎》的山歌:
初一早呵去看郎,
梳头打扮着衣裳。
隔壁有个涎皮嫂,
句句问我去何方?
我到港背看情郎。
……
初五早呵去看郎,
梳头打扮着衣裳。
走进郎门郎在床,
面黄肌瘦泪汪汪。
痛断小妹我的肠!
……
歌声哀怨缠绵,如泣如诉,唱到委婉凄凉处,能令妇女们个个掉眼泪甚至哭出声来。当然更多的时候,八叔与她们混在一起是为了占点小便宜,整日嘻嘻哈哈,有时玩得兴起,这个胸前摸一把,那个屁股捏一下,然后一溜烟跑开,边跑边唱:
一条手巾丢过河,
对面两个婊子婆。
白天为我煮茶饭,
晚上帮我捏卵砣。
……
粗俗不堪的戏谑如果碰上那些没有结婚的小女孩大姑娘们,会把她们羞得满脸通红地跑开,倘若调戏那些结过婚生过小孩的妇女们,可就不会有八叔的好日子过!这些娘们儿火起,几个人一拥而上,把刚刚过完嘴瘾的八叔按在地上踢上几脚,回骂得更不堪入耳,有时弄得八叔躲在家里都不敢出门。当然没过几天,八叔又会出现在做工的女人堆里面。
八叔与队上干活的男人们向来格格不入,但与船工兄弟却称得上是铁哥们儿,只要船工兄弟一有什么新鲜口味,总不会忘记上岸通知八叔的。于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八叔也会挑上几担上等木柴或砍柴时打来的一两只野鸡什么的送到船上,乐得船工兄弟俩常常合不拢嘴。八叔便也常常会搭船到城里去逛逛,慢慢地知道船工的日子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潇洒。
不说平时为了赶急活要起早摸黑,昼夜不得停歇,单是每年冬天货船逆水上滩之难就够呛,江水湍急,北风呼啸,冰凉刺骨,船工冻得脸色发紫发青也得跳下水中推着船帮前进。倘若是载了货,船工中的一个就得用纤绳拴在肩头“嘿唷”“嘿唷”地拉,另一个则要在后面用一根长木棒插入船底用力掀,这个过程叫“肩滩”。粗大的纤绳深深勒进船工背上的肌肉,冰冷刺骨的急流在大腿上卷起高高的浪花哗哗直响,船工脚着麻绳草鞋、弯腰驼背,使尽吃奶的力气往前挪,丝毫不敢松劲,倘一泄气,船就会冲下滩去,一旦撞在礁石上便会船毁人亡。
于是每逢载货进城时,八叔便会整日整夜在船上帮忙,好在他是单身汉,无牵无挂。日子一长,八叔竟也学会了撑篙、划桨、掌舵等船家绝活。比如逆水撑船时,眼前要盯着船头的前方,船头偏左,舱前面的人必须从左面下篙,舱后面的人必须从右边下篙,两边用力夹击,船便会破浪向前,倘若不合规则,船便会在水中打圈。下篙的位置也很重要,不能紧靠船舷,要退开一二尺,身子不能站直,弯腰俯身容易把全身的力量都用上,倘若是横渡起风时,船篙要远远地斜插入水中;否则,风浪一卷,船舷一逼,人就会被船篙反弹到水里。划桨亦有很多技巧,横渡时如果刮逆水风,人必须站在船头桨桩的上方使劲划桨,如果刮顺水风,则要退到桨桩的下方;否则,船就会被吹上或吹下,无法准确到达对岸码头,若遇狂风,则有覆舟的可能……

⊙ 劳尔·杜飞 作品10
一年之后,八叔在干活的人群中又有资本吹嘘了,人们不再叫他“懒汉、二流子”,也不叫“妇女队长”,根据俗语流传“少年撑长河,中年撑横河,老年驮背箩”的“撑船佬三部曲”(“撑长河”指用船做生意赚钱,“撑横河”指赚钱不多的摆渡,“驮背箩”则指老来无依靠只好要饭的悲惨结局),预定八叔将来一定要过“驼背箩”的日子。八叔并不生气,每逢别人取笑他“驮背箩”时,他总是做个鬼脸:“驮你的婆娘。”然后便满足地大笑起来,仿佛赢得了许多便宜。谁知八叔并没有按人们的设想去安排他后半辈子的路程。
有一年河水暴涨,村里人都到河边去看大水,八叔锁好门便来到系在大樟树下的乌篷渡船里打扑克,临近中午,八叔到船舱后生火煮饭,突然从河的上游飞快漂来一挂树排,在翻滚的浊浪中上下沉浮,远远望去隐约可见一个人紧紧抱着筏子凄惨地高叫“救命”。很快木排愈来愈近,岸上的人已经能够看见叫救命的人是一个姑娘,船上的八叔立即操起船篙便要拆绳索救人。
船工兄弟吓得脸色煞白:“老八,你不要命啦!”
八叔“扑通”一声跪在船头上:“两位大哥,求你们救她一命。”
“哎呀老八,你要想媳妇,也犯不上用我们三人的命去换,改天我们去给你找一个。”船工中的老大实在不敢冒这个险,苦苦相劝。
突然,从不发火的八叔铁青着脸,几步跳到船舱里抽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大喝一声:“狗操的,今天你们不开船,我就砍断绳索,都不要活了……”
望着怒目金刚似的八叔,船工兄弟怔住了。
“好,老八,今天就看在你的面上,咱哥俩拼了这条老命吧!”
岸上看洪水的几个大小伙也跳上了乌篷渡船,乌篷渡船立即像箭一样向前射去,有的用桨划,有的掀起垫脚的船板划,终于离木排上的姑娘越来越近了,两岸观看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大声呐喊为八叔他们助威,八叔趴在船帮上,一只干瘦的手臂长长地伸着,嘴里大喊大叫:“快,快抓住我的手!”
就在八叔的手抓住姑娘的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挂树排“嘭、嘭”几声先后撞上乌篷渡船,紧紧抓住姑娘的八叔失去了重心一头栽入水中,姑娘紧紧抱住八叔不放,八叔挣扎了几下,一个大浪扑来,八叔和姑娘再也没有浮起来……
一个星期后,洪水退得干干净净,整个村子里的男人们都出动了,他们敲锣打鼓,杀公鸡烧冥纸放爆竹,沿河一路打捞,终于在离村子六十多里的下游河滩上发现紧紧搂抱在一起的八叔和姑娘。虽然八叔的双眼、鼻孔、嘴巴里面全是泥沙,但脸上却有一丝动人的微笑。人们使劲掰八叔的手指,谁知掰断三根手指仍然分不开,只好把两个人合葬在一起,一生没有娶过媳妇的八叔终于同一位貌美如花的大姑娘搂抱着长眠在村口河边的山地上。
如今下游电站早已投入使用,往日奔腾咆哮的江水已被碧波荡漾的平静湖面取而代之,二十多里长的水面上只有五颜六色装有马达的游艇来回,那古朴的乌篷渡船早已销声匿迹。船工哥俩已随同各自的儿子搬进城里去居住,整天带着孙子在街上闲逛,只有八叔的坟墓依然静静地躺在河边的山地上,仿佛在向游人过客诉说着久远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