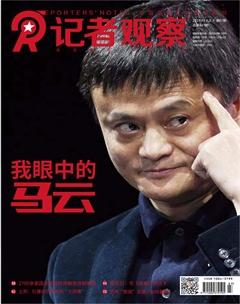贾平凹:写《废都》的日子

1988、1989、1990这几年,一方面父亲去世,家里发生好多变故,另一方面自己得了肝病,身体状况常年不好,几乎每年都在西安住几个月的医院,把西安所有医院都住遍了,而且为治病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当然也有很多社会原因,精神很苦闷,觉得不知道该干什么。
父亲去世时,我是三十六七岁,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亲近的人、亲朋里面有死亡的。年轻的时候,死亡这个概念离得特别远,好像与我无关。父亲得了三年病,做了个手术。那三年,儿女一直在提心吊胆,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发生。去世的时候,他在老家,没有在我这儿住,看完病以后就把他送回去,之后我又返回来,要在城里买药,买好多药。
他胃上有毛病,到晚年特别疼痛,我得在城里给他买杜冷丁。当时杜冷丁不能随便买,必须要医生开证明才能买,一次也不起作用,必须不停地买。他两三天打一次,后来变成一天打一次,一上午打一次,一上午打几次,需要的特别多,我在城里负责给他买药。等我回去,一到村口,看见堂哥穿着孝服,就知道坏事了。父亲最后咽气的时候,
我没在现场。父亲去世对我打击特别大,因为从来没有经受过这个事情,三十六七岁,人生突然有这个,当时特别悲痛。我一想起来就流眼泪,给他写过好多文章,寄托自己那种哀思。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没有跟我享过多少福,因为那个时候我
条件不行。父亲最大的满足就是我发表作品以后,他在外头收集我发表的作品,后来他周围的朋友、同事一旦发现报刊上有我的文章,就拿来给我父亲,他一高兴就开始喝酒。
这是父亲晚年的时候唯一的精神支柱,完全靠儿子还能写东西,而生活上我确实没有给他更多的东西,包括生活上的照顾。
随着自己年龄增长、阅历增加,也思考了好多东西,对社会的问题,对个人生命的问题,和以前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以前写商州的作品,不管怎么写,总的来说风格是清晰的,是明亮的,一切都是阳光的,而这个时候自己对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个人问题、身体问题引起好多思考,对人的命运、人性各种复杂的东西,就有写作的思考。这种思考是以前很少有的,以前更多写写故事,这个时候就不满足于写那些东西。
写《浮躁》的时候,我前言里面专门说:我以后再不用这种办法来写小说,这种办法是指五十年代传下来的一种现实主义写法,全视角的写法,还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那种痕迹,我说一定要变化。但在哪儿变?当时自己也不知道。但总觉得不满意以前的,得重新开个路子,这就写到《废都》了。
创作《废都》,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反正是写作品,至于写哪方面,写什么东西,一定要写出来,当然写的作品肯定是故事,这个故事、这个人的具体境遇、命运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命运相契合的时候,就是交接的地方,把这个地方的故事写出来,就不是个人的故事了,而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的故事。
举个例子,就像我在门口栽一朵花,本来目的是给自己看,自己来闻它的香气。但是花开了以后,来来往往的路人从门前过的时候,都看见了这朵花,都闻见了它的香气,这朵花就不仅仅是自己的,而是所有人的。
每个人都活在集体无意识里面,大家统一一些东西,作品要刺痛那些东西,才能写好。所以在写《废都》的时候,我确实是无意识地把自己的生命和这样一个社会时代交接起来,把发生的故事写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写什么,考验一个作家的胆识和智慧;怎么写,考验他的技术。在《废都》里面写什么?写庄之蝶发生的一些故事,写的主要是他的苦闷,他的无聊,他的颓废,他好像雄心勃勃要拯救好多女的,反倒最后女的也没有拯救好,他把自己也拯救不了,就完蛋了。在写法上,《废都》基本上不按五十年代创作的路子,但具体怎么弄,还需慢慢实验。
一直到后来的《秦腔》和《古炉》,才慢慢走出一个清晰的写法,就是写生活,写细节,写日常,写普通人的一些活动,而不是写一个英雄人物,写一个高大全的东西。
创作永远都是自己做。别人给的经验,只是一种启发,具体还得自己来,就像往上上台阶一样。你站在第一层台阶的时候,根本不了解第三、第四层台阶会发生什么,只有站在第二层台阶才能体会到第三层台阶,站在第三层台阶才能体会到第四层台阶。
你还在第一层台阶上,别人给你说第五层台阶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经常举例子:在瀑布下面用碗接水,永远接不上水,只有在溪流里面、水龙头下面,才可能接上水。强大的思想,当你还没有达到同步的时候,就无法进入那个东西。
写《废都》时,其实是我最痛苦的时期。《废都》是流浪着写的,先在一个水库上写,听人说要几个人在那儿守着水库,有一个灶,可以在那儿吃,那儿清静,我就住在那儿。
那个地方偏僻,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只有一个电视,还是人家的,经常还收不到信号,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娛乐。那个时候年轻,精力旺盛,我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十个小时,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满打满实实在在要写十个小时。
基本上我四十天就拿出了初稿。带着初稿跑到一个朋友家,这时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九十,只要谁给我管饭,我就继续写。作品写完以后,一出来前半年,可以说是好评如潮,都说特别好,才过了半年,就全部开始禁止了。原来说好的不说好了,有些不发言了,有些就反过来说不好了。我感受到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体会到了这种巨大的反差。
当时身体极端不好,记得我的心脏就不行了。我住到一个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一个干部病房,住进去以后,发现几乎每一个病房里的老干部都在看《废都》。那个时候《废都》疯狂到你无法想象的情况,外头盗版也乱,到处都在卖《废都》,病房人人都有,都能看到,都在议论。
突然知道我也在那儿住着,那议论纷纷的,我是住不成的。当时我化名叫龙安,因为我属龙,希望能在那儿安生一点,实际上并不安生。我就不住院了,和朋友到四川绵阳躲起来了。
我第一次受到批评,还觉得特别委屈,后来经历的争议多了,尤其经过《废都》,反倒不是特别强烈地反抗,或者强烈的委屈。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的事情多了以后,就无所谓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废都》给我产生的阴影,影响一直持续了十二年,里面的苦楚只有我自己知道。不说生活受到的影响,不说工作受到的影响,就从文学来讲,也有好多好多影响。
《废都》之后我紧接着写了《白夜》,《白夜》可以说是《废都》的姊妹篇,出版的时候,《废都》正遭受批判,没有一个人给《白夜》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十来年。
《废都》在法国获得费米娜文学奖以后,在国内只有一家小报登了短短几句话,说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法国获奖,获得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的费米娜文学奖,都没敢提《废都》。这只是从作品上,别的事情就更多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东西,对我的生命和文学产生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人有命运,书也有命运,《废都》的命运就是这种,好像一个人遇到了大坎,要判刑坐狱一样。它的传播后来完全靠盗版,盗版对每一个作家来讲都特别反对、特别反感,对作家、对读者都是一种伤害,但具体到《废都》,还得感谢盗版,没有盗版延续不下去。
那十来年,凡是别人来我家里请我签字,都签《废都》。我一看不是原版的,就留下一本,我不是在社会上去收集,而是在家里守株待兔,现在我家里有六十多种《废都》的盗版本,有精装的,还有一部分书是给《废都》写续集的,光写后续的有三四本,人物地点都一样,把故事继续写,挺有意思的。
经常有人问,哪部作品是你最爱的?我说没有最爱的,因为所有作品就像孩子一样,都可爱,我在写它的时候,都盼着它是世界上最能干的孩子,最漂亮的孩子,但长大后它不一定是那个样,不管它长得丑还是漂亮,都是我的孩子,对于我来讲都是喜欢的。但是相比起来,有些是重要的作品,有些是不重要的作品。
什么叫重要的作品?就是在走一条路的时候,拐弯的路边长的那棵树,或者是那块石碑,它给你记录这个拐弯。有的作品就像这棵树一样,它在创作道路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废都》应该是重要的作品。从那以后,我的创作不说内容了,就写法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写法变化以后,一旦走出去是走不回的。
现在让我写《浮躁》以前的那种作品,我就不会写了,也写不了了。就像生命一样,当我活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就无法再享受到二十、三十、四十岁的青春,只有在照片上才能看到当年的模样。具体的我好像没有变化,而实际上不停在变化,只有突然拿出十年、二十年前的照片,才看到自己原来还年轻过。
后面的作品就像年龄一样,把好多东西看透了,阅历增厚了,就像文物包浆一样,变得浑厚了,不是原来那么简单、那么明亮的东西,现在是浑浊的,或者是厚实的、浑厚的东西多了。
以现在我的想法,我喜欢自己后期的作品。后期的作品都是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生活中体会到的东西。而好多人喜欢我早期的作品,当然更多年轻人喜歡早期的作品,早期作品优美、清新,有好多很漂亮的句子,读过去以后可以用笔做笔记,但那些作品太轻浅,好多是我看到、听到、读到一个什么东西,反射过来启发我写出来的东西,而不像后来的作品,完全是在生命和生活中,自己体会到的东西,才把它写出来。
或许是年龄大了以后想法不一样,对世事的看法就不一样了。现在人们写作品,尤其年龄大的写作品,不光看故事,不光看里面的思考,还会看其中对生活、对生命的智慧问题,要把那些东西写进去,作品才能产生一种厚实感、丰富感,而不单纯是一个故事,或者批判谁、歌颂谁,那都太简单。应该包容,应该更丰富,有各种智慧的东西积累在里面。
摘自微信公众号“读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