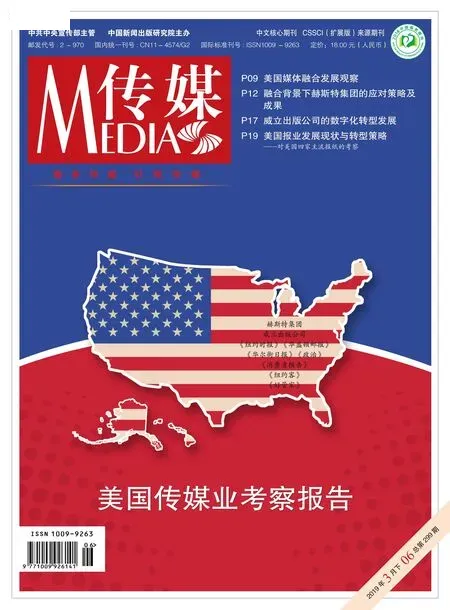社交媒体时代“后真相”的形成与应对
文/张 萌 罗 岱
2016年,牛津字典将“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并做出如下界定:“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这一现象所涉及的一是情感;二是民意,即能够影响舆论;三是弱化乃至忽略客观事实。社交媒体时代,在信息技术与平台的双重加持下,“后真相”现象的负面效应日益显著,不仅延长了舆情动荡周期,而且加大了舆情治理难度,同时引发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信任危机不断加重。从“上海女”在论坛上的爆火,到“东北村庄”刷屏朋友圈,再到红黄蓝幼儿园“恶魔在人间”充斥全网络,所有舆论高潮都得力于智能手机等移动新媒体的助推。可以说,“后真相”现象源源不断,的原因与移动社交媒体密不可分。
一、社交媒体时代“后真相”的形成
在国内的移动互联网中,有如下几个问题最为突出。同时,这些问题对于“后真相”的影响也着实巨大。
1.“信息茧房效应”“回声室效应”等不断加剧。2008年,美国学者桑德斯坦在他的《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了一个名为“信息茧房效应”的现象。他指出,人们只会选择他们所想了解、所感兴趣和能够取悦自己的信息,对于其他信息都会拒之门外。在如今一切信息都被“算法挟持”的全新媒体时代,任何信息在到达用户的手机之前就经过筛选,想要了解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倒是变得比较困难。因此,用户所了解到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社会,而是由算法所呈现给用户的一种“拟态环境”。但是这种环境并不是个人独有的“个性化世界”,会有许多有相似乃至相同的“环境”存在,构成了一个有共同兴趣和话题的“圈子”,成了“道相同才相为谋”的群体。这个圈子和外部的整体社会相似,都会有一个或多个“领袖”,控制着话题与情绪导向。同时,因为有共同的思维模式,任何一个观点都会在这个封闭的“圈子”中反复循环,形成一个“回声室”,甚至成为一种“沉默的螺旋”,不断抑制外部的信息,强化内部信息的同质性。可以说,新媒体时代的影响,虽然可以让所有人实现真正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同时,这些“天下事”的真实性和同质性值得深思。
2.审核证实环节的缺失。在以往的主流化媒体时代,新闻或者说信息是由专业性较强的组织机构和专业从业人员筛选过再往下传递。这种“把关人”的存在虽然被指出是一种对信息和真相的“集权把控”,但确实有它的优势——能够查证信息的真实性。这恰巧是如今“人人都是麦克风”时代所缺乏的一环。任何消息都可以在未被证实的情况下传播,甚至越离奇越虚假,所造成的影响力越大。以往充当“把关人”角色的审核机制和专业人员作用不断被弱化消减,乃至缺位。
3.用户的媒介素养水平与信息量之间产生“鸿沟”。社交媒体时代,一方面信息量暴增,另一方面,用户对于信息的鉴别能力却没有提升,媒介素养水平不高,导致了大量虚假、歪曲的信息得到广泛传播。如果媒介素养教育跟不上,这种“鸿沟”会不断增大,届时将会进一步加重虚假信息的传播。
4.民粹主义的爆发与网络暴力的崛起。“互联网中的民意在极端平民化后,很容易从失序走向失控,进而压制网络里的理性,畸变为网络舆论形态的民粹运动、网络暴力和暴民政治。”在“人人皆媒体”的新媒体时代,人们不再需要有人代表发声,只需通过手机中的以社交应用为代表的一系列途径,就能表达观点、宣泄情绪。但在互联网的“隐蔽性”之下,以及法不责众心理的作祟,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为了宣泄情绪而捏造谎言的情况时有发生,语言攻击、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变成了家常便饭,并且已经激化到不相信任何与自己信念不符的信息,哪怕是客观事实。这种“民主化”已经变成了一种以情绪主导的判断准则,好比当年希腊民众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一般。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后真相”应对
1.构建审核证实机制,确保信息真实性。由于互联网的深不可测,海量的信息无法逐一证实。以往传统媒体的新闻制作流程中所必备的审核环节,能够尽可能地保证从自己手中播发出去的每一条新闻都真实、可信。但随着信息量的量级增加,这种传统的、人工的审核方式不再能够实现全部审核。就近些年频发的各种虚假新闻案件可以看出,不管是哪种媒体形态,拥有一个保证信息真实性的环节,已迫在眉睫。
据路透社新闻研究中心的数据调查显示,新世纪以来,事实核查组织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主机构,发展迅猛,已经遍布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有一半多都是2010年以后成立的。如英国《卫报》早在2011年创办了博客网站“现实核查”,社会非营利组织“全部新闻”,以及专门针对英国公投而创办的事实核查团队等,这些核查机构强调“慢新闻”,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真实性。但就国内来讲,我国新闻事实核查机制并没有得到有效建构,只是零散地存在于各个媒介平台,系统性不强,如腾讯新闻的“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等,尽管形成了新闻审核证实机制的雏形,但对于虚假新闻的“拨乱反正”大多需要依赖于官方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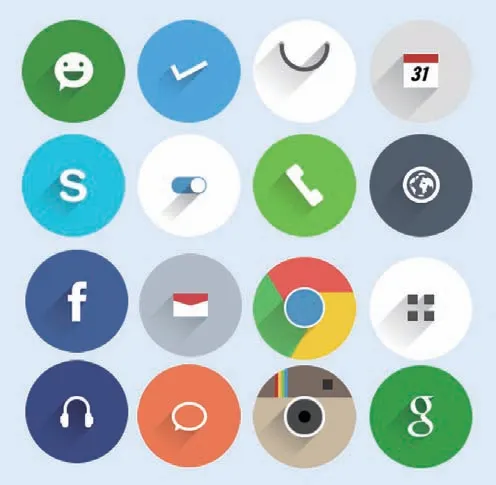
虽然无法保证眼下每一条信息都是真实可靠的,也不能使原有的审核环节完美地融入当今的信息流动环节中,但是我们应该保证的是,让类似于“把关人”的审核证实机制回归传播渠道,做到完全能够证实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信息、尽力证实所触及的信息、尽量接触可能接触不到的信息。同时,也要保证,这种审核的标准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维护事实真相,而不是为了满足某些团体或个人喜好厌恶;做到回归真相而不是另一种“拟态环境”。
2.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传受双方“媒商”。旧有的“慢”新闻时代,新闻流通环节中存在角色划分。新闻是由专业新闻媒体构成的生产者向新闻受众即接收者流动。在这种流程下,只有接收者才更需要提高新闻辨别能力,对于生产者,新闻都是由其筛选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传播,是具有高媒介素养的一批人。而在现如今的信息化“快”新闻时代,每个人既是以往传统的信息接收者,同时,也变成了信息生产者。虽然角色有了转换,但在专业素养上却无法等量对换。
普通民众虽然能代替专业新闻机构及时到达新闻现场,但是他们无法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并且常常在没有证实的情况下便昭告天下。因此,在这种角色硬性转换下,用户不能保证在作为信息生产者时所发出的信息真实可靠,而要求用户作为信息接收者能对所收到的信息做出真假判断,更是难上加难。同时,由于互联网的隐蔽性和匿名性,人的欲望会在不受现实社会的约束下肆意暴露,只为宣泄情绪不顾影响后果。因此,在“人人皆媒”的今天,提高民众的媒介素养必须提上日程,刻不容缓。
媒介素养教育更多的是要培养信息传播主客体的思考批判能力,作为传播者,要具备较强的责任意识,并做好信息把关工作;而作为受众,则要形成辨别是非的能力,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坚守价值本位。面对耸人听闻的信息,要持有怀疑精神,不能盲目随从和造谣;要进行深入辨别思考,通过追本溯源、持续跟进等方式寻找事情真相,而并不是单纯依靠主观惯性思维进行臆断。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诉求,是要培养信息传播主体和客体的行为自觉性,促使他们在长期的信息传播中形成理性思维,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信息传播偏误,全面提高他们的“媒商”。
3.注重舆论引导,提高违法成本。如果无法及时发现虚假或者情绪主导信息,就可能带来巨大的负面社会影响。对于专业媒体,应该主动承担起引导舆论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义务。在社会化媒体这样基于社交网络或者说人际关系网络的传播网络中,能引起广泛关注、得到广泛传播的话题,往往可能与情绪相关。因此,安抚民众情绪、带领理性回归事件本身,也就成了专业媒体在舆论引导中所必须做的重要工作。用真相唤醒理性,用事实击破谎言,这样才能构筑起防御“后真相”现象的一道坚固阵线。
当然,除了主动引导之外,还要从法律维度入手,充分发挥法律的强制规范作用,提高“后真相”中失范行为的违法成本,对个人或团体的信息传播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只有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信息传播行为的管理提供权威依据,才能对不良信息传播者形成有效震慑。
首先,政府要加强自我约束。在传统的网络舆情中,许多行政机关不重视舆情危机的处理,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进行强制“抹杀”,带来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政府权威。如在“雷洋事件”中,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玩忽职守的行为,在抓嫖办案过程中造成当事人的意外身亡,但当引发舆论关注后,案件调查阶段警方以执法记录仪毁坏、监控系统未开等理由搪塞,最终引发了受众的强烈不满与抨击,使得整个案件的舆论走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在信息传播领域,政府必须坚守程序公正底线,维护好自身的公信力,进而提高信息管理的法治权威性。
其次,要加强对媒体行为的法律规制。在日益复杂的媒介生态系统中,我国有关媒体管理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针对新媒体的管制依据不足,《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都属于规范性文件,存在法律位阶较低、界定范围有限、行政权力约束不够等问题。所以,构建完善的媒介管理机制,提高媒体的违法成本,是应对“后真相”的有效路径。
最后,要加大对不良信息传播受众的法律规制。全媒体时代,受众的舆论情绪很容易被意见领袖所左右,被夸大、虚假的言论所蒙蔽理智,最终带来一系列的舆论危机。例如,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中,个别受众恶意散布军人集体猥亵儿童的谣言,在带偏舆论走向的同时,对军队形象产生了严重损坏,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了巨大威胁。因此,在加强道德层面宣传引导的基础上,必须要出台针对性的法律规范,对受众的信息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在发挥民间场域正面效能的同时,提高信息违法行为的成本,消除不良言论,规范大众话语。
三、结语
在如今“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新闻的真实性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有人说信息的失实是技术与科技发展的副作用之一,不可避免。但是凡事无绝对,作为新闻从业者乃至整个新闻界,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应对风险,调整自身状态。只有真实的新闻,才是有营养的,才能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进作用。移动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不应该是对真理的挑战、对虚假的扇风造势,而应该是对客观事实的助推,这才是一个“新事物”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更应该高举真相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