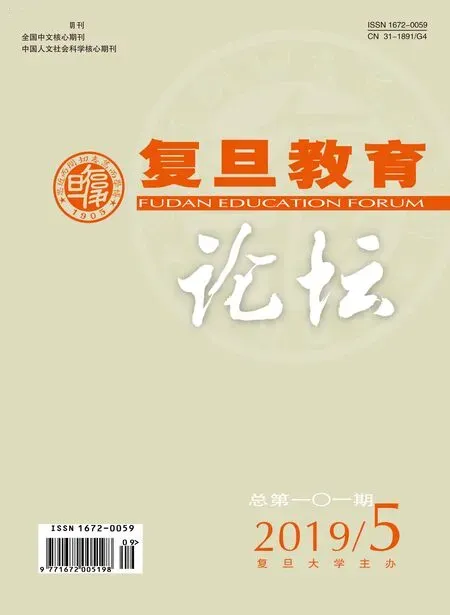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常桐善
(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美国奥克兰946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复旦教育论坛》杂志编辑部邀请我为“海外学者看中国教育70年”专题写一篇文章。我深感荣幸,也颇有顾虑。我没有亲身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国教育,也没有对此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所以对这个年代之前的教育发展不敢妄言。我1997年来美国,10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第一次回国,当时对国内10年间发生的变化深感惊讶。当然,这些变化也包括高校校园的变化、规模的拓展以及在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作为很早就对高等教育研究感兴趣并在高校从事院校研究的我,也常常因未能亲身经历和见证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过程而感到遗憾,自然也没有资格评论这个时期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变迁。非常荣幸的是,在过去10多年中,我通过多种渠道与国内学者开展了诸多合作,特别是通过参加本科教育水平审核工作以及在几所大学兼任教职工作,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现状略有了解,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另外,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20多年中,我也有很多机会听到美国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基于这些信息来源,我想简单谈谈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是在美国的影响力)这一话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可能会受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在加州大学从事院校研究工作经验的局限性的影响,难免会有偏差,还望读者指正。
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十分迅速,但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还很小。我于1990年大学毕业后到陕西省教育厅(当时的名称是陕西省教育委员会)任职,参加了世界银行贷款扶贫项目的论证和管理工作。这个项目除了资助贫困地区发展基础教育外,也资助高校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在与世界银行专家的交流过程中,我常常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顾虑的。其中最大的顾虑是规模效益差,也就是学校的规模过小,贷款建造的教学用房、购买的设备和图书以及培训的教师所产生效益的收益群体过小,达不到世界银行贷款所要求的效益指标。当时,我对规模效益的理解并不十分透彻。从事院校研究工作后,我深深体会到规模效益是检测大学办学绩效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问责制度”(accountability)和“院校效能”(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研究中,规模效益指标显得尤为重要,是衡量大学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关键指标。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界银行的专家多次考察陕西的大学,并与时任北京大学高教所所长、世界银行贷款中方专家组组长闵维方教授探讨,提出通过合并大学来解决规模效益的问题。随后,陕西当时的四所高校合并成两所,才获得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当然,合并后的两所高校在后来几十年的发展中,也遇到了中国所有其他合并高校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通过参加这个贷款项目,特别是通过参加世界银行举办的培训,我有机会了解到美国、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高等教育当时的发展情况,也深刻感受到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落后状况以及在国际影响力上的缺失。
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资助下,我于1997年底来美国做访问学者,并攻读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情有独钟。他在1989年前曾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先后撰写了两本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专著,分别是《从同治中兴到天安门事件的中国高等教育传奇:变革与改革》[1]《中国稷下书院与高深学习的诞生: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教育与古希腊教育的比较》[2]。这两部著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演变,视角非常独特。当时,我的导师也是我们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授课教师中唯一一位在上课时介绍和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教授。其他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知之甚少。他们在课堂教学中除了提及欧洲的大学,也常引述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的高校,但从未提及中国大陆的高校。在我修习的将近20门高等教育管理专业课程中,唯有高等教育发展史这门课的教科书中提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而且也只有区区一小段,寥寥数百个英语单词:
“中国在〔20〕世纪之交的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时,职业教育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在1911年之前,也只有3所西式大学和38所其他类型的大学。到1928年,中国也仅有74所大学。在1937年日本侵华时,也只有108所大学。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截至1948年,在共产党的革命时期,中国已经有55所大学、79所独立学院、81所专业技术大学,合计215所大学;在校学生数为13万,而当时中国的人口数是4.5亿。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尽管共产党利用教育作为发展现代化和宣传的工具,但在‘文革’时期有一半大学关门,这成为具有负面影响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失调的典型案例。在1981年,中国也只有1%的大学适龄人口能够入读大学。”[3]
我没有考证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但从我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来看,真实性比较高。我是1980年高中毕业的,当时大学录取率是非常低的,绝大多数莘莘学子都被大学拒之门外,我也是其中之一。当然,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末期,大学扩招后,大学适龄人口的入学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21世纪之交,按照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模式迈入“大众化”模式,也就是大学适龄人口的入学率达到了15%。但在同一时期,“美国高中毕业生入读本科院校的比率已经超过41%,入读两年制专科学校的比率在23%左右,合计为64%”[4]。显而易见,当时中美高等教育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并不十分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与我的许多美国老师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还不愿意访问中国。关于这一点,加拿大著名的中国教育研究专家许美德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先生在一次关于中国教育发展的对话[5]中也提到了。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过去十多年,我也多次邀请美国学者来中国参加会议。受邀人员包括大学的管理人员、教师、著名学者以及高等教育学会的官员。其中很多学者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们非常高兴能来中国访问。我从他们的反馈信息中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是积极的。有一次,我在地铁上巧遇加州大学主管学术的教务长兼执行副校长,我们聊起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他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访问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在过去十几年访问过中国的很多大学。他认为中国大学的发展速度很快,每次访问都会看到新的变化。他说:“中国大学的校园越来越漂亮;大学好像不缺经费,不像在加州大学,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说服州政府给我们增加经费。”他还说,中国大学充满了活力,教师非常关注创新教育、科研工作和对外合作。他预测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很多大学成为“全球顶级大学”(top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他非常期待再次访问中国。其实,我在美国常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个人也认同他的观点。
这种变化当然是循序渐进的。我记得在2002年前后,我参加了由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组织的一个学术会议。这个会议专门开设了一个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专题讨论会场,主持人是一位很有名的美国学者。这让我颇感意外和好奇。美国顶尖高等教育研究学会组织的高端学术会议能够开设中国专题的讨论会场,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引起了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在这之后,类似的以中国高等教育为专题的讨论会如雨后春笋,遍布美国各类学术会议以及大学校园。我听说,2019年来美国旧金山参加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主办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大会的中国学者有数百人,约占参会人员总数的10%。会议期间来加州大学访问的人员就达30多人。可以想象,他们背后该有多大的一个高等教育体系才能支撑这么多学者来参加国际会议,其国际影响力不言而喻。
参观过美国大学校园的人都会发现,校园里处处可以看到中国面孔的学者。这些学者中有访问学者、短期考察团成员,也有长期任职的学者和管理人员。加州大学伯克利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曾举办过一次专门讨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研讨会。在讨论大学的对外合作和交流这个话题时,加州大学前教务长非常感慨地说,“与中国学者相比,美国的学者是很不幸的,很少有机会到国外学习交流”。仅2017-18学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访问学者就多达827人,人数是10年前的3倍。[6]我想这个数字一定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在中国绝大多数规模较大的“双一流”大学中,教学科研人员约有3000人,比如清华大学有3485名教师,西安交通大学有3047名专任教师,复旦大学有2871名教学科研人员。如果这些大学突然增加1/3的从事教学科研的国际学者,我们在校园里看到的将是一道什么样的风景线呢?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伯克利。其实中国是向美国大学派送访问学者最多的国家,目前已接近5万人,占所有国外来美访问学者总数的1/3还多。[7]除此之外,来自中国政府部门和高校的短期访美学习人员和考察人员也很多。我在加州大学工作的10多年中,帮助安排和接待过的中国访问团队不计其数,其中有国务院、教育部、省(市)等政府部门的高规格访问团,也有大学领导和教师组成的访问团,还有大学生夏令营等。另外,在美国大学担任教职和管理工作的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数拥有中国本科教育学历。这些学者和管理人员中不乏美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著名学者和高层领导人员。我是从事院校研究工作的。我们有一个海外华人院校研究学会,共有300多名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完成的本科教育,之后在美国获得博士或者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高校从事院校研究工作。在300多名会员中,有很多人担任校长、副校长、助理副校长、主任或者副主任等职务。我们的学会是美国院校研究学会所有隶属分会中规模较大、活动较多的学会之一,对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相信中国学者和考察人员的来访以及中国学者在美国大学的教职和管理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和未来发展趋势,对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在美国的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球大学排名是展示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在最近几年的排名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进入全球百强大学行列。例如,在QS的排名[8]中,有4所大学进入百强大学,清华大学已经超过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跃居第16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排在第22名、第40名和第60名;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大学排名[9]中,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也进入全球百强,分别位列第50名和第60名;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排名[10]中,有3所大学进入百强,分别是清华大学(第22名)、北京大学(第31名)和中国科技大学(第93名);在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11]中,清华大学(第43名)、北京大学(第53名)、浙江大学(第70名)和上海交通大学(第82名)也跻身全球百强之列,而在其10年前(2009年)的排名中,中国没有1所大学进入前200名。虽然美国、欧洲的大学没有像中国的大学那样青睐排名,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的位次变化,对提升中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2018年,清华大学第一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排名中的位置跃居亚洲第一。当时美国最大的新闻媒体之一——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CNN)就曾报道:“清华大学取代新加坡国立大学成为亚洲第一。”[12]报道引用《泰晤士高等教育报》对清华大学排名提升原因的阐述:“清华大学排名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教学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大学经费和博士学位授予数量的增加。”良好的教学环境和充裕的教育经费是保证大学办学质量的核心因素。显然,清华大学排名提升的原因说明中国大学已经从本质上迈入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报道同时引用了牛津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学教授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对清华大学排名提升的评论。他说,他对清华大学成为亚洲第一“并不惊讶”,清华大学在工程、数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很多其他大学难以望其项背。当然,排名的大多数指标聚焦于科研成果。但无论如何,中国大学排名的变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在科研方面取得的卓著成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应该否定。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的一项研究,截至2016年,中国已经成为科学研究文章产出最多的国家,每年产出科学和工程研究文章40多万篇。[13]从产出量来说,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在引用最多的前百分之一的文章中,中国也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第二位。[14]这项指标说明中国大学发表的文章在质量上也是不断提升的。
中国高等教育对美国高等教育,乃至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源源不断地为其输送研究生。我没有查到中国研究生在全球高校分布的数据,但2017-18学年美国大学里的中国研究生已超过13万人,占美国大学所有国际研究生人数的34%[15]。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生有7359人,占加州大学研究生总数的13%;其中博士生3324人,占加州大学博士生总数的12%;在工程、计算机和物理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者2377人,占所有这些专业博士生总数的21%。[16]可以说,中国是向美国大学输送研究生最多的国家。如果中国的本科毕业生放弃来美国攻读研究生,恐怕美国的很多研究生院都需要压缩规模,也可能有的研究生院要面临关门的危险,或者降低录取标准,招收学业成绩差的学生。若果真如此,美国的人才培养,特别是工程和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将面临严重短缺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向美国输送研究生是展示中国本科教育成果及对美国研究生教育产生影响的硬核指标。当然,大批研究生赴国外读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本国的研究生教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但无论如何,研究生对提升生源国家的高等教育影响力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有更多的学生毕业后回国工作,对生源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有益的。对中国留学生而言,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形成。
另外,中国在过去20多年来实施的一系列高等教育发展和合作办学项目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例如,“985 工程”、“211 工程”、孔子学院、中外合作办学、“一带一路”项目、“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人才引进项目、“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学科的国际认证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的作用。以孔子学院为例,截至2019年6月,全球已有155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39所孔子学院和1129个孔子课堂,其中,美国有95所孔子学院和12个孔子课堂。[17]孔子学院在交流中国文化、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提升了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如果中国能在高等教育强国开设或者与其合作开设普通高校,国际影响力一定会更大。“一带一路”是另一个极具国际影响力的项目。虽然“一带一路”项目涵盖的国家主要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中国大陆、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区的国家,但在这些国家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育交流和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元素,所以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项目有“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潜在可能性[18]。2018年3月,国际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经济、法律以及政府专业的范·德·温迪(Marijk van der Wende)教授在荷兰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9]。当然,在“一带一路”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大学缺乏经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如何招收外国留学生、如何有效地管理留学生等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影响力是大学实力的展示,也是一流大学最基本的判断标准。上海纽约大学首任校长俞立中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在线专访[20]时提到,他曾经问过密歇根大学的校长,什么是一流大学,怎么理解一流学校、一流教师。密歇根大学校长只说了一个词——“影响力”。我想密歇根大学校长所说的“影响力”一定也包括大学的国际影响力。现如今,虽然中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国际影响力上仍然处于霸权地位。中国开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否能够让中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再上一个台阶,是否能真正起到“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作用,仍然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将是否能够“重塑全球高等教育”作为大学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因为,目前的中国大学还存在很多亟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例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非常缺乏;学术组织领导力在大学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依然很弱;大学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从政府到大学的政策和制度缺乏稳定性和灵活性;课程设置墨守成规,教学模式传统守旧,“水课”泛滥;质量评估形式主义严重,缺乏内部改进动力;对教师的绩效评价还主要以科研成果为主,缺乏提升教学绩效的激励机制;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关注不够,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参与意识淡薄;政府和大学未能提供足够的人文社会学科以及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支持,政府对普通大学的质量提升支持力度薄弱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大学不仅难以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恐怕践行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也会受阻,甚至会陷入发展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