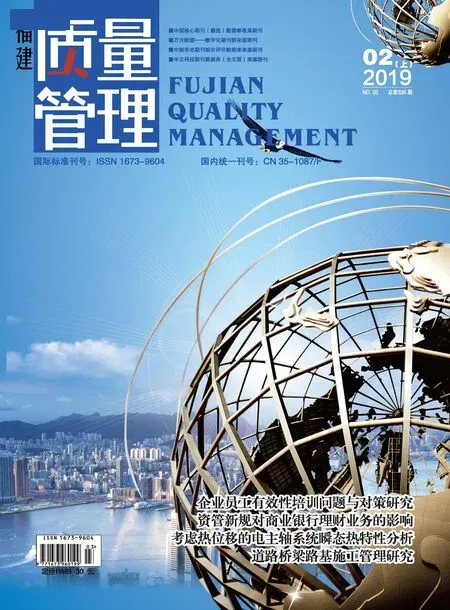强制垄断下经营者法律责任研究
——基于《反垄断法》第36条的规范分析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63)
围绕第36条,笔者将主要分析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该条的体系定位。主要是关于第36条与第32条到第35条的关系,第36条与第37条的关系,第36条与第2章、第3章、第4章的关系。第二,关于强制的认定。“强制”是第36条最为核心的一个词汇,能否准确界定“强制”的含义是正确理解与适用第36条的关键。第三,经营者法律责任的认定。主要是关于经营者被强制从事垄断行为,应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而第二个与第三个问题又是紧密相关,“强制”的准确界定就是为确定经营者法律责任而服务的,在笔者看来,经营者有无“受到强制”是其承担责任的分水岭,所以强制的准确界定至关重要。
一、第36条的体系定位
1、第36条与第32条到第35条的关系。第36条规定的是行政机关强制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并非由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所直接达成,而是以经营者作为中介间接造成的。第32条到第35条,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则是由行政机关直接造成。所以说,第36条规定的是间接行政性垄断,第32条到底35条规定的是直接行政性垄断。
2、第36条与第37条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既有抽象行政行为又有具体行政行为,那么经营者受到来自行政机关的强制,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亦或是两者皆有之?第37条规定了抽象行政性垄断,因为第37条与第32条到第36条并列规定,所以解释上应认为,当行政机关实施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受第37条规制而反垄断法承担责任;当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机关受第36条的规制而承担责任。而就经营者责任承担层面,因第37条仅规制行政机关,无法实现第36条于第37条对经营者的并列规定,所以解释上应当认为经营者受到来自行政机关无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均应受到第36条第规制。问题是抽象行政行为能否达到强制的目的?此一问题,将在“强制”的具体界定上予以澄清解决。
3、第36条与第2章、第3章、第4章的关系。第36条规定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主要就是第2章到第4章所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行为、经营者集中。所以,在认定是否符合第36条的构成要件时,必须审查经营者所为之行为是否符合第2章、第3章、第4章中的相关规定,若经营者的行为并未满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行为、经营者集中等垄断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使受到行政机关的强制,也没有适用第36条的余地。
但是有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却做了这样的规定。一个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第3条,另一个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第17条。这两份规范性法律文件穷尽列举了行政机关强制经营者从事的垄断行为,即垄断协议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而无经营者集中。似乎在此两规范性文件制定者看来,行政机关似乎不能强制经营者从事经营者集中,事实并非如此。
2008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先后发布了数个规范性文件,旨在加快煤炭资源整合,启动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行动,涉及两千余家的国有、民营、私人煤炭企业。在山西省此次对小煤矿的兼并重组中,经济补偿问题是资源整合中最关键的问题。根据2008年9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的规定,被兼并重组的煤矿可按规定获得经济补偿,也可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其在新组建企业的股份。然而,经过调查后发现,当地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资源整合方案中,不顾中小煤矿投资者的呼声,强制小煤矿接受整合,甚至还使出了停产限产拖时间等手段。[1]
本案中,行政机关以限产、停产的手段,迫使经营者参与集中,严重违背了经营者的生产、经营自由。所以行政机关也可以强制经营者从事集中行为。但是在课堂展示,钟老师点评说本案需要垄断行为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能否认定本案属于行政性垄断还有值得商榷的空间,这确实是笔者一开始所忽略的内容。但由于本案涉及面广,原始资料信息难以全面搜集,也并没有经过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也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程序,所以现在已经难以判定本案是否超出产业政策范围而进入到《反垄断法》的规制领域。
二、强制的认定
行政机关的行为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强制?强制的内涵是什么?被强制的经营者是否完全丧失营业自由?行政限定、行政授权是否属于行政强制?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发布行政规定等抽象行政行为,能否达到强制的效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通过案例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契合实际的答案。
通过研究分析“上海市交通委强制黄浦江游览行业游船企业达成并实施了固定或者变更服务价格协议案”与“北京市住建委强制企业统一执行质量控制价案”,我们总结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政机关通过组织引导等方式授意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继而,行政机关通过各种具体行政行为保障垄断行为的顺利进行。
在“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参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达成市场分配固定价格协议案”中,行政机关组织、引导了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并下发通知确定市场分配方案、统一价格,但并未进一步采取措施保障该垄断协议的履行。行政机关的行为并未达到“强制”程度,而经营者也有自由从事经营活动的空间。即使经营者拒绝实施该垄断协议,也不会遭到现实的不利益。因此行政限定并未达到强制的程度,不属于第36条的调整范围。
对于行政授权而言,行政机关授权给经营者,使他享有从事垄断行为的“权力”,这种情形下,经营者可以实施垄断行为也可以不实施垄断行为,享有充分的营业自由,并未被行政机关强制。在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行政规定,要求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经营者面临的不利益并不是即刻就到来的,他依然有行动的自由,只有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定,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才有可能构成强制。行政限定与制定、发布行政规定最主要的区别为一个是具体行政行为,一个是抽象行政行为,但都没有使经营者完全丧失行动的自由,达到第36条所规定的“强制”的地步。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又可以得出,强制经营者从事垄断性行为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必须是违背其自身意愿,被迫做出的。经营者如不实施垄断行为,将会面临现实的不利益。
综上所述,第36条所言之“强制”,应当从两个方面(即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两个角度(即行政机关角度与经营者角度)予以观察。在客观方面,行政机关对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提出明确要求,并通过各种行政手段监督、保障垄断行为的实施;在主观方面,实施垄断行为并非经营者出于自愿,而是被迫实施。而在认定方面,应从行政机关的客观行为出发,在客观方面满足“行政机关对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提出明确要求,并通过各种行政手段监督、保障垄断行为的实施”,即可推定构成“强制”。如有证据证明经营者也有实施垄断行为的主观意图,可以推翻对“强制”的认定。
三、经营者法律责任的认定
《反垄断法》第46、47、48、50条对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包括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和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在经营者被强制实施垄断行为时,其应否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将是本部分讨论的重点。
在“云南省通信管理局牵头组织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铁通四家的云南分公司达成垄断协议案”中,经营者被强制实施垄断行为,最后被处以巨额罚款,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命令等具体行政行为,使经营者违背自身意志实施垄断行为。面对行政机关的强制,作为理性人的经营者别无他法,只有实施垄断行为才是其所处困境的最优解。如果经营者拒绝从事垄断行为,他将直接面临来自行政机关的现实不利益。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在经营者丧失营业自由的情况下,不应当对其处以罚款,这与民法、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非常类似。
从法律责任的功能出发,笔者将进一步对反垄断法上的经营者责任与刑法、民法上的法律责任进行功能性比较。《反垄断法》所规定的罚款与刑法上的刑罚所具有的功能都是惩罚行为人,罚款是较轻的惩罚,刑罚是较重的惩罚。《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与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都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害。在《刑法》第21条规定紧急避险是行为人免于承担刑罚责任的违法阻却事由,在《民法总则》第182条与《侵权责任法》第31条规定了紧急避险可以使行为人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基于法律责任功能上的类似性,经营者被强制实施垄断行为,也应当免于承担罚款与损害赔偿责任。
《反垄断法》上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与民法上的停止侵害(《民法总则》第179条)都是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反垄断法》上的没收为违法所得与民法上的返还财产(《民法总则》第179条)都是要求行为人将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交出来。停止侵害、返还财产又都是着眼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而不过问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如何;换言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项违法行为,就可以要求他承担停止侵害、返还财产。因此,基于功能上的相似性,只要经营者实施了垄断行为,就可以责令他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他的违法所得。因此,笔者认为,当经营者被强制实施垄断行为时,其不应当承担罚款、损害赔偿这两种法律责任,但应当承担停止违法行为与没收违法所得这两种法律责任。
四、反垄断执法建议
综上所述,当经营者被强制实施垄断行为时,其不应当承担罚款、损害赔偿这两种法律责任,但应当承担停止违法行为与没收违法所得这两种法律责任。具体到上面提到的云南省通信管理局强制垄断案,不应对四个经营者处以罚款,而应当对其处以没收违法所得。但是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没收违法所得的比例非常低,根据《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大数据分析报告(2008—2015)》[2],在发改委处理的175个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的案件中,仅有8件没收经营者的违法所得。究其原因,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额的计算非常复杂。反垄断执法机关如果要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将会耗费大量的执法成本。相比较之下,罚款是一个简单、高效、便捷的处理方法。但是执法机关的这种处理方法明显缺乏合理性,也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因此笔者建议,执法机关不能为了处理上的方便,而简单地以罚款替代没收违法所得。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提高自身执法水平,在执法过程中逐步发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法律责任本身所具有的功能,而不能张冠李戴,通过罚款使主观上无辜的经营者受到惩罚,而对其违法所得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