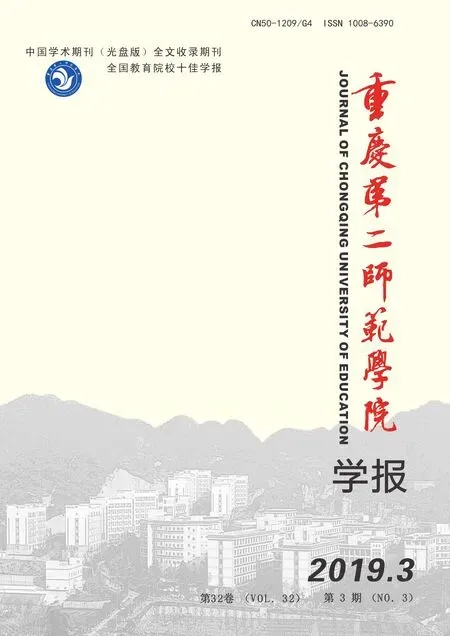江西书院序跋记赋等文本价值刍议
温世亮, 温春晖
(南昌师范学院 文学院, 南昌 330032)
书院乃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教育文化机构之一。有关中国古代书院所承载的教育文化功能的先贤宏论,亦多见载于诗文总集、别集、方志、谱牒、笔记等典籍文献。清代袁枚指出:“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随园随笔》卷十四)[1]由此可见,肇始于学术讲习的书院,自其起名之时,便与学术文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培育人才、积累文化、传承学术的任务,并且以讲学、著述、藏书、刊刻等具体的实践方式,使这一任务得以落实。面对具有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国书院之废止,近人胡适颇为感慨,他在《书院制史略》中指出:
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我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2]
那么,对中国书院的废止,胡适何以会如此痛心疾首?这自是因为千百年以来,书院所承载的那种“自动”的知识积累、文化传播、学术研究等书院精神不复留存于世。
其实,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无论处于怎样的现实环境中,书院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都功不可没。唯其如此,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一个极显分量的部分,地域学术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自当受到书院教育的深刻影响。在这一点上,白鹿书院与江右文化、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丽泽书院与浙东文化,可以说都是极具引证意义的实例。其他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乾嘉汉学的传播等,实际上都与书院有着扯不断、道不尽的关联,这些同样是有力的依凭。
江西乃“理窟”之地,器重书院讲学的朱子学和阳明学于此地先后发育传衍,从某种意义上讲,江西亦借此成为古代书院文化的发达区域。据记载,自唐至清,江西书院不下千所,数量居于国内前列。不仅如此,江西书院文化在许多方面均发挥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诸如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鹅湖书院、豫章书院等。只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和近现代新式教育的兴起,书院文化亦渐趋式微。江西自不例外,许多曾经名震一时、影响深远的书院,在近百年的各种思潮和运动的冲击之下,甚至连遗存、遗址亦已不复存在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书院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命脉,并未因此消亡殆尽;相反,它借助于文史典籍中的序、跋、记、赋等得以传布。这些作品到底流传下来多少,因种种原因,暂时还无法做出全面准确的统计,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为江西书院所创作的序、跋、记、赋,显然具备了较高的文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它们不仅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掘、传承和发展,而且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其具体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借此可以印证江西书院实乃书院讲学的重要源头。从内含上讲,讲学有研习、学习、公开讲述自己的学术理论等多重意思,因此它也具备了传播学术思想、培养专门人才的多重价值。中国古代讲学之风的开启,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不过书院讲学之风的盛行,则要等到有宋一代。对此,近代学者商衍鎏有专门论述,他指出:“唐以前(书院)为藏书之地,宋以后或为讲学,或为祠祀,或为考课,而讲学考课者每兼藏书与祠祀。但书院所重者实在讲学考课两端,其藏书祠祀特附及耳。”[3]234书院最初的功能在于藏书,至于赵宋王朝,它才逐渐发展成为讲学之所,开始演变为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在这一点上,坐落于庐山五老峰南麓素有“海内第一书院”美誉的白鹿洞书院,无疑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最初称“庐山国学”(亦称“白鹿国学”),后因战乱趋于没落。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省庐山市),巡视陂塘和庐山,而由庐山之东始得白鹿洞书院之废址,慨然叹其荒芜而重加修缮,并设立办学规条和宗旨,且亲自登坛讲学,以培育四方之士。继又托东莱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以启发学林。自是而后,书院集藏书与讲学为一体,其教育功能得以强化,其文化价值亦得以进一步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洞书院于书院教育文化功能的开发,确实功莫大焉。其实,于此前贤亦多有阐扬。譬如,清代桐城派文人方东树在其《重刻白鹿洞书院学规序》中说:
书院之设,肇自唐开元中,与古石室精舍相似而不同。始东宫丽正殿藏经籍,置修书院,已而大明宫外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盖用以广购求,事校雠也。逮宋嵩阳、庐阜、岳麓、睢阳各立书院,以居生徒;赐之经传,以相斆学,而白鹿洞经朱子设教,其地其精神所萃,千古犹留。登其堂而思其教,诚问学之津梁,入圣之阶梯也。[4]卷三
江西作为理学渊薮,乃朱、陆并兴之地。南宋时期,书院林立,讲学蔚然成风。一方面,江西书院兴盛的原因,实与当地理学文化的发达关系密切。与白鹿洞书院借助朱熹义理之学而传声于天下一样,金溪的象山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等,同样是借助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性之学而生辉发育,享誉宇内、瓣香后世的。另一方面,理学同样借助白鹿洞、象山、鹅湖等书院的讲学教育功能,方得以传承光大于后世。因此,清代大儒何义门才会在其《鹅湖书院记》中生发出“江右故理学地,必有游于斯而奋乎兴起以绍前绪者”[5]卷二的感想。
其二,借此可以寻绎书院精神的内在本根。书院讲学的宗旨是什么?它的精神本根又如何?是否一如人们所陈述的那样——书院乃科举之门户,终南之捷径,带有鲜明的个人功利色彩?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确乎可以借助这些流传下来的序、跋、记、赋等文辞。
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其设置宗旨,完全是以朱熹所奉行的“道”为准则的。朱熹曾说:
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明日烦教授诸职事,共商量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两学,共讲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听其所之。学校本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岂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学问自是人合理会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会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将来,安在身上,自是本来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己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圣贤紧要警策人处,如何不去理会?不理会学问,与蚩蚩横目之氓何异?[6]2655
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着眼于“义理”阐扬儒家之精义,或者说其治学之本根在于使人明于义理而治于天下。在这里,朱熹很明显是要求学生读圣贤书要读透、读懂,而不是为了科举浅尝辄止。由日常学习入手论高深的学问之道,论“明明德”,这恰恰体现了朱熹读书为己而非为人的基本理念。其实,这种理念也在朱熹所作的《白鹿洞赋》中得以落实。其赋云:
天既启余以堂坛,友又订余以册书。谓此前修之逸迹,复关我圣之宏模。亦既震于余,乃谋度而咨诹。尹悉心以纲纪,吏竭蹙而奔趋。士释经而敦事,工殚巧而献图。曾日月之几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葱珑而绕舍,水汨汨而循除。谅昔人之乐此,羗异世而同符。伟章甫之峩峩,抱遗经而来集。岂颛眺听之为娱,实觊宫墙之可入。
实际上,这一理念也为后学所认可、承继,并渐次发育为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精神的命脉本根。关于《白鹿洞赋》的含义,历来学者予以了阐释、推扬,同时又均将弘道作为其核心予以发挥。在此,谨举几例为证。元儒虞集《朱文公白鹿洞赋草跋》有言:
某尝泛彭蠡,登匡庐,升斯堂,三复于斯文矣。于所谓诚明两进,敬义偕立,凛然有迟,莫无及之叹。[7]卷十一
明人李东阳在《白鹿洞志序》中称:
或乃游昭道之地,览兴亡之本,详创继颠末之因,养之者具,观程有要,日用有需,而乃犹不务实也;又或鲜情饰誉以干禄,附贤躅而罔厚利,则斯洞也,特终南之快捷方式焉矣!呜呼,斯则予伤哉!斯则道之不明不行也哉![8]卷五十
清初文士昆山徐元文所作的揭橥,同样清晰。他在《跋所书白鹿洞赋》中指出:
朱子白鹿洞书院所揭诸楣间者,自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莫不备具,而谆谆道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在于修身以及人,而不在记览词章、声名利禄,其言切矣。[10]卷三十
清中叶白潢所作《白鹿洞志序》,同样是合朱子之意而衡定书院之宗尚的,其谓:
复有书院志者何?曰:重道也。孔孟之道,惟朱子集其大成,而白鹿书院为朱子设教之地,精神所萃,登斯堂而遵斯教,可为学道之津梁。[10]卷一百三十九
晚清桐城派文士陈用光,亦以朱熹学规、讲义为则,揭露抨击“近百余年来,狙诈矫之风其慗置乎”的伪善恶习,倡导“夫重朱陆之讲义,诵之口而反诸身者,将为其实也,非为其名也”[11]卷六。
综上所述,弘道、传道实乃白鹿洞书院创设的宗旨所在,而朱熹教人为学的目的,显然与达于仕宦的个人私利殊途异辙。相反,其本根无非是儒家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中蕴蓄着极其深厚的家国意识。如果带上“个人功利”这一主观意识来评判白鹿洞创设的宗旨,小而言之,是违背朱熹的本意,大而言之,则是对中国书院精神的曲解和亵渎。
其三,借此可以体察书院与文学的内在关联。中国古代社会虽存在重学轻文或重道轻文的倾向,但作为学术教育文化机构,书院却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是从书院教学的内容来看,“四书”“五经”历来是其重心所在。这些典籍被奉为儒家之经典,固然有突显其学术性、哲学性的意味;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无论“四书”“五经”中的哪一部经典,实际上都与文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大都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所以,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总是无法绕开这些经典来谈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又每每将它们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活水,从文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论析它们的思想性、艺术性、影响力等。二是前面论及书院教育首重传道、弘道,概而言之,其实就是对儒家入世精神的弘扬。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先儒所崇弘的“文道合一”思想经由国学、书院等教育而得以深入人心,“文以载道”的思想俨然成为指导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这在上层文学的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道德旨趣的劝诫、高尚人格的培养、社会担当的弘扬等内容融入文学也便成为这一文学群体创作的题中之义,甚至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书院体写作形态,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书院文学”。三是明清之时,受政治制度、择才策略和学术思潮等的深刻影响,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日渐紧密,“许多山长都把讲学与举业统一到书院的教学之中”[12]140,考课成为书院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这种变化固然具有遏制“书院的精神和优良传统”[12]163的不利因素,但是结合明清时期的科考实际,我们不难发现明清以降,特别是“清中叶后,书院崇尚博习经史词章”[13]174。也就是说,和词章一样,经史内容依然是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总的来看,这种变化虽然具有削弱学术研究的可能,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词章(文学)的地位,对促进词章(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对此,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清人戴钧衡的相关评论,他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说:
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胶庠,乡里得而贱之。读经未毕,辄孜孜焉于讲章时文,迨其能文,则遂举群经而束之于高阁。师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学。当是时,不惟无湛深经术、明体用之儒,即求一二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可多得。[14]卷二
显然,戴氏对明清以来书院的教学变化是不满的,但其富于批判倾向的言说却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推动文学发展上,明清书院教学制度的变化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抛开古时那种重经史、轻文辞的传统观念不论,“讲章时文”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它毕竟有利于文化、文学和学术的均衡发展①。
其实,轻文重道,强调以儒家精义来指导文学创作的思想,在有关江西书院的序、跋、记、赋等文辞中亦多有表现,这恰恰彰显出书院文学固有的特点。如何焯《鹅湖书院记》:“今语高第弟子,则文学之科同配圣师朱子,叙道统渊源,并以周程邵张释奠精舍,未尝以其小不同者为病。”[5]卷二此中表达的显然是以学术思想驾驭文学的观点,道重于文的倾向至为清晰。又如欧阳守道在《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中称“自前年创入部阙建议之臣无见于教化之本原,请以授文学之权入官者,而书院滋轻矣”[ 15]卷十四,认为“授文学之权入官者”会影响书院的价值,其轻文重学的思想同样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文以载道思想的存在,使得这些关乎书院的序、跋、记、赋等文本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即便那些文学色彩较为突出的作品也不例外。如朱熹的《白鹿洞赋》,其本身就是一篇艺术性足称上乘的美文,既有大气磅礴、汪洋恣肆的气势,又不失淳雅正则的面目,因此每见于贤达之赞誉。那么,它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呢?质而言之,《白鹿洞赋》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不外乎“请姑诵其昔闻,庶有开于时习。曰: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其创作理路明显受到文道相贯思想的控驭。在朱熹撰写《白鹿洞赋》之后,后人陆续创作了20余篇白鹿洞赋,然而归结到一点,这些作品大抵都未能突破文以载道的范式。
同样,诸如《象山书院记》《鹅湖书院图》《白鹭洲书院记》《江州濂溪书院后记》《澹台祠友教堂记》《安湖书院记》《凤仪书院碑》《兴鲁书院记》《崇儒书院记》《郑溪书院记》《匡山书院记》《复古书院记》这些有关江西书院的作品,如果仅就艺术性而言,尚难以达到《白鹿洞赋》的高度,甚至淡乎寡味——由于过分强调“义理”的表达,教化意味浓厚、文学色彩阙如。也正因如此,在阅读这些作品之后,我们难免会产生那种文心见于道义的体会。
其四,借此可以助力当代文化建设。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存,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回溯、探寻和挖掘的过程之中,同样也从当代文化建设中得以展示。目前,随着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提上新的日程,沉寂了近百年的书院开始呈现出复苏的迹象,从政府倡导到民间组织和个人投资,从高校建设到地方兴建,大有遍地开花之势。不可否认,贴近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大潮,当代书院建设在创办宗旨、建设流程乃至教学内容等方面,其实都面临着诸多困境、存在不少误区。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传统书院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应该说,传统书院是纯粹的人文教育基地,旨在夯实和厚植儒学之根基,培养具有忠、孝、礼、智、信健全道德人格的人才,以有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就其效应而言,这固然存在诸如封建保守性、压制性、奴性化之类的缺陷,但是如果从发挥正能量的角度来考虑,依然是利大于弊的。将传统书院的建设宗旨有选择地移植到当代书院建设之中,同样有利于推动、促进和深化国家的社会建设,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传统书院教育重视义理的阐扬,重视高尚人格的修养,对腐化堕落、损公肥私的利己之风,是极力反对的。“四书”“五经”等经典,作为儒家思想的灵魂所在,传统书院教育正是借助这些看似教条的知识的讲习、研修和传播,最终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正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显然,如果能将传统书院的教规宗旨付诸实践,对于提升当下的道德人心,亦不无好处,对于当前反腐倡廉工作而言,同样不乏实际的警示和宣传价值。另一方面,在当今书院如高校书院建设当中,我们该如何具体操作实施?该如何优化更新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是坚守传统的以经典研习为本位的人文教育,还是将经典教育、通识教育、人文教育、技能教育熔于一炉?这些问题,如果结合当下实际,我们都可以比对和省察那些文史经典中流传下来的诸如序、跋、记、赋之类的书院文本,在去伪存真、剔粗求精的辨识中,做出正确评判和决断。在这个时候,传统书院文本所具有的应用价值也因此得以体现。
此外,在时下极为流行的旅游文化建设当中,江西书院文本同样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和利用价值,它不仅承载着江西的文化厚度,而且堪称一张宣传江西的重要名片。以江西庐山为例,庐山之美,更多在于它所具有的人文资源,而白鹿洞书院便是其中之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庐山正是借助于书院、宗教、诗歌等这些人文景观生辉于世,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有了“文化圣山”之誉。旅游作为休闲文化之一种,虽然存在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但又绝非仅仅在于满足游客的感官需求,同样要注重其内在的精神文化需求(如历史人文精神的濡染和提升)。推而广之,在实际的旅游建设当中,我们可以借助流传下来的书院文本复原曾经的书院实体,但又不可仅止于此;同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充分利用书院的序、跋、记、赋等文本进行人文教育,使游客在旅行中尝试体验古人的修身方式,体会感悟精神的洗礼净化,将书院所具有的优秀文化内涵得以重现延续,使它的精神向导作用重新焕发出来,如果借用前引何焯的话来讲,就是要使游者产生“游于斯而奋乎兴起以绍前绪”的激情。换言之,如果撇开经济效益而论,书院、寺庙、诗歌等文化景观资源,无疑更具有实质性的历史人文精神内涵,它赋予了旅游作为文化的最基本条件。相反,如果只是一味抹杀书院等文化资源的内在精神价值而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高扬(如在现实中,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书院建设“房地产化”的现象,存在借机圈地、牟取经济红利的倾向),或者以此作为捞取政绩的手段,那么,这样的旅游建设绝对只会是一种舍本逐末、急功近利之举,它也势必会在无知无畏中、在无声无息中走向夭折,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实例并非鲜见。总而言之,“风物长宜放眼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是一种大趋势,但如何妥善处理好两者关系,又是当下一个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当前书院文化的挖掘,虽然面临诸多困境,甚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使传统作用于现代、现代受益于传统的契机。我们自应好好地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最大限度发挥书院所具有的文化名片功能。
中国书院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远非上述种种所能涵括。江西作为中国书院文化最为重要的代表之一,其书院文本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与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一样,同样具有相应的典型性和示范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价值意义在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正确引导下,终究会得到全方位的发掘,并日益显现出来。
注释:
①盛朗西认为,“清代书院方式,大别为三:一为讲求理学之书院,一为考试时文之书院,一为博习经史词章之书院”,并引江藩《汉学师承记》所说“清中叶后,书院崇尚博习经史词章。阮云台开辟诂经精舍,延王述庵孙渊如等主讲习,课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许各搜讨诗书条封。至于词章,在乾隆时已多足称。如沈归愚先生为紫阳书院院长时,选王兰泉、王凤喈、吴企晋、钱晓征、赵升之、曹来殷、黄文莲等七人诗,称为吴中七子,流传日本,大学斗默真迦见而心折,附番舶上书于沈归愚先生,又每人各寄忆诗一首,一时传为艺文盛事”,进而指出“迨姚姬传主讲钟山书院,更以古文倡天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