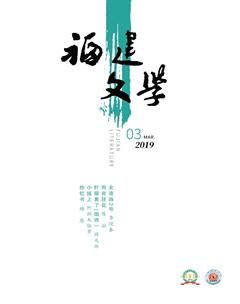野性的天空
梦乡
老北京人喜欢养花种草,也喜爱遛鸟玩虫,这曾经被忙于生计的人所羡慕,也曾经被志存高远的人所诟病。但我明白这并非他们的专利,在我所居住的南方小城,确切地说在这么一个宁静优雅的校园里,这里的知识分子们也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亲近自然。虽然我与他们对自然和生命的理解都不同,但我却从小和他们爱上了同样的东西。即便在很久以后的今天,在我因为种种的生活变故已经和自然的生命存在距离的今天,每当高楼间狭窄的天空掠过成群的白鸽,我还是会想起和它们共处的时光。
城市是属于人类的,但自然却是属于一切生命的。当人们在彼此间繁复的交往和谋划中感到疲倦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或许就是对自然的那份親近。我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本能,一种不需要学习的本能。当我再次推开窗户,无论我身在何处,在那能够看见天空的高度,生命依旧荡漾着原始的自由,就跟童年时的我们一样。
一
从我记事起,我的家就是这座校园的一部分。几十年来,它的面貌发生过无数次变化,但除了那些与学习紧密相关的建筑,唯一不曾变化的就是这里数不胜数的动物和植物。校门里正对的是一个填满了各色花卉的圆形花坛,两侧是几片种植着玉兰和杧果的绿色园地。楼群里除了一座长满翠绿嫩草的山包,还有一座游弋着小鱼的假山池塘。一片名叫琴湖的水面时常翻滚着鲇鱼吐出的气泡,果实累累的龙眼树包住了池塘的一角,周围是一圈罗汉竹围成的篱笆。
听父亲说,在他来到这里工作的那个年代,这片位于市郊的方寸之地周围尽是一望无际的稻田。直到新的食堂建起的前夜,推开围墙上的大铁门,门外仍旧是一片叶浪翻滚的芋头地。这是一片和自然不分彼此的天地,好像每一座建筑都是和生命相生相伴的,就像我家隔壁的老宿舍楼上遍布的爬山虎一样。
这也是一个接受自然馈赠最多的农庄,从前的职工在这里分享丰收的稻米,后来的工人在这里采摘芬芳的玉兰。在我还是学生时的每个假期里,学校都会给每个家庭送去一袋新鲜的杧果。生活在冷漠城市里的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伴着生命的温度慢慢成长,即便我没有父母亲那样与自然界零距离的童年,我也从不会感觉到生活的孤独与寂寞。雨天里我可以在草地边寻觅挂着露珠的蜗牛,晴天里我可以在母亲的帮助下捕捉杧果树上的知了。我爬上那棵长着盘龙般虬枝的老树,把玩挂满枝头的犹如红色镰刀般的花朵。在那座技工学校的老房子尚未拆除的时候,我曾经小心翼翼地从墙根铲下成片的苔藓。在那个培育花卉的苗圃尚且存在的时候,我也曾经兴致勃勃地捞取过水洼里漂浮的绿萍。
那时候我家楼下的大女孩还没搬走,我年迈的外祖母也仍然健在,她们可以陪我在阳光下翻煮刚刚撅起的水萝卜,或者带我逐个拔取竹篱笆上的竹芯回家泡水喝。那时候那个后来成为门球场,再后来成为一片草坪的游泳池仍然闲置着,在孩子眼里深不可测的池底一侧积满墨绿的雨水,上面遍布着可以喂猪的大叶水草。每个夏日的夜晚和黎明,我都是在清晰而夸张的蛙声中入睡和醒来的,那种声音就像清泉里涌出的水泡声一般传出很远,让今天的我联想起辛弃疾那首著名的《西江月》。那时候今天成为我新家的高地也仍旧是荒废的,一片遮天蔽日的老树簇拥着早已无人居住的校长楼,树下是一张枯叶和杂草编织成的松软而厚实的地毯。
那里曾经是我的百草园,暑假里的每个清晨,我都会骑着小单车爬上种满木芙蓉的高坡,来这里寻找亲近自然的快乐。无须介意院墙外的猪圈里飘来的臭气,单是叶影间飞蹿的斑鸠就足以把喜爱打猎的舅舅吸引到这里。还有那棵紧挨着墙边的木瓜树,青绿的果实中总会有一两颗熟透得摇摇欲坠,我和母亲曾经打下过最软的一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品尝木瓜的滋味,那种特别的甜美值得记忆一生。时光飞逝,今天,校园里很多生活的布景早已经永远是记忆了,但那两行高大的白桦树仍然坚强地挺立着,我不知道它们身边是否游荡过父辈的青春,我只知道它拥有撕不尽的树皮,就像千万张纸都写不尽的童年往事。但同样的乐土,《牛虻》的开头只用了短短的一节,幸好有那样一节文字,那是伟大生命的起点,也是疲惫灵魂的归宿。
在那座幸存至今的老宿舍楼里,我曾经的家位于视野良好的第三层,但我却从来羡慕住在一层的邻居们,甚至希望将来的家能够和他们一样。其中的理由很简单,一层的房子直接挨着地面,推开阳台的门出来,迎面便是一块不大不小的土地。住在那里的人们没有一个会让这块地终日荒废着。有人将它们用一人高的篱笆围拢起来,篱笆里种上一畦畦的大白菜,或是一簇簇的大蒜苗,于是日常的蔬菜就可以部分自给自足了,更有甚者完全把它们改造成花园或果园。就在我家楼下,那位大女孩的外祖父母种下了一棵桃树、一棵番石榴和一棵枇杷,每年他们都会爬上高处摘取那里的果实,有时也和住在楼上的我们一道分享它们。而在我已经没有记忆的幼年寓所附近,某位教授的园子里甚至种有一棵高大的桑树,它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初次饲养过的蚕宝宝咀嚼的就是它的主人赠予的嫩叶。即便在我尚不知道何为窃取的时候,我也曾偷偷猫着腰伸手拔过某个园子里的菜苗。我并不是希望用它充饥,只是无端地对那些篱笆后的世界充满好奇,他们为什么会种植那么多东西?它们是怎样长大的?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这样的园地?我一边徘徊在园子周围,一边无数次地问自己。
或许是受了这个难以实现的愿望的激励,还在上小学的我第一次在自家的阳台上开始了无土栽培番茄的实验。实验的材料都是工厂预先加工好的,但当鲜红的小西红柿终于挂满枝头,我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的欢喜。我终于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有所收获了,即便它们远没有那些园子里的那般硕大和完美。要是我能有个这样的园子,我一定也能把它们种出来。我于是一直做着这样的美梦,直到我搬离了那里,并且最终搬到了我从前视为百草园的那片高地上。木瓜树不见了,建设新居的人们如此冷酷地砍倒了它,我从此再也没机会品味那样的甜美。新家果真安排在了一层,但它再也不可能连着一片园地,真正接着地面的成了新的储藏间,门口对着的坡地上已经种满翠竹和绿草,再也没有空余的地面成全我的梦想。就连那棵从老家的邻居那里偷偷拔来的昙花也一样,种在花盆里的它再也接不到地气,开放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后便日益走向枯萎。剩下的只有我对那些从不属于我的园子的怀念。
二
除了我的学校和我自己的家,我最常去的校园就是西郊的农业大学。那时候通往那里的道路还满是尘土,但每到周末,我和母亲还是常常会风尘仆仆地赶往那里。校园里到处是不知名的绿树,还有大大小小的池塘和连绵不绝的试验田。于是我们和许多垂钓高手们一起在路边的鱼塘里钓过鲫鱼,拎着鱼线独自在树荫下的虾塘里钓过龙虾。它们或是成了我们送给亲人的礼物,或是被校园里那家熟识的饭店做成了我们新鲜的午餐。在那条通往田地的杂草丛生的土路上,我曾经把鲜艳得像是红蛋糕的毒菇小心地装进塑料袋,而在田间地头的稻穗上,我也曾经发现和在农科院里秋游时见到过的别无二致的福寿螺和它们猩红的卵带。作为对我发现的回报,我们带回了满满一袋野生的田螺,并且大着胆子在家中烹饪出了一道美味的炒螺片。这是我第一次品尝来自大自然的野味,就像父母亲儿时常做的那样。尽管菜市场里有很多类似的河鲜,但它们再也没有带给过我同样的享受。
但这些其实都是后话了,我已经记不清初次走进这座校园是在何时,只记得那时自己还是个懵懂的孩子。有赖于父亲委托的关系,我们见到了农大养蜂系的赵主任,而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昆虫学家赵修复。面对他和他的学生们善意的笑容,站在他们面前的我既崇拜又兴奋,但看上去却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但他们并没有亏待我这个小昆虫迷,从他们手中,我如获至宝地接受了几大盒昆虫标本的馈赠。其中有各种蝴蝶和飞虫,甚至还有一只闪着油光的大独角仙。这些都是我在那些五彩斑斓的昆虫学书籍上反复浏览过的,我从没有想过此生能有机会拥有它们,但却在他们的帮助下轻易变成了现实。
许多年过去了,对待那些小生灵的态度也已经今非昔比。这或许是一个成年人才会具有的转变,从前的我希望拥有和索取,今天的我则宁愿观察和欣赏。从前的我会在自家附近用独创的手势夹起蝴蝶的双翅,也会在军训的日子里用喝剩的空瓶装起泛着微光的萤火虫。但今天的我更愿意拿起手中的相机,远远地拍下那些昆虫在花草间的倩影。因为我明白它们是和我们一样的生命,甚至由于它们短暂的寿命而更加需要我们的怜悯,何必非要拥有它们的躯体呢?这样只会加速它们的离去。让生命自由地延续吧,这是大自然赋予一切生物的公平。但这样的良知同样应当是一个孩子的本能。记得在某次即将离开农大的路上,我从校园边的草丛里好奇地摘下一个坚硬的灰褐色卵囊。我并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只是在回家后随手将它遗忘在了书堆里。忽然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床上多了许多翠绿的小昆虫,它们的数量顷刻间越来越多,几乎爬满了整个书桌。细看之下,原来那是数不清的可爱的小螳螂。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名叫“桑螵蛸”的虫卵是某对螳螂的杰作。但在那个晚上,我还是和母亲频繁地来往于卧室和阳台,尽可能地将它们转移到家中的花草上。今天想来,我似乎做了一件分内的事,无论我是否拯救了它们的全部,终究不忍心看着它们因为我的好奇而过早离开这个世界。自由的滋味只有被束缚过的生命才会刻骨铭心,当一个孩子被日益繁重的学业禁锢在家庭与学校之间,如果他还没忘记那天的所见,他終会明白自己拯救的不是一群生命,而是自己的心灵。
三
福州的森林公园,尽管它位于偏远的北峰,但我对它的兴趣一点也不输给东郊的鼓山。它们都拥有漫山遍野的植被和树木,但不同的是爬鼓山的人们享受的是征服自我的快乐,公园里的人们体验的却是放飞自我的幸福。记得儿时刚去那里的时候,森林公园还未拥有招揽游人的“鸟语林”,但珍稀植物园却是它一贯的特色。那里的树木遮天蔽日,并且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殊品种。即便对于我而言,那里人迹罕至的氛围着实有些阴森可怖,但每次去公园游玩,这里总是我必到的去处。我会认认真真地核对每棵树木的名牌,然后抬起头向树冠望去,巴望着哪棵植物能够率先开花结果。实在看不清时,我就会低下头在树丛间寻觅,只要有一星半点花朵和果实的影子,无论它们是完整还是残缺,我都会如获至宝地将它们收集起来带回家中。
除了这里之外,森林公园与植物相关的乐趣还有很多。在池塘边我欣赏过“榕树王”深入水面的气根,在温室里我观摩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兰花展览。我的学校曾经不止一次把这里选为春游秋游的目的地,在通往龙潭湖的古道上我甚至品尝过草丛里鲜艳的野莓。但自从“鸟语林”落户公园之后,那里还是会吸引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游人的目光。它的特色似乎在于鸟儿们有条件的“人造自由”,它们被笼罩在一面铺天盖地的巨网之中,走进那里的游人们也一样。它们可以在天空自由翻飞,在人们的脚边随意停留,尽管这里并非真正的森林,也没有哪种森林能够同时网罗世界各地的珍禽,但人们似乎是很享受的,因为他们几乎足不出户就能和这些五彩斑斓的鸟儿零距离接触。但我却仍然感觉到一种透不过气的压抑感,好像在陪着这些动物共度铁窗生涯。
于是在新鲜感逐渐消退之后,我再也没有去那里逗留过,而是仍旧回到我最爱的植物园附近。那里曾有一个露天的饮品店,树下摆着几张西式的餐桌和靠椅,我们常在那儿休息。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地来到一棵大树边,当我小心地掀开它的树皮,一个尖尖的绿色小脑袋瞬间蹿入眼帘,母亲不禁惊叫起来,以为是蛇。但最终我们才发现,那是一只可以托在掌心里的翠绿的小树蛙,它全身布满黏液,显得弱不禁风但却楚楚动人。我们没有放它一条生路,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它带回了家中。我本想用自己的方式喂养它,却又不知道它爱吃什么,一番试验之后仍旧无济于事,我只能将它丢弃在装它的塑料箱里。好景不长,后来母亲告诉我,它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死去的厄运。
为什么“鸟语林”里的鸟儿能够存活下去,而我却养不活一只小小的青蛙?我心里一直存有一种不解的怨恨。今天我再次回味这件悲惨的往事,才隐隐约约有了自己的答案。就像那些常被视为宠物的小猫小狗,那些鸟儿的命运也是掌握在人类手中的,它们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换来的则是有条件的生存机会。但它们早已失去了支配生活的能力,即便将它们放归自然,它们或许也难逃灭顶之灾。和它们相比,那只树蛙才是真正让人敬佩的,它的生存机遇看似并不乐观,但它却可以在与大自然的竞争中获得。如果没有我插手,它或许可以一直这样自在地生存下去。它终归是死在了人类的手上,死在一种用自己的自由替代一切的生命手上。人们可曾想过,倘若我们也单枪匹马地面对自然,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不要以为自由的含义是可以轻易曲解的,更不要以为人类社会有多么的不可替代,它可以强大到制约整个自然,却唯独留不下它最普通的一部分。
四
或者是由于身为省会的优势,或者是符合人类生活的天性,福州城也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花鸟市场,只不过它的位置偏居于城外,而它的规模也远不及北京城里几十座同类市场。或许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反复而频繁地出入花鸟市场的确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几乎从未在其中遇见过自己的同龄人。
印象中的花鸟市场是一条覆盖着高大顶棚的幽暗而深邃的街市,熙熙攘攘的人流伴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木和珍禽异兽,还有充斥着耳鼓的喧嚣和刺激着嗅觉的腥臊,让这条肮脏破败而又热闹非凡的街道看起来就像一片神秘莫测的原始森林。尽管和北京著名的潘家园一样,这里同时也出售琳琅满目的古玩和旧货,但它们从来没有成为我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面对街道两侧鳞次栉比的花草摊位和宠物商店,兴奋异常的我就像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不时在这家停住脚步反复端详,又在那家催促着母亲问这问那,似乎每种前所未见的生物都在撩拨我拥有的欲望,每样可以作为商品的生命都值得我们认真地讨价还价。但事实也的确如此,每次离开那里踏上归途的时候,我的双手总是不会空空如也,或是拎着一两盆心爱的花木,或是抱着一只盛着宠物的铁笼。那时的我也总是心满意足地想,我一定要善待我的新朋友,或是将它们养到开花结果,或是让它们永远陪自己玩耍嬉戏。
但事情的结果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有一次我带回了一棵娇嫩的含羞草,自从把它安放在阳台的角落,一整天的时间我都在不亦乐乎地拨弄它的叶片,看着它们反复张开挺直又反复收起下垂,就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喜出望外。直到有一刻,它的叶片再也没有任何反应,紧接着整株植物开始变得没精打采,最后终于在某天里泛黄枯萎。因为我的迫害,它最终没能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刻。
还有几次,我买回的或是一只可爱的小白鼠,或是一只精神的小白鸽。小白鼠踏着像飞轮一般旋转的鼠笼不停地奔跑,小白鸽在鸟笼里来回踱步咕咕直叫,看上去它们都有使不完的精力,谁也想不到会出现任何的意外。但不幸终究降临了,或许是由于过度的疲劳,小白鼠没有吃进一粒鼠粮便被活活累死了。我这才明白,商家在为它设计这只残忍的笼子之前,他或许就没有指望它活得太久。而小白鸽在吃下我为它准备的不太合理的食粮,接着又被我关了漫长的禁闭之后,也不明不白地死去了。除了在商家和我的手中转换了位置,它最终也没有等来翱翔天际的机会。看着它们娇小而干瘪的尸体,我心里忽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恶心和悲哀,是我这个貌似热爱生命的人亲手断送了它们的活路,如果它们没有被卖给我,它们或许还能够活得再长一些,哪怕仍旧不是完整的一生。我忽然想起电影《U571》里的那句台词,当艇长命令水兵拉比特将同伴的遗体发射出舱外迷惑敌人时,他满怀悲凉地问了一句:“就像垃圾一样对待他吗?”是的,一个鲜活的生命难道就要像垃圾一样被拥有过它们的我们扫地出门吗?但我们别无选择,它们已经死了,如果我們不那么做,它们只能在我们的眼前腐败变质,而这就是从属于人类的生命所面对的命运。
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我买回的那只巴掌大的小白兔在我们全家的呵护下健康地长大,我们专门为它去菜市场捡回新鲜的菜叶,买回大个的胡萝卜,甚至不时专门为它淋浴洗澡。看着它眯缝着双眼舒适地蜷缩在我的怀里,我心里真的有种说不出的成就感。我本以为它会伴我一生,但随着它的日渐长大,家里渐渐无法担负抚养它的责任了,它也只好像那只白鸽一样,伴着浓重的尿骚味被我们锁在了阳台上的铁笼里。谁也没想到,它竟然也难逃死亡的命运。是父亲结果了它的性命,理由很简单,我们已经对继续养着它失去了耐性,或者再也不愿看到它白白地死在我们手上。它终于做出了终极的贡献,它的遗体被送到了幼儿园的厨房里,结果我儿时的同学们每人都在午餐时分到了一碗香喷喷的兔肉。但我没有品尝属于我的那份,甚至不忍心多看它一眼。
在很多时候,人类身边的花草和宠物就是一种被他们生造出来的伴侣,就像他们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一样。它们原本只是和我们萍水相逢,而一旦它们走进我们的生活,它们就好像分享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灵魂的一部分也随之寄托在了它们身上。从此它们就不再只是它们了,当它们因为我们的过错死于非命,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好像被它们的死带走了一部分,这或许就是离开了老屋和老伴的老人很快便会死去的原因。从此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刻意地养花养鸟了。我明白我们也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平凡的生命,当一个个真实的生命亲手终结在我们手上,我们或许才会明白人类在天灾人祸的面前是多么的苍白与无助。生命是需要尊重的,哪怕它只是一个卑微的宠物,因为它的存在意味着一个梦想的延续,而它的终结却意味着一个世界的毁灭。
五
大约就在十年前,在北京逗留将近五年的我终于回到了家乡。那时的我脑海里还残存着后三海碧波荡漾的水面和静宜园漫山遍野的红叶,但重新踏上家乡土地的我不仅远离了所有来自京城的记忆,甚至连儿时那条树影横斜的南后街也一并彻底失去了。一同遭受打击的还有我自己的家,面对被白蚁蛀蚀得千疮百孔的地板,我只得在自己的家乡不可思议地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我最终返回家园之前,我一共搬过三次家。第二次是在一座崭新的小区里,窗外马路上只有川流不息的车辆,房子周围几乎没有多少绿意。第三次则是在一个陈旧的社区里,楼下的绿地虽然也有不少树木,但遍地飞奔的老鼠总让我不由得心生厌恶。只有第一次搬进的那个家给我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印象,那也是一群老旧的居民楼,只不过是位于一条僻静的深巷里。
记得刚搬进去的那天夜晚,拖着沉重行李的我们吃力地走进小区的大门,通往楼群的小路两旁种满了齐腰高的夜来香,幽幽的月光洒在身边的花木上,一股沁人心脾的暗香裹在凛冽的寒风中扑面而来,我瞬间就被这种迷人的环境吸引了。以后我才发现,楼下不大的空地全都种满了各色的果树和花草,把本来不大的空地装点得就像城市荒漠中难得的绿洲。矮矮的木瓜树上挂满了累累的硕果,靠近大门的地方甚至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每到春来的时候,落光了叶片的枝头总会开满火红的“英雄花”。于是细心的看门人夫妇总会架起梯子爬上门房的屋顶,将完整的落花收集起来晾晒成干。
尽管我只在那里度过了短短的一年,但那里的环境最能让我想起我出生长大的那个校园。可是当我重新回到它的怀抱里,它早已面目全非。大片的老屋在改造中化为乌有,大片的树木被草坪取代。在我儿时住过的老宿舍楼下,原先朴实无华的操场也早已替换成了高大的办公楼。那里原是教工家属们放松身心的乐园,但自从周围的绿树和房后的泳池成为记忆,住在附近的人们再也不可能听到清晰的蛙叫和蝉鸣。
看着这些不由自主的改变,我忽然想起了某个夏日里在这个老操场上看到的一幕。当我抬头望向高远的天际,在那耀眼的阳光与洁白的云朵间,竟然有一只像是雄鹰的大鸟缓缓地在头顶盘旋。那时的城市里是不太容易有鹰出没的,年幼的我痴痴地望着它的身影,就好像自己的心灵也瞬间飘忽地升腾而起,高得足以骄傲地俯瞰整个充满野趣与希望的家园。这样的感动只有那么一次,以至于每当我来到那座熟悉的老楼前,我总会习惯性地望望头顶不变的蓝天。那里似乎有一种自由的呼唤,呼唤着我那颗向往自由和野性的童心。
就像最近在电视上播放过的那部融合了自然与生活的纪录片里说到的,一位九十高龄的老钓手在爱尔兰高威市的大河里钓起了一只很大的鲑鱼,当他准备将战利品收入囊中时,那条大鱼却意外地挣脱了。站在远处的桥上观望的游人们却在此刻爆发出一阵由衷的欢呼声,“他们到底是为我欢呼,还是为那条逃走的鲑鱼欢呼,我也说不清。”事后老人淡然地说,他笑得那样开心,似乎丝毫不为自己的坏运气感到遗憾。也许在一位耄耋老者的心中,他最明白自由与野性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也为那条鲑鱼和那位老人欢呼吧,当他们成全了彼此的得与失,属于他们的生命才能像那条滔滔的大河一般奔涌不息。
记得当我们家还住在那座老宿舍楼里的时候,一楼对面的门洞里曾经住着一位沉默寡言的老教授。他用高高的篱笆墙围住了属于他自己的那片土地,透过那些篱笆的间隙,我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里面的花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盆景和宝石花。每天中午或是傍晚的时候,我还会看见他独自一人在花园里慢悠悠地忙碌着,没有谁知道他到底忙些什么,甚至没有谁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如此生活。我只是猜测他似乎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甚至和身边的世界多少有些格格不入。直到有一天,放学时候的我不经意间从他家开着的大门前走过,很偶然地瞥见他家客厅的墙上有一幅毛笔书写的条幅,它只有寥寥四个字,却引起了我无限的感慨和遐思:“草木情真”。这或许就是他对自然的理解,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当一个深刻的学者在字里行间读懂了复杂的世界,他回过头热爱的却是家中那些无言的花草。
今天回想起这些,我耳边似乎又出现了那部描绘爱尔兰小城的纪录片里那些来自寻常百姓的话。“你并不需要知道所有动植物的名字,也能欣賞它们的美,”这是那位年轻动物学家的话。“如果你对大自然缺乏热爱,人生就少了一份乐趣,”这是那位每天出门遛狗的老人的感想。但真正适合描绘那位老教授心境的或许是这样一句:“远离了城市街灯,我感觉内心也变得谦卑起来。”当一个智慧的人向卑微的草木低头时,他才会发现原来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尽在那生命的无言中。如果世上真的有属于人类的天堂,当我们真正拥有它时才会明白,那就是笼罩在一片野性天空之下的那个最纯真的人间。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