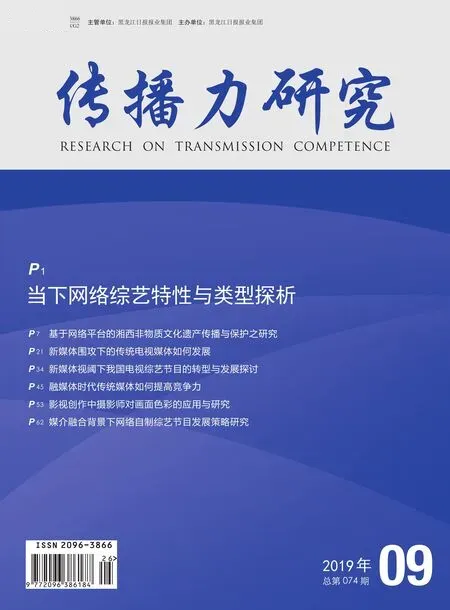我国环境治理中的传媒行动路径
——评《中国环境治理中的传媒策略研究》
郭辉 井冈山大学
我国传播学研究要迈向中国化,就需要贴近本国实际、回应本土问题。环境问题是当前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高风险因素。从水污染、PX到碳排放、PM2.5,环境危机已嵌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而公众对环境议题也由知晓到行动,卷入的程度逐步加深。在此背景下,姚劲松博士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环境治理中的传媒策略研究》聚焦于我国环境治理中传媒功能发挥的可能性与具体路径。该书共五章十五节。
作者尝试突破“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以国家、社会合作的框架,强调将环境福祉的利益相关者整合进环境治理网络,基于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最大化与可持续的目标采取共同治理行动。这应和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6—2020年)》中“构建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推动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共治局面”的要求。作者在书中避开西方治理理论与本土国情“水土不服”的问题,采用“策略—关系”的研究路径,既正视传媒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结构中受到的掣肘,又不纠缠于传媒参与环境治理的障碍,而是策略地将传媒设置为行动者,强调其以能动的实践策略在现有结构和制度的隙缝之间去发现环境治理存在的空间和契机,去促使中国环境治理网络的生成与共同环境治理行动的产生。“策略—关系”的研究路径,既是在实践层面推动环境治理研究的一种策略选择,又是治理理论本土化研究的一种路径尝试。
基于“策略—关系”的研究路径,作者以一章的篇幅分析了中国传媒在环境治理中出场的机会与可能,认为“国家—社会”关系变迁释放的治理空间、中国行政体制变迁提供的治理机会、非制度性因素产制的治理资本,都不同程度地为环境治理提供了空间,而市场的拉力、传媒非常规实践的经验积累、传媒调控机制的变化等因素则为传媒在环境治理中出场创造着条件,新媒体倒逼传统媒体响应社会诉求又驱使着传媒出场。紧接着,作者重点分析了传媒推动环境治理网络生成与共同环境治理行动产生的实践策略,为传媒推动环境治理提供了思路启迪。略举要者如下:
首先,培育具有环境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环境公民。环境公民既是环境治理网络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是最能产生环境治理所需的共同价值、共同原则和共同目标的源泉。所以,培育环境公民是构建环境治理网络的逻辑起点,也是现阶段大众传媒推动环境治理的有效着力点。大众传媒可提供与环境公民身份相匹配的“参考框架”、普及环境治理知识、展示环境治理方法、推动公众参与等途径培育环境公民身份意识、涵养环境治理能力。
其次,为环境治理主体供给舆论资源。舆论资源能为环境治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获取更多的舆论支持和资源供给。在媒介化社会情境下,大众传媒是“社会舆论工具”,是为环境治理产制舆论资源的关键力量。对普通公众而言,媒体要发挥筛选、整合和扩散信息的优势,为公众提供可信赖的环境信息和有影响力的公众话语承载平台,在环境议题中努力将公众话语整合为具有沟通权力和约束力的舆论资源;对环保NGO而言,传媒应通过为其提供表达与展现的空间,提高其社会能见度,赋予其社会地位和身份,为其产制与累积舆论资源;对环保政府部门而言,传媒应主动为其增强执法力度、树立行政权威提供丰沛的舆论资源,使其获得舆论与道义支持。
再次,促使环境治理网络机制的出现与运行。环境治理网络是一种不同于市场和科层的治理结构,有着不同的生成基础与运行机制。作者详细分析了环境治理网络的生成基础与运行机制,认为环境治理网络是多元治理主体形成的合作关系,其运行需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需以多元主体的对话与协商为基础。作者从环境治理网络的结构特征与运行机制出发,重点探讨了大众传媒在环境治理信息的共享与流通、治理主体的对话与协商、治理网络的监督与约束中具有的积极效用及其应该采取的能动策略。
最后,促使共同环境治理行动产生。“一致意向”是产生共同治理行动的必要条件。作者从承认、共识和默契等“一致意向”的生成路径出发,探讨传媒促进共同环境治理行动产生的策略。传媒可通过提高“承认”话语的能见度与感染力、建构“集体认同感”等策略,塑造与重构“承认”话语秩序;可成为“共识达成程序”的一部分,通过“真实在场”和“虚拟在场”两种形式搭建对话协商平台,成为对话与协商的促进者、组织者与传播者,以增益于环境治理共识的达成;可通过将低碳环保、绿色消费等价值与理念融入各类传媒产品,构筑有利于环境治理默契养成的语境。
总之,《中国环境治理中的传媒策略研究》在响应国情展开本土化研究、跳出治理理论的适用性争论、突破“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并就传媒促使环境治理网络生成和共同环境治理行动产生的具体策略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传媒与中国环境议题的研究、丰富了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