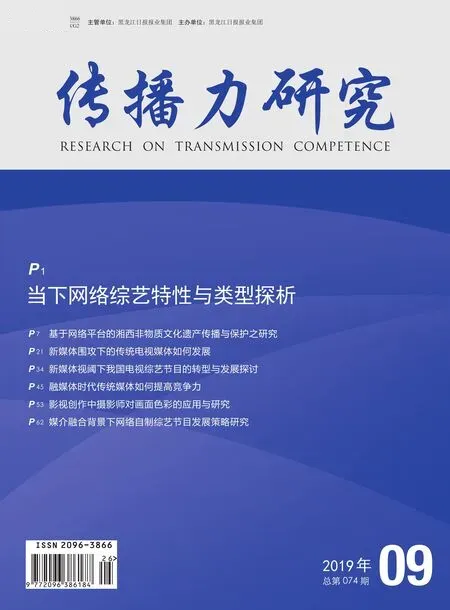论世界视野与中国新诗
黄娟娟 暨南大学文学院
一、概念的萌发:从“世界文学”到“世界诗歌”
1827年,德国作家歌德在与友人艾克曼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共有的共同财产……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我们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周游世界,了解其他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1]
“世界文学”概念自歌德提出以来,或被解读为以西方(欧美)文学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或被解读为对文学创作中民族性、本土性的取消。尤其是对于在世界文坛略显“弱势”的东方文学,“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使一些创作者、文学评论家乃至读者充满危机意识与压迫感。但我们知道,歌德本人对于中国传统小说与古典诗歌有着独特且深刻的见解,在这次与艾克曼的谈话中,他还津津有味地谈起贝朗瑞诗歌与一部中国长篇小说之间的对比。他希望德国作家能够跳出自身文化语境,与其他民族文学(异域文学)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丰富自身的写作。因此,笔者认为,在歌德这里,“世界文学”意味着一种更为开阔和深远的文化视野,这种视野是“世界性”的,是中西之间、各民族文学之间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是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和地理空间的包容与超越。同时,“世界文学”也意味着某种共同的、普遍的价值理念和体系的形成,因此得以超越民族、语言和文明的疆界而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读者心中激起共鸣。而诗歌,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理应具备这种“世界文学”视野。歌德在谈话录里对诗人的使命与诗歌创作提出这样的见解:
“如果诗人只复述历史学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学家走得远些,写得更好些。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人物都显出那位伟大诗人的高尚心灵。莎士比亚走得更远些,把他所写的罗马人变成了英国人。他这样做是对的,否则英国人就不会懂。”[2]
在这里,诗人被赋予了比历史学家更重要的使命。诗人,作为贫困时代的神圣祭司(荷尔德林语),作为人类高尚心灵的代言者,他所写下的诗句,必将比所谓的历史更为丰富、深刻。诗人的目光不应仅停留在本国的人民与读者身上,他的目光必须是“世界性”的,只有当他写下如莎士比亚戏剧般建立在人类心灵丰富性与深刻性根基上的诗句,他才会真正被其民族的人民所理解。诗人的征途不仅在其自身所处的国家、民族,他的征途是宇宙大地,是超越国别与文明而直击全人类心灵深处的广袤之所。
著名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于1990年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中率先提出“世界诗歌”这个概念,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宇文所安对于“世界诗歌”的态度并不乐观,更多的是质疑与批判。在他看来,“世界诗歌”即意味着对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取消,意味着趋同而非差异,意味着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向东方文学的进攻。作为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文明的汉学家,宇文所安表现出对中国新诗(现代诗)发展的怀疑与忧虑,他毫不客气地指出:
在与浪漫主义诗歌初次相遇以后,本世纪的中文诗在西方现代诗的影响下继续成长。正如在所有单向的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中都会出现的那样,接受影响的文化总是处于此等地位,仿佛总是“落在时代的后边”。西方小说被成功地吸收、改造,可是亚洲的新诗总是给人单薄、空落的印象,特别是和它们辉煌的传统诗歌比较而言。[3]
毫无疑问,宇文所安在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的研究上有着极高的成就。然而,在中国新诗这个问题上,其文明视野存在的局限,却似乎有些令人哑然。在他看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民族诗歌”与“世界诗歌”之间是不可调和、相互对立的。这种划分无疑使原本应具备的复杂的、综合的问题意识,陷入纯粹的二元对立的僵局之中。事实上,哪怕是早已具备主流影响力与话语地位的西方文学(西方诗歌),其优秀的创作者也从未曾站在中西两种文明独立的角度去进行创作。反之,他们都选择穿行在异域与归乡之间,博采众长,广泛地吸纳不同文化与文明中的优秀资源,以此来超越自身文化与文明所存在的局限,从而抵达更为深入的写作地带。如美国诗人庞德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吸取与采纳,他将“意象”引入西方诗歌并由此开创了影响了一代英美诗人的“意象派”。借鉴他国文明/文化资源并不意味“被同化”,庞德在运用“意象”时并没有将英美诗歌引向一条与中国古典诗歌相同的道路,相反,他巧妙地将“意象”的内涵延展开来,使其在西方文明的语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与作用。那首《在地铁站内》正是巧妙地运用意象来揭示整个西方社会人类生存境况的杰出之作。无论是中国诗歌(古典诗歌也好,现代诗歌也罢),还是西方诗歌,他们都属于“世界诗歌(世界文学)”之中,并且持续加速地朝着这种不可逆行的方向运行。宇文所安对于浓厚中华传统文明与中国古典诗歌持着一种文化眷恋的态度,但正是这种态度同时限制了他对于中国现代诗可能性的想象。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今日,我们还可能去建立一个封闭的、单一的、僵化的文明体系,继续将自己的文化/文明束之高阁,然后拒绝与其他文明对话吗?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自19世纪末西方强国以坚船利炮强硬地打破我们禁闭的国门后,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始终都处于“西方”影响之中。下文我们不妨梳理一下20世纪西方文学(诗歌)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影响与关系。
二、文明的交流:翻译文学与中国新诗
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孩子》中将翻译文明视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对话的载体,他写道:“文明是受同一精神分子激烈的不同文化的总和,其主要的载体——无论是从隐喻的角度还是就文字的意义而言——就是翻译。希腊式的门廊游浪至冻土带的纬度,这就是翻译。”[4]翻译承载的不但是文字和语言,更是不同文化/文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新诗)对现代性的获取正是在对西方文明(诗歌)与资源的借鉴与参照下完成的。西方诗歌不仅为中国现代诗人带来一种“世界性”的文明事业,一种与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相异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启蒙,还激活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即现代汉语。不论是“五四文学思潮”,还是1980年代整个文学“复兴”的黄金时代,翻译文学所承载的西方文化资源都在中国文学转型之路上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首先是带来世界观念和精神理念的革新与颠覆
在过去几千年的文学传统里,我们的诗歌,哪怕是最伟大的唐诗,始终停留在“诗缘情”、“诗言志”的层面,诗歌的基本主题亦没有超过咏物言志、感时抒怀、家国天下等人们习以为常的范围。但西方诗歌,自哲人柏拉图到尼采的时代,诗歌已完成了诸神、与哲学的接轨。中国古典诗歌走到晚清,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诗歌技艺层面,都已经陷入一种止步不前的状态。面临20世纪复杂的生存环境与文化语境,西方诗歌在揭示人的生存境况与精神状态等思想层面上展示出不俗的成就。整个20世纪,中国诗人对于西方诗歌及其文明养料的借鉴与吸收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如里尔克之于冯至;波德莱尔、马拉美之于李金发;奥登之于穆旦;荷尔德林之于孩子;保罗·策兰之于多多。
海子从德国诗歌传统中发现了诸神与哲学,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成了他精神世界的“灯塔”与“引路者”。荷尔德林曾写下“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荷尔德林本人及其诗歌这种孤独的、神圣的、烈焰似的气质深深地吸引和震撼了海子,同时更将这股强烈的诗歌之火传递到海子的诗歌当中。他在《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一文提到:
看着荷尔德林的诗,我内心的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沙漠,开始有清泉涌出,在沙漠上在孤独中在神圣的黑夜里涌出了一条养育万物的大河,一个半神在河上漫游,歌唱,漂泊,一个神子在唱歌,像人间的儿童,赤子,唱歌,这个活着的,抖动的,心脏的,人形的,流血的,琴。[5]
余虹先生在《神·语·思:海子及其他》里写道:“汉语世界是一个‘天地人’的三维世界,在此,没有神的容身之地。在此,‘神’只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人’,所有的神庙只是人庙,所有的神话都是人话。这个人的世界生下了那么多的人,神不在此。”[6]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诗神”一直都是缺席的,而也正是这种缺席使得我们的诗歌缺乏向存在敞开的深度与广度。余虹说海子使他惊讶,“这位操汉语的中国当代诗人竟走到了汉语失去的本源”[7],是荷尔德林诗句中的神性光辉与献身精神点燃与照亮了海子的内心。诗神在海子的诗歌是“在场”的。这就使得海子诗歌虽然也写乡村、写大地,却有别于传统乡土诗歌。他诗歌中的元素是东方的,是传统文明的,但他的哲思却是西方的,是与形而上的哲学和价值文明相连的。他将神、人、万物、天地、宇宙合一,在他的诗句中,所有传统意象:稻谷、麦穗、琴、马匹……所有的元素综合起来的诗句都是在与“神”对话与交流的诗句。而海子终其一生,都带着他自由、热烈、孤独的灵魂游荡在大地与天空之间,用他的诗句包括生命完成对“诗神”的献身。
另一位,九叶派诗人之一的穆旦,同样深受西方诗歌与诗学的启迪。三四十年代,时值西方学者燕卜荪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穆旦诗学理念以及日后的诗歌创作、翻译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穆旦更是远走英国留学,专心于西方文学的学习。因而他的视野一直都是一种“世界性”的视野,他前期的不少诗歌创作一直都处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接的“互文性”语境之中。穆旦留学回国后,即遭遇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时期,整个官方文学显示出了对世界文学潮流(包括诗歌潮流)的抵抗与拒斥。在缺乏了“他者”的参照下,中国新诗陷入了一种停滞、如死水般的状态。整个诗坛在“地表”上充斥着整齐如一、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政治抒情诗和民族颂歌。诗歌成为政治宣传的口号和工具,整个民族陷入矇昧和愚昧的黑暗状态。在那个诗人集体陷入沉默与失语的年代,穆旦即便受到政治打压(被划为“反右派”),却不忘诗人的使命与知识分子的责任,长达数十年,他独自一人默默忍受着政治上的批判与生活的煎熬,俯首案桌,递过了西方诗歌从黑暗中送来的“灯”,投入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中,而这种译介又“反哺”于诗人,使得穆旦内心的“存在之思”往更深处向诗神敞开。文革后期穆旦的诗在思想与诗艺上走向其整个创作生涯的最顶峰。
(二)其次是带来了语言的变革,激活了我们自身的母语
在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西方话语资源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五四”白话文运动、“诗界革命”之后西方诗歌(文学)经由翻译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里,通过大量的译介与阅读,以胡适为首一批新青年们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诗。我们的现代诗人开始变革我们习以为常的母语,现代汉语应运而生,与古文言之间形成了一种断裂,进入到与作为“翻译体”的西方语言相接的轨道。现代汉语开始背离传统文言,在以西方语言为参照系统下开始独立发展,创建属于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中国新诗(现代汉诗)正是在这种语言变革的环境下,开始其对古典诗歌(包括格律、形式、主题等方面)的反叛与背离,并在对西方诗歌的汲取与吸收中不断地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正如诗人陈东东所言:“译述使现代汉语成为一种自觉、主动、开放和不断扩展着疆域的语言,它要说出的、或意欲说出的,是所谓‘世界之中国’……当一个诗人以作为语言的现代汉语获取所谓‘西方诗歌的语言资源’的时候,他是在把现代汉语的这种能力运用于诗歌。”[8]西方诗歌经由译介进入中国,同时也将“现代性”带给了中国新诗。正是这种“翻译体”激活了我们母语之中新的生命力,为我们的母语创造了一种新生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陌生化”语言的力量。
胡适的第一首新诗正是对在西方文学译介中写下的。在这之后每一位优秀的20世纪中国诗人的语言里,我们都会读到西方某位大师的“影子”。李金发诗句中对奇诡与丑陋意象的运用来自波德莱尔;冯至诗句中的沉潜与形而上的哲思来自里尔克;穆旦诗句中悖论、张力来自奥登;海子诗歌中的神性光辉来自荷尔德林;多多诗歌中的沉默与停留来自保罗·策兰;王家新诗歌中对人类精神与文明的承担则来自他所钟爱的叶芝与希尼……正是在西方诗歌那种“异域的、奇特的”语言影响下,中国现代诗人开始关注诗歌技艺(语言与形式),开始“人为的”地变革与创造一种全新的诗歌语言与诗歌文本。现代汉诗逐步向“困难的、艰难化的、障碍重重的语言”迈进,诗歌的灵魂逐步向真正的诗歌精神敞开。从二三十年代的李金发、冯至到四十年代以穆旦为首的九叶派,到80年代的海子、多多,再到90年代提倡“个人写作”的诗人群体,“陌生化”的西方现代诗歌语言帮助20世纪中国诗人逐步突破统治了中国诗坛几千年的古诗传统,而转向一种更具现代意识,更能与时代发生摩擦、更能切入现实经验的诗歌语言。并且,在这种文明视野的影响下,我们的诗人重返我们母语深处,开掘母语之美与力量,以诗人多多的这首《依旧是》为例:
走在额头飘雪的夜里而依旧是
从一张白纸上走过而依旧是
走进那看不见的田野而依旧是
走在词间、麦田间,走在
减价的皮鞋间,走到词
望到家乡的时刻,而依旧是
站在麦田间整理西装,而依旧是……
在多多的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沉重的望乡者形象。多多在德语诗人策兰的诗歌那里“借”来了沉默与停留,但他写下的并不是像策兰那样一位经历过奥斯维辛之人的沉重,而是写下关于他自己与祖国、与母语之间密切的情感与联系。“走到词/望到家乡的时刻”,不正是一位诗人对于母语与文明永恒的眷恋与热爱吗?可以说,正是在翻译文学(外国文学)与西方资源(西方文明)的帮助下,中国新诗才得以走向诗与思的融合,中国新诗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第一次具备了复杂的、综合的诗歌技艺。
三、诗歌的流浪:在异域与归乡之间
梳理完20世纪翻译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新诗的影响,以及与二者之间的互动,我们再次回到最初的话题。那就是中国诗人、现代汉诗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这种逆转的“世界诗歌”潮流?当我们谈论“世界诗歌”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持怎样的一种态度去对待它?宇文所安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中指出北岛的诗歌是一种“国际诗歌”,他认为在北岛诗歌中早已无“中国”的在场。但正如笔者在上文提到的,美国诗人庞德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引入西方诗歌,但他和他同时代的诗人并没有将美国诗歌变成和中国古诗相同的形式,而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和文明的真实语境,创作出自成一格的意象派与象征主义诗歌。同样的,中国新诗(现代汉诗)对于西方诗歌,也只是借鉴了其语言资源、文化遗产与价值精神,它不会也不可能将整个西方诗歌的模式都移植过来,强行的生搬硬套对诗歌创作只能是灾难没有其它。事实上,完全脱离祖国与母语的世界诗歌是不存在的,每一位诗人身上都流淌着祖国/故乡的血液与气质,这是植根于写作者内在生命的,无论他在精神或者实际生活中走向多远的异国/他乡,只要他是一位具有人文情怀与独立品质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仍旧在精神上牵挂着祖国与人民的命运,他都必然会重返自身母语,回到词语的故乡,用真正的诗歌语言对他的祖国和人民说话。诗人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浮起的橡实》中写道:
对于我们这个职业的人士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之间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变成了命运——甚至在此之前,它已变成一种迷恋或一种责任。活的语言,就定义而言,具有离心倾向——以及推力;它要尝试去覆盖尽可能大的范围——以及尽可能大的虚无。[9]
布罗茨基作为一位“流亡诗人”,他的母语是俄语,他在精神上也不曾远离对俄国的关注。但他的流亡之所——美国,他在流亡之中习得的另一种语言——英语,却使他更好能理解自己的民族和语言。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翻译体”语言将我们的诗人推离母语,但却又使他们不断向母语退却。这听起来似乎是个悖论,实则不然。对于外语的习得和译介,使得异域文明与本土文明进入到一种“互文性”的语境,我们在另一种语言的魅力中开始思考其它文明/文化的方向与维度,进而重新“理解”和“塑造”我们的文明/文化。“换句话说,我们全都在为一部字典而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10]我们的语言真正要深入的,不应仅是母语/民族精神的腹地,它还需要有一种意识,即向人类命运、文明精神不断深入与敞开的承担精神。
因而,当我们谈起“世界诗歌”概念时,我们谈论的理应是一种更为广阔、理性、充满智慧的“世界性”视野与眼光。它要求我们在汲取与借鉴各民族、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发挥诗人的个人才能,从而创作出能抵达人类精神与灵魂深处的诗歌,这才是真正的诗歌与文学精神。试问现代汉语诗歌如果不用承载着个性化精神与独立品格的语言来表达我们所处时代的人类的命运、价值、精神、立场,难道还要回到50到70年代那种乏味无趣、禁锢思想的革命话语里去吗?还是要回到农耕时代所用的文言传统里去,用一种与时代不符的话语来面对我们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这难道不是对五四精神的背离?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吗?
今天,我们早已不是生活在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也不是生活在计划经济、文化黑暗的政治运动与文化革命的年代,而是在市场化与全球化北京下的复杂的综合的时代里。我们的诗歌不是不能借鉴传统,而是要有选择地、智慧地去利用我们的传统,同时也要用一种包容的、开阔的、世界性的眼光去接受和吸纳全世界民族优秀的诗歌传统,就像我们优秀的前辈诗人冯至、穆旦、海子等人所做的那样。这种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精神不也是一种我们理应承继的“传统”吗?相反,把自己、把整个民族诗歌限制在狭隘的、封闭的、局限的视野里,试图利用“文化恋母情结”将中国新诗(乃至中国文学)再次圈禁自己的小世界,恰恰体现出这种观点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世界性”和“民族性”并非不能兼容,那种将二者对立,以一方强烈反对另一方的观点只会陷入一种简单的、幼稚的、意识形态化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中。中国诗人、中国诗歌应该努力在诗歌内部创作规律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这平衡点上继续推陈出新。一位优秀中国诗人,必将在中国话语场域,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出发,经由中国走向世界,经由个人抵达全人类。他必须是在精神自治、灵魂自由的人,这种自治与自由帮助他选择站立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上,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个人、外语与母语、异域与本土之间穿梭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