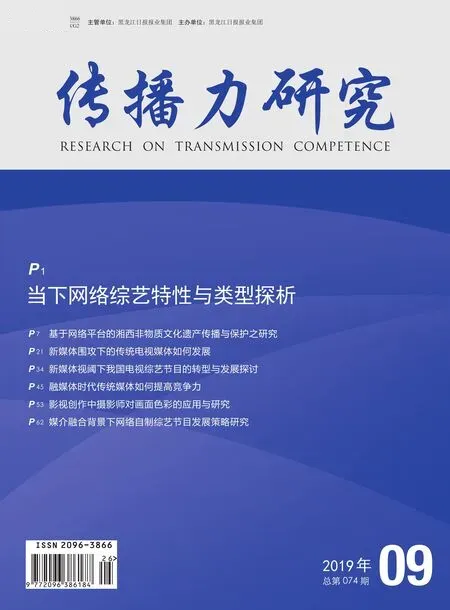浅析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艺术
李铁 沈阳工学院
一、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之路
1957年4月4日,阿基·考里斯马基出生在芬兰的奥里马蒂拉。日后,世界也是通过他,才认识到芬兰并不是只有重金属摇滚乐,还有电影。
作为一个年轻人,阿基·考里斯马基带着民族基因的叛逆和对重金属摇滚乐的痴迷,踏入了电影行当。1981年,阿基·考里斯马基作为导演和制片人,拍出了他的第一部摇滚乐队记录长片——《塞马湖现象》。1983年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长篇小说《罪与罚》是阿基·考里斯马基传统意义上的处女座。从他所选的题材来看,他专注表达出的是处于社会底层人民,这个标签贯穿了他的整个电影人生。
1996-2006年,阿基·考里斯马基创作了芬兰三部曲——《浮云世事》、《没有过去的男人》、《薄暮之光》,这三部曲之后,他跳出了芬兰,将镜头对准了世界性的问题——难民。此时55岁的他没了年少的傲气,更加柔和的他拍出的电影,其中的温暖是可以看到的。
从最初的不为人知到后来的声名鹊起,他在不断探索着进行创新,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电影风格。
二、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美学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作品被誉为“诗意现实主义”,但这个词并不能很好的表达出他的全部气质。他的作品只是在视觉感受和影像风格上看似体现出了“诗意”,其实是明显的超脱了精神,将矛头直指现实本身。
如果我们可以把他的影像内容细细分析,不难发现他对社会的思考并不是简单的将社会现状复制粘贴到镜头下,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转换成一种极具辨识度的视觉表意系统。这种独特的风格使得人们在影院观赏他的作品时,都会有深深的共鸣。
阿基·考里斯马基在电影拍摄中继承了罗伯特·布莱松前辈的风格,古典美学的构图模式。而他在数字摄影机出现后还沿用35mm的胶片进行拍摄,这样更贴近人眼的观察视觉。
考里斯马基在电影的空间运用和色彩构图上沿袭了美国近现代画家爱德华·霍普的风格。比如《浮云世事》中的爱娜和霍普《女士之桌》的女侍都一样的在餐厅中卑微的忙碌着;并且,考里斯马基和霍普对光线都有一种近似偏执的控制,正是这种控制,使得整个电影画面异常突出层次感。
在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对于道具的选用也意味深长。他的死亡是极简的,用一把直击死亡的枪,就表现了所有;他的自由和逃离,是历经磨难的主人公坐船离开;他电影中失意者的激进,是重金属摇滚。这种有着具体表义内容的物件,组成了他的电影美学中独特的部分。
三、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悲惨世界”
(一)身份问题的探究
考里斯马基丰富的社会阅历来源于他年轻时做邮差、力工、洗碗工的经历,这也让他的电影不会有那种对知识分子的谄媚,他的镜头永远关注的是底层的人民,用精简的镜头描述人民的生活。
他的电影主人公,永远都是无产阶级。《天堂孤影》的超市收银员和环卫工;《升空号》中的下岗矿工;《波西米亚生活》中落魄孤单的画家;《薄暮之光》里面的小保安……永远都是处于底层的小人物。
由于自身是一个中产阶级失意者,所以他的电影选材十分贴近现实主义,他将镜头对准的是人物的内在情感,他用克制的画面让电影的政治内容一直在精准的范围内。
在《没有过去的男人》中,M这个男人是一个闯入者,他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愿了解的世界,M在新世界的遭遇都是非常规的。但是影片最后M回到我们熟知的世界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最熟悉的世界,是最荒谬的世界。M的那个新世界是考里斯马基的“理想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看到了超脱经济和经济的人性的善良。但是令人感到无奈的是,这不过是一部电影。
(二)社会的疏远和个体的孤独
在他的镜头下,每一个静寂的街道,幽暗的灯光,都勾画出了主人公个体疏离外部的社会,靠近孤独的内心。那些无奈而又苦涩的细节,给观众带来的哭笑不得的幽默感,都是讽刺着商业主流电影缺少的耐心。
考里斯马基对极简主义电影美学的挖掘在电影技巧和电影话题两者之间做出了一个精湛的平衡。让每一个发生在当代的故事都不会具有时尚话题性,让观影者对故事发生的年代产生怀疑,产生陌生感,这种“怀疑的创造”,正是考里斯马基的惯用手法,以此来表达现代社会。
四、结语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会给人营造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但是他鲜明的主题又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你这不过是一次虚拟的体验,这只是对残酷的现实生活的凝缩。在他的电影中,每一个镜头,每一帧画面都渗透这强烈的时代精神,超脱个人经验的情感,使他完成了对人类命运和时代性的共性的书写。放下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傲,去品味,去感受他的作品,发现自己的渺小。这样看来,结局是好是坏也并不是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