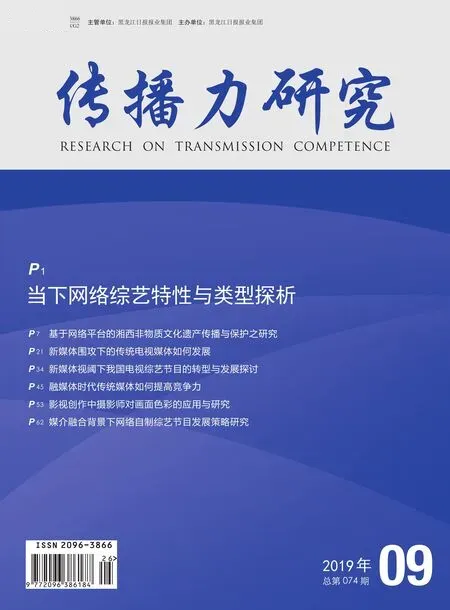魅夜:西安城市“灯光秀”的媒介文化观照
闫斌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9年春节,“西安年·最中国”成为全国最火的节庆灯光文化IP,此后西安市通过实施亮化、美化城市工程,将景点运用光学设计重新包装向外推介,“灯光秀”一跃成为西安文化事业和旅游事业的新增长极。
“灯光秀”,并没有严格定义,在此我们界定为:以光线为主题,以灯光、投影、音响、电子设备等联动变化为表现形式的光环境设计表演。随着灯光科技和演艺事业迅速发展,夜幕中的“光”已经成为一种深刻形塑大众文化环境的媒介。“灯光秀”作为光的聚合性展示,亦衍生出了一套自洽的拟态环境,它丰富了大众的审美体验、打造了城市文化符号,对城市人群和城市本身都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西安“灯光秀”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光文化样本,对其进行媒介文化透视有利于理解当下的城市新图景。
一、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
西安将城市光景观打造成了城市资源开发新路径,“灯光秀”与大遗址、古建筑、地域历史相结合,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光媒的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生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延伸与拓展。
“大遗址,用于专指中国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考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1]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存在众多大遗址,而灯光秀对历史文化资源主要转化方式也是对大遗址“文化空间”的美化及再推广。大唐芙蓉园就是我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公园,它打造出帝王、年俗、陕派、非遗、童趣等百组中国传统文化灯组,大量引用集声、光、电、立体互动为一体的高科技灯组,多维度还原了唐代上元花灯节的盛世景象和盛唐不夜天的历史图景,将已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和文化实力。
“古建筑”与灯光结合,可以形成“媒体建筑”。古建筑通过灯光进行再创造和再艺术化,形成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视觉形式”,这样的“媒体建筑”积极行使着历史育化和文化推广的使命。“唐都上元不夜城”城墙灯会中,城墙灯光秀就集合了传统节庆元素、现代灯光元素和历史人文元素,文化在建筑和人群之间流动,历史认同在其间产生,这种根文化的情感共鸣就是历史文化资源在个人心中的转化。
灯光科技与“地域历史”的耦合塑造着城市的文化个性。一些历史事件经千百年传承凝缩成为西安的特色地域文化,而灯光则成为其推广者和助力器。西安华清宫灯会就包含众多地域历史:“梨园”展区以发迹于大明宫的“梨园文化”为主题,以唐代音乐文化、舞蹈、乐器灯组向游客展示北方戏曲艺术的魅力;“西安事变”展区以著名历史桥段为核心开展灯光投影秀、光雕来缅怀先烈,向游客发扬革命先行者的牺牲精神和爱国情怀。灯光秀作为地域历史资源与照明科技紧密结合的产物,无疑让西安的历史文化符号再一次焕发生机。
灯光与大遗址的融合产生了城市标志性文化空间,古建筑嵌入灯光元素成为传递历史情愫的“媒体建筑”,地域历史与灯光的耦合也造就了身份统一体的共同想象。最终,一座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源在灯光萦绕的魅夜之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升华。
二、光与影下古城形象的重构
作为城市“符号表征系统”,城市形象对内是居民价值认同的依照,对外是彰显城市特色和吸引投资经商的无形资产。“光”已经深入参与到西安城市形象的构建中,曾经的“古城西安”形象逐渐重构为“灯彩西安”、“文化西安”和“年味西安”。
“夜晚模式”的城市中,灯光是人群对一个城市最直观的视觉印象,大规模、多维度的灯光秀甚至能对城市视觉形象造成颠覆性影响。从城市色彩设计看,西安利用灯光对植被、公路、桥梁进行色彩设计,屋顶琉璃瓦与冷色射光、建筑墙壁与琥珀色光、基座与白色泛光的对应关系,展现出建筑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感以及历史感。“灯彩西安”实质上也已经成为内化于人们心中的城市视觉形象。
“文化西安”指城市文化形象上的革新。城市文化不仅体现在城市景观、建筑、遗址,还内嵌于民俗、传说、轶事乃至集体记忆之中。蓝田迎春灯会以“灯光+民俗文化”为模式,将社火、锣鼓、秦腔等民间艺术与灯会结合,突出了蓝田地域文化的风俗人情。“灯光+民俗”让西安的文化形象更迭出了新意,此些“焕发新枝”的传统文化共同建构新西安的文化形象。
“年味西安”指西安在城市品牌形象上的延伸。西安春节灯光秀贯穿“西安年·最中国”主题,己亥年春节期间来西安的游客,可以在灯光节庆中找到阔别已久的年味,在新春灯光嘉年华活动中感受真正的中国年。从新春灯光展到民俗大展演,从乐舞迎宾礼到梦幻灯光,“西安年·最中国”将华人对新年的精神寄托与城市连接起来,打响世界性“西安中国年”的城市品牌形象。
西安的城市视觉形象、城市文化形象、城市品牌形象都被“光媒”深入肌理的改造,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国际范、科技风、地方味的西安城市新形象。
三、以光为媒引发“公共领域”
学术界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成果几乎都以日间环境作为默认条件,关于城市空间夜晚模式的研究还停在笼统的认知层面。中央美术学院的何巍认为“这归结为学者的研究时期问题,当时夜间行为活动较薄弱,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集中在白天时段导致其夜间形态和场所特征也以再现日间状态为主。”[2]随着城市照明的飞速发展,这才形成具有独立特征的夜间公共空间模式,而城市灯光秀更强化了这种公共性。
城市灯光秀作为“媒介事件”引发了城市的公共聚集行为。一方面,西安灯光秀因为政府主导、主流媒体加持、自媒体曝光成为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媒介事件,这为之后的公共聚集行为打下坚实的受众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的短暂性和地理的群聚性特征,城市灯光秀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事件性”特征的媒介活动,刺激大量的、出于各种目的公众参与的同时,顺其自然产生了城市公共领域。
城市灯光秀作为“信息媒介”促进了公共领域的产生。光作为一种媒介将信息在人与人、人与物理空间、人与电子媒介之间传递,为人和虚拟空间的沟通发挥了桥梁作用。灯光秀中的“钢琴路”,人在钢琴键上行走时会触发相应键位灯光亮起。当人们实现从观察者到参与者身份转变时,不仅完成了人与灯光空间的关联,也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灯光成为促成各方交流、讨论、扩散、呈现的必要前提。人类社会围绕灯光秀形成一种包含物理空间中人与物交流、虚拟空间中人与人交流的重叠公共领域。
城市灯光秀同时作为“民主媒介”引发公共领域。城市灯光秀是“公共艺术”的一种,而“公共艺术本质上不是服务于少数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炫耀,而是民意、民情和民主的文化体现。”[3]当民主性贯穿于城市灯光的设计、实践和传播的全过程时,常常引发各个社群线上、线下的“公共讨论”,其中具有一致性的内容形成“公共意见”,最后形成或虚拟或存在的“公共领域”。
四、结语
一种媒介形式的兴盛一定伴随着它对周围环境的“入侵”,这种“入侵”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兴起,灯光对城市公共空间“入侵”也产生了“灯光文化”。随着城市灯光秀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形式不断完善,“灯光”开始深刻形塑大众文化环境,对城市生活、城市人群乃至城市自身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和精神改变。这种情况下,从泛媒介视角进行灯光的媒介文化反思似乎更显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