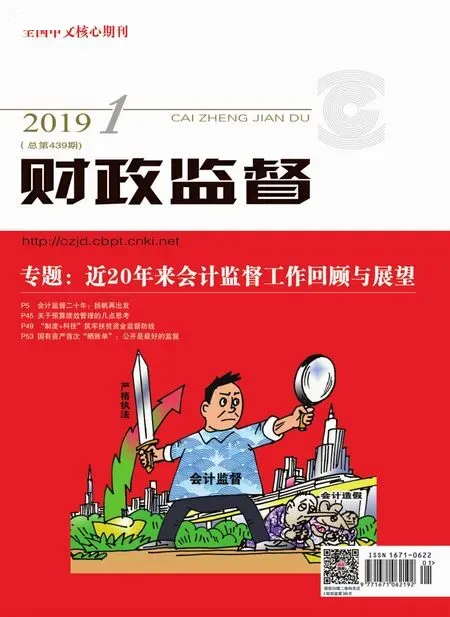浅论财政史学研究的学风、方法及其他
●付志宇
一、评与论
(一)批评的信赖
对于近年来财政史学研究成果的评价,笔者相信外间欣赏甚至于恭维的话都不会少,也相信这些研究成果不会因批评的文章而减色,所以批评的话还是由朋友来讲的好。韩愈说过“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实者,不信也”①,朋友有不同观点而不告以实话,不是伪敬的乡愿,就是庸弱的孱头。如果朋友都默不作声,或张口便称是,学术就没法进步了。接受批评的朋友,也要认真思考各种好听不好听、直接的隐晦的批评,就像孔子说的“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②。
首先,笔者对以数学统计方法为基础的计量史学甚是欣赏。这是近年来财政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流派,是财政史学的“乾嘉学派”,也是对汤象龙、梁方仲等前辈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如清宫档钞、海关收入、外债借款、预算表格等各类统计数据,比起张口就说的定性分析,有更为扎实的数字基础和严密的推算过程,是进行后续研究的质量检验与技术监督。对此等“笨功夫”笔者是积极拥护的,相信其他学者也会有同感。
其次,笔者对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的社会史学诚为感佩。这是从微观角度对财政史的扎实深入开垦,费孝通、张仲礼等前辈做了很好的示范。历朝货币、民间契约、发票税单、印花盐引等实物都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在解释财税制度的实施效果方面能够起到对官修史料的补充作用。笔者对这种走出书斋深入民间的有心人非常钦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吸收采用其成果。
再次,笔者对以采访历史人物为代表的口述史学深表欢迎。这是近代史研究领域新兴的“抢救性”工作,以唐德刚的民国历史人物回忆采访最为典型。要研究新中国财政史上的重大改革如两步“利改税”、国有资本预算改革、分税制改革等历史事件的决策过程,当事人的回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档案的完整性与时效性缺陷。这方面新近出版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广泛关注,笔者认为也确有加大力度的必要。
最后,笔者对以政治学、伦理学为视角的交叉研究相当赞赏。这是运用它山之石跨学科分析财政历史演变规律的跨界研究,韦森、李炜光等学者对此类方法有熟练的运用,其成果对近代财政制度的移植性与公共性具有相当的论证力。运用别的学科的手术刀来解剖财政史可以看出自家的不足,笔者对此也深表理解之同情。
不过,笔者还希望用各种新方法来研究财政史学的朋友要提防流入“独断”的心理,特别是为了要自立门户易产生“标新”的倾向。新颖的眼光讲求独到的意趣,它所自成的门户便不易敞开,对其他学科便难免少了虚心向学的诚恳。财政制度的发展历史主要还是财政活动的自身规律在发生作用,依笔者看来新的财政史学研究成果中有若干处恐怕是有独断之嫌的。章实斋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③,可知独断是与考索互为依托的,而不是以“独断之学”自封以阻断考索交流之路。
就治学论,“独断之学”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一个表面相当完整,内部结构也极精巧,却是运用预定的方法进行演绎的结果,与能够涵盖财政史实的通体的解释或洞彻的认识不相干,就容易陷入“先见不明”的泥沼。李元度说:“世之号称儒者,率是己非人。彼其所谓是者,果是而无一非耶?所谓非者,果非而无一是耶?抑犹有几微未尽协者耶?”每一个学科,每一家门派,每一种路数都各有其长短,都各有其适用范围,谁也不可能做到“尽协”。
在一般不察的读者看来,一家之言必须自圆其说,否则便不成其为一家之言,但在通人面前则不免会用挑剔的眼光找出鸡蛋里会长成鸡骨头的元素来。当然学者总希望能自成一家,自成一家比人云亦云的笔记家和东拼西凑的文抄公要高出不知多少,但是结果则不免把通达的大门给关上了。因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很多的,并不只限于哪一条。
陆务观谈及读书的体会时说:“一卷之书,初视之若甚约也,后先相参,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为发明,其所关涉,已不胜其众也。”④专精固然是功夫,却也不要排斥博杂。天底下的道理本就相通,经史子集乃是后人强分高下,子不如经,集不如子,结果就成了黄宗羲说的“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⑤。前两年笔者在峨眉山举办中国财税史学术研讨会时,有学者专门建议以后最好能把各门各派都请来,不要只在经济学院系里面转圈圈。如果能够打破尊卑拆除藩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⑥,则更近于道了。
(二)辩论的合理
批评是单方面的,如果被批判者有不同意见,就该开展辩论。因为只有辩论才能找到正确或合理的解释,“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明同异之处”⑦。凡不赞同批评意见而又默无一言者,不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之人,就是伪金怕火心虚胆怯之人。这两种人都是妨碍学术进步的退化主义者。只要不是漫无对象地争论,辩论双方总会有所提高。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⑧,辩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其求取真理。真金经过烈火淬炼,不但无损,转而益坚。历史上学术昌明之期正是批评辩难盛行的周秦魏晋,而定于一尊万马齐喑之时则思想僵化文化禁锢,明清文字狱便是铁证。其实辩论真正的信心来源于对学术的尊崇和对规律的敬畏,即使败下阵来也不可耻。鹅湖之会时朱元晦何曾因陆九渊兄弟的辩诘而丢失信心?
梁任公说过:“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接下来,他对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也进行了批评:“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师弟之间都能如此,何况是学术同道?以笔者自身的经历为证,在十年前昆明的经济史年会上,针对笔者提交的质疑“黄宗羲定律”的论文,各位前辈先进均从学术立场出发进行辩难,参与人数之众,论据立意之广,大有稷下学宫之盛。而笔者从中收获之大,也远胜于多年来自己格竹子的一得之愚。
对于批评的反应,除了作木石状,还有一种极为有害的习气,即是魏文帝在《典论》里所说的文人相轻。学者因嫉妒而乱发议论,实是对学术的摧残。辩论的发心动念是就学术论学术,而议论的背后是妄自尊大,或是衔恨攻击,无一而可。《晋书》上讲孙绰与习凿齿互骂对方是瓦砾或糠秕,试问哪个是好?《清稗类钞》则有汪中鄙薄方苞袁枚的记载。瞧不起同行,自己又有何所得?因此,倡导学术争鸣,但切不可堕入随意臧否的陋习。
辩论须有前提,即是孔夫子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⑨的“攻”。先认真学习研究对方的观点与论据,批评起来才可靠,辩论起来也才有交锋。魏源批评纪昀的《宋名臣言行录》因个人好恶以私灭公,的确是下了扎实的功夫,后人读起来才会信服。在辩论之时,论据固然可以另寻,但最好能出自对方的观点与论据,两者的效果还是有些不同的。前者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批评儒家守制三年非古礼时以论孟为证,但却不能反证其非出自孔孟之口。而后者如嵇康的《管蔡论》对周公诛管蔡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则明确指出《史记》的自相矛盾之处。笔者曾经认为某位学者用新兴的财政政治学方法解释财政史值得商榷,便请作者将其论著赐赠,深入学习后列明其观点难以圆说之处,条缕出反对意见,蒙对方重视在会上一一作答,再在会后继续交流,双方对此均能有所精进。
辩论时应尽量破除身份,打破禁忌。当今学术界多以身份地位或门户亲疏断定学者观点有无价值,实在是犯了势利之病。慎到以尧的地位变化为例说明“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⑩,可知贤与不肖与地位高低本无对应关系。方苞质问万斯同参修《明史》时列传的人选名实不符,万解释是受乡土观念所困。声名之取得原有诸多因素,未尽合理的在在皆是。受声名影响辩论时故多有禁忌,不敢怀疑批评。做学问之人如一味回避,哪里能发现问题?蔡尚思对比金元二史,指出前者对位尊者的秽乱存而不削,后者则一切隐而不录,史德高下自见。孔子所以赞赏漆雕开“吾斯之未能信”⑪,乃在其求真知而非轻信盲从。
二、派与汇
对财政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让笔者想起一篇不太相干的文章来,潘光旦为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作的序文《派与汇》,此处不妨就借用“派”与“汇”这两个词来形容财政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分与合。“派”指财政史学研究方法的分途,可以是经济学,可以是史学,还可以是统计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等。吴承明在谈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时讲的“史无定法”就是指的分派。“汇”是指财政史实作为相关学科方法汇聚的终点。不管起点是用哪种方法,最后还要“江汉朝宗于海”⑫,回到财政史实本身来。
潘光旦说:“研究必须有囫囵的对象,囫囵的人,以至于人所处的某一时空段落里的囫囵的情境。”财政史学研究的对象本应是囫囵的史实、囫囵的情景,而非被经济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切割了的人物与事件。学科本是人为的疆界,传统学术中的义理、辞章、考据诸学,被拆开进入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大体成为哲学、文学、史学。孔子一定不会同意把《易经》认为是哲学,《诗经》看成文学,《尚书》当做史学的。接触一个学科之初难免要“正经界”⑬,才能掌握本学科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到了研究阶段,则要“开阡陌”⑭,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文心雕龙》所谓的“百家腾越,终入环内”⑮,才更为接近学术规律本身。
歌德说过一句很有兴味的话:“人类靠着聪明分割出很多的边界,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这正是“由派分而求汇合”的治学之路。财政史学不同的派分各有特色,交汇处在何处?笔者认为是在作为研究对象的财政史实身上。因为对财政史实——特别是财政制度的理解,不该被学科、派系、家数所限,单从经济学或史学的角度来理解财政史实,理解经济制度的因果与影响,肯定是片面的、破碎的。王国维就讲过“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可见分析只是过程,会通才是终点。
派与汇,可以分两个层面的问题来看:一是学科层面的派分,能否突破学科边界;二是作为个人的学术体验,能否达到理想的治学境界。
(一)学科的派分
从边界的突破讲,能互相串门、彼此借力,当然是好事。怕就怕完全羡慕和服膺对方的游戏规则,因“学步”而丢掉了自家的本领。写出来的文章,经济不像经济、历史不像历史,让人看不清楚财政史实背后的意旨。这主要还是由援史入经(经济学)带来的弊病。有时候作适当的区隔未必是坏事。财政史与政治史的不同就在于自身的财政规律,如果单纯性地记述史实而不运用财政理论加以分析就反映不出财政史学的特点了。梁任公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诚爱桃李也,唯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桃李与杉松自有其长短特性,不必因欣羡其秾华或挺秀而随意移植。
财政史学研究向计量史学靠拢的态势,近些年未见减缓,反而渐趋显著。甚至有的干脆脱史入经,直接转入计量经济学,似乎大有脱亚入欧的解放感。为什么财政史学研究会出现逃兵,或潜在的逃兵?这种娜拉出走式的冲动,首先与财政史学自身的学科焦虑有关,也反映出研究者对财政史实的制度变迁、演化性,甚至对“史”的不信任。上个世纪末学界呼唤回到制度经济学,现在说“坚守”经济制度的历史性,都多少带有某种悲情色彩,带有青山遮不住的失落。财政史学的工具转向,折射出研究者对自己的本业、对自家研究方法的不满甚或厌倦。可是,脱史入经是否就意味着实现融入主流呢?可悲的是主流的财政学界并不会接纳这些逃兵,仍然认为财政史学最后应该立足在史学上,就像乾隆对钱谦益的《初学集》题诗“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⑯,并令将其编入《贰臣传》。
除了“学步”与“出逃”两种形式之外,或许还有一种“跨界”的姿态,一只脚迈出去了,还有一只脚留在门内。在主流经济学面前不甘心俯首称臣,在史学园地里又不肯下功夫耕耘。这种“跨界”的心态近年来在财政思想史领域表现得有些明显。徘徊于经史之间,在财政学界表示自己甘愿坐历史研究的冷板凳,在史学的圈子里又以财政学理论自是,就像时下最吃香的学者型官员,时常冒两句流行的用语,又引用几处旧籍的典故。对此李贽早已有言及:“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成言,规迹往事。”殊不知此种姿态可行之一时,难行于一世,到最后二家不愿。“天下果有两头马乎?否也。”⑰
与其做逃兵一走了之,或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不如学江南园林借景造景。不用推倒财政史学研究的学科壁垒,只需在院墙上凿几个洞开几扇窗,就能将邻家的景致巧妙地“借”到自家的院落里来,“造”成自家的天地。借景造景未必就能做到援史入经,或脱史入经,但不妨由史“窥”经,或由经“探”史,墙外开花墙内香,风景自然园内园外都有了,同时带有财政学和史学的意味了。可是真的能从别的学科直接“借”到现成的研究结论吗?以个人的经验为例,笔者在研究财政史时,同时关注财政学和史学的相关成果,却发现很难从中找到现成的景观,可以直接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来。财政学研究描绘的图景与史学研究的取景框往往是错位或不相称的,比如同样是对“两税法”的财政体制研究,财政学者如孙翊刚看重的是预算职能变化,史学界如李锦绣则强调职官的设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回到最原始的史料,耕耘自己的园地,不用去羡慕别人家的风景比自家色彩鲜艳或是角度特别。
(二)个人的体验
从个人的角度看,财政史学的研究,除了学科的“派”与“汇”,还有操作层面的“法”的问题。钱基博对此作过形象的比喻:“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采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并援引孟子论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⑱加以说明。不管是文字、符号、图像还是公式,任何学科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传达思想,因此“文”的重要性就不会比“事”与“义”差。从事财政史教学的人都有过相似的经验,今天的财政史学著作或教材,大多佶屈聱牙,令人生厌。财政史学比起财政学来如果说有什么优势,或许就在可以从“文”上下功夫,这也是传统史家的长项。其实历史上的很多事件如果写好了都能吸引人,哪怕是不懂财政为何物的人,就像乡间不识字的人也喜欢听戏听说书。以历史上的财政改革为例,汉武帝信任卜式打击商人,唐德宗对杨炎开始喜欢后来讨厌,宋神宗把司马光打发回家唯王安石之意是从,都是很好的素材。笔者在台湾看见过一本署名陈雨露的金融史很畅销,赖建诚的《经济史的趣味》可读性也很强,其实学者完全可以给人讲故事,做一些普及财政史学常识的工作。这正是孔夫子说的“诗教”,“兴观群怨”⑲中“群”的道理。
就“文”和“义”两者的关系,吕思勉提出要重视“文”才能正确理解“义”:“治史学的人,虽不是要做文学家,然对于文学,亦不可不有相当的了解。一是训诂……各时代有各时代的语言,又有其时的专门名词……二是文法,亦是如此……三是普通的文学程度,尤其要紧。必能达到普通的程度,然后读书能够确实了解,不至于隔膜、误会。”这几点心得,笔者在学习周朝的财政制度时也能有所体会。如当时的彻法,孟子说的是“彻者,彻也”⑳,如果不懂得训诂与文法,光靠这四个字是讲不通的。王安石说变法是行周官之制,实际上在浇他自己的块垒,如不能看懂《周礼》,就上当了。刘知几在《史通》中认为作史有三难:才、学、识。后来章学诚又增加了一个“德”,当然这是更高的境界。比如对王莽改制,没有较高的史德是不容易正确认识的,胡寄窗和赵靖的判断就很不一样。又如对王安石变法,列宁和梁启超都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也不一定有道理。当然,笔者在这里不打算打笔墨官司,只想说说如何去表达出“义”。前面提到孟子用“丘窃取之”来评价孔子作《春秋》,可见“义”的表达本是个人主观的判断。现在的财政史学著作大多“述而不论”,不知是不能,抑或是不愿?
《增广贤文》上说“财是怨府”,财政史学的文章确实不好写,一不小心就会招来骂声。怎样才能把专业的财政史学让读者既能看懂还愿意接受作者的意见?笔者想借用一下杜预的春秋“三体五例”㉑。简明一点,“三体”就是基本的财政制度要 “发凡正例”,遵循普遍的评价标准;重大的财政变革要“新意变例”,指出其改革的创新价值;特殊的财政事件要“归趣非例”,找到差异存在的原因与影响。“五例”主要指在对具体的事件评价时要微言大义,尤其涉及价值判断时最好能隐恶扬善。如研究“两税法”涉及杨炎和刘晏的私人恩怨时,对历史人物的私德可以略加回避,或者谈及摊丁入亩时,对康熙和雍正的评价应尽量宽容大度。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就不多讨论了。
技法技法,除了基本的“法”,还有“技”的方面。屠隆曾讲到“人之才性,有深沉厚重,有英敏捷迅”㉒,说明先天禀赋还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对于写文章,夏济安有过一个很有趣的比较:“中国人的批评文章是写给利根人读的,一点即悟,毋庸辞费。西洋人的批评文章是写给钝根人读的,所以一定要把道理说个明白。”比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写一条鞭法就像是在写学术论文,《万历十五年》却是在讲张居正和明神宗的故事。由此看来,做学问是需要点灵气的,写文章也讲究个人的颖悟,否则就千人一面,泯然众人了。
三、知与行
财政史学不可避免会遇到财政思想与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问题,这在近代财政史上表现尤为突出。笔者对此差异感受颇深,十年前笔者请叶世昌先生为拙著作序,书中的某些观点叶先生不能首肯,多次信牍往还商榷。当笔者对近代税收思想与制度之间的落差表示空泛之同情时,叶先生劝导光用思想史的抽象概括说明不了问题,一定要兼采经济史的制度分析方法,否则就成了一味地“致广大”而不能“尽精微”。
诚如朱熹所说:“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㉓历史的通常情况是先有思想后成制度,思想指导制度的建设。但是,世间事物并非总是如此整齐划一,知易行难也是历史的常态。王夫之就说过“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也就是说制度可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的思想,但思想并不一定就必然能转化为制度。因此,民国学者曹国卿专门强调“不能实行之规定,在税法中当以不规定为是”。叶老师在拙著的序里这样写道:“任何一种政策,宣布了不等于就不折不扣地实行了,实行的程度与吏治有关。”这正是《尚书》上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㉔之理。
木心曾作过这样形象的比喻:“现实像墨水,我蘸一蘸,写‘永久意义’。但不能没有墨水,不能不碰现实。”笔者年少时不关心财政制度的情况,只对思想史感兴趣,抽象,空灵,很长时间一直如此。但这样是不好的,不行的。一定要有土壤,哪怕是肮脏的土壤,不然生命就没有了,活性就没有了。思想是一个杠杆,需要一个支点。思想的支点就是制度,只有以制度为支点,思想才能翘起来。对于财政史学的研究方法而言,财政思想的“尊德性”要靠财政制度的“道问学”才能翘起来。
从财政史的实践来看,成功的做法是能把自己的思想变成制度,桑弘羊如此,张居正也是如此。思想是支票,制度是现钞。成功的思想观点,说兑换就兑换,比很多经济学家开的空头支票不知好上多少。因此,在研究财政史,尤其是近代财政史的时候,切莫轻信了简单的文本规定。另一位民国学者朱偰曾说“专以官厅法令及经济会议、财政会议议决案为凭,与真相相去甚远”,可见与制度规定不同,财政实践别有怀抱。在考察和判断西方财税制度中国化的实现程度时,要认识到,“即使引进的先进技术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无视文化价值和社会习俗的差异,为使用新技术而引进的外国制度就无法服务于预想的目标,而只能造成社会混乱。”《左传》上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㉕,财政思想先进不足为贵,如何适应中国的国情从而转化成可行的制度才是对思想的考验。
四、余论
鲁迅说过:“我是主张青年发表作品要 ‘胆大心细’的,因为心若不细,便容易走入草率的路。”笔者走过青年胆大而草率的弯路,回头看很多原来的东西都经不住推敲。现在马齿加长,却又转入心细胆小,因愧于少作不敢轻易为文,也是有问题的。因此笔者希望今天的青年朋友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回头来看,笔者学习成长的那个年代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总体上来说学风还是比较端正的。现在的青年朋友接受过更好的学术训练,很多人甚至有海外求学的经历,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既然选择了财政史学这个方向,就要多向前贤学习,这是道脉传承应有之义。“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㉖,笔者在财政史学习与研究的成长过程中有幸得到过许毅、孙文学、杨之刚、李炜光等前辈学者的指点与提携。笔者很能理解青年朋友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困惑,因此也更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学术先进们的指点与提携。
“万里丹山桐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㉗这是人生代谢的规律。相信青年朋友只要虚心向学,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近年来笔者也做了些财政史学方面的翻案文章㉘,有几点体会,贡献出来看看有没有道理:
第一是“高筑墙”。要多读书,坚壁才能清野,各种知识不留死角。尤其是多读无用之书,才能眼界开阔胸怀洒落。大的理论要把握住精神,像九方皋“意足不求颜色似”㉙;小的问题要抓住关节,学庖丁“目无全牛”㉚。读书时要有慧根,把前贤扫除干净,“不向如来行处行”㉛,才容得下自己;要有胆魄,对成说敢于质疑,“于无疑处生疑”㉜,才提得出问题。
第二是“广积粮”。要多积累,以诗证史也罢,多重证据也罢,只要与问题有关的材料,正面的、反面的、侧面的尽可能齐全。研究时要小心,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说与证据无关的话,“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用不着的证据要有去处,不要先组织观点再去寻证据。有两种不好的现象特别要指出来,一是剪裁证据,这是史学研究的忌讳;二是生造证据,主要存在于财政学研究中。
第三是“不称王”。要多问学,承认自己有学问的盲区,任何人的观点方法都可能对治学有帮助。不仅要向先生讨教,更要听取后生的意见。因为后生不会先入为主,不会敷衍塞责,思想活泼,观点新鲜,这正是后生可畏之处。“道在屎溺”㉝,村夫笨伯未尝没有学问,放下身段忘掉头衔,作短兵相接的平等交流,收获反而会大于正式场合的酬酢应对。■
注释:
①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
②孔丘,《论语·卫灵公》。
③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④陆游,《万卷楼记》。
⑤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⑥《金刚经·第六品正信希有分》。
⑦墨翟,《墨子·小取》。
⑧孟轲,《孟子·滕文公下》。
⑨孔丘,《论语·为政》。
⑩韩非,《韩非子·难势》。
⑪孔丘,《论语·公冶长》。
⑫《尚书·禹贡》。
⑬孟轲,《孟子·滕文公上》。
⑭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⑮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⑯爱新觉罗·弘历,《观钱谦益初学集因题句》。
⑰李贽,《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⑱孟轲,《孟子·离娄下》。
⑲孔丘,《论语·阳货》。
⑳孟轲,《孟子·滕文公上》。
㉑杜预,《春秋左传序》。
㉒陆云龙,《十六名家小品》。
㉓朱熹,《答吴晦叔》。
㉔《尚书·说命中》。
㉕左丘明,《左传·昭公十年》。
㉖郑燮,《新竹》。
㉗李商隐,《韩冬郎既席为诗相送因成二绝》。
㉘如关于“黄宗羲定律”的商榷文章,参见《亦论“黄宗羲定律”是否成立》(《现代财经》2011年第6期)、《从历史视角看当前企业税负》(《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第 4期)、《三论“黄宗羲定律”是否成立》(《财政监督》2017 年第3期)。
㉙陈与义,《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
㉚庄周,《庄子·养生主》。
㉛志公,《续指月录》。
㉜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
㉝庄周,《庄子·知北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