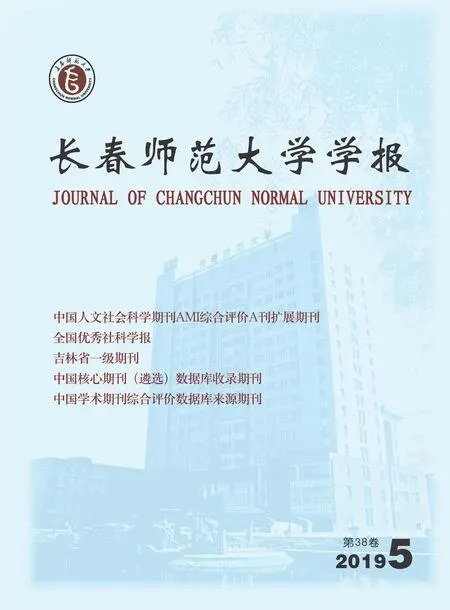论清初流人吴兆骞诗歌的狞厉之美
邓 锋,陶 娥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32)
吴兆骞(1631—1684),江苏省吴江县人,江南名士,其诗作“声情慷慨,格调悲凉,大有山河离别,风月关人之感”。[1]1658年,吴兆骞因受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南闱科场案牵连,被流放至宁古塔(位于今黑龙江省海林市)。
吴兆骞个人戏剧性的命运转折,不仅使他产生心灵上的剧烈激荡,也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念及诗文创作。他的诗文凸显了特殊的流人文化气质,反映了东北边塞雄浑、壮阔、粗粝、苦寒的自然景观,纤细入微地刻画了东北生活百态、流人不平遭际及不同心态,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即本文讨论之“狞厉”之美。
一、狞厉之美的艺术氛围营造
(一)用词色调的选择
吴兆骞诗中对冷寂色调情有独钟,如断云、残雪、苍苍、云阴不散、北风哀、断垣零落、凄凉古塞、白草寒、哑哑乌啼、边色夜荒荒、七月霜、甲冷、笳寒、寒原渺无极、哀笳、秋雪、急雪、霜凄、风急、边雪、硕风、河渚苍苍、寒溪、四野秋风、白月生寒等。
吴兆骞在诗歌创作中比较偏爱清、冷、寂、寒等色调,这既是东北苦寒之地给诗人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与心灵激荡,也是诗人心念故土、黯然惆怅的心有所系的外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诗人对北方的关河、黑土、边塞逐渐产生了深沉的感情,其诗作愈发显现出具有东北地域及民族特色的美学意味。
大凡选取清、冷、寂、寒等色调的诗作中,景物多如树、云、花、林、山、水、溪等自然之物,画面多呈静态,格局一般不会阔大,诗歌意境一般笼罩在宁静、静谧的氛围中,或表达出作者的感伤、怅惘之情。吴兆骞诗却是此类诗歌的异数。这不仅体现在物象的选取上,也体现在情感的表达和丰富上。
(二)物象的选择
吴兆骞选取的实物(景物)偏向于雄浑、壮阔、粗粝、苦寒,诸如:莽莽边沙、落日莽茫茫、万里川原、朔漠、大荒,等等,或如:“黄龙东望沙茫茫,黑林树色参天长”①;“灌木带天余百里,崩榛匝地自千年”;“惊沙莽莽飒风飚,冰河四月冻初消”;“月高亭障前烽出,雪照旌旗万马鸣”。具有浓郁的东北地域和民族特性的物象,在吴兆骞的诗中俯拾即是,呈现出莽莽黄沙、参天林树、万里平原、冰天雪地的壮阔而粗粝的东北风貌。
吴兆骞的诗作中密集地出现东北各地的城镇(名字),以及各地不同的风光、气候、民俗、民情等。追溯其诗作中东北不同地区的轨迹,可以还原吴兆骞的东北活动轨迹,了解他的生活历程和文化交游,也可以一窥其隐秘的内心精神世界。
各种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动物及物品在诗作中也频频出现,动物如鹰、雕、牛、羊、马、鹤、鹿、鱼等,物品如鹿裘、毡帐、毡墙、青羔裘、毳帐、羊裘等,使吴兆骞北迁后的诗风与前迥然有别。像“栖冰貂鼠惊频落,蛰树熊罴稳独悬”、“秋风穹帐松花戍,夜雪雕戈木业关”这样的诗作也只有在东北这样独特的地域下才能形成。
(三)情感的表现
吴兆骞北迁后的诗作由抑郁感伤转化为慷慨悲歌,由书写一已之沦落愁闷之情怀提升为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吴兆骞诗作狞厉之美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吴兆骞北迁之初,其身心难以适应东北异域生活,心绪低沉,诗作中多有怆然作歌、可怜沦落(俱冰天)、肠断、飘零、倦客之语,常抒发思乡之情、怀念亲人之慨:“我亦有家江山上,十年同恨塞垣深”;“十年关塞泪,难望意如何”;“悲歌不尽乡关思,泣向沙场倍黯然”。在思念远方的故乡和亲人的同时,他也自伤身世,抒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内心惆怅、焦灼与愤懑:“却怜负羽边庭客,重过禅扉意倍伤”;“文如刘峻终无命,愤到嵇康始悔才”。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吴兆骞并非一味地沉浸在个人感伤的心绪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东北这片黑土地的风俗、民情逐渐进入吴兆骞的创作视野,东北边疆的战事则激发了他的深沉的爱国情怀。
二、吴兆骞东北边疆诗狞厉之美的具体体现
吴兆骞流放东北宁古塔时,受到巴海等满族高级将领的赏识,给予足够的礼遇,并得以多次随军戍边与出征。吴兆骞从对东北边疆战事的接触中了解了东北边疆战况的紧张与严峻、底层士兵的艰苦与卓绝以及将士众志成城、戮力一心的勇气与信念,深刻触动了他的内心世界,也极大丰富和扩展了他的诗作创作题材。在其诗作中与东北边疆和战争有关之物象比比皆是,如鼓角(战鼓和号角)、烽楼、铁甲、冰卧、荒戍(荒废的营垒)等。诗作中也频繁出现和边疆战争有关的各种乐器,如画角(其声哀厉高亢,边塞军中多用)、羌笛、筚篥(即觱篥,其声悲戚)等。又因地处东北边陲,其诗作中亦不乏严风、严霜如刀、风劲、五更寒等等表示东北苦寒的词语。具体而言,吴兆骞东北边疆诗的狞厉之美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戍边普通戍人、兵士日常生活的着意描绘
如《送人之浑蠢》:“雪深车不度,风劲角初高。报尽平安火,谁怜吏士劳?”浑蠢,即现在的吉林省珲春市,距诗人居住地宁古塔(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大约四百多公里。其时,东北交通不便、天寒地冻,戍人要忍受“雪深”“风劲”之苦,长途跋涉近乎千里之地,只为“报尽平安火”。这是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东北边疆戍人形象描绘,简洁而有力地刻画出了一个驻守边关普通兵士的朴实与坚忍、毅力与执着。吴兆骞的多篇诗作都有对普通兵士的关注,如“十年谪戍头今白,犹着征衣更出边”《送人从军》;“碛断山回合,军孤战死生”(《送人从军》,和前首诗同名但不同作)。这些诗作表现出东北边疆普通兵士平日生活之艰苦以及与敌作战时视死如归的勇气和热血。
(二)对戍边将军、高级将领的有力刻画
吴兆骞深受宁古塔诸将军礼遇,也感佩众将军之领军风范,对将军们的言行、性格、治兵、练军等方面多有描绘,对众将领的奋勇杀敌行为、保家卫国情怀多有真心颂扬。如《送阿佐领奉使黑斤》称赞阿佐领:“持檄遥颁五国东,挥鞭直历千山外”;《木参领还自西域赋赠》:“千载西陲夸右臂,凿空谁识汉臣才?”如《送哈佐领之朝鲜》:“知君谈笑遐荒静,百战宁夸荀彘功”;《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安东都护按剑怒,麾兵直度龙庭前。诗作中巴海大将军,阿佐领、木参领、哈佐领诸将领,或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或浴血杀敌、身经百战,或性如烈火、不畏生死。此外,诗篇中随处可见其他的诸多将领事迹,如郎坦都统、安珠瑚副都统、米参领、唐副帅、萨布素副帅等。
(三)积极备战、浴血抗俄,将士同心之举
如《黑林》中“废营秋郁风云气,大碛宵闻剑戟声”;《秋日杂述》中的“落日旌旗人出戍,秋风笳鼓客登台。”“戍楼鞞鼓动严城,朔塞山川郁战争。”“铁马两甄横塞草,水犀三翼动江涛。”大战前夕,将军身先士卒,士兵厉兵秣马,军纪严明,军威势盛,整饬有度,士气如虹。诗歌题材触及军事备战,自古以来鲜有此气势磅礴。古代如辛弃疾、翁卷等诗,描述了危机前夕,统治阶层浑浑噩噩,只为满足一已之私,备战等同于搁置;现代如艾青诗,描述了日寇侵华,国民党军却醉生梦死,放弃备战。吴兆骞诗作力除清诗之言语空洞之弊(主要由于时代的缘故),一展清朝东北边疆部队的军威军貌,热情歌颂了将士不畏生死的英雄气概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热血之作。
正面直接描写清军部队出发抗战的诗作如《送阿佐领奉使黑斤》:“破羌流尽征人血,好进温貂报国恩”;《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乌孙种人侵盗边,临潢通夜惊烽烟。安东都护按剑怒,麾兵直度龙庭前。”他如“火照铁衣分万幕,霜寒金柝遍孤城。”吴兆骞诗作展现清朝军威,极大地鼓舞了士兵乃至民众的士气,彰显了爱国主义情怀,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
当然,吴兆骞诗作展现将士一心的方面有很多,对他们的日常起居、居住场所、生存环境、日常娱乐(比如狩猎、各种乐器演奏)等多有描绘。
三、吴兆骞诗作狞厉之美的美学价值
“狞厉的美”语出自李泽厚《美的历程》[2],原为评价青铜鼎器饰物美所用。本文借其词语,试图概括吴兆骞诗作的美学风格。吴兆骞和前朝文人以及同时代的南方士人的诗歌内容及艺术风貌迥然有别,即便其北迁前和北迁后的诗文也有天壤之别。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吴兆骞喜好用冷寂色调。喜好冷寂色调本不稀奇,前朝诗人用此法者也不鲜见,著名如李贺、王维、柳宗元等。其可称道者,在于以冷寂色调笼罩东北地域的雄浑、壮阔、粗粝、苦寒之实物,其感情由最初的一已之抑郁感伤之情转化、提升、升华至国家、民族的忧患之思与爱国之情。吴兆骞的诗作绘就了一幅广袤的独具东北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战争戍边、文化交流、地理气候等历史长卷图。需要注意的是,吴兆骞诗作风格并非一味地偏北方粗犷风格,其以南方士人特有的缜密心绪、绮丽文笔、精工之才,着意刻画北地之辽阔、粗粝与苦寒,最终交融南北艺术风貌之所长,并形成自己独有的狰狞之美的美学风格。这里的狞厉之美,指的就是阳刚之美、雄浑之美、崇高之美,也不乏原始拙朴之美。粗粝中孕育着淋漓生气,壮阔中生发出慷慨之情,慷慨悲歌中又蕴含细致温婉,淋漓生气中凸显其粗犷、威猛、豪迈之风。
所谓狞厉之美,也脱离不开作者的思想旨趣。吴兆骞北迁后早期诗歌风格可谓苦、寒、孤、绝,多沉浸于自己的感伤世界之中。但作者到底是南方有才华的士人,是别有情怀的知识分子。北方之壮阔景物、社会百态、严寒奇景、飞禽走兽、铁马冰河均是诗人从所未见之物。因此,诗人很可能会有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巨大冲击,由最初的失意沉沦转为意气振奋、斗志昂扬,以东北地域特色入诗,来表现自己命运蹭蹬之下的“不抛弃、不放弃”的“硬汉”精神。概而言之,吴兆骞狞厉之美的思想意蕴可包括悯人、爱国、知荣辱、重气节。哪怕是自己的人生横遭剧变,却终究能宠辱不惊,以戴罪之身,对东北普通民众和兵士的悲惨境遇寄予深深的同情与喟叹;哪怕是一介文弱书生,却也要厉兵秣马、仗剑而行,以文人身份参加戍边和征战。以莫须有之由见罪于朝廷,却心系家国、民众;以朝廷罪臣身份北迁,却绝不阿谀奉承。此所谓诗人特有之风骨。可以说,正是诗人、诗作呈现出来的风骨,才使得诗作形成狞厉之美的美学风格。
四、余论
当然,吴兆骞“狞厉”的美学风格并不能说完美。实际上,在他流放的二十余年里,他仍念念不忘自己之南归,对北迁事仍如鲠在喉、抑郁难解。其风格时常有反复,比如慷慨有限而以苍凉为主,悲壮中的“壮”少了不少,悲意加深而转化为幽怨。这既是时代对诗人的限制,也是传统文化对诗人的无形影响,更是自身性格难以完全通达所致。本文叙事至此,和前文旨意并不矛盾,因为诗人吴兆骞本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这并不损害一个真诚、鲜活的诗人形象。他抑郁感伤不止,也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他会自怜身世、自怨自艾,也会铁骨铮铮、侠肝义胆。他的作品中勾勒出的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文人形象,这也许就是作者诗集的真正价值所在。
[注 释]
①本文中的吴兆骞诗均选自吴兆骞、戴梓著《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耕烟草堂诗钞》,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